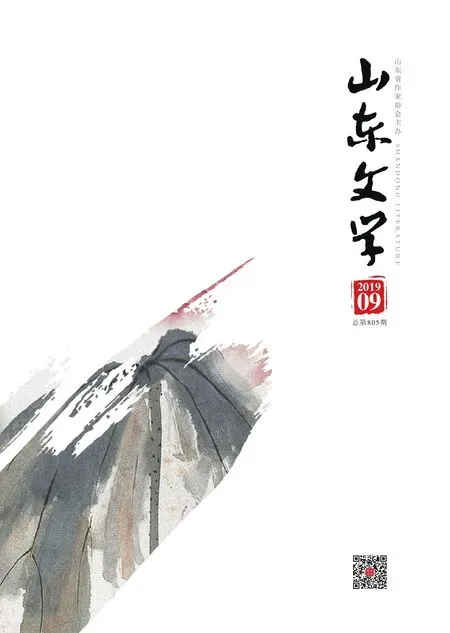泊在岁月深处的临清
2019-11-14李木生
李木生
王树理先生的《临清传》是一本特别耐读的城市传记。其历史的纵深感、城市生命的独特风貌、大运河带给这座城市的古韵今风,以及纯粹而又丰富的文学意蕴等等,都使该书成为“丝路百城”中最为耀眼的名珠之一。读罢静思,特别打动我的,还是《临清传》一书所打捞、记载、再现的临清的文化魅力。
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无疑是这本书的重头戏,临清的诞生与发展,临清生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无不与大运河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临清传》的作者王树理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高屋建瓴的笔触,令人信服地理清了中国大运河的前生后世。他不仅详尽地记叙了大明王朝开拓大运河、疏通大运河,从而让大运河焕发了新生并有了现在规模的历史面貌,更从运河在秦汉隋唐以至元明的历史变迁,条分缕析地给出了运河的来龙去脉,引领读者进入到一个宽阔宏大又具体生动的视野中。
《临清传》中说:“历史永远不是一个按照统治者的主观意图朝前发展的乖孩子。它有自己的规律。规律,往往是遵循着民心——这个看上去像是虚拟,但却很实在、很实用的载体向前运行。”这条规律,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隐形的脉络。如在记述明代大运河的开挖与科技运用之中,作者在最高决策者的运筹之外,浓墨记载了工部尚书宋礼与民间水利专家白英对于大运河建设的居功至伟。尤其是民间水利专家白英,被作者赋之以崇高而又信实的形象——对运河的治理,早已思考了十年之久,并对运河进行过勘察,掌握了山东境内运河一带的地理水情,以及运河漕运受阻的主要原因的白英,是“见宋礼秉性刚直,真心诚意请教”,才决定出山倾囊相助,“提出了六条治河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会通河水源不足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隆重推出临清,并细述了运河文化在临清留下的烙印与临清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当中的重要作用,也就给了临清一个分量极重的准确定位。尤其在京杭大运河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临清片区更是以其大运河临清段的元代河道、鳌头矶和大运河的明代河段、大运河岸仅存的钞关遗址和临清铸钱局等,而成为这份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临清的运河清真东大寺、临清铁塔、临清砖窑遗址等,更使临清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运河文化之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独具特色的临清文化
王树理先生不仅是一位有良知的作家,还是一位文化建设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位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作家,支撑他对文学与文化的好之乐之的,是他心上的热爱,对民众与这片热土的炽热的爱。就是因为这种不变的大爱,才使他在接近七十岁的时候,能够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大书的写作之中,《临清传》的厚重,来自于他对于临清厚重文化的艰辛挖掘与阐释。
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愈加熠熠生辉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结晶,而这样的文化,又往往与民生有关并因此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临清的婚丧习俗、舌尖上的临清、临清人家的市井生活、临清的街巷胡同、临清的哈达、临清的青砖、临清的曲艺、临清的教育,甚至临清的猫事,无不如此。当作者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一一给我们立体而又现代地呈现的时候,真是不能不让人爱上这块锦绣的土地。
比如,从历史到现代,作者将临清的教育梳理得井然有序,从而也为临清的文化寻到了根基。从临清的清源书院,到临清人的读书习惯;从老先生马瑛联合乡贤上书知州重修书院、扩大招生,到临清骄子季羡林于九十八岁高龄为上海世博会山东展馆题写“齐鲁青未了”,有力地展现了临清教育与文化的源远流长。而对于“以乞讨的方式和出卖尊严的诙谐”四处集资兴办义学的武训的浓墨重彩,则体现了王树理先生坚守一生的平民情怀与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由等级森严的贵族式教育到涵盖与普及至穷乡僻壤的平民百姓,作者紧紧抓住武训与义学所体现的历史大趋势,从而将这个人物再一次立体地展现于我们面前。
书中,武训的几次下跪,震撼人心。为了开创贫民子弟可以得到教育的义学,他可以“不惜装猫扮狗,学驴叫,变成大马在地上驮着别人爬来爬去……甚至以让人踢打的方式,来争取几个小钱”。而下跪,更是他以丧失一己尊严换取穷孩子上学尊严的方式。他跪请有学问的人担当义学的老师,他跪求贫寒人家的子弟上学,对于勤于授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于稍有懈怠的老师他又会“跪求警觉”,对于贪玩的学生他还“跪泣劝学”,为了储存好自己千辛万苦乞讨来的办学钱,他在一个仁义的举人杨树坊大门前一跪就是两天……当他办学成功并于五十九岁时病逝于临清县御史巷义学的时候,作者引用了《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卒,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不仅是挖掘与发现、陈述与再现,王树理先生还在此基础上有着独到的思考与深刻的思辨,这也是《临清传》又一显著特点。比如对于以临清为其活动中心的武训,作者在厘清历史脉络的同时,就作了这样的总结:“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较优的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
临清在文学中绽放的魅力
在“丝路百城”系列中,《临清传》在文学中绽放的魅力,必定是独特的、悠长的;而在王树理先生迄今为止所创作的十数部文学作品中,《临清传》又会以其文学元素中的历史厚度与民间立场而独具风采。
王树理是怀着深切的喜爱梳理着临清传统的山东运河小调、山东琴书、梨花大鼓、临清时调、临清琴曲、快板书、道情、落子、西河大鼓、评词、木板大鼓……他找到了朱自清《中国歌》中的临清小曲,发现了华广生《白雪遗音》中的临清《下河调》,他从《中国民族器乐曲集》中发现了八首临清鼓谱,他从京剧大家程砚秋对于临清京剧演出的肯定及京剧在临清的扎根与普及,详细记载了临清数十年间对于京剧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作者甚至还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找到了六百多年前临清的模样。而对于宛秋生与他的临清宛园,王树理则是站在当代城市生命中文化品格与大自然属性的高度,向世人展现了当代临清的理想与风貌。而与临清结下不解之缘的诗人臧克家,则让临清的文学意味更加浓郁。1934年至1937,臧克家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开始了自己的教书与文学创作的生涯,写下了长诗《自己的写照》、诗集《运河》、散文集《乱莠集》。正如作者所说:“临清中学任教的这三年,对臧克家目睹和分析中国的现实……成为一位人民的诗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老诗人又为临清写下一首长诗《临清,你这运河上的古城》,里面有这样的诗句:“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幢幢/从此,我胸怀里老装个临清。”
文学的力量在于点燃情感。在王树理的笔下,连那些临清的青砖、制造这些青砖的匠人与这方深厚的土地,一起不朽于时空里,也不朽于作者的笔墨中。这些“叩之苦钟磬,砌之若磐石”的临清青砖,“带着土地的质朴、母体的温馨,被垒进紫禁城的万仞宫墙,砌进北京的四合院,铺进了皇城根那些有资格到此行走的人们通行的甬道”,当然也被垒砌成庇护百姓的家园,见证幸福与苦难。这哪里是冷硬的砖,分明有着生命与灵性。“作为后来人,每当触摸到临清的砖瓦,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为之一震的感觉。似乎不是在触及一块砖,而是听到了历史的回音壁发出的铮铮鸣响……”,读着这样的文字,再想想被砌进南京中华门城墙、曲阜孔庙、德州减水坝的临清青砖,能不被深深地感动吗?
好的地方传志,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是一个民族命运的缩影,也可以展现生动而真实的历史,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回归与追寻的精神家园。《临清传》就是这样一部精彩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