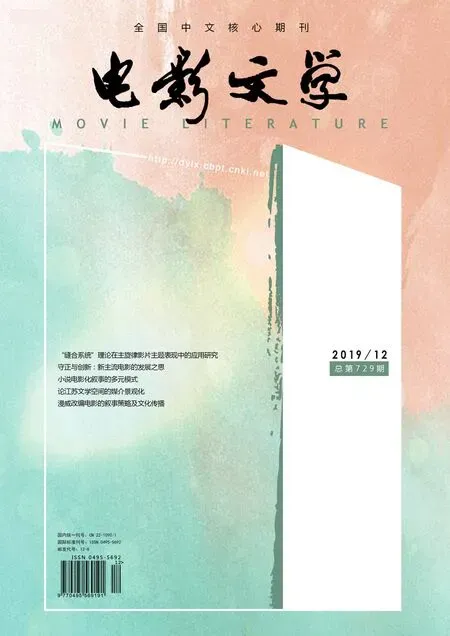《波西米亚狂想曲》:传记片的情感表述
2019-11-14杨雅靖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杨雅靖(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传记电影可视为电影世界中一个成就斐然的大类,以真实人物生平为基础,介绍历史真实,同时展现传主心理真实的传记电影,往往能博得观众与专业影评人的青睐。布莱恩·辛格执导的《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2018)在金球奖与奥斯卡上的斩获就是其中一例。电影以著名的皇后乐队已故主唱,“英国第一位亚裔摇滚巨星”弗雷迪·莫库里为传主,完整地、多层面地展现了弗雷迪的人格发展与内心世界,达到了塑造出“完整的人”这一目标,在慰藉了大量弗雷迪歌迷的同时,也触动了不少原本并不了解皇后乐队的观众。
一、情感与传记电影的“内化”表达
“情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是主观世界的主干部分,是伴随着人类的认识、实践、日常活动而产生的主观体验,是贯穿人类生理、心理与思想活动的精神力量。情感体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起点。情感是组织化了的情绪信息,是被意识到的感情,是前理性的反思,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高级形态。”换言之,脱离了情感的人是“非人”的,而苏珊·朗格则指出,情感与艺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传记电影的本体特性是心理性,塑造出传主的内心世界,是一部传记电影不可忽视的内在要求,人物情感的挖掘程度,以及电影在光影、声音等所有艺术手法上,对人物情感的表达,直接关系着传记电影能否成功。如在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1999)中,电影多次表现了贞德的“姐姐被强暴”这一挥之不去的创伤性体验,将贞德的梦境与幻觉影像化了,从而揭示了贞德所谓的“超能力”,让当代观众完全可以理解贞德的所作所为。因此,绝大多数的当代传记电影往往都有两个链条,一是人物的经历链条,一是人物的心理发展链条,这两者保证了传主是独一无二的,有辨识度的“那一个”。甚至有电影人提出,传记电影应该全面地表现传主的本我、自我与超我,这样人物才能走向真正的立体化。
对于电影这一艺术来说,要表现人物的意识层面,已经是对电影人的一大考验,而要想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层面,及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斗争,这无疑又加大了剧本编写的难度。但人物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显得真实可感,电影也正是在这种情感传达中变为“灵欲之镜”的。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丹麦女孩》(2015)对画家艾纳徘徊于自己是“艾纳/男性”还是“莉莉/女性”犹豫不决心态的表现。只是当下还有部分传记电影,在注重表现人物经历链条的同时,陷入了重事迹而轻心理的误区,将人物的个性和情感淹没在了群体情感之中。所幸《波西米亚狂想曲》并非如此,主人公弗雷迪拥有较大的知名度,皇后乐队更是一直活跃至今,人们并没有遗忘弗雷迪,他的诸多特立独行的事迹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电影更有必要走“内化”表达之路,深入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将观众从一个台下仰望歌星弗雷迪的歌迷,变为弗雷迪生活中的观察者。
二、《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情感类型
观众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得以深度介入了弗雷迪的一生,了解了他不同类型的情感故事,也看见了这些情感在其心上打下的烙印。
(一)亲子情感的对立与和解
首先是代际情感,电影表现了弗雷迪与父辈在情感上从对立到和解的过程。为了增强戏剧性,电影甚至有放大亲子情感矛盾之嫌。在现实中,弗雷迪早在印度度过自己童年时,就给自己起了“弗雷迪”的名字,而《波西米亚狂想曲》则将其改为全家人在英国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弗雷迪当众宣布自己要改名。在不跟父母商量的情况下先改动自己的名字,后又改了自己的姓,并且总是在晚上出去看乐团的演出,这使得弗雷迪与严肃、古板的父亲之间存在着矛盾。父亲博米·巴萨拉对于迎着自己走出门的儿子十分不满,他直接指责弗雷迪对自己的未来毫无规划。思维保守的巴萨拉反复提及“睿智、善言、善行”这一家族信条,认为叛逆、张扬、自我的弗雷迪完全没有向着这一目标去努力,弗雷迪质问父亲:“那你追求这些结果又如何呢?”随即扬长而去,让巴萨拉十分气愤。
《波西米亚狂想曲》展现了两代人在生活观念、价值诉求上的差别,不断挑战父亲权威的弗雷迪让自己的父子关系岌岌可危,也让观众看到了他尖锐的个性。而电影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让亲情从离散走向回归,让人从冷酷对立走向温情沟通。这主要体现在电影的结尾,皇后乐队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拯救生命”演唱会的筹备中,而这一场轰动全球的演唱会也让巴萨拉看到了音乐的力量,弗雷迪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依然愿意为了给处于饥饿中的非洲儿童演唱募捐,他这时候才理解儿子从事的事业其实是符合“睿智、善言、善行”的。当电视直播“拯救生命”时,巴萨拉带着全家人关切地守在电视之前,曾经的父子矛盾至此被彻底消解。
(二) 同性/异性爱情的欢乐与痛楚
弗雷迪的爱情也是《波西米亚狂想曲》重点表现的情感类型。作为一名双性恋者,弗雷迪最先爱上的是女孩玛丽·奥斯丁。电影对两人认识的过程进行了改编,将弗雷迪误会玛丽是布莱恩女友的经历删掉,改为弗雷迪对玛丽一见钟情并开始了强势的追求,同时电影保留了两人的许多生活细节,如躺在一张钢琴下的床垫上,玛丽为了养活弗雷迪而不得一直在彼芭店上班,弗雷迪给了玛丽一枚求婚戒指,然而在两人订婚以后他却再也不提结婚的事等。观众从电影中能感受到两人之间牵缠不休的情感羁绊,即使是在弗雷迪意识到自己喜欢男性的性取向后,他依然不愿意玛丽去交往别的男朋友,并且在自己郁闷痛苦的时候,还是要去找玛丽倾诉。
在这段异性爱情走向痛楚的同时,弗雷迪的助理保罗出现,用亲吻的方式唤醒了弗雷迪对同性的爱慕。然而两人绝非精神契合、情感融洽的伴侣,保罗开始了对成为巨星的弗雷迪的操纵。在一次派对之后,弗雷迪仗着酒意调戏了吉姆·赫顿,在遭到斥责后道歉,两人谈心后彼此钟情。可是吉姆一去不归,以至于弗雷迪用了两年的时间找遍了伦敦所有叫吉姆·赫顿的人。这是电影虚构的情节,吉姆也被从理发师改为了酒保。但是吉姆是弗雷迪最终的伴侣,弗雷迪对于吉姆有着深切的感情这一点却是为电影保留了的。与和保罗在一起不同,玛丽、吉姆和弗雷迪在一起的时候,关系中的双方都是以爱为本位的。尽管作为摇滚乐手的弗雷迪开放的性关系以及模糊的伦理边界不一定是符合观众价值观的,但是弗雷迪将爱视为两人唯一能携手同行的标准,这是观众完全可以接受的。
(三)知己之情的破坏与固守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最为动人的情感,还有弗雷迪与其他几位皇后乐队成员:布莱恩·梅、约翰·迪肯和罗杰·泰勒之间的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知己之情,可以说,这种情感是弗雷迪坚持自己音乐理想的最大精神动力之一。电影中,弗雷迪一开始一直跟踪着微笑乐队,并成功地在蒂姆退出之后进入乐队,为乐队改名为皇后乐队,他也很快成为乐队的灵魂人物。其他三人个性各不相同,但是都服膺弗雷迪,听从他包括录音、巡演,发行长达六分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等在内的安排,在弗雷迪与BBC和唱片公司老板发生争执的时候,三个人也都表示要与弗雷迪共进退。即使是其他人各自组建家庭,他们也并不让家庭压倒乐队对于他们的归属感。摇滚乐手个性鲜明,但是又愿意为共同体而牺牲的双重体验在皇后乐队成员们身上凸显了出来。然而在保罗出现之后,弗雷迪和其他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改变,罗杰等人极端鄙视保罗,在激烈的争吵后,弗雷迪与罗杰等人分道扬镳。而在意识到保罗人品的卑劣后,弗雷迪主动找到三人和解,并将自己罹患艾滋病之事坦诚告知,尽了最大诚意来挽留这段友情。而刀子嘴豆腐心的罗杰也在小小地“惩罚”了弗雷迪后又接纳了弗雷迪,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的歌是唱给孤独者的,他们也都是孤独者,而乐队就是一个“家庭”。电影中弗雷迪对知己之情的恪守与追寻过程,也是他的成长过程。
(四)“我”的再认识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情感同样还有弗雷迪“我”的构型。电影中,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弗雷迪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的过程。他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狂狷的出逃者,被称为“巴基斯坦小子”的他来到英国,确立了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又出逃了家庭,给自己一个大名鼎鼎的“弗雷迪·莫库里”名号,再然而,他又逃出了玛丽的温柔乡,在同性的身上释放激情,甚至沉迷于酒精、毒品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弗雷迪面对的挫折与迷惘渐多,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多重身份:英国的帕西人,双性恋者,以及艾滋病患者。但最让弗雷迪在意的依然是自己的歌手身份,他给人们带来的摇滚乐,不仅有反叛和愤怒,还应该有爱和真诚,以及对生命的执着。因此电影结束于弗雷迪大放异彩的温布利“拯救生命”演唱会,这意味着弗雷迪改变了自己的放纵与任性,在拯救饥饿灾民的同时,他也拯救了自己。和性取向、疾病等和解,坚持音乐,正是弗雷迪建立起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三、《波西米亚狂想曲》情感表达启示
《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情感表达上,对于当代传记电影的创作是有借鉴意义的。首先,电影坚定了“内化”表达,向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寻找戏剧冲突,这对于传主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的传记电影而言是极为必要的。弗雷迪生活的时代距今不远,布莱恩、约翰等人依然健在,“拯救生命”等演唱会更是有影像资料留存,作为“最伟大的一百名英国人”之一,弗雷迪的短短四十五年人生因皇后乐队而辉煌,人们基本上都能对他的演艺经历甚至恋情的走向了如指掌,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选择了提炼、发掘,乃至创造传主少为人知的情感性信息。例如在乐队去到弗雷迪一家吃饭的时候,博米·巴萨拉一直态度冷淡,表现出了完全不愿意融入这群年轻人的姿态,但是在大家传看弗雷迪小时候的照片,弗雷迪去接电话时,镜头却对准了巴萨拉手中一张弗雷迪童年照片,巴萨拉将它放在餐盘前凝视。巴萨拉作为严父的深沉情感以及父子之间的情感隔阂就在这样的加工中得到了表达。
其次,在进行情感表达时,传记电影理应以情节为线索,对人的情感进行故事化的演绎。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弗雷迪的诸多情感的脉络都是极为清晰的,如当唯利是图的保罗介入时,弗雷迪与乐队成员的知己之情就大打折扣直至走向破裂,而弗雷迪意识到要终止与保罗的关系时,他又能重新获得乐队其他成员的谅解,对于即使是并没有组建乐队经历,没有成为性少数者的观众而言,弗雷迪的情感变化都是不难理解的。在性别、年龄、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经历等方面各不相同的观众有可能在诸如弗雷迪的音乐理念,乃至价值观等问题上有着差异性认识,但是对于人物的愧疚、依恋、愤怒等情感,却是完全可以掌握,甚至产生共鸣的。
在传记电影的表达上普遍有着“内化”发展趋势的当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情感表达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情感正是历史与当下,名人与受众之间的关联点,人物多样、隐蔽、不可确定和量化的情感被编织在故事之中,一个立体丰满的弗雷迪·莫库里也由此出现在观众面前,电影在“传情”中完成了“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