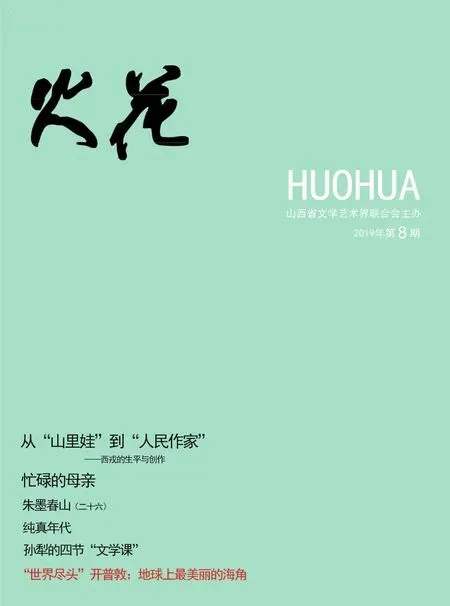载不动的乡愁
2019-11-13范廷伟
范廷伟
隋末铁匠王薄在自己创作的民谣《无向辽东浪死歌》中唱道:“长白山前知事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隋炀帝杨广时期,由于隋王朝统治残暴,骄奢荒淫,连年的大兴土木,不断地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西窝陀村的铁匠王薄就是以这首民谣相感劝,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在村子以外梯子崖以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雕窝峪首举造反义旗,各地豪杰纷纷举义响应,一时间烽烟四起,“拥众聚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事郎”。他发动了以邹平长白山为根据地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活动在齐郡、济北郡之间,点燃了推翻隋王朝统治的第一把烈火。此后,他们先后攻郡占县,杀死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沉重打击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形成了隋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局面。
时隔一千四百多年以后的这个春天,我们市“乡村记忆工程”采访团的一众成员,来到了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故里———地处鲁中的邹平市青阳镇西窝陀村,用手中的相机和笔,去寻访镌刻在我们心底的童年记忆。在这个傍山而建的千年古村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条大街,一眼古井,一棵老树,无不盛满了我们这一代人儿时的珍贵记忆,甚至于一座青砖剥蚀,明显带有风雨和流年痕迹的老房屋、老胡同都感到那样亲切。在我们的镜头里,似乎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都值得抓紧拍下来——因为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火热大潮中,我们所拍下的所有照片、记录下的所有文字,终将印刷成册,留下这个西窝陀千年古村最后的影像和文字资料,成为岁月的纪念、永恒的乡愁。我们任何人都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就应该像“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发起者、“非遗”保护专家冯骥才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时下这样一个物换星移的大时代,我们要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力,为延续养育自己的这方文化做些有益的事情。如今,民间文化已经有了文化遗产的性质,只要性质变了,我们就该责无旁贷地去重新定位它、认识它、挖掘它、保护它、抢救它,恰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历史不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
一直陪同我们寻访乡村记忆的,是首批住上醴泉社区的原西窝陀村退休教师张士意先生,他致力于乡土文化的持续挖掘与研究,目前正在撰写整理《西窝陀村志》。张先生告诉我们说,西窝陀村的立村时间应上溯到隋代以前,现在西窝陀村,东临会仙山,南依雕窝峪,西靠凤凰山,三面环山,风景秀美。西窝陀村的原址在村子的西北部,因为地势低洼,那时叫做“西窝子”,或许由于村子位于西山脚下,还有人称之为“西窝落头”,再后来,可能是由于佛教因素介入该村的原因,从明清时候,改名“西窝陀”至今。现在“西窝子”这个位置的西侧,有一条名唤“小西河涯”的沟渠,村里的雨后积水,由这里流出村外。相隔不远的再西侧是一条唤作“大西河涯”的小河,雕窝峪等山峪中流出的雨水从这里排出。张先生介绍道,未搬入新的社区以前,他的老家原本就在“大西河涯”西面的高地上,是个名为“杨家泉子”的自然村,想当初只有四十来户人家,因为一户杨姓人家最早居住于此,并且后来这里兀自冒出一眼清澈甘甜的泉水,所以这村子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杨家泉子”。上个世纪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杨家泉子”村作为一个生产小队,通过“大西河涯”上一座石桥的连接,由此并入到了西窝陀村。
村西面的凤凰山,在阳光的映射下,闪烁着春天特有的光泽,星星点点的杏花、连翘,在无意中点缀着早春的风景。尚未拆迁的墙体上喷涂着“建设新农村,倡导新生活”的醒目标语。栽种在房前屋后的香椿,簇簇青嫩的椿芽在春风的召唤下,一起涌上枝头,仿佛争先恐后向人们报告着春天的消息。在古老的村庄里,就有这些好处,乡亲们见缝插针地开辟出小小的菜地,或是露天栽种,或是拱棚培植,从春天的菠菜、香菜、韭菜,再到秋天的扁豆、豆角、南瓜等等,绝对比集市上要新鲜许多。古人说享受“清风朗月不花一分钱”,在乡村的邻里之间,隔着墙头你递我一把蒜薹,我送你一把茴香,照样凝聚着村人乡邻间的淳朴感情,填补着曾经瘠薄苦涩的岁月。张士意先生是首批搬入醴泉社区的人家,他说,老百姓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从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迁入社区生活,昔日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全部改变了,他们感情上确实一下子拐不过这个弯来,但村庄搬迁、土地置换等是大趋势、大方向,并且“合村并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整合土地资源,彻底改变部分村庄脏、乱、差的现状。他指着路边一片青油油的麦田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我家的老宅基地,房屋拆迁后复垦出来这么一块庄稼地。如果村子全部拆迁完毕的话,将能置换出上千亩良田。”
随着张士意先生的指引,我们从“西窝子”位置一直往东走,和我的老家一样,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每一座老屋、每一棵古树,栉风沐雨,饱经风霜,它们忠实地守护着古老的村庄,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故事,更有着自己独特的乡土情怀。在“小西河涯”的东侧不远处,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土坯老屋。据张士意先生介绍,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主人是赵怀明、赵怀俊兄弟,它始建于民国年间,虽然是砖坯结构,却历经百年而不塌不倒,后墙上镶嵌着六块石质的拴马桩,足以拴六匹高头大马。高大气派的房屋,博人眼球的拴马桩,彰显着赵氏家族的富足。然而,赵氏后人已经迁入城市生活多年,这座房屋便闲置下来。村里类似的房屋不少,有的房倒屋塌,有的摇摇欲坠,有的顽强耸立,只是大门多被锁上,门环处几乎锈迹斑斑,青石路旁,杂草与苔藓并生。西窝陀村地势南高北低,高低错落,新房旧屋,参差不一,加之首批房屋拆迁以后留下很多的断壁残垣,看上去杂乱无章。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就业,留下了大量闲置宅基地和残败老屋,形成了外实内空、外新内旧、外齐内乱的局面,不由得令我想起了那首关于“空心村”的打油诗:“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宋代叶适在其《留耕堂记》开篇语中说:“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倒是与现在合村并居,土地集约的终极目的完全相契合。
西窝陀村现有在册人口四千三百多人,土地大多是瘠薄的山地,由于地块分散,也没有便利的水浇条件,人多地少,纯粹属于“靠天吃饭”的村庄。因此,在村子里的众多手艺人之中,尤以铁匠、木匠居多。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背井离乡,走南闯北,可谓遍尝人间酸甜苦辣。在走村串户的过程中,我才得以发现西窝陀村不同于平原的普通村庄,他们没有家家户户通上干净便捷的自来水,而是每家每户都有自备的水井。在村民王秀美大嫂家的院子里,就有一口深达二十米左右的水井,井台上早些年架设木制辘轳使用的石质井桩尚在,除了供自己家饮用以外,甘甜的井水还可以浇院子中的菜地,只是原先的木制辘轳早已被便捷的电动自吸泵所取代。水灵灵、嫩生生、绿莹莹的青菜,显现着春天里特有的朝气,令人只要看到就欣喜不已。苏轼曾说“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院子里的几棵竹子青枝绿叶,在墙角朝气蓬勃地耸立着,显示着主人一家的生活品位。房子是旧房子,但室内干净利索,方桌上面的墙上贴着毛泽东主席的彩色画像,画像的两侧贴着“东风浩荡气象新,红日东升山河壮”的对联,王大嫂这一代朴实的庄稼人,对我们的开国领袖和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是他们深植于心底的朴素理念。
在村民赵得家的大客厅里,一家人讨论着村庄搬迁的事情,干货车司机的赵得家情绪不佳,但我们几个人的贸然到访,让他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他不失礼貌地拿出上等的铁观音茶,忙不迭给我们几个人满茶倒水,点烟递火。说实话,看到这么漂亮的房子,看到这么精致的装修,再想到这个家很快就要夷为平地,这个村庄也将很快不复存在,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正常人,在感情上面肯定都一下子“驾”(接受)不了。赵得家告诉我们,自己读书不算好,没有吃上公家饭,只有凭借一把子“笨”力气,起早贪黑,舍家撇业地开货车挣个辛苦钱。原以为这辈子盖好这套前出厦、带双耳房的新屋,就算是给子孙后代置办下了一份可以传世的家业,只是没料想形势转变得这么令人猝不及防,毫无防备。我们丝毫不难看出,声音稍有哽咽的赵得家,他实在是眷恋两口子拧劲把力、春燕衔泥般辛苦构建起的这个小窝。包括我们在座的几个人都是农村穷苦孩子出身,深知盖房子的不易,我们只能陪着唏嘘着、叹息着。可他说:“进社区、住高楼,是社会大趋势,宁有千般不舍,我们也得配合。”他唯一有求于我们的一件事,就是看我们能否帮他处理掉妻子耗时三年多完成的刺绣《琴棋书画图》(又称《十八美女图》),这幅1.2×3.4米的巨幅作品,系用木框与整张玻璃精心装裱而成,实在无法运进空间狭小的楼道,包括一幅尚未装裱的巨幅《八骏图》捎带着也要处理,价格随便说就是。
陪着我们聊天的赵得河,是赵得家的叔伯哥哥,他相比赵得家而言,显得有些木讷,话语虽不多,可搭眼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成持重的庄稼汉,即使插上几句话也是慢言沓语。他说:村里地太少,就剩下一些老头老太太看家了,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在邹平企业打工的多,有钱的都在邹平买楼了;脱不开身出远门的,在镇上的广富集团也不少,自己年轻时在山里干石匠,现在在广富集团干带班,月收入能在五、六千元。他坦言,小时候就企盼着“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好日子,自己也并非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西窝陀土生土长的庄稼孩子,平常素日的,没有觉出啥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真的一旦永远离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个家,确实有一种痛彻心扉的不舍。我们闲谈话语之间,一声声“收破铺衬烂套子来”的声音从街上传来,顿时让我们听出一种久违了的质朴与温馨,仿佛带着岁月的沉积与芳醇,只是听到这一声声的吆喝声,我的心中立马泛起了一种说不出的触动与亲切。在青阳镇政府工作的文友高宪胜,曾在一首歌中写道:捧着这湾水,恋着这方土;心系这条河,情牵这条路。这情真意切的歌词,究竟是多么温润人心的抒情文字,又是恰如其分的真情描写呀!
走在西窝陀村的主干道上,许多轿车相继排成两行,停在街道的两边,这是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有的热闹景象。三五成群的乡亲们分散在街头巷尾,他们说这是镇上的工作人员在丈量宅基地面积,依此进行拆迁补偿,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才回家协助镇上的测量工作。村医王令峰的房子是二层小楼,看到测量人员走进家门,他的妻子心疼得掉泪,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历数着住楼的种种“孬处”,譬如出入不方便了,烧水、做饭要花钱了,吃不到亲手栽种的新鲜蔬菜了,家家都是“关上门子朝天过”等等,全然忘记了他们四十年前最最期待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梦想。同样是在这条街道上,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站在前出厦的屋顶上翻晒东西,看到我们一行的到来,又拍照、又记录,忍不住抹眼搭泪地哭了起来,历数他们盖房的种种不易:直径二十五的钢筋用了多少,灰土地基打下去了几米深,还有房子结实得很,儿孙三五辈子也住不坏等等。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我在乡下也有一套宽敞明亮的老房子,至今我八十岁的父母还为我守护着我灵魂的家园。我是一个念旧的人,爱屋及乌,看到这熟悉的一切即将永远消失,心里升腾起一种莫名的伤感。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感叹时下的“乡愁”别绪,对于喜欢念旧的人来说,它既是一颗“暖心丸”,又是一枚“催泪弹”。
时下的千年古村西窝陀,随便走在哪一条街道上,都有一种远离喧嚣和尘埃的平静与安逸,或漂亮或破败的房前屋后,但凡有一星半点的闲散土地,都由对土地怀了深厚感情的父老乡亲种瓜点豆、搭杆竖架,或是围了一圈篱笆,任由藤蔓昂首翘头,肆意缠绕,用鲜艳的花朵唱响美妙的乡村赞歌;随便走进哪一户人家,除了水井和菜园以外,再熟悉不过的就是那些纯手工的灶台,它们无一不散发着柴草的清香,温润着我们心灵的风景。还有招摇着酒幌的乡村饭店,可以随便赊账的个体小商店,散发着浓郁麦香的馒头房,这种带有烟火气息的村庄,就是如影随行、与我始终不离不弃的家乡。大部分老人不愿意离开,是因为这里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就连岁数尚显年轻的我,对于很多诸如西窝陀这样极具价值的古村落悄然作古,众多的文化遗产灰飞烟灭,特别是看到那些开着农用四轮、三轮车进村的文物贩子,又拉着一车车的纺车、织机、手推车、辘轳、豆腐梆子等木器,一车车的井桩子、碌碡、磨盘、石槽、拴马桩子等石器驶离西窝陀村的时候,同样和这里的父老乡亲们一般恋恋不舍,心存隐痛。“破家值万贯”,这些不可复制、无处存放的民间文化,不仅仅是一门学问,它们还是乡村父老美好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方式。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在了西窝陀村以西的凤凰山上,也洒在了西窝陀村的房屋、街道上,那些被圈在其中的大大的红色“拆”字,在夕阳的映照中分外刺目。今年中,整个青阳镇计有含西窝陀以及郭庄、贾庄、浒山铺在内的四个村庄、约万人即将迁入崭新的醴泉社区。“住进新社区,享受新生活”,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但愿年轻人都有用武之地,发挥才干;但愿老年人都能安居乐业,颐养天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农耕文明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可以不知道未来,但不能不知道来处,我唯有用手中笨拙的笔触,如实记录下西窝陀人这种舟轻愁重的感情。即将离开西窝陀时,我的耳畔仿佛响起歌星郭峰那饱含沧桑的歌声:“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流满眼泪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记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