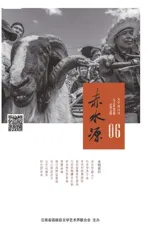我的故事是红小说
2019-11-13季风
季风
红衣
那时我开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经常要去一个名叫二十四岗的地方。据说这二十四岗有二十四个山岗,岗上全是莽莽苍苍的森林。二十四岗太大了,大得来你走进去会产生永远也走不出来的感觉。在二十四岗有一个林场,这个林场更多的不是种树,而是伐木。我通常就是把林场工人砍下来的树木装车运出来,送到一家造纸厂去造纸。
大雨如注。就像天上有无数人正在过泼水节,在尽情地享受欢乐的同时,不经意间就把泼出来的水洒向了我们人间,让我这个驾驶员此时只会苦不堪言。还好像不把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浇个透心凉,就不肯罢休。透过窗玻璃,可以隐约看见公路两边的灌木丛,被雨水砸得东倒西歪。我记得,公路两边原来也是长着参天大树的,后来被林场工人砍伐完了,被像我这样的驾驶员开着大卡车运走了。时间长了,就在原来长满参天大树的地方,长出来了这些又矮又小的灌木。
公路又弯又险,我必须当心。以前也经常会遇到雨天,却没见到过这样大的雨。我睁大了眼睛,可在十米开外就看不见任何东西。我把雨刮器开到摆动速度最快,可刚把雨水刷开,很快就又布满挡风玻璃。我把车速降到30 码以内,还是觉得这车跑得有些快。我在心里祈祷着,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虽说我是我们车队的驾驶能手,生产标兵,可我对眼下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是有些紧张。我感觉到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紧张流出来的汗水把衣服弄湿了,还是车窗外的大雨使驾驶室内湿度陡增,把我的衣服湿透了。
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解放牌大卡车,我的车上装满了一截截的红松。这些红松直径都在一尺五左右,还被锯成长度在一丈二尺上下,这样便于更好地装车。我看见这些红松曾经站立在二十四岗的山岗上,像极了绿色的祥云。我还看见伐木工人用斧子,或者用截锯,把红松砍下来,也可能是锯下来。那些站得笔直的红松会轰然倒下,倒下来的声音传得很远,会弄得山鸣谷应,但却听不见红松哪怕是很轻地哼上一声,难道它们就不知道痛么?这或许就是红松和我们人类的区别,红松其实很痛,但它们却不会喊痛。我们人类有时只是碰伤点皮肉,可我们却会不停地大声喊痛。
很快就要到一个名叫高桥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有一条水沟,在水沟上架得有一座石拱桥。桥不算长,也就十来米;更不能说高,也就四五米。叫高桥真有点言过其实了。用来砌石桥的石材,就是这附近出产的一种青石。这种青石质地硬朗,常被一些人用来砌祖坟。我每次把车开上桥,就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我怕这桥承受不了装满木料卡车的重量。我在这里跑车已经好几年了,这桥还从来没有出个问题,可我开上桥总是会没来由地紧张。我注意过,在桥的旁边,不远处,有一间老旧房屋。可我从这里经过,从来就没有看见冒出过炊烟,也没看见有人在这房屋里进出。这也许是一座年久失修无人居住的荒宅。
这会雨下得更大了,完全可以说得上是暴雨。雨点落到路面上,会很快溅起来一朵朵白色的水花。我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我更加专注地驾驶着汽车。卡车开过高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过桥转过来,我忽然看见在大雨中的公路边站着一位女子,红衣红裤。大雨让红衣女子的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裹在身上,让女子看上去更加娉婷。毫无疑问,这红衣女子是要搭便车的。我把车慢慢地停在了她身边,是我先说话。我说:“这位妹子,你是要搭车吗?雨下得太大了,快上来吧。”我把副驾驶位的车门推开,红衣女子很轻盈地就上来了。红衣女子也不看我,只是望着路的正前方,然后轻轻地对我说:“谢谢你,师傅!”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这女子面容娇好,只是脸色有点发青发白,我估计她这是没有休息好的缘故。我重新把车开动起来,虽然这会在我的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位红衣女子,可她却并没有给我的驾驶室带来任何生气。
车继续往前行驶,大雨开始变成中雨,然后是小雨,最后干脆停下来了。我从驾驶室挡风玻璃看出去的距离已是越来越远,我把雨刮器关了,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把车开得快了起来。红衣女子还是把脸朝向正前方,一只手扶着她旁边的车门把手。从上车开始我就提醒她不要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这样会很危险,但她就是不听,好像这样要是遇到危险,她就能够尽快破门而出,然后落荒而逃。我也知道,我们这些驾驶员,确实有对搭便车女子心怀不轨的,因此一般姑娘对此有戒心并不奇怪,但这样对我,我只会感到委屈。我提醒过了,就不想再管她了,真要掉下去了再说吧。
又走了一段,车离二十四岗已是越来越远。都不说话,驾驶室里安静得像死过去了一般,我只好无话找话。我说:“妹子,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是要回娘家还是婆家?”红衣女子还是不看我。红衣女子说:“师傅,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问我是回娘家还是婆家,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要回娘家还是婆家。我还有娘家和婆家吗?”我借着卡车转弯打方向盘,又侧脸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位的红衣女子。我看见红衣女子一点表情也没有,脸色看上去还是那么发青发白,看不见有一点血色。我只觉得这红衣女子有点怪异,但又说不出到底怪异在哪里?
灌木丛终于被我开的大卡车甩掉,前面开始出现成片的庄稼地。这些庄稼地上生长着玉米,差不多有一人多高,已经开始出花。在很多的玉米秆上,已经挂出嫩玉米,嫩玉米上顶着一缕缕的红缨,粉嘟嘟的煞是好看。坐在我身边的红衣女子开始有些不安,她一会儿目视前方,一会儿又看着侧面的车窗外。她的手从上车就拉着车门把手,好像随时准备要跳车一样,但却一直都没有跳,这让我的心才没有过度紧张。可这会她坐立不安,就又让我开始紧张起来。我真担心她会突然拉开车门,然后破门而出,这样肯定会酿出一场惨祸。我对红衣女子说:“坐好了。我说过,不要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到什么地方下,你只管跟我说,我会停车让你下的。”红衣女子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或者对我说什么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只在心中暗暗祈祷,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啊!
卡车继续往前面开,很快就进入到了河谷地带。顺着河的上游去,有河水从上游带来的水汽扑面而来。这一带河谷比较平坦,河水流动显得很安静。不时会看见有泡沫从水面上升起来,在很平坦的河面上浮动,长久不肯散去。越往上游走,这种白色泡沫会越多,漂满了整个河面,不认真看,还以为漂着很多的鱼儿呢。泡沫多起来,一种怪味也浓起来,让人恶心得直想呕吐。我是知道的,这些泡沫,这种恶臭,都是上游这家造纸厂在生产纸浆、生产卷筒纸时造成的。我一直在做着把二十四岗砍伐下来的树木运到造纸厂造纸的活儿,因此我对这一切,是非常熟悉的。坐在我身边的红衣女子也知道这些吗?我想她应该不会。可是,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再转过一个大河湾,就看得见前面的造纸厂了。可以看见很高的烟囱里冒着浓烟,靠近河沿的岸边,有很大的一条水沟,正在向河里排放着污水。我已经习惯了看见这样的场景,早就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可能我身边的红衣女子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她看着工厂的烟囱,看着那正在排放着污水的排污沟,完全就是一脸的惊讶,一脸的愤怒。红衣女子说:“师傅,我要下车。”这是她坐在我的车里,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我有点吃惊,虽然能够看见前面的造纸厂,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路口,据说可以去到十公里以外的城里。在这里下车,让我很有些不解。不过既然红衣女子要下车,我只能同意。我把车停靠在路边,车还没有完全停稳,红衣女子已经拉开车门,并很轻盈地跳下了车。下车后,红衣女子把车门给我轻轻关上,然后退到路边,再没有说一句话。我轻踩离合,松了刹车,重新发动汽车。汽车向前走了好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红衣女子还在路边站着,还是脸色发青发白,看不见有半点血色。我相信这女子肯定没有休息好,我不知道这红衣女子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没有问,我想我即便问了,她也未必肯回答我。联想到我们一路上很少说话,我就觉得这红衣女子确实很有点特别。
我把装满木料的卡车停放在造纸厂内,让造纸厂的装卸工人过来卸这些木料。这些木料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卡车车箱里,但很快它们就会被从车上弄下来,然后被破碎,被做成纸浆,被生产成卷筒纸。我不知道这些木头还会不会喊痛。不过,它们早就死了,林场工人用斧头、用截锯,将它们砍下来、锯下来的时候,它们就死了,就不会再感觉痛了。我这会已经不再关心这车木料,我只关心我又出了一趟车,我今天的工资又有地方拿了。从林场拉木料到造纸厂的车有好几辆,我们一辆车一天只能拉这么一回。因此拉这么一趟,工作就算完成了。等工人把木料卸完,第二天又从造纸厂把车开出来,再到二十四岗去拉木料。当然,有时候也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拉木料,或者把造纸厂生产出来的卷筒纸运出去。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单调无趣,这像极了我眼下的生活。
我正准备从造纸厂走出来回家,看见王师傅刚好从他开的东风大卡车里走出来。我们私下都称王师傅为隔壁老王,当面却很恭敬地称他为王师傅。我对隔壁老王说:“王师傅,你没有去二十四岗拉木料?”隔壁老王说:“没有。我今天运了一车卷筒纸到一家印刷厂,哪有时间去二十四岗运木料。”我说:“我倒是去了,也才刚刚回来。”我正在想是不是要把在路上遇到红衣女子搭车的事告诉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先开口了。隔壁老王说:“看你欲言又止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新鲜事要告诉我?”我把在路上遇到红衣女子的事告诉隔壁老王,我以为他要拿这事跟我开玩笑,没想到隔壁老王却说:“这事就怪了,昨天我去二十四岗运木料,也遇到这样一位女子,也是穿着红衣红裤。这女子除了脸色不大好,话少,真是太好看了。”听隔壁老王这么说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隔壁老王说:“看你忧心忡忡的样子,莫非是你占了人家便宜?”我说:“我才不会呢!我又不是你隔壁老王。”隔壁老王说:“其实只要能占,又有什么不好,白占白不占。”又说“当然,占了也只能是白占。”
回到家里,妻子已做好饭菜。坐在桌子边吃饭,我忽然想到今天遇到红衣女子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她,以前出车,也没少有人搭车,只要方便,我也都会搭。我虽然不懂什么处世之道,但我知道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这朴素的道理。不过搭过也就搭过了,不会留下什么印象。莫非今天搭车的红衣女子,那一身红衣红裤太刺眼了,也可能是她那略带青色白色的脸,这我还真说不好。我对妻子说:“你说怪不怪,今天半路忽然有一个女子要搭车。穿着一身红衣红裤,一路话很少。一张脸发青发白,一看就知道没有休息好。”妻子说:“看你那样子,你是不是占了人家的便宜?”我说:“那神色,你还敢占人家便宜?还有,你是知道的,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占人家便宜,要真这样做,这不是趁人之危嘛,只会猪狗都不如。”我说这话有点像诅咒发誓,倒弄得妻子一脸的愧疚。妻子说:“快别说了,我也是随便说说,莫非我对你还不了解。驾驶室有空位,给人提供一下方便,这没有什么不好。”
第二天,我去造纸厂把车开出来,顺着河边往下游方向走,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可以离开河边向二十四岗的方向开去。河岸边虽然有庄稼生长,却长得很不好。都说是造纸厂排放出来的污水污染了土地,即使能够长出来一些庄稼,品质也不会好,还说不少人吃这里打下来的粮食得了怪病。可不种庄稼又能做什么,打下来的粮食人不能吃,就拿来喂猪。我不知道用这种人不敢吃的粮食喂猪,猪肉是不是可以吃。不过这好像不是我能解决的,我只是保证我吃的粮食不是这里的,吃的猪肉也是我妻子从乡下老乡那里买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一个有文化的男人曾说过污染猛于虎,可说过这话不久就死于污染。
前方突然起了雾,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酽稠。丈把远的地方就看不清任何景物。我把雾灯打开,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我把车才开到昨天红衣女子下车的地方,红衣女子早已站在路边等候了。虽然有大雾,可我还是在车离她不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她,还是穿着那一身红衣红裤。我有点吃惊,怎么又遇着这红衣女子了?这回是红衣女子先开口。红衣女子说:“师傅,不好意思,我这回又要搭你的车,这你不嫌烦吧?”我把副驾驶位的车门推开,我说:“什么烦不烦的?快上来吧。反正顺路,捎上你一程也没什么。”我看见红衣女子还是面色发青发白,看不见有一丝丝的血色。莫非这红衣女子又没休息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会过得这么辛苦。红衣女子很快就坐上了副驾驶位。我要她把车门关好,她很听话地把车门拉上,不过一只手还像昨天那样,不肯从车门把手上拿下来。我说:“你能不能把手放下来,这样会很危险的。”红衣女子说:“我不动车门把手就是了,这不会有危险的。”我心想,你不动可车会动啊,不过我已经懒得再管她了。
搭上红衣女子,车又开动了。这回,是红衣女子主动跟我搭讪。红衣女子说:“师傅,你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运送木料,不觉得会很累吗?”我说:“哪能不累?干活儿哪有不累的。”红衣女子说:“你难道就没有考虑过不做驾驶员,至少不做这运送木料的大卡车驾驶员。”我说:“这是我想做么?我要能做别的工作,我还真不愿做这汽车驾驶员;还有,我家里要是不困难,我也懒得跑进这二十四岗来运送木料。”红衣女子好像还要说什么,可她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我看到她的脸这会胀得通红,就像是喝了烈酒。原来她的脸色不仅发青发白,同样也可以变红。我知道她这一定是憋的,而且这会肯定憋得很难受。不过红过以后,脸色很快就又变得青白起来。
其实我觉得很委屈。我要做这大卡车驾驶员又是容易的吗?早些年我去部队当兵,被安排到汽车班做了一名汽车兵,到我退伍返乡,驾驶技术已是非常熟稔。本来回来后满以为凭着自己一身过硬技术,要找一份工作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前当兵退伍回来,武装部都会安排工作,可到我退伍,农村退伍兵已经没有了这个待遇,就像当年大学生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现在大学生毕业却要靠自己找工作,以至于会出现众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挤独木桥的景观。刚回家,我曾去一家党政机关做驾驶员,可没过多久,我就被领导开派了。领导对我的评价是驾驶技术确实很好,不过不会来事,因此不方便再用。在乡下又闲了两年,才找人通过关系进了这家造纸厂,做了一名驾驶员,为厂里开大卡车。来到厂里,正碰上厂里搞房改,厂里看我离家远,给了我一个购房指标。由于我才到厂里开车,没有工龄,不能享受购房优惠条件,但比在市场上买房还是要便宜很多。就这样,我和妻子、孩子都住进了工厂的住宿楼。可我也因此欠下了一笔不菲的债。孩子大了要上学,乡下老人老了多病要吃药,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我感觉这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可这些,我应该跟身边的红衣女子说吗?说过又有用吗?
感觉今天和昨天有所不同,我和红衣女子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车快进入灌木林区,前方再看不见有雾,这雾来自河面,现在离河已经很远了,自然不会再有雾出来。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晴朗天气。红衣女子说:“师傅,你知道吗?这里原来跟二十四岗差不多,生长着很多的大树,可后来被砍伐了,就长满了这些矮矮小小的灌木。现在二十四岗还在大肆砍伐,要不了多久,也会跟这路两边一样,生长出这些像小矮人一样的灌木。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这样,不砍树不伐木,就不能够生活了嘛!还有,只顾自己生活,不顾他人死活,这应该吗?师傅,你没有住在这里,你自然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些年水土流失严重,听说有一户人家,就被洪水卷走了。”我说:“我跟你不同,我说不上什么。我只知道,林场这些工人要是不砍树,我也就不会来这里运送木料了。这样,我也就不会遇着你了。”我说完,特意扫了一眼身边的红衣女子,我好像还能感觉得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这和昨天的她完全不一样,虽然她看上去还是那样忧郁。
车行到高桥旁边,红衣女子说:“师傅,我就在这里下车。谢谢你让我搭车少走了很多路。”我把车停靠在路边,红衣女子轻轻拉开车门,很轻盈地就下去了。红衣女子站在车门旁边跟我招手,我能够看见她手臂上的毛细血管,像极了细小的蚯蚓爬满了她的手臂。我把车开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走下了公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要去到那间破旧老宅。老宅已经很老旧了,莫非还能住人,并且还会住着这样年轻貌美的红衣女子?可在这之前,我却并没有看见有人在这老宅出入。我没有再多想,汽车过了这并不高的高桥,就进入到二十四岗了,弯道会很大,我必须全身心地驾车才行。我知道,我每次出车,我妻子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会出什么事。我也知道开车危险,这个跟技术好坏没有关系,因此我开车从来都非常小心,我不能出任何事情。
进入林场,我很快把车停了下来,坐到一边看林场工人把木料装上车。这些工人差不多都是些五大三粗的人,体力很好,两人或者三人,就能够把一根直径过尺长丈余的木头弄上汽车。正像红衣女子说的,像这样大肆砍伐,大肆往外运送,要不了多久,这二十四岗的树木就会被砍伐殆尽,被全部运走的。这些树木要用多少年的时间才能长大,却会很快就被砍伐完。我不愿意再往下想了。工人们已经给我装好了车,我得抓紧把这车木料运出去。今早出来开车有些晚,我不想在路上再耽搁,怕回去晚了让家人担心。
接下来的几天,只要是我去二十四岗运送木料,就都会遇着红衣女子。要么就是在刚过高桥的路边上车,在即将看得见造纸厂的地方下车,或者就是在看得见造纸厂的地方上,在快到高桥的路边下。在车上,红衣女子说得最多的还是林场为什么要砍树,造纸厂为什么要用木料来造纸?不砍树不行么,用其他材料做原料来造纸不行么?还说可以用麦杆啊,用稻草啊,用玉米杆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林场就只会砍树,造纸厂就只会用这些木料来造纸,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曾试着问红衣女子,来来回回搭我的车这是要做什么?可怎么问红衣女子都不愿意说。问得急了,红衣女子说:“师傅你最好还是别问,我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的。”
这段时间,我发现,跟我一样去二十四岗运木料的汽车少了,以前我一天去一趟就可以了,可现在一天去两趟三趟都不够。我不知道其他的汽车是不是拉其他东西去了,比如运卷筒纸到印刷厂。但不会有这么多卷筒纸需要运送啊!这天,我刚把一车从二十四岗运回来的木料停放在造纸厂,让造纸厂的工人卸车。我非常疲惫地走出厂门,恰好遇到了隔壁老王。我说:“王师傅,这几天都没看见你去二十四岗拉木料,你是不是送卷筒纸去印刷厂了?”隔壁老王看了我一眼,对我说:“我没有去二十四岗,也没有去送卷筒纸。莫非你现在还去二十四岗拉木料?”我说:“是呀,就因为你们不去拉,害得我一天要多跑上一两回。”隔壁老王说:“还是你行,那你就多跑点,反正造纸厂发计件工资,这样你还可以增加收入。我不会去了,我想我再也不会去了。”我知道隔壁老王跟厂里某位领导关系很不错,他不去二十四岗运木料,也还是会有自己的工作可做,再不济,还可以不做驾驶员到生产车间去造纸,甚至可以调到厂办公室搞收发。
开年来,有一天,我正准备去造纸厂开车,然后去二十四岗拉木料。我正准备上车,隔壁老王从厂办公室出来,把我叫住了。隔壁老王果真去了办公室,而且还做了主任。王主任说:“你这是要去哪里?”我说去二十四岗拉木料,这几天厂里不是急等着木料碎料。王主任说:“你不用去了,这些年你没见二十四岗的木料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没有多少树木可供砍伐,也没有多少木料让我们去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像二十四岗这样的森林谁还敢砍伐。现在的林场工人已经不是在伐木,而是在种树了。”我说不让我去拉木料,那我还能做什么?王主任说:“这个我不知道,不过现在厂里正有一车卷筒纸需要运出去,一会就让工人们给你装上。至于以后的事,再说吧。”
就此,我再没有去二十四岗。我们造纸厂在没有树木做原料生产卷筒纸,开始用毛竹、麦杆、稻草和玉米杆做原料生产草纸,这样又过了几年不死不活的日子,环保部门说我们造纸厂对环境的污染太严重,要求必须关停,还河水清洁,给鱼虾健康。我知道,我们造纸厂建成这些年来,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环保措施,但其实并不过关,河水被污染了,鱼虾能走的都游走了,不能游走的都死了,河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鱼虾了。现在好了,工厂要关停,虽然我在造纸厂已经开车这么多年,对工厂已经很有感情。但每当看到工厂烟囱冒黑烟,往河里排放污水,工厂附近数公里内奇臭无比,不长庄稼,我就觉得这工厂早就应该关停了。国家给我们每个工人发放了一笔再就业资金,让我们自谋职业。我用这笔资金再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买了一辆小车,很快开上了出租车,收入比给造纸厂开大卡车拉木料还要高。
光阴荏苒,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这天,我开着出租车正在大街上行走,这时有一个微胖谢顶的中年男人叫住了我。中年男人说:“师傅,你这车可以跑长途吗?我想去临近的一个县出差,正愁找不到车前往。”我说:“怎么不可以,只要你肯给钱,我就是送你去北京、上海都不会有问题。”中年男人说:“师傅真会说笑话。那就这样吧,我按规定付给你车费,不过你到时得给我扯发票。”我说:“这没问题,我又不是跑黑车的。”中年男人坐上车,我这才发现我们需要经过二十四岗,才能够到达临近县。我一面开车,一面和中年男人攀谈起来,原来中年男人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志办主任,这次出去是要参加临近县的地方志评审会议。我一看这中年男人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果然不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汽车快开到高桥处,我会突然冒出来某种渴望,我希望路边站着一位红衣女子,正在急切地向我招手,要搭乘我们的车。这一段路,我都在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公路两侧,希望能够看见这位红衣女子。可两边除了林场工人才栽下去还没有长高长大的树,不要说什么红衣女子,就是其他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中年男人有所警觉,中年男人说:“师傅,这一路上我看你好像有些神思恍惚,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可不能开出什么问题来啊!”我说:“领导,你尽管放心,我从十九岁去部队当兵就开始开车,到现在还没有开出过任何问题,这点路拦不倒我。”不过,我已把目光看向前方,一门心思地开车。车已经开过高桥,又走出去好几公里,我知道,这红衣女子肯定不会再出现了。
把中年男人送到临近县,我又沿着二十岗的这条公路返回。车到二十四岗,再不会看见有人砍树,时不时的,倒是会看见有林场工人在植树。我知道,要不了多少年,这二十四岗就又是莽莽苍苍的了。车经过高桥,我有意识地把车开得很慢,甚至在红衣女子当年上车下车的地方,还把车停了下来,可并没有红衣女子站在路边,招手要搭我的车。我还特意把车开到能看见造纸厂的地方,当年红衣女子就是在这里上车或者下车,可这里除了长满庄稼,并没有什么红衣女子等着要搭车。我把车停下来,我需要想想,我需要好好想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还把脸望向造纸厂的方向,原来的造纸厂早已不复存在,而成了一个竖着好几座塔吊的建筑工地。要不了多久,这里将会建起来一所非常漂亮的长河中学。
回到家,我顺便拿起中年男人在车上送给我的一本《市志》。不经意间,我翻到了369 页,这里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二十四岗森林砍伐和长河造纸厂污染。这个小标题下面的文章特别讲到森林被砍伐以后,水土流失严重。某年发大水,林区有一户人家悉数被洪水卷走,空留下一座荒宅。其中有一位穿着红衣红裤的女孩儿,刚从外面读书回来,也遭到了不幸。这个女孩儿正在一所大学读环保专业。那时候,二十四岗林区砍伐下来的树木,差不多都送到了造纸厂打成纸浆造纸。大水过后,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寻找被洪水冲走的这户人家,其他的人都找到了,唯有这穿着红衣红裤的女孩儿没有找到。不久,就有一位穿着红衣红裤的女子,不厌其烦地到当地信访部门上访。直到国家开始退耕还林,二十四岗停止砍伐树木,造纸厂被勒令关停并转,才没有再见到这位红衣女子到信访部门上访。
红鞋
知道民中同学要来我们学校,我和吴星汉都非常兴奋。听说民中的文艺队,还要和我们学校文艺队一起联欢,更是让我和吴星汉在心里好没来由地一阵狂喜。我们学校是一所才建立起来不久的中学,目前有我们初三年级三个班,初二年级二个班,初一年级二个班。我们学校成立得有一个学生业余文艺队,唱歌跳舞水平还不错。没想到民中也有文艺队,我们倒要看看他们的水平如何?
在我们这所学校,我和吴星汉在一个班上课,住宿更是睡上下铺。吴星汉睡上铺,平时像一只灵猴在床上爬上爬下。吴星汉兴奋是因为马兰芳在我们学校文艺队,经常演喜儿和吴清华。吴星汉和马兰芳从同一所小学考取我们这所中学,他俩住的地方又不远,所以每逢周末放学回家,差不多都是一起回去。因此大凡马兰芳排练还是演出,吴星汉只要能逮着机会,就要跑去看。一双眼睛盯着马兰芳穿着红布鞋的脚,看那双脚在舞台上不停地旋转翩跹,表情异常丰富,颇耐人寻味。可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吴星汉兴奋完全是无厘头,后来想大概就因为我和他读书在一个班,睡的还是上下铺。
我们学校对面的县城有两所中学,一所青山一中,还有一所就是民中。说是学校对面,其实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河,平时我们要到对面县城去玩或者买文具,都要坐木船才行。记得有一年对面县城电影院放映《闪闪的红星》,学校组织我们全体同学,其实就是我们七个班的同学去观看,大家分乘几只木船准备过河,船快到河中央,从下游方向忽然开来一条很大的机动船。这下还了得,机动船经过的水域,很快掀起了一两公尺高的大浪,差不多就要把我们乘坐的木船打翻。我和同学们都发出了尖叫声,以为会很快翻入河底。还好,划船的艄公很镇静,要大家坐好,不要慌。船靠岸,我们才惊魂甫定。到了电影院,坐下来看《闪闪的红星》,看到勇敢的潘冬子,才觉得刚才在河上的担惊受怕算不得什么。
一大早,民中同学就要坐船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就是在民中同学到来之前,把我们七个班的同学带到河边站成两排。民中的同学从船上下来以后,就从我们两排同学中间走过。学校鼓乐队很快敲起了迎宾锣鼓,锣鼓声震天响。我们一边拍手,一边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场面很热烈。据说民中的同学主要生活在城里,因此他们穿着都很光鲜。特别是女生,穿着更是跟花儿一样。有一位女生,身材高挑,在女生中都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我至今都记得,她穿着孔雀蓝的连衣裙,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皮鞋。我对女生有好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我觉得女生原来还可以这么好看,我们的校园生活可以有这么美好。
民中的师生到我们学校,自然是老师和老师交流,学生和学生互动。我记得,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和民中一个班的同学,在学校小礼堂互动。民中的同学真不简单,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们在说话,有时还唱歌。而我们班的同学就基本不说话,把互动变成了民中同学一家说唱。我注意到那位穿着孔雀蓝连衣裙的女生,差不多一直都在说话唱歌。她说话的声音很甜,就像我们学校附近糖厂榨出来的蔗糖,轻轻咬上一口,会很快甜进心里去。孔雀蓝女生还是穿着她那双红皮鞋,我每看一次,心里就会慌乱一次。我是又想看又怕看,我怕这种因看而产生的慌乱被同学看见。要是让民中的同学看见了,那就更不好了,没准还会坏事。
天气很好,下午民中文艺队和我们学校文艺队的联欢,就在学校露天舞台举行。刚吃过中午饭,吴星汉就对我说:“我两个抓紧把板凳抬到操场上去,最好能够放到前排,这样就能看到舞台上表演的节目了。”我知道,吴星汉要看的节目,其实就是马兰芳演的吴清华或者喜儿。或许就因为我和吴星汉睡上下铺,因此什么事他都要支使我,尽管我心中经常不情愿。我和吴星汉把板凳抬到操场上,才知道第一排是留给民中和我们学校老师坐的,从第二排开始,先是民中学生,然后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和吴星汉最终把板凳安在了第六排,这里离舞台是远了一点,可是比起后面的同学,这已经非常好了。
联欢会开始了。先是我们学校校长致辞,对民中师生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还说这种交流早就应该搞了,现在终于成为了现实,全校师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接着是民中带队的副校长致答辞。这位副校长是位女性,风度翩翩。副校长说,今天能够到贵校学习,感到非常愉快,从此我们两校的交往将会上一个新台阶。两校领导致辞结束以后,联欢才真正开始。这次的节目安排都是一个学校一个,穿插着进行。有合唱、独唱,还有快板书、相声,当然最让人兴奋的是舞蹈,我知道,马兰芳跳的《白毛女》,或者《红色娘子军》,也就是跳喜儿或者吴清华跳的一段独舞,肯定是整个联欢会的压轴戏。
联欢会进行到五点钟才正式结束。在这之前,我感觉有些疲倦,再看看坐在我身边的吴星汉,却精神抖擞。我知道,吴星汉在等着马兰芳出场,他和我在这里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看到马兰芳出场。这时,报幕员出来报幕,下一个节目是联舞,表演者民中同学乜小丫,我们学校同学马兰芳。报幕员刚报完幕,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学们都知道,真正的压轴戏来了。
首先上场的是马兰芳,她跳的是《白毛女》喜儿等爹爹杨白劳回家过年的一段独舞。只见马兰芳穿着红衣服和绿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红布鞋。我看清楚了,红衣服和绿裤子,是用普通的红布和绿布做成的,红布鞋是一双用红灯芯绒做鞋面白布做鞋底的平底布鞋。马兰芳跳这段舞很认真,她把喜儿盼爹爹回家过年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非常到位。或许她知道,她的这段舞蹈应该能代表我们学校的最高水平,事实上她确实做到了。如果跳不好,那就会给学校丢脸。马兰芳一段舞蹈跳完了,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坐在我身边的吴星汉的巴掌拍得最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巴掌拍痛了?我的巴掌拍得并不太响亮,可我还是觉得自己把巴掌拍痛了。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息,民中叫乜小丫的女生出场了,她跳的是《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一段独舞。乜小丫开始起舞,台下先是很安静,但很快就掌声雷动了。我看见这个名叫乜小丫的女生,原来就是我们白天到河边迎接的时候,看到的那位穿着孔雀蓝连衣裙,一双脚穿着红皮鞋的高挑女生。原来是她!我的心跳忽然加快了,我很担心会被坐在我身边的吴星汉发现,我有意识地把身子向侧面挪了挪。
我不得不说,乜小丫的舞确实跳得太棒了。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专业和业余,等我知道了,才明白那个下午乜小丫跳的舞已经具备专业水准。乜小丫穿的是用红绸缝制的戏服,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脚上穿的是真正的红舞鞋。乜小丫的舞姿更是了得,她的劈腿,她的一字马,惊艳了整个台上台下。最了不起的是,她穿着红舞鞋的两只脚尖还能够立起来,这跟电影里的吴清华没有任何差别。我承认,我的一双眼睛一直在跟着乜小丫的脚尖转,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看着看着,我忽然开始难过,我担心乜小丫的脚尖会很疼,会不小心被折断。我那时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不知道我对乜小丫怎么会是这样。
联欢会结束了,我们把板凳送回教室,待做完这些以后,我和吴星汉才走回宿舍准备拿碗去厨房打饭吃。在回宿舍的路上,吴星汉突然问我,你觉得马兰芳今天的舞跳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吴星汉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很高兴地说确实不错,马兰芳今天跳得真好。我承认,我以前也看过马兰芳的舞蹈,今天确实比以前跳得更好。这时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我对吴星汉说:“你觉得民中那个叫乜小丫的女生跳得怎么样?我觉得跳得太好了,我还没有看过跳得这么好的舞蹈。你看她劈腿,你看她的一字马,那一双立起来旋转个不停的脚尖,真是太棒了!”我才把话说到这里,吴星汉一张脸看上去已经很不好看。吴星汉说:“马兰芳肯定比她强,要是能有一套绸料衣裤,有一双红色的舞鞋,马兰芳的脚尖也能立起来的。”我想到马兰芳跳舞的时候,穿的是一双红灯芯绒做鞋面的平底布鞋,我想可能还真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相信乜小丫跳得要比马兰芳好。
晚饭后,民中的同学就要回去了。因为横渡的木船七点以后就不再开了。或许是为了有始有终,也或许是为了表达我们学校对民中师生的敬意,还像早上一样,我们先吃过饭,就来到河边排成两排,等民中的同学吃过饭,我们就要夹道欢送他们过河回学校。那时已经有了一点傍晚的气息,我看见河面上有不易察觉的水汽在蒸腾,要不了多久,河面上就会有白花花的雾弥漫开来,把整个河面遮挡。一会儿,民中的同学出现了,我们学校鼓乐队率先开始敲锣打鼓,我们站成两排的学生开始高喊“热烈欢送,欢迎再来”。我看见民中的同学都很感动,不断的向我们挥手致意。我看见乜小丫站在民中同学的队列里,还是那么高挑脱俗。她还是穿着那一身孔雀蓝的连衣裙,脚上还是穿着那双红色的皮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中了邪,我只要一看见乜小丫,我的心就会狂跳不止。可我又不能不看她,因为我再不看她,等她上了船,等她过了河,我就会看不见她了。我哪怕整个心脏从嘴里跳出来,我也还是要看。直到民中同学都上了船,船慢慢离开河岸,白雾开始漫上来,我们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河边。
第二天,我们正常上课,好像学校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其实不然,只要是老师不在课堂上,或者在课间,我们就免不了要对民中的同学发一通议论。我们学校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对民中这些来自县城的同学,自然会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瞧人家那穿戴,哪是我们这样的农村同学穿得起的。当然议论得最多的还是那个名叫乜小丫的女生。她要不在舞台上让报幕员隆重推出,她要不把舞蹈跳得那么好,我们或许会谁都记不得她。当然我会记得她高挑的身材,还有她穿的那件孔雀蓝的连衣裙,当然我更会记得她穿的那双红色皮鞋。在谈到舞蹈的时候,有同学说乜小丫真不简单,跳得跟电影上的一样好,比我们学校的舞神马兰芳跳得还要好。我记得吴星汉是第一次和同学急。吴星汉说:“你再这样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们不知道,马兰芳只是缺了那一双红舞鞋。我知道,要是马兰芳有乜小丫那样的红舞鞋,肯定跳得比乜小丫好。”说话的同学见吴星汉要动手,就不敢再说了。确实,马兰芳和乜小丫穿的服装和鞋不一样,马兰芳只是穿着一双红灯芯绒做鞋面的平底布鞋,乜小丫穿的却是真正的红舞鞋,这确实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
到了周末,民中同学到我们学校这事在慢慢淡去。当然,这只是对大多数同学而言。乜小丫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一刻也没有淡化过。我忘不了她那高挑的身材,还有她穿的孔雀蓝连衣裙和红色皮鞋,当然更忘不了她穿着用红绸做的红衣红裤,还有穿着红舞鞋跳舞的光辉形象。大概是民中同学回民中的第二天晚上,我做梦了,梦中我看见乜小丫穿着红衣红裤,脚上穿着那双红舞鞋在舞台上跳舞。我看见她一个劈腿,再一个一字马,然后就来到舞台中央立着脚尖不停地旋转。我觉得我被她转晕了,就只会一个劲的鼓掌,直到把巴掌拍痛了都不肯停下来。第二天早上醒来,睡上铺的吴星汉对我说,你昨晚是不是梦见鬼了,把巴掌拍得啪啪响,把我都吵醒了,害得我没有办法把觉睡好。
就在我们大家都以为不会再有什么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马兰芳把人家乜小丫的红舞鞋偷了。这事在校园里传开来,不亚于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马兰芳什么人?全校同学心目中的舞神啊!同学们根本就不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我问过吴星汉,你相信马兰芳会偷乜小丫的红舞鞋吗?吴星汉一张脸胀得通红。吴星汉简直就是在怒吼:“怎么可能?马兰芳怎么可能!肯定是有人嫉妒她舞跳得好,有意陷害她!”我也相信吴星汉说的话,肯定是有人故意要陷害马兰芳。
这事在校园内不断发酵,脉络越来越清淅了。原来乜小丫回到民中以后,准备穿上红舞鞋练舞,却发现她的红舞鞋不见了。在乜小丫看来,丢了一双红舞鞋也没什么,大不了再买一双就是了,县城要是买不到,还可以托人在上海买。乜小丫只是在无意中把丢了红舞鞋的事告诉了老师。老师觉得可能是来我们学校交流,回去的时候走得急,把红舞鞋弄丢在我们学校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老师跟我们学校老师联系,问是不是有同学拣到了。没想到,我们学校老师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却把这事当做了一个大事件来处理。认为肯定是有同学偷了乜小丫同学的红舞鞋,这太给学校丢脸了。于是学校组织各个班的班委,准备对男女生宿舍进行突击检查,结果最先在马兰芳的床单下面找到了这双红舞鞋。那时,马兰芳还在教室里做作业,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会觉得。
捉贼捉脏,这由不得马兰芳不承认。当马兰芳从教室里被人喊到宿舍,她被眼前的事吓傻了,就差没有晕过去。马兰芳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即使喜欢乜小丫的红舞鞋,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啊!”有老师说:“问题是红舞鞋从你的床单下搜出来了,这你怎么解释。”这时候的马兰芳就只会哭,全然不像在舞台上演喜儿、演吴清华那么光彩照人。老师说:“你不承认也可以,那你能说出是谁拿来放在你床单下面的,这你能说出来吗?”马兰芳听了老师的话,欲言又止,就只会哭。老师说:“说不出来吧,说不出来那你就等着学校对你进行处分吧!”说完,一群人拿了红舞鞋就走。这会,学校领导来到校长办公室,正等着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就在校领导在校长办公室开会研究怎么给马兰芳处分,怎么把红舞鞋送到乜小丫同学手中的时候,吴星汉却像风一样的闯进了校长办公室。吴星汉说:“这事不怪马兰芳,乜小丫的红舞鞋是我拿的。我看到马兰芳跳舞跳得太辛苦了,舞虽然跳得很好,却没有一双真正的红舞鞋,我就动了要拿乜小丫红舞鞋送给马兰芳的心思。马兰芳真的没有错,你们要处分就处分我吧,我不怕处分。”吴星汉在校长办公室待了半个多小时,据说把细节说得特别细,他是怎么想的,怎么下手拿的,又是怎么把红舞鞋放到马兰芳床单下面的,都说得非常清楚,这由不得校领导不相信。校领导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你这就回去吧。还好你能够主动跑来承认错误,要不然我们肯定会给你加重处分。”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总算找出来了,应该可以了结了。可不少同学却开始问这样一个问题,又是谁最先告密的。要知道,老师带着班委去检查,可是第一个检查的就是马兰芳,就好像有谁知道乜小丫的红舞鞋就藏在马兰芳的床单下面一样。要不是有人告密,真要兴师动众的在学生宿舍找,不知要找多久,还未必能够找到。那谁是告密者呢?这知道情况的老师肯定不会说,告密者自己也不会站出来说。好在,吴星汉站出来承认是他拿了,是他放在马兰芳的床单下了。也不是要害马兰芳,是真心实意要帮助马兰芳一下,马兰芳舞跳得这么好,确实需要有这么一双好的舞鞋,尤其是红舞鞋。接下来就派生出了一些故事,都是说吴星汉和马兰芳好的。我也曾生出过这样的联想,要不然周末回家,马兰芳也不会跟吴星汉一道走,尽管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两家相距又不远。还有,但凡马兰芳跳舞,吴星汉只要能逮住机会,就一定会去看,一定会看得如痴如醉。联想到这些,同学们一致认为是吴星汉和马兰芳好上了,早就好上了。
学校给吴星汉处分的第二天,民中乜小丫的班主任老师带着乜小丫来到我们学校,说是要把红舞鞋送给马兰芳。班主任老师说:“前段时间,我因为出了一趟差,没有参加两校的联谊,感觉很遗憾。真是对不起,没想到会派生出这样的事来。有同学喜欢我们乜小丫同学的红舞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况且又不是马兰芳同学拿的,就更不要责怪马兰芳同学了。我听看过马兰芳同学跳舞的老师说,她的舞跳得很好,并不比我们乜小丫同学跳得差。还有也不要责怪拿乜小丫同学红舞鞋的吴星汉同学,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也是有原因的。听说你们要给他处分,我看就不要给了。一双红舞鞋,这也能算个事?”我们学校老师说:“这事确实不怪马兰芳同学,但吴星汉同学肯定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对他的处分已经作出了,昨天才宣布下去。”班主任老师看上去有些失望,停顿了好一会,才说:“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地撤消这个处分。”
民中班主任老师和乜小丫见到马兰芳的时候,马兰芳正在学校的洗衣台前洗衣服。她洗的是她的红衣服和绿裤子,还有那双红灯芯绒鞋面的平底布鞋。马兰芳平时很少穿这红衣服和绿裤子,还有这双红灯芯绒鞋面的平底布鞋,只有等到要上舞台跳舞了,才会穿上这身衣裤和这双布鞋。最近不会再跳舞了,马兰芳想把这身衣裤和这双布鞋洗干净晒干了放到箱子底。班主任老师和乜小丫看到这会正在洗衣服的马兰芳有些感动。乜小丫喊了一声马兰芳,马兰芳就把头掉过来,她看见乜小丫和一位老师正在向她走来。乜小丫和班主任老师来到马兰芳身边,乜小丫从她斜挎在身后的黄帆布包里把红舞鞋拿出来。乜小丫说:“那天跳舞我看见你没有穿舞鞋,我就应该把这双舞鞋送给你的。你看,我现在才送,是不是有些迟了?”马兰芳没有说话,这会在她的脑海里,是乜小丫穿着红舞鞋,尖着脚尖旋转着舞蹈。马兰芳曾穿着袜子试过,她也是能够把脚尖直立起来的。她要是能够有一双舞鞋,能够拥有一双像乜小丫脚上穿着的这样的红舞鞋,那她肯定会跳得很好,甚至会比乜小丫跳得还要好。乜小丫把红舞鞋递到马兰芳面前,乜小丫说:“马兰芳同学,我把这双红舞鞋送给你,等我买到新的,我还会送你一双新的红舞鞋。”马兰芳没有说话,也没有伸手去接红舞鞋。乜小丫把红舞鞋放在马兰芳前面的洗衣台上,回过头来就和班主任老师一道走了。乜小丫在心里想,她肯定会和马兰芳成为朋友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那天乜小丫和民中这位班主任老师来我们学校,正好被我看见了。那时,我端着一洗脸盆脏衣服,要去洗衣台边洗濯,正好看见马兰芳也在洗衣台边洗衣服,我就有些犹豫了。我这人有点懒,都有两个星期没有洗衣服了。自从学校出了这件事,红舞鞋退还给了乜小丫,给了吴星汉处分,同学们更感兴趣的是到底谁是告密者?联想到红舞鞋是吴星汉拿的,吴星汉又和我睡上下铺,因此我的嫌疑无疑最大。吴星汉甚至还把我喊到学校操场上,质问是不是我向老师告的密,那时我感到万般委屈,可吴星汉并不相信,直到我对天发誓,他才没有再追问下去。这段时间,同学们看我的目光都很怪异,好像我就是那个或许永远都查不出来的告密者。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过去洗衣服,就看见乜小丫和他的班主任老师,好像在跟马兰芳说什么,然后就从马兰芳身边走开了。这段时间,我确实有些混蛋,一见到乜小丫,我就会心跳加快。我端着一洗脸盆脏衣服从乜小丫身边走过,可她连头都没有斜一下,这怪只怪我自作多情。
马兰芳洗好了衣服,在洗衣台边站了好久,才端了装着衣服的洗脸盆,拿了乜小丫送给她的红舞鞋,准备回宿舍。我这会端着装满脏衣服的洗脸盆,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我这不是装,我也不会装。我在经过马兰芳身边时,和马兰芳打招呼。我说:“马兰芳,你洗好啦?”马兰芳只是侧过身子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说话。也许,她跟其他同学一样,也在怀疑我就是那个可耻的告密者吧。我感觉到了无助和没趣。我来到洗衣台前洗衣服,我用力揉搓着衣服,好像要把心中的不满都发泄到这脏污的衣服上。
后来,马兰芳和乜小丫就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只要周末不回家,要么马兰芳去民中找乜小丫,要么乜小丫来我们学校找马兰芳。她们在一起,会变得非常开心,她们谈学习谈人生,当然更多的是谈论她们喜欢的舞蹈。有一次,乜小丫忽然要马兰芳让吴星汉去看她们跳舞。那是民中组织的一个慰问演出活动,乜小丫跟老师说,要邀请马兰芳过来一道演出,并要吴星汉跟着过来看她们演出。慰问演出活动被安排在星期天,这并不影响学生上课,因此马兰芳和吴星汉都去了。自从红舞鞋事件以后,乜小丫就很想见到这个吴星汉。乜小丫就曾经对马兰芳这样说:“其实吴星汉很不错的。就算是他偷了我的红舞鞋,是一个贼,可我还是觉得他很不错。他偷我的红舞鞋完全就是为了你,这就不是一般的贼,而是一个义贼。我告诉你马兰芳,我还真有点喜欢这样的义贼。”
没过多久,学校就要进行期末考试了。因为那时我们读的已是初三年级,既要准备毕业考试,还要准备升学考试。据说我们这三个班的初三年级学生,最终只会招收一个高中班。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将会上不了高中。同学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该上课还上课,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休息还睡觉休息。但在私底下,早就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等考完毕业考试、升学考试,等拿上毕业证,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考试前,学校还请对面县城照像馆的摄影师,来给我们这些要毕业的学生照毕业照,先是每一个班的合影照,接下来是三个班在一起的合影照。合影照照完,也有自认为相处得很好的同学要合影留念的。我自认为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一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歹,不过我更没有钱,因此不想和同学照什么合影照。就在我准备回到宿舍的时候,吴星汉却拉住我。吴星汉说:“我俩睡上下铺整整三年了,以后还能不能够睡上下铺,甚至还能不能在一起读书都不知道。来,我们照张合影留个纪念吧!”我说:“我没钱,不想照。”吴星汉说:“谁要你出钱了?我已经出钱把票都开好了,我们这就赶紧过去照。”
这年快到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我收到了我们学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我重新收拾好行李来学校报到。还是熟面孔,我们这个高中班,就是由原来的三个初毕业班的部分同学组成。当然,也还是来了很多新面孔,学校又招收了二个初中班,这些新面孔和还没有毕业的初中同学,很自然地就做了我们新学年的学弟学妹。在熟面孔中我没有看见吴星汉,也没有看见马兰芳。我知道吴星汉和马兰芳的成绩很好,不应该考不上高中的。可我偏偏就没有看见他们。直到我们开始正式上课了,也没有看见吴星汉和马兰芳来报到,这时我才确信,他们是真的不会再来我们学校读书了。
前几天,我们当年在一起读初中和高中的几位同学,在一家名为“星汉酒家”的酒楼聚会,大家坐在餐桌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我知道,中学毕业已经四十多年了,到我们这个年龄,事实上已经很怀旧了。同学之间也很难得在一起,有的毕业以后就再没有相见;有的已经过逝,永远不可能相见了。偶尔逮着机会坐在一起,最容易想起当年在一起读书时的事情。不知是谁突然忆起了当年的红舞鞋事件。一位同学说:“还记得马兰芳不?她那舞确实跳得太好了。可惜了,她要是能上高中,毕业以后再报考艺术院校,或许真会成为著名舞蹈家。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又一位同学说:“吴星汉你们还记得不?就是那个偷了红舞鞋送给马兰芳的同学。他为什么要偷这双红舞鞋,据说那时两人正在谈着恋爱,他就用这双偷来的红舞鞋作为定情物送给了马兰芳。”还有一位同学说:“吴星汉和马兰芳没有读高中,是因为他们没有考上,还是因为他们读书期间谈恋爱,学校以升学考试不录取代替开除处分,这些现在都没有意义了。我倒是很想知道那个告密者是谁,却一直没有看见浮出水面,这怕要成为一个永久的谜了。”说完,在坐的几位同学都用不信任的眼睛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你们信不过我,莫非我还信不过我自己,我还真不是这样的人。”
同学们看见我好像有点生气,就说不说了不说了,告密者是谁并不重要?不要因为这个话题冲淡了我们同学聚会的氛围。我曾听说过,有不少同学聚会,本来是要叙同学情的,却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闹得不欢而散。就在这时,开这家酒楼的老板走过来,手里端着一大杯酒,对我们说:“我听你们谈论得好开心,同学聚会就应该这样。来来来,我敬你们一杯。你们刚才谈到吴星汉和马兰芳没有考上高中,是因为他们谈恋爱,学校本来是要开除他们的,后来采取不录取的办法,既让他们读不成高中,又避免了给他们开除学籍处分的尴尬。因为那时候的中学,是严禁学生谈恋爱的。这件事要放在现在,又能算个什么事啊!还有你们说到偷红舞鞋事件,不就是一双普普通通的鞋么?一双鞋是没有办法走完全部人生道路的,何况这还是一双只可以在舞台上穿的舞鞋。”我注意到了,我们坐在这里吃喝,这位老板就一直在大堂后面看着我们,看我们坐在餐桌边吃菜喝酒,听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叙旧。
在我们离开这家酒楼的时候,我好像才忽然想起,刚才来敬我们酒的这位老板应该就是吴星汉。难怪他要把他的酒楼命名为“星汉酒楼”,难道这只是一般的巧合,我才不相信呢!在敬完我们酒以后,还忽然对我们几位同学说,已经有人为我们买单了,还说要让我们放心地吃喝。我忽然想跑回去向吴星汉打听一下马兰芳现在怎么样?据说马兰芳后来并没有和吴星汉结为伉俪。这并不奇怪,现在大学生、中学生在学校谈恋爱,又有多少最终弄成的?可我又不敢确信这位老板真的就是吴星汉。要真是吴星汉,那他为什么又不跟我们认识呢?还有,我还想打听一下乜小丫的情况,可乜小丫那会只是属于我内心里的一个小秘密,这我又能够去向谁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