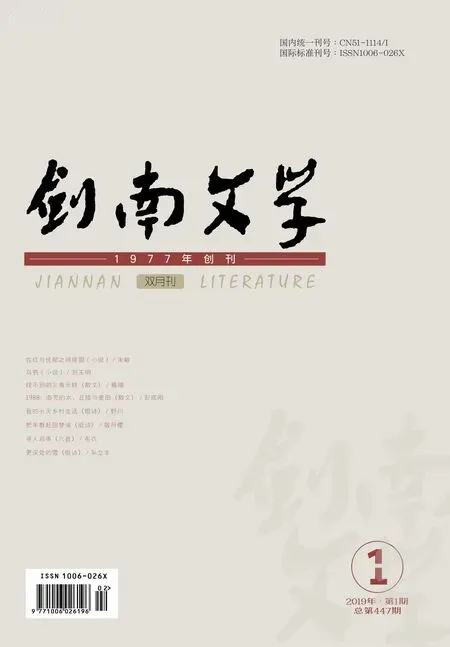作家沈从文是怎样炼成的
——读《沈从文的前半生》
2019-11-12王晓阳
□ 王晓阳
最早知道沈从文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教科书上。记得那个时期的现代文学史教材重点内容是“鲁郭茅巴老曹”等,沈从文没有像几位大家那样享受专章专节的 “待遇”,一般只在某个章节中寥寥几百字介绍,且评价较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内外对沈从文的评价越来越高,沈从文的知名度和地位也越来越高,甚至直追鲁迅。我也先后补课式地读了他的《湘行散记》《从文自传》《萧萧》《长河》《边城》等作品,有些震惊地发现,我的阅读竟然遗漏了一个重要大家。至此,“沈从文何以为沈从文?”“他的那些传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问题长期萦绕我心。
最近拜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所著的 《沈从文的前半生》及《沈从文的后半生》,我的这些问题似乎逐渐有了一些答案。
我们先说《沈从文的前半生》。一般而言,传记都是从开始写到最后。有意思的是,张新颖教授是先写的“后半生”,后写的“前半生”。据作者讲,开始是因为沈从文的前半生大家比较清楚,“有几种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没有必要重复。也可能是在那种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后半生更有研究价值,更为吸引读者,就像当年陆键东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样。
然而,当写完“后半生”后,张新颖的想法又有所改变。他以为,沈从文的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再看他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他又“抑制不下冲动”,倒过来写了这部《沈从文的前半生》。于是,在有了金介甫、凌宇等人关于沈从文的传记之后,读者又有了一部新视角的完整的沈从文传记。
《沈从文的前半生 》自1902年沈从文出生始,至1948年沈从文为悼念好友朱自清而作文终,讲述其间沈从文如何从一个湘西顽童一步步从小兵成长为文学青年,再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书中叙述了他的辗转流荡、传奇与平常、人格“放光”与精神痛苦。
有一个说法流行已久:沈从文没有什么文化,既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学,新近出版的《许子东的现代文学课》也说沈从文“读书少得多”。还有一个传说更是屡见书页报端:西南联大时期有个牛人学者刘文典恃才自傲,十分瞧不起沈从文,多次贬低沈从文。
其实,这是对“文化”的误解或者说把“文化”的概念限制得太狭小了。难道人生曲折的经历,对人世、社会、自然的热爱、领悟、思考、洞见,不是一种“文化”吗?沈从文喜欢把社会、自然这本“大书”与“教育”这个词相连。这个“教育”不同于旧式私塾和新式学校的“教育”,它概念既宽,影响也更根本、更深入骨髓。它是以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为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而进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过程。他说:“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要从一本好书好话上学来。”《沈从文的前半生》写道:“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世界的时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
而且,就以狭小的“文化”而言,学历不高的沈从文也并非文盲,更不是“小学文化”所能限制。《沈从文的前半生》对此作了丰富的叙述和引述。沈从文家学并不浅薄,他祖父沈宏富任过贵州提督,外公黄河清为本地贡生,任过《凤凰厅志》纂辑,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四岁时母亲就教他认字。
他在湘西当兵和从事其他流动职业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在姨父熊捷三家里,他看了很多字画和《说部丛书》,阅读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在熊希龄设立的“务实学堂”图书馆里,他翻阅过《史记》《汉书》和其他杂书。他听过姨父——凤凰名儒聂仁德谈宋元哲学。在随军移防川东的途中,他的小包袱里除日用衣物外,还有《云麾碑》《圣教序》《兰亭序》和《李义山诗集》。特别是在做湘西筸军首领陈渠珍书记官期间,他直接就住在有许多书画、碑帖、铜器、古瓷、古籍的大房间里,学到了许多知识,有机会从容认识接近“人类智慧光辉”。张新颖说他“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一点也不为过。
离开家乡到北平,沈从文认为是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唯其如是,他才会得到当时一批文化名人学者如林宰平、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肯定、关心和帮助,有的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也逐渐进入文艺圈子,写作品、编刊物,崭露头角。如果说沈从文被选聘到中国公学任教,可能是胡适的偏爱,那么后来他先后进入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与众多一流大师学者同时执教,就不能全说成是偶然和运气。至于与刘文典相关的那些传闻是否实有其事,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沈从文的前半生》,我们进一步知道,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大报编辑、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实际上具备有深厚宽广的文化积淀。
当然,深厚宽广的文化积淀可以让一个人成为学者教授,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或者说,造就作家沈从文还有许多其他要素。
1934年1月,沈从文离开湘西十年后从北京第一次返乡,看望病重的母亲。行前与新婚妻子张兆和约定,每天写信报告沿途见闻。此行对作家沈从文特别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另外一个类似时刻。1950年2月,22岁的哥伦比亚青年马尔克斯随同母亲一起回老家去卖房子,标志着世界级作家马尔克斯的文学生命由此开始——此行催生出他的第一篇严肃作品《枯枝败叶》。
沈从文的这次返湘之行同样非同寻常,既是一次身体旅行,更是一次百感交集的内心旅程。他写书信初衷也许只是想给张兆和写情书,但结果却远非“情书”所能限制,它是对湘西风土人情的细致描述,是对往日生命的回顾总结、对今后使命的确认和安排,也是沈从文思想的升华、写作的顿悟。至此,他已站上了写作的至高点,《湘行书简》《湘行散记》《边城》《长河》等一系列代表作也就相继喷薄而出了。
沈从文能成为一个著名作家,首先是与他丰富而独特的经历有关。他出生的地方虽为偏僻之地,却是湘西中心,往往得风气之先。这里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日常活动往往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异常美丽而幽静的自然环境之中,极其平常地上演着人类的各种行为,以至于自然的光、影、声、色,与杀人印象混合叠加,一并成为沈从文童年、少年记忆的主要部分,而童年、少年的记忆往往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题材。
和大多数顽皮儿童一样,小时的沈从文也逃学,为逃避惩罚,他“根据各种经验制作各种谎话”。被罚跪时,他往往开始想象各样动人的事物。他说:“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他从小对自然、社会这本“大书”产生出强烈的兴趣与冲动,身心亲近自然。同时,对日常人事和生活现象兴趣浓厚。上学路上喜欢观察小铺面、小作坊,留心民间手艺。
想象力和观察力,这都是一个小说家的重要素质。特别是在当兵的那段时间里。随着部队的不断移防,沈从文沿着家乡那条河流多次在两岸或者上下游移动,观察各种自然与人事,听到了各种传说与故事,这成为日后他创作中主要抒写的题材。
其次,沈从文对自然、对社会、对人充满了感情。他的作品老是写家乡那条河,他太爱它了。在《湘行书简》中,他写道:“我总那么想,一条河对于人太有用处了。我赞美我这故乡的河。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沈从文写的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很普通的、别人忽视的、遗忘的人和事,但这些东西就是历史深处的、有情的。他在《柏子》文末题记中写道:“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他的代表作品,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现故乡湘西,文字明净、节制,语气亲切、舒缓,有温暖的幽默,有宽厚的悲悯和爱怜。
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沈从文笔下这些人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这一点恰恰与五四时期主流文学的叙事模式区别开来。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启蒙,在许多文学叙事模式中,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第三,沈从文对文学非常执着。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说:“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慢慢地,这个心思变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就成了沈从文反复强调的“责任”。这个责任感,沈从文显然是越来越自觉的,并逐渐扩大到更广的范围里去。正如张新颖在书中所说:“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1942年,沈从文的写作宏愿不断涌现,尽管他的许多书受到审查删节,但他显得淡定而自信。他说:“据我想来,总有一天要战胜流俗,独自能用作品与广大读者对面的。”许多年轻时期的文学同行分道四散,沈从文却在这条路上持续前行。1980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许多人都比我机会好、条件好,用一种从容玩票的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无多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当然,也有觉得再写下去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终于为革命而牺牲的。也有些人特别聪明,把写作当作一个桥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是一个死心眼笨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界,才可能写出点比较像样的作品。”
文学是他生命中自然而然流出的一部分,尽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写下太多,但在最深处,他始终把文学放在一个最自我、最独立的地方,不希望受到任何外在的影响。即便是在和人辩论,他的文字也更像是在和内在的自己对话。
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十分自信。1934年1月,他在校对《月下小景》时写道:“我真为自己的能力着了惊。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必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除了创作,沈从文的文学观点也值得一说。1936年,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谈到《边城》:“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这篇文章还坦陈了他对写作的独特见解。他说:“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独断。”“这个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
该书最后一章名为“北平:一个有‘悲哀分量’的背影。”沈从文的好友朱自清去世,各方悼念文章很多,沈从文也写了 《不毁灭的背影》一文悼念亡友,特意肯定朱自清的“常人品性”“伟大平凡”。他说:“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
此话虽不能解读为沈从文夫子自道,但若说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投射,恐怕也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