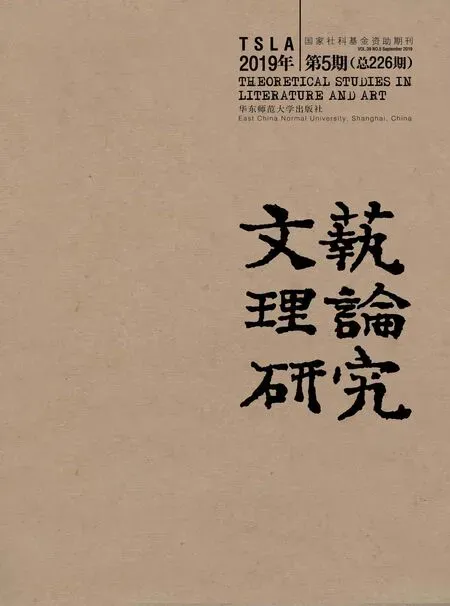狡黠装置与现代文学之痛
——柄谷行人文学论的一种视差性解读
2019-11-12韩尚蓉
韩尚蓉
引 言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下文简称《起源》)中将近代文学视为某种现代“装置”置入的结果,而自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到本世纪初的《现代文学的终结》(『近代文学の終わり』),乍看上去这似乎完成了一个从起源到终结的回环,实际上却暗含着他对装置这一现代产物的拒绝。事实上柄谷行人对“装置”一词并未做出系统的阐述,通常以“认识论装置”“透视法装置”“共同体装置”等形式出现,但通过他的使用也能够对之稍加界定:“装置”作为人工机巧区别于自然生成,是一种认识论策略,它意味着某种确定的权力关系及对认识限度的操控。用阿甘本的话讲,“装置具有一种支配性的策略功能”(Agamben2)。但与阿甘本在继承福柯的基础上更关注“装置”中的权力关系不同,柄谷更多将之视为一种特定的认识论范式,更关注对近代认识论装置之不证自明的揭示。这也正是“起源”所要追问之物。
让人怅然的是,起源只有在终结时才会稍显端倪。而柄谷又说,“我们已无法追问起源,因为向起源的拷问就已暗示出它的终结。”(柄谷行人,『意味という病』15)那么他一再强调起源与终结又意欲何为呢?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在写作《起源》之前,柄谷就曾脱出狭义的文学批评,从视差出发写作了《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マルクスその可能の中心』),而在《起源》之后又有《作为隐喻的建筑》(『隠喩としての建築』)和《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等对视差进行系统阐述。“视差”可看作视域之差,柄谷的“视差”建立在康德批判的基础之上(『マルクスの現在』120),强调先从自己的视点观察,再从他人的立场观察,并将关注点放在两者的偏差中,只有经由这种视角的偏差,才能破除“光学的欺瞒”。它由在视域间进行跨越所得,并随着主体与观察对象之间视角的不断变化而显现出来,但它并不止步于视角的本体论维度,更包含了基于主体立场的关系维度。换言之,在不同关系中进行立场的跨越成为视差的根本前提。齐泽克也在柄谷“视差”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应直面事物乃至人性自身中的分裂与差异,并以分裂的眼光(视差)辨认其中暴露出的现实(齐泽克6)。尽管在写作《起源》的20世纪70年代,柄谷还并未正式提出并系统阐释“视差”这一概念,但若考虑到柄谷同时期的理论创建,将《起源》置于这一脉络观之,则显示出与视差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是构成柄谷视差思想的重要一环。
由此,上文提及的两个疑问或许就能够被解答——起源与终结看似暴露在线性时间之两端,但却处于同一作用力的“场”中,即现代“装置”。换言之,现代装置作用下无论起源还是终结、理性还是感性、浪漫还是写实、建构还是解构,它们看似对立,实际上在辩证法的作用下相互补足并成其所是——这便是装置的狡黠之处。柄谷为此发出警醒,装置不仅仅止步于对现代文学的规制,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启蒙理性的产物,其中视差的缺失则将会导向现代理性制约下认识论的歧途。此时,视差所提供的辩证法的颠覆性内核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在视差的介入下,暴露出、跳脱出“装置”才得以可能。
一、 “装置”与闭合环路的形成
此前诸多关于《起源》的研究已经指出,日本现代文学的产生来自现代文学制度颠倒,主要表现为“风景”的发现——作为现代科学进步的透视法装置置入文学,内面风景作为主体意识被显现。柄谷对此“装置”的剖析,明确揭示出现代文学的产生有其历史性,它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将彼此相异的多样性消解进近代“装置”,并使其原本的存在被忘却。诚然,以往对柄谷行人所言“装置”的剖析也仅仅止步于文学的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多少忽视了“装置”本身及对装置之解构这种双向运动的内在含义。
在柄谷行人看来,至今“装置”似乎还作为一个隐微之物支配着文学及关于文学的诸多观念。他指出了关键的一点:“我在此所要考察的既非制度的目的,也非其意图,换言之,并非制度的内容,而是制度自身所具有的意味。”(『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193)作为“制度”的现代文学的产生有其自身历史性,它终将在滚滚向前的时间流中作为“过去之事”渐行渐远。那么在它已趋于终结之时,现代“装置”已经在当代解构思潮之下趋于瓦解的今天,它如何作用于现代文学就已经不再是目的。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如果对“装置”的解构恰恰与“装置”本身形成了一种相互对抗的双向运动,那么是否就可以将对“装置”的瓦解也同样视为“装置”运作的一个环节?这就涉及以下问题: 装置本身意味着什么?它在今天是否依然作为不证自明的内在机制制霸着文学乃至我们的思考方式?
基于这两个问题,需要将“装置”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而“现代文学装置”则正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既是一种主张,又是一个“症候”(Jameson xix)。解读“症候”虽不是目的,但也同样重要,通过它才能获得窥见其上的整个装置之全貌的可能。在现代,小说地位提升,它便不可避免背上了理性与道德的社会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文学是虚构之物,但却比一般被称为现实之物更能反映真实”(『近代文学の終わり』46)。换言之,之所以会产生现代文学中的透视法装置,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而应向加之于上的更广泛处追问。可以明确的是,柄谷称之为“透视法装置”之物从名称上就显现出与几何学不可割舍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可追溯到笛卡尔对“我思”(Cogito)的确立。
“装置”产生的第一条路径始于理性向绘画术语的不断蔓延——几何学透视法在写实主义文学与风景画中的置入。作为文艺复兴以来几何学在绘画中的奠基性观念,透视法一直强力支配着现代绘画的取景、布局等视图问题,直到照相技术产生才逐渐减弱。此处所言透视并非针对某一孤立对象之再现而采取的观照方式,而是企图在广阔空间中发现深度,并将之呈现为二维平面的作图方式。为此,潘诺夫斯基指出了这种于空间中进行纵深透视的两个条件: 其一是等质空间的成立,将空间视为均质、不变的连续空间为纵深透视提供了方法论前提——使中心视点能够置于等质空间中的任何一点成为可能;其二是消失点作图,将某一固定视点作为中心视点,而空间中全部景象最终都被这一视点吸收——使等质空间最终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为深度空间(Panofsky28)。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固定视点作图是为保证完全理性而在技术上采取的刻意真实的手段,但事实上“它只是纯粹的形式而非真正的现实”(30)。由于其建基于上的均质不变的连续空间是纯粹数学的空间,“透视法只是将心理空间转换成为纯粹的数学空间”(31)。换言之,那只是对心理空间的抽象而并非质的真实。
以此为基础,透视法作图作为“装置”被置入文学,并非如字面所言在现代文学中辅以透视法布局的近代绘画,而是将透视法所采用的“等质空间”“消失点作图”等手段作为观念来创作文学,柄谷行人称之为“认识论透视法的倒错”(「認識の遠近法的倒錯」)(『探究Ⅱ』221)。他指出,西洋文学史中存在一种规范性的转变——首先,在对象面上,描写主题转向普通人和风景,瓦解了原本崇高的宗教历史对象,这正是写实主义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在象征形式面上则采取透视法以期在二维空间中发现深度,表现手段转向以透视法为基础的“写实”——以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为手段,但正如上文中已经指出的,以透视法为基础的写实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甚至是反写实。如志贺直哉之类的私小说家正是看到了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虚假性,因而转向了对这层意义下写实的拒绝。而芥川龙之介则在小说《竹林中》(『藪の中』)中通过三种视角的交替,巧妙展示了“以透视法装置为基础的写实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虚构”(『近代文学の終わり』54)。
其次,与几何学透视法并行的第二条路径是现代哲学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对“我思”(Cogito)的强调。布鲁姆在谈及作家的自我影响时指出,英美文学传统在莎士比亚、但丁等伟大作家的脉络中形成,而“法国文学的奠基人则是一个哲学家”(布鲁姆30)——那正是笛卡尔。他将“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作为认识论的出发点,尽管这一命题至今为止引发诸多争论,但在17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向经院哲学的攻击中,对主体理性的确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它带来的结果自然是主体的确立,但另一方面也使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暴露出来,形成了主体-客体这一二元对立的结构框架。典型如瓦雷里在对17世纪风景画的研究中同样表现出笛卡尔式的追求——对“风景”的把握借助于意识对自身的力量,从而对外界疏远而暴露出极端的内心化。
当几何学透视法与实体化的“我思”相互纠缠时,作用于现代文学的装置便形成了——“我思”之主体与透视法之中心视点相重合。那意味着,自我意识的突显必须以将自我意识与周围“风景”相区隔为前提,换言之,“风景”的发现实际上显示出对“风景”的拒绝。因此柄谷讲“风景”的发现反而是“对现实风景的排斥,或是对现实风景完全不关心的‘内面的人’的外现”(『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35)。另一方面,由于消失点构图原本只是对心理空间之抽象的虚构,那么建基于以突显自我意识的主体为中心视点的文学尽管在形式上显现为“写实”,但实际上只是虚构,所谓“自我意识”也只是对“自我意识”的虚构乃至排除。所谓“颠倒”也就由此产生。换言之,前现代小说中的难题——“自我意识”的缺失——在现代内面小说中消失了。但并非意味着已被解决,而只是被柄谷称为现代“装置”之物隐藏起来。由于“装置”的倒错与隐匿,使被颠倒的对象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重新占据了其对立面的位置,并由此隐藏了装置依然被颠倒这一事实,形成了一个闭合环路——无论从被颠倒的哪一方,最终都只是通向它自身。正如柄谷评论中上健次小说《时空无限》(『地の果て至上の時』)时所言:“我们在弑父前,父亲就自杀了。”(《历史与反复》155)但那并非真的死亡,它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被置换到了“装置”的下层,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二、 “视差”之缺失与“场”的颠倒
至此“装置”中闭合环路已经形成,如果只是将这一被颠倒之物重新颠倒回来,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落入“装置”的陷阱。换言之,如果企图直面“装置”并反对之,不仅无法真正达到对“装置”的瓦解,反而会在相互对立的双向运动中成为对“装置”的强化。因而重要之处在于从外部解构掉“装置”这个倒错之物本身。柄谷虽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发现了隐藏在诸现象之下的“倒错”及造成“倒错”的“装置”。“倒错”一词最初来自斯宾诺莎对将人心的幻象视为自然预定目的这种目的论的批判——“这种目的论实把自然根本弄颠倒了。因为这种说法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本性上在先的东西,当成在后的东西[……]”(斯宾诺莎39)。
但发现“倒错”只是解构“装置”的必经之路,而并非柄谷最终目的。原因在于,首先,柄谷行人对“倒错”一词的使用一方面继承了斯宾诺莎因果倒置,另一方面,日语语境下的“倒错”一词,不仅具有颠倒之意,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怪异、反常的状态,而颠倒本身也是一种反常。因此这里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他对现代认识论装置的狡黠之处的暗示——被置于“装置”中乍看上去相互对立的两方实际上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极——无论“言”还是“文”“风景”还是“告白”“内面”还是“外面”,它们看似理性对宗教的胜利、“言文一致”对“声音中心主义”的胜利等,但这种胜利恰恰显示出它们随时发生翻转的可能。被颠倒的双方一方面是伴随着“言文一致”、透视法作图方式而形成的中心化体制,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反体制之物出现的“内面”“风景”。最终结果是二者相互渗透,表面对立的两极实质上已经连成了一个首尾封闭的圆环,共同强化了“装置”中内容物的倒错,现代自我的确立也正是建基于此。柄谷所批判的真正对象既非“内面”也非“风景”或所谓的“现代文学”,而是基于“装置”内部的颠倒而产生的自明性这种思考方式,从而揭示出任何样式的文学都有其历史性,所谓“文学制度”也不过是文学之历史性的自我复制。
另一方面,既然“装置”中看似对立之物拥有实质上的共谋关系,那么将被倒错之物重新颠倒回来就只会形成新的倒错。换言之,“装置”并非仅属于现代文学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缺乏视差的封闭结构中才会产生的倒错之物。“装置”之所以能够造成颠倒,并将颠倒隐藏起来,在于被颠倒的双方在实质上相互关联相互规定,无法仅从一个视角进行观察。日本现代文学仿佛自然而然地随着现代国家的成立而产生,外在形态上“风景”的发现却暴露出实质上视差的缺失,这也正是主体立场间关系维度缺失的结果。
“装置”是一种结构性的封闭场所,柄谷行人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下越过索绪尔、马克思及卢梭,将笛卡尔视为结构主义的祖师。笛卡尔从认识论上将“我思”视为自明之物,从而将其实体化。从“视差”之视点来看,对“我思”之实体性的批判并非因其中显示出亚里士多德的影子,也非将之视为形而上学唯心论的余音,而是实体化的“我思”具有了排他性,显现出对“我”之外他者的宽泛怀疑。因而柄谷指出“笛卡尔的‘思’中实际上缠绕着‘我疑’与‘我思’的模棱两可”(『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126),它肯定作为实体的经验性“我思”,又从中产生怀疑。“自我”与“非自我”此刻被置于对立的两极,围绕“我疑”与“我思”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场”——二者看似矛盾对立,实际上正因其矛盾而向内相互补足,向外排斥差异。
现代文学中对主体自我意识的强调正是通过对自我意识之外之物的排除而实现,所谓诸多“发现”则成为其前提。诸如“内面”“疾病”“儿童”的发现其目的并非在于发现并将它们突显出来,而是为了将它们与自我意识相区隔。它们原本与自我意识共存于混沌,但当自我意识开始主动抽离,将“非我”之物作为风景甚或自我意识的背景而发现时,那实际上意味着对“风景”的排除。柄谷所言“风景无视外部的人才能见出之物”(『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9)也正是此意义——所谓“发现”,恰恰暗含着一种拒绝。从这个角度来讲,现代文学只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翻转,而非创生,而恰好只有在缺乏视差的封闭结构中,这种翻转才得以可能。视差的缺失使如下翻转得以成立:
首先,“文”与“言”之间视差的缺失造成了由“文”向“言”的翻转。“言文一致”始终与“透明”问题相关——只有表现自我意识的能够发言为声的“言”是透明的,其余皆是障害。但柄谷却认为,根本的障害或许正是它的透明,原因在于,“言文一致并非言从于文,也非文从于言,而是新的言=文之创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45)。从制度上看,“言文一致”作为一种确立近代民族国家重要环节的官方运动,始于幕府末期前岛密上奏建言的《御请废止汉学之义》(1868年)(小森阳一25)。它最初作为一种反制度(就先前的汉制度而言)出现,倒错之处就在于当它一旦被确定下来,它本身就又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
从语法形式上看,只有在“言=文”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言及“自我表现”的可能,这意味着“自我表现”本身有其历史性。主要表现为语尾与人称的转变: 就语尾而言,原本指示主语与时态的与诸多语尾在言文一致中语尾被统一成“だ”,失去了其指示意味,因此在句中指示时间的状语以及指示主语的人称就变得不可或缺,以往绝少使用的“他”“她”以及中性的“我(私)”也开始频繁被使用。就人称而言,以往文语常用的“余”“吾辈”等自我指涉词在言文一致小说中全部统一为“我(私)”。可以说语尾的变化使现代小说产生了一个不得不言说的主体,即蕴含于主语中的“自我意识”,而主语对“我”这类中立指涉的使用则使“我”脱出了与他者的关系而成为中立的指示。换言之,视差从其中被抽离,小说中“だ”和“私”的频繁使用意味着关系的中立,这只有在均质时空中才得以呈现,此时的主体既非处于历史之流中的主体,也非与他者关系中的主体,毋宁说是一种由于对关系的拒绝而处于封闭系统中的主体。
其次,“外面”与“内面”间视差的缺失造成了由“外面”向“内面”的翻转。“言文一致”通过对新的言=文的创生发现了“内面”。但此处“发现”并非真的是发现其存在,而意味着认识论范式的转变,它让人产生这样的一种幻视——随着现代主体意识的增强,小说中人本主义关怀才第一次投诸个体。内面原本就存在,所谓发现“内面”不过是对“内面”与“外面”在“‘场’中的优先位置进行颠倒”(『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53),为原本无意义的“内面”赋予意义。此处的机巧就在于“制度”的创生,为了展现透明,就必须创出一个不透明之物。此处凝聚着“我思”的实体化及由此而来的区隔——通常言及某物为空时往往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某物为空但在结构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即空位),二是某物实际存在但不被看到或发现——实体化的“我思”作为不透明之物已经被先行置入结构中填充着某一位置,从而完成内面向外面的翻转。换言之,内面起初并不存在,但并非真的缺场,只是其存在并未被作为透明之物直接感知。
在这个意义上,与主体相互外在的“文”是不透明之物,而呈现内面并于主体形成新的结合的“言”就成了透明之物。针对这点,柄谷指出,所谓透明之物并非“言”本身作为对声音的书写,而“仅仅是自己能够听到或来自自己内部的声音”(『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72)。此处,表现内面自我意识的“言”原本作为不透明之物存在,所谓发现“内面”,不过是将原本内面-外面的“场”加以颠倒,使原本不透明之物变得透明。发现内面的过程伴随着对外面的批判,换言之,只有拒绝外面,内面才可能被发现,内面才可能成为新的外面;同样,只有排除不透明之物,内面才可能作为透明之物被呈现。如此一来,内面才第一次作为“透明的内面”被呈现,或者说这时被暴露出的内面已经作为了事实上的外面存在,而所谓“内面的人”实际上就成了没有内面的人。内面-外面这种“场”的颠倒中,内面完成了对外面的排除,更进一步,完成了对与外面之关系的排除,使自身沦为丧失视差的封闭结构。
与此相关,“内面的人”的发现,同样是内面-外面在装置下翻转的结果,其成立的手段是“告白”。但重要的并非告白之内容,相反,“告白”被放入翻转的装置中,借由一种结构性错位而实现。内面的发现主要是在私小说中,无论是山田花袋的《棉被》(『布団』)还是国木田独步的《不欺之记》(『欺かざるの記』),又或是德富芦花的《不如归》(『不如帰』),对肉欲的告白成为其中共同的主题。但问题在于,所告白之事却并非已经发生之事,而是由于内面-外面的翻转中被暴露出的内面,换言之,告白的并非是显现为外在的“肉欲”,而是对“肉欲”的压抑,是内面的自我意识。其中暗藏着的同样是“我思”之实体化的暗流。实体化的“我思”已先行占据告白主体这一位置,因此必须创造出一个与此相对的告白之内容的空位。正所谓“他们势必持续注视着内面,而内面也正因这样的注视而得以存在”(『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110)。因而重要的并非告白之内容本身,而是告白之形式。当告白一旦完成,内面-外面的装置就得以被翻转,仿佛告白之内容一开始就与主体休戚与共。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装置的力量,原本意欲通过告白而诉诸的“自我意识”也不过是对“自我”的排斥。
可见,无论是“言”与“文”的翻转,还是“内面”与“外面”的翻转,又或是因翻转而得以成立的诸身份,始终是处于同一“场”内的颠倒。原本内在之物被对象化而突显出来,似乎显现为对某物的发现,实际上只是一种结构性错位——先创造出一个位置,然后再由某物来填补它。因此显现出自明性的“言=文”“儿童”和“疾病”等就成了填补结构性匮乏的替身。正如那个被杜尚摆入美术馆的小便池,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品并不在于它本身有何特质,只因在结构中占据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因此,现代文学的真正立足之处并不在于它传达了何种精神和观念,而在于它如何被表述出,即柄谷所言“装置”之意味。但这种翻转成立于缺乏视差的封闭体系中,实体化的“我思”带来的是“心灵与现实的直接短路”,也即齐泽克所指出的“启蒙的悖论”——“只有当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只有当人类被化约为一种现实因素时,真正的现代性才应运而生”(齐泽克272)。这意味着在近代装置的彻底关闭中,人类心灵因被剥夺了直接感知而彻底自然科学化。所谓“短路”正是柄谷所指出的现代装置的倒置,是在一个封闭的“场”内部才会产生的结果。
三、 论争的必要与徒然
致使现代文学产生的正是现代这一深度装置,其根源要在文学之外寻找,而现代文学本身则成为“装置”之作用的一个症候——恰因其虚构性而暴露出无法被隐匿的现实,即暴露出原本被隐藏而宛如不证自明般的制度原本只是现代装置作用的结果。如果现代文学中的一系列翻转都被视为封闭装置中的结构性翻转,那么就产生了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为何这样的装置结构会造成翻转?它又是否存在越出的可能?事实上这一问题也一直贯穿于柄谷理路的始终,他指出了伴随着现代文学而始终存在的两个争论,一是关于理想,一是关于情节,二者都企图反抗透视法装置。但他并未止步于展示这两种争论,而是“意图将之作为症候来解读”(『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29)。换言之,关于理想与情节的争论,并不在于有理想还是无理想、有情节还是无情节孰可孰不可的问题,而在于争论本身的形态问题。柄谷试图借此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 相互对立的两极本身就构成了“装置”,二者间的争论更强化了“装置”的稳定性。它们暴露出存在于现代文学背后的某种支配机制,为我们在现代文学已经终结之时能够更彻底地回顾与反思提供了契机。
首先,就“无理想之论争”而言,焦点在于小说中的深度问题。已明确的是,近现代文学中所谓“深度”不过是通过特定的透视法装置置入其中的结果。但更值得深思之处在于,为何这种原本与文学毫无关联之物一旦置入其中,就变得不证自明,甚至成为决定文学价值基准?为此柄谷强调,“我们必须重新检讨透视法这种装置,因为这不仅是绘画或文学中的问题,更显示出与‘视角’问题的诸多相关性。”(『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06)此处柄谷将透视法问题在根本上看作视点的问题,装置的发现、对倒错的重新颠倒都需要“视差”的介入。
“无理想之争”主要在森鸥外与坪内逍遥之间,围绕如何抵御透视法装置的问题而起。坪内的理想是拒斥文学中的某一中心点构图,因而他拒绝深层,而森鸥外则试图“从某个‘消失点’看穿文本并将之重新配置”(『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21),企图在拒绝透视法装置的同时找到另一个中心点来编排时代精神。但由于他们的拒斥终究都基于透视法配置,即结构中的颠倒与回环,因而实际上并未脱出受到封闭结构配置的框架。原因在于,反对消失点构图的远近法不能直接从其对立面着手,例如提出“反现代”,原因在于对立与矛盾只出现在同一结构中,以对立的姿态正面反击相反并未越出消失点构图的远近法结构。相反,那只是“理性层面的恶斗”(知性上の悪闘)。
其次,就“无情节之论争”而言,焦点在于小说中的情节问题,主要是芥川龙之介与谷崎润一郎围绕“小说中是否需要情节”进行。芥川认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与艺术价值并没有必然联系,而谷崎则认为情节的组合方式有其自身美的体现。二人的观点乍看上去相互对立,实则存在着微妙的龃齬。原因在于,芥川所言的“情节”是能够进行深度透视的结构,他认为日本的私小说虽也在如实地描写“我”,但那实际上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我”,甚或是“无我”。他看到支配着近代小说的深度透视法装置,将私小说视为对现代文学装置的反抗。而谷崎所谓的“‘情节’则是指诸如前现代的‘物语’”(『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42)中的故事,同样是缺乏深度装置与单点透视的文学样式。在这个意义上,两种乍看上去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殊途同归,即二人都试图对透视法装置制霸下的现代文学进行反抗。他们忽略了“小说与物语的明显不同在于它是近代的产物,其关键在于‘现代’这一形式”(『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38),因此试图在小说中反对“现代”装置就带有了先天的不彻底性。
更进一步,无论是私小说对基于等质空间的现代透视法装置的反抗、对现代意义上“我思”的非实体化,还是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对私小说中异质空间的反抗,始终都未脱离“理性-非理性”这一公式般的概念框架——那样的反抗“无论何者都是在作为制度的‘现代文学’内部作为其产物而进行反抗,因而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或者说是从相同之处而产生的分歧”(『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43)。就此而言,无论是私小说还是物语,只要它们都还处于“现代文学”这一制度中,就无法颠覆作为制度的现代文学,相反,这些争论反而会成为巩固现代文学装置的活性剂,对之起到补全作用,反构成现代文学中的一环。
使论争陷入“两难的困境”的不是其他,正是视差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抗争双方仅仅站在系统内部展开批判反而会陷入与其批判对象同样的陷阱中,“以论争和对立而形成问题的形式来揭露某种现象地同时,也必定会造成遮蔽”(『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14)。为此重要的从认识论上对其加以怀疑。“我思”的实体化则意味着矛盾、辩证的前提是其双方处于同一体系内部,处于一个封闭的循环中,因而在起始时就已看得到终局。如此一来,不仅论争会陷入虚无,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为此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坚持视差的立场,更确切地说,是在“打破共有规则前提之下的与他者的对话”(《作为隐喻的建筑》97)。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柄谷坚持“我思”的非实体性——当“我”被言说时,所指涉的并非是作为实体的我,只是提供了一个“言说场所”,一个基本的自我怀疑的场所,但同时它不能被明确言说,否则便功用尽失。
结语: 作为症候的起源与终结
“起源”是只有在终结处才得以回望的“风景”,那么同样,当开始追索起源问题时,就意味着它已走向终结,因此现代文学的起源是只有在终结之时才能窥见其中所谓装置的机巧。望见起源的柄谷是焦虑的,但他的焦虑并不在于透视法装置在现代文学中的置入,也不在于其中“风景”“内面”的发现,抑或是“言文一致”对现代文学造成的颠倒,因为那已经是线性时间中逐渐后退的往事。柄谷虽遗憾地宣称“现代文学已经终结”,但他深知对这一既成事实感到痛惜依旧于事无补,因为既有起源,就会有终结——辩证法在此刻发挥着统摄全局的力量——终结是伴随着起源就能够预见的事,是终将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真正让柄谷感到焦虑的是辩证法的强大,矛盾对立的双方在根本上似乎事出同源——“言文一致”是在“言”与“文”的相互拉扯中新的“言=文”的创生;“风景”与“内面”的发现伴随着事实上对内面风景的拒绝;甚至站在对立立场企图反抗远近法装置这一结构力的私小说,本身也已经进入了这种结构力的装置中。换言之,透视法装置成为制霸着近代文学的深层布局,正是在破坏深度的动机之下,将原本的深层重新置换为表层,发现透视法这一过程可被视为“深层的发现”,但柄谷指出,这种发现“所注视的不过是所谓的表层,并且试图以此来解构层级化的透视法”(『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10)。可见,对透视法装置的发现本身,亦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知的透视法”(知的遠近法)才得以实现,因而无论如何最终似乎都回到了“透视法”的配置当中。从“我们存在于浪漫派之中来否定自身”中,布鲁姆看到的是“影响的焦虑”,而柄谷看到的则是结构力的“场”的焦虑。他试图揭示的,并非现代文学的起源过程,也并非试图对现代文学加以批判或惋惜,而是这种由结构力的“场”而形成的透视法装置本身。同时,如果不从外部突入,仅仅站在某种特定的透视法的对立面进行反攻,最终只能是处于同一“场”之内的颠倒,反而会对这一结构力的“场”起到补充和活性化作用,无论如何反抗,都无法摆脱在这一“场”中反复循环的宿命。
为扭转这一局面,仅仅在“场”的内部,在反对方的对立面反抗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跳脱出结构力的“场”,从外部将其瓦解,即需要“视差”的介入。换言之,需要跳脱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深层—表层、主体—他者、建构—解构等二元对立结构力的“场”的思维模式。柄谷对此的理想是消灭所有文类(ジャンルの消滅),但那并非在现实意义上消灭掉所有文类,而是使之重新回到克尔凯郭尔所言“异质共振”的状态中。在柄谷看来,文学是脱出某种特定制度规制的纯粹自然,同时也无法仅从某种既定视角来考察之、规范之。在此他借助巴赫金对拉伯雷与果戈理小说的分析,认为“那正是根本上与现代小说相异质的‘狂欢的世界感觉’(カーニバル的な世界感覚)”(『文学の衰滅』389)。在这种残存状态中,深度与层级关系被瓦解,由单点透视作图而被排除在外的他性被重新纳入其中,从而显现出游移的、异质共振的狂欢状态——“这些被引入的视差在不同位置之间形成不可化约的分裂与纯粹性裂缝,其中暗藏着诸多新的维度,而非一个位置相对于另一个的确定位置”(齐泽克31)——无以特定的命名对之加以统合与辨析。而在这个意义上,文类也必须被消灭。
就今天的情况来看,文学重新回到了拒绝深度、拒绝情节,并以此获得世界的狂欢化这一状态中。如此,就赋予了“现代文学的终结”两层含义,其一在于,当代的文学在形式上又重新回复到前现代那种无深度、无情节的状态中;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解构浪潮对透视法装置的瓦解,文学被卷入文化全球化激流。世界各地的民族同一性已经深深扎根,“尽管文学曾经为此作为不可或缺之物,但已经不需要再以想象的方式形成同一性了”(『近代文学の終わり』49)。现代小说曾受制于以民族主体性为视点的透视法图式已漫无边际四散开来,可以说现代文学的终结有着比其产生时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对此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如果说现代文学已经终结,那对居于上位而因此获得整体性的文学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柄谷发问道:“物语消亡了,但人们征服‘物语’了吗?”(『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229)或许我们能够将此疑问置于文学的语境下——现代文学终结了,但人们征服“文学”了吗?柄谷曾以颠倒的方式试图解构现代认识论装置对文学的制霸,但同样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对文学的讨论始终都没有跃出解构—建构—再解构的结构力装置,那么还有必要在这种无限循环中继续讨论文学吗?尽管现在对这一问题尚难以有所定论,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跳出定式,寻找一种新的文学乃至艺术的组织模式指出一条可供反思的路径——理论之后还有理论吗?文学之后还有文学吗?在这个意义上追问起源或终结都并非最终目的,相反,它们作为症候暴露出了看待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有其自身的历史性,只是被建构的产物。尤其在今天,当我们一脚已越出“文学”之时再回头审视,会获得更加清醒的目光。
注释[Notes]
① 柄谷行人原著标题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大辞林》(第三版)中将“近代”解释为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后,尤其是具有市民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时期,就日本来说,是指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而太平洋战争之后则被称为“现代”。李欧梵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指出,“近代”一词原本从日本转借而来,当时日本人用“近代”(きんだい)指代我们通常所言“现代”之意,是为说明西方文明如何被引进的问题。以此为背景,在参考赵京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译本的基础上,若非特殊注明,本文中统一使用“现代”来指柄谷所言及的“近代”。
② 最初连载于《群像》杂志(1974.4~9),随后柄谷在耶鲁任客座教授期间,以结识保罗·德·曼为契机进行了改稿,后于1978年出版单行本。
③ 柄谷1980年留任耶鲁比较文学系研究员期间写作,连载于《群像》杂志(1980.1~8),后与《作为差异的场所》(『差異としての場所』)、《内省与溯行》(『内省と遡行』)等共同作为底本出版《定本 作为隐喻的建筑》。同时间在《群像》杂志陆续发表的还有后来收录于《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的《关于构成力的两个论争》(『構成力について―二つの論争』)。
④ 其中柄谷从认识论角度系统考察了“视差”,将之追溯到康德与马克思,并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跨越性批判”(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transcritique])。
⑤ 透视法,日文汉字写作“遠近法”,赵京华《起源》中译为“透视法”,而台湾吴佩珍译本则译为“远近法”,本文根据汉语使用习惯并参考赵京华译本采取“透视法”这一译法。
⑥ 詹姆逊在英文版《起源》序中将柄谷对装置的发现视为一种通过文学批评而链接到理论的多元主义斗争的“症候”(Jameson vii-xx)。
⑦ 柄谷将结构主义视为从形式化的现代理性中输入的概念,并认为在此意义上,结构主义的祖师并非索绪尔或马克思,更不是卢梭,而是笛卡尔。参照柄谷行人『探究Ⅱ』(1994年,東京都: 講談社),第98页。
⑧ 柄谷在《小说方法的怀疑》一文中借用小林秀雄此言,以说明在现代小说内部反对现代小说实为不彻底之举。参照柄谷行人「小説の方法的懐疑」(2018年,『意味という病』,東京都: 講談社,所収),第238页。
⑨ 柄谷行人在《现代文学的终结》中从文学、传播媒介、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趋势等角度详细阐明了他关于“现代文学已经终结”的观点。参照柄谷行人『近代文学の終わり』(2005年,東京都: インスクリプト)。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gamben, Giorgio. “What Is an Apparatus?”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 Trans.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24.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剖析: 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6年。
[Bloom, Harold.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 Trans. Jin We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6.]勒内·笛卡尔: 《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
[Descartes, René.Discourse
on
the
Method
. Trans. Wang Taiq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Jameson, Fredric. “Foreword: In the Mirror of Alternate Modernities.” Kojin Karatani.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 Trans. and Ed. Brett de B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vii-xx.柄谷行人: 《作为隐喻的建筑》,应杰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Karatani, Kojin.Architecture
as
Metaphor
. Trans. Ying Ji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1.]——: 「文学の衰滅」、『定本 柄谷行人文学論集』。東京都: 岩波書店: 383—93、2016年。
——: 《历史与反复》,王成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History
and
Repetition
. Trans. Wang Che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1.]——: 「マルクスの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マルクスの現在』。京都: とっても便利出版部: 117—62、1999年。
——: 「マクベス論」、『意味という病』。東京都: 講談社: 9—66、2018年。
——: 『定本 近代文学の起源』。東京都: 岩波書店、2008年。
——: 『探究Ⅱ』。東京都: 講談社、1994年。
——: 「小説の方法的懐疑」、『意味という病』。東京都: 講談社、232—45、2018年。
——: 『近代文学の終わり』。東京都: インスクリプト、2005年。
——: 『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東京都: 岩波書店、2010年。
小森阳一: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
[Komori, Yoichi.Critique
of
Modern
Japanese
Language
. Trans. Chen Duoyou.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Panofsky, Erwin.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 Trans. Christopher S. Wood.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巴鲁赫·斯宾诺莎: 《伦理学》,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Spinoza, Baruch.Ethics
. Trans. He L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斯拉沃热·齐泽克: 《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Žižek, Slavoj.The
Parallax
View
. Trans. Ji Guangmao.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