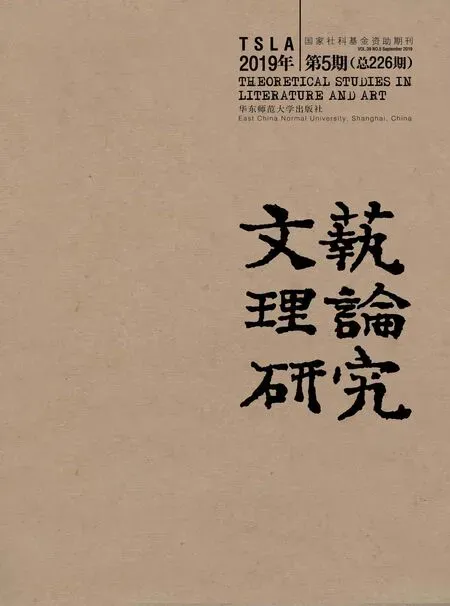作为打开欧洲“未思”的手段
——朱利安中国古典美学建构之解析
2019-12-26韩振华
韩振华
想要批评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或译余莲、于连),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倒不是因为他的大量汉学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声誉,而是首先因为,朱利安的学承和研究经历足以保证他是一位在汉学领域并不存在知识欠缺的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位文体写作高手,对于中国与欧洲之间“间距”(l’écart)的把握、以及对于自己文字可能产生的接受效果有着准确的拿捏。他的著作产生的影响力,早就越出学院派汉学家圈子,在专业哲学家(如保罗·利科、阿兰·巴迪欧)、艺术家、政治分析师、企业管理者直至普通读者那里都收获了大批拥趸。尤其对于汉语学界中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中国美学和思维方式的学人来说,朱利安似乎巧妙而又充分地说出了他们长期想说却说不出来的中式玄妙与精微!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朱利安成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此,批评朱利安,倘若没有更深层的思想立意和自我反思的勇气,不进行一番抽丝剥茧的去蔽工作,极容易因为勉强、轻率而滑向逻辑紊乱。
在朱利安所有涉及中国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内在线索,这条线索也是其基本方法论: 他关注中国,但全面阐明“中国”并非其根本宗旨所在;实际上,“中国”在他那里只是“方法”,并不是目的。他采取的是一种“迂回”(détour)策略,即在中国和欧洲“无关性”(indifférence)的预设之上,将中国视为欧洲的文化“他者”,通过观察中国来迂回地透析欧洲自身的褊狭,通过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促进欧洲思想的自我更新和拓展。多年来,朱利安的汉学研究一直致力于“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迂回与进入》“内容提要”4),因此,在其论证中,“作为哲学研究工具的中国”成了“欧洲”的对照/对立面,二者之间的所谓“无关性”成了事实上的对极化。就此而言,朱利安研究进路已经偏离了欧洲传统汉学追求百科全书式呈现中国面貌的“语文学”(philology)大传统,而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哲学化”色彩。
这种借用和发挥“中国”的方法论,在朱利安讨论中、欧思想“间距”的《势: 中国的效力观》(1992年)、《曲而中: 中国的意义策略》(1995年;中译本《迂回与进入》)、《道德奠基: 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1995年)、《圣人无意: 哲学的他者》(1998年)等著作中,文字层面还留有几分论断的审慎,个别章节甚至还包含了对于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种批评意味。然而,当我们面对朱利安《淡之颂: 论中国思想与美学》(Eloge
de
la
fadeur
:A
partir
de
la
pens
ée
et
de
l
’esth
étique
de
la
Chine
)、《本质或裸体》(De
l
’essence
ou
du
nu
)、《大象无形》(La
grande
image
n
’a
pas
de
forme
:Ou
du
non
-objet
par
la
peinture
)、《美,这奇特的理念》(Cet
étrange
id
ée
du
beau
)、《山水之间: 生活与理性的未思》(Vivre
de
paysage
:Ou
l
’impens
ée
de
la
raison
)等专门论述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著作,我们读到的则是对中国毫不吝啬的赞美。与“间距”并生的审慎完全消失了,有的只是纵情的拥抱、投入与沉浸其中;或者说,他沉浸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之中,以至于久假不归,“中国”反客为主地成为“目的”。何以如此?是因为面对体现于艺术思想中的中国“感性学”,必须投入更多的情感和爱/亲密(amour/l’intime),以致策略性地忽略了那些借助理性反思方能察觉的藏污纳垢之可能性?还是这些中国美学和艺术论著,相比于朱利安的其他论著,更为如实地展现了他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正看法和态度?解答这些问题,必然会将我们带向对于朱利安中国美学建构的批判性阅读。
一、 遮诠、他者性与中国美学


在《淡之颂》中,“淡”对应法文词fadeur(乏味、平淡、暗淡),但“淡”作为中国美学重要品格而被推崇的那层价值意味却无法通过包括fadeur在内的欧洲语言而得到正面言说。在中、西比照意义上,朱利安径直认为“淡”的更好表达是“遮诠”式的“无-味”(《淡之颂》的日文译本亦将fadeur一律译为“无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大”,不在于其“声”“形”这些特殊的“现实化”“外在化”形式,而在于尚未“外在化”“现实化”时的事物,才是包蕴一切可能性、因而也是内寓无穷变化的状态。中国的绘画、雕塑、书法、诗歌、音乐,甚至道德修养境界,莫不以此状态为尚。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意义的方式也是如此。朱利安在书中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 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75年从中国旅行回来,在《中国怎么样?》这本小册子中说,中国人表达意义的方式“朴素到甚至很罕见”,从而他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场域,一个极细致的场域,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个平淡的场域”(《淡之颂》3),这使得到访中国的欧洲人必须“把象征符号的骚动抛到脑后”。然而,出身于欧洲文化的巴特似乎无法完成符号的完全倒转,他不敢(或不能)在正面意义上谈论并肯定“平淡”。朱利安认为,巴特已经察觉到“平淡”这一对于欧洲而言“新的场域”,但终究失之交臂,无法深入领悟这一场域,从而遗憾地错失了一次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打开“间距”的机会。
在朱利安看来,“淡”,意味着“一种从不强调的感觉”,而是“任由现象和境况显现,但绝不让人们受其牵制”(《淡之颂》99)。古代艺术中那些具有“远渺”“萧散简远”风格的作品,往往是通过暗示(而非西方符号学意义上的“象征”)来呈现,“笔画”“味”“景”指向的是“笔画之外”“味外之旨”“景外之景”。这与那种突出“豪放奇险”、洋溢着激情与眷恋之强力的艺术风格(如韩愈的诗,张旭的草书,王蒙的画)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后者往往是艺术家“生存焦虑”的产物,“它唤不起精神的深度”(《淡之颂》129)。二者风格迥异,前者由“之外”引向一种超越性,而后者“并不导向意识的超越”(《淡之颂》132)。尽管如此,二者又共同具有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思想的一致特征——“内在性”: 那些涌现激情的艺术作品往往最终引出一连串的幻灭,指向的其实是“在世存有”,而非某种“出世感”。而在平淡风格的艺术作品中,“那个邀我们去的‘之外’并不是形而上的。它就是此世,——但这是在浑浊沉淀下来的、从现实里释放出来的、重获清新的(独一无二的)此世。”“之外
就在其内里”。“这种淡而无味将人的意识带领到现实的根源
,带回到事物从它开始演化的那个中央
”。总之,平淡的“超验性并不会领我们到另一个世界”,“不需要信仰即能获得”(《淡之颂》106、139—40)。不难看出,《淡之颂》始于中西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上的鲜明对照,亦终于朱利安朝诵暮念的中西文化对话点,整部书呈现出“始卒若环”的述说结构。也可以说,他是借“平淡”这一美学话题操演了一番其独特的中、西文化间谈(dialogue des cultures)主张。看清了这一对照研究框架,当我们面对《本质或裸体》《大象无形》等后续著作时,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抓手”。比如说,在西方,正是因为“裸体”之美具有极致的显露(révélation)本质的能力,这种“自明性”(évidence)使得裸体能够沟通“本质”与“表象”,从而调和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中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紧张关系,所以裸体在西方艺术中一再得到表现。而在中国重视“过程”的内在一致性思想中,裸体并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而且,静态孤立的裸体无法相容于中国绘画崇尚的“气韵生动”原则,呈现裸体所追求的强烈彰显和绝对明晰也与中国绘画暗示自然无穷微妙运化的模糊与转瞬即逝针锋相对。总之,在非形而上学、非二元对立、非象征喻指的中国,裸体是“不可能的”(《本质或裸体》49)。
之所以用“遮诠”这一术语概括朱利安的中国美学论述,一方面是要点出朱利安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受道家以及中国化佛教影响的美学观念,而道、释二家本来就偏爱“遮诠”式的论述,另一方面(也是在方法论上更重要的),是要揭示朱利安专擅在中、西之间设立对照,认识、诠释中国的前提是先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传统观念加以悬置甚至否定,而这样做正契合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合力倡导的“他者性”观念。事实上,朱利安目前正荣任法国人文之家世界研究学院“他者性讲座”(Chaire sur l’altérité)教授,这一称号确乎是实至名归。
二、 自我指涉,或后结构主义的中国“变种”
从中国美学的真际来看,朱利安对中国美学的发扬,当然是极富洞见的。然而在客观上,这种遮诠式“发扬”对中国美学的建构过于后现代化了,而且带有显著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ce)。有意思的是,朱利安主要将这种“他者性”安置在中、西之间,而不愿意将它置于中国美学内部。恰恰相反,他在中国美学中发现的似乎只是内在一致性。即就《淡之颂》一书而言,前文曾论及的,朱利安认为中国美学中的“平淡”与“非平淡”统一于“内在性”之中,就是一例。又如,关于儒、道两家,朱利安当然知晓二者“思想核心、概念或语言的差异”,但他认为,“我们不应再深究他们之间的差异,而应去探讨那个支持他们之间的共同之本,那些容许他们对话的共通点”,亦即“寻找出这两派思想赖以形成,却从未质询过的自明底蕴
”,而这一“自明底蕴”就表现在“非-形而上学”和“非-本体论”(《淡之颂》27)。事实上,在朱利安那里,它岂止是儒、道两家共享共通的,也是整个中国古典思想的共同基础,以及展开中西对照的“出发点”!然而,中国思想的复杂性似乎不容许如此纯化(也是“简化”)的概括。举一个例子,在考察先秦兵家著作《鹖冠子》时,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 Graham)认为其中就存在着一个抽象、超越的“泰一”(《鹖冠子·泰鸿》)(Graham40)。这个“泰一”当然不会跟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共享所有特征,但显然也无法纳入朱利安的论说框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朱利安所采取的“曲而中”方法论本身具有什么致命缺陷(恰恰相反,这一方法论本身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而是在于朱利安的中国美学论述具有太强的自我指涉性。如同《淡之颂》“原序”所说,“平淡”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一经发现,它就“往四面八方开展”,“而且跨越了好几个其他的研究领域”,逐渐洇染、漫延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是,“淡”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美学特征,甚至是本质特征。而“平淡”的这种“开展”“跨越”,极有可能就是自我指涉性的开展与跨越。当“淡”被述说成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时,也就是这种自我指涉性从“局限在博士论文的一章中的一部分”而发展、流溢成“强论述(strong argument)”时。
这种自我指涉性最为突出地表现在: 朱利安的中国美学解读方案听上去更像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某个“变种”或某种改写,这让人怀疑朱利安对中国的呈现是否更像一种“发明”。恐怕再也没有比《大象无形: 或论绘画之非客体》一书所建构的“非-客体”(non-objet)、“去本体论”(désontologie)更为典型了。

朱利安所揭示的“中国人的第一哲学”,注目于“源“上游”“基底”“理(cohérence)”,旨在呈现宇宙的“呼吸(翕张)”逻辑图式,而与欧洲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式”或“神学式”的超越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大象无形》一书中,朱利安明言: 《道德经》所谓“大象无形”,“无休止地言说着那处于正在现实化、即将分化和对立的东西在上游的共存(coexistence)”,而“现实化”“分化”“对立”则是与“再现”逻辑相伴随的诸种表现。这是因为,“再现”依据的原则是“相似性”(la ressemblance),而“相似性既预设了个别化,同时又预设了规定性”(《大象无形》111,113),所以相似性一经明确下来,便因为受到规定性的阻碍而同时使得事物之间的关系变成强制性、排他性、束缚性的,从而干扰/损害了“大象”这一实在样态(modalité du réel)的充沛漫溢(débordement;令客体消失)。就此而言,《大象无形》书名副标题中的“‘非-客体’(non-objet)所质疑的是再现的身份,邀人去思考位于分化之内的未分化(l’indifférenciant)”,而书中多次出现的术语“‘去本体论’(désontologie)操作最终需要在语言里为这个‘去’(dé-)开辟一条道路”(《大象无形》5—6)。这些论述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联想到福柯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宗旨和方法论;特别是以“相似性”理论对《道德经》第六十七章“道大,似不肖”一节的解读,看起来更像是福柯《词与物》一书某个章节的直接改写。有意思的是,福柯在《词与物》“前言”中提到,是博尔赫斯作品中引用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怪异的动物分类法,激发了他探究欧洲千年来构成事物秩序基础的同(le Mème)与异(l’Autre)用法的演变(修正或消失)过程。作为“异托邦(les hétérotopies)”之一的中国是“让人不安”的,因为它腐蚀着欧洲语言,特别是动摇了连接词(les mots)与物(les choses)的更为隐秘的思想句法。而朱利安对中国的建构或“发明”,正是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应和、延续了福柯的“异托邦”思维。
不过,朱利安同时也注意到,《道德经》并没有全然否定“相似性”原则,而是允诺了一种保持开放、不偏私(即并不赋予某物以相似性的特权),因而不会产生排他性的“相似性”——这一点对于绘画来说是至为关键,因为若没有区分/物状,画也就成了“无形画”。在这种“相似性”中,作画虽然画出了分化,但这个分化既露(“显”)且藏(“隐”),仍然“维持着自身所由来的未分化之活力”;作画画出了多样性(分化),但与此同时,事物“未分化”时的“同时性”“同等性”仍然显现着,而正是这个“同时同等性”使多样性自身内部发生沟通并联系着多样性。朱利安称事物之间的这一“同时同等性”是一种道式(taoïque)“统一性”:“不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同时’,[……]并且正由于其‘如此’的可共存性,图像才一直是无拘束的,其相似性才保持开放”(《大象无形》122—23)。显然,这种“统一性”既不是综合式的(synthétique;即分化的事物融合于它),也不是象征性的(symbolique;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归于它之下)。总之,“在这个‘大象’阶段上,相似性不再因为受到规定性的阻碍而成为强制性、排他性的,而是无止境地开放着,始终无拘无束;相似性于是任凭自身无止无尽地舒展着,迎受着每一个新的请求,随心所欲地丰富自身。”(《大象无形》126—27)
表面上看,《道德经》这第二层次的相似性,溢出了福柯作为“再现”基础的相似性之范围。然而,福柯在分析委拉斯凯兹《宫娥》的文章结尾已经提示,“因最终从束缚自己的那种关系中解放出来,再现自身就成为纯形式的再现(pure représentation)”(Les
Mots
et
les
Choses
31)。这种“纯形式的再现”似乎就是两年后福柯在分析马格利特画作的文章《这不是一只烟斗》中所揭示的现代知识型原则: 它并不以建立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之上的“相似性”为基础,而是以建立在差异和分裂之上的“类似(similitude)”为基础,所以,“类似”是一种排除了确定性的“相似”。这种“类似”可以无限重复,形成德勒兹所说的拟像或幻像(simulacra or phatasms)。“类似”的“重复”,在实质上与德里达的“异延(différance)”相同,都是“生产性”的,它无限延展,不断进行着生成和增殖。联系上文所引朱利安的论述,再明显不过的是,朱利安表面上讨论的是“大象无形”或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但实际说出来的却不折不扣是福柯在《词与物》《这不是一只烟斗》等论著里表达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平心而论,借鉴后结构主义对“再现”“相似性”的理论反思来重新观照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离形得似”“气韵生动”等命题,确实有别开生面之感。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美学(主要是道家这一脉络)的理论潜能可以借助后结构主义理论得以开显。问题在于,朱利安几乎原封未动地将后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极度拒斥带入到他对中国美学的论述中来,通过在中国美学与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之间设置整体性对照,二者实质上“走向一种截然的对立”(《大象无形》228)。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必要拥有、事实上也没有与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理论一样的问题预设;倘若强行将这类问题意识安到中国古典美学身上,则必然产生“情境错置”或“过度诠释”的谬误。所以,当读到朱利安批评当代中国评注者不加分析地接受了欧洲“摹仿说”(mimésis)的影响,做出“公然违背了古代文献原义”且“极端无价值”的现代诠释(《大象无形》126),我们恐怕要起而反驳他的指责,并指出他的独断与不必要的排他性了吧。
退一步来看,即便基本认同朱利安对于“大象无形”等特定命题的诠释方案,我们也无法接受他对中国美学同质化的解读策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朱利安建构出的“中国”,反而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 他努力挖掘的,是潜藏在中国思想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不断生成意义的形式先决条件。这正是结构主义者热衷的工作。就此而言,朱利安以一种略显吊诡的方式,背叛了他在精神上亦步亦趋努力追随的福柯,因为福柯本人始终一以贯之地否认自己是一名结构主义者。
三、 颠覆,还是延续?——朱利安与汉学史成见
朱利安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中国美学的欣赏,以及处处从中国回照欧洲的往复、反衬手法,对于近代欧洲汉学传统而言,确有某种“哥白尼式的颠覆”意味(Thierry Marchaisse语)。但是,从深层的论证逻辑来说,朱利安在许多方面仍然延续了黑格尔-韦伯讨论中国思想时的做法(只不过是在新的哲学情势下颠转了黑格尔原来的负面评价),精巧的论述之下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汉学史成见的深刻反思。
此处以朱利安念兹在兹的“内在性”概念为例,试申说之。
在早期著作《过程或创造: 中国文人思想导论》(1989年)一书中,朱利安参照王夫之的易学思想,视“过程”(Procès)为“中国世界观的基本表征”,并将它与“其他地方,尤其在西方所熟知的人类学、哲学模式”(即“创造”,Création)对立起来。朱利安把“过程”等同于“道”,认为“过程总是自成的。它以自身为模式,又是卓越的典范。既没有外来干涉又没有外加的规范: 我们彻底远离如同所有‘创造’原型都必需的‘创造者’”(Proc
ès
ou
Cr
éation
77)。在朱利安看来,过程思想与西方的创造思想是截然二分的,“既没有作为起始原因和第一动力的创世者的必然性——过程逻辑排斥这一点,也没有从更深层的角度讲的对他者——超越性的绝对的经验,我是说上帝——的参照。”(Proc
ès
ou
Cr
éation
79;王论跃26)进而,朱利安把“过程”与“创造”的对立扩展到“内在性”与“超绝性”的对立,认为《周易》卦的模式是内在性的显露。欧洲思想关注超绝性,其特性是“试图探究他者的他性(即他者何以真正地为他者并得以构成外在性)”,“与这种对彼岸的开放相反,内在性思想的特性是试图凸现他者内的所有能关联起来的同一性的价值,让它们运作起来”,而统摄《周易》和中国思想的便是两极运作的组合逻辑,从这种逻辑自然可以引出连续的互动性运作。“因此《易经》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向我们显示内在于过程的连贯性。”朱利安《内在之象: 〈易经〉的哲学解读》(1993年)也正是要以王夫之的《周易》诠释著作为立脚点来构建一种“内在性逻辑”。

回溯西方汉学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朱利安关于中国思想“内在性”的讨论,其来有自。考察这一问题的“前史”,我们须把目光投向200年前的欧洲。黑格尔依据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国认知,认为孔子的学说欠缺超越性、宗教性,身处“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的中国人并不需要一位“最高的存在”,因而中国宗教在黑格尔那里仅属于低级的“自然宗教”,并没有迈进“自由宗教”的门槛(黑格尔130—33)。黑格尔的以上观点绝非孤鸣仅响,其实是典型欧洲思想的一种折射。故而,这些观点甫一提出,便在西方产生了普遍的应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儒教与道教》(1916年)一书中,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超越尘世寄托的伦理,没有介乎超俗世上帝所托使命与尘世肉体之间的紧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向,也没有原罪恶根的观念。换句话说,中国思想是世俗性的,在这一点上它迥异于西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传统。
总之,从黑格尔到韦伯一系的西方思想家在看待中国思想时,习惯为其贴上“缺乏超越性”“无主体性”“无历史”等标签,而汉学领域里葛兰言(Marcel Granet)、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陶德文(Rolf Trauzettel)、陈汉生(Chad Hansen)、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黑格尔-韦伯”式的论断。即便安乐哲(Roger T. Ames)、朱利安这样对中国思想评价很高的汉学家,也只是将黑格尔的负面评价反转为正面评价,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和反思“黑格尔-韦伯”模式的立论基础(罗哲海9—30)。于是我们读到,当黑格尔嘲讽孔子的言论罗嗦冗长、读来无益时,朱利安却在其中发掘出了“平淡”的美学价值(《淡之颂》5—9)。
“内在性”理论的确捕捉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一项(不是“唯一”!)重要特征,但是它与生俱来地带有某种“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大量价值话语附着在这一理论之中,最终使得“内在性”理论似乎成了西方汉学界解读中国文化的“不二法门”。就此而言,作为与西方哲学外在超越模式相对照的关键点,中国思想之“内在性”逐渐成为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成见”或“迷思”(myth)!不管是朱利安这样纵身于中国“内在性”中、全情拥抱它的汉学家,还是像黑格尔、韦伯那样置身事外、冷酷剖析它的思想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没有人质疑将“内在性”标签贴到中国思想上面的合法性,亦即未能将这一汉学史成见“问题化”(problematize),所不同的只是对“内在性”这个未经反思的错误前提断言做出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已。
尤其是对于朱利安而言,“内在性”似乎成了中国人思维世界的“先验”(transzendental)预设,仿佛抓住这一关键,所有中国思想便可得到内在一致的解读。然而,朱利安的“内在性”预设主要停留于理论文本解读的圆融自足性追求上,而很少进入具体的历史经验。与之同时,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经验中的超越性或批判性维度被严重忽视甚至抹煞了。在众多关乎或无关乎中国美学的论著中,朱利安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避免讨论与超越性和批判性密切关联的当代政治话题,不仅面对欧洲如此,面对中国时也是如此。这种在当代政治议题上的含混不清,使得他2010年获得“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Hannah-Arendt-Preis für politisches Denken;以延续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思这一传统而著称)这一事件显得颇具反讽意味。
四、 争议: 可疑的美学政治性
在大量涉及中国思想的论著中,朱利安反复自陈心迹,他的目标是借中国思想这一“他者”,反衬、反思西方“我思”(cogito)传统的偏见和盲视,由此促进西方哲学的涅槃更生。揆诸这一哲学家/思想家目标,任何指陈其汉学研究“顾此失彼”“以偏概全”“夸大差异”“不够严谨”的批评声音似乎都失去了重量。同时,前文业已指出,朱利安是一位文体写作高手,仿佛总能站在哲学/逻辑的制高点上,成功避开知识学意义上的质疑与追问。事实上,朱利安的汉学知识本不存在欠缺,他采用这种突出差异性的写作方式完全是自觉的选择。那么,朱利安就可以免于批评吗?显然并非如此。
事实上,与朱利安的论著大受欢迎的情形相伴随,朱利安也领受了来自多个领域的学术批评。其中,批评朱利安较为系统、深入的是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François Billeter)。
1990年,针对朱利安《过程或创造》一书,毕来德发表长篇书评《如何阅读王夫之?》(“Comment lire Wang Fuzhi?”95—127)。他一方面肯定朱利安对中国思想的解读确有其优胜处,另一方面又针对朱利安的整体比较策略、表述方式、对读者的误导等方面展开批评。毕来德认为,朱利安将王夫之思想本身视为一个绝缘于外部世界的存在,这种结构主义化的呈现忽视了王夫之的生平以及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因素;这是一种从现实中抽离、因而缺失了批判性的呈现。而且,朱利安的比较研究既简化了王夫之,也简化了西方;尽管朱利安自称摆脱了那种幼稚错误的中西比较模式,但其研究结论停留于由外在的异质性“他者”激发新的疑问、由“之间”确立相互身份,然而中、西思想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质却使得二者无法真正碰面,“之间”也不能提供某种独立的尺度标准,因而最终并没有如其预期开启一种明晰、有效的哲学思考路径。
朱利安很快针对毕来德的书评撰写了答复《解读或投射: 如何阅读(另一种)王夫之?》(“Lecture ou projection”131—49),并展开反批评。朱利安认为自己著作的目的是从王夫之出发,而非停留于王夫之;对于王夫之,值得提倡的是一种“问题化的理解”,而非那种简单地从生平到思想的雷同介绍。朱利安认为自己的比较研究可以开启一种双重视域: 既照亮欧洲思想的“未思”(impensé),又揭示中国思想的“未思”。在朱利安看来,毕来德所持的其实是一套教条主义的主张,它不能激发反思,只会让我们对王夫之的理解更为贫乏和枯竭。朱利安则认为自己强调的是“中国”对于欧洲的“别处性”(allogène),而非中西之间那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性(alérité)。而毕来德所说的比较基础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类比,是经不起推敲的。毕来德把王夫之的思想概括为一种意识现象学,但朱利安认为“意识现象学”只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的一种产物,并不适合用来描述中国思想。争论至此告一段落。
2006年,不屈不挠的毕来德出版小册子《反对朱利安》(《驳于连》216—44),将争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批评朱利安的所有著作都建立在中国相异性(altérité)这一神话之上,因此,对于中国,朱利安只留意“过程”,忽视了“创造”;注意到中国思想的“内在性”,而并未批评这种内在性与专制政治的共谋;强调“哲学”,而忽视了历史背景(尤其是中国的王权政治大背景)。毕来德重申其在1990年书评中的观点,认为中西比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它们之间要有共同的对象;而朱利安只强调差异,这导致中西无法真正相遇,朱利安的比较研究最终成了自说自话。
特别是,朱利安突出并理想化了中国思想的“内在性”,但是“一刻也不曾想到要对这种思想进行批判”。而毕来德认为,内在性思想天生就与帝国的封闭秩序相默契、共谋,最终滑向对于权力、手段、计谋和效率的追求,从而成为发展个人观念和政治民主化的障碍。毕来德强调应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和专制独裁(despotism),以及与这种统治术捆绑在一起的内在性思想,而不是为中国古代传统唱赞歌。

紧接着,毕来德又发表了对于《在路上》一书的评论《朱利安,说到底》,指陈朱利安善于在哲学家和汉学家之间游走,“两边通吃”,“披上哲学家的权威外衣来为他的整体论述增加信用,而一旦这个论述惹起争议时,就躲到哲学家不受约束的权利伞下寻求庇护”。进而毕来德又剖析朱利安思想大受欢迎的隐秘背景:“二战”之后在海德格尔存在论影响下形成的追根溯源式哲学思考风气成为热潮,这种“势”正好造就了朱利安;但是,朱利安仅仅满足于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却毫不顾及“自己行动的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效果”。通过对比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毕来德尖锐地指出,朱利安像海德格尔一样,“或许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正因为朱利安的论著正在发挥有害的影响——就像海德格尔思想一样,它虽有“极端雄心”,实际却只能“造成一种雾里看花又迟滞耽搁的效果”,“阻碍人们审辨、提出当代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毕来德才感到非常有必要公开发表他的观点。毕来德认为,他与朱利安的分歧“主要不是汉学研究方面的问题”,而是“哲学立足点”上的根本对立。
完整回顾毕来德与朱利安的争论并非本文的主旨。然而,透过这场争论,朱利安所遮蔽的历史与政治空间,或者说朱利安思想的盲视之处得以彰显。朱利安重视“形式现实化之前之未分化基底”,在当代西方思想地图上,这确乎是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关切。朱利安的中国美学建构,亦如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都具有不介入、非政治性的倾向。就像海德格尔一样,这样做即便具备巨大的哲学/美学雄心,实际上却在现实社会(政治)难题面前犹疑、迟宕,因而其美学建构的当代政治相关性(relevance)也是可疑的。
小结: 回到方法
前文已经谈到,朱利安是一位对方法论非常自觉的学者。他在每一部论著、每一次演讲中都会讲到自己的研究方法论: 从外部解构欧洲。他瞄准的是欧洲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却总是要绕道中国这块“思想工地”,通过旁敲侧击地触及欧洲的“未思”,来重新发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领域的思考。他反复说过,他的工作并不是建立在“同一/差异”基础上的“比较”,而是致力于发掘中欧思想的“间距”,以富有生产力(productif)和孕育力(fécondité)的“间距”概念取代无生产力的“差异”,并且在由“间距”打开的“之间”(l’entre)中自由操作,开展“文化间谈”。朱利安认为,这样做可以摆脱肤浅的普世论(l’universalisme facile;导致欧洲中心主义)和懒惰的相对论(le relativisme paresseux;导致文化主义)。
朱利安自承,“我不做比较,或者说,我只有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并且针对限定的片段进行比较。”(《间距与之间》34)方法论表述如此,但朱利安实际做的,似乎却“陷入无意于比较的比较研究”(何乏笔85),最终滑入文化相对论的理论阵营。从历史层面看,他的中欧“无关性”预设问题重重——远的不讲,即便从400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来看,朱利安的这一预设也是不成立的。
他强调“间距”富有孕育力,并且要通过“文化间谈”让中、欧思想“面对面”,然而,他实际做的,却似乎是让中、欧思想各居其位,相互绝缘,停留于一种死板僵化的、避免“受孕”的静态分析。他为“间距”允诺的孕育力无法落实,“文化间谈”亦停留于纸面上。面对中西思想交流的这一困境,另一条出路似乎更为可行: 开掘真实的历史经验,并藉由这些历史经验重新开启中、欧之间的思想对话,惟有如此,对话方能真正而深切地做到“中的于现状,发言于心声”,而不会流于失重的方法论空谈。
注释[Notes]
① 这与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之方法论论述是相近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思想家式的致思路径。(参考: 沟口雄三125)
② 朱利安著有《论亲密: 远离喧嚣的爱》(De
l
’intime
:Loin
du
bruyant
Amour
, 2013年)一书,主张挖掘“亲密(l’intime)”之价值,以弥补“爱(amour)”之缺陷。③ 汉语学界常常用“生命超越”来界定中国美学的核心品格,认为中国美学“具有突出的重视生命体验和超越的特点”。(朱良志“引言”2)
④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赞赏地评价朱利安对中国的建构是“发明中国”:“他(朱利安)所力求发明的中国绝对是为了对我们有点儿用处的,而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对自己的存在认识得更加清楚”。(夏蒂埃 马尔歇兹89—90)
⑤ 按照福柯的看法,“类似”与“相似”的最根本不同在于,“类似”没有与“相似”缠绕在一起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源头:“相似具有一个‘模型’,一个本原元素,[……]相似预设了一个起规定和分类作用的原始参照。类似之物则在一个既无开端也无终点的序列中发展,[……]类似之物没有等级秩序要服从,它们从细微差异中的细微差异扩散。相似服务于再现,后者支配着它;类似服务于重复,后者在它里面漫游。相似使自己基于一个它必须返回而且必须揭示的模型;类似则使仿像(simulacrum)得以流通,而仿像就是类似物之间无限而且可逆的关系。”(This
Is
Not
a
Pipe
44;马元龙123)⑥ 20世纪西方研究《周易》的学人,多有借重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来展开论述者,如程石泉、唐力权等皆是。但朱利安所言“过程”极为排斥“创生论”话语,此点值得注意。(参考: 韩振华 赵娟61—70)
⑦ 朱利安区分了“超越”(going beyond)和“超绝”(above and cut off),他认为中国思想有超越性层面,但这种超越并不指向一种绝对的外在性,而指向“绝对的内在性”(absolutization of immanence)。
⑧ 早在《过程或创造》一书第十一章《过程的语言表现》,朱利安就讨论过,汉语中用来表达思想的术语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语义单元(semantic units),而是通过与其他术语的交互关联(correlation)、群丛网络,成为二元性(duality)的构成要素。汉语术语这一“交互关联”的性质正好与汉语最突出的特征——平行对应性(parallelism)——相契合。这是“过程性”逻辑,而非欧洲语言的“创造性”逻辑。
⑨ 与笔者的观点相似,汉学家金鹏程(Paul R. Goldin)亦直斥西方汉学界“中国没有创世神话”这一陈词滥调本身就是一种神话(“China has no myths of cosmogony” is a myth.)。(金鹏程83)
⑩ 毕来德认为,一般读者感兴趣的其实是朱利安著作中最薄弱的一面,“他的书讨人喜欢,正是因为复活了法国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哲学派’中国的神话”。(《驳于连》23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毕来德:“驳于连”,郭宏安译,《国际汉学》1(2010): 216—44。
[Billeter, Jean-François. “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Trans. Guo Hong’an.International
Sinology
1(2010): 216-44.]Billeter, Jean-François. “Comment lire Wang Fuzhi?”Etudes
chinoises
1(1990): 95-127.- - -.Contre
Fran
çois
Jullien
. Paris: Allia, 2006.- - -.“François Jullien, sur le fond.”Monde
chinois
11(2007): 67-74.皮埃尔·夏蒂埃 梯叶里·马尔歇兹主编: 《中欧思想的碰撞: 从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说开去》,闫素伟、董斌孜孜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Chartier, Pierre and Thierry Marchaisse, eds.Chine
/Europe
:Percussions
dans
la
pens
ée
. Trans. Yan Suwei and Dong Binziz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米佳燕译。《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87—305。
[Foucault, Michel. “Qu’est-ce qu’un auteur?” Trans. Mi Jiayan.Postmodern
Culture
and
Aesthetics
. Ed. Wang Yuechuan and Shang Sh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2.287-305.]Foucault, Michel.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
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 Paris: Gallimard, 1966.- - -.This
Is
Not
a
Pipe
. Trans. James Hark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金鹏程:“‘中国没有创世神话’就是一种神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8): 83—94、117。
[Goldin, Paul Rakita. “That China Has No Cosmological Myth’ Is a Myth Per Se.”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5(2018): 83-94,117.]Graham, Angus Charles. “The Way and the One inHo
-kuan
-tzu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 Ed. Hans Lenk and Gregor Paul. New York: SUNY Press, 1993.31-44.韩振华 赵娟:“过程哲学视域下的《周易》时间观念”,《周易研究》6(2012): 61—70。
[Han, Zhenhua, and Zhao Juan. “The Concept of Time inBook
of
Change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Philosophy.”Studies
of
Zhouyi
6(2012): 61-70.]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Philosophy
of
History
. Trans.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何乏笔:“混杂现代化、跨文化转向与汉语思想的批判性重构(与朱利安‘对-话’)”,方维规主编: 《思想与方法: 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4—135。
[Heubel, Fabian. “Hybrid Modernity, Transcultural Turn, and the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ought: A Dialogue with François Jullien.”Ideas
and
Methods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 Ed.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84-135.]弗朗索瓦·朱利安: 《美,这奇特的理念》,高枫枫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Jullien, François.Cet
étrange
id
ée
du
beau
. Trans. Gao Fengf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6.]——: 《本质或裸体》,林志明、张婉真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 - -.De
l
’essence
ou
du
nu
. Trans. Lin Zhiming and Zhang Wanzhe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从存有到生活: 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卓立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 《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 - -.Detour
and
Enter
. Trans. Du Xiaozhe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淡之颂: 论中国思想与美学》,卓立译。台北: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 - -.Eloge
de
la
fadeur
:A
partir
de
la
pens
ée
et
de
l
’esth
étique
de
la
Chine
. Trans. Zhuo Li. Taipei: Laurel Books Co., Ltd., 2006.]——: 《大象无形: 或论绘画之非客体》,张颖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 - -.La
Grande
image
n
’a
pas
de
forme
:Ou
du
non
-objet
par
la
peinture
. Trans. Zhang Ying.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7.]——:“间距与之间: 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卓立译,《思想与方法: 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方维规主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0—39。
[- - -. “L’écart et l’entre: Ou comment penser l’altérité culturelle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Trans. Zhuo Li.Ideas
and
Methods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 Ed.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20-39.]
Figures
de
l
’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
king
,le
classique
du
changement
. Paris: B. Grasset, 1993.- - -. “Lecture ou projection: Comment lire (autrement) Wang Fuzhi?”Etudes
chinoises
2(1990): 131-49.
马元龙:“再现的崩溃: 重审福柯的绘画主张”,《文艺研究》4(2018): 114—26。
[Ma, Yuanlong. “The Collapse of Representation: Reexamining Foucault’s Ideas of Painting.”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4(2018): 114-26.]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Mizoguchi, Yūzō.China
as
a
Method
. Trans. Sun Jun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罗哲海: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瞿德瑜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9年。
[Roetz, Heiner.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xial
Age
. Trans. Chen Yongming and Qu Deyu.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9.]王论跃:“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08): 25—32。
[Wang, Lunyu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fucianism Studies in France.”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1(2018): 25-32.]汪民安:“‘再现’的解体模式: 福柯论绘画”,《文艺研究》4(2015): 134—42。
[Wang, Min’an. “The Disintegration of ‘Representation’: Foucault on Painting.”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4(2015): 134-42.]朱良志: 《中国美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Zhu, Liangzhi.Fifteen
Lectures
on
Chinese
Aesthetics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