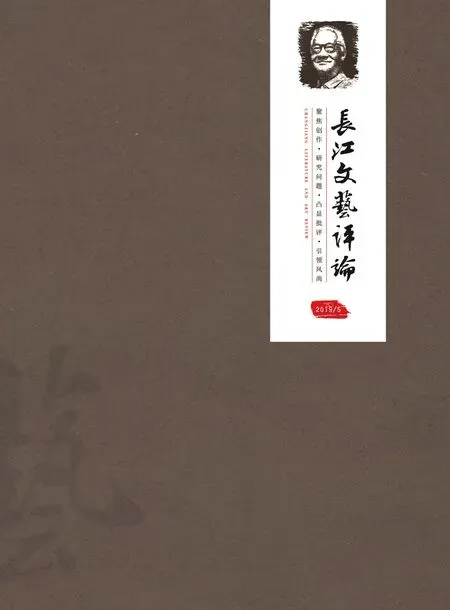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日”
——读王键组诗《夜航》所感
2019-11-12荣光启
◆荣光启
读王键组诗《夜航》,我不能不想起之前的埃塞俄比亚空难。那架波音737在起飞后六分钟失踪,生生扎向地面,一团巨大的火光中149名旅客和八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如果我也在那架飞机上,最后时刻我会怎样?“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日……”
“夜航”是一种特别的经验。在国际航班的漫长的旅程中,我们进入了一个纯粹的毫无依靠的时空。在那个凝固的、漆黑的、没有什么声音的空间,似乎时间也凝固了。生命在这里,是一个飘浮的存在物:“我们游行在看不见的云里/我们穿黑色的泳衣”。作为生命的主体,又不得不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我是怎样的存在?死亡离我到底有多近?
“夜航”其实是一个哲学化的处境,它将存在主义者所言的人的“被抛”状况生生凸现出来,逼着你不得不纠结于与生死相关的命题。“此在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海德格尔用被抛状态来标识这一基本的生存论环节。此在永远在被抛掷之中。然而此在却多半不正视这一事实,试图以种种方式背向这一事实。只有在一种最基本的情绪——畏——之中,这一事实才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诗作的开头将这种“被抛”处境的原因道出:“我们被那个破损的星球/流放/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那破损的 / 罪人”。“罪人”(sinner),这个词对我们相当陌生:我们似乎没有在法律意义上犯罪,为何是“罪人”?那这里的“罪”(sin),所指向的应该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处境: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无依无靠,我们无法获得信心,我们不知道将自己交给谁,我们是一种极为脆弱的存在,如同“将残的灯火”。在这种处境中的人,能体会到人的一种根本性的缺乏。对这种“缺乏”的经验乃是关于“罪”的经验。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在寻求可以信靠的对象,如常人一样,首先是飞机本身:“我与地面已失去一切联系/手机关机,或者没有任何信号/这个时候,我唯一能信靠的人是机长//我对他说:给你,请带我回家”。甚至,空姐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能带来安慰:“北京和纽约/我拥有两个不同世界的/敌意和冷漠/差异,呈现出它们粗砺尖锐的性质/而温柔的部分总是相同/比如,从你身旁走过的空姐悄悄/打开你头顶的那盏小射灯”。
整个航程,也是作者的思绪、想象与叙述的急速延展。旅程中的一切,对应着人在此特殊时空中的思与言。
“夜航”成为一种夜语,成为心灵的独白与辩诘。“无论我们怎么飞也飞不过/时间/我们都在时间里/腐朽”。
在漆黑夜空中飘浮的飞机,对应着晦暗的自我:“什么是漂泊?当我们对某种高速度失去/感觉时就是漂泊,譬如飞行//譬如人生”。
而机舱里的状况,一方面显出人的一种命运:“有一阵,机舱里安静极了/灯光全都熄灭,机舱的黑同/外面的浑然一体了//我看见,无数的头颅在黑暗里/囚渡”。无数的头颅在黑暗中泅渡,这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人之命运的象征。而另一种情景,则是现代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一种荒诞景象:“小而密闭的空间,装着/两种人/一种人要回家,另一种人要离家//我有点迷糊:为何怀着完全相反目的/的两种人会在同一条船上?”由于这种荒诞得不到解释,人只能陷入“虚无”:“在机器的内部:你紧挨着我,他也/紧挨着我 但我们彼此不说话/有时,一段紧密的关系相等于/一段陌生的关系//我陷入词的空虚与黑洞”。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对无依托的境遇的恐惧、对死亡的凝视的局促不安,另一方面,作者也出示了他从何处得着了常人没有的平安。似乎有一种力量一直与他同在,比如“一阵剧烈颠簸的片刻/我紧张,害怕/双手攥紧空气/这时,有一只手/放在我发抖的肩头/让它安静”。这是谁的“手”?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作者其实也有提示,在某一组诗里,他提到了“父”:“我们飞行在辽阔、不着边际的空间/却不偏离轨道,因为总有一股力量/拉扯着我们往下//而此刻,牵引我的不是万有引力/或者引力波/而是父亲曾经坐过的那把空的轮椅/它仍谦虚地立在房间的/那个角落”。这个“父”的象征意味是什么?
如前所言,我们既然因“罪”被流放,现在,我们又因“父”而得到“牵引”、得到安慰,那这个航程,其实是一次关于罪、死之恐惧与救赎的思想之旅。
关于死,作者虽然也想到一些俗常的后事,但让人惊讶的是,他说:“我不止一次想到死,在高空/我想像着死亡的突然降临/但我想得最多的却是/我的墓志铭://‘他死后变成了一个好人’”。在死亡的催逼中,作者思虑的是“干净”,虽然他说的是“肠胃”,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在说灵魂,或者说整个的人——“一整天,我只吃一片面包/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日/我宁愿我的肠胃/干净”。在犹太人的文化中,“肠胃”实质上就是指全然的人。
奇妙的是,思虑成为一个“好人”与“悔改”,使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在诗作的最后,日光出现,人得自由。“越过白令海峡,飞机/像个被抛出去的铁锚/一头扎进白昼的岸上//天,一下子亮了。我从/逼仄的座位上起来/向空中舒展蜷曲已久的身体”。如同“肠胃”意象指向全然的人,这里的“身体”也是指向个体完整的生命:在一场揪心的黑暗旅程之后,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身体的“舒展”所表明的是心灵的被光照、是灵魂的“自由”的来临。
组诗《夜航》既是现实性的,又是象征性的,将漫长航程的琐屑记忆、芜杂想象与不断更新的经验有机呈现出来,作为诗歌文本,极有秩序性和结构性。同类题材的写作,让我想起当代著名诗人于坚的长诗《飞行》。对这样的杰出诗作的阅读,其中的跌宕起伏,也让我如同经历了一场有颠簸、惊悸、绝望和平安的飞行。
注释:
[1]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6页。
[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揭示出一幅极端冷漠、残酷、自我中心、人与人无法沟通思想情感的可怕图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在《门户关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这可以看作现代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宣言。”袁可嘉、董衡、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