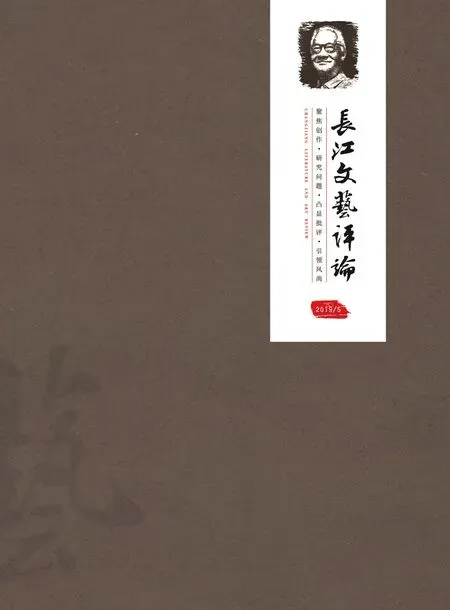试论罗泓轸电影美学的叙事策略
2019-11-12李斯卓
◆李斯卓
罗泓轸是韩国知名新生代电影人,他的多部作品在韩国、欧美频获奖项,口碑良好且票房火爆。作为新世纪“韩影西进”的领军导演,罗泓轸有着不断拓展本土电影市场的民族野心和艺术追求。他执导的影片大多是犯罪悬疑题材,与韩国社会现实紧密联结,不仅呈现了凛冽的视听奇观,还蕴含着深刻的人性反思意味。本文主要选取罗泓轸导演的三部长片《追击者》《黄海》《哭声》,运用电影叙事学的分析方法,从影片的叙事母题、叙事结构、叙事悬念、叙事空间四个方面分析其影片的叙事美学策略,以期对中国电影的叙事美学有所借鉴。
一、叙事母题
罗泓轸导演的作品常常结合韩国本土社会议题,通过国际化的影视语言进行故事讲述。这种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和个人因素,即东亚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融合后的转变,以及罗泓轸本人对基督教的笃信、对韩国“恨文化”的寻根。在他的《追击者》《黄海》《哭声》中,他从未改变对其叙述母题的视听阐释。
有别于六十年代朴正熙时期的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对于人性的压抑、文化传播的抑制,韩国于1993年金泳三上台后,拉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序幕,政府逐渐开始关注民众个体的命运,并给予电影制作者极大的创作自由。但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韩国内部压抑已久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越发加剧。关于都市化进程中“人的个体化”“人性的异化扭曲”便成为了韩国现实题材影片中最常见的故事主题。“在对旧时代的反思中,‘恨文化’逐渐兴起,韩国的‘恨文化’并不只是指通常意义上那种狭隘的恨,而是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恨’一种别样意义,即一种在国家机器因法律不健全、政治顾虑等不能将以罪恶绳之以法时,个人将‘恨’作为行动的源动力来寻求暂时的正义,同时也是确认民族身份的一种积极的文化特质。”
“个体化”是一种社会学概念,是指在当代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和劳动、就业方式及社会生活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他的独立性、独特性、主体性充分地得到表达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专业化,个体的差异性只会越加明显,人与人的理解沟通将愈加无效,著名的社会学家鲍曼将此称为“后现代的最大悲剧”。身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显然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只不过,它还面对着更为复杂多样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都市与乡镇的关系,如何消解都市中边缘人物与主流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罗泓轸作为对本国国情有着深刻体悟的电影作者,也时刻关注着韩国目前所处的时代困境。
影片《追击者》《黄海》都体现出罗泓轸凛冽的批判风格,同时展现了小人物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不公正的抗争。《追击者》中,妓女美珍作为都市中的边缘群体最终得不到官方(警察)的保护,惨死在杀人犯手下。而男主人公严忠浩为美珍复仇,在脱离社会现存法律秩序之上,蜕变出人性的暖色基调,抚慰了韩国社会中的焦虑情绪。《黄海》中,导演以客观的视角向大家展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对于身份的追寻,对于孤独的坚守。金久南作为不被主流人群所接受的身份卑微的底层人物,一心只想回归故土、坚守本心,最终死在了茫茫的黄海之上。虽然影片的结局无限凄凉,但罗泓轸展现了他对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边缘人物的敬重与关怀。而在影片《哭声》中,导演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信仰——基督教、土俗迷信、邪恶超自然力量。诸如影片中的十字架便是基督教的标志,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植入。而暗中守护小镇的神秘白衣女子则象征着韩国本土文化中的土俗迷信。此外,行踪飘忽的入侵者——日本人则是邪恶超自然力量的象征。罗泓轸通过这些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他的信念——宗教并不能使人的心灵坚守如一,一个人在面对那些全然陌生、可能改变自己信仰的事件时,只有平静的接受才会得到心灵的平静,从而摆脱挣扎的困境。
二、叙事结构
罗泓轸的《追击者》采用了好莱坞因果式线性叙事的手法,影片的一开头便直奔叙事主线,构置起戏剧性情境。男主人公严忠浩是一名组织色情交易活动的老板,在发现手下几个拿走预付金的妓女,均是与手机尾号为4885的男人交易而失踪后,他发誓要找到这个“卖掉自己女孩”的男人。紧接着,被他派出和4885交易并寻找线索的妓女美珍,遭到了4885的击杀。随后,严忠浩和4885戏剧性地在狭窄的居民区相遇,展开了二人间激烈的追击战,以二人均被警察拘留结束。严忠浩不断向警察重申池英民(4885)卖掉了自己手下的妓女,池英民则始终不予回应,说是自己杀了那些女人,严忠浩却只当这是胡言乱语,二人间的话语对立,是影片的第一个矛盾冲突点。严忠浩由一开始对“池英民杀人”的不屑一顾,到影片中段了解池英民曾“用锤子击打侄子头部”后猛然心惊,对美珍的女儿感到极度愧疚,使影片达到了情感上的高潮。在影片的尾声,男主人公严忠浩通过向杀人犯池英民复仇完成了个体生命救赎的神话。同时,罗泓轸还借鉴了经典模型中对荣格“原型”的运用,将皮条客严忠浩比作与恶势力搏斗的平民英雄,而将与他互为对手的杀人犯池英民比作潜伏于黑暗中的阴影。二人之争代表着“正义”与“罪恶”的互搏,观众对于“正义必胜”的强烈渴望使得其认同心理随着剧情展开不断强化。
影片《黄海》在叙事结构上做了些许调整,以“欲望和回归”作为叙事主线,展现了男主人公和两个次要人物之间因欲望交织而展开的生死搏斗。男主角金久南穷困潦倒,老婆偷渡到韩国失去音讯,自己为此欠下巨债。还上巨债、寻回老婆的欲望,使得金久南听从黑头目绵社长的命令,去刺杀金教授,但却在实施刺杀时被他人抢先,阴差阳错地割下金教授的大拇指。警察对金久南展开了猛烈地追捕,影片的第一个冲突出现。紧接着,两个黑帮老大同时追杀起金久南,企图掩盖犯罪事实,影片于金久南在漫长的流亡途中的绝望痛哭处达到了叙事的高潮,情感的极端爆发使得现实格外冰冷残酷。观众于阴郁灰暗的镜头中,感受到现实带来的悲痛酸楚。同时,影片中的人物塑造遵循了荣格的“原型”理论,综合了沃格勒提取的“八个基本功能性角色”的功能,有力地刻画出主要人物的形象,深化了影片探讨的人性主题。例如,金久南的原型是“英雄”,他的人物动机与信念是寻回老婆、回归家乡,能被观众所理解。而两个次要人物,绵社长和金泰元的原型是“阴影”,都是典型的反面角色,不断阻碍着男主人公金久南归乡的行动。
《哭声》更像是一部犯罪惊悚片,它的叙事结构更为特别,融合了基督教、韩国土俗信仰以及某种邪恶力量的对抗,并向观众抛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个人的信仰在面对外来力量的迷惑时,是否能坚守不变,毫不动摇?其二是,宗教和信仰是否能拯救一个内心动摇的人?整部影片塑造了一个惊悚、神秘、暴力、危险的故事环境,远离都市的韩国小镇上突然出现了几起因加害者误食毒蘑菇感染而造成的恶性杀人事件,男主人公钟久作为小镇上胆小懦弱的警察只能根据寥寥无几的线索追寻事件的真相。戴锦华曾说过,惊悚片里的“真正威胁”往往源于“主人公内心的黑暗”。《哭声》通过向人们展示男主角钟久信念的动摇、重建、毁灭,以及肉身的陨灭,使观众不得不正视人内心由于信仰缺失导致的阴暗面。首先钟久对小镇里“外来的日本人是凶手,他曾经强奸过女性”的传闻嗤之以鼻,但当他发现女儿被日本人侵犯感染病毒、自己不断梦见日本人的暴行、听到神秘白衣女人“日本人是恶魔”的说辞后内心开始动摇。他对母亲请来给女儿驱邪的巫师言听计从,这场浓墨重彩的戏成为了全剧的第一个高潮点。大巫师在倾盆大雨中不断舞动着,口中发出尖锐凄楚的念咒声,炽烈的火焰升腾而起,高度仪式化的场面,加剧了影片中如影随形的诡谲气氛。钟久为拯救女儿,从懦弱无能变得凶狠有力,他毫不犹豫地将日本人扔下山崖,女儿终于恢复了理智。好景不长,女儿无故失踪,神秘白衣女人的忠告因其异于常人的手掌温度变得不够可信、巫师义正言辞的话语蛊惑力十足,钟久失去判断能力,信仰彻底迷失。他听从了恶魔的蛊惑,最终惨死在妖魔附体的女儿之手。观众在罗泓轸构筑的异世界奇观中,感受到人的渺小无助,渐渐被一个接一个的谜团所困,只能不断寻找真相和答案。
好莱坞经典叙事结构除了“因果式线性叙事”外,还不断运用平行叙事结构来创造崭新的意味。平行叙事结构的最明显特征可以归结为,故事发展具有两条及两条以上的叙事线索,这些线索随着剧情的推进“分头叙事”或“同时叙事”,在对比中体现特别的意图。平行结构不仅在叙述层面上对时空进行重新建构,还体现在故事时空的多维、错乱上。罗泓轸导演的《追击者》《黄海》中便继承了这一叙事手法。
《追击者》中的平行叙事段落十分精彩,主要用来塑造深沉的环境氛围。在影片的一百分钟时,严忠浩不断地奔跑着去寻找美珍;同时,浴室里,美珍苏醒过来奋力逃向小卖部;而池英民被无罪释放后进了小卖部,拿起锤子,警察却无力阻止。导演使三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运用了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桥段,镜头节奏和运动充满着戏剧张力,为观者营造了强烈的悬念。对于美珍是否能够获救,观众本是充满着希望,导演却在三条叙事线索交汇之时,使观众的希翼彻底落空。逃出生天的受害者再次落入变态杀人犯的手中,警察在一门之隔外毫无作为,受害女性宝贵的生机被彻底扼杀,随着鲜血的飞溅,观众被迫接受了令人绝望的残酷现实。
《黄海》中同样运用了平行叙事结构,渲染出影片中人物的极端情绪,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男主人公金久南在割下金教授的大拇指后在树林中仓皇逃亡;警局派出大批警力和猎犬对金久南不断追捕;同时,黑帮头目金泰元也在持续寻找金久南的下落,企图杀人灭口。三条故事线平行交叉,最终汇聚在金久南于树林中拼命奔跑的场面。他绝望地捂着中枪的手臂嚎啕大哭着,犹如一头皮开肉绽的丧家之犬,使得观者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一同沉浸在绝望惊惧的情绪之中。同时,剧情在三条叙事线的平行交叉中逐渐明朗,“刺杀金教授计划”的两个主谋——黑帮头目金泰元和银行职员金社长,各自不同的目的开始浮出水面。
《哭声》中的平行叙事结构极具神秘惊悚色彩,体现了纯真灵魂的堕落和阴险恶魔的得逞,展现了影片的主题——个人在外来力量的引诱下,不坚守本心,就会堕入深渊。影片的90分钟处,一段三个空间内的平行叙事满足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男主人公钟久紧抱着挣扎发狂、尖声呼嚎的女儿,满眼都是痛惜和恐惧;口念咒语的驱邪巫师于熊熊篝火前疯狂跳跃,宽大的衣袖、手中的扇子不断舞动着,喧闹的唢呐声震破耳膜;同时,外来的日本人在自家封闭的密室中耸动身体,面对烈火,敲击着手中的小鼓。这三段平行叙事,同时将画面中的核心人物的面貌扭曲,塑造了幽怨凄楚的故事氛围。
三、悬念设置
在犯罪题材影片中,好莱坞经典叙事结构常常通过限制性视角制造悬念,观众只知晓少量信息,在对线索的抽丝剥茧中于故事的最后才能揭开凶手的真面目。或是,通过非限制性视角制造悬念,使观众比剧中人物知道得更多,从而为剧中人物的命运翻肠搅肚。而罗泓轸导演的影片结合了限制性视角和非限制性视角,通过视角不停的转换制造悬念,调动观众的强烈好奇心。
影片《追击者》在影片开头便采用非限制性视角告知观众凶手的真实身份,将悬念转接到“受害者是否能获救,杀人犯是否能落网”上。随着剧情中杀人犯被警察抓住,承认杀人后,导演则采用限制性视角,将悬念变为“杀人犯的犯罪证据是否能被找到”上。由于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的权力纠纷,杀人犯短暂关押之后就被释放,且受害者的所在之处并没有受到警察的重视。一种对繁华都市下冷漠的人情现实、无能的政府机构的批判之意跃然银屏之上。对真凶的追寻并不是电影的母题,而只是使观者反思韩国社会现状的有力切入口。
电影《黄海》结合限制性叙述和非限制性叙述,时而只给观众透露有限的信息,使他们迷惑不解,时而又使观众站在上帝视角,为角色的宿命时刻提心吊胆。比如,直到影片的二分之一处时,观众才得以知晓指示男主人公金久南刺杀金教授的幕后黑手中,还有一个叫金泰元的黑帮头目。影片的前半部分观众一直跟随着男主远渡黄海,在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妻子、实施杀人计划,却始终对隐藏的真相毫无知觉。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观众又在复杂的多线交织的叙事中,站在上帝视角,得知了真相的全貌——黑帮头目金泰元因报复金教授和自己的老婆有私情找到绵社长刺杀金教授,同时,金教授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为了私奔而蓄意谋杀金教授。在影片的结尾部分,金久南历经磨难终登上了归家的渔船,观众无限期盼着他的回归与新生,却不由得陷入绝望的情绪。久南重伤死在了船上,冷漠的船家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尸体和他妻子的骨灰扔进了黄海。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常用的概念,意为“一系列的双向对立”,是电影叙事学频繁分析影像文本的得力工具。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中,创作者总是会塑造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建立“善与恶”对抗的叙事结构,符合观众“善恶有报”的观影预期。而罗泓轸导演的影片则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他的影片《追击者》《黄海》建立了多元对立的冲突,使得影片不只聚焦在两个对立人物引发的冲突之上,而是在多条冲突的交织下,彰显出对于时代大潮下个体生命的尊重。
在《追击者》中,皮条客严忠浩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好人,他不过是个落魄度日、利益至上的边缘人——妓女的老板,他一开始对池英民的追捕只为追回自己的钱财。而代表着正义与公平的警察确是影片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标志,他们是一群对底层人物漠不关心、无能无耻的社会蛀虫。杀人犯池英民也不像传统犯罪片中的罪犯那般无知愚蠢,他对基督教的虔诚笃信使人不得不对他的杀人动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思考。导演的“反二元对立冲突”叙事策略使得观众看见小人物身上人性暖色的回潮,比如严忠浩对妓女美珍女儿的保护关心、对于司法不公的愤怒,同时也折射出韩国的社会问题。
电影《黄海》则更为明显地建立起“多元对立”式的冲突模式。主人公金久南和两个次要人物绵社长、金泰元三人之间地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三人之间的对立制衡使得人物背后冰冷残酷的现实深渊清晰可见。在金钱、欲望、性的包裹之下,个体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男主角金久南因着“寻妻还债”的欲望,踏上了不归之路;绵社长因着膨胀的金钱欲望,替金泰元雇佣男主角杀人,并被金泰元恨之入骨;金泰元为了惩罚情人的背叛,雇凶杀人,最终自食恶果。罗泓轸以“反二元对立冲突”的形式,展现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焦虑与渴求以及顽强的生命力,重构了民族心理。
四、空间营造
电影的可见叙事空间是可见可感的故事发展空间,创作者利用巧妙的空间设计勾勒出准确的空间形象,制造环境氛围,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并引导主线剧情的发展。电影艺术是一种时空的艺术,对空间的准确表达,不仅仅可以再现生活中的视觉体验,更能够塑造环境氛围,表现人物精神状态。
在《追击者》中,电影借助空间的设计凸显出韩国社会底层边缘群体(诸如妓女)的可怜境遇。妓女美珍和她女儿生存的空间极为狭小幽暗,位于阴暗潮湿的地下,没有几件家具,暗示出其生存空间的逼仄,和其抑郁、无奈的心理伤痕。此外,导演将凶杀案的现场设置在一个逼仄狭窄的私密空间——浴室里,通过妓女美珍寻找手机信号的内在情节逻辑,使我们跟随她的步伐看清了这个空间,四周都是墙壁,窗户外是被焊死的砖墙,不透一丝光线。而影片临近结尾处,美珍在窄小局促的便利店隔间里被实施二次虐杀,则使人悲愤痛苦。
电影《黄海》中也多次出现意味不同的空间。比如男主人公金久南社会身份低微,只能出入赌场这等狭窄拥挤的低级娱乐场所,他的生存困境在这逼仄的空间里得到极大的展现。此外,金久南偷渡之后曾为了寻妻去过首尔的“朝鲜族密集地”,那里小商铺林立,小巷幽深蜿蜒,到处都是干体力劳动的朝鲜族人。这两个段落中的空间不仅仅是地缘上的空间,而是覆盖了更广义的文化空间。此外,影片中,金久南偷渡时所呆的船底密室、金泰元审问时的阴暗房间,都使人感到压抑与可怖。导演通过将暴力犯罪设置在不见光的密闭空间中,使得画面更具有视觉震撼力。
影片《哭声》中对于空间的运用则更为复杂精致。比如,小镇上出现的几起凶杀案件的第一案发现场都是封闭昏暗的房间,且房间里都有鸟巢和乌鸦,这和后面男主人公钟久的女儿房间的布置如出一辙,暗示着已被恶魔侵犯的事实,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再比如,钟久和妻子在封闭狭窄的空间——轿车里发生了性行为,妻子还提到“钟久可能比不上别人的老公”,女儿对二人行为的习以为常,这些都暗示着钟久后期面对灾祸时的无能为力,也隐晦地表明女儿孝真可能已被恶魔侵犯的事实。
罗泓轸导演的几部影片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他善于在表现人物极端情感的画面中,反复使用与“水”属性近似的意象。比如在短片《汗》中,导演在交叉剪辑中运用了汗水的意象串联起生产中的女人、做爱中的男人形象,放慢镜头速度,刻画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情绪,女人是痛苦万分、声嘶力竭的,而男人则是极致快乐、铿锵有力的。同时,导演抽去了画面中的同期声,配上了跟随人物动作节奏不断加快的低沉鼓点,营造出一种急促不安的情绪氛围,使观者的所有感官意识被积极调动起来。在两个通过视听对照联系起来的空间里,影片浓郁的批判、讽刺之意力透银屏。在《追击者》中,导演则是在三段平行蒙太奇的剪辑中放缓镜头速度,通过血珠、汗水串联起三段叙事线索,抽空同期声,配上平稳缓和的吉他音乐。在三个独立空间的交叉对比中,一种对韩国社会现实中边缘人物的人权遭到漠视的哀伤悲凉、愤怒无奈的情感传递给了在场的观者。在《黄海》中,将血水、海水的意象融合在同一个段落中,配上充满着苍凉意味的复调吉他音乐,营造出一种人类渺小、命运不可违、魂不可归故里的绝望氛围。狭小的渔船上的空间和广阔的大海的空间对比强烈,观众不由得通过金久南悲惨的命运,思考起个体命运的发展。
注释:
[1]王志亮:《韩国犯罪电影叙事学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页。
[2]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