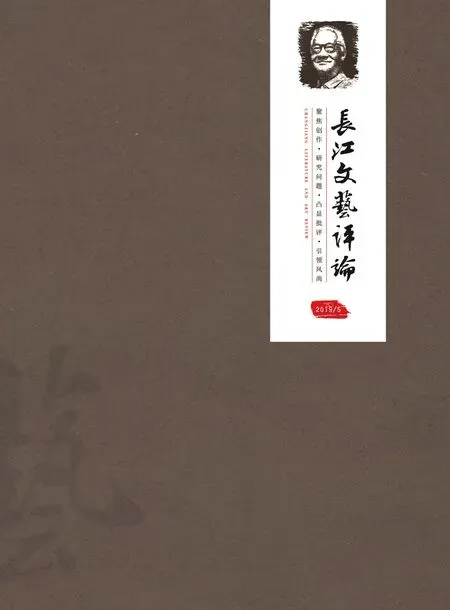转型时期家具生活美学的经典
——读刘显波、熊隽《唐代家具研究》
2019-11-12张玉能
◆张玉能
刘显波教授、熊隽博士的《唐代家具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不仅填补了目前国内外唐代家具研究的空白,为建构一部中国古代家具通史准备了充实而详细的材料,而且为开拓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家具生活美学的崭新领域做出了创新性的探索,从唐代家具的具体方面入手,给中国当代生活美学和美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可贵的启示。
一、唐代家具断代历史的建构
《唐代家具研究》以详实的考古学、艺术史、文学等材料,建构了唐代家具断代历史,揭示了唐代家具的典型类型、工艺技术、文化内涵、审美趣味,比较全面地从家具制作、类型、文化、审美的综合性角度展现出了唐代生活美学的丰赡、缤纷、转型的面貌和风采。
众所周知,家具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器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家具不仅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而且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家具,也许人们司空见惯,似乎并不感觉到它们的实际存在,虽然古今中外都有研究家具的学者和收藏家,但是,相对于人类的其它文化形态的研究就显得不那么引人瞩目。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分类之中,甚至就在物质文化研究之中也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眼中,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这种形而下者,尽管天天在使用和享受,往往并不受到重视,一般很少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至今都没有“一部体系完备、内容翔实的古代家具通史类著作问世”。刘显波、熊隽二位学者是要通过《唐代家具研究》首先建构起一个转型时代的断代史,同时在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贡献和探索的明清家具收藏研究的基础上,为建构起中国古代家具通史类著作而做出他们的重要成绩。
之所以从唐代的家具研究入手,因为一方面,他们已经在中国古代家具的高峰期——明清时代进行了大量的材料积累和细致研究,并由此将视野扩展至中国家具通史,从而发现了唐代家具这一研究空白领域;另一方面,因为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非常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家具恰恰可以反映出唐代的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映射出唐代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高度发达,显现出唐代人们的审美风尚和艺术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的确,唐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继往开来、国力强盛的一个转型时代的古代高峰,这一时期家具文化的发展包含着传统的自身演变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两个方面的因素,研究唐代家具,不仅是中国家具史研究的需要,亦将充实唐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唐代家具研究》在历史文献、图像资料、考古实物资料等详实的材料的基础上,不仅填补了唐代家具研究的空白,而且极大地充实了唐代文化史的研究。
《唐代家具研究》在唐代以前的中国家具概述的基础上,以较大的篇幅比较详尽地介绍和探讨了唐代家具的类型。该书对于唐代家具的分类方法、概念范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在学界把家具分为卧具、坐具、承具、庋具、屏具、架具六种的通行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新增设了兼具坐卧两种功能的“坐卧具”和区隔空间、划分方位的“屏障具”,以适应唐代家具的中外融合“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过渡”的转型特点和实际情况;同时,在概念范围方面,以今天通行的“木制家用器具”家具概念为参照,也将相关金属、玉石等其他材料的家具纳入研究范围。这样就显示出了唐代家具的特征和现实状况,也就成就了作为断代史的唐代家具史的特色,表现出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创新开拓的精神。
二、中国古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
《唐代家具研究》首次确立了唐代是中国古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的观点,对于中国家具史研究是一种创新性研究,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家具通史的建构也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唐代家具的“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实质上正是中华民族逐步融合,形成多民族大家庭和趋向统一的风俗习惯的历史进程的文明果实。实际上,在秦国统一中国、汉代逐渐巩固汉民族国家之后,华夏大地上仍然处于中原地区汉民族与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互相对抗的状态中,长城的构筑就是历史的见证。正是经过了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连年战乱和分裂,在唐代才真正形成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加上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土的印度和中亚的生活习俗和佛教文化,逐步改变了席地而坐卧的生活习惯、尊奉先祖的礼教仪礼,逐渐使得唐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的确,人类的家具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通,从家具的形制、工艺、装饰、陈设、布置、使用等等就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化、文明的变化。《唐代家具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唐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文化、文明的。
《唐代家具研究》论述了转型过渡的关键因素:外来文化影响、工匠精神弘扬、生活美学渗透,从而使得唐代家具成为了中国古代转型时期家具生活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经典。
首先看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这种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日积月累、逐步积淀的。该书指出:“低坐家具体系的发展,是汉代家具文化的最大特征,同时,一种腿部交叉折叠、坐面由丝绳编成的高型坐具‘胡床’,在汉末传入中国,并被少数上层阶级所接受和使用。”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高型桌案”等中国传统高型承具的早期形态。这些来自于所谓“胡人”的生活习惯及其家具的影响,在当时应该看作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主要是中原九州,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被视为“外国人”。接着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外来文化影响。《唐代家具研究》指出:“随着异族文化进入中原和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在汉末受阻于传统礼制和习俗而未能广泛传入的高足家具在接近四个世纪的长时段中逐渐进入中原,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再加上“受到思想文化的自由风气影响,过去传统礼俗中认为失礼行为的箕踞、垂足等更为放松的坐姿取代了跽坐,被贵族阶层所接受”,“中国家具走上了传统低坐家具和外来高型坐具混同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从历史渊源来看,高型坐具的椅子最早出现在古代西亚、北非地区,公元前1000年以后逐渐传播开来,公元前400年左右传到古希腊,公元前327年随着马其顿帝国入侵印度,椅子类家具传播到了印度地区。“通过丝绸之路,椅子大约在汉晋之间就已经随同佛教一起传播到了新疆地区。”“直到初唐或盛唐时期,受到佛教文化的推动,杌凳才比较缓慢地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家具研究》就是这样从胡床、椅子等许多不同的高型坐具的逐渐流行而言之确凿地论证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影响,使得唐代家具逐渐“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
再来看唐代的工匠精神弘扬。由于唐代家具制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工匠精神高度弘扬,才使得中国古代家具的这种“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能够顺利完成。工匠精神的弘扬当然首先就应该是家具制作技术的工具的显著进步,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种工具的改进使得制作高坐家具所需要的制材的薄度和平整度能够达到要求,这是其一。其二,“唐代工匠的平木技艺十分高超,这必然需要在平木工序上不惜时间与精力,以弥补加工工具的弱点”。这里面的工匠精神是可以从《唐代家具研究》中所列举的一系列唐代家具以及日本仿唐家具的表面平整光滑、线脚精致入微等等一目了然。其三,唐代工匠的框架式家具制作工艺也促进了“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唐代的工匠精神也就造成了唐代家具的审美趣味的转变:“由扁方形直材的视觉效果来分析,它仍带有一定的板面特征,从家具的正面看上去,其体式雄壮浑厚,侧视则又不失轻盈挺拔,可视为代表箱板结构向框架结构家具过渡时期的典型审美取向。”其四,唐代工匠的一些新型工艺技术应用使得“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变得既实用又美观。比如,车木技术、榫卯技术的运用。车木技术可以使得高型坐具的腿部制作做得精美,形状多样,更好地抬高坐卧具和承具以及庋具的高度,适合于各种不同的场合人们的应用需求和审美要求。同样的,榫卯技术也使得形形色色高坐家具接合更加牢固,形制更加多样化,从而也更具有审美的性质。
最后来看看唐代生活美学渗透到家具制作和应用的领域,从而从根本上使得唐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成为现实。人类的日常生活与一般的高等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类除了日常生活的实用性的需要满足之外,还有着审美化的需要追求。而在中华民族的审美历史发展上,人们的审美是与伦理(政治和道德)密切相关的,因而形成了与西方的科学型美学思想不同的中华民族的伦理型美学思想。唐代则是中华民族古代社会最为注意伦理型审美和美学的时期,审美和美学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最普遍的家居生活中的家具当然也就浸染着中华民族的伦理型美学精神。根据《唐代家具研究》的探究,“唐代是高坐和低坐家具并用的时期,因此家具的使用情况较之后世更为复杂,在不同的场合和事由之下使用不同的家具,体现着社会意识中的身份、礼仪等级问题”。而这其中也就渗透着伦理型美学思想。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尊卑贵贱有别的家具使用,在中华民族伦理型美学精神的实质上也包含着审美上的差异,因为只有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才可能产生在实用需求之上的审美追求,而相对而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比较丰富,统治阶级也比较讲究生活质量和日常审美的时代。为了美化家具,唐代工匠在形形色色家具上配上了涂装、镶嵌、雕刻、染织、书法、绘画,把日常生活的用具点缀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充满着伦理型美学精神,从而也把家具主人的身份地位渲染、烘托得一目了然,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家具使用的性别差异,也使得唐代家具的生活美学和审美情趣在比较开放的女性,特别是皇家贵族女性的家具之中尽显姿色。另外,唐代的家具陈设和使用也正好反映了唐代伦理型美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从而也促进了唐代家具的“由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转型”。作者从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论述了唐代家具的由低到高的转型过程,实际上也就蕴含着日常生活美学思想改变着家具的陈设和使用,从而影响到唐代家具的形制由低到高的转型,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陈设和使用家具,除了物质的、政治的、道德的实用目的以外,审美的、艺术的目的也是一个决定性方面,尤其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的唐代就更应如此了。比如,在前面分别论述“唐代家具的陈设和使用”时,就提到了茶道、书房、宴饮、由分餐制到共餐制的变化等等,就无不包含着生活美学思想的讲究和追求在内。
总而言之,正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工匠精神的弘扬、生活美学思想的渗透,改变了唐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产生了唐代家具由低坐家具到高坐家具的转型。这是《唐代家具研究》的结论。这一结论应该是符合事实而又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刊之论。
三、唐代家具生活美学的现代启示
该书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历史断代史的扛鼎论著,而且将直接影响中国当代美学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生活美学遗产,进一步建构和发展中国当代生活美学。
《唐代家具研究》从家具的特殊角度让我们窥见了唐代生活美学的主要特征,也可以窥见唐代生活美学通过家具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与唐代的总体美学思想之间的微妙关系。生活美学思想是人们最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观念的一种方式,因此,它既可以成为一个时代、一群人们的总体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普遍表达,同时,它也可以促进、改变一个时代、一群人们的美学思想。比如,唐代美学思想,在总体上具有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倾向,同时也有追求华丽鲜艳的“浓艳”情调,因此,在唐代的家具的制作、装饰、陈设和使用上都可以见出这样两种审美情趣,而这种家具的生活美学思想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唐代的总体美学思想的特征。唐代的家具髹漆工艺中的金银平脱、银棱、螺钿平脱等等,就是表现了“一种灿烂奔放、极其夺目的装饰效果”,“装饰风格繁密”的审美追求,当然多为一种贵族阶层专用的家具审美风格。唐代家具髹漆工艺的素髹和染色罩透明漆工艺是大唐家具制作和装饰的一大进步,这一进步应该与唐代“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种审美趣味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启先河的“崇尚自然”审美传统在唐代的重大发展和推进。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是一种道家美学思想的时代跃迁。于民先生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指出:“从审美倾向的总体来看,与初盛唐到晚唐政治思想变化的同时,存在着一个从崇尚壮丽雄浑到崇尚淡雅自然的转变。”这种审美倾向的总体变化就十分明显地显现在唐代家具生活美学思想之中,而《唐代家具研究》就以十分具体细致的家具实例个案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使我们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唐代家具生活美学思想。
我们在进一步发展中国当代美学的过程中,除了基础理论的深入广泛的研究、探讨、创新以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一些具体的生活美学部门中开掘出新的领域。刘显波教授、熊隽博士的《唐代家具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他们的家具生活美学是以唐代家具的转型经典为案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附上了十分精美的唐代家具线描图,从一个非常具体入微的角度和方面,以十分感性、可触可摸、可见可视的角度和层面,提供发展形形色色理论美学的材料、启迪、视野、思路、路径,可以让我们的中国当代美学在诸如家具生活美学、休闲生活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生活环境美学等等具体感性美学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深入广泛发展,让中国当代美学真正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美学,让美学从理论的象牙之塔走出来,奔向正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的中国人民身边,让中国更多老百姓受到美学的雨露阳光的沐浴和洗礼,逐步在各种各样的生动活泼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实践中造就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要知道,新时代中国当代美学不应该仅仅是高等院校课堂上的一门选修课,也不应该是某些专家高谈阔论的舞台,更不应该是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美学的本根应该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美学应该是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指南,是塑造人类美的心灵的养习所,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教科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从事这样艰苦细致的具体生活美学的研究和探索,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上繁荣发展中国当代美学,把中国当代美学提升为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美学体系,为世界美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注释:
[1][2][3][4][5][6][7][8][9]刘显波、熊隽:《唐代家具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第5页,15页,16页,82页,271页,285页,370页,303页。
[10]于民:《中国美学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