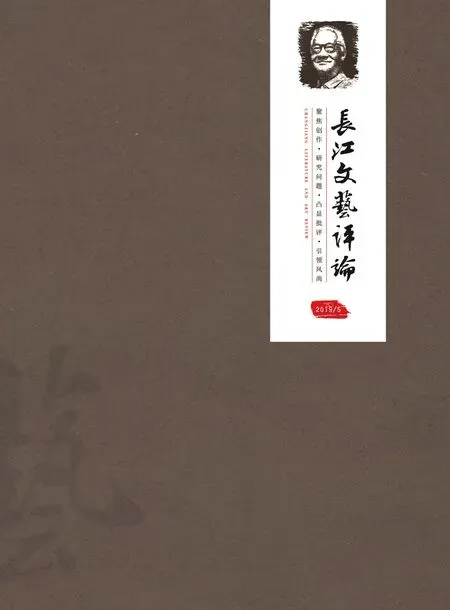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及其童心坚守
2019-11-12张德澳亚
◆张德澳亚 李 纲
在一次儿童文学研讨会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文学可以只谈文学价值,而儿童文学却要看销量?”这个疑问针对的是存在于全社会的一种普遍认知,那就是和被视为艺术品和精神食粮的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似乎更像是一种商品。当下,不仅全社会都在热议儿童文学作家的高额收入,甚至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也将自己作品的销量与营收挂在嘴边,将其视为作品取得的成绩。许多原本没有涉足儿童文学出版的出版社和文创公司也纷纷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进入童书出版领域,企图在儿童文学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种种迹象表明,儿童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片受人瞩目的商业热土。
然而,商品属性绝非儿童文学的专属。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一般理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而文学活动也包括生产、传播、消费这样一个连锁的动态过程,文学作品正是在读者购买和阅读的过程中,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文学活动都会受到市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创作、编辑、出版、销售以及产生相关衍生品过程中,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能在每一环节为相关生产对象带来利益,文学的商业价值就体现在其最终所产生的利益上。因此,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任何文学作品,只要它进入了出版与销售流程,商品属性就成了它本身所固有的属性。那么,为什么在当下的普遍意识中,唯独儿童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会格外受到关注?在文学生产日渐被纳入商业化运作的背景下,作家利用商业资本的介入为儿童文学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又该如何规避以逐利为目标的商业活动对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是当前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应该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儿童文学的商业价值
儿童文学的巨大商业价值与儿童文学特殊的受众是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且,儿童文学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启蒙功能和教育功能也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作为商品来说,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儿童而言可以说是成长道路上的“必需品”,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种“刚需”。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文学在当前只是文化消费的选项之一,与影视和游戏相比,文学在成年人文娱市场所占的份额可谓微乎其微。两相对比之下,儿童文学稳定的消费群体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市场保证,这也使得儿童文学的商业价值明显高于成人文学。所以,与其说儿童文学太像商品,不如说成人文学因为无法产生巨额的利润,在与其它文娱产品进行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没有彰显出其本身应有的商品属性。
此外,从商品消费的角度看,儿童文学的消费者也有其特殊性。文学作品的消费包含购买和阅读两个层面。对成人文学作品而言,通常情况下购买者即为阅读者。当读者有阅读需求时,便会购买文学作品满足自己的需求。换言之,一旦阅读需求被满足,购买行为便不会发生。但儿童文学不同,虽然儿童是文本的阅读者,但购买者却通常是家长。对子女成才的期待,以及在期待中不自觉形成的焦虑往往会造成一种过度消费,即家长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购买量会超出儿童的实际阅读量,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儿童文学的消费市场。而且,鉴于教育与升学竞争的日益激烈,语文学科在高考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当代社会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可以预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儿童文学市场将会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
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面对这样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涉足其中。资本的介入一方面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推广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也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引入了儿童文学领域。这也意味着儿童文学被纳入商业市场,儿童文学的创作一定会受到商业生产准则的影响。2018年9月15日,湖北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和武汉出版社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成立了“董宏猷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这是国内首个由出版机构、研究机构和作家共同组成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儿童文学又一次开了全国之先河。
出版社为作家的创作和学者的研究提供经费支持和出版便利,此举对于湖北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无疑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出版社作为自负盈亏的商业单位,在儿童文学事业中追求经济效益也是合理的诉求。资本、创作和研究三者结合后,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创作、编辑、出版、销售等各环节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商业社会中,不管儿童文学的从业人员是有心还是无意,儿童文学都已经势不可挡地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
二、商业化对儿童文学的积极影响
儿童文学与商业化生产模式结合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儿童文学作品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能为儿童文学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资本和人力上的保障。中国儿童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终于在21世纪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正是得益于儿童文学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庞大的少年儿童消费群体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有着巨大的需求。但这并不表示儿童文学作品的目标是成为书架上待售的图书,而是说商业化社会使得儿童文学拥有能够更好发展的条件,商业资本也成为了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动力。
在商业化社会中,作家与市场之间的付出是双向的。作家为市场提供了作品,市场也不会辜负作家的心血,除了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是对作家劳动的应有回报。以前,对于体制之外的作家而言,全职创作即便不是一种幻想,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但现在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却使全职创作成为一份收益颇丰的工作。当创作不再需要靠情怀苦苦支撑,而是能够带来足以谋生的酬劳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这一事业,从而促使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就当代湖北儿童文学创作而言,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梯队齐全的队伍。董宏猷、徐鲁等老一代作家继续肩扛湖北儿童文学的大旗;萧袤、黄春华等中年作家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舒辉波、陈梦敏等青年作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已经跻身国内一流儿童文学作家的行列;邹超颖等新生代作家也是佳作不断。众多有才华的作家源源不断地出现并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之中,与儿童文学市场为他们提供的收入保障是密切相关的。
有市场就会有竞争,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之一。哈罗德·布鲁姆曾用“影响的焦虑”来描写作家之间的关系,但他对这种关系的描述只是局限在作家与前辈经典作家之间,即“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阴影,后来诗人就必须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争取自己的诗作在诗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对于商业市场中同代作家之间的竞争,布鲁姆并没有考虑。事实上,儿童文学商业化的环境下,当代作家包括儿童作家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商品生产者。这就使得所谓“影响的焦虑”在他们身边变成了双重焦虑。一方面,作为精神文化产物的生产者,他们渴望自己能跻身经典作家之列;同时,他们也必须通过与同代作家的竞争,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其实背负着比自己前辈更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也促使作家不断提升自我,突破自我,以便在竞争中彰显自我。以湖北作家黄春华为例。黄春华的文学生涯始于小说创作,以《杨梅》为代表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帮助他奠定了自己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但此后黄春华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近年来在童话、绘本等领域多有新作,作品基调也逐渐由伤怀抒情变为轻松诙谐。这种变化既是作家的一种自我突破,也是对于日益扩大的低幼童话和绘本市场的一种回应。当竞争的压力使得作家无法安然躺在功劳簿上,只能不断寻求新的创作增长点时,最终受益的依然是读者和整个儿童文学事业。
从商业化中受益的不只是作家,还包括读者。用户购买商品,是因为有使用该商品的需求,但现代商业运营已经进入了主动创造、挖掘用户需求的时代。如果说以往儿童文学作品是静静躺在书店的书架上等待读者去选择,那么在当下,资本已经将作家和作品推送到了读者面前,主动激发读者的购买和阅读欲望。当其它文学作品还停留在传统的作家签售这一营销方式的时候,儿童文学已经在资本的助力下主动走进了校园和社区,各个绘本馆、亲子阅读机构和儿童阅读推广组织也成了推介作家作品的前沿阵地。这种几乎无孔不入的推荐方式不仅让儿童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作家和作品的机会,也强化了他们对于儿童文学的认知与认可,进而从文学阅读中受益。
三、商业化对儿童文学的消极影响
商业化确实为儿童文学注入了活力,但是商业化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任何一种商业行为都是以逐利作为最终目标的,而这种逐利动机一旦渗透到从文本创作到终端销售这一系列环节中,一切都将以利益为先,使得文学艺术有“完全掉进了商品世界之中,是为市场生产的,目标也在市场上”的风险。儿童文学市场亦是如此,销售量成为衡量一本童书价值的主要标准。在消费社会中“顾客就是上帝”,商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刺激消费者进行消费。虽然儿童文学作品的实际购买者是作为家长的成年人,但其真正的精神消费者依然是儿童。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市场中的儿童文学就是待售商品,儿童是目标顾客,儿童文学“一切为了孩子”的创作宗旨在这种环境中就多了一层刻意迎合的意味。“儿童至上”的内涵在某些情况下从“儿童文学创作应该引导儿童”逐渐变为“儿童引导儿童文学创作”——即儿童文学创作以取乐儿童为主,投儿童所好,用儿童喜欢的题材、语言和内容吸引儿童。商业化的儿童文学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和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蕴,而是儿童是否愿意、喜爱阅读。有意地去满足儿童的喜好,归根结底,能够成功出售才是商业化儿童文学的首要目标。这显然有违儿童文学的创作初衷,因为“儿童文学是儿童成长的教科书”,其价值之一就是引领孩子更好地成长。
在市场的指引下,会有越来越多的畅销因素、商业写作技巧显露、成型,再被投入创作中运用,久而久之儿童文学的创作之路会越走越窄,最后被困于儿童文学市场的某一端。短时间内速成的儿童作品几乎没有生命力,儿童文学创作也容易陷入儿童文学市场的虚假繁荣中,在市场动向的指引下进行模式化创作的儿童文学必然缺乏不断拓宽写作范围的创新力。当然,这种创新的阻力并不主要来自于作者对市场的迎合,更大的阻力其实来自资本的要求。因为出版社会更乐于投资、出版受到当前市场欢迎的作品,这就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的出版路径。对任何一种文学来说,创新都是其不断向前发展、紧跟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动力。失去创新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力,图书市场中成功的商业化童书背后的成功轨迹正在不知不觉中削弱儿童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在现代商业社会,为了童书的热卖、畅销,最大程度地吸引尽量多的儿童读者,除了作品本身的内容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外,宣传造势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各种作者见面会、签售会、分享会。商家创造出一个平台,提供儿童读者和儿童文学作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往往有一个隐性且必须的要求,即需要携带或现场购买作家的书,实际上这是一种以作家亲笔签名为表象的捆绑销售行为。这样的活动对于作家、出版社、书店来说自然是多多益善,却无益于儿童读者的阅读和儿童文学的发展。现代的儿童也面对着沉重学业压力,课余阅读时间本来就并无富余,频繁的宣传活动反而会占据儿童原本的学习时间以及课外阅读时间;另外儿童读者心理发展尚未成熟,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也很薄弱,在商家的大肆宣传下更容易跟风而行,盲目购买图书而不顾作品本身是否具有阅读价值;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过多的宣传活动也会占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的时间、精力被挤压、被分散,在这样的状态下也很难创作出优秀的儿童作品。
四、商业写作与童心坚守
现代商业文明是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环境,儿童文学商业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不可避免地会追求商业价值。而且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更为深广,这就使得儿童文学成为了商业化时代里文学捍卫自身艺术属性和精神价值属性的前沿阵地。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首先,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作为主要受众,而作家在创作时,也已将儿童作为隐含读者,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儿童文学先天具有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保住艺术底限和价值观底限的能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成人身份的内涵之一就是“成人对儿童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也曾将儿童文学分为“父爱型”和“母爱型”两种类型。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身为成年人的作家在为儿童创作文学作品时,其成人身份决定了作家不可能无视儿童文学,必须有益儿童成长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呵护儿童、关爱儿童实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这一物种得以生存延续的重要保障。所以,儿童文学受众的独特性既是儿童文学商业化日益增强的原因,同时也是儿童文学能够坚守艺术底线和道德底线的重要保证。
由此不难发现,如果想充分利用商业资本为儿童文学产业提供更好的运营生态,同时也使儿童文学事业避免受到商业运营模式中产生的一些不利因素影响的关键仍在作者。或者更具体地说,在于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如何呵护自己的童心,保护读者的童心。只要我们的作者能坚守住这颗童心,就能在创作中创造万物有灵、平等和谐的世界,弘扬真、善、美的品质。借助商业推广的力量,这种文本能被更多的读者阅读。一旦读者的童心被有效地呵护,并养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阅读品位,就会愿意购买相应的作品书籍,资本就会更乐于推动此类作品的出版与传播。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无疑是作家、读者、资本三方的共赢。
此外,各级作协和政府宣传部门设置的儿童文学奖项也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商业生态中发挥着弥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官方的奖项是以价值观和艺术水准为评价依据,作品的销售量和作家的版权收入并不在考量范围内。但是由于官方奖项具有足够的公信力,所以一部作品一旦入围荣获某一奖项,甚至只是进入候选名单,都可能成为这部作品的绝佳卖点,为作品带来丰厚的销售收入。2018年,两位湖北作家的作品,即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和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这两部作品都是作者应出版社邀约而创作,并且出版社在策划选题时就将冲击奖项作为了预期目标,最后的结果也未负众望,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由此可见,商业化对文学来说绝不是洪水猛兽。目前儿童文学行业的整体生态要求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必须适应商业化,但是商业化运营和文学创作并不矛盾,相反,还可以相互助益。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在坚守文学艺术本质的基础上,适应商业化时代的要求,创作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满足当下少年儿童的审美需求、倡导积极价值观念的作品,既是对儿童文学读者的关爱和负责,也是对商业社会中的文学创作如何兼顾商品属性和艺术属性具有示范性的探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2页。
[2]【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周志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5]李纲:《英国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