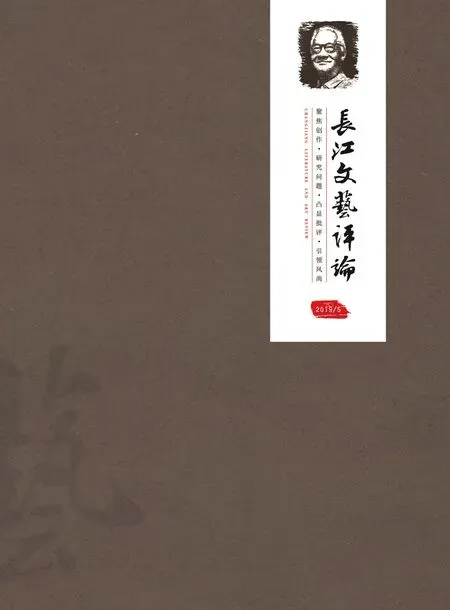苏童的“旧美学”与“新文景”
——兼议《黄雀记》的存史问题
2019-11-12沈杏培
◆沈杏培
对于熟悉苏童写作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返初”或“重复”之作,几乎聚合了“香椿树街”母题和“南方美学”的全部元素:破败潮湿的江南小镇,阴郁躁动的小儿女和动荡、暴力的青春往事,逼仄压抑的生存环境和无可逃遁的悲剧。苏童似乎用《黄雀记》重返写作的起点,悉心演绎关于城北或桑园式的江南之境和阴郁往事,这是对“南方”的一次深情回眸,也是一次带有总结意味的重复。苏童今后的写作将会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追问的是,在这部带有苏童印记的长篇小说中,苏童如何使他的“旧美学”焕发新的光彩?在众多直击现实的长篇巨制中,苏童的现实美学呈现怎样的特点,为当下炙手可热的现实主义写作开辟了怎样的空间?在读者视野中,这部标签之作在经典化和存史向度上受到了哪些质疑?
重复与挽歌:母题的再现与敌意的“南方”
苏童的写作起步于“枫杨树”和“香椿树街”两个系列,这是两个带有标识性的地理标签,尤其是香椿树街,在后来的写作中屡屡出现,几乎成为苏童的一个写作母题。在王德威看来,苏童塑造了一个纸上的“既真又假的乡愁”,他的小说有两处地理标记,一个是作为想象故乡的枫杨树村,一个是故乡父老落籍或移居的香椿树街,苏童在这两个空间建构出关于南方的“民族志学”,苏童以一个南方子民后裔的视角,表达了对于自己文学原乡的“暧昧”立场:“他是偷窥者,从外乡人的眼光观察、考据‘南方’内里的秘密;他也是暴露狂,从本地人的角度渲染、自嘲‘南方’所曾拥有的传奇资本。南方的堕落是他叙事的结论。”诚哉斯言,堕落的南方,以及外乡人和本地人的二重视角一直贯穿着苏童的原乡写作。
苏童为什么要写《黄雀记》这部小说?
最直接的触媒便是,他熟悉的一个腼腆的街坊男孩,意外卷入一起轰动一时的青少年轮奸案,以及青少年时期上学路上总会看到的独居老人瘫痪在床,臭气熏天的场景。这些原型事件和原生场景,是引发苏童塑造祖父、保润形象并因此铺衍蒙冤、复仇、忏悔情节的现实因素。苏童用这篇小说,试图为这些或蒙冤或沉默的生命招魂立传。其实,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苏童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讲述发生在青春小儿女身上的悲戚往事,或是简单呈现香椿树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变迁,而是试图以香椿树街为窗口,去透视后“文革”时代的历史变迁——以保润、柳生和仙女这些小儿女们青春时代的孽债去摹写浮躁年代中人们的失魂、罪孽、救赎等精神生态和生存困局。从叙事形式来看,《黄雀记》走的是香椿树街的老路,实际上,苏童言近旨远,他只是在借南方叙事的壳去拥抱这个大时代的“新现实”。在苏童以往的叙事格局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烟尘和时代面影,是他津津乐道的内容。而《黄雀记》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椿树街依然是香椿树街,但小柺、红旗、舒工们的“文革”时代已过渡为保润、柳生、黑卵、春耕的改革开放时代,苏童关注的时空已转向了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大地。“我写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小城,似有怀旧感,其实是把自己的时代记忆移植为人物所处环境中了。八十年代很有活力,甚至还有点浪漫,启蒙的大幕拉开了。”
如果把《黄雀记》放在苏童的写作谱系上看,它并不是一个异数,而是对苏童既有写作的一个总结。《黄雀记》的主线是一个典型的苏童式香椿树街叙事:游荡在香椿树街的少年顽劣无序,青春懵懂,荷尔蒙旺盛,惹出强奸祸事,最终引发家庭分裂、少年入狱和蒙冤复仇等诸多悲剧。同时,《黄雀记》又有着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切入现实病症的巨大社会批判热情。发表于2002年的《蛇为什么会飞》是苏童的转型之作,被视为“苏童创作的第一部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作家为当下的中国病态社会及其病态人生提交的一份病相报告”。《蛇为什么会飞》描绘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高度物质化和欲望化的社会生存图景,“蛇”作为欲望的符号对应着消费时代林林总总的欲望景观和世态丑相。若即若离和高度隐喻化是这部长篇小说处理现实的基本特点。如此来看,《黄雀记》既是苏童香椿树街的南方母题的再现,又显示了他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浮世绘的专注刻绘。从大的立意来看,《黄雀记》已不再是对作为一己记忆的香椿树街少年心史的记录,而是以少年史演绎时代大戏,香椿树街的小风情和时代的大画卷相互映衬。在《黄雀记》中,香椿树街作为苏童的“原乡”,不仅仅是对原有乡景的呈现,还包含了他进击大时代和新现实的更大宏愿。
熟悉苏童作品的人都知道,苏童的“南方”从来都不是温润的、阳光的、和谐的,而是充满了暴力、死亡、偷窥、淫乱、犯罪。在《黄雀记》中,进入八九十年代的“南方”依然是堕落的,苏童对他的南方依然充满深深的“敌意”。从人物塑造来看,苏童笔下的少年顽劣阴郁,常惹祸端,少女妖娆美丽,而香椿树街的居民则精明世故,聒噪、“喜欢嚼舌头”。柳生第一次把怀孕的白小姐带进租好的房子时,小说这样描写乡邻们的围观:“她和柳生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看见香椿树街居民射灯般的目光,她像一个走T台的时装模特,面对着两边观众的挑刺或者赞赏,有一种裸身过市的尴尬。空气里有来历不明的嗡嗡的欢呼声,她听清了他们的议论,大多在赞美她的容貌,漂亮的,身材很好,脸盘也很漂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刻毒的声音传到了她耳朵里,漂亮是漂亮,就是那做派,有点像小姐吧?”这几乎是香椿树街的市井群像图,他们的神情、语言、动作日常而毒辣,他们貌似热情友好实则欺生排外,他们不放过每一个耳闻目睹的秘密或新闻。这是八九十年代香椿树街的群体肖像和民间精神生态。从《桑园留念》《南方的堕落》到《黄雀记》,时代在变化,香椿树街居民的日常姿态似乎没有变化。
这种人格气质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接近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在香椿树街,一直活跃着孙阿姨、绍兴奶奶、邵兰英、粟宝珍、马师母这样的市井人物,她们总是在探头张望,喋喋不休,神神叨叨,她们制造和传播着关于别人的流言蜚语,又成为别人的谈资与焦点。在《黄雀记》中,每个“事件”周围——比如祖父失魂,遣返祖父回医院,比如保润蒙冤入狱,比如白小姐租房子,都围着黑压压的香椿树街居民,他们仅仅是来围观这些“景观”的。小说最后部分,保润酒后捅死柳生后,人们把怨气撒到白小姐身上,展开了对白小姐的“围堵”和复仇。小说这样描写众人的围观场面:“最初是几颗石子投在阁楼的窗子上,然后是一块碎砖,最后,有只啤酒瓶子咣当一声飞进来,窗玻璃碎了,啤酒瓶子穿越阁楼,滚下楼梯,在她的脚下滚动。她捡起酒瓶回到阁楼窗边,看见下面浮动着一堆大大小小的脑袋,邵兰英披头散发,面色灰白,坐在大门口。”这些“大大小小的脑袋”俨然正义的化身,在死者母亲非理性的讨伐身影里,群情激愤地充当着帮凶。他们并不会去辨析在保润、柳生、白小姐的复杂纠葛中,谁是悲剧的制造者,谁是受害者,他们更不会体恤白小姐挺着大肚子水上逃命的危险,或是同情她的被强暴的青春和动荡的人生。香椿树街的这种民众性格和人格气质所具有的原始性、暴力性,彰显的正是苏童南方地理上颓败的人性风景。
一直以来,苏童一直钟情于这个充满腐败和魅力的香椿树街,而香椿树街在实际生活中都有具体的原型。无论是现实的故乡,还是这样一个文学原乡,苏童都充满着某种敌意。他曾说:“我从来不认为我对南方的记忆是愉快的,充满阳光与幸福的。我对南方抱有的情绪很奇怪,可能是对立的,所有的人和故乡之间都是有亲和力的,而我感到的则是与我故乡之间一种对立的情绪,很尖锐。在我的笔下所谓的南方并不是那么美好,我对它怀有敌意。”可以说,苏童一直书写的幽暗、潮湿、凝滞和阴郁的香椿树街是具有某种挽歌气息的文学原乡,这里的景致并不美,这里的人也不可爱,时时带给人压抑之感和逃离之感。苏童已在这个“堕落的南方”故乡深耕细作三十余年,从几年前的大都市(《蛇为什么会飞》)、油坊镇(《河岸》)再次返还香椿树街,堕落的南方依旧颓败不堪,而苏童对南方的“敌意”也未消泯。《黄雀记》是否是苏童关于南方的绝唱,苏童在“敌意的南方”写作征途上还能提供哪些气象与文景,这些问题关乎到苏童写作的未来走向,值得期待。
被缚与丢魂:普遍的时代困局与苏童的现实美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社会经济和物质水平极大提高,同时在全球化浪潮和经济利益的裹挟下,面对传统向现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数度转型,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诸多社会乱象和精神困境。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社会在剧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以及作家们集体转向对现实的言说,正是对于这一时代的回应。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极花》、陈应松的《还魂记》、东西的《篡改的命》、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及苏童的《黄雀记》,都是对这个时代病症进行描摹、试图探究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的重要文本。
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苏童从来不喜欢那种“贴得太近”的现实美学,而是主张既贴近,又若即若离,保持“离地三公里的飞翔”。在苏童看来,对现实的发言,不必步步紧跟正在发生的、或是离当下很近的那些现实,而应借助时间来沉淀、淘洗纷繁复杂的现实症状。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现实观:“我一直觉得写当下其实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当下的问题提炼成永恒的问题,可以囊括过去和未来,这倒是个问题。当你提炼不得或未提炼成功的时候,不应该急匆匆地扑到当下中去。”
在《黄雀记》中,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复杂纠葛,以及三个家庭的动荡或解体中,我们能够轻易捕捉到大时代的面影,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由这些碎片化的现实和症结构成了关于八九十年代生动的时代肖像。但苏童的兴趣并不在此。他感兴趣的是对“疯人院”这一精神空间,以及“丢魂”这一意象的精雕细琢。在小说中,井亭医院是一个处于郊区、交通不便利的精神病医院,这里“活跃着”各种精神病患者:声称丢了魂、整日挖地找魂的祖父,撅着苍白干瘪屁股在走廊上蟹行的古怪病人,眉头紧锁逢人声称被迫害的秃头男子,还有得了花痴病露乳募捐的柳娟,得了妄想症总是怀疑有人要暗杀他的城南首富郑老板——“疯癫”是《黄雀记》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祖父在小说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象,考察祖父的疯癫史,会看出现代社会文明内部的虚伪性与残酷性。这种意义有二:第一,祖父的疯癫史昭示了现代“理性社会”的秩序和暴力。丢了魂的祖父被当作疯子送进了井亭医院,至此祖父也开始了他的漂泊之路和被驱逐命运。祖父离开家后,随着经商浪潮在香椿树街弥漫,祖父的房间很快被儿媳粟宝珍租给马师傅开了精品时装店。这还不算,祖父房间的家什被处理殆尽,连那张祖父安身的红木雕花大床也被儿媳贱卖给了古董店。祖父在这个家庭从未得到儿孙们的孝敬和优待,“失魂”后到处挖树的行为给儿孙带来了无数的麻烦,由于照顾他的任务繁重,儿子因此中风瘫痪。在粟宝珍的詈骂声中我们能够看到年老的祖父在这个家庭中的尴尬处境。从家人对祖父房间的清理来看,他已被送上了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愚人船”,“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病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病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这也意味着,送往井亭医院后,祖父已被这个家庭从家族的空间意义上除名了,这种驱逐在精神的意义上与中世纪的愚人船并无二异。但似疯非疯的祖父有着回归家庭的热望,他日夜巴望着回家,甚至花了三十块钱买通门卫偷偷跑回家。回家的祖父看到的当然是没有了其栖身之所的陌生环境,有家不能归的祖父此时成了失去家园庇护的孤儿。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井亭医院管理祖父和大部分普通病人的最有效措施是捆绑。比如在把祖父遣返回医院的过程中,并没有大费周折,仅仅依靠一段绳子便让盛怒和绝望之中的祖父乖乖就范。经年被缚的祖父,看到捆缚自己的绳子,犹如犯人见了惩戒自己的刑具一样顺从。在小说中,捆绑是一个重要意象。捆绑最初是由保润发明,在看护祖父的百无聊赖中,他发明了名目众多的捆绑方式。事实证明,这些松紧不一的捆绑方式给医院的看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得到了院长的赏识。保润因此获得了“捆绑艺术家”的美誉,并被安排以“业余专家的身份”给医院护工上捆绑观摩课。在这里,捆绑不仅是无业青年保润确证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也是医院积极推广的一种新式管理路径。疯人的顺从与反抗、守纪与越矩,决定了捆绑的方式。在这里,捆绑这种原始手工艺术,“有效促进”了理性与疯癫之间的交流。当然,再温柔的绑缚仍然是奴役和束缚,井亭医院并非一个真正以病人为本位,积极改革从而提升服务品质的社会机构。苏童意在通过这种带有想象的意象呈现当代医院存在的种种乖张和荒诞。实际上,在祖父和家人之间,在祖父和医院之间,真正的交流是缺位的,没有人会去关心、理解和帮助祖父,祖父孤独地行走在自己的挖掘找魂和偏执反抗中,而这种寻找和反抗被理性社会看成是病,得到的是更大的惩戒。
第二,祖父的疯癫具有巨大的隐喻意义,祖父的寻魂和找魂在更大意义上是在隐喻当代精神失范、灵魂空虚的社会现实。“失魂”是小说不断强化的一个概念。在各种找魂与治病的行为中,郑家姐弟的招魂之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了暴发户式的放荡和浮夸,显示了资本和金钱在当代社会的巨大宰制力量:因为郑家姐弟有钱,他们可以住特等病房,因为他们有钱,可以雇年轻女子为郑老板进行女色治疗,因为他们有钱,乔院长不得不准许他们在医院搭建私人香火庙。当然,这种恃钱而骄的做派在小说中遭到了以康司令为代表的权力人物的抵制,权贵和资本为此展开的博弈,谁胜谁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之下的拜金思潮和各种丑陋现象开始在香椿树街登堂入室,瓦解着原本封闭和单纯的生存法则。当香椿树街的“万元户越来越多”,枫林镇成了“买春的天堂”,人们精神的失范和灵魂的扭曲似乎并不奇怪。苏童关注的恰恰是被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的“南方”,究竟是怎样堕落的?这些失态丢魂的人们又是如何应对这种生存困境和心灵危机的?
在失魂的人群中,祖父显然是那个执着要找回灵魂的“堂吉诃德”。在自己的幽暗世界里,只有祖父明白自己的“理想”与“逻辑”:失魂的他一心想找回丢失的魂,以免除下辈子不能做人的恐惧。但祖父的挖掘行为和偏执的寻魂之旅破坏了理性社会的秩序,落得被驱除出家,终日被捆缚在医院的下场。祖父显然是理性社会的异类和疯人,他具有显豁的隐喻之意,这种隐喻也即福柯所说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福柯指出,由于疯人所具有的巨大“象征”功能,在文学作品中,病人、愚人或傻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见惯的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他此时的角色是对故事和讽刺作品中的疯癫角色的补充和颠倒。当所有的人都因愚蠢而忘乎所以、茫然不知时,病人则会提醒每一个人。”
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高度写实的作品,这种写实并非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实”,而是以夸张和荒诞的形态表现出的具有高度象征和隐喻意味的社会之实。被缚和失魂,是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一种困境。香椿树街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浓缩了这个时代的飞速剧变,以及社会转型之中人们失重、纷乱的精神。苏童将长大了的香椿树街的小儿女们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喧闹语境里,让他们成长,让他们直面生的烦恼,承受生存之重。螳螂、蝉与黄雀之喻,无非是苏童对复杂人世间人与人,情与情、关系与关系复杂纠缠而又相互掣肘、此消彼长的一种含混譬喻。
混响与正典:两极化批评视野与存史的可能性
根据M.H.艾布拉姆斯的“世界—作品—作家—读者”的文学四要素理论,作家的意义表述和文本价值的实现,不应仅仅局限在“作品—作家”这一封闭的系统里,还需要经过读者接受这一重要环节才能最终实现,这也是接受美学在考察文本价值极为看重的方面。《黄雀记》能否走向经典,是否具有存史的可能和内涵,读者的批评视野不可忽视。纵观《黄雀记》发表以来的读者阐释史,批评与肯定构成了读者批评的两极。
先看那些批评之声。由于《黄雀记》是一部体现苏童“旧美学”的新作,如何看待苏童再次启用这些旧元素、旧场景、旧情节来构建文学时空,成为一些读者与批评家的关注焦点。批评家唐小林将《黄雀记》视为苏童的“换汤不换药的旧房改造”和“重复写作的拼凑之作”,他认为,这部新作是苏童对以往“香椿树街”系列故事的又一次“大炒冷饭”,“《黄雀记》的写作,不但没有突破苏童原来香椿树街的写作模式和描写的内容,反而让人看到了他在写作上的一次不幸的堕落”。在他看来,这种雷同体现在人物和情节的类型化上。同时,唐小林对《黄雀记》中的露乳募捐和烟头烫乳的暴力描写,感到不寒而栗,将“畸形的性描写”和“渲染骇人的暴力事件”视为苏童小说最显著的“两大标配”。另有学者将《黄雀记》放在苏童自先锋到回归的轨迹里进行考察,认为“这是苏童摆脱先锋派烙印的一次努力,但依然明显地留有先锋派的影子,在这里,苏童依然十分关注小说的表现形式,在文本意识和叙述策略上下足了功夫,以意识流的方式将记忆的碎片一一整合,技巧十分娴熟”。但由于过度依赖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技巧,小说的整体性和重返现实的努力大打折扣。还有研究者从长篇小说的体例和品质角度指出,《黄雀记》在长度上没问题,但“密度不足”——人物密度和事件密度都不尽人意。“小说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在小说的结构功能上意义重大,但每一部中的人物都不太复杂,一些人物的象征性功能盖过了人物本身。事件的密度也不足,小说中重要的事件往往和历史有关,介入现实并不那么深入。”
在这些批评之声外,不少研究者对《黄雀记》给予了肯定。王宏图将《黄雀记》视为苏童在其漫长的创作历程中经过诸多不无艰难的探索后的一部回归性的作品,同时指出苏童在创作《黄雀记》时面临的矛盾创作心理:一方面苏童擅长在虚拟的历史布景下展开艺术的想象,写实并非苏童所长,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感召唤下意欲通过介入现实的方式实现创作的转型,开拓写作的疆域。而区别于《菩萨蛮》中的“亡灵叙事”和《蛇为什么会飞》中的“反讽方式”,《黄雀记》“成功地创造出一种以象征的手段重新介入现实的方式”,“为文学如何面对现实发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2015年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显示了学界对这部作品的主流看法:苏童的短篇一向为世所重,而他对长篇艺术的探索在《黄雀记》中达到了成熟,这是一种充分融入先锋艺术经验的长篇小说诗学,是写实的、又是隐喻和象征的,在严格限制和高度自律的结构中达到内在的精密、繁复和幽深。
纵观这些关于《黄雀记》的尖锐批评与褒赞肯定的两极化阅读视角,可以看出,读者对于苏童写作中的风格化与转型、艺术真实与逻辑真实、如何介入现实等命题意见不一。这些阐释与争论确实也从各个层面彰显了《黄雀记》这一文本的意义与局限。《黄雀记》能否成为苏童长篇小说的代表性文本,能否成为新世纪众多写实文本中的经典之作,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而成为茅奖作品中的正典,这些问题取决于评价主体的当下标准,更取决于苏童这部作品自身的品质。布鲁姆在《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一文中说:“作为批评家,我们只能进一步确证真正强有力预言家和诗人的自我正典化。我们不能随意虚构他们的正典化。”确实如此,评估作家的文学品质及其经典化问题,是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内在要求,而能否入史,则是见仁见智的难题。同时,作家的经典化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其建构和内涵具有历史性。
尽管如此,在布鲁姆看来,走入正典的作家并非没有共通之处。在他精心挑选的进入“正典”的二十六位作家中,布鲁姆找到了这些作家与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对于苏童来说,已然经典的南方美学和香椿树街标识,已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恰恰是依靠这种原创性带给读者的陌生性和文学震惊,成就了苏童的声誉和文学史坐标。问题在于,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而不是以逸待劳的流水作业,这就需要作家在现实的土壤和想象的王国里常写常新,常常能带来形象、主题、形式、思想的“陌生性”,这种陌生性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刻意所为,而是基于文学自身革新和变化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苏童和当代作家来说,守护写作原创性的方式不是简单重复既有文学品牌,而是常常在这种原创性的文学质地中注入新的品质,让陌生性成为文学的常态。具体到《黄雀记》来看,在苏童的写作生涯中,《黄雀记》具有总结意义和标签作用,体现了苏童式的香椿树街母题和南方美学,它所提供的关于当代社会“丢魂”和“被缚”的精神困境,及其若即若离的隐喻式介入方式和苏童式的阴郁悲剧美学,都使这部小说成为颇具文学“陌生性”的文本。
注释:
[1]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读书》,1998年第4期。
[2][3]苏童:《我写〈黄雀记〉》,《鸭绿江》,2014年第4期。
[4]李遇春:《病态社会的病相报告:评苏童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小说评论》,2004年第3期。
[5][6]苏童:《黄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254页。
[7][14]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196页。
[8]刘科:《苏童推出新长篇〈黄雀记〉》,http://cul.sohu.com/20130606。
[9][10]【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10-11页。
[11]唐小林:《苏童老矣,尚能写否?》,《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1期。
[12]唐宝民:《苏童回归传统的失败》,《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3期。
[13]张晓琴:《“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论〈黄雀记〉与小说家的自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15]徐勇:《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6]【美】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17]【美】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