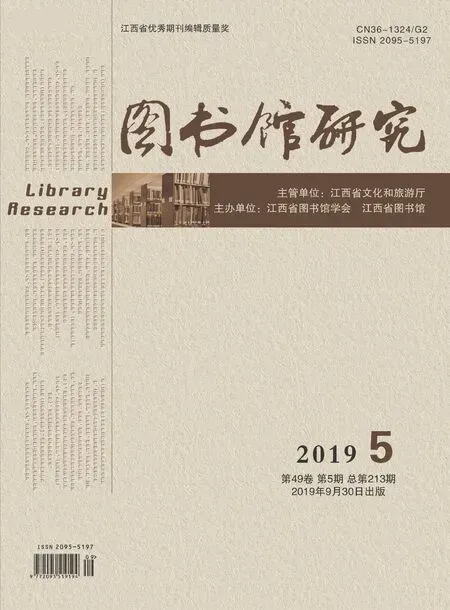近代山东教会图书馆史略
2019-11-11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199)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58年,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各国传教士可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这些教会建教堂、创学校、兴机构开展宣教活动,从而巩固并扩大教会组织势力。山东的烟台、青岛、威海等城市先后被迫开埠,传教士亦纷纷大批进入山东传教,先后以登州、烟台为据点,继而深入内地,划分教区。山东天主教和基督教等教会势力在全国来说都占有靠前的位置。“基督教在山东布道区之多,居全国第一;信徒人数,居全国第二;西教人士,居全国第五;教会中小学数,居全国第一;教会医院数,居全国第四等”[1]。山东天主教徒在全国之地位,光绪三十三年(1907)占全国教徒总数的7%,次于直隶、江苏、四川(包括西藏)、广东,居第5位,民国九年(1920)次于直隶和江苏列第3位。[2]
1 山东教会图书馆概况
开展教育事业是教会传教活动的重点之一,至1918年,全国教会学校已达13 000所,绝大多数为中小学,教会大学相对建立较晚,基本上是在20世纪初教会所属“学堂”“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主教会在山东创办的中学与全国的天主教中等教育相比,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据1930年统计,全国共有天主教中学51所[3],其中山东十多所,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山东的基督大学仅有齐鲁大学一所。
教会图书馆则是随着学校或文化机构的兴办而发展起来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图书馆,多附设于学校,一般规模都很小,较大的图书馆一般附设于各大教堂中,济南、青岛、烟台等的教堂附设教会图书馆,藏书都较丰富。如圣言会兖州教堂,该教堂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巨野教案赔款修建的,藏书就比较多,据说教堂建起后,余款均购买了图书。不过,教会图书馆的藏书多是神学方面的,一般不对外开放。

表1 基督教学校图书馆民国二十五年藏书情况[4]
从表1各学校教会图书馆藏书数量上可以看出,除齐鲁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在10万册以上,其余皆相对较少,最多才1.5万册,订购杂志种数更是少之又少,有的甚至没有,进一步印证了学校图书馆规模之小。
除了教会学校图书馆以外,山东省各地设有青年图书馆(烟台、济南、青岛等),还有与博物馆共存的广智院图书馆和创办较早的尊孔文社藏书楼等。本文通过对这4所不同类型、性质的教会图书馆进行深入分析,以窥民国时期山东教会图书馆之全貌。
2 山东四大教会图书馆
2.1 齐鲁大学图书馆
齐鲁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868年的登州文会馆的藏书室,1904年登州文会馆和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潍县广文学堂,藏书室改名为广文学堂图书室,1917年广文学堂又与济南共和合医道学堂合为齐鲁大学,三校藏书亦合组为图书馆,即齐鲁大学图书馆,当时三校合计藏书也只有19 000余册。[5]
图书馆开始设在校内柏尔根楼上,不久又移到考文楼。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奚尔恩出任首任馆长,聘王天纲任图书馆主任,办理全馆事务,另有馆员5人,分别负责编目、出纳、阅览、典藏、文牍和购书等事务。1921年,齐鲁大学接受加拿大危培格(Winnipeg)之奥古斯丁(Augustine)长老会支会捐款,开始在校内的东南角修建一所新的图书馆,于1922年竣工并投入使用。为了对奥古斯丁长老会表示感谢,此馆亦称为奥古斯丁图书馆。奥古斯丁图书馆曾先后聘巴达、桂质柏、皮高品、陈鸿飞、邢云林等为主任,诸君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界的重量级人物,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图书馆无论是藏书、文献组织、业务管理等都有长足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另齐鲁大学图书馆设有一医学院分馆,医学文献资料均存放于此馆。为了方便检索馆藏,馆藏目录卡片制作两份,一份存总馆,一份存分馆。
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主要由各学系自行购入,但须经图书馆查重,再送图书馆保藏,同时接收社会捐赠。1929年“馆内原有书籍约24 000余册,中西书籍约各半数,并备有西文杂志200余种,中文杂志400余种”,“民国十九年度复筹款添购中国书籍约50 000余册。”[6]至1931年藏书已达到74 000余种。1935年“图书馆又新购中文书2 140册,外文书1 200册,共3 304册”[7]。1936年增至118 000余册。

表2 齐鲁大学图书馆1917-1946年藏书统计表[8]
1938年,济南沦陷,齐鲁大学西迁成都办学,一部分藏书随学校转移至华西协和大学暂存,另有89 000余册由山东省图书馆接收。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省馆又将书全数返回齐鲁大学图书馆,“本馆现存中文图书87 000余册,西文图书18 000余册,共计105 000册”[9]。1952年,新中国推行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分割解散,齐鲁大学图书馆也随之消失。
2.2 烟台青年图书馆
1896年,美国教师韦丰年(George Cornwell)在烟台创办了青年会,1915年青年会全国协会为其颁发证书,1916年,会员达到700余人。[10]青年会大力宣传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先后举办公民教育、职工研究团、农村演讲等,后又特请南开大学校长、天津青年会董事张伯苓等来烟台青年会演讲,轰动一时。
1930年,基督教青年会为了进一步体现青年会宗旨、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创办了“青年图书馆”,成为烟台第一家公共图书馆,“胶东王”刘珍年还献上他亲笔书写的“文化渊薮”贺匾。青年图书馆从启动到建成,每个阶段皆群策群力,悉心筹备。首先公举筹备委员会长1人、委员2人。据统算,购书建筑两项费用,共需银1.2万元,创办费用不足,分别动募,成绩亦佳:“决定先由青年会内部捐募,以示提倡,于是地方长官,商界领袖,闻风兴起,解囊捐助。”[11]不到数月,创办费已达半数。其次派代表参观江浙各大公私立图书馆,对其建筑、藏书、布置等都一一详细研究。再次主要向大的出版社采购图书,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以为图书馆公共阅览为采访原则,共万余卷,数量在当时来说也算比较丰富。拆除旧房,改建二层楼房1所,内部计30间。管理员的人选非常严格,必须是有学识、有爱心、有耐心之士,因此派专门管理人员赴上海东方图书馆学习,以资参考。
青年图书馆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成了中共烟台地下组织的活动阵地。中国共产党在烟台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后任烟台临时市委第一任书记、1931年8月在济南英勇就义的许瑞云烈士以及1927年介绍许瑞云入党、1928年5月被选为烟台历史上第一位党支部书记的徐约之等早期共产党人,都经常在青年图书馆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2]
1945年,烟台基督教育青年会领导人离开烟台,青年图书馆随之关闭。
2.3 尊孔文社藏书楼
尊孔文社藏书楼既是青岛第一座图书馆,也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图书馆之一。1914年尊孔文社藏书楼在礼贤书院内落成。礼贤书院为卫礼贤于1900年在青岛成立的教会学校。当年的礼贤中学是清末民初胶州湾地区最新式学堂样板,是我国北方地区建立最早的现代中学之一,也是卫礼贤留给青岛的最大的一笔“遗产”。卫礼贤,德国传教士,1899年进入中国传教,在其57年的生涯中,有24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其中在青岛多达21年。他本人喜爱汉学,尤其尊崇孔子,对儒家学说佩服不已,学习中国文化孜孜不倦,“卫君最好学,手不停挥,目不停览,虽炎夏不避,危坐译读晏如也,是故精通华语及文义”[13]。其将《论语》《孟子》《易经》等20多部中国典籍翻译成德文,在西方广为传播,著名学者季羡林将卫礼贤称为“东学西渐”的功臣,被誉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辛亥革命后,大批清朝遗老跑到青岛,其中就有著名学者、学部副大臣劳乃宣。1912年,卫礼贤在礼贤中学校舍旁成立了尊孔文社,由劳乃宣主持社务。1914年又在其旁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收藏图书,开展借阅活动。虽名藏书楼,性质上已是为公众服务的现代图书馆。“藏书楼”匾额由当时寓居青岛的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题写。劳乃宣在《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论》中写道:“德国卫君礼贤以西人而读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也。时居青岛,与中国寓岛诸同仁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同人乐赞其成。”
2.4 广智院图书馆
广智院的创设者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于1887年在山东青州府建设博物堂,因其规范狭小,参观人数每年不过5 000余人[14]。为扩充起见,于1893年附设于“郭罗培真书院”。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济南既为省会,又交通便利,人文荟萃,故于1905年造新学堂于济南南关山水沟旁,同年落成典礼,更名为广智院,意为“广其智识”。教育学家黄炎培写到“院长英人怀恩光君,自购地建屋,于今十年,灿然大备。院长谓十年购地建屋及一切布置陈列约超耗费银九万六千圆,皆陆续捐募得之”[15]。山东巡抚杨士骧参加开幕庆典,怀恩光任首任院长。其后潘亨利、魏礼谟、斐礼伯、胡维恩、林仰山先后任院长,均为浸礼会传教士。设有各国人种模型室、万国史记室、商务研究室及阅书报室、体育室等,“所陈列各种标本模型写真与图表等项有二千余组,共计一万余件”[16]。广智院的建立可以说是济南科普教育的开端,它对开阔人们的眼界,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具有重要启蒙作用。
广智院作为社会教育机关,虽然没有设立独立的图书馆,但其开展的读书阅览活动一直未曾中断,初创期就设有阅报室,后又增设巡回文库,反映了其新式公共空间的特征。阅报室有报章杂志数十份,任人阅看,“阅报室陈列图书报纸,阅书用盘使,授受时书不着手。英文报告,一年阅书报者总数三万九千人”[17]。1920年上海广学会向广智院捐赠大宗图书,又创办巡回文库,由职员携书至各机关、学校、商号、寓所等巡回送阅,方便了民众的阅读,也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为了方便在官兵中布道,1913年4月,怀恩光还在济南纬十二路的辛庄军营附近设立“军界广智院”,设有演讲厅、阅览室、俱乐部、课室等,到1919年,“前往参观者达47 000人,其中军人占3万人,当年前往阅书室读书者达3 600人”[18]。
1917年广智院被并入齐鲁大学,名齐鲁大学社会教育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该院被日军接管,改为科学馆。
3 教会图书馆的读者、藏书及本土化
3.1 为特定读者群体服务
早期的教会图书馆受创始人(管理者)、馆舍建筑、馆藏条件、服务理念等限制,服务群体有其特定性,即读者中教徒占多数,如教会齐鲁大学图书馆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师生,不对校外读者开放,在其借阅条例中有“凡本校教职员学生,均享受借阅之权”,显示了它的服务对象是在校师生。而齐鲁大学在招收学生时,要求“至少须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是由基督徒的家庭来的,或者他们本人是已做基督徒的”[19]。1924年齐鲁大学基督徒学生比例高达89%,1934年仍为70%[20],进一步说明图书馆读者以教徒为主。
尊孔文社藏书楼初创时期依附于礼贤中学,“现只供礼贤中学教员及学生应用”[21],服务群体以礼贤中学的教职员和清朝遗老为多。烟台青年图书馆创建之初亦主要为青年会服务,也向社会开放。随着图书馆本土化的发展,教会图书馆开始面向公众,具有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
3.2 以西文文献为主的馆藏结构
教会图书馆的性质、读者群体的高教徒比例及创办者的理念,决定了教会图书馆的馆藏结构以西文文献为主,重视外文文献的收藏也成为各教会图书馆的主要特点。如齐鲁大学作为西式教会大学,为使西方文化“涵化”中华文化,无论是出于传教的目的还是教育目标,在教学中大量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设数学、物理等现代科学课程,故对西文书籍有较大需求,大量西文书刊被引入图书馆,“统计馆内书籍有一万六千余卷,其中之六千余卷为汉文,余一万卷为英文”[22]。1926年新馆落成后,“馆内藏书统计约一万九千余卷,内有汉文书籍约六千卷,英文书籍约一万三千卷”[23]。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西文书籍比汉文书籍占比要大。
在以西文文献为主的馆藏结构下,教会图书馆无论是西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在搜集时又以宗教类的图书优先入藏,而且藏量很大。同时这些图书馆亦非常重视珍本善本古籍收藏,如尊孔文社藏书楼,多方收集经史子集等文献。1935年许晚成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记载:尊孔文社藏书楼的“藏书有6 000余册中文,3 000余册德文,2 000余册英法文,共12 000多册,其中有不少善本”[24]。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成立,将图书馆馆藏特别是古籍善本书的收藏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栾调甫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图书资料的完备,1930—1932年共购入7 000余部,并专门成立善本书室,且编有《善本书目》及《书库总目》[25]。到1935年齐大图书馆藏书近10万册,扩充的部分大都为国学文献。
3.3 教会图书馆的本土化
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和北伐,更使许多传教士认识到教会图书馆本土化的必要性。“当他们开始比较了解中国文化而尊重中国文化时,他们便试着使西学与技术来适应中国国情”[26]。表现之一就是教会大学把服务乡村建设作为传播宗教的媒介,使乡村服务与传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如齐鲁大学在乡村建设上利用书籍进行乡村教育,充分发挥自身教会图书馆的优势,在龙山试验区内创办了“书报室”,把学校的图书资料免费向民众开放,“有日报:平民、大公、申报三份。周报三份:农村新报、民教周刊、兴华报”[27]。并指导民众认字读书看报。表现之二是出版书刊。卫礼贤主持编写了《德华课本》《德华教科书》《德华单字、语法、翻译》和《德文入门》,这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中学德语教材,也是中德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重要载体。表现之三就是重视汉文书籍和地方文献收藏,从图书馆的始建时西文占比较大,到后期汉文书籍超过西文书籍,也说明图书馆在收藏上逐渐本土化。
4 教会图书馆与近代山东社会
“图书馆应该是传教士的外会客室,在传教事业上是一种最直接最有力的工具”[28]。虽然教会图书馆是其传教的工具,但同时也应看到其对山东乃至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一定的促进作用。
4.1 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山东教会图书馆的出现,在客观上使得以藏书楼为基本形式的传统图书馆开始向现代图书馆转化。经过传教士在收藏文献上的主动选择,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文献得以在山东收藏、传播,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在西方得到认可。如,卫礼贤作为一名德国传教士,特别喜爱中国文化,劬勤不倦。他在后来的《中国心灵》一书中曾写道:“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德语。”他翻译的20多部中国典籍在西方广为传播,为东学西渐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方面看卫礼贤的尊孔文社既是一个研究儒学的机构、学习汉学的最佳场所,又是联系流亡到青岛的清朝学者和德国在青人士的组织,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4.2 对山东地方文献的搜集与保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山东教会图书馆在文献的采选上基本上都偏重于西文,但随着教会的本土化,收藏也开始向中文文献偏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齐鲁大学图书馆在其国学研究所1930年成立之后,根据自主购书权,国学研究所可以根据所需有选择地采购,抗战前的收集主要集中在齐鲁文化方面,1936年之后,几乎收集了山东所有地区的地方志,“据1935年年报统计,图书馆当年收集到的志书数目达到了726部9 613卷,丛书达到22 338种,并都进行了系统编目,制作了子目通检和一万多张目录卡”[29]。这些地方文献都是调查研究山东社会、历史和农村等方面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由此也形成了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的地方志特色。同样,尊孔文社藏书楼因创办者卫礼贤的个人喜好,四处张罗募集和购买经、史、子、集、诸子之书,馆藏有不少的古籍善本。地方文献被图书馆搜集、收藏,使其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流传下来。
4.3 对山东早期图书馆事业产生有益影响
教会图书馆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制度保证了图书馆工作的正常运行。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借阅规则上,如1936年齐鲁大学的借阅规则就有5大条30小条,包括了借阅范围、借阅册数、借阅时限、借阅手续、赔偿制度、阅览管理等非常详细的条目。同时制度也涉及购书、编目、藏书等。齐鲁大学在编目时采用先进的编目规范,依桂质柏先生编译之杜威书目十类法,西文书依杜威氏原本,另编著者号码表、西文书著者号码。详细的规章制度和先进的工作方法为山东早期的图书馆事业提供了借鉴。
4.4 对山东当地人民开启了思想启蒙
山东的这几所教会图书馆几乎都向公众开放,烟台青年图书馆面向社会,前来借阅的除青年会会员外,亦有洋行、商号职员,教师,学生和平民百姓。广智院图书馆在1924年的扩充计划中曾写到“本院近三年来承广学会惠予书籍,特出资聘用人员接洽,商学各界巡回送阅颇著成效,奈济南地广人众普遍难,期时引为憾,倘荷阅者,赞助或惠寄书籍或慨捐款项,使地方人士多获读书之益,禆益社会宁有既极”[30]。从中可以看出该院的巡回文库很受民众的欢迎。“1924年,阅报室有阅览者35 000人,由巡回文库借书看的有200余处,看过1 000多册书”[31]。 民众通过图书馆获取所需知识,开启了思想启蒙。
5 结语
教会图书馆是随着学校或文化机构的兴办而发展起来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先出现的新式图书馆,不仅有中国了解和观察西方近代图书馆的史料,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山东的这些教会图书馆更是山东较早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推动了图书馆事业在山东的传播,促进了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对研究山东的图书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