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语言、秩序
——《俄狄浦斯王》中的差异与同一
2019-11-08黄政培
黄政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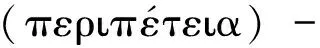
一、雅典启蒙
德国美学家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提到:“最初,西方文化根本就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但它首先得变成视觉文化。视觉的优先地位最初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初叶……进而言之,它主要集中在哲学、科学和艺术领域。”(4)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假如韦尔施的论断正确,那么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就经历着一场规模浩大的视觉的崛起,但韦尔施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崛起背后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视觉的崛起背后本质上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启蒙的逐渐加深,之所以用“启蒙”这个词,乃是因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的这一深刻转变同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样,都意在挣脱旧有宗教对人的束缚。在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中,启蒙,就意味着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运动所面对的是长期凌驾于人理智之上的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康德强调要“勇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其实就是在强调以无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来取代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的权威。(5)参见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31页。同启蒙运动类似,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先知体系和神谕体系也凌驾于雅典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处在对先知体系和神谕体系的绝对依赖当中,因此从这一绝对依赖的状态解放出来就是所谓的雅典启蒙。这种启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运用知识和思想自律地掌控世界和生活,而不再只是他律地依据和听从宗教先知颁布的神谕来行动。从感官的类型学差异来看,听觉倾向于被动地顺从,而视看更倾向于主动地探索。(6)关于视觉与听觉的感官类型学差异,参见Jonas, Hans., “The Nobility of Vision: A Study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nses”, In The Phenomenon of Lif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135-151.所以,原本处在对先知神话体系的绝对依赖当中的雅典社会就更多地表现为以听觉为主导的文化类型,而随着启蒙的加深,雅典社会开始悄然向着视觉主导的文化类型转变。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7)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希腊语、英、汉对照》,罗宾森 英译,楚荷 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对光的狂热追求一样,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延续着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判断,表现出了对于光和眼睛的巨大热情。这一时期的人们展现出了一种对人类的能力和成就,尤其是对科学和哲学探究的异常乐观的态度。以医学为例,《论古代医学》(OnAncientMedicine)的作者就写道:“医学不像某些探索的分支那样,一切都依赖于一个无法被证明的假设。医学已经发现了一种原则和方法,长期以来,通过这种原则和方法,探究者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发现,如果探究者有能力,知道曾经有过哪些发现并以之为自己探索征程的起点,那么剩下的那些没被发现的东西也终将被发现。”(8)Goldhill, Simon., Reading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200, p.200.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对人类运用理性之光照亮处于黑暗的未知事物的信心,也展现出了人类在朝向整全的知识和掌控万物这一终极目标上的不断进步,一种通过理智的不懈奋斗带来的进步。(9)Goldhill, Simon., Reading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200, p.200.
这种对人类理智的信心在柏拉图的洞喻中达到了它最强有力的表达,洞喻最基本的意象:阴影、火光、上升、实物、光明、水中倒影、太阳,全都贯穿着一条视觉的线索,柏拉图的洞喻实际上就是视觉的隐喻。在其中,人的上升本质上就是视觉能力的提升:从只能看阴影的眼睛到能看火光、实物和洞外水中倒影的眼睛,最后是能直视太阳的眼睛,由此视觉化的洞喻也就成为了整个雅典启蒙精神的某种隐喻表达。自此以后,存在的基本决定因素开始被称为“理念”,人类的发展道路也从此被界定为“从洞穴剪影的黑暗,通过长久的实践,最终到达光明之源太阳,那纯粹之善的象征。这条道路自始至终由视觉所主导,宇宙的真理开始通过视觉的语法来追索,而不再依赖于聆听神谕的听觉”(10)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第177页。。此后不久,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以颂扬视觉开篇,以它为每一种洞见,每一种认知的范式所在,隐秘地奠定了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的传统。视觉至上就此为可见的将来奠定了基础:“它支配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光的形而上学,一如它支配启蒙的现代和现代人对光的热情一样,视觉至上就这样规定了人类的道路。”(11)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第177页。如果说柏拉图基本上可以看成是雅典社会向视觉范式转变的完成,那么在柏拉图之前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时代就是从听觉范式向视觉范式转换的最激烈时期,虽然在此之前,埃斯库罗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Bound)中就已经表现过这种宗教与启蒙之间的尖锐冲突并试图找到某种平衡,但随着启蒙的深入,埃斯库罗斯尚能保持的这种平衡已逐渐变得不再可能。在矛盾日益激烈的启蒙深入时期,索福克勒斯开始重新表现这种冲突,但他的立场已不像埃斯库罗斯那样力求某种平衡,也不像后来的欧里庇得斯那样偏向启蒙一边,而是偏向于站在传统宗教一边,扮演着一个保守的角色来对抗日益加深的启蒙和视觉的力量。在索福克勒斯看来,理性和技术的控制并不一定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来源,他在其中看到“这同样会是人类的束缚和局限性的潜在来源”(12)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65页。。关于这一主题的沉思,正是在《俄狄浦斯王》这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悲剧典范的作品中(1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8页。得到了最深刻而完整的表现。
二、俄狄浦斯与“人颂”



在俄狄浦斯作为“舵手”的形象中,俄狄浦斯的成就和毁灭则突出地表现在“舵手”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倒转上。戏剧开场不久,祭司就悲叹说:“我们的国家像一艘失事的航船在海里颠簸,它已无法抬起它的船头以脱离深渊,摆脱血红的巨浪。”(22-24)。他所祈求的俄狄浦斯正是那个“为国家掌舵”的人(104),是“曾在亲爱的国土遭遇危难之际,曾经正确地为它领航”的人(694-695),也是那个现在可能“显示出色的领航才干”的人(696)。在俄狄浦斯预感到真相逼近而感到恐惧时,伊俄卡斯忒(Jocasta)也用“舵手”的比喻向神明祈求:“如今,看见他恐惧,我们也害怕;就像船上的乘客看见舵手恐惧时一样”(922-923)。俄狄浦斯以城邦的“舵手”这一形象出现就是强调俄狄浦斯利用他的个人才智对他自己和城邦的航行的掌控。但是,随着真相的逼近,俄狄浦斯的“舵手”形象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歌队开始将他所受的灾难比喻为波涛汹涌的大海:“可看他现在,那可怕的灾难的波浪已经吞没了他”(1528)。于是,这个曾经的掌控者,现在成了大海所控制的对象,他为城邦领航并没有将城邦带出灾难,相反却将城邦带入瘟疫这一更大的灾难当中。他靠着自我的智慧,“借着星座辨别方向”(796-797)为自己领航,试图逃离命运的诅咒,却相反地使自己重回命运的港湾,正如忒瑞西阿斯曾经警告的那样:“哪里不会成为你哭声的港湾?……当你知道你婚姻的秘密,当你发现你家里的婚姻原来是你一路幸运航行之后驶进的不幸港湾”(420-423)。俄狄浦斯从伊俄卡斯忒那里出生,她是他的启航之地,而现在,她又成了他的航行所到达的港湾。为城邦领航却将城邦引入更大的灾难,想逃离母亲却重回母亲的怀抱,俄狄浦斯作为“舵手”的控制与被控制在这些反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是作为“医治者”的俄狄浦斯。和“舵手”的形象一样,俄狄浦斯作为“医治者”的形象也在一开场就表现了出来。开场不久,面对祭司们的祈求,俄狄浦斯的回答就使用了医疗救治的语言:“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生病了……经过检查,我发现只有一种治疗办法,并且我已将这一疗法付诸实行”(59-68)。但最后他发现,他自己才是最需要被医治的人。于是,俄狄浦斯开场的这些医学词汇也就反噬到他自身,尤其是在俄狄浦斯第一次谈到城邦疾病的那番话中:“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病了,但尽管你们有病,却没有一个人的病和我的相等”(60-61),也就是说他自认为是病得最重的人。而事实证明,他正是这次瘟疫的起因,所以他自认为是病得最重的人也就无意间指向了事实的真相。并且,俄狄浦斯在一开始就把城邦民众唤作“孩子们”。因此,在这里,他无形地是在说“你们[这些孩子们]不能和我相等”。但事实上,他与“孩子们”的真正关系又是“相等的”,于是这句话,尤其是“相等”这个词也就呼应着忒瑞西阿斯退场前所说的那句可怕的预言:“你将与你自己的孩子之间建立悲惨的平等”(424-425)。在某种意义上,“相等”就是俄狄浦斯所患的疾病,因为现在他不仅占据了和他父亲一样的作为同一片土地的共同播种人的位置,同时他和他母亲生出的孩子也既是他的孩子,又是他的兄弟姐妹,他与他的父亲和孩子们之间原本天然的代际差异和不相等不复存在,而这种天然的代际差异“正是确保每一代人在时间秩序和城邦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的保证”(19)让-皮埃尔·韦尔南,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古希腊神话与悲剧》,张苗、杨淑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由此俄狄浦斯的病和城邦的病之间也就显示出了相同的结构。按照祭司的描述,城邦的病在于:“田间抽穗的庄稼枯萎了,牧场上吃草的牛羊倒毙了,临产的妇人突然死了。”也就是说整个城邦的病在于绝育,而绝育也就意味着整个城邦宗法的自然根基——新老更替——的破坏,在结构上正与俄狄浦斯父子之间天然的代际差异被破坏一致。由此我们看到,在俄狄浦斯作为“医治者”的形象中,不仅表现出医治者与被医治者之间的倒转以及二者之间差异的抹平,同时也暗示出了俄狄浦斯所生疾病的本质,也就是在他那里各种他借以界定自身的差异——猎人与猎物的差异(文明和野蛮的差异),农夫与种子的差异,舵手和航船的差异,医生和疾病的差异,父亲和孩子的差异——统统不复存在,他成了一个在城邦秩序中无法被归类、被定义、被言说的对象。
三、俄狄浦斯所用的视觉语言及其反噬

在光明尚未到来之前,一切都处在悬而未决、隐而未显的迷雾状态当中。因此,所谓的带来光明意指的就是带来可以为视觉所识别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光明是清晰性和确定性的条件,(21)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507E。“看不止是看者和被看者之间的二元结构,根本上还需要有第三者,也就是光的介入。”(507e)对光明的追求本质上是对清晰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也就是对知识的追求。但是,这种清晰性和确定性如何体现出来?正是通过差异。如果一切都相互混同,那人也就没有认识的必要了。由此这就与俄狄浦斯身上差异的消失,也就是他的模糊状态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视觉、知识与差异的关系,最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明确谈到过。他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2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视觉与知识最突出的关系就在于视觉所具有的“显明事物之间差别”的能力。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最骄傲的也正是他所具有的显明事物差别的分辨能力。一方面,他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解出斯芬克斯之谜,因为斯芬克斯之谜所要求的正是解谜者能否分辨出同一人身上童年、成年与老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内在同一;另一方面,他认为真相大白的关键在于“拉伊俄斯是被一伙人”还是被一个人杀死的,因为“一无论如何不等于多”(845)。可以说,俄狄浦斯是一个最具眼力的人,而这种眼力在文本中尤其以他所用语言的区分功能体现出来。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的语言学原理,语言的意义正在于差异。单词本身是虚无的,它只有通过它与其他所有单词的差别才能被“区分性地”建构出来,因此,差异正是语言的基础,正是凭借差异,语言才显示出意义。(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4页及以下。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也提到这点,他说:“人根本没在命名,他是在分类”(24)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5页。。更早地,柏拉图在《克拉底鲁》中也说:“名称是教导和区分真实的不同部分的工具”。(Cratylus388b13-c1)所以,语言最根本的功能其实就是它在意义、类别、概念上的分隔和确定作用,这与视觉的分辨能力如出一辙,乃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的这种区分功能就是建立在视觉的分辨能力基础上。(25)对于这点,海德格尔对λογοζ的分析尤其能给我们启发,他说:“λογοζ作为话语,毋宁说恰恰等于δηγουν:把言谈之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亚里士多德把话语的功能更精细地解说为αποφαινεσθνι(有所展示)。λογοζ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话语‘让人’απο(从)某某方面‘来看’,让人从话题所及的东西本身方面来看……λογοζ之为αποφανσιζ(展示),这种‘使……公开’的意义就是展示出来让人看。”(《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8页)由此我们看到,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看比语言更加源始、更加直接,话语提示人们如何观看,让人从某某方面(基于差异性)来看。在俄狄浦斯用来定义自己的语言中,他尤其把自己清晰地界定为狩猎者、舵手、农夫和医生,而在俄狄浦斯认识到自己弑父娶母后,所有他用来界定自身的命名全都崩塌了,他不再能够用这些形象和名称来定义自己。并且,由于性关系的混乱,他的家庭内部各种亲属关系也发生了混乱,他的婚姻不再是婚姻(1214),他的妻子也不再是妻子(1256)。兄弟、孩子、妻子、母亲等所有这些词语都不再能够恰当地界定这个家庭里面的各种关系。在俄狄浦斯这里,原先坚持“一无论如何不等于多”的他最终实现了“一”与“多”的混同。

结 语
追求光明,结果自己却是那个最需要被隐藏起来的黑暗存在。追求清晰,结果自己却是最不清晰的无法归类的存在。视觉突出的能力是分辨,俄狄浦斯却因这种突出的视觉能力使自己成为无法被分类和定义的存在。知识所确证的不再是身份,而是没有身份;不再是自身所处的权位,而是一个难以命名的位置。基于视觉分辨基础的语言没有成为一个维持秩序的工具,相反却成为了一张充满瑕疵和裂隙的网。在这部剧里,作为各种迹象的解释者、各种谜语的解决者,作为通过理性探究来寻求知识的自信的追求者,作为寻求清晰性和确定性的探索者的俄狄浦斯在寻求真相上成功了,但在其生存意义上却失败了。在这种安排中,真正被质疑的不是基于视觉语言的探索及其带来的秩序,真正受质疑的是把基于这种视觉语言的理性当作探究一切事物的决定力量,是相信可以用理性解决一切的野心,也就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极力批评的“理性乐观主义”。于是,俄狄浦斯在生存论上的悲剧也就返回到了人颂的最后一节,虽然基于视觉的理性取得了诸多文明成就,但这种理性探究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当俄狄浦斯所代表的理性探究开始取代神灵作为城邦一切的基础,对众神的崇拜衰落,人妄图取代神时(907-910),城邦开始遭遇瘟疫,俄狄浦斯也就此踏上了破坏自己生存意义的毁灭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