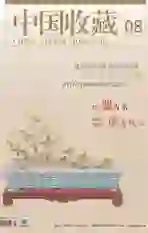一面是格调。另一面是气息
2019-10-28王箐箐
王箐箐



本期的策划进行到这里,相信大家对于器座,或多或少地已经产生了不一样认识。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进器座的世界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学问实在是深不可测,与器物有关,更与人有关。那么关于器座,还有哪些知识点不容错过?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冲刷后,文物又是如何焕发新生?作为压轴篇,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主任、木器文物修复专家、副研究员屈峰。也许很多人之前曾通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认识了他,对于器座文化,他会如何解读呢?
《中国收藏》:其实提到器座,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只是“附属物”。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故宫开始重视宫廷器座的修复保护?
屈峰: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很多器座在此过程中与其所承托的器物分离、失联,再也找不回自己所服务的对象了。加之当时的保管条件和思想认知所限,很多此类器座,特别是木质器座都有所损伤。它们中有的由于黏接剂老化而开胶、分散;有的由于温湿度变化的影响,造成了变形和开裂;有的是因为部件的遗失,残缺不全;还有因为外力作用而导致磕缺、损伤的。所以这些藏品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文物资料,在我们的库房里面保存着。
2013年開始,我院实施“平安故宫”项目。项目启动后大家就建议,将这些器座作为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尽快对它们进行抢救性修复。于是,我们部门随之专门成立了“木器底座文物修复”的子项目,来抢救这批常年存放在库房的存在各种伤况的底座。
大家在嘉德艺术中心此次的“故宫藏宫廷器座展”中看到的这40余件木质器座,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这个修复项目之中。比如展品中有一件比较小的器座,是紫檀雕覆仰莲纹形式的,由覆莲和仰莲上下相扣构成。仰莲这部分的莲花瓣之前是有几处残缺的,通过补配,终于让它重新成为了一件完整的器物。还有一件紫檀仿竹枝的篮架式底座,修前开胶、变形,所有部件都散了,我们对其进行了整形,然后重新黏合,这才有了大家今天所看到的面貌。
《中国收藏》:此次展览筹备的过程中,什么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
屈峰:应该是展览的理念。将器物的底座、支架这些日常被看成是陪衬的部分,作为一种文物的主体,从与其所组合的文物关系中抽离出来,改变其常规的定位,成为一个完整圆满的独立展示物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又对不同材质的分类加以梳理,多形制、多工艺、多材料综合呈现,为器座以一种丰富、全面的状态成为独立展品、媲美其他文物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我想这样的理念是对文物审视视角的转变,也为观众提供了新的观赏和研究角度。这既是认知的创新,也是研究专业化的体现。而少部分器座与原器物关系在展览中的呈现,也呼应了传统认知习惯,提供了对两种认知的讨论以供观众思考。
所以说,新视角、新思考是策展时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中国收藏》:这种修复会很繁复吗?
屈峰:器座的修复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根据伤况。比如缺损比较多需要补配部件的器座,修好它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在修复中你会感觉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一件器座,工艺可是一点儿都不简单。
从常规的修复上看,目前倒还不存在特别大的技术难点需要去突破。但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器座的尺寸小,一些异形的,特别是圆形类或者类圆形类,往往是由几个部分攒合组成的,一旦当中有个部件变形,如何将其恢复至原来的合适的弧度,跟其他部件进行拼合,这个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经常需要先根据尺寸做一个箍架,然后结合传统软绳缠绕的方法,利用这两者的结合逐渐对器座进行整形。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近年来在技术难点上的一个小突破。
《中国收藏》:感觉特别是在乾隆时期,宫廷器座的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期。
屈峰:乾隆时期,大量器物需要大量的底座,所以宫里造办处的木作、玉作、牙作、铜作、镟作、雕銮作、珐琅作等都会承接制作器座的任务。特别是木质器座制作量很大,于是乾隆皇帝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广木作。这个机构大部分承接的任务就是给器物做底座。
专门设计的器座,不管是形制还是装饰题材、纹饰内容,都会有很多讲究,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呼应关系。比如做山石、水纹这些,一般上面会有动物、山水等等,正因为这些元素之间有关系,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东西。
而且有些器座的样式,需要在设计完后,经皇帝审阅才能做,皇帝自己也会提出一些器座样式的要求。这说明了当时对器物的配座,皇家作坊里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会要用象牙、玉、青金石、珐琅等材质来做宫廷器座了。
《中国收藏》:清官的器座制作,在地域特征上有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比如苏作居多?
屈峰:以做宫廷木质器座的这部分群体为例,他们主要工作都是做家具的,来自各地的人都有。雍正时期到乾隆早期主要是苏作,在宫廷做家具的大部分都是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而到了乾隆中期,广作兴起,更多广作的匠人开始进宫,并且随后逐渐超越苏作匠人,成为了宫廷木作的代表。
当然了,这当中还会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匠人,只不过宫廷档案里面对此明确记载的就是苏作和广作。
《中国收藏》:对于器座和器物的呼应关系,又该如何理解?
屈峰:诚然,器座最早的产生就是为了承托器物。一件好的器座,能够对器物的展示、摆设不仅能起到加固作用,而且在审美构成上更加丰富,形成的对照关系会使得器物看起来更加高雅、高贵,从而与所承托的器物一起构建象征寓意和审美意境。
宫廷器座的制作事实上也是这么一个基础。在制作的过程中,肯定先是考虑以座来配器,所以当时很多器物的底座都是专门为该器物制作的。当然也分情况,比如有部分器物形制差不多,尤其是简单形制的那种,底座基本上可以通用。但一些特殊的器物,只能专配,这样的器物和器座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种审美意象,器座是这个意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既要能衬托出器物的审美特点,同时也要作为器物审美的有效补充,这样这个意象才可能完整。
《中国收藏》:对于器座的鉴赏,有什么要诀吗?
屈峰:我想专门的要诀也谈不上。因为我们中国人做的東西,从一定层面上说审美基本都是相通的。虽然很多时候器座只是小件,但与其他很多大件一样,审美追求基本是一致的。
就拿鉴赏器座和家具来比较,标准大同小异。首先,我们需要看这件东西的形制怎么样,这个里面就存在很多讲究,比如说构成关系是不是和谐?还有就是如同我们看人一般,精不精神?所呈现出来的气质是高雅、简约还是繁复?这些都是审美必不可少的因素。
同时,对于器座,我们还要看它和其所承托的器物关系是否和谐,是否真正有效地做到了烘托器物的审美。再者就得看它的制作工艺,例如做工是否精细、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材质结合是否恰当等等。比如木质的器座对于木纹的利用是否跟其形制设计有关,诸如此类。
还有个重要之处在于,器座每一个部件的制作是不是能让人觉得有活气。可能大家会觉得不解,物件怎么会有活气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评价一件作品,都说要看活力、气息,指的即是一种整体贯穿的精神力量。比如说一件器物的腿儿,它的弯度、曲线应该给人的感觉很有力,是稳固而又多姿的。如果弯得让人感觉站不起来,这就不好了。这些细节都是可以作为审美来探讨的。
另外,一些器座上面会有装饰、纹样,那我们也可以去欣赏其设计是不是跟器座结合得很合理,能够真正的起到一种提升器座品质的效果。你看,其实说到审美有很多方面,但总的来说离不开两大要素:一个是工艺结构,另一个是格调气息。
《中国收藏》:随着修复工作的推进,您个人有没有新的体会?
屈峰:从木质器座的修复,再放眼到文物修复,我想这实际上是一个探秘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之所以说探秘,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层层剥离,找出这些文物伤况背后的原因,从而找到更为合理、科学的解决伤况、保护文物的方法。而所谓对话,则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需要你去不断地去揣摩古人之思,他的意图、追求和注重的是什么?不断去探索当中蕴含的审美道理,以及不断去体会这些技艺的特点和高明之处。这种探秘和对话的过程,也是作为文物修复师自我成长和学习、提升的过程。这给了我们途径去体验,进而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收藏》:关于宫廷器座的文化内涵,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屈峰:它实际上是整个宫廷文化有机组成的一个部分。虽然器座可能很小,但是它的审美追求和制作工艺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其他类别的文物。更为重要的是,器座蕴含的工艺特征,以及所崇尚的审美要求,恰恰也是可以作为整个宫廷文化审美的一个缩影的。因此可以说,研究器座能够让人从一个点去窥探整个宫廷文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比如我们此次展出的40余件木质器座,基本上都是乾隆时期的底座。借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推断乾隆的审美,比如他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创新,他能把很多元素拿来混搭等等。从这些五花八门的形制,还有丰富的装饰和纹样中,可以窥探出乾隆时期文化的活跃性,也能看到这一时期所倡导的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感和混合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开放的状态(注:本文藏品配图均为故宫博物院提供)。
清宫旧藏 嵌珍珠嘎巴拉碗座
此碗及座制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其造价昂贵,所有宝石、珊瑚、松石、青金、蜜蜡、垫子等皆由皇室内库挑选并择优使用。据造办处统计,仅珍珠一项便“共用正珠四百三十二颗”。又如底座的御制赞文的总字数近达四百,字头虽小,但布局合理,笔法流畅,历经200余年仍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