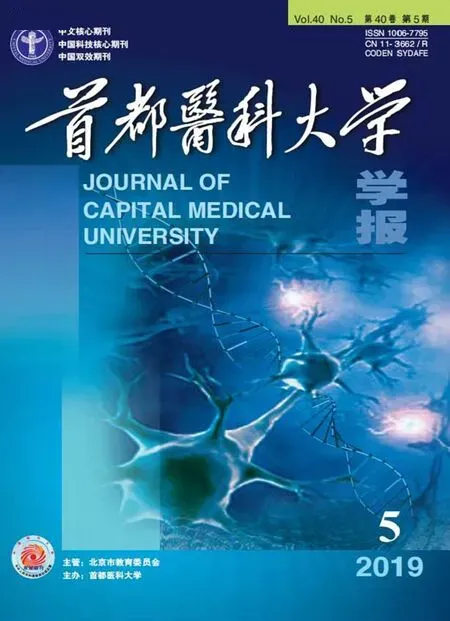低氧诱导因子:氧稳态的砝码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简介
2019-10-24焦时宇于宝琪曲爱娟
焦时宇 于宝琪 曲爱娟
(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 重塑相关心血管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69)
北京时间10月7日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来自哈佛医学院丹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William G. Kaelin、来自牛津大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Peter J.Ratcliffe,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Gregg L. Semenza共享201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理解细胞感知和适应氧气变化机制中的贡献。这一革命性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氧如何影响细胞代谢和生理功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治疗贫血、肿瘤等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1 获奖者简介
1.1 William G. Kaelin
William G.Kaelin(图1),1957年11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医学家,哈佛大学医学教授,致力于研究p53等抑癌基因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1979年,Kaelin获得杜克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得杜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实习,后转至丹纳·法伯癌症研究所;1992年Kaelin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于1998年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1 William G. Kaelin
1.2 Gregg L. Semenza
Gregg L.Semenza(图2),1956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皇后区,美国医学家。1974年从斯里皮高中毕业后,Semenza进入哈佛大学学习遗传学。之后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在宾夕法尼亚儿童医院做了博士研究。1986年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成为该校教授。Semenza对生命系统如何利用、调节氧气做出突破性的研究。他的团队发现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 HIF-1)所调控的基因能够作用于线粒体呼吸,调节细胞对缺氧适应性反应。他于200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0年获盖尔德纳国际奖,2016年获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

图2 Gregg L. Semenza
1.3 Peter J.Ratcliffe
Peter J.Ratcliffe(图3),1953年生于英国兰开夏,英国医学家、分子生物学家。1972年赴剑桥大学和圣巴多罗买医院学习医学。1978年,Ratcliffe毕业后转赴牛津。1989年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Ratcliffe对缺氧时红细胞生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缺氧时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EPO)表达明显升高,调节机体对于缺氧的适应性反应。

图3 Peter J.Ratcliffe
2 主要科学贡献
包括人类在内,绝大多数的生物都离不开氧气。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多数生命体都通过复杂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不断摄入氧气,保证器官与细胞得到足够的氧供应。但人体对于氧的需求又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当氧气缺乏时,人会窒息而死;当氧气过量时,人体又会发生氧中毒。因此,生物体内也衍生出了诸多应对机制,来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譬如在氧匮乏的高原环境地区,人体内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就会上升,增加血液循环内红细胞数量,进而提高氧气供应来应对氧缺乏。
其实科学界早已意识到机体感知氧的重要性,早在193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颁给了比利时医学家Corneille Heymans(图4),以表彰其“发现机体通过颈动脉体感知血氧变化并与大脑直接交流来控制呼吸频率”。虽然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层层解开氧气之谜,但机体如何适应氧水平的变化一直是未知的。

图4 Corneille Heymans
2.1 低氧诱导因子的发现
20世纪90年代,Semenza与Ratcliffe开始研究EPO是如何被氧调控的。Semenza通过转基因技术将EPO转入小鼠体内,让小鼠体内生成更高水平的红细胞。他发现,是位于EPO旁的一段特定的DNA序列介导了氧对于EPO的调节。与此同时Ratcliffe 也研究了不同氧浓度对于EPO的调节。虽然EPO通常是由肾脏细胞分泌,但是Semenza和Ratcliffe发现,通过基因编辑手段,将这段序列放到其他基因附近,这些基因就会被表达。说明不仅仅局限于肾脏细胞,几乎全身的组织中都存在氧感知机制。这一发现提示,细胞对于低氧感知是普遍存在的,具有广泛的生理意义,在机体的各个部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探究是什么细胞成分介导了EPO的氧依赖性调控成为了研究组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在离体培养的肝细胞中,Semenza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可以与特定DNA片段结合,他将这种复合物命名为缺氧诱导因子[1]。随后,Semenza开始了对HIF复合物的广泛研究。1995年,Semenza发现,HIF-1α在暴露于1%(体积分数)O2的细胞中大量表达,并在细胞氧浓度恢复到20%时迅速衰减[2]。这一研究对于推动人们理解氧感知领域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但HIF如何调控氧稳态,以及HIF本身受到哪种分子的调节还是未知的。
2.2 低氧诱导因子介导的细胞内氧稳态调节
蛋白质在体内发挥作用需要多种因素的调节,包括磷酸化、泛素化和乙酰化等。其中,泛素-蛋白酶体途径(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 UPS)在维持细胞稳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常氧情况下,小肽泛素(ubiquitin)会结合HIF-1α蛋白,促进HIF1-α降解[3]。而泛素如何通过氧依赖方式结合HIF-1α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Kaelin正在研究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希佩尔-林道综合征(Von Hippel-Lindau disease,VHL综合征)。这种遗传性疾病导致遗传性VHL突变家庭中某些癌症的风险显著增加,表现为血管母细胞瘤累及小脑、脊髓、肾脏以及视网膜[4]。他发现,当缺乏VHL蛋白时,葡萄糖转运蛋白(glucose transporter-1, GLUT-1)、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 3, IGFBP3)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受HIF-1α调节的基因表达升高[5]。表明VHL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缺氧的调控。随后,Ratcliffe于2000年在文章中表示,VHL可特异性结合HIF-1α,并且增强了HIF-1α泛素化,促进其氧依赖的降解途径。这一关键的结果为VHL在此过程中的功能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至此,HIF-1α的氧依赖性降解途径与VHL的关系终于被发现了。
科学,就是一个难题接着另一个难题。虽然科学家们又做了很多工作来说明VHL与HIF-1α的关系,但是氧含量如何调节VHL和HIF-1α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是一片空白。2001年,Ratcliffe与Kaelin同时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表明在正常氧含量情况下,HIF-1α的特定位置被脯氨酸羟化酶(prolyl hydroxylase, PHD)修饰,经过羟基化修饰的HIF-1α可以被VHL识别,进而使HIF-1α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降解。脯氨酸羟化酶又称为氧感知酶,其活性依赖于氧浓度,当细胞处于低氧环境时,酶活性也降低,无法使HIF-1α羟基化,所以导致HIF-1α降解受阻,在细胞内累积,从而发挥生物学效应。这也解释了正常氧含量可以调控HIF-1α快速降解(图5)[7-8]。
2.3 HIF-1的结构
通过纯化发现人HIF-1α全长含826个氨基酸, 第1~ 390位为最适DNA 结合的区域,其中第1~ 166位介导其与HIF-1β的异二聚化。羧基端第391~ 826位包含两个拓朴相关结构域(topologically associating domains, TAD), 氨基端的激活区为NAD( N- terminal activation domain) ,羧基端的激活区为CAD( C-terminal activation domain) ,二者被一个抑制结构域隔开,它们所含的氨基酸序列各家报道有所不同。此外,HIF- 1α还包含核定位信号(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 NLS)序列,氨基端的NLS 位于第17~ 33 位,羧基端的NLS位于第718~ 721位。HIF-1α还具有氧依赖的降解结构域(oxygen-dependent degradation domain, ODDD),ODDD位于第429~ 608位,是HIF-1降解所必需,对调节HIF- 1α活性起中心作用,去除此区域后,HIF-1α能自发地异二聚化,出现DNA结合和反式转录激活(图6)[9-11]。

图5 HIF-1α的氧依赖降解途径
正常氧含量时,HIF-1α被脯氨酸羟化酶修饰,羟基化的HIF-1α与VHL蛋白结合,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迅速降解;氧含量较低时,脯氨酸羟化酶活性降低,失去羟基化修饰的HIF-1α不能被降解,在细胞内大量累积,进而转运入核,与ARNT结合成异源二聚体,启动下游靶基因转录。HIF-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VHL:von Hippel-Lindau.

图6 HIF-1α结构[11]
bHLH:DNA 结合的区域;PAS:在缺氧条件下,与 β亚基发生异二聚化;ODDD:氧依赖降解结构域;N-TAD:N端TAD结构域;NLS:核定位信号;C-TAD:C端TDA结构域;HIF-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VHL:von Hippel-Lindau
3 科学意义
氧气是绝大多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各个物种依靠氧气不断进化、演变。HIF-1与低氧领域的发现是一项教科书般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对细胞在不同氧环境下如何做出反应有了新的理解。HIF-1及其通路介导的细胞适应性低氧反应让人类在低氧环境下维持新陈代谢成为可能。
自细胞感知低氧通路发现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到这个领域,不断发掘低氧与疾病的关系。在肿瘤学研究中,HIF-1的大量表达可作为衡量肿瘤侵袭程度的一个标志[12];在部分肺疾病,如低氧诱导的肺动脉高压疾病模型中,可检测到HIF-1的过表达,提示HIF-1在肺动脉高压中发挥重要作用[13];而在代谢性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中,敲除HIF-1能够有效地抑制疾病发展[14]。所以HIF-1也被认为是多种疾病的潜在治疗手段,其抑制剂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中藏经》中讲到,“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行血、摄血,故为血之帅,血能化气,故为气母”。这其中就涵盖不止氧感知通路,而且还有二氧化碳感知、一氧化氮感知等,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挖掘生命科学的秘密。让我们在恭喜3位科学家共享诺奖的同时,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向生命科学的未知领域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