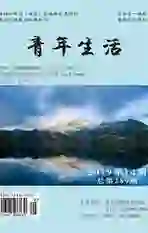人生不止 寂寞不已
2019-10-21韩冰
韩冰
摘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小说以作者的家乡和童年为原型,以一个童年的视角,描绘了一个北方小城人们的生活,是一副北方小镇的生活风俗画。
关键词:萧红 童年视角 风俗画
《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于1940年,1941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小说以作者的家乡和童年为原型,描绘了一个北方小城里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个小女孩的寂寞童年。无论是单调的小镇,充满地域色彩的风土人情,愚昧又善良的人们,被间接伤害致死的女子,还是那个小说的叙述者——“我”的一段童年往事,都融进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明丽哀婉。该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萧红因病死于香港,时年31岁。
一、这是一幅北方小镇与人的生活风俗画。
这是一个北方边地小城,冬天很长,几条街道,有金银首饰店、粮栈、学校、扎彩铺店、染坊等等。所有街道里,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东二道街上的一个大泥坑。这个大泥坑里多半是在旱年比较危险,一不小心,赶车人的马或是小动物掉进去,很难救出来,救时又免不了一大群旁观的人群。泥坑是沉滞、封闭的,如沼泽一样,一旦陷入,很难脱身。呼兰河城其实也如这个泥坑一样,单调、沉闷、死寂,活在里面的人们大都失去生命应有的色彩,他们对于生、老、病、死,都没有太大的感情,可以说这些人们,仅仅是活着,而不是生活。
尽管如此,小镇里还有是一些精神活动的。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等,只是这些丰富的活动,除了唱秧歌,其余都是为鬼而做,而不是人,人去看的,不过是热闹,“揩个油”罢了,连秧歌也装的“滑稽可笑”。
如此这般,呼兰河城犹如“一幅多彩的风土画”,真实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这是一曲寂寞童年的挽歌
在“我”家的后花园里,可以随心的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都是自由的,明亮的。“呼兰河这小城里面住着我的祖父”,祖父成了“我”童年时代唯一的玩伴。和祖父一起在花园里栽花,拔草,种菜,还和祖父开玩笑,把玫瑰花悄悄放在祖父的草帽上,然后一起大笑,快站不稳。和祖父在一起学唐诗,吃烤小猪,烤鸭,是掉进泥坑淹死的,直吃到饱得不能再吃为止,这些快乐,足以消除了冷淡的父亲、凶恶的母亲和会用针刺她手指的祖母带来的阴影。
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同样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带着淡淡的感伤,但英子的善良和清澈,为小说增添了许多温情,城南的故事,舒缓而不悲凉。而呼兰河城里的小女孩,关于童年的记忆,却是快乐背后透出无言的寂寥,这样寂寞和孤独,又伴随了作者一生。
三、这是一声被传统落后文化戕害的人们的叹息
说是被戕害的人们的叹息,似乎不是很准确。小说以小女孩的口吻来写,未曾理性的对命运多舛的人们评论什么,对于人们经受地苦难和艰辛,“我”往往是睁大眼睛去看。“我”的年幼无知,更显出人物命运的凄惨,比如小团圆媳妇。
这个才刚刚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初来时就被左邻右舍当热闹来看,后更因为“太大方”、“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长的高”而被打地夜夜哭泣很久。十二岁,本应还在父母的关爱里成长,偶尔撒个娇的年纪,然而在婆家里,被多次打昏过去,再用冷水浇醒,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小团圆媳妇躺在床上看见弹珠,还想坐起来玩,被婆婆凶狠地制止了。在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对“我”说,“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如此语气仿佛在说别人,更不要说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了。经过花样繁多的折磨,小团圆媳妇最终难逃一死。
故事里的人们是愚昧、麻木、残忍和不自知的,深受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这一点在有二伯身上表现地最为明显。胡家媳妇死后,请邻居吃饭,有二伯等人吃饭回来后,不仅没有为这个无辜的生命感到半点惋惜和怜悯,反而对人家的饭菜评头论足,“人死不如一只鸡”。而有二伯也是一个受害者,他落魄、潦倒,还死撑门面,背地里被小孩大人欺负、嘲笑,也没有人对他有过丝毫同情,日子过地荒唐而可笑。
这些看似欢欢喜喜的人们,在沉滞的小城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闹剧,幼小的“我”看地开心,读着他们的故事,读者不免会发出长长叹息,为了老中国的儿女们,为了曾经鲜活的生命,为了那些受伤的身体和麻木的灵魂,为了那些个仿佛停滞了的年年岁岁。
四、这是一生寂寞凄凉的女作家的生命体验
萧红创作该小说时,已是贫病交加,身处异地,一生爱过两个人男人,却无果而终,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伤害,加之没有留下多少幸福回忆的童年,一生都倍感寂寞孤独,及至生命的最后时段,更是觉出世上人情淡漠,从心底感觉到人生的荒凉,这一点在小说里有很好的体现。
“悲凉”,是在描述跳大神一节中,一再出现的一个词。在呼兰河城里,跳大神,本是为了治病,由人装鬼,而生活单调的人們,逢到哪家请神,远近人们像看大戏一样前往。安静的夜,伴着寂寞的鼓声,又勾起不幸人们的万般思绪,越来越悲凉,以至作者感叹到:“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荒凉”。
至于“我”的家,作者一再重复:“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住在前后左右的那么多邻居,有养猪的,开粉坊的,有拉磨的,赶车的,每家每户都有些有意思的事,“我”却一再的感到荒凉,可见,荒凉不是来自于生活,而是发自作者的内心;荒凉不是来自于幼小孩童对生活的理解,而是短短三十多年的生命体验在童年生活上的投影。人生不止,寂寞不已,作者不由地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融进小说里。
呼兰河城里,“流光容易把人抛”,自然界的荒凉和人事的辛酸交错纵横,共同构成了小城里缓缓流淌的岁月。萧红平和细致地讲述记忆中的家乡和人们,没有刻意造势,抒情感伤;没有消极悲观,哭诉不幸;也没有批判社会,抱怨人生。虽然这不是小说的重点,但因为有了这样的人们,对于生的坚持和柔韧,所以,呼兰河城的故事充满了悲凉色彩,却并不让人绝望。
结尾里,萧红这样写到:“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作者半生遭遇无数白眼和冷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回忆童年家乡,也许是漂泊半生后对家和安宁生活的向往,对亲情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