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
2019-10-20朱巧云
朱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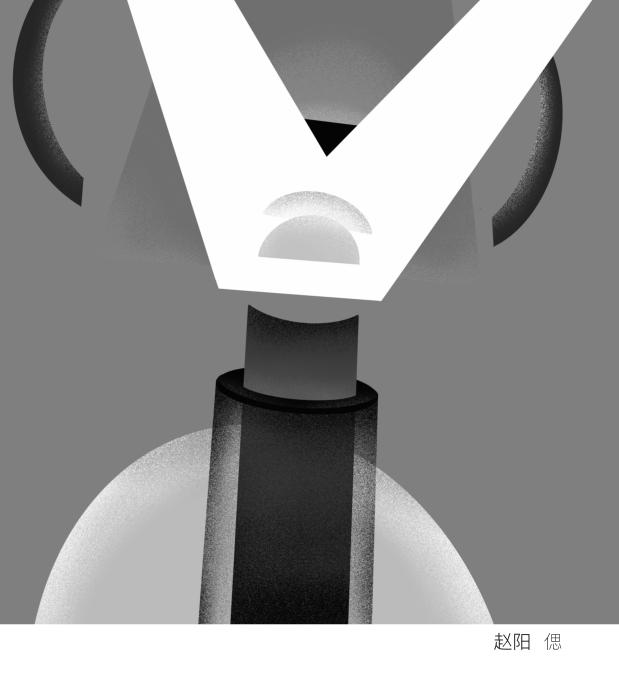
这一刻,凤想起谁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家的幸福总是建立在一个人默默无闻的付出,甘当配角的基础上。凤觉得为爱情而结合是所有婚姻中最不牢靠的一种,爱情会消失,消失后,谁的婚姻不是在凑和呢?
——题记
国庆节刚到,他们家就先把万年青捧了回来。那盆万年青看上去绿油油的,可底部已有几片老叶尾梢渐黄。辉担心它受不住寒雨夜风。凤母亲却说,它们不娇,老家的鸡常年在其丛中打滚,即使风雪中被滚得一地鸡毛歪头耷脑,来年屋檐水滴滴,一样活色生香昂首挺胸。
凤母亲是小学老师,说话总比凤生动。
万年青是凤母亲从农村老家屋后挖来的。去年凤家旧房装修,搬家时母亲按新房风俗置了鞭炮、猪头等一应物什,另外就是用红布包扎了一株万年青。母亲用的是银红绸布条,凤当时心里便有点怨。青城旧风俗,嫁人做小才用偏红,否则喜事都用大红,只有大红才代表正室,红红火火。母亲说,旧黄历,早翻篇了。凤不想让人看到,便私下偷偷把银红布条塞进垃圾袋,可母亲还是看到了,当然也不便为这点小事拦着,便只惋惜地嘟囔一句:“好好的,还可以扎扎米口袋,怎么就扔了?”凤也不解释。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怎么就这么敏感,以前和那个家伙在一起时,她是不在乎这些的。现在她常常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些小物件上。比如现在她经常对这万年青有些期待。到底期待什么?其实她也说不清,当她和辉和睦恩爱时,她就想它长好些;当她看辉不顺眼时,她就想它应该和辉一样,滚一边去。当然,很多时候她对一切人和物都是没期待的,她认为生命里遇到的一切都是该遇到的,所谓定数。这个时候她心里是禅定的。可自从她把自己的生活与万年青纠缠在一起时,她心里的淡定就少了些,她很想知道万年青的定数。
母亲挖的万年青太高,加上换了风雨移了屋檐,栽在娇小的青花瓷盆里,总是直不起身,微风过时,点头哈腰,几天下来便瘫倒枯死了。
輝很难过,凤却没有,她觉得也许是万年青用生命在提醒自己该好好审视自己的生活了。
辉说留着一盘枯花不吉利,还是把它扔了,换别的吧。凤无所谓,母亲却不让,说,枯木逢春,再等等。可等了一个月,没反应,两个月,没动静,就在大家都不抱希望的三九天里,它突然吐了口气冒了个芽。凤母亲怕自己老眼昏花,又让凤和辉仔细看了,都说:“错不了。”那一天全家开心,闷在心里一直没敢说的话,都吐了出来。辉喝了二两老白干后,兴奋地说:“这下可好,本来我以为我和凤又要遭什么劫数呢!”凤母亲也咽了一口红酒不等缓过气来就说:“我也这么想呢,没想到这是老天爷故意的欲扬先抑。”凤没想到,大家原来都把万年青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后来看到万年青仿佛初生的婴儿。凤母亲就说:“这是万年青的第二春,预示着你们第二春也会越来越好。”凤却不咸不淡地说:“也未必。”母亲的话让她的心情仿佛光滑的皮肤上突然长了倒刺。
凤和辉都不喜欢第二春这个词,第二总让人想起第一,当初决定在一起时,他们是把彼此想成初恋初婚的。为了不跟过去沾边,他们甚至在房子上动起了脑筋。不买新房子,倒也不是买不起,只是为孩子们将来考虑。他们最后决定扒掉过去房子上的所有痕迹,重新装修。本以为一切可以重新来过。可后来凤才发现,一切都如梅所说,过去的其实并不会过去。就像他们家,不管怎么涂抹,梅初进时,想到的第一句还是:旧瓶装新酒。当然,如果住的是新房子,相信梅的感觉还是一样,只是修饰语换成:新瓶装旧酒。总之,无论是旧瓶里的新酒还是新瓶里的旧酒,都难回原装的味道。
梅是国庆节来的,这是她第一次到凤的新家。见到凤家里的装修,梅先是眼睛一亮,然后心里一疼,最后忍不住说了这句。
梅和凤是初中同学,虽然梅在春城,凤在青城,可两家却只隔一条河。所以学生时代,梅常在河的这头给凤扔果子,凤也常在河的那头给梅扔山芋、萝卜。后来,成家了,凤去了梅的春城,梅却远嫁了,两人便少了往来。虽然少了,却也没有间断,每当梅回老家来,常常不先回自家,先去凤的被窝里钻一晚。凤离婚后回青城娘家住的那些年,梅回来还是照旧找凤,倒是这几年,凤再婚后,梅回来没再找过凤,虽然凤一再约,梅却总是忙。直到这个国庆,凤加班,接到梅的电话。梅说,老家铁将军把门,求收留。凤值的是夜班,梅陪她在单位宿舍窝了一宿。第二天,正好中秋,凤苦留梅再住一天,梅觉得不妥,但也没推辞。
凤的家里,除卧室一张外国美女意气风发的水墨画像,的确看不出一点新的感觉,是内行人喜欢的低调古典的奢华。辉喜欢文玩,什么都喜欢弄成核桃菩提子之类旧旧的感觉,所以家里的全部家具门框都是用实木上清漆做成古铜钱的颜色。当然梅这么想时,并非因为外行,更多的是带着忌妒和不甘承认的一点倔强。
梅大概想说的是人,辉和凤是再婚夫妻。在梅心里,无论是物还是人,加了再的,都是二手的,旧的。人们对待旧的总不是那么积极,所以旧的都应该含着点,不该张扬。就比如凤,梅认为她和辉就应该简单领个证,然后再埋头过日子,犯不着又是装修又是请客的。历史讲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生太过高调也会跌得很惨。梅当然不希望凤再跌跟头,作为闺蜜,她祝福凤在多年寡居之后觅得如意郎君,何况辉还是她的远房表哥。可别人的如意又常常刺得自己心疼。所以她的祝福有时又带着虚假的复杂的甜蜜。不过,她说出口的话,永远恰到好处。
凤和梅到家时,辉正抓着一酱红、一深蓝两个雨披准备出去。
凤说:“怎么,我们回来,你就出去?”凤边说边收了雨伞,然后帮梅拍拍肩上的水。
梅用略带撒娇的语气说:“姐夫,今天姐姐收留我,你不会不欢迎吧?要不人家这才来你就走?”梅公开场合从来不叫辉表哥,梅跟凤说过他们那点八竿子打不着的表亲关系实在是长江里扔了一只鸡,舀碗水说是喝鸡汤的感觉。
突然见到梅,辉有点懵,不过很快就释然了,凤不止一次跟他说过这个闺蜜,他都表示,对这个远房表妹印象不深。当凤说要请她到家里玩玩时,他总说人家大概未必有空来咱们这寒门小户。辉说这话时,其实带了嘲讽,只是凤不明事由,没听得出来。
辉说:“团团应该要到车站了。”辉边说边看着凤,没有回梅的话。他对这个表妹除了客套的笑并没有多少热情。
凤“哦”了一声,带着长长的尾音,然后又短短说了一句:“那你快去吧。”
凤在“快“字上加了重音,辉反而不动了。
梅有些难过。凤,黑黑胖胖的,除了个子比自己高半头,哪方面都在自己之下。
当然梅的难过是不动声色的。今天是中秋佳节,可她注定在哪儿都只能是一人,家里的那位是肯定要去陪那个小的。这些年为了儿子,他们貌合神离,到了节日,他总是舍不下外头那个。虽然老天爷知了她的心事,提前下起了雨,免了她独自赏月的忧伤。不过,月并不能带走她的烦恼。她有家,所以过去总觉得比寡居多年的凤优越,现在凤跟表哥成家了,她本该祝福的,心里却多了几分无名的惆怅。凤家装修好有一段时间了,她始终没去,虽然凤多次约,自己也想去,可总调整不出合适的表情和情绪。这次是真的耐不住,她想见见辉,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所以才计划好回来的。
可辉就在眼前,却并不看她。
辉把那件酱红的雨披放下来掸掸上面的麻灰,然后又小心地沿着旧印子叠起来,说:“唉,雨越下越大呢!”
凤有些不耐烦,也不看辉,边给梅找拖鞋边说:“你去呗!”
这次重音在“去”上,辉于是干脆放下了雨披,两手不知所措地搓着。
梅有些心疼,又不便多言。心里那个悔,无法言说。如果不是自己当初被猪油蒙了心,现在就没凤什么事。
辉只比梅大两岁,两人从小一块上下学。双方父母给他们订了娃娃亲,虽是口头上的玩笑,两人却是彼此认定了的。可是梅初中毕业进城打工后,认识了一个老板,一切就变了。梅当时觉得辉虽然高富帅占了头尾两个,但家底子太薄。嫁过去,永远也过不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日子,于是心一横,眼一闭,就上了那个老板的床。那个老板是死了妻子的,所以梅一开始过得是正牌太太的舒心日子,可好日子不长。当发现丈夫和另一个女人滚在自己的被窝里时,梅虽然愤怒,然而相信因果的她,最终还是原谅了丈夫。或许一切都是自己任性的果报吧,梅收拾收拾心情重新回来找辉。却发现,辉已经成家生女,梅的心便如同老家风雨飘摇的草屋。后来,当她听说辉的女人病死了,心下止不住快意奔腾,她以为这次辉一定是她的,她不能放弃唾手可得的幸福——即使是做后妈,她也无所谓。她于是厚着脸找辉道歉,可辉说他过去不懂事,其实一辈子就爱过孩子她妈。梅的心情再次回到原点。后来,不知道是为了离开伤心地还是为了摆脱她,辉甚至卖了老房子,把家迁到了隔壁的青城。
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不再有交集,梅或许并不怪辉,只叹这就是命。可现在她真的看不出凤哪里就比自己好。看辉那样,她真想像小时候一样,揪揪他耳朵,让他反醒反醒。然而恨又如何?一块馒头搭一块糕,馒头再黑再黄,糕再漂亮,碰在一起,糕还是会主动粘上去。
只见辉蹲下身子,帮凤刷鞋,边刷边嘟囔:“唉,这雨怎么就不见小呢!”
凤不耐烦,一手抽过辉手里的刷子,然后抹了抹刷子上扬起的硬毛,见怎么也抹不顺,便随手扔进鞋柜上的抽屉,然后说:“去吧,没人拦你。”凤这次没加重音,辉有点蠢蠢欲动,但欲进还退。
梅接过被辉刷过的鞋,虽然那刷的两下心不在焉,可梅还是感觉到一股暖流自脚心滚来。于是她决定帮他一下。其实任何情况下她都想帮的,只是她要考虑如何能帮得不动声色。
梅说:“外面的雨好像没停的意思,要不用我的车去接吧。”梅知道辉是会开车的,只是家里没车,而凤不会开,凤说过没兴趣,买了也不学。梅这么说时,有过开车送辉的念头,可也只是一闪便灭了。
梅掏出钥匙给凤,她想让凤陪辉去,可凤却没接。凤让梅陪辉去。凤想看看辉是不是真心如磐石。可她不知道,很多时候,男人是经不住考验的,当然,她即使知道,也一样认为她的辉除外。辉也的确如她所想。
梅有一瞬间的兴奋,她多想他们能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有人说不管什么样的男人,只要把他关在电梯里,和一个漂亮的女人,都一定会心猿意马。梅恨从来没有一個能够同时容纳他们俩的电梯,虽然自己算不上漂亮,可也还是可爱的。然而梅的兴奋没能持续下去,因为辉给她的是拒绝的眼神。梅只能退而求其次,稍作迟疑后一把拉了凤,说:“同去。”梅打趣道:“姐夫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家呢。”
凤没什么兴致,觉得这一大帮人要兴冲冲接团团,她心里就有疙瘩。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嘛!其实她也不是跟团团有什么意见,一个后妈跟继女多数是隔了一层的,可要说有多大仇,倒真谈不上。凤跟团团就是这样,见与不见,彼此都无所谓。可凤认为辉对团团的过分宠爱,抢了自己在辉心中的位置,便无端的给团团加了一份恨。凤说:“你们去就行了,要不,他一人去也行,咱俩还没好好聊呢!”然后拉梅坐到沙发一角。梅把钥匙顺手放到玻璃茶几上。看辉还站着,梅怏怏的,有点于心不忍的样子,可是想到他只是想凤去的意思,便也硬硬心肠,低下头跟着凤一起不理。过了一会子,听没动静,凤才又递过一个不冷不热的眼神,说:“快去吧,别迟到了。”
辉盯着钥匙看了一眼,到底没拿,走了。梅没坚持,凤也懒得理。直到听到他下楼的“踢踏踢踏”声,两个人才又恢复之前的表情和声音。
凤打开电视开始追剧,梅没想到凤追的竟然和自己追的是同一个。
梅说:“看得出来,姐夫很怕你。一个家男怕女,才是幸福的样子。”
凤说:“虽然谈不上不幸,但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梅说:“一个大男人,都被你弄得跟太监一样臣服,还不知足?”
凤说:“我情愿他在外面呼风唤雨,回来大男子主义一点。”边说边端出辉刚削好的苹果。梅也不客气,立即拿着最上面一个大个的,毫不淑女地啃起来,边啃边叹:“凤,你还是知足吧,姐夫可真懂得体贴呢。”
凤撇撇嘴道:“切!我不看也知道你刚才拿的那个不是完整的。”
梅把苹果握在手上转了一圈,果然有个地方掏过一个洞,不是虫蛀就是局部坏了。梅有点迷惑,问凤:“你有天眼?”
凤说:“我这也是规律。每次两个孩子在家,辉端出水果,总是把最大的或者最有看相的放最上面,让圆圆先挑,圆圆认为辉疼她比团团还甚,于是总是心安理得的拿最大的。后来我发现团团并没有因此有半点生气。我想,一个半大的孩子,正是争食抢强的时候,怎么会这么懂礼让呢,不定有什么机关猫腻吧。后来我就仔细观察,发现,每次辉端出来的水果,没问题除外,如果有什么问题,那问题水果一定是隐蔽地放在圆圆最容易拿的位置。当然,我没跟圆圆说过,我还不想破坏辉在她心中的形象,毕竟自己成家一半也是为了圆圆能有个完整的家庭,享受完整的爱。”
梅不太相信,从前的辉,从来都是恨不能摘天上的星星给她的。梅说:“也许凑巧了吧?”
凤说:“我倒希望是。”
梅说:“比如,一篮苹果,碰巧就一个大个的,偏巧有指甲大点儿结节,挖出个小洞,放下面,给团团吧,圆圆肯定认为辉偏心,放上面给圆圆吧,偏巧被你看着了。”
凤强调说:“其实也不止这一件事。比如刚才你看到的那件酱红雨披,本是圆圆的,被他给团团用了两次,就顺理成章是团团的了。再说拖地这种小事,他也能分出彼此来,总先拖团团的房间,这个不谈,总有先后,可他拖团团房间时,就定会趴着把床下也拖了,到圆圆房间,他就只是画‘眼睛框。”凤本来不想说这么多,可一想到辉的小心眼,她就咬牙切齿。
凤说:“看他那小气样,常想和他分,有时甚至杀了他的心都有,想到将和这么一个人过一辈子,总是悲从中来。”
梅说:“分了也未尝不可,我也常想分,只是他不肯,说为了孩子。”梅心下想,凤要是分了,她回家立即分,这一回她有信心把辉夺回来。
梅开玩笑,问凤:“有没有入眼的桃花?”
凤说:“还桃花呢,连个狗尾巴草也没有。”说到这个,凤就恨,说:“最初我还和两个异性同学有联系的,后来一拿到手机,辉就怀疑,就生气,然后就甩脸色不理人。什么事也没有,他都能生几天气。后来,我就当着他的面,把异性同学的号码全删了。”凤问梅有没有,总不至于到孩子大了还这么守着。
梅说:“我就天天埋在花丛中草堆里,我们家那个也不管,他没得嘴巴说人,只是我自己心里没有再容别的花草的地方了。”
凤并不知道梅和辉相爱过,至于娃娃亲的玩笑许多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开过,谁也不会当真,凤当然也不会。凤劝梅:“既然他回不了头,你也别太苦了自己。”
梅说:“他除了心被小的拴住,对我和孩子出手倒大方。零花钱一万两万的都不要自己主动开口要。”
凤说:“你终究好命,我自从跟了辉后,都好长时间没尽兴逛过街买过衣服。节前,买了条裙子,其实还没到一千,就被辉数落了一番。说上班穿不了裙子,放橱里也浪费。”
梅想说:“说明辉不够爱你。看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就看他舍不舍得为她花钱。”再想到自己,终究没说。不过,梅对凤所说的并不完全相信,她想,女人是男人的学校,男人如何,全看学校的教学质量。辉以前不是这样的,如果换作自己,辉不会这样。
两个人就着茶几上的杨梅和南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边聊边看着电视。追的剧结束了,两个人也没发现,其实电视里放的什么,两个人并没在意,倒是那些南瓜子,让梅想起来曾经和辉一起掏南瓜瓤拣南瓜子的旧时光。那些滑溜溜的瓜子总是躲在滑腻腻的瓜瓤里,梅总是拣不过辉,常常急一头汗,然后用沾有瓜瓤汁的手撸汗。当辉看到她不是眉上沾一丝瓜瓤,就是额上沾一丝瓜茎,便笑出声。辉笑起来特别好看,两颗小虎牙总让梅看得发呆。有一次梅大着胆子,将食指伸进了辉的虎牙下。辉当时有点懵,来不及反应,便本能地咬了一下,梅也懵了,竟忘了疼。等两人反应过来时,都羞得一脸红。这是两人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所以梅常常在午夜梦回时,拿出来咀嚼。
当然,梅不会告诉凤这些,只问凤:“你们俩都喜欢吃南瓜子?”本来,她想问是不是辉喜欢的,想想单独关心人家丈夫喜好,怎么想来都不妥,出口时便成了“你们俩”。
凤说:“其实是我更喜欢。”梅随后补了一句:“辉应该也会逐渐喜歡的。”
梅知道辉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自己坚持的爱好,常常喜欢着别人的喜欢。本来辉是从不吃南瓜、山芋之类的瓜菜的,就因为梅喜欢,辉就常常让他妈给他煮,自己吃罢总给梅偷偷用袋子揣藏些。
凤回道:“的确,他现在也慢慢喜欢了。他说喜欢陪着我一起嗑瓜子浪费时间。你说一个大男人,说这种话,还有没有点出息?”
梅一下子鼻子有些发酸,这句话曾经辉跟她说过不止一次。以前她喜欢瞎逛,他便陪着她逛,她喜欢弄花,他便跟同学要了花种帮她栽。他总说,喜欢和她在一起浪费时间。她一直认为他没出息,整天围着女人转。尤其是遇上丈夫后,她曾想,男人就应该是干点大事的,贾宝玉似的整天围着女人转,结果只能当和尚。那时很庆幸,自己没跟辉。后来丈夫不回家,才知道他并不是干大事,也是整天围着女人转,只不过不是自己。她突然很想辉,要是跟了他,再没出息,至少整天是围着自己转的。
梅好想再听辉说一句:“好想陪你一起浪费时间。”
倒是得到的人和她当初一样不珍惜。凤边嗑瓜子边不屑地说:“其实我不喜欢男人嗑瓜子的样子,琐碎、小心眼甚至有些猥琐。”梅不知道凤怎么总把这些跟男人联系上。梅说:“难道你喜欢他出去吆五喝六?”凤说:“吆五喝六总比窝在家陪女人好吧?”凤想起以前的那位,现在记得更多的是他豪爽豁达的性格,她记得他从不小心眼,当然她也没忘他常常应酬到深夜不醉不归的情景。不过,凤现在想来却已经不讨厌了。
梅想说句俗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梅没说出口,辉已经站在门口。
辉一手抓着雨披,一手捋前刘海上的水珠。那黑黑的刘海中已经开始夹杂着花白。倒是那黑黑的眼珠仍和从前一样,发着闪烁的光。当然这光束只射向凤。
辉说:“没接到团团,倒是接到大爷电话,说刚在车站送人看到团团,顺便接回了家。让我们下乡吃饭。”说完,将雨披下的菜一并放在桌上,然后用眼角余光瞟了一下梅。
凤以为辉是征求梅的意见,忙拉了梅说:“一起去,一起去,没什么要犹豫的。正好见见你老舅舅妈他们。”
看到辉带回来的菜,凤又有点恨。她真想像泼妇骂街一样骂辉:“没用的东西,就知道在家小心眼,有本事跟老爹老妈争去?回家吃顿饭,还带菜?他们退休工资过万,你怎么沾不到几根毛?”有梅在,终究没说出口,可越想越气,越气越恨自己怎么遇到这种人。
梅其实并不是真不想去,虽然那什么舅舅舅妈是九曲溪拐了十八弯。可她想去看看凤在辉家的地位,顺便给自己打打基础,虽然这基础也许日后也用不上。当然她心里越想去,说出口的话越是场面,她说:“我还是不去吧,我一外人去恐怕会破了你们全家的团圆氛围呢。”
凤不依,说:“我们还要坐你车呢,外面下雨我可不想成落汤鸡。”
梅又嗔道:“姐夫还没同意呢。”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叫表哥,但终没说。
凤笑道:“姐的意见就是姐夫的意见。”
辉的一切不情愿,都会在凤的笑里融化。所以凤笑了后,辉连一点不耐烦也没有,小媳妇似地拎着菜跟在凤后面。他仍然是喜欢着对方的喜欢。梅感叹:为什么有些男人就永远有初心呢?感叹归感叹,表面上却是极其周到,梅把车一直开到凤家门前水泥地坪上。
倒是凤,想到要和那一大家子尤其是辉的毒舌大嫂一个桌上吃晚饭,她觉得这比中秋夜吃月饼吃到一只苍蝇更让人难受。凤瞧不起大嫂的粗鄙态,大嫂也瞧不起凤的酸文样。但没有合适的理由不去,凤只好怏怏地跟在辉后面。
辉一手撑伞,一手开车门,让凤先上了车。凤本来想跟辉一起坐后排的,想着不能留梅一人开车,就又抬脚上了副驾驶座。辉则坐到了凤的身后,然后跟梅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是辉这天跟梅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梅调侃道:“欢迎麻烦。”然后三人一路无话,车很快到了辉的父母家。
辉的大嫂穿着雨披站在门口井边洗菜,直到梅按喇叭,她才知道这白色小迷你车是来她家的。本来她还想,凤今天坐辉的摩托车,虽不至于真成落汤鸡,但头发一定没往常整洁,小脸一定也没以往的红晕,没准还和自己一样滴着水呢。辉的大嫂本来还有点幸灾乐祸这雨下得好,不曾想,凤衣着光鲜神采奕奕地从小迷你车里出来,然后看辉从另一个门下来,正准备问“啥时买的车”,却又看到梅从另一个门下来。她对梅不熟悉,脑子瞬间短路,忍不住:“演双花记呢!”辉大嫂从小爱听说书,大概双花记听多了,头脑里就只有个双花记。
辉苦笑,凤抢先说道:“双花算啥福气,指不定什么时候还弄出个三花来。”然后把梅向大家做了介绍。
大嫂是自来熟,对陌生人总比家里人热情。公公、婆婆象征性的点头微笑后,把菜拿去厨房。公公说:“以后回来不许买菜。”凤抢白道:“这个是梅买的。”然后跟辉会意一笑。凤婆婆便又回头盯着梅看。梅没等凤婆婆开口,便主动报了家门,然后叫了舅舅舅妈。凤公公感叹道:“怪得,我说怎么这么像北堂小妹呢!”凤的婆婆很快也认了出来,说:“小时候我们还替你和辉说过娃娃亲呢。不过那时小,估计你们也不定记得了。”梅心下想:“怎么会不记得?刻骨铭心呢。”不過梅没说出口,只是任由凤的婆婆问长问短。
婆婆那热情劲儿,凤觉得像看到新媳妇上门。她可从没受过公婆如此礼遇。本来,对于再婚媳妇,公婆的热情是要打了折的。所以,凤也见怪不怪。
倒是辉,怕凤难堪,悄悄拉过团团。团团也算懂事,没要辉关照,便围着凤阿姨长阿姨短的聊起学校的事。
团团已经上大二,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小姑娘,对身边的人和事也都有些自己的看法。团团悄悄地问凤:“为什么到奶奶家总是闷闷的像换了个人?”凤说:“也没有,就是换了环境,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团团说:“其实我也不喜欢来奶奶家,空气里总觉得喷了清香剂,有假假的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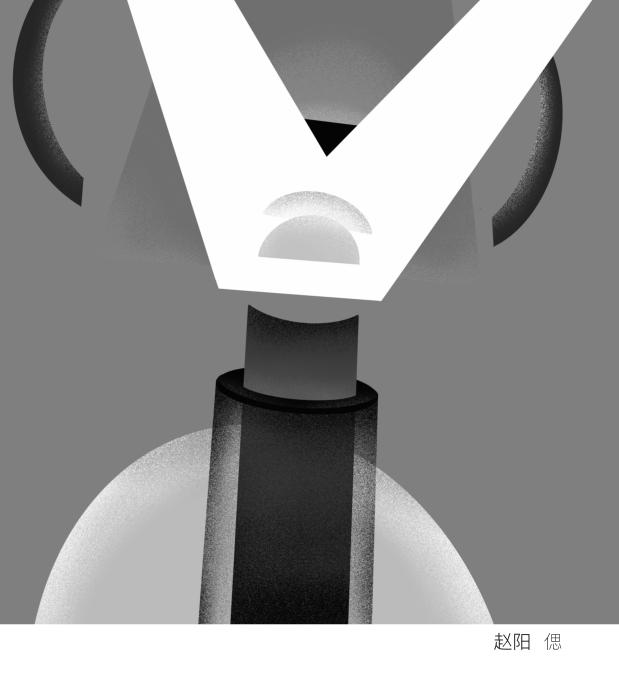
假假的香味!凤觉得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好。每一次她都有同感,只是没能像团团这么总结出来。凤觉得团团不应该有这种感觉的,爷爷奶奶对于自己孙女,即使不是自己带大的,怎么也比一个没有为自家儿子生过一男半女的二婚媳妇要亲的。凤想,或许是为了安慰自己吧,团团这孩子太过善解人意了。
对于团团,凤是不排斥的。如果不是辉的过分自私的热情和小心眼,凤相信自己甚至会喜欢上团团。可每次看到辉对团团那不着边际鸡毛蒜皮的关心,如果团团咳上一声,他会问上一堆废话:是不是穿少了,是不是受凉——是不是那个大姨妈要来了,不是还有一星期的嘛,多喝点水再加件衣服,诸如此类。凤听到就烦,然后就会连着团团一起烦。团团爱扎在男孩子堆里玩游戏,要不是这个,高考不会只考个本二。每次看到团团玩,凤就忍不住在心里嘀咕:有其父必有其女,小心眼的家庭走不出大气懂事的孩子。有时凤也会在圆圆面前抱怨两句。圆圆跟凤不同,圆圆开朗没偏见,跟团团倒是处得像亲姐妹。圆圆是直肠子,有时就会直接批凤:“妈,你不应该这样带着成见看人的,其实姐姐还好。”有时还会给凤讲道理,说:“成绩并不是万能的,我虽现在成绩比姐好,将来生活也未必就强过她。”凤有时也会因此自责,不过很快又会被辉的小心眼打破,继续陷入抱怨的循环。
辉其实也不叫小心眼,只是对团团过度保护,因为家庭的破裂,对团团的伤害总或多或少存在,辉总想降到最少,所以常常不经意间忽视了凤的感受。女人的感受常常抢在男人的动作前,所以凤有时的敏感辉是不知道的。比如,团团叫辉的大嫂“大妈”时,凤会感觉那亲热劲要胜过自己,尽管她知道团团是带了点表演性质的,可心里仍然会有逆流。当大妈放下菜,双手在围裙上擦擦,然后一手拉着团团,一手向凤招着,转头跟团团说:“叫你阿姨过来坐坐,那边有大爷和你爸忙就行了。”凤又觉得大嫂是故意在“阿姨”上加了着重号的,凤又多心了,总觉得“大妈”的份量是要比“阿姨”重些的。这些感受虽然只是弹指间,没有人注意到的,然而凤的心头却已经打过几层浪。
凤也知道太过敏感是种病,她也不想,可感觉总在不经意间跑出来。所以看到婆婆对梅的热情,她虽表面上不在意,心里却早已把罪归在了辉头上。她觉得他们还是分了好。想到分,她便又想到了前夫。他酒后出轨,多次道歉,可她仍坚持要离,并发誓一定要嫁个不会出轨的。现在想来,不出轨的也未必就是好的,窝囊得出不了轨的也说不定。辉是这样,辉那个整天拴在厨房的大哥,想来也差不多。女人没有女人样,多数因为男人没有男人样,大嫂的强悍精明或许也是被大哥逼出来的。想到这,凤突然觉得大嫂也是可怜之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大嫂聊了起来。
她们聊着的当口,辉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梅引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那房间比城里普通三室一厅的房间要大一倍,里面塞满了沙发、彩电、冰箱一应物什。不过衣橱仍用的几十年前家里的陪嫁,是那种手工做的红漆雕花描金镂空双开门的,上下门左右各镶一个椭圆镜。梅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出嫁时母亲能陪一个这样的大衣橱,她和辉一早起来各站在一个椭圆镜前穿衣服。现在再看看这土掉渣的橱子,梅觉得当初的自己实在是幼稚。当然梅只是心里这么想。梅说:“舅妈,我小时候做梦都想有这样的橱子呢。”边说边帮辉母亲收拾摊在桌子上的干南瓜子。
辉母亲不无遗憾地说:“辉没福气,要是娶的是你,我们就有福气了。之前的那个,正经倒是挺正经的,可惜是个病团子。现在的这个是个搞舞蹈的,我们一想到就悬着心。”
梅说:“舅妈多虑了,凤为人挺好的,只是爱跳舞而已。”梅也不是想帮凤正名,只是实话实说。看来婆婆对再婚媳妇的成见很难一天消除。
辉母亲道:“也不是不让跳,那些大妈跳的广场舞,我就不反对,可是那跟男人抱在一起跳的交谊舞,我担心会不会跳到床上去。”
梅真想笑,可看辉母亲一本正经地说相,也不好调侃。便说:“凤每次跳,都是辉陪着去的,舅妈不必担心。”想到辉爱好着凤的爱好,心下又是恨恨的。
辉母亲叹口气道:“但愿吧,我担心也没用。辉就这命。那个死鬼走了以后,也没少说媒的,可他总怕团团受委屈。每次总先把团团放在前面说,哪个女的对一个非亲生的孩子能一开始就表现出好感来呢,真不知道凤当时是怎么想的。”
至此梅才知道,凤和辉原来也是通过相亲相上的,只不过凤说过愿意把家里最好的先让团团挑,一下子就感动了辉。梅本来还以为他们是自由恋上的。想到自己不如一个相亲的,梅又是一阵子难过。不过跟辉母亲也不便说这些。谁能真的走进谁的心呢?
辉母亲问梅:“你和凤关系不错?”
梅说:“中学同学,闺密。”
辉母亲便低声道:“那你能不能劝劝凤,再生一个。”梅惊讶,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再多一个,得多大负担?见梅不解,辉母亲补充说:“怀孕生了孩子,身体走了形就不用跳舞了。”
看梅还是不解,辉母亲干脆兜了底,说:“这事只有我和你舅知道,连凤也不知道,团团不是辉亲生的,是前面那个怀在肚子里带来的。”
梅心里有小地震。辉母亲又补充道:“论良心讲,凤对团团倒还不错,衣服、生活费哪样也没少。这些也都承了凤的情分。可没个共同的孩子,他们的感情能长吗?再说,我也很想辉有个自己的孩子。”
梅虽有个儿子,可她还是想为辉生个孩子。当然,她不会轻浮到跟辉和他母亲说这些。梅说:“放心,舅妈,我会劝凤的。”当然,她不会告诉舅妈她不希望凤和辉有孩子,一个牢牢捆住他们的纽带,她可不想他们太牢。
至此,梅和辉母亲因为团团的秘密,关系似乎又深了一层。两个人聊着聊着听到楼下辉父亲的开饭声,便一前一后牵着下了楼。
凤看她们握在一起的手,心里有些羡慕。自己嫁辉五年了,和婆婆还是客人一样,别说牵手,就是話也没一下子说了超过五句的。要是说上三四句,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接了。
饭桌上,辉母亲故意让梅坐到自己身边。梅本想应了,可看辉的眼神,好像自己使了什么手段。梅便推让凤坐,凤不从,依辉坐了。梅又推让大嫂,大嫂说,天天在家靠着呢,也没意思。梅便只好依辉母亲坐了。席间,辉母亲对辉说:“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有没有考虑再要一个?”凤不等辉开口,抢先回答说:“妈,政策是放开了,可再要一个我们就是三胎了,怎么养得起?”凤没说自己不想生,只说经济问题,其实这也是最现实的问题。没想辉母亲一口承下,说:“你们要是再生一个,费用我们全包。”大嫂不答应了,说:“咱妈这是重男轻女,想孙子想疯了。咱家玲玲和二爷家团团哪里就比男孩差了?这是欺负我们年纪大生不出来吗?赶明儿我也生一个。”辉母亲立即回道:“你要生出一个男孩,费用我也全包。”说归说,大嫂是早已奔五的人了,不会冒这个险。一直沉默的辉最终开口说:“不生,再生对团团和圆圆就不公平。”这话像是赦免令,本来弟兄俩使出看家本领做出的一桌团圆饭,因为一个二胎问题,吃得没滋没味。听了这话,饭桌上开始有了生机。团团忘了在学校一直嚷着要减肥的宣誓,梅似乎也有了味口,大嫂的话开始多起来,人也热情起来。可一时不知道该对谁热情,便只顾往梅碗里夹菜,大概是觉得梅是外人,更没有危险吧。辉母亲便也往梅碗里夹菜,辉的父亲倒是不理他们的热闹,只顾和团团一问一答的。从辉父亲的言语,倒看不出,他对这个孙女有多少偏见。
中秋节的珍珠团圆大肉圆,梅碗里一下子堆了三个,梅便顺手给辉和团团各一个,她知道凤是不爱吃这些的。可就因为这个动作,又让凤多想了一层。梅更像家里人,给丈夫孩子夹菜,自己倒像多余的。
一顿饭各怀心思地吃完。饭后,团团说约了同学逛街看电影,向辉伸出小手。辉会意,便从皮夹掏出一张五十的,算算,电影票加爆米花,有点紧巴巴的,便又给了一张二十和一张十元的。辉在门前拦车,可不大不小的雨中,硬是没见一辆的士。梅说:“我送。回头再来接你们。”
辉母亲立即上楼拿南瓜子,说:“炒了让梅带着,她小时候就爱吃。”
辉大哥真是好人,母亲说要炒瓜子,他立即搬来一捆适合文火的稻草。梅过意不去,抢着要烧。凤知道她这个闺蜜,比自己还懒二分,虽说从小生在乡下,可什么时候真烧过火,便自己抢来烧。辉是最清楚凤的,烧个饭还能夹生,炒瓜子岂不要糊了?于是不声不响地把凤拉过来,然后自己一本正经地坐下来烧。梅嘴上说不好意思,却并不承情,毕竟辉是舍不得凤才替换的。
后来,梅没能来接凤和辉。梅发信息说:“丈夫出了点事,要匆匆赶回。”凤问:“都快离了,还这么关心?”梅说:“不离了。”梅没告诉凤,她被辉给团团零钱的小心样刺激到,大手大脚的她不能忍受日后与这样的男人同床共枕。不过她很义气地告诉了凤,关于团团的秘密。
凤先是很吃惊,随后想想,便对辉之前的小心眼释怀了。凤觉得,是自己想多了,一个男人对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婆,又能差到哪儿去?
回家时,大哥说要开摩托车送,凤没让,说他们打车。可一路上不断有车子在他们身边停下,他们却是没坐。凤一路上拉着辉的手,她似乎是第一次觉得辉的手是那么有力。看到辉手上做家务磨出的老茧,她便不时用手抚抚。这一刻,凤想起谁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家的幸福总是建立在一个人默默无闻的付出,甘当配角的基础上。凤觉得为爱情而结合是所有婚姻中最不牢靠的一种,爱情会消失,消失后,谁的婚姻不是在凑和呢?
责任编辑:朱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