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白:“穿越光影写春秋”
2019-10-18池艳萍
池艳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李少白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史学家、教育家。他参与编著了新中国第一本电影通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该书89万字,以翔实的史料清晰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前电影发展的历程,奠定了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基础,对之后的中国电影研究及学科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少白开创了中国电影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他积极呼吁和倡导电影学硕士和博士点的申报与建设,培养了新中国第一届电影学硕士生、博士生,极大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电影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他穷其一生为中国电影学的教育与研究奋斗,不断自我革新,长期坚持在电影史论研究的前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学者,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晚年他在诗中写道“教书不意居清苦,编史何期享誉名”,道出了他编纂影史、教书育人的甘苦,也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注解。
走到红旗下的青年
1931年7月,李少白出生在安徽省太和县三塔集镇,父亲李道明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中医。李道明国学素养深厚,喜欢写诗作画,尤其钟爱诗人李白,或许这正是他给自己儿子取名“少白”的缘由。李少白幼承家学,萌发诗性,对诗的爱好贯穿一生,晚年出版了古体诗集《灵府轨迹》。他在序言中写道:“诗,情感的旅程,心的旅程,再也没有别的文体能像诗那样透露人心底的隐含了,不管这隐含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所以诗贵真;只要包藏着真情实感,心切、意切、理切,哪怕一时不被别人所理解、认同、接受,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对诗的这一体悟正契合中国传统美学中 “诗言志”(《尚书》)、“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叶燮)的思想。诗是李少白的心灵伴侣,他不仅有着对“诗贵真”的深刻理解和认同,更将“求真”作为他为人与治学的准绳。
小时候,李少白在家接受传统家族式的学前教育。他跟着父亲的学徒一块儿从《三字经》背到《论语》《孟子》,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8岁,他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语文、数学等科目。在家期间,李少白看到父亲艰难的创业过程,看到学徒们不厌其烦、日复一日的辛苦制药,这让他懂得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孜孜不倦,一丝不苟。
1945年,李少白入中学,时值国内局势动荡,学校师资迁移频繁,他先是转学到阜阳的中学,次年又转学到长淮临时中学。暑假期间,他第一次走进了电影院,看了《海茫茫》和《万家灯火》两部中国电影,前者镜头的意境和后者深刻的主题,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看电影是很费钱的消遣,看一次电影的票价抵得上他租数十本小说的花费。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前夕,他随学校由阜阳搬到杭州。作为一名流亡学生,他身无分文,只能到灵隐寺借住,夜里睡在大雄宝殿的屋檐下,蜗居了一个多月,后转移到徽州落脚。1949年5月,皖南解放,他徒步从徽州走到芜湖,先乘船到南京,再乘火车回到蚌埠家中,这才结束了皖南的漂泊生活。高中毕业,李少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升入大学;要么就业。然而,连年战事,经济萧条,家中已无力再支付他上大学的费用。父亲李道明希望他能去银行或是邮局供职,他都没同意。李道明的朋友李晨是皖北西部地区地下党领导人,李少白在与李晨交谈后受到激励,拿定主意参军,就此踏上了红色革命的旅途。
1949年9月,经李晨介绍,李少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初入部队,他受到老红军们的关照,很快地融入了部队的生活。在南京集训期间,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等一批革命领导人亲自给他们讲课、作报告,传播党的理念和思想,这些新知对李少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回忆说:“这仿佛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受益匪浅。重要的是使我找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确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在部队这所“大学”,他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坚信奋斗就有前途。1950年,李少白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诗意情怀与科学的马克思辩证思想并行不悖,共同构筑起他的思想根基。

李少白任西南服务团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七中队文书(摄于1949年宜昌)
1949年10月,李少白所在的西南服务团开始向目的地重庆进发。出发前,他被分配到西南服务团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七中队,担任文书。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地方还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出于安全考虑,部队选择先北上再南下的迂回路线。李少白跟随部队先步行至下关,乘轮渡到浦口,再搭火车,经徐州、郑州,后往南到汉口停留了一个月后,又乘船沿长江逆行而上,十天后到达宜昌。行程中,因为怕敌人偷袭,他们只坐铺着稻草的闷罐火车,乘船时不上甲板,长时间待在颠簸的船舱内。在宜昌,李少白拍了生平唯一的军装照,寄回家向父亲报了平安。次年1月,他再次乘船,数日后到达重庆。这场历时三个月、行程七千里路的远征磨炼了李少白的精神意志,使他从流亡学生蜕变为一名不畏艰苦的革命青年。
误打误撞与电影结缘一生
1950年1月,李少白到达重庆后等待分配岗位,参加大西南建设。部队领导起初想把他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继续做文书,但他受父亲影响,希望能从事技术工作。部队领导通情达理,默许了他的想法。1950年2月,西南大区影片经理公司成立,来部队招人。负责人口音很重,李少白把他说的“电影”误听成“电业”,满心高兴地答应了,结果一去才发现是“电影公司”而不是“电业公司”。他心里难免失落,但再开口要求退出会让人觉得他挑三拣四,因此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留了下来。19岁的李少白就这么误打误撞进入电影业,并与之相伴一生。
李少白在西南大区影片经理公司秘书科负责起草公文。为了补充电影知识,他有意识地搜罗电影书籍和资料,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拿来阅读。新中国成立初,国产新片的数量还不多,能看到的大多是苏联电影。1950年,他在重庆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影评《谈苏联影片〈起死回生〉》,后来写影评逐渐成为他的一个爱好。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影评后,李少白获得了一些名气,也打下了撰写影评的基础。
1954年,大区撤销,李少白从重庆调到北京的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宣传处工作,住进了位于西交民巷的单位宿舍。在“中影”,他负责起草电影宣传方面的工作指示。这项工作要求熟悉国家政策,写出符合规范的宣传指示,这训练了他写作中的政治意识。李少白还负责组织电影观摩,邀请报社、期刊社、新闻社、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来“中影”看片,有时还要组织小型座谈会,听取各方的宣传意见。此外,他还参与引进外片的审片任务。虽然是看电影,但并没有想象中的惬意,有时候他和同事一天最多要看六部影片,几乎是件“体力活”。他们要从数量庞大的外国影片中初选出优秀的作品进行推荐,这无形中帮助李少白积累了可观的看片量。
工作的关系让李少白接触到不少新闻记者,加上他有优先看片的机会,因此不少报刊邀约他撰写影评。三四年间,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艺学习》《大众电影》等报刊发表影评五十余篇。崭露头角的李少白被《文艺报》聘请为“特约评论员”。
谈起影评写作,李少白说:“写电影评论最需要的是真情实感,第一直觉很重要,空有缜密的理论分析、没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是不能感人的。”对于报刊的影评邀约,他要求“两情相悦”,“自己不想写或想不出如何写的东西,都婉言推辞”。50年代初,电影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相对陌生的艺术形式。新中国成立前,电影院主要分布在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观众以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为主,只占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艺为人民服务”口号的提倡,大量人民群众进入影院,而影评成为他们学习如何鉴赏电影的一个重要渠道。
1956年,李少白在《光明日报》发表影评《推荐〈马路天使〉》,文章先是对影片人物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接着浅显易懂地点出导演袁牧之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手法,不着过多笔墨就勾起了人们的观看欲,而已经看过影片的观众则会在他循循善诱的文笔中对影片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影评《〈如此多情〉问题在哪里?》以客观公允的分析,平息了这部影片在当时引发的多方争议。他的影评善于从电影的艺术特点出发,注重将感性的艺术直觉与理性的辩证分析相融合,凡所言必有充分的依据做支撑,情理兼备,广受读者的认可。因此,李少白被称为中影公司的“四大笔杆”之一。倪震形容他的文风“像拧干的毛巾,干货多,水货少”,很中肯地总结了他影评的特点。
“中影”三年,李少白的思想建构、学识沉淀和写作能力日趋成熟。1957年10月,他由“中影”调到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1997年改为中国电影家协会)艺术研究部工作,成为单位第一个在职在编的电影艺术研究人员。1958年,27岁的李少白进入《中国电影发展史》(后文简称《发展史》)撰写小组,开始了在史学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为中国电影史筑基
50年代初,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想要筹办电影大学,并要求:“电影大学的课程必须要讲述中国电影的历史,应该让年轻人知道,不仅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电影能够有今天的局面也来之不易”,进而提出要编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想法。1955年,《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起草完成,得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的首肯。1958年《发展史》项目正式上马,由程季华负责,李少白、邢祖文和王越三人组成“中国电影史小组”写作班底。
李少白回忆当时《发展史》写作是“既有条件又没有条件”。“有条件”指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中央电影管理局为支持《发展史》写作曾向各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发公函,希望他们把看到的与电影相关的资料都打包寄到中央电影管理局。公函一经发出,很快得到积极的响应,中央电影管理局陆续收到四面八方寄来的资料邮包。写作小组成员王越还专程去上海图书馆藏书楼内拍了一个多月的微缩胶卷,把上海主要报刊上有关电影的文章都拍了下来。这些搜罗来的资料整整堆满了一个十四五平米大小的房间,为《发展史》写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弹药”。
“没有条件”是指在《发展史》之前,中国虽有《中华影业年鉴》(1927)、《中国影戏大观》(1927)、《中国电影发达史》(1934)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等电影史方面的著述,但在史观和史料的系统性、完整性上尚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还没有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上回顾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著作,同时可资借鉴的外国电影史类书籍又极为有限。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官修电影史,《发展史》写作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新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下勾勒出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因此必须树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一切都需要撰述者从头摸索。
写作开始没过多久,成员王越就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压力过大而生病,退出了写作小组。《发展史》的写作规划也缩短到1905年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电影历史,写作任务落到李少白、邢祖文身上。两人各有所长,李少白理论素养扎实,邢祖文精于史料的挖掘与整理。
对《发展史》理论框架的构建,李少白依据了几份重要的文献:一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30年代文化革命的肯定;二是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谈中国电影的继承传统时肯定了30年代的进步电影;三是夏衍在《翟秋白的二三事》及一次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回应;四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艺与30年代进步文艺之间关系的论述。在这些重要文献的基础上,《发展史》梳理出一条从30年代左翼电影到延安时期的人民电影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郭安仁认为《发展史》最鲜明的特色是“它对中国电影历史发展规律所进行的严肃探讨”。
《发展史》写作采用“交叉作业”的方式,李少白和邢祖文各自完成负责的章节后互相修改。二人对文稿反复修改,写完以后回头再看,感觉不行,就重新再改,这个过程来回重复了三四轮。写到“软性电影”斗争,邢祖文觉得这部分理论性太强,难以把握,转交给李少白起草底稿。李少白在阅读了20万字的材料后,发现当时舆论话语纷繁复杂,论战双方的语气都非常激烈,一时也难以下笔。30年代,“软性电影”与 “左翼电影”针锋相对,刘呐鸥、黄嘉谟等“软性电影”评论家从电影的属性出发,主张电影的娱乐性。他们发文批评“左翼电影”人将电影视为宣传“反帝反封”的工具,对《春蚕》这类具有左翼倾向的电影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但“软性电影”对娱乐性的坚持也揭示了电影的重要特性。如何对“软性电影”斗争做出定性,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这有相当大的难度。李少白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他认为“软性电影”主张对电影的本体研究有一定建树,但在抗日战争一触即发,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软性电影”与“左翼电影”之争的实质就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他借用鲁迅的话说:“看一篇文章不仅要顾及全文,还要顾及全人,就是说要看这个人所有的文章,另外还要顾及时代。”这样的思考与评价足以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领悟与贯彻。
1961年,李少白与邢祖文在完成《发展史》初稿后,马上进入集中修改阶段,直到校对阶段他们还在字斟句酌,不断对文稿中感觉不足的地方进行调整,甚至引来了印刷厂工人的抱怨。《发展史》印刷后交陈荒煤、夏衍、蔡楚生、袁牧之等几位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审阅,书中一些基本观点获得认可,并根据审阅意见进一步做出修改。1963年2月,《发展史》正式出版,初版印刷4200册,立即销售一空。此书的出版成为新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但紧随其后的是,《发展史》遭遇政治劫难,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部电影史著作才又一次迎来自己的春天,重新再版并多次重印,累计印数已达4万册,同时在美国、日本等地有多个译本。
《发展史》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历程,树立了中国电影史研究范式,成为电影史学研究的一座丰碑。陈山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研究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电影史学者的写作理念。”李少白在《发展史》中所作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性价值。在当今多元文化思潮冲击下的电影史学研究中,《发展史》依旧是标杆式的著作。
电影所的“大树”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掩盖自己在30年代的不光彩历史,将《发展史》诬指为“文艺的大毒草”,要求将所有印好和已发行的书全部销毁,《发展史》的作者也受到牵连。1967年,李少白被隔离审查。1969年9月,李少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拉耠子、打草、拾粪,干各种脏活累活。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期间系统地阅读了德国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没能让他放下手中的书本。
1973年,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为修订《中国电影发展史》,李少白从“五七”干校被抽调回京,担任国务院文化组艺术研究机构电影组组长。囿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修订工作一直没有展开,但他全身心投入电影研究和评论工作,组织王人殷、黄式宪、郦苏元等几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同志,借“影研”的谐音,以“尹岩”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十来篇评论样板戏电影的大篇幅文章,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
1975年国务院文化组正式撤销,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更名为文学艺术研究所,李少白任电影研究室主任。1977年,文学艺术研究所从东四八条迁到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后院。李少白在一幢俗称“九十九间半”的二层楼里,继续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电影研究。1978年,文学艺术研究所改为文学艺术研究院。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室改为电影研究所,李少白任副所长。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大量西方理论思潮涌入国门,东西学术交汇,国内理论界、思想界活跃非凡。面对电影界活跃的理论创新局面,李少白提出要办一本电影理论刊物,除了为单位内部的理论研究开辟阵地,更重要的是为整个电影学界提供一个讨论交流的平台。

李少白爱惜人才,也会用人才,提携后辈。随着电影所的队伍不断壮大,不少从文史专业“半路出家”的新人加入。对待小辈,李少白从不摆领导架子,更不以专家自居,他总是用心、耐心地指导他们,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干。张震钦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到电影所工作,李少白为了锻炼她,安排她去采访老导演吴永刚。张震钦心里没底,拿回了采访稿,不知道如何组织成文,李少白认真阅读后建议围绕吴永刚的经典影片《神女》展开。文章刊出后,吴永刚看了也十分满意,并主动表示愿意继续接受张震钦的采访。沈及明刚到电影所时,负责《大百科全书》电影词条的撰写。她没有这类工作经验,写出来的词条不合规范。李少白知道后,拿过沈及明的稿子,耐心告诉她问题在哪、如何修改。正是由于培养、聚集了一批影视人才,《电影文化》越办越红火。1986年,电影所机构改革,《电影文化》划入中国电影资料馆,更名为《当代电影》。沈及明后来担任《当代电影》编辑部主任,她曾回忆:“我常常想起少白,要不是他为我指明了最适宜的工作路数,让我在《电影文化》经历磨练,传授我许多工作方法和经验,我就不可能在《当代电影》得以施展。”

写作中的李少白(摄于20世纪80年代)
1982年,在李少白的带领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成立,招收了全国第一届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开创了电影研究生教育的先河。早在前一年,李少白就不辞辛劳地为招生资格奔走。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美术、音乐、戏剧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上已经比较成熟,但电影学教学基本上一片空白。这不免让不少人担心电影所这样的研究机构能不能搞好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李少白看到国外的电影研究生教育已经起步很久,深感有义务和责任推动我国的电影研究生教育迎头赶上。他将想法与时任教育部艺术学科副组长的王朝闻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沟通后,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顺利获批电影学硕士招生资格。
1982年3月,电影系进行了首次招生考试,录取了陈犀禾、鲍玉珩、钟大丰、张爱华、刘牛、王汉川六人。为了做好电影研究生教学,李少白倾注了大量心血。从设计课程、制定教学计划、聘请名师讲课到联系电影观摩,他都亲力亲为。他聘请汪岁寒、沈嵩生、汪流、郑雪来、周传基、俞虹等名师授课,保障了培养学生的师资队伍。学生们都很珍惜学习与深造的机会。
李少白将“史言当有言凭据,论判须正判目光”的治史观融入教学,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方法训练。学生们在他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治史态度、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注重反思的学术思维。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得电影学博士招生资格,成为中国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李少白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2003年,72岁高龄的李少白指导了最后一届博士生。丁亚平、李道新、石川、高小健、秦喜清都师从李少白,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从事电影史研究,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与教学队伍中的领军人物。

20世纪90年代,李少白和单位同事(右四为李少白,右三为邢祖文)
在学生们眼中,李少白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对每一个学生,李少白都给予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指导。鲍玉珩入学后自觉底子差,成绩总是不尽人意,李少白为他专门“开小灶”补课,教他如何读书。多年后鲍玉珩还清晰地记着,李少白拿出自己的读书笔记给他看,对他说:“要做到开卷有益,不但要多读书,而且要勤记笔记,写出心得体会;不要当书呆子。”石川从上海考到北京跟李少白读博,想到石川来自南方,不熟悉北方气候,一入学李少白就把石川叫到家里,把一床干净的夹被扎捆打包好送给他,果然一入深秋,这床夹被就派上了用场。
李少白毕生尽其所能为中国电影学教育发展添砖加瓦,使中国电影学科不断开枝散叶,壮大发展。1997年,李少白促成并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联合开办“电影历史及理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为上海大学设立电影学研究生教育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在担任国务院学委办公室通信评审委员期间,支持促成了北京电影电影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电影学科建设。
老同事刘树生谈起李少白曾动情地说道:“每至夜深人静,浮想‘九十九间半’前石榴树的花、果,就自然联想起了少白。作为老友和后学,我衷心地希望他真的就像那些老石榴树,虽苍老枝干弯曲,却依然枝叶繁茂,花朵红艳,硕果累累。”对电影所而言,李少白就像是一棵老树,它枝叶繁茂,“大树”上结成的果实,已然纷纷落地生根,为我国电影学的前行发展增添了新的绿茵。
自我革新中前行
1979年5月,李少白在《人民日报》发表《总结经验,解放思想》一文,以知识分子客观自省的态度主动回应思想解放的时代召唤。20世纪80年代初,在提倡多元化的学术思潮下,电影学界积极寻求更新电影史学观念,《发展史》的重写被提上议程。李少白率先有意识地反思《发展史》中的观点,对《发展史》的时代局限和不足,形成了清晰的认识。他想要按照“电影作为艺术”的思路,考察电影作为消遣的玩意儿如何成为一门艺术,其艺术形式又是如何发展丰富起来的,并探讨电影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李少白电影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的自我革新,他力图站在新时代的角度推动中国电影史研究走向更加综合、更具学理性的高度。1984年,李少白开始酝酿编纂《中国电影艺术史》,这一课题试图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一是对《发展史》做出重要的补充和修订,通过重写更全面、公正地勾勒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回应时代赋予中国电影史学者的历史召唤;二是进一步丰富史料,《发展史》虽然有扎实的史料基础,但还是有一定缺失,通过艺术史的撰写,可以补充新发现的史料;三是勾勒出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逻辑,梳理它从娱乐到艺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变化过程,更深入地分析影人、公司的艺术个性,更客观地评价歌舞片、喜剧片等类型电影的价值和贡献。为此他开始组织重新搜集电影资料,在尚未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与所内同事吴瑞庭专程前往上海,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楼查阅资料。

李少白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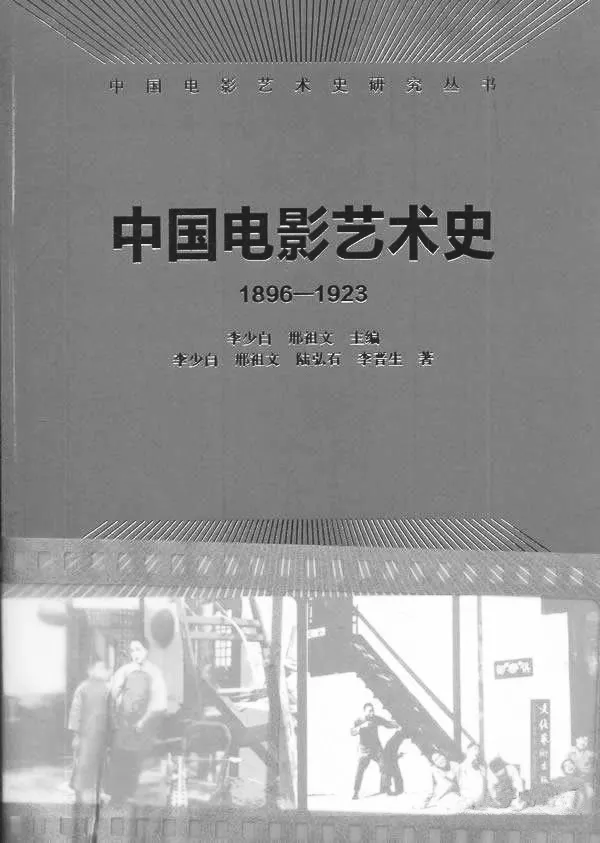
《中国电影艺术史》
1986年10月,李少白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交了《中国电影艺术史》(后文简称《艺术史》)课题立项申请。1987年,李少白完成了约5万字的《艺术史》(上卷)编写提纲,全书计划共六编(卷)。同年,《艺术史》被列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研究项目。《艺术史》由李少白和邢祖文任主编,编写组成员有俞虹、周培龙、刘树生、李晋生、陆弘石、吴瑞庭、朱天玮、王永芳、王汉川、钟大丰、张爱华、郝国欣,另聘王素萍、李凯南负责资料搜集,耿在镳负责编辑。课题立项后,陆弘石和王素萍再次赶赴上海,到上海藏书楼、上海书店等地购买老电影期刊。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电影所宝贵的学术资源,为后进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989年,第一编(卷)提纲和稿子在经历多次推翻和重写后完成。李少白和编写组成员的研究也不断在深入与细化,他们已不仅单纯从美学的角度看待电影,而是把电影放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格局中把握电影发展的内在规律。1992年,《艺术史》获批为艺术学科“八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李少白把“自我革新”的态度贯穿在《艺术史》课题的研究中。在多篇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论文中,他提出以“新兴电影运动”或“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来取代以往的“左翼电影运动”概念,进一步纠正《发展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个提法启迪了很多后学者,扩展了他们的研究思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艺术史》课题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已有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电影史学观念的更新、电影史写作实践的扩展和电影史料的丰富,取得的成绩为学界公认。2006年,李少白主编出版普通高等学校电影教材《中国电影史》,提出“顾及全面、突出重点、讲清史实、指明规律”的写作要求,从电影学教育的角度,再一次推动史学观念的翻新。
在他一生的学术探索中,李少白总是敏锐地回应时代发展对电影史研究的新要求。电影史研究如此,在电影理论的探索上更是如此。“一史一论”是李少白治学的两把板斧。李少白在理论探索中积极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和理论争鸣,先后发表了《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电影和电影文学》《电影本性纵谈》《电影民族化琐议》等重要文章,深化了中国电影学理论研究成果。李少白还在《对电影学科体系的构想》一文中,以十分具有前瞻性的目光率先提出“建立电影学科体系”的这一重大命题,文中的观点和论述至今都是我国构建电影学科体系的重要参考依据。陆弘石说:“这些新意迭出而又立论有据的文字,即体现了作者不懈的学理求索精神,而且也从特定的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学术工作的成果风貌。”
李少白的电影理论探索集中体现在他的电影学论文集中,《电影历史及理论》《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增订本)、《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等著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理论探索轨迹和对电影学的深入思考。在“探赜”与“榷略”的背后,跳动的是他对电影的炽爱之心,同时也显示出李少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谦逊与冷静:以赤子之心探索电影奥秘,以严谨、开放包容的态度治学。如今斯人已逝,但李少白的学术遗产和治学精神将滋养着中国电影学不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