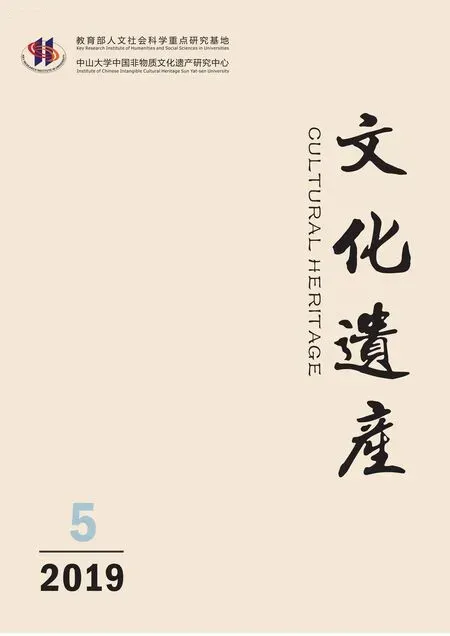作为技术的建筑:近现代集中化茶厂推动的中国乡村茶业现代化进程*
2019-10-12黄华青
黄华青
引论
茶业在中国乡村拥有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茶业作为我国18~19世纪主要出口行业,在中西方资本运作下较早开始尝试现代化转型,但由于集中化组织的现代机械化茶厂与小规模的家庭手工生产模式的冲突,乡村茶业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茶村社会,茶叶种植、加工、流通各环节与社会、生活和空间景观深刻密切的交织构成贝斯基(S. Besky)所谓的“茶叶社会生态”(1)Sarah Besky,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3-4.,使这种技术现象背后的社会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和建筑学意义——如现代化转型对茶农生活的影响、对乡村茶农身份的主体重塑、与乡村生产空间及景观变迁的互动关联——成为研究茶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内涵。本文试图通过茶业史料和一个典型茶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中国茶叶技术的现代转型是何时、如何发生的?它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
何谓“农业现代化”?建国之初,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即“合作化+机械化”,毛泽东提出“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体制推进,又延伸出“产业化”和“科技化”的内涵(2)杨少垒:《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农村经济》2015年第10期。。放在技术与社会研究(STS)语境下,这种二分性源于“技术”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套“社会-物质网络或者系统,包括成套的技能和设备,但也包括受过培训的人力、原材料、理念和制度。”(3)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吴秀杰、白岚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页。故茶业现代化可从“机械化”和“产业化”两个层次理解。“机械化”即物质层面,指制茶方式从依赖手工劳动转向现代机械驱动;“产业化”则指社会层面,以国营茶厂等方式促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集中化,解决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矛盾,并推动茶工的主体重塑。更关键的是后者,借福斯特(G. Foster)的“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概念来说:技术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和技术接受,它是一个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接受过程。伴随着一种技术变迁,人的价值观、信仰、心理和行为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变化。”(4)George Foster, Traditional Societie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2-3.这暗示了茶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
集中化茶厂是本文研究茶业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变迁互动关联的切入点。集中化茶厂是现代茶叶技术的承载物:发源于英属印度茶种植园的集中化茶厂,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术与西方工业化技术融合的产物,传入中国后成为茶业现代化的物质载体。同时在技术的社会性重构——即福斯特所谓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接受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空间-社会”过程可借布迪厄(P.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诠释:“一个生成性的、有结构能力的策略与社会实践原则”,架设在个人行为与社会变迁二者间断带上的桥梁(5)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72.。布迪厄在对柏柏尔人住宅的分析中,将房屋空间视为灌输“惯习”的主要场所,传递“意会知识”的力量比其他知识更为巨大(6)Pierre Bourdieu, 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Honour, 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人类学家英戈尔德(T. Ingold)发展了这一空间-主体的互动建构作用,将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中的身体和栖居概念,作为融合过程与现象、非语言实践活动与地点建造之间主客关系的媒介;认为个体通过参与观察、切身接触和体验以实现本体论意义上的“测度”(mapping)行为,使客观世界在认知主体眼中从“占用的表面”(a surface to be occupied)成为“栖居的世界”(a world to be inhabited)(7)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London: Routledge, 2000), p.232.。技术史学家白馥兰(F. Bray)在对明末清初中国居家空间的研究中,沿此路径探讨家宅中“私人领域”崛起对于现代性意义上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作用,将空间及其伴随的日常生活实践定义为一种“居住之术”(8)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吴秀杰、白岚玲译,第150-183页。。以上研究指向,空间作为身体体验的容器,不只是客体世界变迁的承载物,也通过“测度”和“惯习”参与到主体世界重构之中。
在此视野下,本文赋予茶厂建筑作为“技术”的双重意涵——集中化茶厂不仅就其空间布局而言是现代茶业“物质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凝聚着与之相匹配的现代组织方式和生产理念的“社会技术”。作为技术的茶厂,凸显了空间对主体意识的塑造力:通过茶农身体的“测度”使卫生、标准的现代生产方式深入到传统生产意识之中,也使作为工人的职业精神和经营者的市场意识嵌入到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小农经济之中。建筑作为技术,其物质空间表征可视为推动技术社会性建构的重要媒介。
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以来民间及国家层面建造的集中化茶厂的考察,展现茶村社会如何在与现代茶叶机械及茶厂的接触过程中,完成生产观念至社会组织的现代转型。本文指出技术物质性和社会性内涵的同步是茶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集中化茶厂则是推动二者交融的桥梁——如果说19世纪末民间效仿印度建造的机械化茶厂因社会重构相对于物质更新的滞后而失败,那么20世纪国营茶厂及人民公社茶厂则通过以政治或市场力量将茶农收编至茶厂中劳作的实践,推动机械化与手工化的制茶技术融合,亦促进了小农经济向农业产业化的社会组织模式转变,最终走向乡村茶业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一、近代机械化茶厂的社会性困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茶叶出口的盛期、亦是衰弱的开端(9)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总量第一次超过中国。[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12页。,中国近代茶业现代化的若干尝试大多从物质技术改进着手(10)庄晚芳:《国茶改良之回顾》,《福建农业》1943年第3期。——以引进建造机械化茶厂为标志(早期机械化茶厂尚无法满足集中化茶厂的定义)。只需在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等社会性层面与集中化茶厂源头的印度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与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碎片化的小农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致使机械化茶厂无法获取与其物质性相匹配的社会性条件,这或是早期茶业现代化尝试大多无疾而终的主因。
从印锡引进茶叶机械、在重要茶产区兴建机械化茶厂是这场“官督商办”的改良运动的行动指南(11)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142-160.。民间资本和政府先后组织对印度、锡兰考察,如1898年《农学报》记载,“闻福建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制茶”(12)转引自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1905年两江总督周復派遣郑世璜、陆溁等率团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叶生产,回国后撰写《乙已考察印锡茶务日记》,推动现代制茶理念传播(13)《中国考察印锡茶业的第一人》,《茶报》1937年5期,第26页。。当时中国制茶者虽然知晓印锡茶业核心优势在于机械化——“机器制茶,最为迅速”,较手工制茶“较为洁净”,比“用炭焙制,味大加美”,且“价甚廉贱”(14)《论印度制茶缘起并中国宜整顿茶务》,《时务报》第59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一日。;但早期机械化茶厂却很难融入地方制茶体系。1873年俄国伊凡诺夫公司(Ivanoff&Co.)在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开设砖茶厂,却很快不得不搬到偏远的南垭口和三门,原因是“激起当地民众的怒火和抵制”(15)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pp.69-71.;1890年地方及外国茶商合资成立的“福州茶叶改良公司”,购入英国茶叶加工机器,聘请印度锡兰茶厂的英国技师、中国工人,但由于“遭遇丧失工作的劳动者的抵制”、茶青质量低下、高税收等原因草草收场(16)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1915年,在修水白鹅坑成立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图1),亦遭当地居民的激烈抵制,再加上地利欠佳、缺乏人才等因素,几经转手经营不善,后被收购并入祁门茶业改良场(17)孙文郁、刘润涛、王瑞华等:《江西宁州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北京:商务出版社1935年,第135页。。至解放前,中国茶叶手工生产比例仍占90%以上(18)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九章,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
早期机械化茶厂推行的步履维艰,原因或在于“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式茶园凤毛麟角”(20)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即与集中化茶厂相匹配的“社会技术”条件。当时中国的茶叶种植模式是以家庭、寺观为基础的分散化种植,如波尔(S. Ball)、福琼(R. Fortune)等人笔下的19世纪红茶主产地武夷山:“红茶一般种植在山的较矮处,或者村民家的院子;”(图2)山中分布“不下999座寺观”,“佛教和道教的僧侣在庙宇周围种植茶树,每年自己采茶”;农民和僧侣的茶分散加工为毛茶后,送至崇安县城、星村镇、河口镇的茶行加工包装后销往国外。”(21)Robert Fortune,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third edition, v2(London: John Murray, 1853), pp.183-186; Samuel Ball, 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8), pp.41-42.与集中化茶厂相匹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于同期印度茶种植园。19世纪30年代起在印度开辟植茶业的英国殖民者,最初将从中国收集的茶树、茶种和茶工送至阿萨姆(Assam)、坎格拉(Kangra)等地,“效仿中国式家庭种植模式,划分为较小的种植片区;”(22)Sarah Besky,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 pp.51-55.但英国种植园主很快认识到中国式种植模式效率低下,工人水平及茶青质量难以把控。在19世纪70年代茶叶机械发明和普及、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制度便利(23)与土地零散分布于佃农的坎格拉不同,大吉岭、阿萨姆皆拥有宽松的土地政策,租约所赋予的土地权可在个体间流转,这使早期开拓者得以将租约土地出售或转让给新的“主人”,为大规模种植园创造了条件。Sarah Besky,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 pp.54-55.、土著转化为稳定劳动力等因素作用下,阿萨姆、大吉岭(Darjeeling)等植茶区诞生了一种机械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高度集中的现代生产模式——种植园(plantation)(图3)。如阿萨姆公司茶园7710英亩,一般种植园面积也在数百英亩(24)吴觉农:《印度锡兰之茶业(续)》,《国际贸易导报》1937年2月第9卷第2期,第83页。;同时,英国人从印度焦达讷格布尔高原、尼泊尔东部山区等地招募土著,永久性定居于新开辟的植茶区,使种植园获得可持续的廉价劳动力(25)Jayeeta Sharma, 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9-40.。1916年,印度的4486个茶园共雇佣工人634339人,临时工92487人(26)耐庵:《印度之茶业》,《农商公报》1920年6月第71期。。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和劳动力的规模化是种植园这一现代茶叶“技术”的社会性特征。
集中化茶厂便是种植园技术诸多社会前提下的物质产物。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印度的大型萎凋楼(chung):采用半开敞式铸铁框架、锡皮四坡屋顶;室内中央走廊两侧皆为竹制萎凋架,架子用粗麻布分隔为数层,每层间距约3英尺,足够让小孩子爬进去摊放青叶即可;架子最多可有十层之多,建筑高度十米以上(27)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395.。下图可见(图4),黑色皮肤的印度土著劳工背着巨大的竹背篓,源源不断地将新鲜采摘的茶青送到萎凋楼中。若没有种植园中高效的加工机械、大规模标准化的茶青供给和稳定的劳动力,是无法支撑集中化茶厂的生产规模的。
图2RobertFortune书中记载的19世纪中国家庭式制茶场景(28)图片来源:Robert Fortune,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third edition, v2, p.1.
图319世纪末英属印度、锡兰的现代茶叶种植园景观(29)图片来源: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p.424.
图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印度的大型萎凋楼(30)图片来源: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p.395.
对比同期中国机械化茶厂,民间资本虽强调物质性的机械引进,却无从克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上的社会性困境。就茶青收购而言,碎片化的家庭种植模式使集中化茶厂很难获得茶青品质和数量的稳定;且大多数融入国外资本的集中化茶厂被禁止深入到内陆产茶区建设,更加大了收购难度(31)一位英国商人评述1899年福州茶叶改良公司倒闭时提到,“如果该公司处在Pan Yong、Soomoo、Saryune等地(皆位于闽北产茶区),或许会获得成功”。H. Baker给I.C, Bois的信件,福州,1899年1月26日。存于英国John Swire and Sons, Ltd.档案馆。。当然,机械化茶厂对传统家庭构成的潜在市场竞争亦是不可忽略的原因。而在劳动力问题上,机械化茶厂需要大规模劳动力,但茶工多系“客氓”,“熟采多,彼此分雇各厂;若谷贵茶亏,则相聚剽敚”(3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04-305页。,给地方治安带来极大困扰,是早期机械化茶厂与地方社会发生矛盾、进而遭到农民抵制的又一动因。
归结早期机械化茶厂的建设与茶业现代化转型的失败,除了近代战争时期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抵制情绪,机械化茶厂所暗示的规模化生产与以小农家庭为中心的分散化生产的社会性矛盾是更深层的原因——中国农业的分散化模式始终能在不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前提下应对不断增长的贸易(33)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 p.173.(可参照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3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致使中国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外来的现代化改革一直未能在农村发展壮大。早期机械化茶厂的失败便是对这一普遍现象的微观注解。
二、从茶农到茶工:近现代 国营茶厂的社会重构
祁门茶业改良场是近现代中国最成功的一个效仿印度种植园体系建造的国营茶厂。1915年,农商总长周自齐提出建设“全国范围的茶叶示范种植园体系”,后在祁门开设第一家示范茶园(35)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p.148.,初名“安徽模范茶厂”,由曾赴印锡考察的陆溁担任首任厂长(36)孙文郁、刘润涛、王福畴等:《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1932年更名为“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1934年成立“祁门茶业改良场”(37)资料来源:安徽祁红博物馆。。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茶业现代化从“官督商办”的民间行动,转化为自上而下的制度行为,促进了“社会技术”的现代转换——通过转变茶叶生产组织模式,将茶农收编至集中化茶厂工作,使建筑空间参与到从“茶农”至“茶工”的社会身份重构之中。集中化茶厂由此成为茶业现代化改造的催化剂和见证者。
祁门茶业改良场的现代化不再仅依赖制茶机械的引进,也在茶厂空间布局、组织方式等方面效仿印锡种植园体系进行改良。根据陆溁回忆:“部长嘱即拟办预算,我即准备祁门之行……就南河交通之平里村西所查勘的高低山场全部荒芜熟地,向章祠租用……购小箱罐用的锌片,造揉茶机用的零件,预备金山自造装茶的小箱、揉茶木机。抵祁门平里……当即垦荒造路,建设茶场,并租定茶号空房,准备明春收茶农鲜叶,直接制造精茶输出。”(38)资料来源:安徽祁红博物馆。虽然祁门只在160亩的范围内种植了大约60000株茶树,规模并不算大,但其中涉及租用种植土地、配备制茶机械和茶厂、建立茶青供应网等现代化种植体系的关键因素,是早期机械化茶厂到现代集中化茶厂的系统性转变标志。
这一转变在祁门茶厂的空间布局中得到明确表现,将茶叶加工工序科学整合于茶厂中。在印度:“茶厂一般为两三层,阁楼用作萎凋,一层为揉捻、发酵、烘干和包装车间。”(39)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pp.280-281.1936年祁门建设的初制工厂和精制工厂采取了类似形制:“初制工厂为西式二层楼房,楼上是萎凋室,右面装暖室……楼下分成三部分,一为揉捻室,安装双动式揉捻机、解块机各一部。二为烘茶室,装备干燥机,将茶叶烘干……干燥机旁装有干茶分筛机,以分别茶叶的等级。三为发酵室,厂外有水塔,用自来水管将水接到室内以调节湿度,开关窗户和放黑布窗帘以调整室内温度。精制工厂最下一层是筛、扇的场地,第二层是拣场。烘房为单独建筑,可容烘笼三百多个。”(40)张小坡:《近代安徽茶叶栽培加工技术的改良及其成效》,《中国农史》2011年第2期。
茶厂空间布局的专门化,成为工人分工细化及身份重构的基石。祁门茶厂的技术现代化由我国第一批茶叶技术专家引领,包括陆溁、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人都曾在此工作(41)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而茶农则转变为职责分门别类的茶工——从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到萎凋、揉捻、发酵、烘干、包装等不同车间的专门化工人。每个车间相对独立,茶工不再是家庭生产中需独自承担以上所有工序的茶农。此外,集中化茶厂有着严明的组织记录,如1934~1949年担任场长的胡浩川,以“个人不离场,工厂不空废,茶园不生芜”为准则,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从未停止茶叶生产(42)资料来源:安徽祁红博物馆。。严格的纪律性,将过去只在丰年制茶、茶亏则“相聚剽敚”(4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304-305页。的游民式茶工转化为有组织的现代化茶工。(图5)
图51934~1949年的祁门茶厂(前景为担任场长的胡浩川与茶厂员工合影)(44)图片来源:安徽祁红博物馆。
祁门茶业改良场还通过茶叶运销合作、技术传授、人才培养、广告宣传等方式,将现代技术理念推广至茶农群体。从1933年在平里首办茶叶运销合作社,至1940年发展到71个茶叶产销合作社,占全县茶箱总数21.9%;编印《祁红毛茶怎样做法》、《制茶工厂怎样管理》等技术说明图册发放给茶农;1935年和1936年举办两次春季合作制茶讲习会,培训学员43人、技工61人(45)资料来源:安徽祁红博物馆。。1937 年的《茶报》创刊号上刊登了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广告:“祁门红茶是全世界最好的红茶,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出品是红茶之王,香气浓厚,滋味纯正,机械制造,清洁卫生。”(46)汪德滋:《祁门茶研所百年史拾遗》,《茶业通报》2015年第3期。通过宣传,祁门红茶在20世纪上半叶茶叶市场中的优异表现,被与其现代生产技术联系起来。茶农群体与集中化茶厂的关系也从早期的竞争与抵制,转变为憧憬与模仿。这进一步推动了集中化茶厂及其技术理念在农村社区的融入。
祁门茶业改良场采取的专业细分的现代化生产技术,使人想起人类学家艾约博(G. Eyferth)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概念——将技术从手工艺出身的茶农手中“收缴”至“以国家名义说话和行动的专家们的手中”(47)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页。;更准确地说,茶业现代化作为一种“技术改造”,通过集中化茶厂的社会介入将现代生产技术传播至农民群体。将原先分散化、很难管理的茶农通过政治或市场力量收编至集中化茶厂中,推动了传统茶农向有组织纪律、职业化的茶工的身份转换,为乡村社会重构及制茶技术的现代化转型铺平了道路。这条从物质性到社会性的技术转型之路,在政治介入更为强势的人民公社时代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三、从菁楼到厂宅:人民公社集体茶厂的主体重塑
以下通过一个村级茶叶公社的田野调查案例,展现现代化茶叶技术如何蔓延至乡村家庭和个体层面。作为技术物质性载体的集中化茶厂,在人民公社期间茶工的亲身“测度”和“惯习”的作用下,从社会组织层面的身份重构深入至个体认知层面的主体重塑;而从人民公社的菁楼对当代分散化厂宅的空间形制影响,则印证了技术“惯习”的社会性维持其物质性存在的韧度。
桐木村所在的武夷山市(旧名崇安县)为18~19世纪主要红茶产区,也是印度制茶技术的源头(48)在Robert Fortune、Samuel Ball等人来中国寻求茶叶技术的书籍中,皆亲自来到武夷山这个公认的最佳红茶产区,并提到19世纪中叶该地区普遍使用的萎凋楼。。20世纪中叶,随着吴觉农、张天福等一批茶叶技术专家在武夷山创立“崇安茶叶研究所”(49)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续)》,《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现代生产理念从祁门、宁州等改革前沿传播至此。70年代人民公社期间,武夷山星村公社的茶师陈德华发明了一种将现代生产方式与当地传统木制萎凋楼相结合的集中式茶厂——“菁楼”(50)根据笔者对桐木村老茶人梁骏德的访谈,2016年10月,于桐木村。。菁楼以地方性知识整合集中化茶厂的生产模式。对比祁门茶厂(其楼上萎凋和楼下烘茶都需电能制热),菁楼利用在底层燃烧松木的当地传统做法,形成一座高效利用热能、为加温萎凋和熏焙提供适宜温度和烟气条件的“烤箱”式建筑:在地下砖砌燃烧室燃烧松木时,热气透过“U”字型坑道进入一层温度最高的熏焙室;二层调温降温;三层和夹层温度适宜,用作青叶萎凋。一层前方加构一座遮雨棚,设置揉茶机等辅助机械。菁楼生产单元纵向组织,每个单元面宽4-5米、进深8-10米;单元可任意增减,以满足人民公社时期全村人在一栋菁楼中共同作业的需求。如1979年的庙湾集体菁楼,共有十个生产单元,建筑长度近60米,在乡村农宅的尺度反衬下如同一座乡村工业的“圣殿”(51)黄华青:《武夷山桐木村当代茶村厂宅的空间与社会变迁》,清华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4-145页。。(图6-7)
尽管菁楼具有木结构建筑的传统特征——当地人也常将它作为桐木村制茶历史的象征——但就建造时间和生产理念而言,菁楼无疑是一座贯彻了现代生产技术的集中化茶厂。除了剖面上的热源控制方法以及与制茶机械的配合运作,其“社会技术”亦体现于茶农的分工和协同作业所需的职业化精神。当地人回忆,人民公社时期每个家庭至少派一名男性劳动力在菁楼中参与制茶以换取工分。茶工中等级最高的是“青师傅”,即经验丰富的茶师,其工作是“看青”——根据茶青含水量、制茶温度湿度、发酵程度等掌控茶叶加工各道工序的衔接时机。其他年轻男性则分布在萎凋、揉茶、熏焙、发酵各个步骤中充当学徒;学徒必须充分遵守“青师傅”的调配安排,为了提高效率,在各层走廊地板上还设置了上下传递茶青的洞口,加快各楼层不同工序的衔接。女人和小孩主要负责前期采茶和后期分拣等工作,成为这个现代茶叶技术体系的一份子。
在人民公社集体茶厂中劳作的经验,让茶农通过身体力行的空间体验,将现代化生产技术“在体化”(54)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第49页。地储存于四肢和感官之中。通过笔者在对多名老茶人的访谈不难发现,菁楼中艰苦、纪律严明的工作在其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整栋菁楼充斥着木材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炙热烟雾,“年轻时在菁楼没日没夜地焙茶,眼睛被烟熏得通红,每天回去感觉要瞎了一样,母亲用两片海带放在我眼睛上,第二天才能看得见,继续工作”;“脚下的竹编地板呀呀作响,好像随时会断裂”;集体菁楼中的纪律不容侵犯,学徒“稍有偷懒就会被青师傅狠狠地打”。(55)根据笔者对曾在集体菁楼工作的老茶农朱有福、胡必胜、胡和平等人的访谈,2016年9月,于桐木村。
在菁楼中的身体“测度”将这种“社会技术”塑造为桐木茶农生产的“惯习”,影响着人民公社至今的生产及空间实践。首先是菁楼这种空间形式及其伴随的组织理念的延续。包产到户后,集体菁楼大多被拆除卖掉,但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部分茶农又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技术原理在个体家庭重建新的菁楼。然而,哪怕是家庭中只有一到两个单元的菁楼,相对于包产到户后单个家庭的生产规模来说依然是不理性的(56)根据笔者调查,一间面积50平米的菁楼,一次可萎凋上千斤茶青(烘干后可制成约两百斤毛茶);但桐木家庭户均年产量仅七、八百斤毛茶,每天采摘的茶青数量根本不足以充分利用菁楼。。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生产空间,是通过类似于人民公社前期的互助协作模式来弥补的。少数建造个体菁楼的茶农,会将菁楼借给亲戚、朋友使用,获取金钱、物品或人情上的偿付。茶农这样做,是由于八、九十年代极不景气的茶叶生意,从而选择继续集中化模式来节约成本。
“惯习”的另一个表现,是将菁楼代表的制茶技术视为当地“传统”(57)在当地语境,“传统”指向的是明清时期的手工艺传统,而非人民公社时期的传统;他们也普遍将菁楼视为一种源于明清时期的传统构筑物。工艺,进而成为当代制茶技术的重要载体。2005年以来,随着金骏眉带动桐木茶叶市场的繁荣,个体经济取代家庭互助成为更主导的制茶模式,但依然存在不少富起来的茶农,在自己砖混结构的新厂宅旁加建一间木构菁楼。他们常骄傲地说,只有在菁楼中通过松木烟熏制作的茶才是“传统”正山小种。因此,在家家户户都已具备机械化条件的当代桐木村,依然广泛存在机械化和手工化并存现象(图8)。他们同时售卖机械工艺制作的“赤甘”和“传统”工艺制作的“正山小种”这两种原料相同、口味微差的茶叶——不仅出于市场需求,因为“传统”茶的市场接受度及价格经常还不如前者高。当地人坚持的这种“传统”,不妨说是在70年代人民公社及80年代乡镇企业的集体茶厂中工作形成的“惯习”——菁楼制作已在茶农社会共识中成为更高茶叶品质、更正统茶叶品味的象征。将这种现代茶厂的“惯习”与长期形成的“传统”区分开来是必要的:哪怕在人民公社前,桐木村普遍的茶叶烘焙方式还和武夷山其他地区一样采用炭焙,但炭焙产量低、速度慢;正是在人民公社的规模化产量要求下,地处深山密林、周边遍布伐木场的桐木村才全面转向使用松木来完成红茶的烘干工序。
图8桐木村胡必忠宅,木构菁楼和现代茶厂并置(58)图片为作者摄于田野调查期间。
当代桐木包装在“传统”木构建筑之下的制茶技术演变,可视为我国茶业现代化进程的生动注解。茶业现代化在村级层面的推进,与人民公社集中化茶厂的营建及使用有着密切关联。首先是“物质技术”的传播,菁楼将机械化与松木烟熏结合的茶叶加工技术,在80年代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工作经验一起“下放”至每个茶农家庭——这种“下放”不仅包括字面意义上茶叶机械设备的分包至家庭,还指向比喻意义上这种制茶技术观念之普及。更重要的是菁楼作为“社会技术”的传播,其中包括艾博约所说的“家庭作为经济主体”的现代生产理念(59)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第187页。:首当其冲的是集体茶厂的领头人,如青师傅、销售经理等获得的管理经验,帮助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很快成为当地茶叶技术拓展、市场化经营的开拓者;而广大普通茶农,也在菁楼艰苦的劳作中成为训练有素的茶工,如今他们在个体茶厂中熟练地在手工和机械生产之间自由切换——若没有集中化茶厂中获取的规模化、标准化和职业化经验,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的茶农家庭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到当代茶叶市场的竞争和建构之中。
小结
最后试图回答篇首提出的关于茶业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在将茶厂作为“技术”的研究语境下,茶业现代转型进程体现于技术物质性与社会性的互动、同步和校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机械化茶厂所暗示的以生产资料集中、劳动力集中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以分散化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组织理念相矛盾,导致技术的社会性滞后于物质性发展,故而作为物质性表征的机械化茶厂大多胎死腹中;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营茶厂及人民公社的集中化茶厂,则通过政治或市场力量将茶农收编至茶厂中成为有组织纪律的茶工,使茶农在物质空间中的技术实践影响“惯习”的重塑,进而将现代化茶叶技术理念推广至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完成了茶叶技术的现代化转型;这种技术“惯习”亦贯穿至人民公社解体后的今天,依然塑造着茶农效仿集体菁楼模式重建个体菁楼的空间实践。可见,技术的社会性虽在现代化进程初期滞后于物质性的发展,但一旦“社会技术”渗透发展成熟,它在政治、社会、经济层面所拥有的韧度,也许远强于以茶厂形式为载体的物质性。
放在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集体时期兴建集中化设施的目的“不仅是提升农业产量,也是为了加强对农村的政治控制。”(60)Dwight Perkins and Yusuf Shahi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3.茶叶技术现代化转型通过其社会介入,亦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形成一定同构。当代茶业广泛采取的“龙头企业+农户”(61)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2009年第04期。或“中间商+小农”(62)武广汉:《“中间商+农民”模式与农民的半无产化》,《开放时代》2012年第03期。的产业化模式,以及随之导致的乡村社会阶层分化(63)Qian Forrest Zhang,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China: Dynamics of Accumul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15, 15(3), pp.338-365. Huang Huaq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middle farmers: accumul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tea consumption revolution in China,”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Revue canadienne d'e' tudes du de' veloppement 40, 2019(1), pp.48-63.,便是以人民公社时期技术变革所完成的社会重构为基础的。在当下不断变化的生产技术背景之下,技术所承载的社会结构无疑也酝酿着新的冲突和调整。
这些社会事实建立了当代乡村建设中建筑空间反作用于社会的关键前提。作为“技术”的集中化茶厂,透过身体“测度”和“惯习”作用,成为沟通技术的物质性与社会性互动关联的桥梁。建筑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其介入乃至影响社会变迁的能动性是本文力图揭示的。在中国农业技术的物质和社会根基进入新一轮调整的21世纪,对作为“技术”的农业建筑的反思和研究,也可能为乡村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