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领袖文明观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
2019-10-09谢茂松
【摘要】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领袖的文明观,拥有的共通的底线共识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共同存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一整套“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以及“以大事小”的思想,这是对于其他文明的真正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如此才能“欣赏所有文明之美”,进而“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大胸襟、大心量,也应该是大国领袖在底線共识之上更为高明而博厚的文明观。
【关键词】大国领袖 文明观 理一分殊 君子成人之美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国领袖的文明观应该具有哪些共识、具有哪些普遍的特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大国及其领袖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文明观”这一问题兴起的历史脉络。
世界大国及其领袖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明观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1987年推出的《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一书的前言中说明“本书包含了我与苏联、美国和中国这三个重要的世界大国交往的回忆和评价”,全书“分三大部分来描述我个人对俄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印象,特别是我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亲身感受”。他在1989年的中文版序言中解释全书为何是谈三个国家的原因,首先,就中国来说,他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次,施密特认为这三个大国是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在其辞典中并不意味着霸权,而是中性的,是基于其战略判断:在20世纪快要结束时,“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还另有许多对世界具有伟大意义的国家,像“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但它们“对于将要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61亿人来说”,“所起的作用仍将是相当有限的”,相反,“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府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可避免的几乎涉及整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作为德国这一欧洲最核心国家的总理,施密特深刻地把握了“世界大国”超出其他国家对于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影响力,同时把握了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冷战时期是以意识形态来区分美、苏两大阵营,同时也派生出“三个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以此来取代之前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理论。他认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取代意识形态,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具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冲突”,还有是美国与东正教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明观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文化区别、文明认同离不开对于敌人的区别与制造,文化区别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循此思路,亨廷顿更是在“9·11”事件之后写了一本书来专门讨论“我们是谁”,即“谁是美国人”,而“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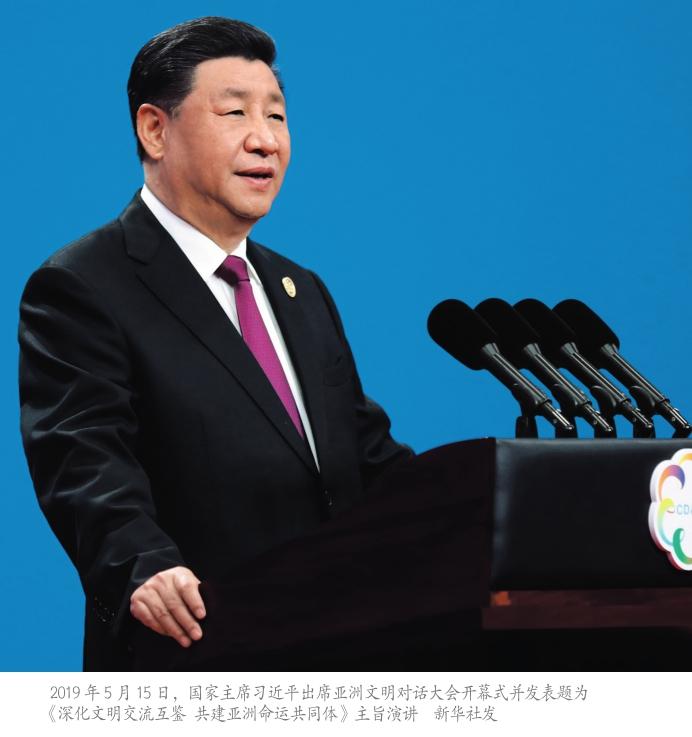
“文明冲突”一时成为冷战后美国一些人的新战略思维,甚至是总体战略思维。“文明冲突论”就像亨廷顿之后另一位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样,本身可能会带来一种自我实现的后果。就是说,当你这么来设定时,原来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就很大可能照此自我实现了,这就是危险的观念之危险性所在。当全球化在今天出现问题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行单边主义,在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尤其是对中国加征史无前例的关税,并从打贸易战蔓延到打科技战、意识形态战,甚至发展到所谓文明之战: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29日声称,美国正在“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美国“第一次遇到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虽然“文明冲突论”在西方盛极一时,但也不乏批评该理论的西方学者。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尼尔·弗格森在其《文明》一书中批评“文明冲突”这一模型“作为预言,它没有应验,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此”。就亨廷顿所声称的“较之同一文明内的冲突,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更频繁,更持久也更猛烈”,弗格森认为事实不是这样,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增加,持续的时间也不比其他类型的冲突更久。过去20多年发生的战争多数是内战,而只有少数的冲突和亨廷顿的模型相符,“在无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内的种族冲突更为常见”。尼尔·弗格森的结论是,各大文明之间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而是“文明内部分类的趋势恰恰有可能导致亨廷顿所指的文明面临崩解”,所以弗格森认为“文明的冲突”不如称为“文明的崩解”。今天美国、欧洲内部流行的民粹主义倒是证明了这点,同时也提供了对于亨廷顿观点的反证。
“文明冲突论”出现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亨廷顿所认为的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力量在上升,而西方文明与所有文明一样,都会经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过程。今天的西方正在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如此则包括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及其普世价值观形成的挑战,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是维护西方文明。作为政治学学者的亨廷顿与作为政治家的施密特同样强调大国领导者的重要作用。
世界史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国往往以其文明优越感而热衷于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改造、取代。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一书对于美国及其领导人的评价是“华盛顿不管由谁执政,总喜欢单独行动”,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是以理想主义、罗曼蒂克以及“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伟大”为特征的,“如果其他国家不能适应美国人的理想以及不能适应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方法,那么其他国家的处境就会更为糟糕”。面对此种态度,施密特指出,美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两种对立的结果:美国要么采用军事手段来给世界建立一个较好的秩序,又发明了“保护的责任”的玩意儿,但人们从来弄不清这背后是否隐藏着美国自身的强权利益,这一口号已成为西方很多政治人物维护其正在消失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要么另一种结果则是美国决定对其他国家不予理睬,实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而孤立主义是一种非白即黑的片面道德观,把所有国家分成两类:站在美国这边的是好人,不站在美国这边的是坏人。施密特自述,由于他本人明确反对西方国家打着人权、打着“保护的责任”而对别的国家实行干预反而带来灾难性结果,而极可能在欧洲政治中属于少数派。
中国领袖“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的思想
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三点:“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作为非西方文明国家力量上升标志的中国的崛起,对于其他大国及其领袖文明观的塑造有着特殊的意义。施密特说中国作为富有深厚文明传统的大国快速实现了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舞台。面对众多的全球性问题,施密特提示西方“必须习惯于只有在中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些议题”。当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时,作为世界大国领袖的中国领导人,又会向全世界展现怎样的文明观呢?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认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三点:“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系统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而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针对美国、西方盛行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西方文明优越论”提出的。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具有深厚的中华文明根源,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的思想。《周易》是中华文明原典的《五经》之首,《周易·系辞下》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明是“同归”“一致”之理,即文明之为人类文明的共性、普遍性;而“殊途”“百虑”则是“分殊”,即每一种文明的特殊性或特色所在。从二者关系来看,文明的普遍性是要在文明的特殊性中存在的,文明的特殊性中包含了文明的普遍性,二者不是割裂的。《周易》的核心要义是《周易·系辞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的阴阳之道是说阴、阳二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阴、阳分别意味着各自的差异性;另一方面,阴、阳又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体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即阴、阳又有和谐、合同的一面。必须将阴、阳的“别异”与“合同”这两面合而观之,才是对于阴、阳的全面、完整把握。我们看待自己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也是一种阴、阳的辩证关系,这是当代中国文明观背后的中国哲学思维。
每一种文明都具有“分殊”的独特性、差异性与多样性。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作为价值、宗教、习俗和体制的历史总和,是各自不同的历史长久累积的结果。正是因为每一种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性,所以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世间万物的差异性是本然的状态,承认文明的差异性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文明冲突论者、文明优越论者则将文明的差异性视为负面,必欲以各种手段去之而后快,习近平主席则正面肯定文明差异的意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每一种文明都要有对于自己文化、文明的自信;另一方面,“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需要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批评“人种优越论”“文明優越论”等论调与做法:“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习近平主席强调需要有对其他文明的包容,这也是基于每种文明的独特性,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内在动力。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中国领袖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系统、完整的文明观,是对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克服
竞争绝不是西方思维所认为的敌我式的斗争,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竞争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带动、共同发展的结果。唯如此,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
重视文明的独特性,不等于文明的自我封闭,而恰恰因为“独特”本身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与“共通”相对才存在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体。所以一个文明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还需要与其他文明对话,在对话、学习、交流中相互借鉴,不断扩展、丰富、充盈各自文明的主体性。但在文明互鉴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这是针对有的大国一直以来热衷于对他国强制性地输出价值、制度与文明的霸道现象。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所以“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不回避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竞争,但竞争绝不是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西方思维所认为的敌我式的斗争,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竞争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带动、共同发展的结果。唯如此,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而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也需要有生态系统,这是过往的大国领导人尤其是西方大国领导人所忽视的。
只有具备良好的生态系统才能保证创新,所以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还强调文明的时代创新性。文明要永续发展,就要返本开新,激活文明的源头活水,如《易传》所说“与时偕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领袖的文明观,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共同存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文明观的“理一”,即各个大国领袖文明观中普遍的特质。除了“理一”,作为大国领袖的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观,这是“分殊”。“平等”在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中被排在了首位,而“平等”正是代表社会主义的最为核心的文化价值。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是对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克服,也是对于六十多年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深厚的“文明”的底色。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外溢效应”,就在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开始,习近平主席对于文明观作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论述,这是其他大国领袖中所不多见的。其他大国领袖对于文明观的论述相对是零星的、片段的,更多的是智库的战略家在做。两相比较,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文明意识上的自觉,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文明的复兴,是要在更高的层面回到“历史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除了具有各个大国领袖普遍的共识性的特质之外,中国领袖的文明观还有更高远的精神品质
作为大国文明,中国文明传统尤其强调“以大事小”,强调对于小国、对于其他文明谦逊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中国领袖的文明观除了具有各个大国领袖普遍的共识性的特质之外,还有超出于这些相对属于底线共识的特质之上的更高远的精神品质。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其文明传统尤其强调“以大事小”,强调对于小国、对于其他文明谦逊的态度。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国家领袖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谈他关于各种文明的感受:“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习近平主席列举的古玛雅文明已消亡,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所在的国家不是大国,他完全是抱着谦虚的态度,要去深入了解这些不同的文明的真谛。这与过往西方的文明优越论者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截然相反。
“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明观,是大国领袖在底线共识之上更为高明而博厚的文明观
“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心包含了对于其他文明的欣赏,所以是“消极中的积极”。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己独立自主发展好了,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但却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改造对方,所以“积极中有消极”。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上强调各文明之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出自内在的平等心。唯有这样的真正平等心,才能“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生态系统的建立,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唯有这样的平等心,才能有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所说的“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进而是他在大会上提出的“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这一真诚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中国领袖文明观中对于其他文明的“君子成人之美”之大胸襟、大心量,这正是大国之为大之所在,“大”是心量、器量之大。这也就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说“志如其量,量如其识”,有志于至善之志,则心量就大,心量有多大则见识就有多远大。这也是史学家钱穆所说的政治家的风度,风之所及,所过皆化,影响于国内、国际政治。
中国领袖如此之心量与风度,根本上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大心量。“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题中应有之义,平等心包含了对于其他文明的欣赏,所以是“消极中的积极”。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己独立自主发展好了,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但却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改造对方,而是完全由对方独立做主,所以“积极中有消极”。
“厚德载物”的思维与西方中世纪的暴力改变信仰的原则截然相反,也与西方近代的均势外交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施密特反省“以暴力来改变信仰的原则是在欧洲产生的”,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产生了。均势论则强调通过战争、斗争而达到各国势力的均衡,西方当代一流的战略家基辛格及其密友施密特都秉持均势外交理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观中普世主义本身的反省,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亨廷顿批评西方普世主义对于各方的危险性:“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同样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接着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我们看到“文明冲突论”最后的落脚点竟然是强调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不为大家熟知的面向。可以说,亨廷顿是将自己的“文明冲突论”最后推向了其反面,倒是与中国强调的每一种文明的独特性走到了一起,这或许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同归而殊途”?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③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5月15日。
④[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大国和它的领导者》,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
⑥[英]尼尔·弗格森著、曾贤明等译:《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⑦[美]吉米·卡特著、裘克安等译:《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⑧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⑨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