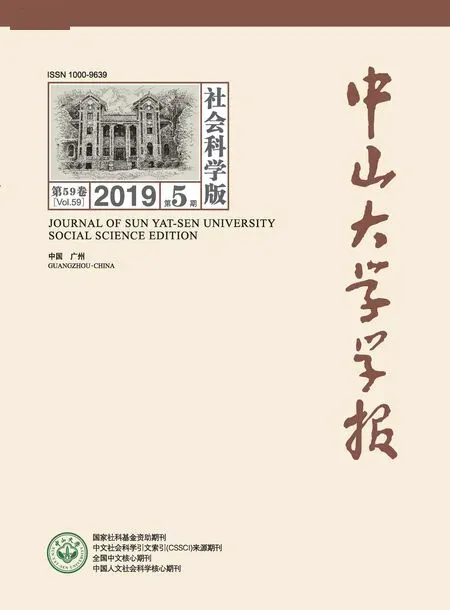9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
2019-09-21朱丽双
朱 丽 双
一、前 言
佛教文献中有一些与佛法最后灭尽相关的作品。其故事梗概说:未来某时,一方面由于僧人不守戒法,入世营利;另一方面由于世人不再信奉正法,不喜佛僧,致使佛教逐渐衰落。当时出现三位不信正法的恶王,攻占了广大国土。后来他们带领大军攻打天竺俱闪弥国(Skt.Kauāmbī)(1)汉译又作憍赏弥、拘舍弥、拘睒弥、具史罗,是公元前7—4世纪印度十六国之一跋蹉国(Vatsa)的都城。本文汉译据P.2139法成译《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朱丽双:《〈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645页);关于此城情况,参见刘屹:《印度“Kauāmbī”法灭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89—190页)。,但被俱闪弥国王全部消灭。尔后,为消弥杀戮众兵之罪,国王召请世上所有僧众至俱闪弥国,欲忏悔己罪并为僧众举行供养。但僧众聚集俱闪弥国后,内部发生纷争,自相残杀,全部死亡,佛法自此灭尽。
佛教于俱闪弥国最后灭尽的故事很早即已存在。据研究,其最早编成的时间不晚于公元2世纪,最初编纂之地可能在西北印度或其周边地区(2)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Cal.: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1.p.3; Idem, “A Prophecy of the Death of the Dharma,” in Donald S.Lopez, Jr.ed., Buddhism in Practice: Abridge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9.。此故事保存在各种语言的佛经中,据前贤梳理,主要有以下这些(3)以下有关各种佛经的情况及其相互关系,见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rans.Sara Webb-Boin, Louvain: Peeters Press, 1988, pp.201-202;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145-204; 刘屹:《印度“Kauāmbī”法灭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第189—204页。刘屹在其文《憍赏弥国法灭故事在于阗和吐蕃的传播(文献篇)》中将有关于阗的三种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Li yul lung bstan pa)》《牛角山授记》(Ri glang ru lung bstan pa)和《无垢光请问经》(Dri ma med pa’i ’od kyis zhus pa)亦列入有关于阗法灭的基本文献,此不取。其文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8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25—451页。:
(一)汉语本
(1)《佛使比丘迦旃延说法没尽偈百二十章》,T2029,失译人名,西晋(265—316)时译出;
(2)《阿育王传》(Aoka-avadāna),T2042,此经主要部分据称由安息僧安法钦306年译出,但包含俱闪弥故事的最后两章被认为5世纪初时才译出(4)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p.201.那体慧书作5世纪末,似误。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151.;
(3)《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T2028,失译人名,南朝刘宋(420—479)时译出;
(4)《杂阿含经》(Sayukta-āgama),T99,求那跋陀罗(Guabhadra)436—443年译出;
(5)《摩诃摩耶经》(Mahāmāyā-sūtra),T383,昙景南朝萧齐(479—502)时译出;
(6)《月藏经》(Candragarbha-sūtra),乌伐那(diyana)僧那连提耶舍(Narendrayaas)566年译出,586年编入《大方等大集经》(Mahāsanipāta-sūtra,T397)(5)David Wellington Chappell, “Early Forebodings of the Death of Buddhism”, p.145; 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171-172.《开元释教录》载《月藏经》译出于北齐天统二年(566)。见[法]烈维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Quelques documents sur le bouddhisme indien dans l’Asie centrale),《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卷第9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68页。;
(7)《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Mahāvibhsā),T1545,玄奘656—659年译出。
(二)藏语本
(1)《百业经》(Lasbrgyathampa),收于《甘珠尔》经部。此经著录于吐蕃时期编纂的《登噶目录》(lDan/Lhandkarma),故其最晚译出时间当不晚于824年(6)那体慧据早年拉露(M.Lalou)的观点,认为《登噶目录》编成于墀松德赞时期,从而将《百业经》译出的时间定为不晩于8世纪后半。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151.;
(2)《月藏经》,无全本,仅存其中《月藏请问经中佛说入灭后教法住灭授记经》(Zlabasnyingpos’zhuspa’imdolassangsrgyasmyanganlas’dasnasbstanpagnaspadang’jigpalungbstanpa’imdo),收于《甘珠尔》经部,另敦煌藏文写本IOL Tib J 601.1亦是此经内容。据《布顿佛教史》(Bustonchos’byung),《月藏经》的译者是释迦斡(Shākya ’od)。此人于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stan,742-c.800)时期翻译佛经,活动年代约在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期,精通于阗语,翻译过《于阗国授记》《牛角山授记》等有关于阗的作品(7)朱丽双:《〈于阗国授记〉的成立年代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117页。。如此看来,藏语本《月藏经》很可能亦译自于阗语。虽然迄今人们并未发现于阗语本《月藏经》(8)和田发现了一件梵语《月藏分诸阿修罗诣佛所品》(H 143, SA.10)。A.F.Rudolf Hoernle ed., Manu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ut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16, pp.103-108;[日]广中智之:《汉唐于阗佛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2—123页。,但敦煌本《月藏经》和一件《于阗阿罗汉授记》(Liyulgyidgrabcompaslungbstanpa,IOL Tib J 601.2)抄写在一起,说明此经和于阗有所关联。确实,早年烈维(Sylvain Lévi)曾指出,《月藏经》叙事以于阗为中心,很可能创作于于阗或其附近地区(9)[法]烈维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第209页。。关于藏译《月藏经》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及其英译,见那体慧书第九章(10)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228-277.关于英藏藏文写本IOL Tib J 601.1的翻译,又见其文 “A Prophecy of the Death of the Dharma,” pp.179-186。。
(3)《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dGrabcompadge’dun’phelgyislungbtsanpa,以下简称《僧伽伐弹那》),收于《丹珠尔》书翰部(spring yig),释迦斡811年前后译出,详后。
(4)《于阗阿罗汉授记》(以下简称《阿罗汉》),收于《丹珠尔》书翰部,但《丹珠尔》本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作为《于阗国授记》的一部分编入《于阗国授记》内容之前。后来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发现了《阿罗汉》的三个抄本IOL Tib J 597、598、601.2,又发现P.2139法成译《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是《阿罗汉》的汉译本,才认识到《阿罗汉》曾独立存在,它被编入《于阗国授记》是后期藏文大藏经编纂者的失误所致(11)朱丽双:《〈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第605—676页。。
(5)P.t.960《于阗教法史》(Liyulchoskyilorgyus)。这部文献的内容并非前后连贯,而似有关于阗的佛教文献集成。虽其尾题记由大德论道沙门(Mo rgu bde shIl)译自佛经《日藏经》(Suryagarbha-sūtra)《月藏经》和《无垢光请问经》,但察其内容与现存《日藏经》《无垢光请问经》并无密切对应关系。某些段落反而与《于阗国授记》《牛角山授记》《阿罗汉》《僧伽伐弹那》较为接近(12)参见朱丽双:《〈于阗教法史〉译注》,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14—417页。。
(三)于阗语本
目前所知只有一种,即《赞巴斯塔书》(TheBookofZambsta)。写本20世纪初发现于和田,它不是首尾完整、内容连贯的著作或译作,而类似佛典集成。原书共298叶,包括5种抄本,其中年代最早的抄本被判断为5、6世纪,故推测其最初编撰的时间可能在5世纪,代表着于阗人首次开始用于阗语撰述佛教文献。有关法灭故事见第24章,情节和藏语本《月藏经》较为接近(13)R.E.Emmerick, The Book of Zambast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dem, A Guide to the Liteture of Khota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2, pp.40-41.文献年代据Mauro Maggi, “The manuscript T III S 16: Its Importance for the History of Khotanese Literature,” in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Reimer Verlag, 2004, pp.186-187。。
以上这些佛经有的专述法灭故事,有的仅在叙事过程中有所涉及。不同版本的故事在情节和细节方面皆有差别,为方便起见,学者将其统称为“俱闪弥故事”(14)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3-4.。关于不同版本的俱闪弥故事及其关系、俱闪弥故事与历史事件的联系,1958年法国佛学家拉莫特(Étienne Lamotte)在其名著《印度佛教史》中展开了初步研究(15)Étienne Lamotte, Hi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58; 英文版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rans.Sara Webb-Boin, Louvain: Peeters Press, 1988, pp.191-202。。1991年那体慧(Jan Nattier)的专著《于未来世:佛教法灭故事研究》作了更细致的分析(16)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另外,1980年查贝尔(David Wellington Chappell)曾著文讨论佛教法灭思想的印度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17)David Wellington Chappell, “Early Forebodings of the Death of Buddhism”, Numen, vol.27, fasc.1, 1980, pp.122-154.。近年刘屹发表多篇论文,专论汉传佛教的法灭与末法思想并及法灭思想在于阗和吐蕃的传播(18)刘屹:《印度“Kauāmbī”法灭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第189—204页;《佛灭之后:中国佛教末法思想的兴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93—515页;《法灭思想及法灭尽类佛经在中国流行的时代》,《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第39—47页;《憍赏弥国法灭故事在于阗和吐蕃的传播(文献篇)》,第425—451页。。
前述各种有关法灭故事的藏语文献中,三部与于阗有关,即《僧伽伐弹那》《阿罗汉》和P.t.960《于阗教法史》。尽管那体慧书有专节讨论这三部文献,刘屹对其年代先后亦有所梳理,但笔者近年系统整理这些文献,感到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谨略说如下。
二、《月藏经》佛经群之法灭故事
为更好地理解《僧伽伐弹那》等三种文献中的法灭内容,我们需先了解《月藏经》佛经群描述的俱闪弥故事。如同那体慧所论,在所有俱闪弥故事中,《月藏经》佛经群的故事影响最广,我们此处所论文献也皆与《月藏经》有关。《于阗教法史》尾题即记此经乃“简要录自佛经《日藏经》《月藏经》和《无垢光请问经》”(19)朱丽双:《〈于阗教法史〉译注》,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附录二,第468页。。《阿罗汉》开篇称一比丘学过律经且见了《月藏经》,故问其师阿罗汉有关于阗佛教的住灭情况。《僧伽伐弹那》虽未及《月藏经》,但其开篇有僧伽伐弹那之一弟子“学过律经,闻说释迦涅槃后二千年释迦教法将于天竺之俱闪弥国衰落”之语,故被那体慧归入佛涅槃后2 000年法灭的佛经群。不同佛经对佛教最后灭没的时间有不同设计(20)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pp.192-198; 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27-64.,佛涅槃后2 000年法灭的佛经除《僧伽伐弹那》,还有藏译《月藏经》、汉译《月藏经》和《阿罗汉》(21)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52-54,172-174.。
《月藏经》佛经群的俱闪弥故事包括三种文献,即汉、藏语译本《月藏经》和于阗语本《赞巴斯塔书》(22)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52-54,172-174.。其故事梗概大体如下:未来佛教逐渐衰落之时,将出现三位恶王,据藏语《月藏经》和于阗语《赞巴斯塔书》,是叶婆那王(Tib.Ya bha na; Khot.Yavanä;指希腊人)、释拘王(Tib.Shag ku na; Khot.-Dakanunä;指塞人)和波罗王(Tib.Pa la ba; Khot.Palvalä,指帕提亚人,汉籍作安息);据汉译《月藏经》,是波罗、百祀(23)那体慧推测百祀指波斯,见其著第177页。笔者怀疑百祀仍是对帕提亚(Parthia)的音译。换言之,汉译《月藏经》的波罗和百祀实指一地,同时为维持三位恶王之数,此经缺写了叶婆那王。和善意释迦。当时俱闪弥国(汉译《月藏经》作睒弥国)大军王(Tib.Mhen dra se na/Men drha se na / Men dra se na; Khot.Mahindraysenä; Skt.Mahendrasena)生子难看(Tib.Drus spra sa ha / Du spra ba sam / Drus sprha lha hra; Khot.Dspraysavä; Skt.Dsprasaha)。难看12岁绍继王位(汉译《月藏经》作7岁;于阗语本不详)。三恶王各统领十万大军围攻俱闪弥国。经过12年奋战,难看王消灭了三恶王及其军队。难看王为消除杀戮众兵之罪,迎请世上所有僧伽至俱闪弥国。僧伽聚集俱闪弥国后,于15日晚举行布萨(Skt.psadha)法会。法会上三藏法师失师迦(Tib.Shir sha ka / Shir she ka / Shir sha ga / Sher she ka / Shir she kya; Khot. -Där akä;Skt. -Dīsaka)与阿罗汉涑罗多(Tib. Su ra ta / Su ra da; Khot. Sūratä /Sūradä;Skt. Sūrata)发生争执。三藏法师的一名弟子鸯伽多(Tib. Ag na dhe / A gan; Khot. A-ggadī; Skt.Agada)杀阿罗汉涑罗多,法会上一位夜叉目佉檀提(Tib. ’Dhid rha mu kha; Khot. [Da]dämukhä; Skt. Dadhimukha)怒而杀鸯伽多,复有一位比丘杀三藏法师。随后僧众陷入混战,互相残杀,至天明僧众皆死,佛法自兹灭尽(24)参见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 170-187。。
这个故事与更早的俱闪弥故事一样,重点在描述佛教如何在俱闪弥国最终灭没。其中藏语本和于阗语本的三位恶王叶婆那王、释拘王和波罗王分别指希腊人、塞人和帕提亚人,他们曾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先后入侵西北印度(25)(1)公元前2世纪,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Greco-Bactria)帝国先后在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c.171-145 BC)、米南德(Menander,统治时期150-135 BC)等君主率领下进军印度,攻占了旁遮普(Punjab)等地。印度梵语文献称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为叶婆那(Yavana),此词来自俗语(Prakrit)Yona,而Yona又借用自古波斯语Yauna。(2)公元前85年,塞人(-Daka)在毛厄斯(Maues)率领下占领了犍陀罗地区的塔克西亚(Taxia),随后于印度河建立起一个印度—斯基泰帝国。(3)公元1世纪时,印度—帕提亚王朝(Indo-Parthia)的贡多法勒斯(Gondophares)打败印度—斯基泰帝国的塞人领袖阿泽斯二世(Azes II),他们在印度文献中被称为帕拉瓦人(Pahlava)。见Richard 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C.H. Beck, 1983, pp. 177-204, esp. 185-187, 194-195, 201; Himanshu P. Ray, “The Yavana Presence in Ancient Ind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31, no. 3, 1988, pp. 311-325;[匈牙利] 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2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北京:中国外对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68—70、142—157页。另见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p. 201。。在所有早期俱闪弥故事中,除《佛使比丘迦旃延说法没尽偈百二十章》例外,能够解读出来的入侵俱闪弥国的恶王都是这三位(26)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 157-165, 188, 205, 288-289。《佛使比丘迦旃延说法没尽偈百二十章》作大秦(指罗马)、拨罗(指帕提亚)和安息,且其所处方位亦与其他不同,称大秦在前,拨罗在后,安息在中央,故被那体慧认为是所有俱闪弥故事中最早的版本,产生于巴克特里亚(Bactria)。。此三恶王组合以及大军王和难看王的父子关系、三藏法师失师迦与阿罗汉涑罗多争执等因素,皆反映了其对早期俱闪弥故事的继承。
三、后期于阗语改编本的法灭故事
前述《月藏经》等文献描述的俱闪弥故事皆与于阗无关,但在《僧伽伐弹那》《阿罗汉》和《于阗教法史》这三种佛经中,故事皆从于阗佛教的衰落开始。换言之,于阗佛教的衰落成为佛法最后灭没的最初社会背景。又由于这三部文献皆涉及8世纪前半叶发生的历史事件,且多少皆保留了从于阗语翻译的痕迹,因此那体慧将它们与其他俱闪弥故事区别开来,称之为“后期于阗语改编本”(late Khotanese adaptations),认为这三种佛经最早当形成于于阗或其周边地区,虽然它们以藏语的形式保存下来(27)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pp. 188-189.。
在这三种后期于阗语改编本中,《僧伽伐弹那》的描述最为详尽。故事是说:一比丘学过律经,闻说佛教将于释迦牟尼涅槃后2 000年灭尽,遂问其师阿罗汉于阗佛教多久住世及其灭尽的原因。阿罗汉为之授记说:佛涅槃1 500年后,各地将现无正信之人,为使正法灭没而互相侵扰,是时于阗佛教亦日渐衰落。于阗王不信正法,于阗比丘亦不守戒法,行在家人之事。于阗比丘的生活资具被大臣等强占,生计无出,遂前往佛法初被之地赞摩(Tsar ma)伽蓝商议办法,最后决定前往吐蕃。当时吐蕃国王乃一菩萨,娶汉公主为正妃。汉公主迎请众僧至吐蕃,供养之。当时安西(An rtse)、据史德(Gus tig)、拔焕(Par wan)、疏勒(Shu lig)、吐火罗(Tho kar yul)、迦湿弥逻等国之比丘因受无正信之人的伤害亦都在勃律,闻说吐蕃兴佛,皆往吐蕃。三年间,僧众在吐蕃享受供养。三年过后,由于魔众等之扰乱,吐蕃出现天花等各种疾病,公主因此而亡。吐蕃大臣将疾病的出现归因于边鄙僧众前至吐蕃的缘故,驱逐僧众。僧众前往天竺乾陀罗国。吐蕃和汉地的僧众亦前往乾陀罗国。途中他们得到伊罗叶(Tib. E la’i ’dab;Skt. Elāpattro)龙王的帮助而顺利抵达乾陀罗国。于此他们获得国王的供养。两年后,国王死,二王子争王位。信奉佛法的王子因僧众之助绍继王位。然不久僧众复杀信法王子,任命一比丘为国王。两年后,乾陀罗国人杀比丘王,且追杀乾陀罗国一切比丘。尔时天竺之外出现三位无正信之国王,分别是大食王、突厥王和吐蕃王。此三王各带领十万大军,征服了天竺之外的一切国土。当时天竺俱闪弥国王名难忍(bZod dka’)。大食等三国王前至俱闪弥国,与难忍王战。三个月间,难忍王尽灭三无正信国王及其军队。尔后难忍王思消除杀戮众兵之罪,迎请波梨国(Tib. dMar bu can gyi yul; Skt. Ptaliputra)三藏法师失师迦(Tib. Shir sha ka)。失师迦建议王召请世上所有比丘至俱闪弥国进行供养,且做忏悔。难忍王按其言而行,遂有十万比丘齐聚俱闪弥国。尔后15日晚,众比丘做布萨,请失师迦念诵《别解脱经》。失师迦言:“尔等要《别解脱经》有何用?断耳之人要镜子有何用?”比丘众中有一位阿罗汉涑多罗(Su ta ra),言自己从未犯戒。失师迦十分羞愧。失师迦的弟子安迦比(A kan bi)执门闩杀阿罗汉,阿罗汉之弟子迦罗多(Ka ra ta)杀失师迦。尔时比丘分为两派,互相残杀,全部死亡,佛法自兹灭尽(28)参见朱丽双:《〈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译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8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53—482页。另见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re Time, pp. 194-198。。
《阿罗汉》的开篇与《僧伽伐弹那》相似:在第7代于阗王时,一比丘学过律经,又阅《月藏经》,遂问其师阿罗汉有关于阗等地佛法几时及如何灭没的问题。阿罗汉为他授记道:佛灭后2 000年,佛教将会灭没。尔时汉、吐蕃、苏毗、突厥、回鹘等“贼”(dgra)将相继侵扰于阗、疏勒、安西等地,导致于阗佛教衰落。于阗僧众亦信心渐薄,求世利誉,致令正法逐渐衰耗。于阗王亦不喜佛法,令僧徒还俗或出向他境。当时吐蕃之王为菩萨化身,娶汉公主为妃,吐蕃之境广兴正法。于阗僧众于赞摩伽蓝商议,决定前往吐蕃。僧众到达吐蕃,得到汉公主的供养。安西、疏勒、勃律、迦湿弥逻等地的僧人亦前往吐蕃,汉地僧人因汉王崇尚道士法亦到吐蕃。三四年后,公主心上长出恶疮而亡,其后吐蕃发生痘疮病,吐蕃群臣将此归因于边鄙僧众前至吐蕃的缘故,下令驱逐僧众。僧众往西去乾陀罗国。吐蕃境内的其他僧人亦随之流亡。途中他们得到伊罗叶龙王的帮助,得达彼境,且获国王的供养。两年后,国王去世,二王子争王位,信法王子得到僧众的支持而继位,但不久被一比丘杀害,比丘自立而王。乾陀罗国人怒而杀比丘王,驱逐一切僧众。当时西方国王、北方国王和叶婆那王各带领十万兵攻打俱闪弥国,但被俱闪弥国王全部灭之。俱闪弥国王为消除杀戮众兵之罪,召请世上所有僧众至俱闪弥国。后因僧众内部斗争,互相残杀,全部死亡,佛法自兹灭尽(29)参见朱丽双:《〈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第605—676页。另见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re Time, pp. 189-194。。
P.t.960《于阗教法史》所述法灭故事共有五部分:(1)于阗都城未来毁灭而成海子之情形:当未来于阗人众不行十善,东、西玉河之水将汇集于于阗都城之内,于阗将成海子,直到弥勒佛来作世间护主,于阗海子复将干涸,转成桑田。(2)世尊之告诫:凡俗人不宜持有《于阗国授记》(YullIyulgyIlungbstan),亦不宜对比丘等行法者讲授此经。笔者推测此处所谓《于阗国授记》实指《于阗教法史》,因此经描述了灭法经过,故言不宜对一般人讲述,“以免扰乱其心”。(3)于阗最后正法毁灭之情形:于阗人为魔所惑,不信正法,盗窃信财,驱逐僧众。僧众于赞摩伽蓝商议,决定前往吐蕃。(4)吐蕃兴佛:吐蕃神圣赞普娶汉公主为妃,公主迎请于阗僧伽至吐蕃,吐蕃之境广兴正法。(5)佛法最后灭没之情形:12年间,吐蕃境内僧伽和在家人多行佛法。后复因魔众扰乱,出现黑痘等病,公主因此而死。吐蕃人遂不再信奉正法,将黑痘等病的出现归因于边鄙僧众前至吐蕃的缘故,驱逐僧众。僧众前至乾陀罗国。尔时天竺俱闪弥国大军王(Man ’dre seng ge)生子难看(’Dre spe sad)。尔时汉王、吐蕃王和回鹘王率十万大军与俱闪弥国难看王鏖战,12年间,全军覆没。俱闪弥国王为消除杀戮众兵之罪,召请世上所有僧伽至俱闪弥国。僧众抵达俱闪弥国的当晚作布萨法会之时,法会上一位三藏法师失师迦(Zhir zhag)之弟子安伽(Tib. Ang ghan)杀阿罗汉须赖(Tib. Su rag),阿罗汉的守护神夜叉大提木佉(Tib. ’Dra dha mu ka)杀三藏法师失史迦。尔时僧伽分为两派,互相残杀,僧伽皆死,佛教自兹灭尽(30)参见朱丽双:《〈于阗教法史〉译注》,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第413—468页。另见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re Time, pp. 199-204。。
从这三种佛经描述的法灭故事看,重点在于阗等地的僧众如何一再流离失所,生计无出。他们先从于阗逃到吐蕃,又从吐蕃逃到乾陀罗国,后来又被乾陀罗国人追杀。这些内容在《僧伽伐弹那》和《阿罗汉》中描述得最为详尽,其中伊罗叶龙王化身为巨蛇、为僧伽架桥以便他们渡过海子的情节尤其生动感人。相对而言,佛法最后在俱闪弥国灭尽的故事已不突出。事实上,《阿罗汉》对此最后灭没故事仅一笔带过。另外在其他细节方面,三种文献也有不同,比如于阗等僧众在吐蕃居住的时间、吐蕃出现各种疾病的原因、三位恶王的名字、俱闪弥国王的名字、俱闪弥国王与三位恶王作战的时间等等。看来,不同佛经在其编纂过程中皆参考了其他俱闪弥故事的文本,并据编者所处年代而有所加工创造。总体而言,《僧伽伐弹那》和《阿罗汉》在情节编排上较为接近,不过《僧伽伐弹那》的描述更为详尽,《阿罗汉》则相对简略,颇让人产生二者一为扩展版、一为缩略版的想法。不过细读之下,二者在细节上仍有差别,比如僧众在乾陀罗国支持信法王子绍继王位后,据《僧伽伐弹那》,5个月后众僧杀信法王子而立一比丘为王;据《阿罗汉》,则是半年后一比丘杀信法王子,自立为王。不过最大的差别是两种文献中三恶王的名字完全不同。《僧伽伐弹那》作大食王、突厥王和吐蕃王,反映了6世纪以降西域政治形势的变化;《阿罗汉》则作西方国王、北方国王和叶婆那王,更多地继承了早期俱闪弥故事中三恶王的组合。看来,虽然两种文献基本情节类同,但很难说它们是直接继承关系。
至于《于阗教法史》的法灭故事,其前半有关于阗法灭的部分与《僧伽伐弹那》和《阿罗汉》接近,应存在借鉴关系,但多出于阗都城未来毁灭而成海子的情形以及世尊对此法灭授记不可随便授人的告诫;后半有关佛教在俱闪弥国灭没的部分则与《月藏经》法灭故事更为接近。尤其大军王与难看王父子的名字与《月藏经》皆合,《僧伽伐弹那》完全没有出现大军王,难看王的名字亦不同,作“难忍”;难看王与三恶王会战的时间,《于阗教法史》作12年,亦与《月藏经》同,《僧伽伐弹那》则作3个月。看来,《于阗教法史》的这部分内容与《月藏经》关系较密。不过对于三位恶王,《于阗教法史》复与其他所有俱闪弥故事不同,作汉王、吐蕃王和回鹘王!显然,这反应了编者对其所处时代新的政治形势的认识。
四、后期三种于阗语改编本的成立年代

吐蕃于8世纪后半墀松德赞时确定弘佛,此后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815)和墀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841)时期皆继续执行兴佛政策。但从《僧伽伐弹那》行文来看,其编者显然对吐蕃持有成见。文献最后一段话预言,佛教将在于阗王尊历治下兔年之后一百又二年灭没,即表明作者认为吐蕃不会很好地护持于阗的佛教;另外,文献所述与俱闪弥国王作战的三位恶王是大食王、突厥王和吐蕃王!大食成为三恶王之一不禁令人想到8世纪以来唐、吐蕃、大食争胜西域的历史。突厥成为三恶王之一自然与唐兴以前突厥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有关,《新唐书·西域传》述及唐史所载第一位于阗王尉迟屋密时,即言他“本臣突厥”(37)《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于阗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5页。。吐蕃成为三恶王之一正反映了编者对吐蕃的负面态度。不过,当于阗在吐蕃治下之时,于阗官方自不敢有此意见。看来,《僧伽伐弹那》大概是某位于阗大德据当时于阗流行的法灭文献而编纂的作品,编成时期最有可能在811年前后。
《阿罗汉》的编成年代,笔者曾定在9世纪20—50年代之间(38)朱丽双:《〈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第669页。,现在看来应作修正。
第一,《阿罗汉》开篇将于阗佛教衰落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汉、赤面、苏毗、突厥、回鹘等贼”的侵损,这是相当不寻常的。“贼”这个词是法成的汉译,藏语作dgra,意为外敌。从这种用语来看,推测当时于阗已摆脱唐朝或吐蕃的统治。如果我们同时阅读其他相关文献,这种倾向尤为明显。比如《无垢光请问经》就通篇没有对汉人的负面描述,反而称当吐蕃侵扰于阗时,于阗人应寻求汉人的帮助。《无垢光请问经》著录于《登噶目录》和《旁塘目录》(’Phangthangma)(39)参见朱丽双:《〈于阗国授记〉的成立年代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9辑,第112—113,112—115页。,笔者推测它当编成于唐朝统治时期。《阿罗汉》此处所述的这些部族或政权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侵扰或占领过于阗。比如苏毗曾在3—4世纪间活跃于于阗南山,对丝路南道诸国构成威胁(40)[日]山本光朗:《カロシュティー文書No.272について:鄯善国とスピ族》,《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第55卷第1号,2004年,第23—34页。。西突厥在唐兴以前控制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诸国(41)朱丽双:《〈于阗国授记〉所载早期于阗王统研究》,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211页。。回鹘是否掌控过于阗,史无明文,但它曾在8世纪末9世纪初与吐蕃在丝路北道作战并取胜;802年疏勒受制于回鹘,与此同时,吐蕃治下的于阗亦处于回鹘进攻的威胁下(42)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第254页;Y. 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in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Christiane Reck and Dieter Weber 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 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2009, pp. 349-362.。从《阿罗汉》此处的叙述来看,它似应编成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以后。
第二,藏文大藏经所收有关于阗的五部文献中,《登噶目录》著录了《无垢光请问经》《牛角山授记》《僧伽伐弹那》;稍后的《旁塘目录》著录了《无垢光请问经》和《牛角山授记》;再后的《论典目录》和《布顿佛教史》著录了《于阗国授记》(43)参见朱丽双:《〈于阗国授记〉的成立年代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9辑,第112—113,112—115页。。换言之,早期藏文佛经目录无一著录《阿罗汉》,而其他四部文献皆著录于一种或数种目录。这是否因《阿罗汉》罕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敦煌留下了这部文献的三个抄本和一件汉译本,说明它曾相当流行。它不见于吐蕃时期编成的佛经目录只有一种解释,即它编成于这两种佛经目录之后。再后《阿罗汉》被编入《于阗国授记》中,自然不再出现在后期的佛经目录中。
第三,《僧伽伐弹那》叙述吐蕃大臣驱逐境内僧伽时,有这样一句话:“尔时乃众生诤劫之时,汉地之众比丘亦为痛苦逼迫,前往乾陀罗国。”《阿罗汉》亦述及汉地僧人流亡乾陀罗国之事,但用词很不相同:“公主来至赤面国后,汉王兴崇道士法,故一切汉僧悉皆来至赤面国界。”当吐蕃大臣驱逐僧人,一切僧众前往乾陀罗国后,“汉与赤面、婆罗门国、于阗国等,直至恒河,像法灭没,更无有余。恒河彼岸俱闪弥国,像法三月住世,最后灭尽”。这里《僧伽伐弹那》对汉僧的流亡并未说明特别原因,不过因劫数至此。但《阿罗汉》则明确指出这是由于汉王奉崇道教,而且随后“像法灭没,更无有余”的描述更体现出作者浓重的悲观态度。如所周知,在唐朝的不同时期,佛道各有赢亏,且金城公主出嫁吐蕃的时间是在710年。但《阿罗汉》的这种行文仍令人想起会昌年间(840—846)唐武宗的毁佛事件(44)[美]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6—140页。。很有可能,这部文献的编纂者将唐朝毁佛与佛经中流传的法灭思想联系到了一起。只是由于文献的“授记”性质,致使历史事件与虚构交错。
第四,《阿罗汉》编成的下限,由于存在法成汉译本P.2139《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而相对容易确定。一般推断P.2139是法成晚年译作,即9世纪50年代的作品,则《阿罗汉》不应晚于860年。
综合以上,《阿罗汉》当是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于阗人创作的作品。至于说其中三恶王的组合保留了早期俱闪弥故事的遗痕,也是好理解的,因为于阗本传播《月藏经》等包含法灭故事的文献,《阿罗汉》的编者肯定有所接触。
在这三部佛经中,P.t.960《于阗教法史》无疑最为晚出。前谓这部文献所述第56代于阗王即《于阗国授记》记载的于阗王赞藏赞罗旦,他于9世纪初吐蕃统治于阗时接续尉迟曜为王。笔者过去推测《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皆编纂于这位于阗王在位期间。现从于阗语文书来看,吐蕃统治时期至少有过5位于阗王(45)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8年,第19页。,赞藏赞罗旦/赞历的在位时间不可能长达30年。笔者过去的推测有误。《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的上述行文表明两种文献叙事至赞藏赞罗旦/赞历为止,但不能说明两种文献一定编纂于他统治时期。从《于阗教法史》所述与俱闪弥国王作战的三位恶王为汉王、吐蕃王和回鹘王来看,文书似编纂于9世纪中期以后,彼时唐朝已发生过会昌毁佛,吐蕃和漠北回鹘也已崩溃。他们都成了损毁于阗佛教的罪人。《于阗教法史》的叙事虽无严格时间顺序,但其内容编排还是反映出编者,即某位于阗大德一定的思想倾向。在他心目中,于阗无疑是最神圣之地。因此在叙述佛教最后灭没后,他接着又描述了护持于阗的佛像、无热(Tib. Ma dros; Skt. Anavatapta)龙王及其在于阗弘佛的故事、于阗二部僧伽之数。最后并称“至今于彼诸僧伽中,许多乃是菩萨以方便化身,利益众生”。虽然这看起来与前面的法灭故事有些矛盾,但在法灭故事的开始作者叙述于阗都城未来毁灭而成海子时,即称彼时诸龙将寻找其他舍利,于各自之住所供养。七世佛舍利所在之地亦将闭合。当未来弥勒佛出世,于阗海子复将干涸,转成桑田。奉安七世佛舍利之伽蓝所在的小谷沟亦将开放,成为弥勒佛及其眷属之应供处所(46)朱丽双:《〈于阗教法史〉译注》,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第442、468页。。显然,这里编者是在为未来佛法毁灭而又在于阗复兴埋下伏笔。看来,在这部佛经编成的年代,作者对于阗僧伽的状况是满意的,对于阗王国也是充满期待的。在《僧伽伐弹那》《阿罗汉》和《于阗教法史》三部文献中,前二者纯为法灭故事,末世思想浓重;后者则如有关于阗的文献集成,法灭故事仅是其中部分内容,且编者对于阗佛教尚存某种乐观态度,似乎暗示佛教灭后仍可复兴。如此看来,《于阗教法史》很可能编写于9世纪中后期于阗重新获得独立的时期吧。
五、于阗法灭思想形成的原因
8至9世纪间法灭思想在于阗似颇盛行。以上所列13种有关佛法灭没的文献中,竟有4种出自于阗,分别是藏语本《僧伽伐弹那》《阿罗汉》《于阗教法史》和于阗语本《赞巴斯塔书》。从这些佛经与《月藏经》的关系来看,《月藏经》在于阗当亦传播甚广。和《僧伽伐弹那》等所谓“后期于阗语改编本”相比,《月藏经》佛经群的俱闪弥故事保留了较多早期俱闪弥故事的遗痕。看来,有关佛教灭没的文献可能曾长期在于阗传播,乃至于阗人自己编写的佛典集成类作品《赞巴斯塔书》亦载有法灭故事。当8、9世纪之际随着西域政治形势的变化,于阗人又进行新的创造,写出他们自己的法灭故事,从而产生出《僧伽伐弹那》《阿罗汉》和《于阗教法史》这样的作品。确实,从历史来看,自5世纪中叶以降,由于吐谷浑、柔然、丁零、嚈哒、突厥等势力先后对西域的控制,于阗国势日蹙,佛法日衰。《后汉书·西域传》记于阗有胜兵三万(47)《后汉书》卷88《西域传》于阗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5页。;《三国志》言三国初年,“南道西行,且志(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穴(皮)山国皆并属于阗”(48)《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9页。。而《隋书·西域传》记于阗胜兵仅数千人(49)《隋书》卷83《西域传》于阗条,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2页。;《旧唐书·西戎传》则明确记为四千(50)《旧唐书·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5页。。当401年法显求法到达于阗时,“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51)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12页。。而玄奘644年到于阗时,于阗“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52)玄奘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2,1027页。。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百余年间于阗国势衰微和佛教衰落的程度(53)朱丽双:《〈于阗国授记〉所载早期于阗王统研究》,孟宪实、朱玉麒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第212页。。可能就在此过程中,佛经中原已存在的法灭思想渗透进了于阗佛教界。《大唐西域记》述于阗媲摩城雕檀立佛像时,有“闻诸先记曰:释迦法尽,像入龙宫”之语(54)玄奘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2,1027页。,表明至少在玄奘驻留于阗时,于阗僧徒已认识到佛法必有灭没之日。7世纪中,于阗归附唐朝。8世纪末9世纪初,于阗为吐蕃所有。佛经中本已存在法灭思想,由于5世纪中叶以降不断受到外敌入侵,若说于阗佛教界因此对法灭思想有进一步发展,似亦合理。当然,在于阗僧人看来,于阗佛教的衰落主要是出于苏毗、汉、吐蕃、突厥、回鹘等外敌先后侵扰与损毁的缘故。《僧伽伐弹那》和《阿罗汉》包含的法灭思想当与此有关。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磨(Glang dar ma,r. 841-842)遇刺身亡,吐蕃王朝崩溃。848年沙州张议潮举兵赶走吐蕃守将,建立归义军政权。861年张议潮收复凉州,吐蕃在敦煌及河陇的统治相继结束。865年仆固俊率部攻克西州等地,建立西州回鹘政权。推测在此前后于阗亦从吐蕃的羁绊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王国(55)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第35页。。《于阗教法史》体现的乐观态度或与此有关。刘屹指出,于阗的法灭思想虽加入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故事,但总体上仍服从于印度佛教的法灭传统。相对而言,汉传佛教却在法灭思想上逐渐作出了脱离印度佛教传统的尝试,将汉传佛教置于印度俱闪弥法灭之后的历史延长线上(56)刘屹:《印度“Kauāmbī”法灭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第204页;《法灭思想及法灭尽类佛经在中国流行的时代》,第40—47页;《憍赏弥国法灭故事在于阗和吐蕃的传播(文献篇)》,第425页。。从前文讨论来看,《僧伽伐弹那》和《阿罗汉》确如其所言,没有脱离印度法灭故事的传统,但《于阗教法史》则不同。《于阗教法史》在描述未来于阗都城毁灭时已为更后的佛教复兴埋下伏笔。在描述法灭故事后,紧接着叙述了护持于阗的佛像,且称于阗各地若发生战争或灾害,可念诵《妙法莲花经》《无垢光请问经》中佛曾亲自演说之一百零八真言藏,从而增进福德,使正法长住,国土长治久安。接着又叙述无热龙王前世化身为龙的因缘及其转世在于阗坎城(Kham sheng)弘法的事迹,故事末尾且有释迦牟尼对无热龙王将如愿成佛的授记(57)参见朱丽双:《〈于阗教法史〉译注》,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第454—466页。。后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汉文《佛说弘道广显三味经》和藏文《无热龙王请问经》(’Phagspaklu’irgyalpomadrospaszhuspazhesbyabathegpachenpo’imdo)都记道,当无热龙王成佛时,其土人民没有贪婬、恚怒、愚癡,永无相侵,人们生活安隐,享用不缺,即一片喜乐佛土的景象(58)朱丽双:《从印度到于阗——汉、藏文献记载的阿那婆答多龙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9—100页。。《于阗教法史》的这种编排表明,其编纂者并没有完全遵循印度法灭故事的传统,而是暗示法灭之后,于阗佛教仍有复兴的可能。前文指出,《于阗教法史》可能编纂于9世纪中后期于阗国重新获得独立的时期,因此作者对于阗佛教抱有一种乐观态度。由此我们或可大胆推测,佛经的形成往往反映一定的现实,如果说中土佛教徒撰述的《法灭尽经》将印度佛教的法灭思想进行了本土化,从而延长法灭之后的佛教历史(59)刘屹:《印度“Kauāmbī”法灭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第202—203页。,则《于阗佛教史》可以说是于阗佛教徒据于阗的历史现状对印度佛教法灭思想的改造,同样是对法灭之后佛教历史的延长。而其中所述当未来于阗人不行十善,于阗将转成海子的预言则如同警钟,告诫于阗人仍需慎重行事,否则相同的法灭故事仍将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