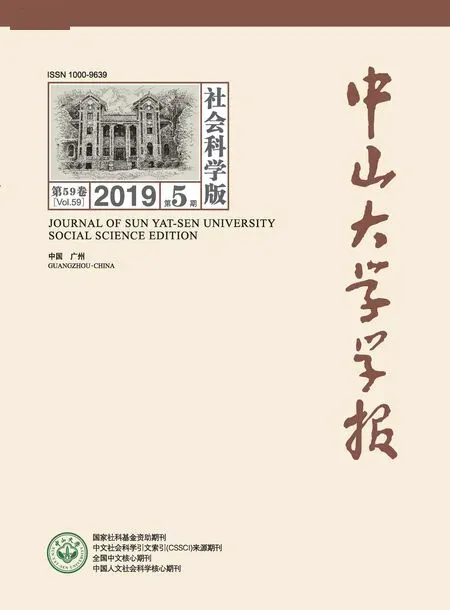《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2019-09-23王小惠
王 小 惠
“五四”学人(1)对于“五四”的时间划分,学界历来有如下5种分法:(1)1919年的“五四”,以蔡元培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为代表;(2)1919年截至“民国十年止”的“五四”,以周作人的《五四运动之功过》为代表;(3)“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以茅盾的《“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为代表;(4)“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以张奚若的《国民人格之培养》为代表;(5)“1915年到1920年”的“五四”,以胡绳的《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代表。本文采用的是第三种观点,将“五四”的时间划分为从1917年到1922年。而“五四”学人是指在1917年至1922年显露于学坛者。这些“五四”学人在“五四”及其之后对《诗经》的论述,延续着建立新文学观的思路。同时受“五四”学人影响的闻一多、俞平伯等也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激烈“反孔”,讽刺“尊孔”是“尊屁”(2)钱玄同:《今之所谓“评剧家”》,《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视孔学著作为“粪谱”(3)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79页。。但他们却对《诗经》非常地喜爱,欣赏它的“挚情之真叙”,称赞它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五四”学人对《诗经》的重释,更是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以建立新文学观的尝试。中国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以文言文为文学的正宗,“五四”新文学则反其道而行之。
一 、新文学观的形成:从“载道”到“主情”
“六经”确立的道德伦理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张之纯称“经传为文学之正宗,一切文章体例,本于经传者居多”(4)张之纯:《中国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页。。马崇金认为“文学之变迁虽无穷,覈其所作,大抵不能越六经之藩篱”(5)马崇金:《中国文学沿革略论》,《约翰声》1919年第3期。。但在“五四”,胡适等试图改变“文必有关‘圣道’”的现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新文学须“言之有物”,其中的“物”是指“情感”与“思想”,“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陈独秀也在《文学革命论》重申“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以及“社会文学”,以抵抗传统的“载道文学”(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第2月1日。。
为实现此目标,“五四”学人选择以“六经”之一的《诗经》为突破口,尝试从传统经学的内部瓦解“载道”文学观。孔子称“不学诗,无以言”,后世也尊《诗经》为“圣道王化的偶像”。但“五四”学人却仅视其为纯文学的性情之作。周作人强调,《诗经》本是文学,可被经学家改造成“作劝善的工具”,譬如《关雎》本是“一首新婚时的好诗”,却被解读为“有天经地义似的道理在内”(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6页。。郑振铎指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成了“圣经”后,“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焕,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的微弱了”(9)郑振铎:《文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3页。。
胡适也以文学眼光读《诗经》,强调它本是“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却因道学家的“附会”,使“情感真挚的诗解得僵直不成样了”,比如《诗经·国风》原是“男女感情的描写”,可经学家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让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完全失掉它的“真意”(10)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第5卷,第430页。。为此,他指出应将《三百篇》“作诗读,勿作经读”:
读《诗》者须唾弃《小序》,土苴“毛传”,排击“郑笺”,屏绝“朱传”,于《诗》中求诗之真趣本旨焉,然后可以言《诗》,读《诗》者须知三百篇之作者,并非尧舜文武,并非圣哲贤人,乃是古代无名之诗人。其人或为当时之李白、杜甫,或为当时之荷马、但丁;其诗或作小儿女声口,或作离人戌妇声口,或作痴男怨女声口,或忧天而感世,或报穰而颂神,其为诗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1)胡适:《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胡适文集》第9卷,第660—661页。
与胡适一样,钱玄同指出,要“趁讲白话文学史”的机会,打下《诗经》的“经字招牌”,为它“洗一个澡”,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12)钱玄同:《钱玄同致胡适函(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4页。他在《论诗经真相书》中说道:
(一)《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13)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顾颉刚更用“蔓草和葛藤盘满了”的“高碑”,比喻“被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的《诗经》:
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决不知道是一座碑……等到斩除的工作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14)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189页。
周作人、顾颉刚等的论述,以激烈的态度扭转了《诗经》原本的经学思路,将其从“经”“贬落”为“文学”。“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包含了一个文化传统最基本的宗教信条、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15)张隆溪:《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9年第3期。,拥有神圣不可僭越的权威,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规约着人们的情感、行为。可《诗经》一旦成为“文学”,它承传的“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圣贤之仁”也随之瓦解,其纲领地位不复存在,后世只会借鉴它的一些文学创作方法而已。
对“文学真相”的突出,使《诗经》在“五四”时期从“经”回归“原经”。汉、魏、唐、宋、明、清等不同时代的经学派别通过解经,给《诗经》注入时代元素,形成一套完备且稳定的“诗教”传统。这表明在“诗教”传统中,不只有“原经”,还有不同时代的解经师对《诗经》的“笺”“注”“解”“疏”之类,如《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魏了翁《毛诗要义》,赫敬《毛诗原解》,朱熹《诗集传》,戴震《诗经补注》,廖平《诗说》,皮锡瑞《诗经通论》等。它们让《诗经》获得超时代的“微言大义”,也展现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制度。后世可通过前代人的“笺”“注”“解”“疏”等理解经文,并诠释出不同的义理,使《诗经》的“诗教”传统得以延续。
但“五四”学人认为,前人的“笺”“注”“解”等是“牵强附会”, 毁坏了《诗经》,使其支离万状,真趣尽失,让作为“经”的《诗经》已非原始的《诗三百》。顾颉刚梳理出《诗三百》被“附会”的历史:(1)“战国时诗失其乐,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而强要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去,使得《诗经》的外部蒙着一部不自然的历史”;(2)“删诗之说起,使《诗经》与孔子发生了关系,成了圣道王化的偶像”;(3)“汉人把三百五篇当谏书,看得《诗经》完全为美刺而作”;(4)“宋人谓淫诗宜删,许多好诗险些儿失传——此说若在汉代起了,一定发生效力”(16)顾颉刚:《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卷,第71页。。
为此,郑振铎建议,“研究《诗经》,便非先把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否则“《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17)郑振铎:《读毛诗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242页。。胡适也提出:“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 彻底地祛除历朝历代强加给《诗经》等国故的“枷锁”,从而“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1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第3卷,第10页。。
在分离《诗经》与“诗教”传统后,“五四”学人直接称它为《诗三百》,挖掘其中“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元素。傅斯年欣赏《诗三百》的“挚情之真叙”,指出其艺术之美在于“直陈其事,而风采情趣声光自见,不流曲折以成诡词,不加刻饰以成蔓骈,俗语即是实言,白话乃是真话,真说乃是信说”(19)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胡适称赞它是“一种深切的感情的表现”(20)胡适:《〈蕙的风〉序》,《胡适文集》第3卷,第560页。。其后深受“五四”学人影响的俞平伯、闻一多等,继续提倡《诗三百》的抒情性。如俞平伯赞赏它的“情文悱恻,风度缠绵”(21)俞平伯:《茸芷缭衡室读诗札记》,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308页。。闻一多更将其定义为中国抒情文学的开端:“《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22)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10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五四”学人努力将《诗经》从“经”逆转为“文学”,消除“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的“穿凿附会”,表明“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23)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第5卷,第430页。。这可看出, “五四”学人重释《诗经》的背后,是他们建立新文学观的努力,企图使“文学”从传统“经学”中获得独立,清除传统文学中的道德教化,表明文学的本质是表现人的内心情感。鲁迅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24)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8页。周作人也强调:“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漶灭。”(25)周作人:《文章之力》,《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页。郑振铎更声明:“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26)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在“五四”及之后,《诗经》成为秦汉时期与“新文学”概念最相契合的抒情作品。当时诸多文学史皆用大量篇幅来论述它在中国抒情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认为,《诗经》传达出“真恳的情绪”,“在文学上给了我们不少的抒情诗的珍宝”(27)郑振铎:《文学大纲》,第143,137页。。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视其为中国第一部平民抒情文学的古书,认为它“真能代表匹夫匹妇的情绪的歌谣”(28)胡适:《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第123页。。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也强调它所代表的抒情诗歌传统,肯定其作品中情感的自然流露。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明显地突出《诗经》的“朴实无华的真挚心情”(29)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第11页。。施慎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则提倡:“当以纯文学眼光来读《诗经》,不必拘牵于前人的注疏。”(30)施慎之:《中国文学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第5页。其他的文学史如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谭正壁《中国文学史大纲》、曹聚仁《中国平民文学概论》、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胡小石《中国文学史》等都没有再谈及《尚书》《礼》《乐》《易》《春秋》等“五经”,并大多将《诗经》直接称为《诗三百》,视它为中国抒情文学的开端。一些文学史还从作品主题、意境、情感、形象等文学角度,剖析它与西方诗歌《荷马史诗》等的异同,以凸显《诗三百》的抒情特色。
与此同时,在新文学观的映照下,《诗经》中那些曾被经学家诟病的“情诗”“淫诗”,成为“五四”及其后文学摹仿、讴歌的对象,即“以淫荡为正经”(31)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周作人肯定了前人反对的男女之情,认为《诗经》的“淫奔之诗”很有“非礼教的色彩”(32)周作人:《猥亵的歌谣》,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第77页。,强调“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33)周作人:《情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自己的园地》,第63页。。胡适称赞《关雎》写活了男子的“相思苦情”(34)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第5卷,第431页。。顾颉刚赞赏《诗经》的情诗源自“性爱”,是忠于情感的产品(35)顾颉刚:《〈诗经〉情诗今译序》,陈漱情:《〈诗经〉情诗今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 页。。其后深受“五四”影响的学人如闻一多、刘大白、魏建功、钟敬文等,也从民俗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肯定这些“淫诗”的文学意义。比如闻一多在1927年发表《〈诗经〉的性欲观》,提出“《诗经》是一部淫诗”,赞叹其中的“劳人思妇的情绪之粗犷,表现之赤裸”(36)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190页。。
由于“五四”学人的推崇,这些“淫诗”也成为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称:“这些恋歌真是词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它们可占到极高的地位。”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认为《诗经》的“淫诗”都是“最能表现社会上一般男女们真实性情的作物”(37)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33页。。曹聚仁《中国平民文学概论》也指出,这些 “恋爱之诗”写出了“先为相慕,经之以热恋,终之不幸者则有失恋”的“恋爱过程”(38)曹聚仁:《中国平民文学概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第4页。。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赞赏《诗经》的“情诗”肆无忌惮地写出“男女间的相悦相慕”与“两性间的幽欢欲感”,是“永远不朽的好诗”(39)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第6页。。这些文学史注重书写《诗经》中大胆叛逆的男女之情,而为了突出起见,其中的一些文学史几乎只讨论了“淫诗”。
综上可知,“五四”学人对《诗经》的重释,实则是他们重新建构“新文学观”之努力。《诗经》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用其来诠释“新文学观”,就很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让一般的读者和知识分子接受。并且他们的重释,也使《诗经》的抒情经验融于新文学的创作之中,特别是对白话新诗产生了一些影响。周作人认为若订正《诗经》旧说,对于“新诗创作上一定很有效用”(40)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自己的园地》,第26页。,并以《诗经》为参照,发现了“五四”白话新诗的手法过于倾向“白描”“唠叨的叙事”“唠叨的说理”,“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故而他倡导吸收《诗经》中的“兴”,使白话诗含有抒情的“余香与回味”(41)周作人:《扬鞭集序》,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第45页。。鲁迅也认为,《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男女情感的书写,为白话新诗人开辟了很好的道路(42)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4页。。
但“五四”学人对《诗经》绝对文学化的处理,也屡被质疑,至今仍遭到很多反驳。反对者认为,这颠覆了几千年来《诗经》的发展史与研究史,否定了几千年儒学文明的成果。例如吕思勉指出,《诗》的作者距今已有三千年,其作诗之意,绝非“吾侪臆测可得”(43)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当代学者也指出,不破除“文学”之局限,就不能弄清《诗经》之历代注疏,也无法理解二千年引《诗》论政说事之历史,更不能理解《诗》教的涵义(44)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二、《国风》与“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合法性
在“五四”,陈独秀主张“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45)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胡适也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之正宗”(4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傅斯年强调“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47)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2号,1919年2月1日。。但这受到许多“谣诼诬谤”(48)鲁迅:《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213页。:林纾批判陈独秀等“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指责这是“覆孔孟,铲伦常”的“非圣无道”(49)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胡先骕责备白话文“以浅陋以文其浅陋”(50)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章士钊讽刺“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51)章士钊:《答适之》,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20页。。
在“白话文”遭到非议时,“五四”学人将“行用土语为文字”的源头追溯于《诗经》中的《国风》。胡适1921年编著的《国语文学小史》指出,《诗经》里的许多民歌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但这些到了汉朝已成为古文学了,故要将其撇开。钱玄同不赞同胡适,他在1921年12月7日致信胡适,认为“国语文学”应从《国风》讲起,建议道:
《国风》是的的确确千真万真的白话诗,而且很真很美。如《谷风》,如《氓》,真可与《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媲美;如《郑风》中的“淫奔之诗”《褰裳》、《溱洧》、《子矜》等诗,亦何让《子夜》、《懊侬》?
钱玄同认为,《国风》是“很古很美的白话文学”,应大大地表彰它,而胡适所说的“《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是腐儒将其误认了,所以关于《诗经》的研究只要探讨它的本质是“白话文学乎,是古文学乎”而定之,而“腐儒误解的,我们更要替它洗刷,留它的‘庐山真面目’才是”(52)钱玄同:《钱玄同致胡适函(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3—104页。。
胡适接受钱玄同的建议,复信钱玄同,写道:
《诗经》确应该收进去。但此一篇很不容易做。等此书写定付印时,我一定加上一篇,也许不止一篇,或须三四篇。大旨是:(1)《诗经》的白话文学。(2)这种白话的区域——东到山东,北到秦晋,南到江汉流域。(3)这个区域内各地方言的同异。最要紧的是求出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来。(4)拿这个普通话来比较战国时的文章。考定:战国时的文章与《国风》时代的白话相差若干?(53)胡适:《胡适致钱玄同(1921年12月10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0—1121页。
胡适在1922年3月24日定出了《国语文学史》的新计划,将“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纳为第二章。他强调:“这个计划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54)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第130—131,137页。这部《国语文学史》后来又以《白话文学史》(55)但胡适未完成他在1922年所订的关于《诗经》的研究计划,他解释道:“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为名在1928年出版。
为清晰地呈现《国风》开启的中国白话文学发展脉络,钱、胡进行了相应的整理。钱玄同认为,中国白话文学虽“屡屡被文人学士们踢到阴沟里去”,但至今依旧绵延着《三百篇》开启的白话文学传统,即从《国风》到宋以前的白话诗词,又到元朝的北曲、南曲等白话戏剧,再到明朝的《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白话小说,继续到清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如今到鲁迅、郁达夫等创作的白话文学作品(56)钱玄同:《〈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70—71页。。胡适认为“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5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第183页。,即从《国风》到《楚辞》,再到汉代的古乐府诗,又到南北朝戏剧,继续到唐朝的平民文学,又到宋朝的白话小说,再到元曲,又到明清的小说(58)胡适:《〈国语文学史〉大要》,《胡适文集》第8卷,第121—123页。。
钱、胡的归纳,强化了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阐明“五四”新文学是历史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之结果。正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所讲,由于“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了种子,造成了空气”,所以新文学是中国白话文“时机成熟”的体现(59)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第130—131,137页。。同时他也用具体例子阐释“五四”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主张,实则只是《国风》以来的“自然趋势”,因为“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60)胡适:《谈新诗》,《胡适文集》第2卷,第125页。。这种历史进化的寻根溯源,很自然地证实了新文学在本国的传统,让白话文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
胡适等传达的白话文学史观,影响了“五四”及其后的文学史著作。这些文学史大多应用了胡适等的进化逻辑,将《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白话诗歌集,为中国文学找寻出新的历史开端。例如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认为,“新文学运动成功之迅速,固由于胡适、陈独秀等之竭力提倡”,而其最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千余年白话文学之演进,已达于成熟时期”(61)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第165页。。再如徐嘉瑞的《中国文学概论》认为,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国风》开启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而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62)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胡适文集》第3卷,第547页。。文学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判断其价值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这些史学家对《国风》以来的白话文学发展规律的书写,直接拔高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地位,证明新文学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演进之体现,属于不证自明的自然存在。
确认“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五四”新文学一直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提出“文学”的三大主义,以求推翻“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以及“迂晦的艰涩的”文言文学,以建构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6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第2月1日。。陈独秀的主张虽然激烈,但缺乏历史的支撑,很难说服人,犹如“尽在空中挥拳”(64)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1页。。为此,钱玄同悲叹“至于白话文学,自从《新青年》提倡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65)钱玄同:《致信周祜》,《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4日。。鲁迅感慨,白话文的“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甚众,而应援者则甚少”(66)鲁迅:《190116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针对怀疑与反对,钱玄同、胡适等调整思路,从孔学“圣经”《国风》中寻觅历史的依据。 胡适在1952年的一次演讲时,回忆说:
究竟什么是活的语言,什么是死的语言,什么是活的文学,什么是死的文学,这更是偶然加上偶然的事体。他们大家都反对我的主张,我便要找证据来反驳……所以我们最古的一部文学书——《诗经》——是白话文,尤其是《国风》。我们看《国风》的全部,《小雅》的一部分,都是老百姓痴男怨女,匹夫匹妇用白话写的。(67)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胡适文集》第12卷,第36页。
胡适的回忆表明,“五四”新文学对《国风》的重释是为树立“以白话代文言”的历史合法性。就连主张推翻一切传统的陈独秀,也援引《国风》来论证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认为《国风》中的“当时里巷之言”,可表明“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门物”(68)陈独秀:《1917年2月1日答陈丹崖》,《陈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4页。。顾颉刚也用《国风》来表现白话文学的特征,认为“《国风》的大部分,都是采取平民的歌谣。如《召南·行露》乃平民受了损害而说出的气愤之语”(69)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3卷,第196页。。
在寻求到“合法性”后,“五四”学人竭力推崇白话文学的“独尊”地位,视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胡适声明:
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7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胡适通过彻底否定文言文学,使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中心地位。钱玄同也指出,《诗经》中的白话文章被“民贼文妖弄坏”,所以现在重提“白话是文学的正宗”,以“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71)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0页。。胡、钱二人的论述表明,中国文学中《诗经》所开创的白话文学最有价值,从而让“五四”白话文学获得了绝对的正当性。他们同时强调,《国风》《楚辞》“古乐府邸诗”“南北朝的民歌”等早“从草野田间爬上来”,成为“公认的正统文学”(72)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胡适文集》第3卷,第545页。。这显示白话文学已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表明“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73)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第134页。。
“五四”学人经由历史溯源,让《国风》成为白话文学的重要支撑,为使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他们又用“五四”白话文翻译《国风》。胡适曾讲,“《国风》的全部”虽然“都是当时说的白话”,但“后来一般书呆子摇头摇尾的念成为古文,继续下来成为士大夫阶级文学的路线,就是读书人模仿的死文学”(74)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胡适文集》第12卷,第37页。。为复原《国风》中被“淹没”的白话生命力,当时诸多学人尝试以白话文对其进行翻译。郭沫若就将《国风》中的40首“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译为白话文,这些译文被收入《卷耳集》。他在《卷耳集序》指出:
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75)郭沫若:《卷耳集序》,《卷耳集》,上海:泰东书局,1925年,第5页。
用白话文翻译的方式,让人们对《国风》的“白话味”得到最直观、最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这在“五四”及之后影响很大。顾颉刚、张履珍、谢祖琼、魏建功、董作宾、房儒林、刘化棠、王经邦等对此皆有尝试。顾颉刚就用白话文将“女德而有法度”的《邶风·静女》翻译成 “一首儿女的情诗”:
幽静的女子美好呵,她在城角里等候着我。
我爱她,但见不到(或寻不见)她,使得我搔着头,好没主意。
幽静的女子柔婉呵,她送给我硃漆的管子。
这个硃漆的管子好光亮,我真是欢喜你(指管)的美丽。
从野里带回来的荑草,实在的好看而且特别。
但这原不是你(指荑)的好呵,好只好在是美人送给我的。(76)顾颉刚:《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332页。
顾颉刚等的古诗今译,是站在“五四”白话文学的立场,改造、转化、利用《国风》的尝试。如果说钱玄同、胡适从学理的角度证明了《国风》为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那么郭沫若、顾颉刚等的翻译则从感性上让人们感受到《国风》的“白话的味儿”。这些翻译大胆地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重现《国风》作为白话诗的情调以及意境。从诗中直接“感受它的真美”,不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彻底解放了《国风》中被“后妃”“文王”“贤人”等淹没的“白话生命力”。
不论从学理上追本寻源,还是以白话文翻译《国风》,都让“五四”白话文学从《国风》中寻求到了历史的根据。这表明,“五四”学人虽激烈地反传统,但仍不断地挖掘传统中的有效资源,并将其转化到新文学建设中,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当然,“五四”学人对《国风》的处理也受到很多质疑。例如朱东润《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从内容、词汇、名物等方面考察《国风》,认为它并非民间的白话文学,而是统治阶级创作之产物,比如《周南·关雎》中的男子追求“窈窕淑女”时用的“钟鼓”“琴瑟”等,就并非一般老百姓所能使用的(77)朱东润:《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国立武汉大学文史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
三、重释的分歧:“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
《诗经》并非“圣经”,而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这是“五四”学人重释《诗经》的前提。但他们在重释时也存有分歧。
胡适在1918年9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从现代社会学等角度认识《诗经》,以展示当时人共同的情感状态与生存处境。比如他从《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发现“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又从《小雅·正月》《魏风·伐檀》等分析“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78)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第167—169页。。钱玄同称赞胡适“根据《诗经》来考老孔以前的社会状况”,“可谓巨眼卓识”,指出“中国的文学,实在是真正的中国历史”(79)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1月2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9页。。郑振铎也赞同之,认为《诗经》“把它的时代完完全全的再现于我们的前面,使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的生活,那时代的思想,那时代的政治状况”,具有“任何古书中所最不易得到”的史料(80)郑振铎:《文学大纲》,第143页。。
“五四”之后,胡适更加大胆、竭力地挖掘《诗经》的社会学、政治学价值。他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讲演时强调,《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而研究《诗经》的途径之一就是“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81)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第5卷,第426—427,431,431页。。在讲演中,胡适还通过对《野有死麕》《葛覃》《嘒彼小星》等的大胆剖析,展示了用现代社会学等方法诠释“文学”的思路。
周作人不赞同胡适等从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过度解读《诗经》的做法,他看到胡适在武昌大学的演讲稿后,认为胡适关于《诗经》的论述 “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在他看来,读诗歌时需要“不求甚解”,它的“诗意”应由读者自己去领会,而胡适过度地从诗中寻求政治史、文化史等材料,是“甚解多不免是穿凿”(82)周作人:《谈谈谈诗经》,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第146—148,146—147,147页。。周作人对胡适的质疑,有如下三例。
例一,胡适认为《野有死麕》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因为“初民社会的女子多欢喜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野麕,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83)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第5卷,第426—427,431,431页。。但周作人反驳道:

例二,由于指认胡适以为《葛覃》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周作人讽刺道:
我猜想这里胡先生是在讲笑话,不然恐怕这与“初民社会”有点不合。这首诗至迟是孔仲尼先生在世时发生的,照年月计算,当在距今二千四百几十年以前,那时恐未必有像南通州土王张四状元这样的实业家在山东纠集股本设立工厂,制造圆丝夏布。照胡先生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种情状:妇女都关在家里,于家事之暇,织些布匹,以备自用或是卖钱。她们都是在家里的,所以更无所归。她们是终年劳碌的,所以没有什么放假。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85)周作人:《谈谈谈诗经》,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第146—148,146—147,147页。
例三,胡适强调《嘒彼小星》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说道:“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86)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第5卷,第426—427,431,431页。周作人嘲笑道:
“嘒彼小星”一诗,胡先生说“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引《老残游记》里山东有窑子送铺盖上店为证。我把《小星》二章读过好几遍,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虽然也不能说这是一定描写什么的。有许多东西为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只好阙疑。我想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定实这是讲什么,譬如《古诗十九首》,我们读时何尝穿求,为何对于《诗经》特别不肯放松,这岂不是还中着传统之毒么?(87)周作人:《谈谈谈诗经》,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第148,148页。
在周作人看来,胡适对《诗经》的诠释是“尽欲甚解”,过于“武断”,因为“一人的专制与多数的专制等是一专制。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周作人引用英国民间故事中“狐先生”(Mr.Fox)榜门的文句,警示道:“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88)周作人:《谈谈谈诗经》,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第148,148页。
顾颉刚比胡适更激烈,他肆无忌惮地从《诗经》中寻求与现代社会学契合的历史材料,认为《葛屢》“本是刺上流社会的阔绰,女工的苦恼”(89)顾颉刚:《读诗随笔》,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233页。。特别是他对《野有死麕》的解读尤为大胆:
第一章说吉士诱怀春之女。第二章说“有女如玉”。到第三章说道:“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帨,是佩在身上的巾。古人身上佩的东西很多,所以诗经中有“佩玉锵锵”,“杂佩以增之”的话。“脱脱”,是缓慢。“感”,是摇动。“尨”,是狗。这三句的意思,是:“你慢慢儿的来,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不要使得狗叫(因为它听见了声音)。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90)顾颉刚:《野有死麕》,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279页。
顾颉刚以“性的满足”分析《野有死麕》。这让一向大胆的胡适都觉得有些不妥。胡适指出“‘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否则很容易误解成“肉蒲团里说的‘干哑事’”。但胡适赞同《野有死麕》是描写怀春之女被诱惑的诗:“野有死麕一诗最有社会学上的意味。初民社会中,男子求婚于女子,往往猎取野兽,献于女子。女子若收其所献,即是允许的表示。此俗至今犹存于亚洲美洲的一部分民族之中。此诗第一第二章说那用白茅包着的死鹿,正是吉士诱佳人的贽礼也。”(91)胡适:《论野有死麕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卷,第281页。
周作人指责顾颉刚与胡适对《野有死麕》的分析 “故意穿凿,反失原来浅显之意”,讽刺道:
他(胡适)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但是死鹿白茅究竟什么意思,与这私情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能臆说,只是觉得旧说都不很对而已。(92)周作人:《岂明先生与平伯书》,顾颉刚编:《古史辨》第3卷,第286页。
胡适与周作人之间关于《诗经》的分歧,背后是“五四”学人内部文学观之间的差异。在胡适看来,“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93)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集》第2卷,第106页。。文学承载着不同时期人的不同情感,那么它就是时代变迁中的史料,后人可通过现代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来剖析不同时期的文学,以求论证不同时代人们所共同的情感状态以及社会生活状况。但周作人认为:
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他在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9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自己的园地》,第20页。
为此,周作人不赞同过度地用现代社会学等角度来阐释文学:“研究文学的人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能够分析文学的成分,探讨时代的背景,个人的生活与心理的动因,成为极精密的研究,唯在文艺本体的赏鉴,还不得不求诸一己的心,便是受过科学洗礼而仍无束缚的情感,不是科学知识自己。”(9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自己的园地》,第41—42页。在周作人看来,胡适应用现代科学知识的解读方法一旦过度,很容易导致“武断臆测”,继而做出违背历史语境的“新解”,使文学成为现代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的附庸。故而阅读文学作品时需要“不求甚解”,不能篇篇咬定“这是讲什么”,否则会丧失“文意”。
“五四”学人内部关于文学的争议,至今影响着当下的文学评论界。一些学者延续胡适的思路,认为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记载,应从现代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来认识,以求从文学中找寻出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材料,以挖掘文学中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意蕴。而另一些学者则受周作人的启发,认为“文学是个人的”,倡导“不求甚解”,反对在文学中过度地寻求“伦理”“政治”“历史”等,并认为如果过于强调文学的“史料价值”,会让“文学”丧失其“本性”。
结 语
关于《诗经》的现代解释,与“五四”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胡适等通过重释《诗经》,期望瓦解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确立“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新文学观。在重释时,“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其差异性。
由此可看出,新文学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它们既决绝地否定“吃人”的伦理道德,却又努力地发掘传统的潜力,使其成为新文学的重要支撑。新文学要确立其自身的地位,不仅要建设自己的新文学观,拥有异于传统的新作品,而且也需要对中国传统进行重新估量,以求在传统中找寻与自己契合的历史资源。胡适认为:“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9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这表示,从传统的脉络中确认新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更具有历史的说服力与时代的感召力。所以,“五四”学人在借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时,得到了很多青年与知识分子的认同,继而形成了一股变革文学观念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