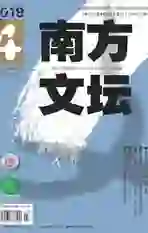“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
2019-09-17易彬
易彬
对现当代作家的研究而言,档案材料往往有着独特的效应,但它的获取却始终是一大难题。此前,我在2010年版《穆旦年谱》中较多采信了穆旦生前任职单位的档案馆所藏的一批档案材料。当时有一个最直观的判断,尽管“八卷本《穆旦译文集》和两卷本《穆旦诗文集》已出版,亦有专门的年谱和传记,穆旦写作和发表的主要格局已定”,但是,“穆旦的生平材料实在太少,毫不夸张地说,穆旦生平之中的若干重要转折点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最终破解这一难题的,就是这批档案材料①。当时是尽可能穷尽地利用了该档案馆的材料,且以为这类材料只会见于档案馆一类机构,未曾料到先是2015—2016年间,坊间出现了两批穆旦及夫人周与良留学归来之初的材料,它们与原有档案略有重叠,更多的则是新见材料②。近期又有多批次、更大量的此类材料流出。这些材料原本亦是应归入相关档案卷宗的,不知何故流散书肆之间。
大致说来,坊间新见穆旦材料,以交待材料为多,包括个人交待材料和外调类材料,亦有少量的相关部门或人士所写的材料。从各材料的写作时间来看,此前所披露的两类材料时间跨度为1953年年初至1965年年底,而本文所披露的材料,虽然绝大部分都是1968—1969这两年间的,但总的时间跨度为1965年年底至1973年间,两者在时间上也可说是前后衔接,正可谓全新的材料。
1968年12月8日,穆旦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周多,外调较多。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对这件事,我所抱的态度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尽自己所知的一切,向党向人民做交待。过去已犯的罪,有多少就交待多少,不夸大也不缩小。”③这里所谓“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正可涵盖此一阶段穆旦的境况。“历史”的“重新审查”,既会涉及一些新的人物和事实,可供新的作家年谱采信;而各色思想总结、检讨,即如当时日记里较多涉及的关于“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的自我辩解,直接外化了“审查”的效应,这些也值得深入的估量。
一、个人交待材料
新见穆旦个人交待材料有十种,其中,完整披露的有八种:
1966年1月,《学习主席思想,加紧改造自己》,12页。
1968年5月1日,《思想检查》,3页。
1968年5月27日,《最近的学习和劳动感想》,1页。
1968年10月2日,《我的罪行交待》,8页。
1968年10月9日,《交待问题》,1页。
1968年10月10日,《思想小结》,仅见第1页,未见全件。
1969年1月,《清算我的“民主个人主义”教育及其余毒,彻底改造世界观》,12页。
1969年3月29日,《全面交待我的罪行》,5页。
1971年12月,《一年总结》,仅见第1页,未见全件。
1973年7月20日,《外语人员调查表》,2页(正反两面)。
这些材料中,《外语人员调查表》是由天津市有关部门下发的正式表格,主要就是个人基本情况、语种及翻译能力、简历等。实际填写的内容很简略,基本没有思想检讨的内容。其中如“本人参加过何种反动党、团、军队及反动会道门、是否已结论”板块,填有“参加过伪入缅远征军和伪207师,已做结论”。“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板块,填有“1959-61受管制”。表格最后几栏为“本单位领导的意见”“上级干部部门意见”“市有关部门审查意见”,均为空白。
其他各材料所用的纸张,仅有少数为专门的材料用纸,多是普通白纸,也有一些为稿纸——部分稿纸上端印有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白纸上所写材料也有几种开篇即抄录有语录,如“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最高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等等。
根据1968年9月30日南开大学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对于查良铮个人的审查意见,本年4月29日,穆旦被“革命群众”送到专政小组进行劳改,至9月20日,由宣传队接管。由此可知,写于1968年5月初和月底的《思想检查》和5月底的《最近的学习和劳动感想》,也就是穆旦在此次劳改初期所作检查。两份材料的篇幅有限,看起来彼时的审查压力尚不太大。
《思想检查》是当天学习了“几段最高指示”之后所写的,这些指示“句句是真理,深深击中了自己的心深处,因为自己过去的罪恶历史,都可以在主席的光辉的思想照耀下看得清清楚楚,无一能逃开主席所指出的历史发展规律”。材料谈到“要认清阶级斗争的大局”——“认清大局,选择今后的道路,这对自己是最重要的事;对改造自己,这的确是关键问题”。《最近的学习和劳动感想》也是从改造说起,“对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党和革命人民是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以便不再为害社会主义。因为地富反坏右,就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如不改造好,就是人民的绊脚石。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有迫切自我改造的要求”。接下来则是展现了由权威言论而“联想”到自己的“罪行”的自我批判思路:“自己过去抱有嚴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具体表现为‘向上爬‘成名成家‘享乐主义等。最近学习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正是批判了这种世界观,对自己很有教育意义。因此我联想到,为什么自己要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这正是因为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是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
这两份材料的基本路数基本上都是对于思想问题的反复追诘,而少有事实的陈述——前者虽然触及新中国成立前“给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服务”、回国后的“外文系事件”④等“事实”,但非常粗略。类似的处理方法,在篇幅更大、主题被明确标示出来的《学习主席思想,加紧改造自己》《清算我的“民主个人主义”教育及其余毒,彻底改造世界观》之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前者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方面,即从主席著作的学习中,“吸取了自觉改造自己的力量”“认识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认识到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材料是1966年1月——“新的一年”之际所写,带有新年发愿的意味,即如结语所示:“对自己的改造当然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既有些微成绩,也有很大的不足。自己决心在新的一年中,努力做到以主席思想挂帅,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跟上形势的需要,做好工作,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周身环境都很有利于自我改造,我相信在党的关怀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自己定能取得自我改造的迅速而彻底的胜利。”
后者是“在学习主席思想的高潮中,自己带着这一问题,重新学习毛选第四卷的最终几篇光辉著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之后所写的。材料指出,自己“正是主席著作中所指的大小的‘新式的知识分子之一”,“自己算不算民主个人主义者,虽然不太清楚(因为主席把这种人看作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有所区别的),但是从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熟悉的思想体系看,正是属于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范畴,把自己的世界观标上‘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标签,大约是很合适的。既然如此,主席的这几篇著作对自己就有了针对性”。此材料即是“经过反复学习和思索,通过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想比较全面地清除一下自己所受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教育和思想余毒,给自己的思想来一个大破大立,以加速自己的改造”——“把自己所接受的‘民主個人主义教育和世界观,分列为五点,加以批判”。首先,谈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之所以迷惑过我”的三个方面:“(一)迷信选举制”,“(二)迷信民主是目的”,“(三)迷信个人对社会的抗议”;其次,“批判自己所受的个人主义教育的两点影响”:“(四)迷信个人英雄主义”,“(五)迷信个人自由”。通篇写下来,也是不断检讨思想、深挖病根的写法,而基本上全无“事实”的交待。
也有几种材料如《我的罪行交待》《全面交待我的罪行》,是对于个人“罪行”的“全面交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事实”。稍早的《我的罪行交待》先是概述了从出生到报名参加入缅甸的远征军的情形,然后分十一段交待“职业和罪行事实”。差不多半年之后的《全面交待我的罪行》,先是抄录了两条“最高指示”——与上文提到的语录不同的是,这里明确涉及对于“反革命”的处理问题,其第一条为:“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材料开头则叙及背景:“参加3·28落实政策大会后,在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政策感召下,自己作为一个对人民犯有许多严重罪行的人,感到必须全面彻底地交待自己的罪行,以求得人民的宽大。并在此一基础上,争取重新做人。”接下来,先是简略谈到家庭出生,然后从十个方面“分别交待”“自己过去对党对人民所犯的罪行”。
两相比照,材料所交待“罪行”的起止时间略有差异:前者始于“在伪入缅远征军第五军中作少校翻译”时期,止于“回国后”;后者始于“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期”,止于“翻译外国十九世纪浪漫诗歌”。所交待的“事实”重点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后者对于写作于翻译方面的情况以及回国后的“罪行”做了更多的交待——“1954年的外文系事件”即单独列出。这种差异,或可认为是显示了穆旦对于“事实”的隐瞒,同时,也可能是基于不同的交待主题或现实动因,即如后者对于“外文系事件”的交待,或跟稍早时候——1969年2月7日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位老师所写的揭发材料有关,该材料写在油印的专用“揭发材料表”上,称“外文系事件”、“查良铮是否和巫宁坤等还有联系”等问题,“都是值得审查的”。
穆旦的这批材料较少或者不涉及个人写作的情况,仅有《交待问题》一篇,通篇就是交待写作和翻译方面的情况,该材料篇幅不长,如下:
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的外国文学,喜爱的就是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作品,深中其毒。解放前自己也学写一些诗,出版过“穆旦诗集”,“旗”,(都在1966年交图书馆的革命组织)其中是一些令人难懂的诗,宣扬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和颓废思想。这些诗为极少数的人所欣赏,为广大革命群众所反对。在当时革命形势下看来,我写的那些诗只能瓦解革命斗志,起着极坏的影响。解放后,(1954-57)自己又在翻译工作上介绍了外国十九世纪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其中有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英国诗人拜伦、雪莱等,他们的作品,仍然是资产阶级作品,其中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却不能辨别出来加以批判,反而加以吹捧,1957年就写过一篇文章(“漫谈欧根·奥涅金”,登在“文艺学习”杂志1957年)吹捧普希金。这样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只能起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用。1962-64年我在工余时间还有兴趣翻译些拜伦的诗(稿子已散失),这种盲目的工作使我看到,自己由于出身和教育是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会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自己清楚认识到若不狠狠改造自己,总是要放毒的。过去自己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点也不假,上列事实可以说明。以后若不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若还是在传播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罪上加罪了,因此更感到彻底改造的必要。
纵观穆旦的各类交待材料——包括此前所披露的材料,极少这般对于个人写作和翻译的评价。而诗集“都在1966年交图书馆的革命组织”之语,与其后代的回忆之间,也构成了某种有意味的对照。⑤
除了上述材料之外,还可从2018年11月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第1218号拍品信息获知,还有一批1968年至1971年间的穆旦手写“思想小结”类材料,共十四份四十三页,展示出来的仅为1968年10月10日《思想小结》的第1页和1971年12月所作《一年总结》的第1页,至少在这里,还有四十余页材料可待考察。
二、《新报》相关的外调类材料
前文提到,1968年12月8日,穆旦的日记中有“这一周多,外调较多。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之语。所谓“外调”,今日读者当已是非常陌生。这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术语,即外出调查,指的是在某一运动中,每个单位为了彻底查清本单位某些人员过去的政治历史问题,通过各种线索(包括本人交待材料),专门派人分赴各地,向有关各当事人作进一步深入了解,以掌握更多情况,查清到底有没有隐瞒的罪行。
从坊间新见的这批材料来看,从1965年12月16日所作关于杨淑嘉等人的材料到1969年4月16日所作关于《新报》的材料,标题指向明晰,均属穆旦接受其他单位前来外调时所写的材料。而1968年7月7日所作《交待材料》,实际上也是交待他人的情况,也可归入此列。统合起来,总共计有三十余种。这些外调材料多盖有手印,当是穆旦本人的。因为两类外调材料所涉篇幅较大,这里分而述之。
新见关于《新报》的外调材料达到十八种,数量实可谓不少:
1968年7月16日,《关于刘兰溪》,1页。
1968年10月28日,《关于“新报”》,2页。
1968年12月10日,《关于新报》,1页。
1968年12月23日,《关于沈阳新报》,1页。
1969年1月11日,《关于张金刚》,1页。
1969年2月5日,《关于褚世昌》,3页。
1969年2月5日,《关于傅琴》,2页。
1969年2月8日,《关于徐露放和新报(补充材料)》,1页。
1969年2月11日,《关于陈达夫》,2页。
1969年2月16日,《关于林开
1969年2月23日,《关于王敬宇》,2页。
1969年3月7日,《关于新报》,1页。
1969年3月10日,《关于新报》,1页。
1969年3月22日,《关于新报》,1页。
1969年3月24日,《关于长春新报》,1页。
1969年3月26日,《关于李德怀》,1页。
1969年4月12日,《关于新报》,2页。(说明,此件内容是关于《新报》的,但未见标题,依前例,此处亦以《关于新报》名之)
1969年4月16日,《关于裘海亭》,1页。
《新报》时期是穆旦生平经历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但由于缺乏资料,长期以来语焉不详。这一难题,结合南开大学档案馆所藏档案和当年的《新报》,在总体上已经解决。但从这十八种新材料来看,新议题也不少。
从篇幅看,这批材料基本上都比较简短,实际叙述也有大致的模式:一是介绍《新报》的情况,其中除了一般性的介绍外,还有是否有“特务组织或特务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叙及与某某的交往情况、某某的政治情况,等等。前者往往有更大的篇幅,后者則往往比较简略。不妨以目前所见第一篇此类材料《关于刘兰溪》为例来看:
我开始认识刘兰溪是在沈阳新报馆。那时他做记者,我做总编辑。我记得他初写新闻稿时,不很熟练,我曾给修改一个时期。对他的印象仿佛他是伪207师的复员青年军士兵。现在经过谈话,才知他是在伪207师军报中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对他到新报以前,在207师的活动自己是不知道的,是不认识他的。他在新报期间,仿佛他没有军衔,不拿军队的薪水。这是我凭印象这样说的。因对他没有个人交谊,了解不深,当时他是否确实如此,则不知道了。
我在新报1947年9月被查封后不久,即离开了沈阳,去到北平。离沈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刘兰溪,一至今日,也没有再听说过他。
我任新报总编辑时,不做夜工作,开始时还看看外勤记者的采访稿,以后也不怎么看了。夜晚的编辑工作,由编辑主任邵季平负责(他现在天津红桥区制药厂中教夜校),看最后的大样由徐露放负责。我在报馆中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社论,自己每日写一篇二三百字的“日日谈”,同时看读者来信。在1946—1947年之间的冬季,自己曾被罗又伦(伪207师师长)调到抚顺两三个月,去教他英文。在这期间自己就不管报馆的工作。
我在207师的职务是英文秘书(中校、上校),主要是教教罗又伦的英文。在新报期间,仍是207师的英文秘书,支上校薪水。我从未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或任何特务组织;我不知新报馆中有任何特务组织或特务活动。关于刘兰溪被派到东大搞特务活动,自己是不知道的。
我最后一次看到徐露放,是在1953年初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当时知道了他在北京茶叶公司工作,便写信给他到我家,谈了一次。以后便和他没有任何来往。
王先河是在伪207师中认识的。自己离开新报以后,和他便没有任何来往,也不知他在何处。
刘兰溪在报馆当记者,是很有活动能力,很能采访新闻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特作补充。
这里记有“经过谈话”,其他材料如《关于李德怀》中又有“经过看他的像片和考虑他交待的细节”之语,由此可知当时前来外调的一些情形,如谈话、对方的交待材料和相关物证的呈示、谈话之后所写交待(外调)材料等。
在这批材料中,一些人物和事实被反复谈到,《新报》的构成(分经理部、编辑部和印刷厂),穆旦本人的总编辑身份,董事长罗又伦,社长(或总经理)徐露放,主笔王先河,仅徐、王和自己属于207师的编制,其他雇用人员都没有军衔和军待遇。其他被较多提及的人物还有编辑部主任邵季平、经理朱叔和等。其间,还有几个要点可单独一说。
一是,关于所询问的人物的政治活动、“是否反动党团或特务组织的成员”以及《新报》内“有无反动党团及其他组织的活动”等问题。看起来,这是《新报》外调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话题,各材料均有涉及。纵览之,不管是对于所调查的个人还是《新报》的反动活动,穆旦一开始均表示不知情,同时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参加,此类说法,上述材料中有,其他材料如《关于“新报”》中亦有:“我不知道。我当时未听说过有此事。我自己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及至1969年4月12日的《关于新报》——在“通过多次外调”之后,终于交待出自己当时是被蒙蔽了:“新报内有无反动党团及其他组织的活动,我当时不知道;现在通过多次外调,经人告我,才知道这种活动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