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且行且吟的信仰表达
2019-09-16张秀峰
张秀峰
远古的神话,穿过历史的迷烟,走得缓慢而又固执,然而却并不孤独,作为华夏儿女,我们似乎并不厌烦这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信仰表达。这压根儿就无须刻意谨记,化骨入髓的历史情感已经成为了基因,分明能够感受到那种诗意的、史诗的成长与成熟。对于华夏民族来说,陕北的这块地域就是根之源,地位与住着十二个大神的奥林匹斯山相当,却远比那诸神演绎的希腊神话更亲切、更自然。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载:“黄帝崩,葬桥山”。借助于桥山的风景,朝圣者们只要站在这里就能穿梭时空,先验的想象、人文气场的挟裹和文化移情在我们还没有亲临拜谒之前就开始运转。在这里,景深照彻的是隐喻的历史,无须有过多的言语,仅仅凭依一种因袭的成长体验,古老的神话就已经叙述完整,或行、或站,借助朝圣的眼睛,隐伏于身体中的情怀与遥远传说的主人公们遥相呼应、渐渐凝聚、升腾,直至扩散于全身。那种分明的自豪感,拖拽着我们来来回回地穿梭于时空,时而茫远、时而切近,时而混沌、时而明晰,古老的神话,穿越历史长廊的回音,给予了还活着的我们一个现时的,具有生活与思想景深的视野。
在桥山,人文初祖大殿是拜谒黄帝的主要地方,而由东门进入陵园向左的汉武仙台,潜藏着的,则是遗址与权力之间漫长、深厚且意义深远的关系史。将遥远的文化记忆与现时感知建构起来,成为一种伟大精神的别样凝聚。《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刘彻“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庆祝凯旋、夸耀武功也罢,祭告祖先、祈求长寿成仙也好,总之,于遥远的汉代而言,这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帝王无愧于历史赋予他的那份担当。这并不起眼的平台上,凭想象脑补的祭祀盛况毕竟难掩后续历史更迭背后的辛酸与悲怆,历史在辉煌与没落、精神和文化、和平和社会动荡之间循环往复,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们几乎在这种宿命般的认可之下体会和亲历着史诗般的文化进程,唯独不变的,是那种强大到足以抵御任何空难的民族精神与寻根问祖所衍生出的向心力。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然而又如同蝴蝶效应那样偶然,秦汉之亡如是,隋唐之亡亦如是。至于明清,则已经由内部的纷乱演变为弱肉强食的必然。这是对经验、感情、精神和历史经验的直觉感受,不是对过去作盖棺论定的无情挞伐,而是作为华夏子孙内心真实的震动与反思,毕竟历史还在向前,反思过去,是为了能够在以后的行进中能够走得更好。
桥山巍巍,莽莽苍苍。曾经的丰功伟业演变为驭龙升天的美丽传说,携带着古老的文明在陵园上空萦绕盘旋。抬头向天,黄帝、炎帝和那些曾经为中华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的先人们,仿佛仍在这个聚焦千年灵气的地方,像盘旋的飞鸟,满怀悲悯地俯视着我们。由他发端,开枝、散叶,华夏民族逐渐壮大。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谶语犹如无解的劳伦斯魔咒。在这里,无论是上古传说还是现今真实的生活,作为生命的个体,只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被动赋予的位置,谁也不是民族整体的发言人,自然也无须为族群整体背书,然而对于圣人来说,族群的发展是个人意愿的投影,“公”与“私”之间因诉求一致而和谐,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和炎帝、伐蚩尤,“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化野分疆治,德行明法典。根深方能叶茂,其后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到如今。所以,司马迁由衷地称赞他说:“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惟有这样,民众才头脑清楚,不致迷信,神也不至于羼杂着人的阴谋诡计,才显出他的高超纯洁。他们各尽自己的职分,各治自己的事情。人对神恭敬不敢亵渎,神对人只是普遍的降福,赐给他们丰收的五谷,人对神只要拿祭品供献。神是向全人类讲话,单个的人不能分别的祈求。遍观世界,远古的神话从未能如此贴近世俗的生活,或者可以这样说,现在活着的我们,就是远古黄帝神话的延续,它的意义已经不只局限于桥山一隅,已经成为充满整个中华大地、世界华人心中的具体的历史体验与记忆,一种独有的精神特质。历时久远而生生不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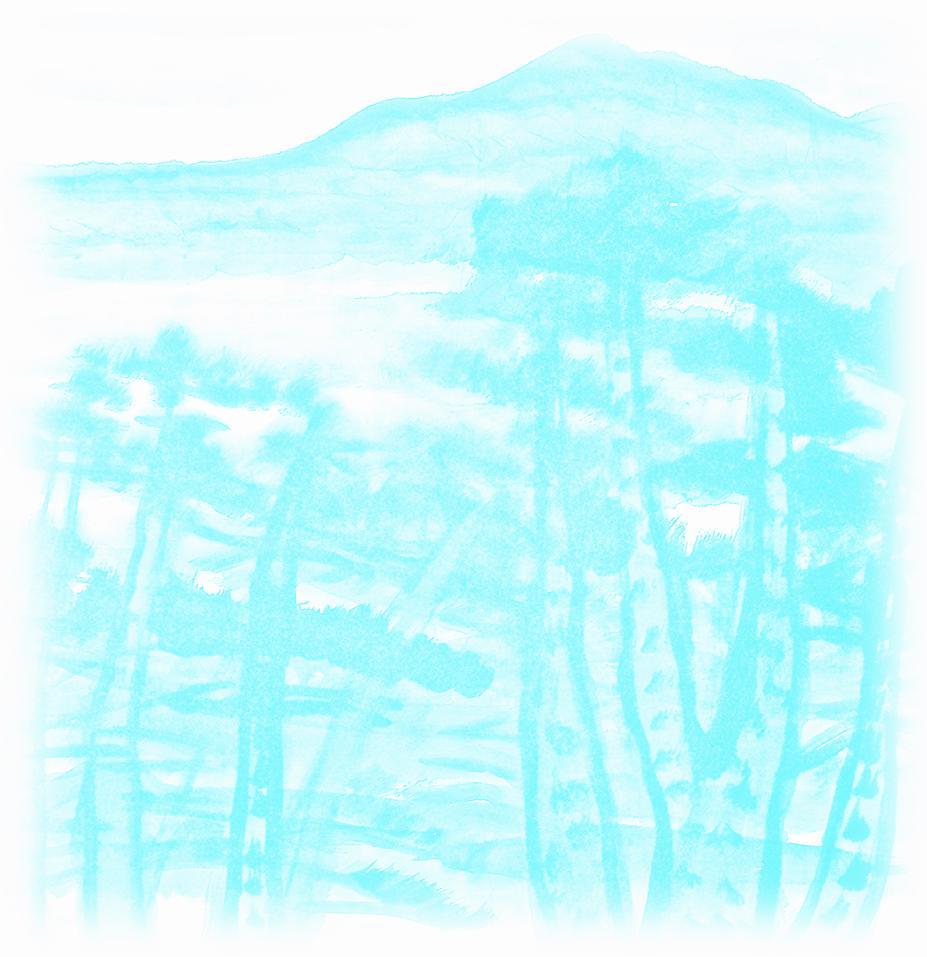
正像托马斯·奥弗伯里所说:“一个除了荣耀的祖先而一无所有的人,就像一个土豆唯一适合他的地方就泥地下面”。与托马斯·奥弗伯里一样,约瑟夫·欧纳斯特·勒南则从实证主义出发,发出“现代人身上总有其祖先的种种烙印”的论断。是啊,在我们面对神话一律的歌颂与历史遗迹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是民族自信的终极体现。文学家们将更多的眼光放在神话的延续与传承形式上,力求完美地诠释神话内在的教育功能。更多的人则不同,他们只是想知道自己的根本所在。那些存在千年的与神话有关的物什就会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散发出温情,重获激活我们现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愿望与轩辕黄帝“修德振兵”之间的血脉密码,古今一体,心意相通。
陵园中的黄帝手植柏,虽历千年而精神犹壮。年轮随历史演进而层层叠加,千百年哟,可不是什么酣酣一梦,睁眼已是沧海桑田!我相信她永远都是清醒的,因为清醒,所以要承受更大的苦痛;因为历练,从而更能够明白奋起的必要。当年的她未必粗壮,风吹雨打、经寒历暑,一路挺过来,一活就活成了千年的模样,成为华夏子孙膜拜的对象。不说别的,仅孜孜以进、不屈不挠的那股精气神就很值得我们景仰,更别说还有黄帝所给予她的人文情怀在。
行走于陕北这片土地上,所有的赞美都统统失语。说什么好呢?伟大、神奇、抑或是震撼?不,不,都太苍白了!任你有多少华丽的词藻,都只能在心头奔涌,只要还能说出来,就已经差着万儿八千的火候,能做的,就唯有走、不动声色地走。
如果说陕北是一本厚重的书,黄陵,则是这本书扉页之上的寥寥序言。当真是微言大义!千百年来,黄陵就以一座山的名义端坐于此。日升月落,千古不变,将精华集萃,赋予了陕北厚重的精神。读懂了她,也就基本读懂了陕北。然而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秦皇汉武没有做到,唐宗宋祖也没有做到。伟人毛泽东倒是有所领悟,带领红军过雪山草地,奔波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并由此开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十三年的时间里,以他的睿智,未必没有参详出丁点这其中的奥秘,然而绝不可能悟透。近根而聚气,正如修剪對于树木,削枝散叶并不是戗害、不是摧残,而是作为积蓄生命原力、以图更加肆意蓬勃的必要。也正因为如此,在离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能够由衷地说一句:“陕北是个好地方,地好,人更好。”
在古人用神话与历史勾画着美德所表征的轩辕黄帝的丰功伟绩中,陕北这块神秘而又古老的土地,更多的演绎了苦难与灾祸,无论是何朝何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都是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出现,更多的时候,人们将过多的目光投向秀美的江南,能够让人们记起这里的,除了战祸,就是天灾。陕北,就是一首诗,朗诵者在陕北,倾听者却遍布四海之内。
“赫奕我祖,人文之光。肇造吾华,大国泱泱。勋绩彪炳兮,懿徳与日月同辉;惠泽绵延兮,福祚并江河共长。追缅鸿烈,子孙用光志业;缵承远祖,神州崛起东方。
……
桥山巍峨,沮水流长。虔告吾祖,恭荐心香。钟鼓锵锵,百花吐芳,大礼告成,伏惟尚飨!”
这是2016年清明时节,万人公祭轩辕黄帝时的祭文。每一次的朝圣,都是在将黄帝这一神化的人文初祖向生活进行了还原,隔着神话的迷雾与历史的距离,华夏儿女寻根问祖,不仅是从神话向生活的还原,也是对全体华夏民族共性的还原。
我曾為自己不能像老荷马那样为他生活的土地而歌唱感到羞愧,因为缺乏诗人的气质,我不能为我的祖先歌唱,尽管他曾创造的文明成为比希腊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滥觞。《荷马史诗》体现的是一种穿越了历史时空的诗性智慧。对希腊诸神们作了向生活世界还原式的重新书写。而我却不能,除了偶尔的到访,在桥山下走一走,感受那浩浩文明之风的荡涤,实在无法再做什么,心里激情鼓荡却无法说出来,那种感觉实在难过,悲哀得要命,几近于绝望。
在陕北高原行走的时候,我们要具备超越普通观光者的眼界与高度,将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与历史、人文、遍布于沟山峁梁的历史遗迹,以及那些与传说有关的历史人物串联起来,向历史寻求生活世界最为真实的还原。陕北人笃信神灵,这不同于相对纯粹和固定神祇膜拜的三大宗教。因为长期多民族杂居融合,民俗宗教信仰呈现多样化融合的显著特征——没有非常严格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完善的宗教组织,崇拜的神灵多样且都比较原始,多为“自然神”或者“偶像神”。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自然成为陕北人最为信奉的“偶像神”。
作为中华文明的观光者,我愿意作一个时间痕迹的解读者,或者说,就是历史的侦探,我不愿意过多地掺和到历史的本真中去,将个人意愿强行赋予它,我只是作一个历史与现实的缝合者,力求将神话与生活的距离拉近了再拉近,借助桥山,借助那些由此演绎的丰富的神话传说来凝聚人心,尽最大可能扩展自我,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闯过精神的辽阔疆域。
这,就是历史,历史站在眼前。夕阳映着山野,这轮照古又照今的日头,它一直没有走远。一切都没有走远。
当我离开黄帝陵,于车上回望桥山的时候,蓦然发现:时光让历史沉寂到黑暗中去,却把桥山隆升成为精神的高地,目的是让山水给时光做个见证:历史不是僵化、冰冷的,历史是充满温情的。人类固然渺小,然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桥山已经存在了五千多年了,依然是那么的祥和、那么的谦逊,我们的祖先尚且如此,我们又为什么不静心反思,放下那些浮华的噱头,静静沉下来,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那座山,那个让我敬仰的圣地,在与我深情的对视当中渐行渐远。我不知道,我且行且吟的信仰表达,能否引发她的共鸣,把历劫万年的心语,传达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