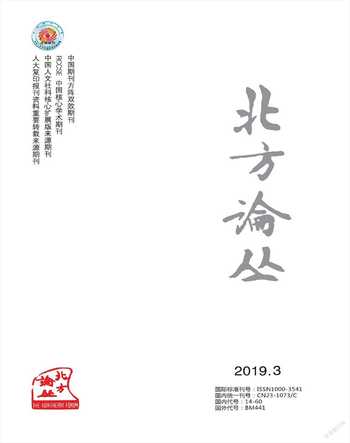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
2019-09-10李海涛
李海涛
[摘要]人工智能激起了人类的关注和自我怀疑,人们在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和价值边界上产生困惑,也在科技伦理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因此,在科技上充分开发人工智能的同时,哲学反思尤其对人工智能的本质和价值的反思是必要的。作为根据和参照,智能首先需要反思。智能是生命主动适应外在环境的自然性生成,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性生成。智能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不是简单的推理能力,而是统一“知、情、意”的直觉能力。人工智能在形式上是物理运动,完全就有别于智能的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在本质上是智能的模仿、数理逻辑规则的物质化。人工智能没有替代或超越智能的可能,它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具有社会性,更加没有主体地位。
[关键词]智能;人工智能;逻辑;直觉;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137—06
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项科学或技术能够像人工智能一样,激起人们的热切关注、复杂情感甚至自我怀疑,仿佛预言着人类的自由和未来将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尽管很少有人像霍金或加里斯那样预言人工智能是人类的挑战者和终结者,但许多人也认可人工智能的超人能力和社会性,恰好这两个方面对人类而言具有毁灭性。显然,人们的苦恼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二是人工智能的价值边界。当然,它们是硬币的两面,能力边界在实践上决定了价值边界,价值边界则在理论上影响着能力边界。与诸多困惑和分歧的生成一样,人们没有真正反思和直面人工智能的本质,观点基本上停留于直观化意见或情绪性判断。在思维逻辑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扰乱了思维,内涵失范的概念制造了分歧。在思维方法上,目的与规律、主观与客观的不匹配,既可能造成夜郎自大,也可能造成妄自菲薄,于是,伪命题应动而生,伪命题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同样只会生产困惑和分歧,坚持的人却因暗合主观的抽象目的而暗自得意。所以,我们应该厘清人工智能的概念,从人工智能的本质出发去生发我们的判断,从理论上触摸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和价值边界。
一、什么是智能
无论是中文的“人工智能”还是英文的ArtificialIntelligence都是一个偏正词组,人工(artificial)是修饰语,中心词则是智能(intelligence)。所以,首先需要清晰智能的概念,然后才可能清晰人工智能的概念。
在汉语语境当中,智与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智就是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能就是行动的能力或才干,“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智与能联合起来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意识领域,智能就可以理解为认知能力与决策能力。
古希腊荷马时期的“智”近似于汉语语境的“智能”,泛指精熟于某种知识或技能,优秀的雕刻匠、造船工、战车驭手都被称为“智者”。轴心时期的“智”才狭义地指脑力劳动,主要指哲学、科学、艺术或政治等脑力劳动,“七贤”就是“七个智者”的意思。到了智者学派,他们以掌握知识和论辩技巧为“智”,于是,“智”脱离了对象的具体性,抽象为一般性的思维能力。斯多葛学派用“理性”替代“智”对思维的表征,此时,理性与智都在强调思维的认知功能。在斯多葛学派之前,毕达哥拉就用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开辟了一条理性主义道路。巴门尼德规定了理性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一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感性认识就不被肯定为“知识”而被定义为“意见”。苏格拉底从内容和原则上确立了理性主义,树立了理性的权威。他断言,只有智慧能够把握真实的存在
(柏拉图称之为“理念”),它是灵魂的根本属性,有别于肉体的意志和欲望。理性主义从此被注人新的含义,即一种方法论的内涵、一种工具主义的内涵。斯多葛学派将理念称为理性,作为人及一切存在的存在根据和存在规范,也将智慧称为理性,并且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理性,同时,也只有神、天使和人拥有理性,于是,理性不但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和主体性地位。斯多葛学派为理性主义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旨趣和思维原则,并为其后的理性主义坚守,2000多年后的布兰顿表达出几乎完全一致的思想:“用我们的理性和理解能力而把我们从万事万物中分辨出来,表达了这样一种承诺:作为一系列特征而把我们区分出来的,是智识(sapience)而非感知(sentience)。我们与非语言性动物(例如猫)一样,都具有感知能力,即在清醒的意义上有所意识的能……而智识涉及的是理解或智力,而非反应性或兴奋能力。”2在笛卡尔那里,理性不但与情感、意志等严格分开,而且在方法论上等同于“分析”,于是,理性就成为对“是”与“否”的判断力,苏格拉底那里流传下来的“理性即推理”的思想理路不再需要含蓄地表达了。弗雷格和罗素则完成理性主义向逻辑主义的最终转变,世界被定义为逻辑的世界,思想是逻辑图像,“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最终,理性等价于逻辑运算,并成为强人工智能的思想根据。由此能否得出“智能=逻辑运算”?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盖格瑞泽的适应行为和认知科学理论,生命行为就是对环境的适应而且是主动的适应,尤其是人的行为。在主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人与环境交互式否定与推动,人的认知能力得以生成和发展,同时,人的实践能力也得以生成和发展。通过人的自我否定,认知能力从表象现象深人到建构本质,从感性认知发展到理性思维,积极建立和积累一般性、普遍性的认识,为解决特殊问题:尤其是可能出现的当下问题提供一般性的经验和原则。可见,认知是决策的前提,并以决策为目的。同时,学习是提高认知能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最为高效的手段。现实的个人当然可以在个体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和新的知识即“通过反应的结果所进行的学习”(班杜拉),更多的学习内容却是在社会生活中,以非遗传的方式在同代和代际那里传播的间接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即“通过示范所进行的学习”(班杜拉)。知识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智能行为的基础,智能不再局限于感性经验的累积、分析和抽象的能力,更加上升为知识搜索的能力和寻找满意解的能力,实现了智能的再一次的质的飞跃。因此,尽管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智能有着千差万别的理解,但却达成以下共识:智能所表征的能力不仅限于认知功能,还有决策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就是说,智能≠逻辑运算,智能>>……>邏辑运算,准确地说,智能远远、远远大于逻辑运算。
智能可以看作生命进化最后环节的产物,是具有最高意义的生命行为,是生命解决生活问题的意识能力。根据对人脑已有的认识,结合智能的外在表现,我们可以确认,智能核心在于思维,它会构建起关于对象规律和本质的抽象性认知。智能来自大脑的思维活动,也可以看作大脑从事思维活动的能力。不过,智的全部能力却根据智能对自身存在的感知和认知,即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智能的根据在于自我意识,尤其在于为保证其存在的生命冲动或者说欲望及其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主体性意识。同时,智能根据的自我意识不但表现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而且表现为类的自我意识,并被上升为道德范畴,从而成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意识能力和意识内容。
由于人的社会性,智能当然就是社会性行为。加德纳即把智能定义为在某种社会、文化环境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有效产品既有物理产品,也有非物理产品,那么,智能的对象也就既有物理对象也有非物理对象。苏格拉底把“智”上升为对“善”的形上把握,并赋予其道德和社会意义。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是道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佛教的“智”,指人们普遍具有的辨认事物、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或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多元结构的智能的各个维度并不是独立的或孤立的,因为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一个维度的独立性或特殊性都不在于其自身而决定于当下的问题。斯皮尔曼就将智力因素分为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并声称是G因素而非S因素决定智力的水平。
我们之所以把智能看作对“是”与“否”的判断力,其根据在于我们把意识分解为认知、情感、意志等三个方面,并把它们隔离开来。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在分析思维对象的各个侧面或各个要素上是有效的,它适应了我们有限的思维能力和刻板的语言规则,但所谓认识是整体性认识,而整体总是不小于部分的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一个对象,并非为了清晰它的现象,而是为了把握它对于“我”或者说对于实践的价值,并以此生成思维的意向性。如果抛开想象力、情感、意志等被分离出去的意识形式,我们不可能生成意向性,不可能理解对象的意义,即不可能把握对象。当这些方面或要素重新复合起来回归对象本身时,“总和”从来不会等于认知、情感、意志的物理相加。总之,没有无知无情的“意”,也没有无知无意的“情”,更不会有无情无意的“知”,任何意识行为都只能是知、情、意统一的意识行为。
“理性为原理之能力”,从有条件追溯无条件。即使我们形而上学地分离出认知功能,并把它理解为智能或者说智力,那么智力既会表现为对量的识别,也会表现为对质的认识,准确地讲,智力表现为认知对象的质与量的统一在思维中的重构。我们之所以说“重构”,是因为思维材料收集于认知对象对感官的显现,而思维对材料的处理总是基于思维的能动性,因此,认识不是“再现”或“再建”,而是主体的“重构”即对象性认识。思维的重构当然会以思维的材料为基础,但思维重构的目的却是对意义的发掘。那么,无论理性的对象还是理性的过程,一定都渗透了人的主体性、充盈着人的能动性。没有了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情感、意志等所谓非理性意识形式,理性也就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和动力,“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因此,理性不会是简单的推理能力,即使它经常表现出对推理的偏好,因为意义不会全部涵盖于逻辑,而会更多地延展在逻辑之外;相反,智能、思维、理性只能是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至少以统一认知、情感、意志为必要条件。因此说,如果我们把理性回归为原理的能力,那么直觉就是最高的理性。如果我们把理性界定为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智能在思维方式上,就应该以理性为环节并实现对理性的超越即直觉。智能以直觉为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否定工具理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假设,也就有可能具有可错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认识世界的两次飞跃、实现改造世界的根本飞跃。人正是依靠直觉思维能力,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
在人工智能的定义中,麦卡锡的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接受:人工智能就是要让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就像是人所表现出的智能行为一样。“看起来像”就明确了“不是”,机器的智能不是真正的智能,或者说,不过是一种隐喻而已。人为了自己“偷懒”的需要,将连续的机器动作链接在一起,组装成一个机器“黑箱”,就像洗衣机一样。人类把劳动从若干分解的操作动作简化为一个命令输人,然后就可以静待取出干净的衣物,而无须在过程中多次介人机器的运作。利用机器,操作者可以在过程中置身事外,于是,我们说洗衣机是智能的,因为我们既减少了自己的体力劳动,也减少了自己的脑力劳动,仿佛古代或中世纪对奴隶等“他者”的驱使和奴役。
这样看来,人工智能的修饰语“人工的(artificial)”,首先,申明了人工智能作为创造物的本质地位,是社会实践的工具和产物即“非天然的”;其次,相当于古汉语当中的“伪”即“假”,“假”并非“虚假”“不真实”,而是“代理”“借用”或者“非原本”“非本真”。人工智能就是对智能的模仿,准确地说,对智能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过程的模仿,但模仿只能是赝品和A货,智能与人工智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人工智能没有生命冲动,也就没有欲望,更没有自我意识,所以,也就没有自主进化、独立发展的能力,只可能发生数据的倍增和公式的卷积。人工智能全部“行为”限定于操作者设定的动作,既不会超出也不会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变,它连“自己”的概念(准确地说,“自己”这个概念的意义)都没有。没有自我意识,也就没有与环境互动的欲望,当然也不存在与环境互动的可能,只有根据预定程序的对输人数据的逻辑运算。如果说智能是人的主体属性,那么人工智能则是人的主体意志的体现。人工智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结果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既没有本体论意义,更不具有主体性。因此,人工智能也就没有社会性。人工智能与手机等信息终端一样,仅仅是社会主体交往的物理中介。一个具有表情等社交能力的机器人,为了良好的人机互动,智慧代理人也需要表现出情绪来,至少它必须出现礼貌地和人类打交道,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一种人工设定,而不是自觉的主体性行为。由于社会主体之间(即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在”,人工智能在空间上突显出在交流中的在场,于是被社会主体误认作交流对象。人工智能不是社会交往的主体,社会机器人或者是一个虚概念,或者是一个隐喻。
有人提出,弱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意识,但强人工智能却可以通过极其复杂的程序来推理和解决问题,可以独立思考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甚至有知觉、有自我意识、有生命本能和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系,因此,也可以自我进化,一句话,强人工智能是真正的智能甚至高于生命智能的新智能。“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计算机不仅是用来研究人的思维的一种工具;相反,只要运行适当的程序,计算机本身就是有思维的”。也就是说,机器不再“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而是“同”人一样思考、“同”人一样行动,并且是理性地思考、理性地行动,这里“行动”应理解为采取行动或制定行动的决策,而不是肢体动作。所谓真正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强人工智能,且不要说它在哲学意义上的虚无,即使在科技上也不可能,可以说,智能的人工智能完全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理想甚至幻想之上。
以现在的思维科学水平,我们谈论智能时应该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人类自认为最为成熟的物理学“到现在为止研究过其微观结构的物质很可能只是宇宙中物质的小部分(5%左右)。而绝大部分物质的本性还或多或少地停留在理论推测之中”。我们对智能的认识基本局限于外部现象,根本没有真正认识智能的本质、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可以说,仍在管中窥豹,坐井观天,其中充满了猜测和臆想。因此,我们没有能力为智能设定能力边界,更没有能力谈及模仿。人脑工作过程的确有生物电现象,但仅凭此一点就把智能还原为物理电运动非常牵强和荒诞,更何况把智能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还原为电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强人工智能论至少同意以下的观点:人不过是一台有灵魂的机器,大脑本身只是一台机器。他们只是重申了拉美特里的思想。拉美特里为人类从上帝那里争取自由和主体地位起到重要作用,但他的唯物论是机械主义的唯物论、物理主义的一元论,否认不同运动之间的质的差异,无视物理运动上升到生命运动后运动所发生的质的跃迁。“人是机器”把生命运动还原成物理运动,完全混淆了生命运动与物理运动。智能与人工智能存在质的不同,智能存在和体现于人内在的精神生活,人工智能却仅停留于机器外在的部件运转。
强人工智能论坚持逻辑主义原则,把情感和意志等所谓非理性意识形式排除在思维之外,智能被狹义地定义为逻辑运算能力,即大脑被简化为生物的信息处理器。然后,裁定了它的逆命题的正确,如果一台机器可以处理信息,它就拥有了思维。问题在于,思维不是纯粹的信息编码,推理和决策同样不是逻辑运算,它们的确有信息编码过程、逻辑运算过程,但这些过程是为意义服务的,而且是在意义的条件下完成的。塞尔认为,意向性是一种自然或生物现象,是自然生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中文屋试验证明,机器可以运行特定程序处理编码形式的信息,给出一个智能的印象,但它们无法真正地理解接收到的信息。真正的思维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统一,它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且是在想象和创造中处理信息、理解信息、做出推理、做出决策。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模仿式地输人输出过程,而完全没有意向性,它都没有可能通过一般性的图灵测试。
强人工智能理论把智力设定为纯粹的逻辑推理能力,纽厄尔、西门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智能是对符号的操作,最原始的符号对应于物理客体。符号假说奠定了强人工智能论的理论基础,但完全颠倒了智能与逻辑的关系。思维为有效地把握现象、积累经验,建构起对象世界,并无限地从具体中抽象出所谓的普遍和一般也就是广义的逻辑。逻辑是思维的产物,思維建构了逻辑。操作符号的确是智的能力,而智能不单纯是符号运算;操作符号是评价智力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是充分条件。而且逻辑并非对象的普遍和一般,而是思维以注意到的对象的特征为变量建立起来的抽象的模型,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正确地反映对象,而在于有效地实践。因此,即使智能的逻辑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符号的操作,但是,它既不对应于物理客体,也不会体现为永恒,而是对应于实践客体,并处于无限地试错当中。人工智能在认识论上建立在表征理论之上,在本体论上是逻辑的实体化。人工智能以表征符号为数据,以电运动形式实现的以物理实物为介质的逻辑运算,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人工智能活动,包括机器所具有的自动控制能力和根据环境自我调节到能力或者应激性等,只能按照预先设定的确定性和必然性运行,即使模糊判断、概率程序、卷积运算、监督学习也不过是设定程序的运行和固定公式的计算。
机器的“智能”必然性地被必然性约束在一个由既定的封闭空间——基础算法不可突破,机器也无法突破,因此,人工智能拒绝错误。从本质上说,所谓错误就是对现有逻辑的破坏,而否定旧逻辑正是建立新逻辑的必要条件,正如布兰顿所说:“错误经历就是实现真理的过程。’无论学习、创造和认知都是旧逻辑的否定和新逻辑的建立。可见,人工智能不可能拥有学习能力,也不可能拥有想象力,当然也就不可能拥有创造力,当然,学习力、想象力、创造力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人工智能那里,程序可以无限运行和自我生成,不过,全部的运算都是量的扩张与叠加,因此,任何质的发展和创造都被严格地排除。深蓝可以让卡斯帕罗夫认输、阿尔法狗可以让李世石投子,但它们没有胜利,它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胜利和为什么能够胜利。学习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缺失,以及欲望、情感、直觉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工智能只是一台被操控的机器,而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更谈不上自觉。
强人工智能论把智力水平的评价标准设定为信息的存贮能力和计算速度,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必然地依赖于技术能力无限性的假设,也依赖于科学知识无条件性的假设。强人工智能论几乎设定强人工智能机器计算速度为无限快,加里斯认为,至少高于人的思维速度的1024倍。机器之所以有如此高速的计算能力当然在于机器元件的工作速度,加里斯之所以相信机器元件的如此高速在于他对摩尔定律的信仰。尽管被验证了半个多世纪,摩尔定律仍应该被认定为观测或推测的假说,而不是一个物理定律或自然法则。任何物质介质都会有自己的物理极限,物质的这种自然属性严格限定了机器的运行速度和性能,因为任何先进的技术也必须实现于一定的物理实体。摩尔法则一定会崩溃!不仅在技术方面,即使在理论方面,强人工智能的预测都建立在科学理论没有约束条件的无限推论之上,但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一定条件约束的特例。机器的贮存能力和运行速度一定是有限的,尽管我们努力地放大它们,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和理论条件。
三、人工智能的价值边界
人工智能使个人生活发生着深远和更将深远的影响,它可以完成枯燥的重复劳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最大限度地从体力或操作性L作中解放出来。人们因此可以更多更好地从事创造、情感和思想等工作,“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人工智能在形式上模仿着人的智能,在效果上超出人们的预期,以至于激发起人们无限丰富的想象和期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时代的特征便是工具的完善与目标的混乱。”也许资本推动、也许宣传需要、也许人类关怀,社会出现了三种对人工智能的极端预判:第一种预判充满了乐观和积极,他们把强人工智能赋予创造人类幸福的力量,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幸福生活的承诺;第二种预判恰好相反,他们把人工智能看作人类存在的终结者,人工智能会出于自身的需要消灭人类;第三种预判与第二种预判一样,不同的是“对这种结果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自然进化的必然和必要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光荣和延续。三种预判都有一个前提,即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建立在一系列不真实的条件之上的虚幻假说,而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之所以引出诸多哲学、社会学的伪命题,根源在于基于人的生命本性而具有的宗教情结。生存欲望和保证生命绵延的本能意识是恐惧,没有恐惧就没有有意识的生命绵延,因此,人们恐惧超自然力量的危险,也渴望超自然力量的护佑,所以,以色列人创造了金牛犊。超自然力量在科学面前分崩离析,可与生俱来的生命恐惧却不会消失,图腾崇拜从天上降到人间、从超自然力量转向人的力量,宗教迷信转变为科学迷信。其实,每当认识世界或改造世界的能力有了质的进步的时候,新的科技成果都会受到人类情不自禁的崇拜与恐惧,这些全部都在表达着人类对自我力量的崇拜和对幸福的期待。人工智能毕竟只是洗衣机而不是弗兰肯斯坦,它既没有能力担负人类幸福的承诺,也没有能力成为主导物种而自觉地去消灭人类,除非人类主动地消灭自己。人工智能不过是又一次的技术进步,人类解决问题的一个全新的方案。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也不能像人那样思考,更不会具有自我意识、主体性和社会性。在“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当中,所谓“人工”就是外在现象的模仿,所谓“智能”根本是一种修辞或愿望。
不过,人工智能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的确需要我們认真应对。首先,当下的紧要问题是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地替代目前人类正在承担的工作,许多人因此失去或即将失去劳动岗位。当然,这是技术进步固有的负面社会影响,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明都曾经如此,工业革命就曾经被咒骂制造了“撒旦的黑工厂”。新技术必然地要取代人类从事的一些劳动,这也是新技术的价值;但它并不是要取代人的价值,相反,是让人从较低的劳动上升到更高的劳动,从而提升人的劳动价值、提升人的生存意义。只是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人需要否定自己、提升自己,否则就会带来一定的困扰和痛苦。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完成人工智能推动人的自我否定过程,是我们切实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其次,更为久远和尖锐的问题是,技术没有道德属性,人工智能可以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也可以毁灭人类;不过,毁灭不是机器对人的反捕,而是人类的自杀——人类操控机器来高效地毁灭人类。因此,我们不必担心机器变得像人,而必须担心人变得像机器。技术一定要注人人性,将我们的价值观注人技术中,让技术成为对社会、对家庭更美好的承诺。有一种所谓的宇宙主义,认为强人工智能有着超人的智能,比人类具有更高的生存权利和存在的优越性,因此,人工智能应该和必将成为地球的主导物种,而人类应该和必将像恐龙一样成为历史。这样自然界才回归了进化的正轨。显然,他们混淆了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机器代替不了生命,但是,可怕的是其深层的反人类思想。以智能水平评估生存权利,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的信仰者,完全否认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的意义,为强权政治、种族灭绝辩护。人工智能研究必须坚持人本原则,必须坚持技术为人类所用,必须坚持不危害人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健康发展。
霍金悲观地预言:“成功地创造出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但这极有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后的进步。”这里需要修正的是,不是“人类历史”也不是“人类文明”,而应该是“理性主义”,准确地说,“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的精神开启了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创造了当代令人类自身都为之惊叹的进步,但理性主义以可分析的假设为起点,假设了思维及其对象的可分析性;逻辑主义以精致的语言、严谨的规范构造了一个确定性和必然性的分析空间,也就虚构了一个与世界相分离的实体,拒绝着思想的丰富性和无限性。人工智能是逻辑的实体化,也是逻辑主义最高的物质成果。严格地讲,逻辑空间是一个表达的空间,不是一个思想的空间,而思想空间应该先在于表达空间,也决定着表达空间。如果相反,以思想空间论证表达空间,一定会产生诸多无意义的概念和只会产生争议的伪命题。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但强人工智能只是乌托邦式幻想。机器模仿人类的运作模仿到完美无缺也不能证明它不只是一个复制品,它们也并没有生命,更何况“模仿”也只是一个暗喻。人工智能不会造福人类,除非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为自己造福;它也不会毁灭人类,除非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自我毁灭。
[参考文献]
[1]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德]J.哈贝马斯.从康德到黑格尔: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J].韩东晖译。世界哲学,2005(6).
[3][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王平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Searle,J.Minds,Brains,andPrograms[J].BeharioralandBrainSciences,1980(3).
[7]黄祖洽.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8]人工智能是伟大的进步,但极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后的进步[EB/OL].http://www.sohu.com/a/206086868_114986,2017—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