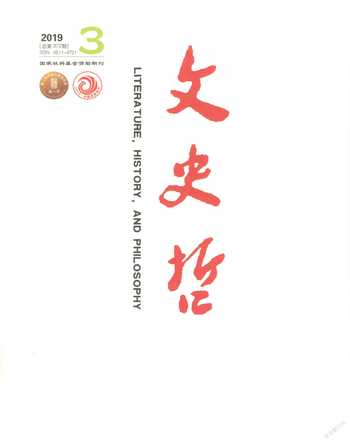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2019-09-10杨少涵
摘 要:《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為“书”的过程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关键词:《中庸》;《礼记》;升格;佛道;经学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06
一、《中庸》“回流说”及其内在问题
无论是从中国经学史还是从中国哲学史来看,《中庸》升格为经都是一个令人称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庸》能够“升经”①的内在原因一直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尤其是佛道二家对《中庸》之发现与流传的影响,更是学者们反复念叨的话题。清初姚际恒曾说:“予分出此帙,以为伪《中庸》者,盖以其为二氏之学也。”②姚氏所谓的“二氏”即释、老二氏。他还斩钉截铁地说:“好禅学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禅学。”③现代学者们对《中庸》与佛道二家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更为细致严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4)中述及宋初僧人智圆在宋明儒学家之先对《中庸》的大力提倡④。钱穆也曾先后撰写两篇专文《读智圆闲居编》(1947)及《读契嵩镡津集》① 在中国经学史上,宋代以后出现了以《四书》取代《五经》之势。而在《四书》中,《中庸》《大学》《孟子》都曾有过一个升格为经的过程。这个过程简称为“升经”。“升经”之说最初是用于《孟子》的升格运动。王应麟《玉海》卷四二《艺文·经解、总六经》曰:“国朝方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关于孟子“升经”的过程,可参考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
(1977),分别讨论了智圆与契嵩对《中庸》的孤明先发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第103-136页。。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以余英时与杨儒宾两位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2003年,余先生大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问世。在该书的超长绪说中,余先生基于陈寅恪、钱穆二先生的前期研究,遍考相关文献,最后提出这样一个“假说”:
首先我要提出一假设之说,即《中庸》的发现与流传似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的关系最为密切。与道家、佛教都有交涉的戴颙曾注《礼注中庸篇》,佛教徒梁武帝则有《中庸讲疏》。此外《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列《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可能是臣下记梁武帝关于《中庸》的另一著作。这种情况似乎表示《中庸》最早受到重视是出于佛教徒“格义”或新道家“清谈”的需要。李翱所读的《中庸》大概也来自佛教徒所传的系统。这一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智圆“以僧徒而号中庸子”这个事实。《宋史·艺文志一》所载宋代儒家专讲《中庸》之作,以《胡先生中庸义》为最先,但胡瑗已远在智圆之后。因此我假定《中庸》在北宋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第130页。
根据余先生的考察,宋代儒家从心性义理方面阐释《中庸》肇始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但早在胡瑗之前,南朝的戴颙、梁武帝萧衍,中唐的李翱,宋初的智圆、契嵩,都已对《中庸》给以相当的重视。而这些人要么直接就是佛徒,要么与佛老有亲密交涉,他们出于佛教徒的“格义”或新道家的“清谈”需要而重视《中庸》。从这样一个历史顺序来看,确实是佛道两家提倡《中庸》在先,儒家重视《中庸》在后。对于原本就属于儒家经典的《中庸》而言,从佛道两家之提倡到道学家之重视,这个过程的确呈现出一种从佛道回到儒家的“回流”现象。所以余先生的这个“假设之说”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回流说”。
相比于余英时先生的“回流说”,杨儒宾先生关于《中庸》与佛道之关系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回应说”。这一说法集中见于其《〈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一文杨先生此文最初写于1999年,题为《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载于《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12月)。后经大幅度修订,《学》《庸》分论,《中庸》部分题为《〈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初载于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0-518页;后又收于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195-238页。。在此文中,杨先生认定《中庸》本来就有一种天道性命学说,但后世对此天道性命学说的诠释却有分歧,并逐渐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心性论的系统,一个是气化论的系统。唐代以前,前一个系统以戴颙、梁武帝、梁肃、权德舆、刘禹锡等释老之徒或佛教居士的诠释为代表,后一个系统以郑玄、孔颖达等人之汉唐注疏为代表。在杨先生看来,宋代儒学是为回应佛道而出,“理学的重要语汇背后,几乎每个词语都有相对应的佛老概念与之角力”杨儒宾:《作为性命之学的经学——理学的经典诠释》,《从〈五经〉到〈新五经〉》,第22页。。所以到了宋代,《中庸》的两个诠释系统因为儒学的这种历史责任而遇到了不同的宿命。杨先生说:
这套学问在李翱、周敦颐兴起之前,确实未曾受到正视。虽然汉唐儒者也有他们的“性命之学”,一種气化和融、人与天协的中和或中庸状态始终被他们视为人格的最高境界,但这样的性命之学在基本存有论的视野下如何能证明自己,或者如何能回应像佛、道那般具有深刻思辨力道的义理体系,他们不能说明。难怪自从兴起后,气化论的性命之学却被他们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直到晚明,才有一个可以较圆满的统合气化论与心性论诠释的新《中庸》之学出现。杨儒宾:《〈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从〈五经〉到〈新五经〉》,第238页。
“这套学问”即以“性命之学”为核心的天人之学,显然属于《中庸》的第一种诠释系统。在儒者内部,这套学问开端于中唐的李翱与北宋的周敦颐,中经张载、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理学家,最终大成于朱熹。《中庸》的经书地位也在这一诠释系统中得到确立。《中庸》的第二种诠释系统即气化论则为宋代的司马光所继承。但是气化论的诠释系统无法“回应像佛、道那般具有深刻思辨力道的义理体系”,于是也就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回流说”与“回应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中庸》心性之学之源始有不同的判断。“回流说”试图说明《中庸》的心性之学维度是由佛道之徒诠释出来的,然后再由儒家接手;“回应说”则力证这种心性之学之维本来就是《中庸》思想的一种诠释可能,只不过在唐代以前,佛道学者比儒者更容易走进这一可能,到了宋代,儒家出于回应佛道的需要,才重新捡回了自家的老本行。
当然,“回流说”与“回应说”也有相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两组追问来逼出其相同之点。对于“回流说”,我们可以追问:那些佛道之徒在“格义”或“清谈”时为何不选取儒家其他经典,而单单选中《中庸》?对于“回应说”,我们可以追问:即使《中庸》本有心性之学的诠释维度,但何以唐代以前的儒者没有发掘出来,而必须等到宋代儒家面对佛道的挑战时才去“复活”此意义?或者问:如果没有佛道二家对《中庸》心性之学的重视,那么宋明儒家是否就不会去“复活”《中庸》的心性之学?而佛道二家又何以单单重视《中庸》而非其他经典呢?这便又回到了与“回流说”相同的问题上去。所以“回应说”其实可以纳入“回流说”。也正是在这意义上,本文正标题前半部分只取“回流”二字。
总之,“回流说”的短板在于,它只看到了佛道二家重视《中庸》,而没有回答二家何以只重视《中庸》。这其实也是前述姚际恒所面临的问题,他说“好禅学者,必尚《中庸》”,但“好禅学者”何以只“尚《中庸》”,《中庸》何以会进入好禅学者之法眼呢?这是《中庸》升经的一个“知识考古学”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庸》升经的终极原因便始终隐而不彰。
二、《礼记》自立门户与《中庸》水涨船高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故此,考察《中庸》的升经过程,就不能不关注《礼记》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变动情况。中国古代经典依其性质有经、传、记之分。《博物志·文籍考》曰:“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卷六《文籍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春秋左传注疏》曰:“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文,传示后人。”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这说明经是圣人所作之原创文献,传是贤者对经所撰述之解释文字,而记则是后学对经、传文本所作之补充说明性的“补记”王葆玹:《两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第45页。。根据以上区分,《礼记》一书最初只“是记而非经”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蒋伯潜、蒋祖诒:《经与经学》,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第64页。,“是补经之作”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页。。更具体地说,《礼记》之“礼”是经,即《礼经》,而《礼记》之“记”只是经之补记,是附属于《礼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吕友仁:《礼记正义校点前言》,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两汉有所谓“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其中的《礼》即《礼经》,亦即后来所谓“三礼”之《仪礼》。只不过当时《仪礼》并无“仪”字,以《仪礼》指称《礼经》是南朝梁、陈以后之事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既然《礼经》是《仪礼》,那么《礼记》作为礼经之补记,起初就只是对《仪礼》经文的解释性内容。在作为经的《仪礼》与作为记的《礼记》之关系中,前者居于本体地位,而后者只是其附释性材料。此即朱熹所说“《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88页。。
《礼记》最初虽然只是《仪礼》之补记附释,但今传《礼记》的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对今传《仪礼》的解释。其中的原因在于今传《礼记》异常复杂的文献来源及其编纂过程。河间献王刘德“修古好学”,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将私藏先祖旧书献奉于他。河间献王“从民得善书”,其中就有《仪礼》与《礼记》。这是《礼记》的第一个来源,即献王得书。鲁恭王刘余“好治宫室”。他在扩建自己王宫的时侯,把孔府的墙壁给破坏了,结果在孔府墙壁里发现了一批古文经传,其中也有《礼记》。这是《礼记》的第二个来源,即孔壁藏书。《汉书·艺文志》载有“《记》百三十一篇”,这个《记》即《仪礼》之“记”。这一百三十一篇《记》文,据考就包括以上献王得书与孔壁藏书两个来源朱学勤:《郭店简与〈礼记〉》,《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页。。现存《仪礼》十七篇,其中十二篇的末尾都附有“记”文沈文倬说:“《士丧礼》上下篇的‘记’集中在《既夕》篇末,表面上是一篇,其实是通乎上下的,应该说十三篇有附‘记’。”参见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第6页。,这些“记”文应该与这一百三十一篇属于同一性质的作品。当然这一百三十一篇《礼记》只是一些补充解释《仪礼》的零散文章,并非一部编辑完整的著作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台北:大安出版社,2014年,第249-250页。。当然,从这些零散的文章到编辑完整的今传《礼记》,还要经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删削编纂过程。戴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礼记》的最初编纂者就是戴圣,其所编之《礼记》被称为《小戴礼记》。《小戴礼记》编成以后,东汉末年的马融、卢植传小戴之学,并皆为《礼记》作注。可能他们仍嫌《小戴礼记》复杂,于是就“去其繁重”,并将《月令》《明堂位》《乐记》等其他释《礼》文献合进来,这样就成了一种新版的《礼记》。也就是说,新版《礼记》不仅采用了直接解释今传《仪礼》的记文,还将与今传《仪礼》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一些著作中的或单独成篇的通论性文章也吸收了进来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内容与《礼》没有直接关系,而很可能是这部分内容所对应的《礼》没有流传下来。参见吕友仁:《礼记讲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对今传《礼记》贡献最大的当属郑玄。郑玄通注《三礼》,其注兼采古今,不法一家,删裁繁诬,简洁明了,所以郑注一出,天下归往,“自汉末至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注》为中心”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页。。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其最大影响是使《礼记》脱离《仪礼》,开始摆脱其附属地位而独立行世。从此以后,《礼记》不但与《仪礼》《周礼》并驾齐驱,鼎足而立。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博士十九人”,《礼记》与《周官》《仪礼》等经书“皆列于学官”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三《大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64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页;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19页。。这是《礼记》在经学史上第一次立于学官。东晋元帝践阼之初,简省博士,郑注《礼记》与其他诸经共置博士九人,而“《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尚书左仆射荀崧以为不妥,遂上疏力请增置郑玄注《仪礼》及其它三经博士各一人。荀崧之请虽蒙元帝允准,但适会王敦之难,终不得行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五《荀崧传》,第1976-1978页。。所以在这次置立博士官中,“三礼”之《周官》《礼记》皆入选,而盛行于两汉的《仪礼》却旁落。这是《礼记》在经学史上第一次越位于《仪礼》。
《礼记》虽然在魏晋时期立于学官,置有博士,并有超越《仪礼》之势,但这时的《礼记》仍然只是一家之学,还没有成为天下共习之业。要超脱一家之域而为天下共习,最简捷的路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官方教材,也就是取得的经书的地位。《礼记》的这一身份转换,是在科举兴起之后的唐初完成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经文既正,贞观十二年(638),又诏孔颖达与诸儒撰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最后刊定,“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05页。。于是“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天下士民,奉为圭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4页。。《五经正义》之五经依次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第30页。。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周礼》《仪礼》与《公羊》《穀梁》才重新成为明经科考的内容,于是“五经”也相应变成了“九经”王溥:《唐会要》卷七五《明经》,第1373页。。从唐初直至终唐,以《五经正义》统一经典这一做法屡遭诸儒批判。但这种批判始终未成普遍风气,唐室原则上始终以官定教本为举国贡举之依据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84-311页。。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太宗诏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与汉武帝纳董仲舒谏独尊儒术,对中国儒学史有着同样重大的意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3页。。
我们知道,“中庸”二字首次以书名出现是在《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关于“子思作《中庸》”的说法,后世学者多有辨疑。参见杨少涵:《中庸考论——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附论第一节《〈中庸〉成书的九大疑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78-408页。《汉书·艺文志》与《中庸》有关的记载有三条,其中《六艺略》“礼”类有两条:(1)“《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2)“《中庸说》二篇。”《诸子略》“儒家”类有一条:(3)“《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这三条内容与今传《礼记·中庸》的关系有以下三个层面。首先,“《记》百三十一篇”应该属于孔门七十子后学解释《仪礼》的早期《礼记》类作品。其次,“说”与“记”属于同一性质,都是对“经”之解说补记,那么“《中庸说》二篇”也应该属于释《礼》类作品徐复观认为《中庸说》二篇“即今《礼记》中之《中庸》别行者”(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2004年,第164页),所以《中庸说》与《中庸》一样,可能也属于释《礼》性质的作品。。“《记》百三十一篇”与“《中庸说》二篇”既然各为一条,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中庸说》二篇并不属于一百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而南朝齐梁人阮孝绪《七略序》认为刘歆《七略》又是根据其父刘向《别录》“撮其指要”而成。据此可以推测,《中庸说》二篇很可能是刘向以前的西汉儒生所做之《礼记》类作品,而且在班固纂修《汉书》时仍然能够见到。最后,今传《礼记·中庸》原本可能在《子思》二十三篇之内,后来被戴圣合入《礼记》南宋王柏已有此想:“因见《汉志》有‘《中庸说》二篇’五字,心颇异之,求于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窃意《大学》、《中庸》当在二十三篇之内矣。”(王柏:《鲁斋集》卷一○《中庸论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6页)。郑玄《礼记目录》引用刘向《别录》说《中庸》在《礼记》属于“通论”,那么在刘向以前,《中庸》已是《小戴礼记》之一篇。《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说:“《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令狐德棻:《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88页。这就是说,《子思》二十三篇本有一篇与礼有关的论文《中庸》,后被合入《礼记》,又因为其与《仪礼》的关系不是十分紧密,所以被刘向《别录》放入“通论”。这篇《中庸》随着今传《礼记》被保存下来,而《中庸说》二篇则因为没有被合入《礼记》而逸失不传,到郑玄那个时代就已经见不到了。总之,《汉书·艺文志》所载以上三条原本各自独立,今传《礼记》之主体应该是由《记》一百三十一篇而来,后来《子思》二十三篇中之《中庸》被合进来,这就是今传《礼记》之第三十一篇。
以上考察旨在说明,《礼记》在郑玄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基本完成了其升经过程。《中庸》作为《礼记》之一篇,随着其母体之经学地位的抬升而水涨船高,进而受到社会的普高关注,也是自然而必然之事。
三、宋戴颙与梁武帝之注《中庸》及其“《礼记》学”背景
《礼记》由“记”升格为“经”,为《中庸》由“篇”独立成“书”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庸》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随着《礼记》成为“经”,自然会被士人所熟悉并关注。但仅仅有此契机,并不足以保证《中庸》必然能够脱离《礼记》而单独成为“经”。因为《礼记》共有四十九篇,为何偏偏是《中庸》能够抓住契机,终获殊荣呢?根据余英时的“回流说”,北宋初期至中期,在沙门士大夫化的儒释互动过程中,《中庸》先是被佛门高僧研读,然后再“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并为儒者所重视。这一说法对考察《中庸》独立成经的过程,确有发覆之功。但这一假说所着重考察的只是北宋初、中期的情况,而《中庸》走向独立的过程所牵扯到的历史背景却更为广阔,其中的情况甚为复杂,远非“回流说”所尽能范围。
《中庸》与佛道二家明确发生关系始于南朝的戴颙。戴家是隐逸世家,戴颙父兄“并隐遁有高名”,戴颙还名列《宋书·隐逸传》第一人。《隐逸传》这样记载戴颙:
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7-2278页。
这一记载显示戴颙有两方面的浓厚兴趣。首先,戴颙崇尚自然,并著《逍遥论》以“述庄周大旨”,由此可见戴氏在道家之学上造诣匪浅。其次,戴颙还工于佛像制造,连专业的雕像工人也“无不叹服”。后世对戴氏父子的佛像雕刻技艺更是赞叹有加:“二戴像制,历代独步。”弘赞:《兜率龟镜集》初集《戴颙处士》,CBETA,X88,n1643,p0055,c10-11。但从上引材料中可以看出,佛道二家对戴颙的影响并不相同。戴颙不但在生活方式上融入道家,而且在道家学术方面也有相当造诣;相反,在佛教方面,戴颙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兴趣爱好,尚谈不上学术创发。
当然,《宋书》此处所载最为重要的是戴颙曾注《礼记中庸》篇。这是史书上个人研究《中庸》的最早记载。《宋书》所载不明卷数,《隋书·经籍志》载为《礼记中庸传》二卷。另外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经籍艺文志的记载,除了《礼记中庸传》以外,他还著有《月令章句》十二卷,而《中庸》《月令》都是《礼记》中的单篇。从这些史载来看,戴颙的著述仅限于《庄子》与《礼记》。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戴颙虽然有佛教的背景,但这种背景尚只是一般性的观玩兴趣,对其学术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应当是道家的《庄子》与儒家的《礼记》。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戴颙所著《中庸传》很可能是以道解之,至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则尚处于潜在状态;而戴颙对儒家经典独情钟于《礼记》,也决非偶或使然,必定与《礼记》地位的抬高有着内在的关联。
有佛道背景而注《中庸》的第二个人物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佞佛谄道,闻名史册。梁武帝与道教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他与道教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的交游上。萧、陶很早就开始交游了,《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说“(梁)武帝与之交”,《隋书·经籍志》亦说“(梁)武帝素与之游”。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萧衍起兵叛齐,兵围建康,陶弘景曾遣弟子“假道奉表”,表示拥戴。在齐梁禅代之际,陶弘景又用图谶来为萧衍登基制造天意合法性。萧衍即位后,对陶弘景更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陶弘景则以炼制丹药作为回报萧、陶交游的具体情况,可参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一章《陶弘景交游丛考》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23-41页。。但是天监三年(504)四月初八佛诞日,四十一岁的梁武帝刚刚即位三年就下了一道《舍事李老道法诏》,舍道归佛。诏曰:“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52,n2103,p0112,a16-18。改元普通以后,梁武帝更是大建寺庙,数次舍身,召开大会,升座说经,并令王侯弟子皆受佛诫,让臣下奏表上书称其为“皇帝菩萨”,对佛教的信仰无以复加。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梁武帝作为一个皇帝,却如此佞佛谄道,这一现象极易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儒学对梁武帝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梁武帝下诏舍道入佛后的第三天,即勅门下:“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52,n2103,p0112,a27-29。在这道诏书中,梁武帝把儒家的周、孔二圣与道家的老子同归入邪道,可谓严厉批判。这就更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儒学只是梁武帝的批判对象,根本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事实并非如此。梁武帝曾写过一首广被引用的《述三教诗》,此诗的前半部分如下:
少时学周孔,弱冠窮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
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52,n2103,p0352,c12-17。
在此诗中,梁武帝非常简练地总结了自己一生问学的三个阶段:“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这就告诉我们,梁武帝在青少年时代所学者为周孔儒学,甚至在弱冠已经穷读六经。改信道佛,是中年以后之事。梁武帝这一自述作为诗,固然有简单化之嫌,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多少也可能有些“文学上的夸张”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周一良集》第一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但征之于史书,还是大体可信的。《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曰:
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袪等递相讲述。……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梁书》“少而笃学,洞达儒玄”与《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几乎完全照应。梁武帝所造诸书几乎皆与儒家六经有关,可见其“卷不辍手”当指儒家经典。“万机多务”是指他处理公务。萧衍十九岁出仕,二十岁始受道法,四十一岁改宗佛教。如果“万机多务”从他出仕算起,那么他在信道宗佛的过程中,仍然在坚持阅读儒家经典。相反,其“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则只是“兼”之。
《梁書》的这一记载,也与梁武帝治国与著述的情况相契合。从治国方面来看,梁武帝治国,“并敦儒术”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360页。。为了尽快振兴国家的基础教育,梁武帝“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招内后进”,“立孔子庙”,“幸国子学”,“亲祠明堂”(《梁书》卷二)等等,都是他在治国方面并敦儒术的具体措施关于梁武帝以儒治国以及梁代儒学发展的详细情况,可参考杨恩玉:《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第六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一节,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179-186、230-234页;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100-107页。。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也很高。根据《梁书·武帝本纪》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他一生著述上千卷,大半属于儒学,另一小部分属于佛教,道教部分几乎不名其一。这就呈现出一个与戴颙相似的情形:佛教对戴颙的影响可能仅限于佛像雕塑等兴趣爱好,而道教对梁武帝的影响,可能也仅限于炼丹吃药等个人兴趣,尚不足以渗入其深层生命世界。梁武帝的儒学著述涵盖《诗》《书》《礼》《乐》《易》《孝经》等经书。这些著述仅量多,而且还在思想层面“洞达儒玄”,“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这都是一般的儒家经生也难以做到的。由此足见,无论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是政治实践方面,儒学在梁武帝的生命中都占有很大的份量。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称周孔为邪道的那道勅令,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是其本人所作,还是推尊佛教的沙门人士所为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武帝的著述中,就有《中庸讲疏》一卷。大同六年(540),朝臣朱异、贺琛还“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想必此书是梁武帝相当得意之作。《隋书·经籍志》还载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从制旨两字看来,恐亦萧衍所作”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周一良集》第一卷,第421页。。根据前面的介绍,道教对梁武帝的影响仅限于炼丹制药,那么其所著《中庸讲疏》受道教思想影响到底有多大,便大可商量。按照梁武帝《述三教诗》的划分,《中庸讲疏》应该是他早中期的著作,那么《中庸讲疏》更多的还是儒家思想,佛教影响可能不会太多。《中庸讲疏》即使是其中后期著作,那么这也只能说明梁武帝以佛教思想来反观《中庸》,而《中庸》本身则早已在其生命中渗透流淌。说得更明白些,以《中庸》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早在其生命中根深蒂固,佛教思想只不过是重新审视此生命之根的一个视角而已。
以上考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戴颙与梁武帝之注《中庸》不可避免会受到佛道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在《礼记》独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郑玄之注,《礼记》开始脱离《仪礼》而单独行世,到了南朝齐梁间,《礼记》《周礼》《仪礼》等三《礼》之学更是风生水起。这从《南史·儒林传》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南朝士人中,“传三《礼》”“受三《礼》”“撰三《礼》”者不绝于缕,“明三《礼》”“好三《礼》”“通三《礼》”“善三《礼》”“长三《礼》”“精三《礼》”者,代有人出。在这种经学大背景下,《中庸》作为《礼记》之一篇,在南朝受到关注也是必然之事。由此而言,戴颙与梁武帝之注《中庸》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因为这只不过是《礼记》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四、《礼记》升格为经与中唐士人共话《中庸》
戴颙《中庸传》与梁武帝《中庸讲疏》在唐代已经失传,时人与后人又其只言片语之摘引,所以今人根本无从窥其义旨。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庸》重新受到关注及其义理得到初步发挥,是中唐以后之事。唐初《礼记》列入《五经正义》,成为明经考试的官定教材。唐代科举科目众多,但是在取士倾向与考试难易等多重因素的促动下,“士人所趋,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明经侧重于识字记诵,进士侧重于杂文策论。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以后,明经与进士都要加试“帖经”。“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历代制下》,第356页。帖经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填空题,给出一行经文,帖住其中三字,让考生填写郭绍林:《驳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帖经等考试定式要求考生必须把整本经文及其注疏都背得滚瓜烂熟,才能应付科考。所以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对考生的经学素养都要求极其高龚鹏程:《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在唐代的科考命题中,《礼记》占很大的比例。在唐代科考诗、文、赋三种形式的命题中,在试律诗与试律赋两个方面,从《礼记》中所出试题都占据绝对大的比例据统计,唐代科考诗、文、赋三试所引诸经次数如下:
参见洪铭吉:《唐代科举明经进士与经学之关系》,台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第295、300、323页。。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随之显耀于士人眼中。中唐以后,知识阶层对《大学》《中庸》的重视已经形成习尚涂耀威、周国林:《韩愈与〈大学〉及其相关问题考述》,周少川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二十八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这种习尚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明经策试开始从《中庸》中出题。贞元十九年(803),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蹈白刃或易于中庸”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642页。《补正》引文“中庸”二字有书名号。根据《中庸》原文,书名号当删。一语,即出自后来朱熹所订《中庸》第九章。贞元二十一年(805),重臣权德舆曾以《大学》《中庸》策问考生:
《大学》有明德之道,《中庸》有尽性之术,阙里宏教,微言在兹。圣而无位,不敢作礼乐。时当有闻,所以先气志。然则得甫、申之佐,犹曰降神;处定、哀之时,亦尝问政。致知自当乎格物,梦奠奚叹于宗予。必若待文王之无忧,遭虞帝之大德,然后凝道,孰为致君?尔其深惟,以判其惑?权德舆:《明经策问八道》,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40頁。
其中的“尽性”“不敢作礼乐”“哀公问政”“文王无忧”“凝道”等词分别见于《中庸》第二十二、二十八、二十、十八、二十七章(按朱熹《中庸章句》分章)。科举考试有一个规律,往届考试从某书出题,后面的备考者必然会对该书大加关注。根据这一规律,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应试者心目中,《中庸》必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考生答题,多引《中庸》。随着《礼记》的升格,《中庸》成为天下士人童而能诵、耳熟能详的内容,考生在答题时征引《中庸》的情况也逐渐增多。韩愈的省试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贞元八年(792),经过四次进士考试,韩愈终于登第。但是根据唐代的科举制度,进士登第只是获得了入仕的资格,要想穿上官服,还要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于是韩愈就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当年的吏部考试,但在复审时被驳下落选。贞元九年(793),韩愈二度应考,并作《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者则拳拳服膺而不失矣。”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一四《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24页。
此次省试的题目出自《论语·雍也》,而韩愈此论的基本材料则包括《中庸》第二十一章“诚明”“明诚”、第八章颜回“择乎中庸”与《孟子·公孙丑上》知言养气章的内容。根据唐代贡举规定,考试教材虽然是《礼记》等九部“正经”,但“《孝经》《论语》并须兼习”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页。。所以考题出自《论语》,韩愈应之以《礼记·中庸》,以及后来《原道》对《礼记·大学》的引用,都属于当时一般士人的正常知识储备。从思想层面来看,韩愈认为过与无过不在外在的言行,而在内在的心性。根据人的内在心性,他把人分为两等,一等是无过之圣人,一等是有过但不贰过之贤者。韩愈还将这两种人与《中庸》第二十、二十一章的内容进行对应比照:无过之圣人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自诚明者,不贰过之贤者是择善固执之自明诚者。宋代道学开山周敦颐名著《通书》曾盛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周敦颐:《通书·志学》,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页。。而“《通书》‘学颜子之所学’一语,已为当时士人所习闻”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卷二《颜子所好所学论释义》,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1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2页。,故而才会有胡瑗以之试十八岁的程颐,由此成就的理学名篇《颜子所好何学论》,其中心思想和典据文献与韩愈《颜子不贰过论》也多有相似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7-588页。胡瑗试程颐事,见《伊川先生年谱》,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38页。。由此亦可见,韩愈对宋代儒者影响之巨。
最后,时人行文作论也常以《中庸》为题材。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梁肃在《止观统例议》一文中两引《中庸》梁肃:《止观统例议》,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七,第5258页。该文所引《中庸》两句话分别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此在《中庸》第四章。“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此在《中庸》第二十章。。在该文中,梁肃提出了“复性明静”之说。此说明显是努力将《中庸》“自明诚”和“诚之”思想与佛教天台宗的止观思想进行会通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被后人誉为“闽学鼻祖”出自《闽政通考》,转引自王春庭:《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欧阳詹与中原文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的欧阳詹年青时曾与乡人“灵源道士(蔡明浚)、虹岩逸人(罗山甫)有潘湖合炼奉养之契”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王式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245页。关于欧阳詹与蔡、罗隐居之事的辨正,可参阅张伟民:《欧阳詹年谱及作品系年》“肃宗至德二年(757)”条,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杨遗旗:《欧阳詹生平考辨三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贞元八年(792),欧阳詹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应举期间,欧阳詹曾撰《自明诚论》:
自性达物曰诚,自学达诚曰明。上圣述诚以启明,其次自明以得诚,苟非将圣,未有不由明而致诚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诚者也,无其性不可而及矣;颜子游夏,得诚而明者也,有其明可待而至焉。……先师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谓自性而诚者也。”又曰:“学而知之者次,所谓自明而诚者也。”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235页。
此论中有关“诚明”的几句内容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后面引其“先师”之言中“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则出自《中庸》第二十章。
韩愈与欧阳詹两论中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都以《中庸》的“诚明”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这个议题一直到宋代仍然在持续。北宋范仲淹在科举考试中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陈襄也曾撰《诚明说》并进献给宋神宗陈襄:《古灵集》卷五《诚明说》《进〈诚明说〉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526-527页。,南宋王柏则有《诚明论》王柏:《鲁斋集》卷一○《诚明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159-161页。。可以说,《中庸》的“诚明”问题在唐宋两代是一个热门的普遍话题除了“诚明”问题,《中庸》的“性情”问题也是中唐士人颇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韩愈的弟子兼侄婿李翱。贞元十五至十八年间(799-802),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复性书》最主要的一个理论命题就是性善情昏。此书上篇开卷就说: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106-107页。
一般认为,李翱“复性说”的直接来源是梁肃的“复性明静”说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310页。。李翱的确也曾师事梁肃。比较李翱的《复性书》与梁肃的《止观统例议》,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论证方法上,两书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李翱对性的理解完全来自《中庸》。李翱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来解释《中庸》首章第一句“天命之谓性”。关于这种天命之性,《复性书上》说“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到了《复性书》中就说得更明白了:“性无不善”。这说明,《复性书》是肯定性善论的。
关于性情问题的讨论,后面的脉络就广为人知了。韩愈读到《复性书》后,对其中灭情复性“杂佛老而言”相当不满意,佛门中人甚至还形象地描绘韩愈当时曾叹息地说:“吾道萎迟,翱且逃矣!”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七《唐朗州药山惟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4页。于是韩愈就写了“五原”,其中《原道》一文将李翱所开示的儒家道统系统化,而《原性》一文则全面阐述了自己著名的“性情三品说”。同为韩愈高弟的皇甫湜对韩愈的观点有所保留,在《孟子荀子言性论》一文,他更倾向于孟子之言“合经为多益,故为尤”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二《孟子荀子言性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74页。。杜牧更是直接就《原性》中所提到的孟子、荀子、扬雄三人而写了一篇《三子言性辨》,但结论却肯定了荀子:“荀言人之性恶,比于二子,荀得多矣。”杜牧:《樊川文集》卷三《三子言性辨》,《景印文淵阁四库全书》第1081册,第580页。
也就是说,中唐士人围绕《中庸》开展出了一系列的中心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诚明”与“性情”问题。这些士人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免会涉及到佛教思想。但他们之关注《中庸》,以及佛教在其中的影响,都是在前述《礼记》升格为经的科举背景下进行的。
五、结 语
北宋初、中期,随着韩愈、李翱等人所推行的古文理论与实践风行士林,由他们所开辟的以《中庸》为中心的情性论,也为新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儒家各派以及以契嵩为代表的佛教人士所接棒。后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继续推向深入,并最终合流为北宋新儒学的兴起。
当然,《中庸》由“篇”独立为“书”,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书,还需要宋、元两朝儒者与皇权的双重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宋、元两朝的两位仁宗一头一尾,起到了关键作用。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国科举史上出现了一项创举,即《中庸》被作为御书颁赐新科进士人手一册,并令宰相当众宣读王应麟:《玉海》卷三四《天圣赐中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第78页。。御赐《中庸》“自后遂以为常”,作为常制,推行下去御赐《中庸》作为常制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2年。。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此举意义非同小可。元世祖期间《四书》成为必考书,而《五经》则降为选考书。这是“《四书》地位凌驾五经的一个表征”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第673页。。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诏考试程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四书》正式成为科场教材。《中庸》由“篇”独立成“书”,升格进入新的经书系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至此完成。
回顾以上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些与“《中庸》回流说”相逆的命题。首先,《中庸》受到戴颙、梁武帝等崇佛之人的重视,他们专门为之作注,此与经学尤其是《礼记》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礼记》得到郑玄作注进而自立门户,这是《中庸》身价抬高的一大关键。如果不是由于郑玄作注而独立出来,《礼记》仍然附属于《仪礼》,可能根本不会被立于学官,当然也就不会受到世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礼记》之一篇的《中庸》,也就不会被单独提出来进行研究。戴颙、梁武帝之注《中庸》,即使是为了与道士清谈或与佛徒格义,但如果不是《礼记》被立于学官,他们恐怕根本不会选择《中庸》。有谁会拿一部名不见经传的著作来与人清谈呢?又有谁会选择一部没有社会地位的文章来与佛经进行格义呢?
其次,《中庸》在中唐受到士人的广泛关注,是由《礼记》升格为经所决定的。唐初,《礼记》迈越《仪礼》《周礼》,成为“五经”之一,有唐一代,《礼记》独大。更重要的是,唐承隋制,科举取士,《礼记》成为科举考试的必选教材。仕途攸关,天下士人无不熟读《礼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唐以后,科举考试从《中庸》出题,考生答题广引《中庸》,渐成风气。学思日久,《中庸》里面的很多话题,比如“诚明”“性情”等,也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士人讨论的中心议题,甚至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李翱的“灭情复性”论是其典型代表。
最后,《中庸》能够从《礼记》四十九篇特出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与其文本体裁有关。章太炎在分析《汉书艺文志》书目时曾提出一个“原理”与“支节”的区别:“原理惬心,永远不变。一支一节的,过了时,就不中用,所以存灭的数不同。”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章太炎著,章念驰等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二辑《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有些书多讲人生社会方面的“原理”,这可称为原理体裁;有些书多讲支支节节的“技术”,这可称为技术体裁。原理体裁的书因惬于人心而流传久远,而技术体裁的书则往往因技术过时而不为后人所關注。《中庸》在刘向《别录》中属于“通论”,更具有思想性和议论性,属于原理体裁的书。只有这种文本才适合清谈与格义,才适合用来讨论身心性命的问题,而且也只有这种文体才方便科举考试策论出题与答题。相反,《仪礼》《周礼》及《礼记》之《月令》《内则》《玉藻》《明堂位》等则重于具体礼制仪式方面的内容,很难与佛道思想贯通,而且又由于其时效性太强,出题时联系现实的弹性不大,考生答题时发挥的空间太小。所以戴颙、梁武帝不会拿它们来清谈或格义,中唐士人也不会在仕途爽意时想到这些支节技术,在科举考试中,赋论部分往往也不会从中出题,考生在答题时也难以引用其书。这就是说,《中庸》之受到科举考试的青睐,是自身的文体性质使然。当然,刘向《别录》所举之“通论”有十六篇,何以只有《中庸》获此殊荣呢?这大概要归因于《中庸》尤其是其“诚明”“性情”等方面的内容更具有哲学上的思辨性与普遍性,故才能够成为永恒的话题。
总而言之,《中庸》升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礼记》的升格,《中庸》也水涨船高,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必读熟读书籍。这是《中庸》升经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庸》自身文本富含思想性、思辨性,能够成为道士清谈与佛徒格义的借鉴文本,也方便科举考试的策论出题与考生引以答问,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庸》升经的内在原因。在儒释道三教互动过程中,佛道对《中庸》的关注虽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总体上必须在这两方面原因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北宋儒家之所以会高度重视《中庸》,最主要的原因应该也还是这两个一言以蔽之,《中庸》在唐宋时代蒸蒸日上的威望,并非是从佛道回流而来。相反,宋初智圆、契嵩等佛徒之所以会大力提倡《中庸》,反而完全可以用这两个原因来解释。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