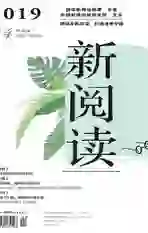星期六下午时分的轮船
2019-09-10吴越
吴越
三月细雨如吹烟。午后尚早,在复兴中路一带典雅的历史街区打伞步行,历数着一栋栋老洋楼,耳边就响起孙甘露老师的男中音,犹如小说开头的娓娓道来——“上海黄浦区有片掩映在法国梧桐中的老洋房,拱形窗、卵石墙,这就是思南公馆。”一抬头,徐则臣就在思南公馆的拱形窗下卵石墙边站着吸烟。一别经年,模样没变。今天,是第288期思南读书会,徐则臣带着长篇小说《北上》来了,我是这场读书会的主持人。
整整五年了,每周六下午,总会有几百名读者来到这里,听文学名家的讲座,这就是“思南读书会”。读者在这里读书、遇见世界,也把海内外的作家、编辑、出版家、书评人、读书人、艺术家引至此间,慢慢润色为共同的心灵。
“思南读书会”,有点像一个暗号,每周六下午两时到四时,将上海这座城市代入一个属于文学和文化的时区;又像一场堂皇的“快闪”,每当有路人好奇向玻璃门内张望,或索性信步走入时,我都感觉到:文学以见面、交谈、约会和观看的方式出现在字纸之外的一个真实场所,是多么地必要,又是多么地珍罕。
前些日子,在北京已经为《北上》举行了多场规格颇高的作品研讨会,而上海思南读书会的这场活动,按照我的想法,希望亲切一些,家常一些!毕竟,上海这座城座落在运河南端终点——杭州又再东去两百公里之处,这里是中国的河流文明与世界的海洋文明的交会点,上数三代,这里聚集了大多来自江苏、浙江,以及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的人口。在上海,开口谈运河的故事,首先唤起的是一种类似乡情的水的记忆。另外,我以为,则臣对上海也有某种乡情,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因为他的作品每每由北京而南飞到上海,发在《收获》上的数量是最多的。
我调用主持人的特权,临时想了个策划,和两位嘉宾——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翻译家黄昱宁女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先生,商量着,在开场之际,压缩常见的寒暄、介绍,改为一人读一段《北上》中自己最有感触的段落,稍加解释和点评。这样做,首先一个理由是,《北上》的语言干净轻灵,经得起读。其次是因为,我想让读过这本书和没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尽快进入《北上》的语境和情思。
两位嘉宾欣然同意。于是,一开场就进入了朗读环节。在满座读者屏声静气的聆听中,黄平教授读了小说接近尾声时的一节文字:
雨歇风住,雷声远去。邵家父子和周海阔回客栈休息,胡老师去取意大利信件的复印件,我和宴临沿河边栈道往北走。天上挂出一道彩虹,七色彩虹正横跨在运河上。我们俩越说越激动。一个个孤立的故事片段,拼接到一起,竟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仿如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
黄昱宁女士读了马福德与如玉在船上避开搜捕:
我们坐在芦苇荡里,船晃晃悠悠,芦苇在黑暗里波浪一般涌动,水鸟在梦啼。只有黑夜,只有我们这和片大水,大清国、义和团和瓦德西率领的联军都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只说不能相见的时间里各自的生活,主要是我说;如果我不说话,完全可能整个晚上我们都面对面傻坐着。我们中间隔着正在燃烧的蒲棒,她不许我把手伸过去。她能过来,孤男寡女共处一条船上,对一个中国姑娘已经是天大的尺度了……
这时,则臣把我手中的书要了过去,轻轻地翻着。我低声问道:“你是不是也想读一段?”他点头。这比我的“策划”更走远了一步,让我顿时踏实下来。
我接过书,找到谢平遥、小波罗和邵常来等夜泊邵伯闸的一段:
谢平遥转身,他们后面也聚集了几十艘船。跟他们一样,没点灯火的船上,船头也蹲着一两个抽烟的人。夜幕低垂,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声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以及船只晃动时木头榫枘挤压摩擦的细碎吱嘎声。偶尔有人咳嗽,早睡的人打起第一声呼噜,说第一声梦话。有人惊呼某个宝贝东西落水里了。有人偷偷摸摸往运河里撒尿。这就是烟火人生。有那么一会儿,谢平遥觉得自己正在沉入生活的底部,那是种幸福的沉实感……
然后,书到了则臣手里,他说请大家别介意,他想读的书中马思意临终前的状态,因为“整本书,只有在这里,我动用了我个人的真实经验,我祖母的去世”。
……守着母亲,胡念之和姐姐见证了母亲离世的全过程。死亡从来不会仓促降临,它一寸一寸地来,它把生命一寸一寸地从它选中的身体里赶出去。……其实母亲已经不会有什么在动作,即使死亡如此残暴,她也不过是腿动一动,胳膊动一动,头动一动。开始腿还能动,伸缩蜷曲;接着胳膊,过一会儿就要拿掉盖在身上的薄被,她热,将死之人心里有一团火;然后距地,脑袋在动,生命已经被死亡驱赶到头颅,驱赶到头顶;当驱赶出最后一根头发丝后,马思意死了。
这时,读书会才算正式开场。则臣等于是一开始就交了心了,他的坦诚、真挚和深沉,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这场读书会被命名为“河流的秘密”,我感觉到,我们似乎真在一艘轮船上,在星期六下午的这个时分,深入这本书丰富的肌理,深入它所内蕴的思想感情,也深入了一个人去世界又从世界回来、并且把世界与中国写进家门口一条河流的这样一种生命格局。有时,我为了调节一下严肃的气氛,会稍微开个小玩笑,但现场仍然有一种在不断融化着流淌着什么的感觉。我可以从他们专注的眼神和极为安静的秩序中感受到这一点。其中两位参与本次讲座的听众留下了这样的感言:
“《北上》这一期读书会,我比往常收获了更多,作者分享、嘉宾分析、读者提问,在相互启发之中,一些朦胧的共识丝丝缕缕地抽离出来。这些细弦是感性的,它与徐老师写作的心路历程一起,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一起,与读者阅读时的感悟一起,演奏出动人心弦的文学乐章。我沉浸在知识的共鸣里,试图抓住那些即兴出现又转瞬即逝的话语,因为我知道,这些是出了思南读书会后,再也无法重新演绎的精彩对白。互联网时代下的年轻人敏锐又孤獨,相似的经历与熟悉的情感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却碍于视角的狭窄,看不到共识之上的东西。因此,我们才更需要拥抱不同的视野,阅读那些用不同焦距描绘出的万千世界。文学时而能够放大个体的体验,在文字搭成的戏台上排演着平常人的生活,时而也能缩小个人的身躯,俯瞰历史的沉浮,悲悯着人类的渺小。流水无意唤起想象,却启发着运河之子走向远方。河流不曾允诺归宿,我们却将她的怀抱称作故乡。”(《思南读书会田野笔记之三》,作者何钰成)
“在思南读书会上,徐则臣不仅给我们上了一堂文学课,也顺带补习了历史课和地理课。好几位读者的笔‘唰唰唰’在笔记本上停不下来,绝无运河水荡悠悠的休闲情致。……一位读者问徐则臣‘为什么两次写到尾骨骨折’,徐则臣像小学生一样保证‘不会再有第三遍了’,他当初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写过两次了。另一位读者肯定了他的运河写作,却又发问‘生生地开凿了一条运河是否破坏了生态’,徐则臣取下了眼镜,揉了揉眼睛,又摸了摸后脑勺,直呼‘汗都要出来了’。《北上》的文字里有转承,有起伏,一种不可言状的微妙会在你的头脑里散播开来,嘴角稍稍上扬,这样的表情也是高级的。”(《漫话徐则臣》,作者 岑玥)
上海思南读书会的读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常严格的读者,对艺术品质极为敏感和挑剔。显然徐则臣的新作《北上》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时间的河从未停止过流淌,期待徐则臣这部描摹运河与时代的《北上》在未来的日子里取得更多更长久的收获。
作者系《收获》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