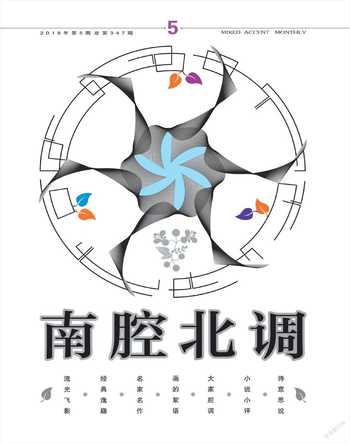当代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
2019-09-10李延

摘要:“诗歌”“诗人”“作品”“写作者”等几个词语是有明确界限的,而在日益浮躁“物化”“异化”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把它们混淆而不能加以区别。“诗歌”是诗人写出的,那些“伪诗人”只能算是“写作者”,写出的最多只能称作“作品”。合理地区分、欣赏当代诗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下大众的权利与义务。坚守诗歌的精神性与神圣性,在写作中寻找最高的审美向度,才是诗歌写作者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背景下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关键词:当代诗歌 日常生活审美化 诗歌圣殿的重建
我国文学史上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裁就是诗歌。从描绘原始狩猎的《弹歌》到内容丰富的《诗三百》;从瑰丽变幻的楚辞到异彩纷呈的唐诗;从缠绵多情的宋词到提倡白话的“五四”新诗,我国的诗歌历史从来就不缺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描摹,但此时的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愉悦,以求获得审美的自由。而当代诗坛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更多的受制于消费主义带来的感官享乐,诗人更多的是要面对世俗社会的种种诱惑,其内心的欲望之火燃烧于物欲横流的冲击之后。
一.当代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出现的原因
(一)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的产生
其实,审美一直就在我国日常生活中,审美一直没有离开过生活世界。只是生活世界的外化形式一直在发展,比如中国形而下的器物方面,瓷器,绘画,书法,饮食,服饰等都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也在这期间接受着美学熏染,有时候只是不太明晰。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怎能不具有审美化倾向?如果不这样理解,又如何理解当下学界繁荣的审美文化研究?比如在断代史审美文化研究中,大多会抽取某一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归纳,总结出当时的审美特征审美理想等。如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弹歌》,虽然只有两句:“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但语言质朴节奏明快,能说这样的日常生活没有审美化?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以贯之”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狭义意义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产生和这种狭义意义上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会发现,西方学者特别是费瑟斯通与韦尔施,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考大都从现代的大工业发展和人类物质文明的繁荣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文化”切入。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产生背景与“后现代主义”相关
“后现代主义”是与前现代、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和特征是“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1]简而言之,就是“去分化”与“消解”。它以“无所畏惧的劲头”冲散了现代主义确立的边界和领域范围,打破了现代主义的体制化、规整化。当“后现代主义”进入艺术、生活领域后,特别是以波普艺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旨在消解艺术的纯粹性,比如波普艺术中的玛丽莲·梦露的头像等,“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就在二者的融合中应运而生。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产生背景与“消费文化”相关
“消费文化”引导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中文化与消费结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广告、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2]此刻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中,有文化的印记,更多的是后现代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变革,“消费文化”正是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商品化大背景下,引导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进行“消费”时,“商品”已不再只是简单的具有实用价值,更深层的是大众对“商品”选择时看中的“非实用价值”。
二.当代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的表现
虽然日常生活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需要诗人们去发掘其中蕴含的真正的精神价值和美学内涵,但当代诗坛上的大部分诗歌写作者却在发现日常生活之美的路上,渐行渐远。庞大数量的诗作背后却是质量的下滑,这种虚假的繁荣与当代诗歌的“审美异化”和庸俗化密不可分。
(一)当代诗歌“审美异化”倾向
当下现实中把“审美”渗透入“日常生活”,虽然实现了表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但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审美化,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被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大机器设备所物化、异化一般,这种与消费主义密切关联带有功利性的审美化,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审美异化”的发生。诗歌在审美化的表达上也受到了消费主义中功利性的冲击,比如,“非人化”生存状态的描写。
在这一类诗歌中,写作者把自己比作或看作“老鼠”“蚂蚁”“青蛙”“蚯蚓”“狗”等的一分子,这样写作虽然在视觉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实质上并未直击现象的本质,造成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漠视人类的生存發展,站在动物的角度蔑视大众,将诗歌的审美视角异化。“打工诗歌”中更多表现的是普通工人进入城市,那种归属感的缺失,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丧失对城市的兴趣却为了生计不得不留在这里,由此“愤而为诗”。这样的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身居城市的人以深思和同情,可过度地运用大众的同情心理而缺乏自身独特的生命体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远的。比如被一只老鼠感动:“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张守刚《老鼠》)比如在蚂蚁窝上欣赏风景:“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没错,是蚂蚁窝/可以感受到它在风中不断摇晃/你看,那么多又黑又大的头颅/彼此参差着,攒动着。”(游离《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比如观看青蛙的跳跃:“一只青蛙 千万只青蛙/情愿奉献一切/让热爱者的欢笑/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刘洪希《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比如为蚯蚓落泪:“你不会流泪吧 蚯蚓兄弟/为乡音飘渺 为命运多舛/透过季节深处 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 便匍匐前进/失去了手你索性用头颅耕耘。”(罗德远《蚯蚓兄弟》)
(二)当代诗歌庸俗化倾向
所谓的庸俗化,就是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写作者妄想走一条捷径,更快地被世人看到自己“诗人”的身份,不惜牺牲自己的品性。有些写作者屈服于媚俗事件的极致叙述,有些写作者打着生活诗歌的幌子招摇撞骗,有些写作者则干脆走进浅白叙事窠臼。同时,还因为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被娱乐与市场操纵,各项“诗歌大奖”也席卷而来。
1.庸俗化倾向中的“媚俗”现象
庸俗化倾向的“媚俗”大都集中在当代诗歌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等现象上。这种“挑逗”词语的使用,实则是肉体的狂欢,是大众生活进入审美化之后,庸俗化的表现。而且这方面的写作者还聚集到一起,为自己的这种写作倾向大张旗鼓地命名、欢呼。比如沈浩波的《一把好乳》与伊沙的《阳痿患者的回忆》,单从题目来看就足够让人侧目,“肉体”狂欢在内容中更是比比皆是。“后来居上”的李少君,比沈浩波宣称的“男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漏洞”[3] “更胜一筹”,把“下半身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作品中“老是喜欢盯着女人的奶子和‘脐下三寸’,总是弥漫着一股腥臊的荷尔蒙气息。”[4]如“春天一来,男人就像一条狗一样冲出去/吃了壮阳药一样冲出去/趴在别的女人身上喘气、喊叫/深夜,又像一条狗一样回来。”(《老女人》)“清早起来就铺桌叠布的阿娇/是一个慵懒瘦高的女孩/她的小乳房在宽松的服务衫里/自然而随意地荡着。”(《四行诗》)这样的作品非但没有遭到大肆地批判,反而被鼓吹其大胆、奔放、自由与抗争,他的后继者们还在大力发扬。“最后一次,他握住我的乳房又松开了手/像是早已接受这结局的虚无。”(莫小闲《情人正在老去》)“她们夜里像隐忍绽放的海棠/用力推开比爬架子还要性急的男人/你又贪,明天在架子上腿软!/即使例行一周大事,也会咬住嘴唇,被角……咬住男人粗壮的肩膀和沉重的喘息/咬住架子板搭成的床波浪似地摇晃。”(英伦《姐妹》)
2.庸俗化倾向中的“倡懂”现象
庸俗化倾向中很多写作者还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幌子,大肆鼓吹复归诗歌的大众化。追求平易近人、浅显易懂的诗歌,这个主张没有错,我国的诗歌传统也有类似的提倡,可浅显易懂并不意味着“大白话”和“分行成诗”。这时的“倡懂”已经远远脱离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中“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真谛,“口水诗”“羊羔体”“白云诗歌”(“乌青体”)等,哪里还有诗歌的含蓄,哪里还有诗歌的韵味。
一是“口水诗”。“口水诗”顾名思义就是口水从嘴里流出来一样随便地写或说。这一写作特点的开启应该与赵丽华有着很大的关系,她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还让她得到了“梨花体”派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其實这就是一句话,分成四行书写而已,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美国人威廉姆斯的《便条诗》:“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可能是/留着/早餐用的/请原谅我/它们太好吃了/又甜/又凉。”简单的一句留言,分成行就成了诗,那我们能不能在报纸上随便找个句子分行就成诗呢?其实这个做法外国人也发明过了。
一是“羊羔体”。这一“雅号”的获得者是当年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车延高,他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另一种口语诗。无论是《刘亦菲》还是《徐帆》都是用记叙文的句子写作,只是分了行而已。“我和刘亦菲见面很早,那时/她还小/读小学三年级/一次她和我女儿一同登台/我手里的摄像机就拍到一个印度小姑娘。”(车延高《刘亦菲》)当然,大众关注他这种作品的同时,更饶有兴趣的是他当年省纪委书记的身份。
一是“白云诗歌”。“白云诗歌”又被称为“乌青体”,是因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而得名。他在其中写道:“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此作品一出再一次“刷新”了大众对诗歌的认识,诗歌的神圣性的地位又一次被践踏。
总之,我国当代“泛诗人化”的倾向应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审美泛化”相关联。“随着中国改革力度的推进,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出现如同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后现代的景象,购物广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酒吧歌厅里灯红酒绿肆意狂欢,艺术画廊里人潮涌动却自顾拍照晒朋友圈,这种光和影的炫目,视觉和听觉的交织,充斥着大众的日常生活。”[5]大众正经历着一场当代“审美泛化”的“蜕变”。这场“蜕变”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中发生,前者将“审美的态度”引入日常生活,后者力图抹去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审美泛化”很容易造成价值领域的“真空”,需要大众清醒地对待周遭种种诱惑。在现代的语言环境中,大众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会写作。”针对这种“泛诗人化”现象,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会写字的人叫做诗人,也不可能把会写几个断行或押韵句子的人都叫诗人。诗歌与诗人的真正含义应与自然、社会、人类自身三个方面,保持密切地联系。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当代诗歌圣殿的重建
当下诗歌的种种问题,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诗歌这一传统文学体裁,几千年的古诗传承,百年的新诗探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中汲取到有利于诗人坚守、诗歌创作的精髓,足以去抵制消费主义经济洪流对诗歌的冲击,重新建构起诗歌的圣殿。
(一)寻找诗歌的诗意所在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物质、现实状况与此前大不相同。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大众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也有着明显的提高,但在消费娱乐中伴随而来的也有轻浮、污秽、堕落的社会现象,比如标榜时尚前卫的攀比消费、追求政绩的形象工程、暗藏“潜规则”的娱乐圈文化圈等等,他们披着“审美化”的外衣,却是对美的亵渎。写作者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是很容易产生“异化”“庸俗化”倾向的,重建诗歌圣殿关键就在于寻找被世俗“遮蔽”的诗意。
1.诗歌写作者要以“心灵的诗意”发现“诗歌的诗意”
首先,所谓“心灵的诗意”,就是写作者内心要保持敬畏、勇敢、坦率、真诚和天真,无论是伤感还是喜悦,无论是振奋还是低落,一颗“诗心”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明朝末年李贽的《童心说》,也提倡要真实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赤子之心”。无独有偶,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艾伦·退特也说过:“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诗人对谁负责呢?他对他的良心负责。”[6] “良心”也就如李贽的“童心”一样,呼唤着纯真、真挚的诗篇。其次,“真”是“心灵诗意”的内在,也是“诗歌诗意”的诉求。反观当下的诗歌写作者又有多少人在表现“真”。“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口水诗”等等一系列诗歌写作的变异,在这些所谓的“诗人”笔下也是有“真”的,是真的欲望、真的贪婪、真的异化。当然,当下诗歌写作者中也不乏追求内心诚挚、纯真坦率,比如:“雨天,天空响起三声闷雷/雨水便开始在上面流淌/我没在意后来雨水流向了哪里/我只记得两片亮瓦在一场雨后/冲洗得特别干净、明亮/母亲借着一片亮光缝补我的白衬衫。”(田禾《两片亮瓦》)在诗人的眼中雨水与亲情交织,亮光不仅是自然之光也是心灵之光,是母亲的,也是孩子的。
2.诗歌写作者要坚守诗歌的精神性与神圣性
真正的诗人,无论他的创作类型是哲学的、宗教的还是艺术的,诗歌中一定包含着诗歌精神性、神圣性的价值。要坚守精神性,诗歌写作者本身就应该具有神性的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持“道的无限性”。正如丁来先先生所说:“一个诗人,只有他的身上真正具有那种道的无限性,他才能够完成诗歌的较为高级的任务,也才能够通过其诗作让这个破碎了的世界图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完整与完善。”[7]“破碎了的世界图景”,就是大众面临的现实世界,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下的物质世界。真正的诗人不是去打破已经破碎的世界图像,而是去复原在“神性”基础上的“精神世界”。当下,也不难看到诗歌写作者的努力,比如“面壁者坐在一把尺子/和一堵墙/之间/他向哪边移动一点,哪边的木头/就会裂开//(假如这尺子是相对的/又掉下来,很难开口)//为了破壁他生得丑/为了破壁他种下了/两畦青菜。”(陈先发《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诗人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审视着面壁者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生何尝不是“面壁”与“破壁”的一生,人生真谛在“两畦青菜”中升华。
3.诗歌写作者要始终胸怀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
首先,人文关怀就是要与读者的心灵走向一致,写出来的作品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的心灵诉求并非指那些被社会世俗化的要求,这里的诉求远离物质、利益和欲望,最终指向人类美好的心灵。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也谈道:文艺创作者“要用全部的热情和真诚的人格力量去拥抱生活,把人民正确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愿望化合为自己的艺术血肉,升华为独具个性和感性生命的艺术力量。”[8]这里的“人民正确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愿望”是当下诗歌写作者必须认识到的,人民的正确思想而不是“一小撮”人的被“异化”、被“腐蚀”的物欲私念。
其次,社会担当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者时刻保持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当下的某些寫作者,打着自由的幌子随意写作,他们在淡忘、漠视写作者的历史使命,毫无顾忌地追求金钱、利益和欲望。但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与其相对的是义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代会上所讲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9]一样,诗歌写作者也要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显现的种种弊端,勇敢地走在文学艺术的复兴之路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创作出具有高尚品质与丰富精神内涵的诗歌。
(二)寻找诗歌审美向度
现代社会的大众,开始以追求视觉、听觉感官的快感为审美需求。在视听觉感官下,大众是分不清美感与快感的,一旦美感的要求放松警惕,快感就会脱缰而出,大众开始追逐着奢靡、华丽的对象。当然,不能否认美感与官能感受的关系密切,马克思也曾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话,但是官能的愉悦并不代表庸俗的感官狂欢。在欲望的刺激下,在感官的沉沦中导致了精神的沦丧。“一切向钱看齐”的价值偏差,充斥着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大众一头扎进被资本、权力、科技控制的社会里,逐渐迷失自我存在的意义,成为物质生活的傀儡和附庸。如何让大众重新回到文学的审美,诗歌的欣赏,这需要诗歌写作者对诗歌本身的建构,通过对诗歌审美向度的寻找,使得大众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拥有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与超越性。
1.诗歌需要具有独特的形式
首先,诗歌的形式需要色彩美。诗歌写作者和画家一样都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身处的世界,强烈的色彩感能够引导欣赏者走进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色彩通过人的感受、联想、情感等的中介而可能具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含义。”[10]因此欣赏者在期间感同身受进而领悟诗歌的魅力。第一,色彩感需要丰富性。“色彩类由红、橙、黄、绿、青、蓝、紫以及由它们以各种比例混合而成的无数种颜色。”[11]具体到当下诗歌写作者的色彩运用上,色彩丰富性的作品还是非常少有的,需要当下诗歌写作者进一步提高。第二,色彩感需要有层次。当然,诗歌写作中也并不能一味地色彩填充,需要适度而又有层次。
其次,诗歌的形式需要“建筑美”。这里的“建筑美”是重提闻一多之说,但又不同于闻一多之说。在闻一多看来的建筑美是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12]自由新诗的产生本身就是在对古代律诗形式上的冲破,新诗的句子形式自由,在长短不一的排列中尽显“建筑美感”。当然诗歌写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诗歌的“建筑”水平也就好坏不同了。
2.诗歌需要具有诗性的语言
首先,诗性的语言是诗歌魅力的所在。语言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至关重要,不由得想起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但当代大部分的诗歌写作者,为了所谓的“个性化”,即兴拆解,随意搭配,粗糙滥用,把语言破坏得七零八落。比如“两张纸屑在首义广场上空飞舞/婉转,轻逸/肯定不是风筝。我发誓/当它们降下来/以蛇山的沉郁为背景/我可以感受到它们的重量/而当它们高于山顶/我的视线无以为继/如此被动地飞/看上去却是主动的/阳光照在纸面上/我险些看见了黑暗的笔迹/而奇怪的是/那天广场上并没有风/两张纸屑飞累了以后/依然依偎在一起。”(张执浩《奇异的生命》)这首诗还有一个身份,第二届“陈子昂诗歌奖”获奖作品,而语言却像是思维错乱的醉话。要知道真正的诗歌语言是“纯粹性、精微性与精神光芒的言语”[13],这才算得上诗性的语言。
其次,诗性语言能够唤起欣赏者的想象力。第一,诗歌的写作者为能够唤起阅读者的想象力,营造一种朦胧的美感,会经常采用一些写作手法,比如象征、比喻、隐喻等等,其中象征因为其符号与意义之间的隐秘性,使得诗人经常使用。第二,诗歌的写作者也不能够忽视语言的跳跃性。语言的跳跃中所形成的“空白点”和逻辑衔接时造成的“空灵感”,更能够考察诗歌写作者的“功力”。比如“她来自比道路更遥远的地方/她触摸草原、花朵的赭石色/凭借这只用烟书写的手/她通过寂静战胜时间//今夜有更多的光/因为雪/好像有树叶在门前燃烧/而抱回来的柴禾上有水珠滴落。”(法国诗人博纳富瓦《雪》)
最后,诗歌写作者既需要高超的语言表达,也需要警惕单纯的文字游戏。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高超的语言表达需要诗歌写作者运用一些技巧和手法,但要合理利用。不能为了象征而象征,为了隐喻而隐喻,如果这样,非但不能最终达到目的,还可能“事倍功半”写出一个“四不像”的作品来。警惕单纯的文字游戏,可当下的某些诗歌写作者却不以为然,拿着技巧当法宝,比如“化验这本书,它的高速公路试管里淌出的墨渍/挖掘机履带的印刷体,土地在它日益扩大的嗥叫前后退//在它辉煌的笔杆下我们挖出自己的眼,铲断我们的手/当昨天消失。”(蓝蓝《钉子》)写出一些梦中的呓语。
3.诗歌需要具有“天地”的境界
所谓“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先生针对人生方面划分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杨守森先生则把这一人生境界化用到了评论文学创作上。即,作品的自然境界表现“注重的只是对客观事物或生活现象的描摹,或主要是作者本能经验的呈现”;作品的功利境界表现“一是抒发个人怨愤,二是批判社会现实”;作品的道德境界表现“一是批判落后,二是痛恨于道德的沉沦,三是呼唤道德良知的觉醒”;作品的天地境界表现“作家能够站在宇宙之一员的立场上,以凌空高蹈的博大襟怀,面对现实,观察万物,体悟人生,从而在作品中开创出更为宏阔的诗性精神空间。”[14]依次来看,文学艺术的境界是从低到高的,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同样适用于这四种境界。诗歌需要有“天地”的境界,只有诗歌写作者达到“天地”境界的时候才能实现。纵观当下的诗歌,大部分还停留在“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少数“道德境界”的作品又因为缺少诸如独特的形式、诗性的语言而“泯为”常诗,更不用说具有“天地”境界的诗人和诗歌了。我国新诗的成长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结语:
当“审美”进入“日常生活”后,因为“审美泛化”“审美异化”,再加上日常生活领域的宽广,使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满“艺术品”。“艺术品”的泛滥带来的不是艺术的繁荣,而是人类审美的疲劳、麻木,也使真正的艺术品陷入了没落的境地,被贴上“腐朽”的标签。由此西方大批哲学家比如黑格尔、阿多诺、丹托等人,开始思考艺术终结的问题。当然并非如此,日常生活处于审美化中并不会导致艺术的终结。主体在审美实践中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可以突破日常生活的“世俗化”的束缚,从中发掘出有利于藝术产生的积极因素,另外还可以利用艺术自身固有的价值冲破日常生活中“世俗化”的藩篱,回归到艺术、审美的康庄大道。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代诗歌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1][英]费瑟斯通著.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94.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7.
[3]朱大可.流氓的盛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84.
[4]唐小林.当代诗坛乱象观察[J].文学自由谈,2017(8).
[5]李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两幅“面孔”[J].南腔北调,2018(5).
[6]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68.
[7][12]丁来先.诗人的价值之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1-252.
[8]李鲁平.文学艺术的伦理视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5.
[9]习近平.中国文联第十八次全国代表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大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
[10][11]王杰.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2-74.
[13]闻一多.闻一多论新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82.
[14]杨守森.艺术境界论[J].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