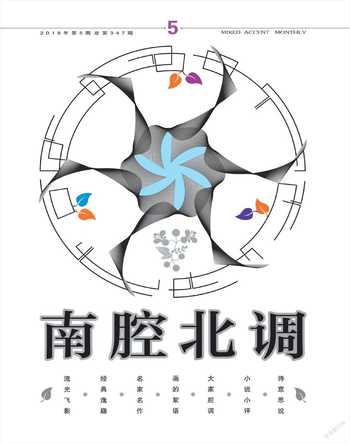沈从文的乡土
2019-09-10高盛
高盛

一.沈从文是活在今天的
对同一所见,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风景。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境,也会有不同的观感。天上没有两朵完全相同的云,地上本无一模一样的人。我读沈从文,进入他笔下的湘西,边城的世界,缱绻的乡土,便类似于这一种。
沈从文,湘西,凤凰,《湘行散记》《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流播近百年。前30年蜚声文坛,后30年寂寞无名,再30年添为经典,至今而为一种传统。也许并不被庙堂奉若神明,然而创作者却颇为亲近,呼之为别开洞天的“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他记得的那样多,知道的那样多,想了的那样多,写了的那样多,这真是少有的事。”(汪曾祺语)。多年来关于他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湖南师范大学的凌宇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新颖教授,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等都有持正公允的著述。如果对这些逐一检索,浏览,考证,恐非我等力所能及。遂但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读者一己之愿,沿着沱江、辰河、沅江的水岸做一次流浪,顺流也好,逆流也罢,不管蜻蜓点水抑或走马观花,渴望沉浸到沈先生深情挚爱的边城故土,到他丰润的笔尖、柔软的心头去游历一番,来做些许文本阅读的坦诚体验。
笔者不才,30年前初识沈先生名讳,大约在1991年,30年后重读《边城》已经到了2018年,时光悄然流逝了近30个年头。在这30年里,“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张充和语)的沈从文,究竟在心里埋藏了多深我不确切,唯一确切的是遗憾没有通读,更别说读通。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束之高阁,谬之大矣。
由此看来不读书虽然犯下过失,但也不见得就活不下去,似乎助长了愚昧的读书无用论。可是除非你心甘情愿陷身于赚钱,花钱,喝酒,恋爱,打麻将,扯闲淡,浑浑噩噩欲罢不能的沟壑,那么读书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可是一旦读了,整个人终究不一样。你将从读书中找到思想的灯塔,灵魂的烛光,精神的坐标。或许从此你也将视读书为人生一大乐事,不会堕入沈从文所说的“一种准乎自然的生老病死”,更不会留下“青年时有时间没读书,中年时想读书没时间,老年时眼花体弱什么也读不了”的慨叹。
前几年曝光的某些高官、富商、明星,丢掉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沉沦于自我麻醉的唯心宿命论,出门花天酒地,闭门吃斋念佛,天南地北拜师傅,东寻西找认干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就可以保佑一生一世,福荫三生三世,实在是钱赚得多了,书读得少了,四体不勤享受惯了,心脑手眼逐渐荒废了,最终找不着北的缘故。除了歪门便是邪道,除了荒唐还是荒唐。其实,工作和劳动,公益与慈善,就像耕读传家,书香门第,才是贵人、富人、明星们心灵皈依的宗教,把这当作信仰去做才是真正的内心解脱之道啊。
通读一遍沈从文(说是通读,其实他的全集还有许多不曾读过),循着《湘行散记》的足迹,到《长河》两岸,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边城》做较长时间的停留,多么渴望遇见那个刚刚喝过一杯甜酒的非常擅长用文字让人灵魂轻轻浮起的“乡下人”,或者邂逅名门闺秀的“三三”,又或者那个成天忙碌于摆渡而纯情羞涩的小姑娘“翠翠”。
我读沈从文,隐约之间有一种意识在闪烁,有一种感觉在跳跃,有一种悟思在萌芽,有时模模糊糊,有时断断续续,有时影影绰绰,有时又分外明朗:沈从文分明在借桃花源的表象,用小说性的语言描述他民生观的内核。这一点《边城》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边城》“美丽”,我想这是对的;有人说“忧愁”,我想这也是对的;还有人说“美丽的忧愁”,我想这也是对的。可是无论谁读《边城》,抢眼的首先还是那幅渔歌缠绵的山水美图。是的,车路,马路,山路,水路,农人,兵士,商贩,水手,湘西到处都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人。放眼全国也到处都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人。不管是尘封已久的1930年,还是当下的2019年,这幅图画似乎都不曾被谁从我们头脑中轻轻抹去。
我们如果以《边城》为出发点,那么《湘行散记》是序,是采风,是写生;那么《长河》就是跋,是下篇,或者说姐妹篇。《边城》写“昔”,写“常”,写久远的记忆;《长河》写“今”,写“变”,写眼前的人与事。只是这个“今”、这个“变”并没有写完,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搁置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写完,为什么被搁置了,按沈从文自己的意思,大约是再也“不忍心写出来了”。
看得出来,沈从文是以一个地道的边城的边民之心态,之眼光,之视角,却又是跳出了边城之外,而不是站在所谓精英的角度,来追忆这座位于湘川黔边界的边城的边民的日常生活的。恰巧,笔者亦是以一个地道的边民之身份来阅读这些文章的。我整个春节假期几乎都在领略这些美妙的文字,每逢有趣的章节都会品读两三遍,其滋味远超走亲访友餐桌上的大鱼大肉。在全面决胜小康之年的今天,酒足饭饱成为常态,各种酒宴隔顿不隔天,天天都像过年,我们以边民的心态来阅读边民的文章,自然别有一番感思的。或许也算普通读者与高明作家之间穿越时空的交流互动。我说这话内心是很真诚的。而真诚恐怕也正是沈从文基本的创作态度。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说到。
沈从文的创作态度不是要人消沉出世,而是要人振作进取。《边城》也好,《长河》也好,《湘行散记》也好,都寄寓着这种向往。在小说里,作家往往会把主观的意愿蕴含在具体的表象之中,借作品之手畅行己意。这方面沈从文堪称圣手。诸如他把“乡土朴素的人情美”,“城市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民族兴衰,事在人为”的愿望,等等,对过去美好的保留,对现在堕落的悲痛,对未来期望的热情,都一一诉诸笔端,而且永葆一种自始至终不折不扣的执拗。
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曾评价说,如果按照进化论的逻辑,沈从文的创作似乎看起来真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笔者以为沈从文的创作恐怕更应看作是一种记忆、留存和保鲜——对农耕社会的记忆,对乡土传统的留存,对历史陈迹的保鲜。沈从文也提醒过我们:“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們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由此得见,他的《边城》并非挽歌,也不是牧歌,而是希望之歌,向往之歌。套用一句“只对金钱有感情”的现代人的话来说,这叫“冻龄”。就像谭咏麟宣称的“永远25岁”,某大腕女星渴望的“永远21岁”,普通人挂在嘴边的“今年18明年17”的俏皮话。年轻貌美的不想长大,年老色衰的不愿离去。可是即便拥有沈从文留存的乡土经典,我们也日益面临彻底失去渐行渐远的乡愁。
经典永不过时。张新颖说:“沈从文不是过去的人,不是过气的作家,他是活在今天的。”——是的,或许只有活在今天的沈从文还能留给我们一丝安慰。而这当然就是经典的价值。
二.中国乡土文学源远流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乡土文学一直是主流。“五四时期”、“建国前后”、改革开放40年“新时期文学”,乡土文学均占据着主要地位。笔者以为:在城市文学开始崛起的新时代,乃至目前所能眺望的未来,乡土文学将会一如既往占领主流文学阵地。
我这样说也许读者诸君马上会提出异议:你说乡土文学占据了既往文坛的主流,但是未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可就很难说了。的确,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提法。因为这不但关系到乡土文学的渊源问题,也关系到乡土文学的流向问题,以及未来乡土文学能不能持续、够不够坚挺、会不会消失的问题。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他说乡土文学终有一天会消失,但不会那么快终结。好吧,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孕育、发生、发展、成熟、衰老、消亡的过程。但对乡土文学来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得可能会超越我们任何人的想象,就像宇宙诞生、人类进化一样,理论上可能有一个起点,但终点遥遥无期,甚至永远看不到终点。
因此,在这里我仍然想弱弱地说一句:只要人类还在,恐怕乡土文学永远不会消失。即便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对于乡土的回望和眷恋,恐怕不会厌弃而只会更加强烈。况且就我的理解,贾平凹对乡土文学谈的最多的不是“有一天会消失”,而恰恰是“不会那么快终结”。我想这应该是他忧虑所在的言外之意。
那么,乡土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又十分纠结这个命题。简单释义一下,乡土文学是指描述某一地域而形成的文学作品形态。这种文学作品不但描述地域风土人情,也从风土人情看世界,看人生。这是我的理解。
这里还有必要释义一下乡土这个概念。就笔者看来,乡土是个地理范畴也是个心理范畴。就地理而言,乡土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城市是乡土的聚点,乡土是城市的延展。就心理而言,生我养我的地方皆为乡土。比如故乡,家乡,从前的家乡,现在的家乡。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天下之滨莫非王臣。这个王就是国,这个土就是家,这个臣就是我们自己。乡土乡土,是我们的国,也是我们的家。
如果说乡土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从世代变迁而来的,从母体与生俱来的,那么乡土文学就是每个人天赋的文学本能,只是你有没有发掘它而已。久而久之,文而化之,乡土与乡土文学就变得好比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哪一只鸡下了一个漂亮的蛋,哪一个蛋孵了一只漂亮的鸡。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从乡土而来,那我们身上都天生携带着乡土的DNA,都天然地散发着乡土的气息。无论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无论你身在城市还是根在乡土,你必然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也许是身的往返,也许是心的往返。尤其是当你人到中年,远离故土,而恰巧你又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文学趣味,那么你对乡土的怀旧,留恋,反思,向往,都足以燃起你无限的乡愁。如果情之所至再行诸文字,那就是乡土文学啊。或许也能给他人以同样的怦然心动。
因之,城市与乡村,都市与边城,全局与一域,必然在乡土文学作品中要么非此即彼,要么纵横交错,或通畅,或阻碍,或融和,或冲突,或激情汹涌,或旁逸斜出,势必粗狂与柔美并存,现代与传统兼容,文明与愚昧杂糅,而生发出各种摇曳之态来。
从古到今,有多少文人骚客被乡土缱绻,有多少乡土文学作品被后世传颂。《诗经》国风,屈宋楚辞,嵇康阮籍之竹林七贤,唐诗宋词之乡旅边塞,及至明清小说、小品文,描写乡土之作比比皆是。又譬如,李白流连高山大水,杜甫关心民间疾苦,白居易要作老妪听得懂的诗歌。苏东坡为官一生跌宕起伏,其绝妙好诗好词好文,都出自穷乡僻壤的黄州惠州儋州。曹雪芹出身官宦之家,可惜到他这一代已没落了,据说他穷居西山批阅《红楼梦》之时,“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他们哪一个不是眷恋乡土之人?
到了“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大批作家都在写乡土,也大多以乡土文学作品闻名于世。鲁迅和周作人写绍兴,茅盾写上海忘不了双桥镇,老舍写北京离不开大杂院,沈从文却偏爱写湘西的边城。接下来赵树理写解放区,孙犁写荷花淀,分别形成了乡土文学的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柳青写《创业史》落户农村十几年。
后来,古华的《芙蓉镇》,莫言的《红高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余华、格非、苏童的江南小镇,毕飞宇的王家庄,阿来的藏地等等,这些作家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毫无例外都浓墨重彩聚焦于乡土,从而奠定了乡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主流地位。现在进入新时代,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里也不乏钟情于乡土文学的坚实拥趸。而他们正代表着中国乡土文学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的基本流向。
不过,乡土文学写乡土,并非仅仅写你的家乡,写你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家乡的事。而是可以写你所遇到的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事情。有时是这个人的头脸,那个人的手脚;有时是这个地方的经历,那个地方的体验;有时是这件事情的起因,那件事情的过程,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结果,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你的生花妙笔,你的左顾右盼,你的前后勾连,你的左右逢源,你的八面玲珑,你的张冠李戴,你的移花接木,你的乾坤大挪移,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就像果树嫁接,你有一个根,也有一个梗,你可以让它开一个花结一个果,也可以让它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甚至多分杈多接枝,直到花开满树,果挂满园,让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
可能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以为写乡村才是乡土,写故乡才是乡土,写其他的地方算不得乡土,而且拿沈从文只写湘西、莫言只写高密东北乡以为佐证。又或者有人说写一个地方才是乡土,写几个地方不是乡土,并且又找了《诗经》写了几十个诸侯国之风、苏东坡写了好几个州、鲁迅和毕飞宇都写了好几个地方作为佐证。然而综上所述,实在来说这些认识不说偏执至少还不够清醒。
三.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传统
沈从文半生成就的湘西系列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上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学史意义,现今而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如何在文艺批评界得到进一步解析、阐释、具体化,乃至重新认识、发掘、经典化,是一个具备了足够充要条件的研究课题。
所谓沈从文传统,笔者勉为其难罗列诸端:
其一,沈从文乡土文学描写边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及其自然渗透而出的人性人情美,正是纯天然、原生态的湘西写照;他非常注重描摹乡土人事的实感,质感,情感,性感,发现真,呈现善,表现美;而乡土是美好的,城市是糟糕的,“城市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欠缺乡土“朴素的人情美”,欠缺乡土“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边城》是他童年眼中的乡土,《长河》是他成年眼中的乡土,而且叙述视角就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的口吻。
其二,沈从文乡土文学从“‘五四’精神:科学、民主、自由、进化论”四个宝贝之中,拾取了一个叫做“自由”的瑰宝(“自由”现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因为时代释义不尽相同,我们这里仅取“创作自由”一说),在文学创作上不为政治,相信文学即便无益于政治,亦将有益于人类,而唯愿供奉人性的小庙;向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追求乡土文学的纯美境界。
其三,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像一口大锅,水是容器,人情是汤,爱情是主菜,妓女是调料,水越轻越柔,汤越浓越香,情越纯越真,料越土越重;也许他并不着力于爱情,而更关注爱情背后的生活,也许二者同样着墨兼而有之,悠然自得地在生活中谈“情”说“爱”,毕竟爱情是生活的明珠,而生活是爱情的渊薮。
其四,沈从文乡土文学的语言像个大萝卜,朴素,实在,耐看,水分饱满,滋润可口,而且富有营养,是菜园里的尤物,餐桌上的佳肴,舌尖上的美味,百吃不厌最养人;又像个大箩筐,生活,生存,生命,人性,人情,人生,什么都能装,什么都装得下;还像个大篦子,在生活的原始森林里,在人事的汪洋大海中,密密地梳篦,细细地打捞,篦过的都有成色,捞起的全是精华,完全可以称之为“篦子笔法”。我有时甚至想不如干脆呼之曰“沈篦子”。
其五,这恐怕也是沈从文乡土文学最重要的特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一种结构之气,不但一部小说、一篇散文有这种结构之气,几乎全部的写作、全部的作品都蕴藏着这种结构之气——他与众不同的民生史观体系。这个独特的价值体系支撑了他的写作,给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光,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磨难。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大约可分两种流派:一种鲁迅式的革命启蒙的乡土文学,革命者看到故乡的愚昧,落后,颓败,不作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着笔于讽刺和揭露,主旨为“改造国民劣根性”。另外一种就是沈从文式的自由浪漫的乡土文学,城市不怎么样,乡村还保留些美好传统,可是乡村也因大环境慢慢变坏下去,于是又多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虽愿为民族品德的消失而去重造,并发出“民族兴衰,事在人为”的呼号,但途径可能并非鼓吹革命。
沈从文式的乡土文学与鲁迅式的乡土文学,身份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所见所闻所想所写均有不同。鲁迅是革命急先锋,沈从文是改良慢郎中;一个拿笔做匕首投枪,一个无意于政治不受鼓动。虽然他们两人有着颇为相似的人生阅历:鲁迅弃医从文,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革命;沈从文弃武从文,从此不愿卷入政治或战争。但他们两人都矚目农村,也因此成就了各自的乡土文学。
然而,中国当下的乡土文学与鲁迅式或沈从文式的乡土文学已经非常不同。随着40后、50后、60后的乡土记忆逐渐老去,70后、80后、90后的乡土印迹逐渐模糊,更因为“全媒时代”迅速到来,当下的乡土文学已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本土文学。乡土即本土,城市亦本土。于是采取了零度姿态,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就让它赤裸裸地躺在那里。然而有人以城市为家,有人在城市漂泊,有人无所谓。城市的繁华无法慰藉内心的孤独,当不起一缕乡愁的温存。君不见人们身在城市,心早已开始逃离。人们更愿意往山的深处去,往水的深处去,那里有白云悠悠,鸟语花香,那里有热望的故乡,梦中的乡土……
都市发展多是靠外来人口推动的,本土原住民顶多算个支撑。深圳就是一本说明书。早茶,晚茶,宵夜,老火靓汤,充盈着满满的乡土味道。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可是这种滋味只有本土人真正体会得到,外来人是根本吃不出来的。笔者所在中部某市,按惯例排名,算得上一座名副其实的三线城市。可是这座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最引以为自豪的并非古城区、古村落多么让人魂牵梦绕,而是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雄心万丈的工业立市。
大城都市担当不了乡土之实,县城小镇也正在失去乡土称谓,越来越多的乡村也渐渐安放不下人们对乡土的寄托。振兴农村,精准扶贫,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我想就是要让农村像个农村,该种的种,该养的养,该游的游,该管的管,而不是到处搞开发或工业园,把农村做成城市的翻版,环境破坏,生态受损,然后再花费巨资去进行漫长的治理。那不是振兴,那是震晕,可千万别跑偏了。
文学乃人学,小说即生活。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每个阶段每个节点就相当于一部中短篇。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亦即小说。目前中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一半一半,但大部分人的身心还挣扎在半城半乡之间,经常陷于一种纠结的情绪当中。这种纠结简直是个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断无挖尽的一天,也给乡土文学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土壤和广袤的创作空间。此情此景,斯人斯境,千头万绪,如此种种,乡土文学什么时候写得了,又哪里写得完呢?
有人顾虑乡土文学正在消退,有人说后续青黄不接,有人说已经快要消失,说白了都是一种纠结与焦虑。其实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民生越幸福,人们越渴望乡土文学的洗礼。物欲横流何时够?人间最爱是清欢。当人心陷入迷惘之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或能给我们灵魂以救赎。他笔下的那片柔情、纯净、明亮的乡土世界,自然而然将成为我们内心分外向往的目的地与栖居地。
四.《边城》的真善美
《边城》集中展现了沈从文乡土文学的美好传统。那首记忆中的田园牧歌,那片令人神往的乡土风光,那份赤子之诚的温爱,那种不屈不挠的眷恋,“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氛”。人事是真的,人性是善的,人情是美的。由真,而善,成美。也许沈从文的创作意愿并不为引导我们去湘西旅行,从而提供一部现代版的《桃花源记》,可是在《边城》的世界,他没法不让读者自发去旅行,并在旅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体味他曾经有过的思考。
《边城》予人的第一印象,是小说的故事,结构,语言,真的很简单。反复揣摩之后,却又觉得这部小说正需要这种简单。因为边城的边民,生活本来就是极其简单的,而唯有简单能透出真诚。生活是真诚的,作者也是真诚的,而唯有作者的真诚,才能发现生活的真诚,并真诚地讲述生活的真诚。真,需要实,因此沈从文用篦子一般的写生素描的笔法写实了。这种实,是所见所闻所忆,并非他的猜测、预测,而是他的发现。“就沅水流域人事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地保留下来。”诚然,他真的做到了。

善是个什么东西?善就是好,对自己好,对别人好,核心是对别人好。仁者爱人,发乎仁心,见于善行,止于至善。边城的边民也爱利,也仗义。“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在那个边陲小城里,即便娼妓也有她们的眼泪和欢乐,也有她们的忠厚与温情。沈从文说“美在生命”。湘西,地理的边城,历史和文化的边城,山美水美人情美。爷孙情,爱情,兄弟之情,都散发着原始的本能的馨香。爷爷,重义轻利的朴实老汉;翠翠,心底单纯的孩子;黄狗,乖巧懂事的帮手;大老二老,兄友弟恭的手足;船夫,妓女,商贩,走卒,卑微得可以不一一言说其姓名,正如河街上来去匆匆的路人甲乙丙丁,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各人有各人的一份哀乐。“他们从不思索自己工作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他们知道吃好吃的,穿好穿的,玩好玩的,却不愿去想好想的,既不去想生,也不去想死,更不去想为什么生,为什么死,就这样浑浑噩噩度过一生,把一个一个日子打发下去。你不能不说这样活着也是一种生命本能的美,虽然这种美总夹杂着世俗的无奈和莫名的忧伤。
但是,“现代”二字毕竟也到了湘西。车路,传统的媒妁之言;马路,现代自由的爱情;碾坊,嫁妆丰厚的富家女;渡船,自食其力的贫家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什么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是嫁娶的资本。这两条功利之线也束缚着当时的年轻人对爱情的选择。一次并不明朗的说亲,成与不成,无须大惊小怪,千百年来边城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反观当今的剩男剩女,爷奶爸妈齐上阵,催婚逼婚代相亲,手拿文凭、房产证、工资表,也难以找到心仪的对象,似乎反不如当年的朴素举动。你说这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
重读《边城》,我不想拘泥于小说的故事或结构之类,想着重探讨沈从文的篦子笔法(前面说过这是我的提法)。这种说法常人可能所见不多,但有两件小事你想必经历过。一个是理发。你看理发师手里总会拿一把细密的梳子或篦子,在你头上梳篦一番,一为清除碎发,一为立起发根,好下剪刀,也为好看。好的理发师总会一根一根帮你剪,时间长一点,价钱贵一点,当然理得也好,頭上功夫了得。另一个是小眼网捕鱼。在海边,江边,河边,湖边,再不济也在堰塘边,一网下去,大鱼捞不到,捞起的全是小鱼小虾,个头差不多,拖泥带水,活蹦乱跳,味道最鲜。
梳篦用眼,打捞用心。沈从文乡土小说梳篦过的,打捞起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小鱼小虾。《边城》的真,沈从文的天真感,首先体现在这里。这种笔法,看似混沌,实则梳篦;看似繁复,实则简单;看似平淡,实则有趣。这种生活和积累,轻声细语,闲言碎语,慢慢说起,娓娓道来,绝非惯于行色匆匆、快言快语、一目十行的现代人所能有的。非有严谨的态度,缜密的心思,踏实的作风,这种文章是做不来,也学不来的。
沈从文是一个真正写实的作家。他总是不慌不忙,不疾不徐,拿笔,运笔,起笔,落笔,手中一支笔,万变不离其宗,慢慢脱去矜持、生硬、浮夸、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直抵真实,像极了一个调动语言文字的大将军。记得在哪里看过一幅画,他一个人坐在小河边,慢慢抛下竹篾捞虾子。这真是鲜活的写照。
比如下面这一段,简单几句话,把乡土生活梳篦一遍,打捞起三五件日常的作息,勾勒出小城人家的居家琐碎。
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和青菜。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用棕衣作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他硬壳果,也多悬挂在屋檐下。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一座一座如宝塔。又或 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
又比如那条不知名但乖巧的黄狗。这个“黄”字暴露了它的身份和身价,并非纯种名犬。那是乡土最常见的狗,每个普通人家都可以养一只两只。在沈从文笔下,那么活灵活现。
黄狗坐在船头,每当船拢岸时必先跳上岸边去衔绳头,引起每个过渡人的兴味。有些过渡乡下人也携了狗上城,照例如俗话说的“狗离不得屋”,一离了自己的家,即或傍着主人,也变得非常老实了。到过渡时,翠翠的狗必走过去嗅嗅,从翠翠方面讨取了一个眼色,似乎明白翠翠的意思,就不敢有什么举动。直到上岸后,把拉绳子的事情作完,眼见到那只陌生的狗上小山去了,也必跟着追去。或者向狗主人轻轻吠着,或者逐着那陌生的狗,必得翠翠带点儿嗔恼地嚷着:“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且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谁学得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狗俨然极其懂事,便即刻到它自己原来地方去,只间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轻轻地吠几声。
沈从文篦子笔法的最大特色是真,最大特质是爱,对边城农人兵士的温爱,具有宏大的包容心。这就不得不说到善了。比如老船工不愿多收过渡人的钱,常常嚷着:“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到河街上买肉,他绝不肯多占屠户一分钱的便宜。又比如“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泅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顺顺的两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贩夫走卒一类的行脚商人,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上行船下行船,必定撑桨划船睡舱板,走山路也肩挑背驮,裤腰带上带短刀。“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在当下振兴乡村、精准扶贫、均衡发展的语境下,这种担当精神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底层奋斗的小人物也有他们的梦想,他们明白必须“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勿有所遗,不管大梦小梦都是中国梦,不管大故事小故事皆为中国故事。
《边城》的人情美通篇可见。比如端午节到了,翠翠和爷爷争抢着谁该去看船,谁该去撑船,有几句很妙的对话:
“人大了就应当守船呢。”
“人老了才应当守船。”
“人老了应当歇憩!”
“你爷爷还可以打老虎,人不老!”
又比如,爷孙俩相依为命,谈论到谁陪伴谁的问题时,也有几句读了让人既温馨又伤感,既快乐又凄凉的话:
“我走了,谁陪你?”
“你走了,船陪我。”
“船陪你,嗨,嗨,船陪你。”
“你总有一天要走的!”
“爷爷,我不走,我不去,我替船陪你!”
关于爱情当然是三个年轻人之间的事。翠翠与老二在河边初遇,从此心有牵挂,听说老二在青浪滩过节,故意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老二与翠翠心心相印,月夜过碧溪岨扮竹雀唱情歌,歌声扰乱了姑娘的芳心,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而摘下一大把虎耳草。因为两兄弟同时爱上了翠翠难以取舍,相约以唱歌的方式决定姑娘的归属。老大为成全老二下行船时遇险人被淹死了,老二因顾念手足之情心有所忌过川东下桃源,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让失去爷爷的翠翠对心上人美美的期待,蒙上一层淡淡的忧愁。
总之,评论者研究沈从文的篦子笔法是非常有益的。梳篦生活,全程扫描,既无遗漏,又经打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若稀罕,它便是个宝,看得你心碎,心动,心痒痒。你若无暇顾及,它们复归自然,自有他人采撷,收藏,淘洗打磨,价值连城。
五.历史像一条长河
沈从文在多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真的历史像一条长河。我想在沈从文眼里,这条长河是边城的长河,也是边民的长河;是历史的长河,也是文脉的长河。而《边城》的姐妹篇就起名为《长河》。《边城》写“常”,《长河》写“变”。“常”与“变”是历史的辩证法。当初那个“变”被搁笔了,那个“常”被打破了,现在恰恰又成为人们新起的向往。“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习惯的延续,在进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

这里有一个沈从文与众不同的创作观问题。他15岁从军,流荡于湘川黔边界旧军阀阵营里,看惯了杀戮和草菅人命,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要改造这个民族,1923年他弃武从文,成为一名北漂,受困于窄而霉的小宅励志写作,而后闯荡京沪十多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观。这种创作观,关注主流而不合乎主流,颇有一些不合时宜,就像苏东坡一样,在不合时宜的年代,做了不合时宜的人,写了不合时宜的作品。既不受革命派待见,也不受顽固派接纳。满腹经纶皆何物?一肚皮不合时宜。沈从文有独特见解不同于人,奈何他兼容于人,人却对他失之包容。
上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对时局,对革命,可以说还没有形成完整清晰的认识,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不可知的不确定的疑惑,对革命并不抱坚定的信念。他发现了国家与民族、城市与乡村面临种种危难,并试图有所改变,可是民族文化重造的出路并不十分了然。他只是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从自身阅历出发,形成并发出了朴素的思考和近乎偏执的宣言。但是理想的未来到底在哪儿,这仍然是个谜。正如《边城》里那座白塔,既希望它坍塌,又渴望它重建。
历史从来分两种,一种大人物的历史,一种小人物的历史。大人物的历史大江大河,碧波巨浪,波澜壮阔,但不见得是历史的全貌,或者说并非完整版,而只是历史长河里耀眼的浪花,洪流,洪峰。小人物的历史是水滴,水珠,水花,自然流淌,千百年来逝者如斯夫。每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都希望变成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设若大势所趋,英雄出现,弄潮儿应运而生。小人物也幻想抓住历史的机遇,可他们往往抓不住,抓不牢。他们活着无非为自己,为吃喝,为子女,蝇营狗苟,得过且过,并不真正懂得去追求精神上的价值。其实大人物也是从小人物冒出来的。英雄也是人民的一员。小人物的人生注定入不了史,只能添做一段流水,而這流水恐怕才是真的历史,真的人生。英雄也不例外。所以实在来说,人民只有人民称得上英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英雄。
文学通常扮演了书写小人物历史的重任。沈从文就是一个看穿了此道并热衷于此道的例证。他活在水深火热的革命年代,然而却执意回避政治和战争,与主流的革命文学脱节,一个人开独家药铺,创作他头脑中认定的乡土文学,书写小人物的历史,走上了不合时宜的“第三条路”,势必遭遇不可承受的重压。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人们也逐渐明白了,沈从文及其文学原来像一个心底单纯的孩子。非左即右,至少还有中嘛;非红即黑,至少还有灰嘛。说到底还是个思想解放的问题。不免让人感叹一句:短短几十年,历史的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了。
其实沈从文也是人民的一员。首先取决于你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他有儒家思想,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他有道家思想,顺乎自然,无为而治,自力更生,自生自灭。他也有佛家思想,生死有命,因果轮回,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他更有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民以食为天,耕者有其田,向往人性的善,人情的美,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新时代的民生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号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无疑比沈从文式的牧歌理想先进多了。
虽然沈从文的《边城》写了乡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也给了翠翠一个美丽的可期待的结局,但这个结局还带着隐痛,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到头来或许是个悲剧。据此我们应该可以说,这个福祸未明的结局是翠翠的结局,也是沈从文的结局,也是沈从文民生史观的结局。我们现在重新读起他,不是因为他多么高明,多么伟大,多么令人推崇备至,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