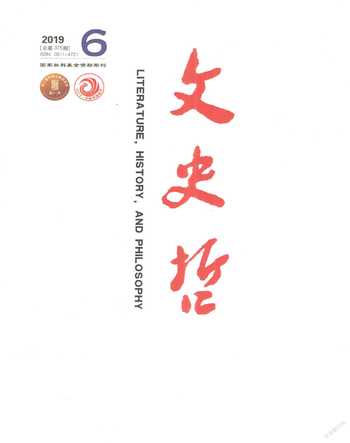选举制与推举制
2019-09-10谢文郁
摘 要: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治领袖的机制有很多讨论,但对儒家仁政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则几乎没有涉及。这两种机制可以分别被称为选举制和推举制,它们基于两条不同的正义原则,即:通过选票表达公意的正义原则,和在君子之道中呈现民心的正义原则。选举制以选票为决定因素,忽略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从而无视“公意”可能为恶的情况。推举制强调民心为政权之基,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持君子身份,敬畏天命而体察民心,行君子之道。但是,民心的不确定性使得推举制下的权力运作,可能走向结构性腐败。对选举制和推举制进行平行考察,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二者的基本思路、运作逻辑,及与之分别相应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特征。
关键词:选举制;推举制;正义原则;公意;民心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6.04
政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最高领袖的产生机制,或称君王产生机制。就历史而言,最常见的是血缘继承制,即子嗣在血缘关系中传承王位。近代以来,英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放弃了血缘继承制,而采用君主立宪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实际上的最高政治领袖(议会、内阁和首相)。其他西方国家陆续效仿而放弃了血缘继承制;虽然各国随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但民主选举却是它们的共同点。为了讨论方便,本文用选举制称呼这种政治领袖产生机制。就思想史而言,这种机制在卢瑟福、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说明,并在启蒙运动中成为全社会所共享的意识形态。鉴于西方世界通过选举制在政治治理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们往往把选举制视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在世界各地加以推广。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中国清朝政府于1898年和1905年先后有过两次以英国君主立宪制为范本而进行的所谓立宪改制,但都归于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终止了血缘继承制,建立了北洋政府(1912-1928),模仿西方各国的制度,甚至企图移植美国式的联邦制①。这些努力也未成功。相应地,中国思想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追求“德先生”(民主),企图在思想上发起一场“启蒙运动”,对国民进行教化,使选举制成为共识。其间虽因战争而暂时搁置,且有另类民主实践,但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却又得以在自由主义旗号下继续推进这个理念,直至今日。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进行的,直接导致儒家政治思想资源被弃置一旁。然而,在对选举制与中国社会之适应性问题缺乏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与讨论的情况下,强行推销选举制,一心一意要在中国社会建立一种选举制,这样的努力是危险的,也是难以成功的。
既然如此,便有必要回到更原始的问题上去:废除血缘继承制之后,除了选举制,中国社会在政治领袖的产生机制上是否还有别的选项?本文欲提请关注的,是孟子的推举制。孟子对尧舜让贤这个故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是推举制(也有人称之为禅让制)。不过,在血缘继承制的现实约束下,儒家一直无法在君王产生机制上落实孟子的推举制,这导致儒家仁政一直在瘸腿走路。为此,儒家便只好努力尝试教育现有的王子们,以期培养真正的君王。但就历史经验而言,这种教育大都是失败的。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昏君、庸君或暴君。无论如何弥补,符合儒家仁政要求的君王,始终都无法在血缘继承制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原因很简单,血缘继承制对儒家所期望的君王的培养和产生过程,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而相应地,在废除了血缘继承制之后,孟子所提倡的推举制就值得特别重视了。为此,本文将分别追踪选举制和推举制的理论预设和根据,在对比中呈现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所以,这不是在设计一种理想型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而是要通过平行地分析选举制和推举制,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权力运作做一些准备工作。
一、现代西方政治与选举制
在世界文明史上,王位占有者作为最高政治领袖,其更替模式有两种,一是血缘继承,一是暴力取替。相比而言,血缘继承是较为平和的过渡方式。而一旦出现昏君或暴君,社会治理就很难维持既定秩序而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社会秩序,暴力取替就成了唯一的选项。然而,暴力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历史上,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在这两种模式中,血缘继承一直是君王更换的首选模式;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暴力取替模式才出现。在这两种模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项?
我们先来追踪西方社会的近代史。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始于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这场革命的起因可以大致叙述如下: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Elizabeth I,1558-1603),得益于英国国力强大而出现了一批因海上贸易而致富的新阶层,或称新兴资产阶级【参阅马克思:《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83年,第247-253页。马克思认为,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是国内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宗教性因素(例如卢瑟福这样的宗教界人物)在英国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参阅谢文郁:《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他们通过利益交易或金钱购买而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控制了下议院,所以也稱为新贵族。他们的财富成了英国王室的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新贵族大都在尼德兰一带或长或短地居住过,深受当时欧洲大陆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影响,在宗教上采取新教立场(路德宗、改革宗、长老会等),因而追求净化英国国教而使之完全新教化(清除天主教势力),因而又被称为清教徒。也就是说,他们同时拥有三重身份: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清教徒。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在位期间,国王和下议院的关系日趋紧张,并于1642年完全破裂,导致双方进入战争状态,史称“英国内战”(1642-1651)。内战的前两年,议会军队在作战时虽占优势,却缩手缩脚。议会军的最高将领一直希望国王能够回心转意,和议会妥协,重新回到王位上。这种想法导致双方在战场上处于胶着状态。追踪其思想根源,在当时英国国教主导下,人们根深蒂固地拥有绝对王权和血缘继承制观念,认为不顺服君王就是不顺服上帝。
为了加强这种观念,保皇派马克斯韦尔于1644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基督教君主的神圣王权》(Sacro-Sancta Regum Majestas),从《圣经》出发为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进行辩护。马克斯韦尔的观点并不新颖,而是相当传统但却是主导性的观念。这一点可以在内战初期的议会军司令曼彻斯特的说法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如果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后代也仍将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全部都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将成为奴隶。”【引自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王觉非、左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0-101页。】虽然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血缘继承制可以加重人们对绝对王权的敬畏情感。进一步,如果《圣经》主张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观,那么,人们在英国国教主导下就会培养出这样的想法:反对血缘继承制下的绝对王权就是违反《圣经》的主张。这意味着,无论议会军队暂时有多强大,他们都无法战胜保皇派。换句话说,在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观这个社会共识中,议会军队是无视上帝命令的叛乱者,而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在上帝的保守和祝福下终将赢得这场内战。
同一年,卢瑟福(Samuel Rutherford,1600-1661),时任圣安德鲁大学的新学院(隶属长老会)神学教授,出版了他的《法律与君王》(Lex Rex)【卢瑟福:《法律与君王》,李勇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这本书以马克斯韦尔及其所代表的保皇派作为靶子,从《圣经》诠释的角度,对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进行了彻底的批评和否定。是年底,英国国会的长期议会开会,议员们几乎人手一册《法律与君王》。也就是说,1644年的长期议会议题基本上是按着卢瑟福这本书的思路展开的。这次会议之后,议会军队不再对国王及其支持者手软,直到1649年把国王送上绞刑架。卢瑟福指出,马克斯韦尔误解了他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实际上,这些经文恰好是反对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论的,因为《圣经》赋予了每一个人以自卫权。自卫权就是对绝对王权的限制【参阅谢文郁:《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英国内战的整个发展线索都和《法律与君王》相关。无论是在议会和国王的战争(第一次内战)中,还是在议会和军队下层的人民公约派的分歧中,以及在议会和苏格兰长老会的战争(第二次内战)中,都可见到这本书所留下的浓重痕迹。限于主题,本文不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卢瑟福作为神学教授,他对《圣经》的解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本书之后,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论和圣经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两种解释,而卢瑟福的解释在议会中获得了共鸣!可以说,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说从此不再主导英国思想界。
卢瑟福的《法律与君王》在英国内战期间所形成的影响,对于王权的血缘继承制来说具有毁灭性效果。进而,在思想界,人们很快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绝对王权和血缘继承,政权应该如何产生?其合法性在哪里?1651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出版了他的《利维坦》,提出契约论来解释政权的起源和合法性。他谈到,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一切权利,并在契约中放弃一部分权利,并将其交给政府管理而进入社会状态。政权(或王权)由此产生。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它能恰当地管理公民所交出的权利。契约是双方的,除非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契约。契约赋予了王权甚至奴隶制政权以权威性和合法性【参阅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8-20章。以及谢文郁:《权利:社会契约论的正义原则》,《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霍布斯的契约论并没有否定王权的权威性,但认为,既然王权是在契约中产生的,血缘继承就是不合适的了。
霍布斯从契约论的角度谈论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当时英国思想界来说,乃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不难理解,如果不是《法律与君王》对绝对王权观和血缘继承制的破坏而导致人们对政权(王权)合法性的理解出现空白状态,霍布斯大概不会提出上述契约论解释,而且即便提出来,人们也不会对它有什么巨大的反应。实际上,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后,英国思想界出现了震动【参阅Thomas Hobbes, Leviathan-Revised Edition, edited by A.P. Martinich and Brian Battiste (Peterborough: Broadway Press, 2010).编者把当时学界的一些回应也作为附录编入,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思想界对此讨论之热闹。特别指出,Robert Filmer的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of Government upon Mr Hobbes’s Leviathan便在其中(附录A)。】。 尽管批评是主要的(因为它不否定甚至捍卫绝对王权),但是,这种强烈反应反而推动了契约论的传播与关于契约论的广泛讨论,这从根基上改变了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导演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光荣革命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于1690年出版了《政府论》【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上篇)1982年,(下篇)1964年。英文本参阅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90),edited by Peter Laslet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对君主立宪制进行理论说明。洛克写作这本书时,有两个主要关注。首先,霍布斯的契约论强调契约的绝对权威,并且否定任何單方破坏契约的努力。这就是说,如果国王不愿意放弃王位,臣民就不能破坏契约而推翻国王。因此,契约论在逻辑上是可以用来支持绝对王权的。这一点对于议会派(或新贵族,洛克属于其中一员)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其次,尽管霍布斯没有否定绝对王权,但是,契约论对血缘继承制的否定却是彻底的。这一点对于保皇派来说则是致命的。因此,保皇派对霍布斯的批评火力更猛。比如,菲尔麦(Robert Filmer, 1588-1653)为此写了《先祖论,或论国王的自然权力》【Robert Filmer, Patriarcha, or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Dodo Press, 2008.不过,鉴于《法律与君王》的强大影响力,他生前没有出版此书。《先祖论,或论国王的自然权力》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版的(1680年)。洛克《政府论》上篇便是以菲尔麦的《先祖论》为攻击对象的。】一书,坚持从《圣经》出发,从血缘继承制出发为绝对王权进行辩护。
洛克继续采用霍布斯的契约论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基本权利”观念【国内学界关于洛克的“基本权利”观念几乎没有讨论。拙作《权利政治与社会契约论》中有关于洛克的“基本权利”的分析和讨论,参见谢文郁:《自由与责任四论》第二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洛克提出三个基本权利:私有财产、人身自由、追求幸福。基本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现代英国政治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至于基本权利究竟包含哪些条目,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是可以讨论的。】来回应上述两个关注,认为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他进而引用卢瑟福的说法,认为公民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即是行使自卫权。因此,他指出,菲尔麦所鼓吹的绝对王权和血缘继承都是不合时宜的。同时,洛克还提出了“三权分立”的设想,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独立运行而相互制约。简略而言,在洛克看来,在君主立宪制的框架中,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君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只能在法律规范中行事。政权运作采取“三权分立”原则: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内阁为最高行政机关;司法体系独立执法。洛克的这些观念代表了当时英国议会的主导性立场。1689年公布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宣告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在这个体制中,國王在名义上是最高首脑,但国王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或者说,必须在议会的框架中行事(这相当于取消了国王的行政权力)。内阁和司法体系都是通过议会任命建立起来的,一旦建立,就独立于议会而运作。于是,议会实际上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这是现代西方政治的最初形式。
英国下议院是议会(或国会)的主体。作为英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成员构成是关键所在。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大部分下议院议员身份的获得都和金钱有关(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新贵族”的原因)。“光荣革命”之后,议员在程序上虽然是通过选举产生,但是,议员的候选人资格是和财产(不动产)挂钩的;实际进入议会的人一般是大地主,通常是地区自治的头领。这种统治形式一直持续到1832年的改革。1832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剥离议会席位分配制度中的财产(不动产)和土地因素,转向按人口分配席位的做法。从1689年的《权利法案》到1832年的改革,其动因就社会变迁的角度而言,是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了一批没有土地却拥有雄厚资本的资本家的产生;他们需要在议会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因而需要更多席位。1832年的改革剥离候选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导致了选民的选票成为候选人当选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对于这个转变,我们注意到,除了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城市化因素之外,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17-18世纪)以及法国大革命(1789-1799)也是关键性因素【关于英国1832年改革和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可参阅Seamus Dean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1789-183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启蒙运动传递了“人权”理念,法国大革命传递了“平等”观念。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也不会影响整个欧洲。学界通常认为,欧洲启蒙运动起于1751年开始出版的《百科全书》(由狄德罗主编)。其中的一位重要作者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最重要贡献正是他提出了“人权”理念。
在卢梭看来,“人权”就是人的契约权。他在《社会契约论》第4章中讨论奴隶问题时指出,人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奴隶。就概念而言,奴隶是那种放弃一切权利(包括财产权和生存权)的人。卢梭谈到:“说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就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版,第11页。】这话的意思是,现实生活中的“奴隶”都是出于理智不健全的缘故,因为人不可能“无偿地奉送自己”。也就是说,任何人的奴隶身份都是无效的。没有真正的奴隶。人是在契约中使用契约权通过交换某些权利而进入社会的。无论达成什么契约,人都必须行使契约权。缺乏契约权就无法与他人定立契约。从这个角度看,人无法交出契约权;交出契约权等于无法进行契约活动,包括交出契约权这个契约活动。因此,人可以交换他所拥有的一切其它权利,唯独不可能交换他的契约权。卢梭称此为“做人的资格”。当然,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理智状态出了问题而以为自己没有了契约权从而不再使用它。卢梭认为,这正好是欧洲的现状。契约权是不可能丧失的;它永远和人同在。人们的这种错觉需要启蒙。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之契约权的不可剥夺性。契约权允许人交换各种权利,既可交出,也可收回。基于这一点,卢梭认为,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改变的;更直接地说,革命是合法的。
卢梭进一步指出,人的契约权既然与生俱来,便不是法律赋予的。相反,人的契约权必须成为法律的基础;法律必须从人的契约权出发,维护保障人的契约权。在这个思路中,卢梭认为,表达自由(或表达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受到法律保护。表达自由如果得不到法律保护,人的契约权就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表达自由一般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言论自由。人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人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从而无法进行契约活动。当人的意志得到充分表达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公意”。这个公意表达了社会的共同利益,是永远不会错的。其次,在充分享受言论权的基础上,人就可以通过自由选举而进入实际性的契约。最后,当自己的意志未能在契约中得以表达时,人还可以公开表达抗议。只要人的表达自由得到了法律的完全保障,社会的公意就能够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秩序的形成。他说:“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136页。】可见,卢梭提出的“公意”概念是通过言论自由、投票自由和抗议自由来呈现的。或者说,人的契约权是在表达自由中实现的。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的人的契约权概念成了理念,即:唤醒人的理智状态而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人的契约权,并随己意而使用之。启蒙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拥有契约权,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独立主体与社会其他主体进行契约活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便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反过来,法国大革命运动又推动了这种人的契约权意识的广泛传播。英国的1832年改革深受这种人的契约权理念的影响,率先在议员选举中落实民众的选举权。可以说,现当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政治制度是从此开始的。
小结一下,作为现代西方政治的第一种形式,英国革命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破坏了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并在基本权利观念主导下建立了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君主立宪制。具体而言,卢瑟福在《圣经》诠释中为人民的自卫权辩护,冲击了绝对王权观和血缘继承制,导致政权合法性问题成为思想界的热点和显学。霍布斯企图通过契约概念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但在逻辑上无法消解王权的绝对性。洛克推进了契约论思路而提出基本权利观念,彻底摧毁了绝对王权观。然而,以私人拥有土地自由为基本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契约政权,其合法性并不充分。卢梭从契约权的角度界定基本权利,把契约政权的合法性归为人民的选举权。从理论上看,人的契约权—选举权完全坐实了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观念通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传给了英国。英国1832年的宪政改革容纳了卢梭的这种观念。于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就定型了。
二、儒家仁政与推举制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在儒家仁政思路中进行治理的。不过,受到血缘继承制的制约,儒家仁政在中国历史上未能得到全面实行。如今,血缘继承制已经废除,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儒家仁政的基本思路,就成为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现代西方政治模式尽管主导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制度变革,但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在落实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上的努力并未获得良性回报。究其原因,任何成功的政治实践,都是在历史惯性中进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也是如此。现代西方政治的成功经验当然可以借鉴,但是,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仁政思路形成良性互动。这里,我想深入分析孟子所提倡的推举制,呈现儒家仁政思路上的君王产生机制。
儒家仁政在社会治理问题上关注这两种根基性关系,即天命与君子;君子与平民。首先,在天命与君子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宇宙秩序(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在天命中给定的。敬畏并遵循天命是为政者的原始性情感。遵循天命需要认识天命。凡在敬畏中追求并认识天命者便是君子。君子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治治理主体;一类是道德教化主体;合起来,君子乃是社会生活中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作为道德教化主体,君子是道德模范和教师,因而是作为个人而起着教化的作用。政治则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活动。君子作为政治主体所从事的并非个人活动,而是群体性活动,这其中是有秩序的。秩序由具有上下等级的政治地位来界定,其中的顶层位置称为王位。位居王位的君子称为君王或君主。当然,君王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君子身份,然后才能带领君子群体敬畏、认识和遵循天命而治理社会。君子当道的社会,如荀子在《王制》中的描述:“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这里,荀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天命秩序的维护者。严格来说,君子是敬畏、认识并践行天命的群体。
就个人修养而言,敬畏、认识并践行天命是君子的使命所在。无视天命则无法成为君子。成为君子的第一标志是敬畏天命。敬畏是一种情感。作为一种生存倾向,敬畏情感指向天命,并把天命界定为一种中性力量;一种既可祝福人亦可损害人的力量。从人的生存角度看,人期望得到祝福,避免受损。当人对天命有所认识时,人就可以顺从天命而得到祝福。儒家很早就有“敬德”的说法。这里的“德”指有德之人,或认识并践行天命的人;“敬德”就是敬重那些拥有天命知识的人,并接受他们的指导。但是,天命高高在上,人如何能够去认识它?思孟学派在“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的说法中指出一条认识途径。人是在天命中出生的;每人都有天命在身;因而只要能够认识并践行自己的天命,就能做到天人合一,成为知天命的有德之人。这条认识天命之路也称为修身养性。因此,人是在修身养性中敬畏、认识和践行天命并成为君子的。
其次是君子和庶民的关系【学界对“庶民”的界定尚无定论。我把庶民理解为指所有的人,包括君子在内。就原始含义而言,“庶”指的是多,如《诗·大雅·灵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君子并不是与庶民相对的不同群体。与君子相对的是小人(不追求天命,只求自己眼前利益的人)。关于“小人”的分析,可参阅谢文郁:《君子困境与罪人意识》,王博主编:《哲学门》总第26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1-304页。】。《荀子·王制》谈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用舟水之喻来说明君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表达了儒家仁政的思路【实际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中国历史上是对君王的警语。《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中记载魏征对唐太宗说的一段话:“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作为政治主体的君子,一方面,他们必须敬畏、认识并践行天命;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安抚庶民,保护庶民的利益,让庶民在秩序中安居乐业。这里所说的“庶民”是一个模糊观念,指的是一般的人,几乎可以包括所有的人。庶民的心思意念便是民心的组成部分。君子作为天命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知民心,安民安政。在儒家仁政中,天命和民心是有内在联系的。知天命必知民心,反之亦然。《尚书·泰誓》中便有这样的句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知天命和知民心是同步的。无视民心,即无视天命。因此,君子在追求天命时,还必须敬畏并了解民心。
把天命和民心挂钩的思路提供了君子知天命的另一条途径,即:通过了解民心来认识天命。何为民心?——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民心不仅仅是一些人或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情感或看法。同时,人和人之间的追求并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而且,人的利益可以区分为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的观念也在变化过程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当下,只顾眼前利益,并无追求天命的冲动,因而他们的观念就极为有限,自足而封闭。当然,他们的想法需要得到一定尊重,属于民心的一部分,但并不能代表民心。其次,民心甚至也不是当代人的观念。同代人在利益和观念上总会有某种共同性。当代人得到的各种好处,往往是前辈留下的业绩,因而必须尊重前辈的心思意念。或者说,民心包括了前人的心思意念。最后,如果只顾现时的好处,当代人的决策往往会给后代带来不可逆转的害处。因此,子孙后代的心思意念必须包含在民心之中。当代人的利益和观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民心的重要构成。但是,民心的构成还涉及其他时代的人的利益、情感和观念。毋宁说,民心涉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人的心思意念。
显然,如果天命和民心有某种相应关系,那么,君子以追求天命为使命,就可以通过与同代人的交往来了解庶民的利益和观念,并在其中体验并把握民心,以及其中的天命。不过,仅仅通过同代人来体验民心显然是不足的。从古到今,前人积累了他们对天命的认识,并且在践行天命时给当代人带来了福祉。君子还可以通过阅读前人的经典,理解前人留下的传统,体验古人的心思意念,并从中领受古人关于天命的认识。而且,君子还是要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因而他们还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体验他们的心意。因此,君子在体验民心、认识天命时必须思前虑后,因为民心系于全部人(古人、今人、后人)的共同福祉。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如此归纳君子身份:“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谓“君子之道”,其实就是对君子身份的界定。“本诸身”指修身养性;“征诸庶民”要求考察民心。怎样才能做到呢?首先,要从古人那里认真领受,因为古人积累的天命知识可以成为进一步认识天命的基础;其次,所形成的天命知识不能与自然秩序相冲突,因为天命秩序包括了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再者,还要力求达到无所不通、面面俱到,不能尝浅辄止;而且,这些天命知识能够造福于子孙万代。君子要从这四个方面去考察民心、认识天命、践行天命。
在儒家仁政思路中,君子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前提,这给健康政治提供了践行主体。政治治理是一个系统性行为;系统如同一个网络结构,通过网结而联结起来。这些网结亦即政治制度中的职位,这些职位必须由相应的君子来担任。这里,分配职位是政治治理的第一步。其中,君王的产生机制是重中之重,这也儒家的千年难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无法抗拒西方列强的入侵。学界往往将这个事实解释为儒家仁政失败的明证。人们甚至做出进一步引申,认为儒家仁政乃是几千年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个结论近年来在学界开始受到质疑。本文无意就清政府的失败进行深入分析。不过,尽管儒家仁政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一直起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在君王产生机制上被动地接受了血缘继承制,未能完全贯彻仁政思路。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检讨的。血缘继承制要求从现任君王的血亲后代,特别是亲生儿子中选择继承人。现任君王的男性后代在人数上极为有限。从儒家仁政的角度看,君王的候选人必须首先成為君子,在敬畏中追求并认识天命,然后在君子群体的认可下成为君王,带领君子群体践行天命。如果现任君王的儿子们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君子而成为君子之首,在儒家仁政中,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何保证现任君王的儿子成为君子,并成为君子之首呢?历史上,在血缘继承制中,王子们是被要求成为君子的,即:通过对王子们进行严格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君子。然而,成为君子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冲动,而不是外在压力。因此,通过教育来培养王子们的君子身份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如果一位非君子成了名义上的君王,儒家仁政的政治治理就必然失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打破血缘继承制,儒家仁政就是不彻底的。
在儒家仁政思路中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君王产生机制呢?《孟子·万章上》中关于尧舜传位的论述属于彻底的儒家仁政思路,值得重视。孟子的想法可以说是“推举制”。在孟子看来,儒家仁政中的职位分配应该是由下级向上级推荐,经过上级考核、锻炼、审查而任命的。君王作为君子群体的首领,也必须通过推荐来传位。君王的上级就是上天。君王推荐程序分三步走。第一步,“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天子乃是在位君王。在继承者问题上,他无权传位给任何人。但是,他有权向天推荐继承人。天子在向天推荐继承人的同时也向民众公开,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继承人,以便看看民众是否会接受他。这个向天推荐继承人的权利只属于天子。当然,下级君子可以向天子推荐人才,但能否成为候选人的决定权在天子手上。一位君子是否适合于天子位置,只有在位天子最清楚。没有做天子的经验,就不可能知道做天子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和资质。因此,只有天子有资格和权利向天推荐君王继承人。
第二步,当君王候选人公示之后,候选人需要在相关职位上加以历练,发展并展示其品格和能力:“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这里的“主祭”涉及天命敬仰,要求主持人在祭祀时不仅有恰当的外在表现,在主持各种仪式时能够把握好分寸;同时他还需要拥有足够的内在敬虔,祭神如神在。归结起来,君王作为君子群体的首领必须拥有纯正的天命敬仰。而且,天命系于民心。候选人需要通过担任一些职务展示并发展领导能力,做到“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这里的“百姓”主要指相关职务所涉及的人群,包括领导人的同事、部下以及受惠群众。一件事做得好坏,只有那些与这事相关的人觉得做好了,才能说做得好。当朝天子的推荐固然重要,但候选人如果未能展现出品格和能力来,天子的推荐就可以归于无效。
第三步,君王候选人还必须得到君子群体的信赖和支持,进而建立社会对他的信任。对君王候选人进行好坏评价仅仅是针对他过去的作为。因为事先并没有特别关注,所以,针对他的评价也就只能就事论事。这类评价都是大概而论。如果事先没有专门的注意,候选人即使“主事而事治”也未必可靠,因为就事论事意义上的成就也可能是出于偶然的。当人们因为他做得好而开始注意他时,人们就会对他产生期望情感,并进而在期望中观看他的作为。观察者在期望情感中看他的作为,可以获得更为细致的印象,从而对候选人的品格和做事方式有更深入的认识。进一步,当候选人的所作所为满足了人们的更多期望时,人们的期望情感就会转变为信靠情感。君子群体以及社会对候选人的信靠情感一旦形成,他成为君王就是众望所归!于是,“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就是说,君王需要得到君子群体和社会的信赖。这种信赖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天命的彰显。
三、选举制和推举制之比较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清朝政府尚未被推翻之前,曾经比较过中西政体的差异。他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丁韪良在《汉学菁华》(1901年)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科举制,认为科举制是最民主的制度。参见丁韪良:《汉学菁华》,沈弘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7章。他还出版了《中国觉醒》(1907年)一书。该书出版时,清政府已于1906年废除了科举制。丁韪良在该书中谈论唐朝政治时仍然盛赞科举制,认为主张民主制度的人一定欣赏科举制。参见丁韪良:《中国觉醒》,沈弘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03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皇帝和士大夫阶层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的相互制约十分有力;而且,科举考试允许底层人士源源不断地进入士大夫阶层,从而可以把底层的利益和要求带入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因此,中国的政体也属于一种民主政体。丁韪良的观察是相当深入的,他的表述也值得认真对待。我想在以下文字中,围绕着选举制和推举制,考察现代西方政治和中国儒家仁政在正义原则和官员选拔机制等方面的一些特征及其差异。
(一)公意与民心
现代西方政治的正义原则在于卢梭的“公意”概念。卢梭认为,“公意”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所在。“公意”是不会错的,永远正确;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政权因而就是合法的、正义的。“公意”只能通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和表达。因此,一人一票的投票结果就能产生“公意”。也就是说,选票就成了现代西方政治的正义原则。类似地,儒家仁政则从“民心”出发谈论政权的正义性。“民心”与天命相连,涉及过去、现在、未来。建立在“民心”的基础上,政权就是顺从天命,因而是合法的、正义的。“民心”是通过君子之道来表达的。因此,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在于君子之道。这里,作为正义原则,“公意”和“民心”对于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来说都具有终极性意义。因此,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两种政体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引导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们先来看在选举中呈现的公意。现代西方政治强调每位成年公民一人一票。公民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选民的选票决定了何为公意;而公意永远正确。因此,任何一个政权的确立,其正义性或合法性均取决于选票。对此,可以作如下分析: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对于任何一位选民来说,他的意愿来自于他所关心的生存问题,他在一定的思想結构和价值体系中对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的进行判断,他拥有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如此等等。这些因素都属于他的责任意识范畴。选民自主地在自己的责任意识中投出选票。当然,不同的背景因素,包括生活经历、所受教育,以及情绪类型等,往往意味着不同的责任意识。但是,在卢梭看来,只要选民是独立(自由)地投票,就一定能够表达公意。然而,选票在不同的责任意识中所表达的“公意”是有偏向的。这种偏向并非如卢梭所言一定正确。如果不考虑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则所谓的“公意”就不过是群体或国家的多数派愿望,这种主流愿望往往与当下的文化潮流直接相关。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认为这种“公意”或主流愿望必然正确,而不去深究可能存在着的偏差,则政治运作就会盲目地为潮流所驱动。
进言之,现代西方政治对选民资格的规定主要是以年龄为界,比如,凡18岁以上者,只要没有触犯刑法而被剥夺选举权,就拥有选票。在这个界定中,选民背后的责任意识不在考虑中。然而,人是在自己的责任意识中投票的。在责任意识没有根本性差别的选民中,他们的投票意向就有某种共同性,因而可以产生所谓的“公意”。然而,有些选民会关注传统的传承而体会祖先的意愿;有些选民会关注未来而顾及子孙后代的意愿;有些选民会为他人乃至全体的人着想;有些选民则只会关心自己的当下利益,等等。在选票中形成的“公意”的质量,取决于选民的责任意识的整体水平。如果大部分选民既不关心传统,也不关心未来,只是盯着当前的利益,那么,从这些选票得出的“公意”必然是短视的,比如,德国二战前选出希特勒就是一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难指出:在缺乏对选民的责任意识进行分析和检讨的情况下,卢梭关于自由选票产生的公意必然正确的说法,乃是缺乏足够论证的。
在儒家仁政框架内,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其正义性必须建立在“民心”基础上。民心和天命相连,认识并把握了民心,就是认识并把握了天命。因此,民心具有终极性意义。我们的分析指出,民心并非仅仅是人们的眼前利益和心思,亦非同时代人的心思意念,它还包含了祖先和后代的心思意念。祖先的意愿可以在经典书籍上寻找和体验;后代的意愿则是通过当代人对后世福祉的关怀和思虑来呈现。如果一个人想知道民心,他就不能终日想着自己当下的利益,而是要“慎终追远”,追求天命,即:他在敬畏天命中追求天命,心胸宽阔而兼顾他人利益和心思;敬重祖宗而继承古人意愿;思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乃至子孙后代之福祉;等等。然而,人是在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因而不能不关注当下的时刻,趋利避害。不关注当下利益,就不可能进入生存。同时,如果人只关注当下利益,无视天命在他的生存中的本质性作用,那么,他就只能在利益冲突中走向毁灭。
儒家区分了两种人:君子和小人。君子敬畏而追求认识、把握、践行天命,因而他们的意愿中就会包含越来越多的对于民心的感受和认识;小人虽然畏惧天命但无意追求天命,他们只关注并追求自己的当下利益,因而他们的意愿仅仅局限于对自己的利益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更多地是在描绘两种生存倾向,而不是两个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并非是两个固定的封闭群体。一个人是否为君子并不在于他的出身、社会地位,甚至也不在于他是否曾经做过君子;成为君子的关键在于他当下是否仍然敬畏并追求天命。也就是说,君子群体是开放的,进入者为君子,离开者为小人。君子在社会成员中比例增大,这个社会对天命和民心的认识就会加深。小人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无意追求天命。尽管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也是民心的组成部分,但是,除了表达自己的利益之外他们无意去认识更大范围的民心。
民心在哪里呢?无论是君子的意愿,还是小人的意愿,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心。不过,在儒家看来,这个程度差异是十分重要的。小人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并为之费心奔波。对于古人的意愿、他人的利益、后代的福祉等等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兴趣去关怀;而对于自己的眼前利益,他们却又斤斤计较。因此,“小人喻于利”。但是,君子关怀的是天命。天命涉及过去、现在、未来,涉及普天之下的民众利益;因此,关怀天命就需要去通过圣贤之书来学习前人积累下来的天命知识,体察民情以体会同时代的众人意愿,忧患社会治理而为子孙后代免灾积福,并在自己的修身养性中一点一滴地形成天命知识。因此,“君子喻于义”。在这样的天下情结和关怀中,君子的意愿是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水平上表达了民心。如果是这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君子的意愿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的意愿在表达天命这一点上是不平等的。对比卢梭的“公意”概念,选票所产生的“公意”充其量不过是“民心”的一小部分,远远不足以表达“民心”。
在这个思路中,重要的是如何辨认和选拔君子。我们谈到,君子的天命关怀是一种内在的情感倾向。这种内在关怀无法用简单的外在指标来加以分辨。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从隋朝设置科举制度开始,可以说,儒家仁政实际上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辨认并选拔君子的。随着清朝政府于1906年废除科举制,中国社会等于是放弃了这种定式。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儒家仁政的实施需要设置君子辨认和选拔程序,科举制则只是已经废弃了的辨认和选拔程序。至于能否找到其他更有效的辨认和选拔程序,本文暂搁不论。
简言之,现代西方政治的正义原则是在选票中呈现的公意;儒家仁政的正義原则是在君子之道中呈现的民心。
(二)官员遴选
官员占据政治地位,因而是社会秩序的主导者。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在遴选官员问题上,基于各自的正义性原则(公意和民心),两者的思路也有方向性的差异。比较并分析这里的差异,对于我们理解这两种政体的实际运作有实质性的帮助。
前面提到,卢梭认为,公意是由选票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现代西方政治把政权的正义性落实在选票上。对于选民来说,投票是重大决定,因而在决定之前一定会进行慎重考虑。这里,选民的慎重考虑所依据的是他个人的现有责任意识。一个人的责任意识涉及他的利益关注(包括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社群利益、民族利益、天下利益等等),以及知识积累、善恶观念、自我克制能力、情绪类型等等。一般来说,选民的选择是由他的责任意识来决定的;有什么责任意识就做什么决定。不过,现代西方政治强调一人一票,一个只考虑自己眼前利益的人,和一个心怀天下生灵的人,他们的选票具有同等的份量。在选举领导人这一点上,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对于选举什么样的领导人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拥有什么样的责任意识,他们就会选举出怎么样的领导人;而在一个意识形态分裂的社会中,通过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就一定是备受争议的。
在现代西方政治的选举制中,选民和候选人的纽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我们看到,在一个较大的社群中,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并不相识,因而选民无法直接了解候选人的品格。选民虽然可以通过间接途径而对候选人的人品有所了解,但是,这些间接知识无法成为选民的投票根据,因为这些间接知识的可靠性是需要进一步求证的。可以说,选民在投票时主要地不是考虑候选人的人品。那么,选民的投票根据在哪里?前面指出,选民是在自己的责任意识中投票的。一般来说,如果候选人在竞选时提出的理念(竞选口号)与选民的责任意识相吻合,选民就会把选票给他。这就是说,候选人为了得到选民的选票,他必须了解选民的责任意识,体会选民的情绪状态,顺从选民的心思意念,然后提出选民乐于接受的理念,讨好选民。在实际操作中,在许多情况下,候选人为了选票而不得不提出一些自己并不认同的理念作为竞选口号。这一点可以通过如下观察而得到支持:候选人一旦当选,就会选择性地落实竞选时的许诺。从这个角度看,竞选理念是联结选民和候选人的主要纽带。或者说,选民是通过候选人的竞选理念来认识并选举他们的。
儒家仁政则要求官员必须来自君子群体。在儒家仁政中,政权之正义性来源于民心(天命)。尽管所有的人所表达的意愿都是民心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君子才有意识地追求体会和把握民心。前面指出,民心涉及古人对天命的追求,涉及其他人的利益和观念,涉及未来的子孙后代之福祉。因此,只有主动追求民心,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把握民心。在这个思路中,把那些努力追求天命且对民心有深入把握的君子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就成为儒家仁政得以落实的关键环节。
谁来辨认和选拔官员呢?我们先来看看平民百姓这个群体。平民百姓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虽然这也算是民心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在意识上并不追求认识天命,因而他们的意愿也就只限于自身利益和观念。显然,受限于自身的利益和观念,他们只会认可能够给他们带来眼前利益的官员。这样的官员是不符合儒家仁政思路的官员。因此,平民百姓这个群体在选拔官员这件事上只占比较轻微的份量。当然,这里所谓的份量划分并非固定不变的,比如,当社会秩序混乱而伤及他们的生存时,平民百姓就会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而积极参与政治领袖的选拔,甚至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上位的决定性力量。不过,越是社会秩序井然的时代,这个群体在官员选拔问题上的份量就越轻。因此,儒家仁政不主张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程序来选拔领导人。
再来看君子群体。作为追求天命的群体,他们的意愿在同代人中包含了最高的天命知识,最大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民心。在儒家仁政思路中,民心是正义性的基础。因此,得到他们认可的官员就是合法的官员。可以说,他们是辨认并选拔官员的主体。由于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主要是由这个群体的成员所占据,他们自己就是官员。一般地,在儒家仁政中,在位官员有资格根据他们的观察而向上级推荐候选人,并在制度上设立相关的考核程序对候选人进行考核;只要通过了考核,候选人就能上位。这里,在位官员必须是追求天命的君子。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天命知识辨认并推荐候选人。候选人之所以被选上,他的品格、能力和观念都是考量的指标。他是作为一个全人而被考察的。当然,如果在位官员不是君子,那么,他所推荐的候选人就不可能是君子。特别地,在最高领袖的遴选问题上,如果在体制上无法阻止非君子的候选人上位,那么,官场中的君子官员就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这个政权走向完全腐败而没落。
简单来说,现代西方政治通过选举遴选官员,候选人和选举人的纽带是候选人提出的竞选理念,而官员上位的决定因素则是选票。儒家仁政根据君子之道推荐候选人,被荐人的个人品格、能力、学识需要综合考量;而官员上位需要由上而下的体制制约,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被荐人的君子身份。
(三)官员罢免
权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杠杆,同时也会因腐败而被用来满足私利。因此,官员罢免是健康政体运作所必需的。在现代西方政治中,权力制衡,如洛克提出的三权分立,主要针对的问题便是权力腐败。不过,归根到底,民选官员还是必须由选票来决定。儒家仁政对此问题也有深刻认识。但是,在儒家仁政中,所有官员都是上级任命的。监察机构亦遵循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此,罢免也只能由上级说了算。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不同,因而两者的官员罢免机制之差异也值得重视。
在现代西方政治中,民选官员罢免主要还是通过选票来解决。一般地,现代西方政治采用定期选举制。就实际操作来看,通过选票来解决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上简单明了。在这种程序中,任何民选官员,即使发现权力腐败,从选票的角度看,他或她在形式上仍然是合法的,并且可以完全在正义程序中繼续占据官位。当然,选民可以通过各种压力而迫使官员辞职,或者促成相应的调查行动将其绳之以法。但是,选票作为正义原则拥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如果官员不肯辞职,如果该官员有足够的能量从司法调查中脱身,选民便只能通过下次选举来解决他或她的罢免问题。就制度设置而言,官员罢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通过选票,而是直接诉诸行政手段,如当民选官员继续保持职务将危及社会安全时,在三权分立体制内还可以启动行政罢免程序,强迫民选官员辞职。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民选官员的罢免必须通过选举。民选官员在位期间必须为他的选民负责,为选民谋利益。只要选民满意,就可以继续获得选民的支持。就其职责而言,他不需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不需要为选区之外的人负责,甚至也不需要为选民的长远利益负责。民选官员是在他的责任意识中做事的,因而不同的官员做事方式并不相同。但是,在选票正义中,民选官员的心思主要在选票上。只要有选票的支持,他或她就可以在法律框架中继续连任。
儒家仁政在官员任命问题上遵循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肩负追求天命、体贴民心的使命。一旦停止了追求和体贴,君子就成了小人。君子小人之间只有半步之遥。占据高位的官员,一旦成为小人,他就不再代表民心,从而丧失了继续占有权力的正义性。设立健全的罢免制度,以监察在位官员的君子身份,保证他们作为民心代表的资格,乃是维持政权之正义性的重要环节。然而,君子之道具有内在性;在位官员是否保持其君子身份,并不是可以简单地加以分辨的。实际上,很多在位官员在丧失君子身份后,其做事方式仍然可以显得像个君子。这种人称为“伪君子”。尽管伪君子官员“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是,除非上级检查及时,在位官员中的伪君子很难被发现并被罢免。传统儒家仁政下的权力腐败因而成为一种顽疾。特别地,君子群体中的君王若无法保持其君子身份,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出现集体性的权力腐败。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政权集体性腐败后,民心之正义原则就不得不通过改朝换代来彰显。由此看来,儒家仁政在官员罢免问题上需要有更严密的制度设置,以维持君子之道。
总地来说,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的社会治理在思路有一些方向性差异,这导致两者在设置政治领袖的产生机制上有着极大的不同。现代西方政治把政权的正义原则落实在选票上,称为选举制。在实际运作中,选举制规范划一、操作简易,在某种意义上,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实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过,选举制作为正义原则完全不考虑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对不同责任意识引导下的选票去向,或公意之善恶倾向,处于盲目状态。一旦出现“恶”的公意,政权就会成为一种恶的力量,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是君子之道,强调君子群体在政权中的主体性,重视君子的责任意识培养,推动君子追求天命、体察民心,以此作为政权之正义原则。我们称之为推举制。由于天命—民心的不确定性,君子之道在政权中的运作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权宜而调整。然而,君子的天命追求是一种内心活动,外在制度只能引导,不能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仁政中的权力腐败是结构性的,或者说,是不可能根除的。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避免整体性的权力腐败,保证君子之道的运行,乃是儒家仁政的核心课题。
【责任编辑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