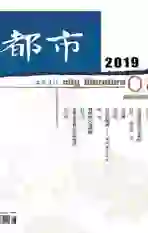在低处写有光芒的生活
2019-09-10赵少琳
赵少琳
为人的书稿作序,是件苦恼的事情,因为我怕对人家的作品说不出道道来,就有些发怵,深怕贻误了人家的美意。好在爱玲不是个挑剔之人,让我为她的诗集《尘世之光》说几句话,我也就壮了几分胆子,尽力去征服自己的一些浅见,说说自己的心想。当然,这里假如有些地方我说得不好,说得不对了,也请爱玲诗家悄悄地在私底里放我一马,给我点面子。
一、好诗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好诗长得是什么样子的,似乎我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我看到了你写的《野菊花》《雪花纷飞的日子》《不,落雪是不需要解释的》等等诗歌,已看到了你的诗歌生长的面孔、生长的势头。譬如《野菊花》:
是谁从天上借来了太阳的色彩/在十月燃烧的记忆里/蓬勃出野菊花傲然的情怀//每一片花瓣都热烈/每一个花蕊都奔放//在快要断流的小河岸边/在被秋风无情切割的荒原上/在峭愣愣的崖壁上//野菊花是一团一团小小的火焰/给裂变的岁月以金色的幻想//一枚草籽,一枚野菊花的草籽/它从虚无中来,又走向虚无/短暂的辉煌里,燃尽了所有的豪情//不卑不亢,不喜不怨/从容地接受风雨,面对落幕//芳华过后,我们所能看到的/依然是落在泥土里的一枚草籽/它知道,它的生命不会散场
———任爱玲:《野菊花》
你对一个卑微的生命体察得如此细致和周到,此诗或许也交织了你过往和日常的生活。季节里,在未知的日子和未知的地方,生活总是一次次地脱轨,一次次地把我们撂在边远和陌生的路口,似乎要让低沉、沮丧、刮痕和沟壑删改我们,让我们失去灯光、失去亲人。是的,生活在继续。事实上,我们也不会像稗草一样随时都会倒伏。正如野菊花,她柔弱,但头颅上却镌刻着太阳的颜色。
《野菊花》这首诗歌写得明亮且具有暗示性。作者用拟人的手法,以汤沃雪。这样,让我们对于低垂的生命有了彤红的理解。平日里,有些人把诗歌写的很模糊,他们认为,看不懂的詩歌就是好诗,其实恰恰相反。看不懂和模糊的写作是两个概念,看不懂或许是我们缺少生活的经验,缺少对语言微妙表达的感受,看不懂的诗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增加着我们对其诗歌的领悟。而模糊的诗歌就让读者搞不清楚南北,这样的诗歌带来的问题是:语言没有紧密的联系,段落偏离于核心,立意暧昧和左右摇动,甚至变形,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很是让读者感到读这样的诗歌比拉一车煤都要费劲。
除有以上的问题之外,有些诗歌不讲究相貌,就像人的五官,好端端地让语言留下了一些伤疤,也像是让诗歌的脸上长了一些雀斑。往仔细里说,有些诗歌让读者看得总是感到疙疙瘩瘩、磕磕绊绊的,让人看得血糖都低了,很是不舒服。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作者无意去梳理自己的诗歌,也不关心诗歌是不是一口气接着一口气地活着,也不去修补语言的中间是缺一根钉子,还是需要去稍稍地打磨一下,这不是偶然和意外,这绝对是作者的粗心和任性。
好诗长得是什么样子的,除《野菊花》和上述提到的两首诗之外,诗人任爱玲还写出了《这一年》《又一年》《七夕,浸泡在一场秋雨里》《用艾草,拯救那一片碎了的时光》等等,不断吸引我站定对其诗歌张望。当然,这里有我个人的偏爱、个人的敬礼。相信读者会超越我的这种看法。
好诗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借这样的场地,我也想把我看到的诗歌推荐给你,有些让你相亲的意思,看你能不能为之动心。
南海紧张那几天/母亲彻夜祈祷/不时地问我,会不会打仗?/我说,不会的,放心吧//母亲还是半信半疑/我说,打也轮不上我/母亲好像松了口气/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她又睁开眼来/拉着我的手说/真不会打/我连连点头//半夜,我上卫生间/还能听到母亲祈祷的声音//几天后,我半夜加班回来/母亲从沙发上站起来问/是不是还在打仗?/我想了想,认真地对母亲说/妈,仗已经打完/母亲像不认识我一样/将我全身仔细打量一遍//不一会儿/房间传来均匀的鼾声
———杜思尚:《妈妈,仗已经打完》
我想,积极地去破解别人的诗歌去强化自己,也不失为是在为自己的诗歌锦上添花。
二、在低处写有光芒的生活
什么诗里写有光芒的生活,这需要我必须举出例子来说明,否则,就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譬如诗人牛庆国的诗歌《风雨中》是这样写的:
一片黑云从山头上翻了过来/田里劳作的人们逃向家门/但有一个女人那么柔弱/却非要把一捆柴草背回家/刚刚被闪电照亮的身影/接着就被风雨模糊/仿佛听见柴草让她先走/可她没有山路泥泞柴草越来越重/一次次被风雨推倒在地/她一次次又背了起来/仿佛把那片黑云也背到了背上/当她靠着地埂喘气的时候/低头看见湿衣服紧裹着的身体/忽然有些羞涩/那时她的男人已跑回了家/她的毛驴和两只山羊也跑回了家/只有她和一捆柴草还在路上/没有人知道她曾感动过一场风雨
———牛庆国:《风雨中》
这首诗写一个女人,当然也是在写一个母亲,为了生活,她与闪电和风雨做着较量,她柔弱,几乎被泥泞的路途吞没,她趔趄,却绝不放手背上的柴草,风雨一次次地把她推倒,她又一次次地站起,即使是黑云的重量,也没有让她低首。
一个低矮处的母亲,一个双手沾着泥草气的母亲,一个说不出来真理的母亲,为了生活,她用胸怀做了生活的栅栏,她用十指和手背做了亲人的帐篷。有时,我们听不到一个母亲站在土屋后的低泣,看不到她们咬紧牙关时唇齿间渗出的血来,她们默默地像一块砖,而不奢求人们的目光和双手的抚摸,只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她们会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她们所做的每一件细微的事情都有着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表达,只是我们没有把这许多细微的事情组合起来,便显不出这些事情和岁月相加相乘起来的巍峨。母亲是纯金的,太阳因为有她们填加的柴火而在每一天可以升起。
我们要记住母亲的好,她们吃尽了苦头,却用奶水滋养了生活,滋养了我们的手臂、前额和奔跑的双腿,对于母亲灵魂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次集体的跪拜。
在低处,写有光芒的生活,这是我们诗人一生中应该干的没完没了的事情。前些日子,我还读到过《记忆》这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像一枚钉子,一直在往我的泪水里钉着:
能不能借我一毛一?我想/喝碗汤。人群中的一个陌生人/轻声这样说。他看起来跟我/一样年轻,衣裳穿的比我还洁净//坐在油漆剥落的联排木椅上/我疲惫地摸着身旁的行李/抬头看看却没有回答,因为/跟他一样,在秽浊的空气中//在没有暖气的冬夜,在等晚点的/火车。可在他转过身去的瞬间/分明看见他眼里的泪水,在昏暗的/灯光下,仍能看见寒意与伤害//记忆是一笔未能偿还的债务/包含着不良的自我记录,尴尬与酸楚/那一时刻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商丘火车站,春节刚过//如今伙计,但愿你早已是个暴发户/即使你仍是一个背着包袱/南下打工的老头,我也想再次/遇见你,我们该与我们的贫穷和解//一毛一分钱和一个人的眼泪/一毛钱是一个人的窘迫,是另一个/人的内疚,我们是两个年轻人/而该死的岁月曾如此贬低了我们两个
———耿占春:《记忆》
日子,拒绝为阳光签证、为生活放行。一个窘迫的人,已被生活碾压到了灵魂之外,为了基本的需求,他已顾及不了所有体面的方式,他被迫把手伸出来,以求得对身体的一次加温。
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是一次无奈而又潮湿的相遇。在黑白影片的年代,谁的个头也高不出那时的生活。而这终究成为了一种记忆。而这种记忆不时冲洗着一个人低沉的内心。这种自责来自于一个人的善良和人性,却带着现实的苦涩与苦衷。这种内心的挣扎、自责和不安,是有着温度、有着不会生锈的光芒的。
我想说这就是低矮处的光芒。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矫情和琐碎。
在这一点上,你也写过《母亲的陶罐》这样一首诗:
老房子拆了的那天/母亲的心也被洗劫一空了/狼藉满地,不知道该收拾哪里/她摩挲一下秋风里/那个黝黑的陶罐/自语了几句,又放下//它的价值几何呢/这笨重的罐子里,曾贮满了/那个时代的艰难吧/半罐子高粱面/或者玉米面,榆皮面/大约是那些时日的全部指望吧//如今,这些记忆/都与眼前乍离了枝头的落叶一起/成了对往日的祭奠了/母亲目光游移/不知所措/整个人在那个陶罐里下沉
———任爱玲:《母亲的陶罐》
一只陶罐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但时间久了,它和人便有了交情,它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器物了。面对即将逝去的旧物,母亲便有了伤心和疼痛,因为这只陶罐曾与母亲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可以想到,有时,母亲把那只陶罐擦洗得干干净净,让它有模有样地站立;有时,母亲顾不上照顾它,它便默不作声地守着盛在它心里的粮食,像个懂事的孩子。一只陶罐总是顺从着母亲的旨意,憨憨的,在寂寞的日子里,陪着母亲一同走着。如今,这旧有的器物就要被拆散了,就要远去。这让母亲感到了日子的断裂和生活的缺失。纠结中,母亲突然发现,那就是她苦命的神,让她重新地去打量和感念着这只陶罐的恩德。
我相信,这样的诗歌是善良的,这样的诗歌能够唤醒我们的目光,让我们记住了人的德行和花香的存在。读这样的诗歌是脚踏实地的,没有凌空的眩晕。
是的,这样的诗歌会赢得更多的人气和更长久的生命力。
三、一个能写长诗的诗人
写长诗,那绝对是一件压迫心脏、压迫大脑、压迫精神的事情。
爱玲能写长诗,这在我的意料之外。在她的这本诗集中,我看到她写的长诗就有三十首左右。
写长诗,首先要解决一个脑力的问题,其次是一个体力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耐力的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摇曳的女子能够肩起的重活,就连男人写作长诗,也要拎一拎自己是否能够吃了这碗干饭。
除此而外,长诗难写难在布局,因为一首长诗要流畅地写下去,写什么?有多少内容可写?这确实让一个写作者犯难。无话可说,无事可写,找不出事物的线索,就让一个诗人陷入了写作的泥淖和处在了萧瑟之中,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讲,是一件尴尬的事情。
我钦佩爱玲的勇气,敢于在高坡上行走,当我看到《农事》这组诗时,更加确认了我的这种判断,我想就《农事》一诗再一次有选择性地谈谈我对你的诗歌的看法。在《农事》的第2节中你这样写道:
选一个阳光正好的日子/把家里的两只小笸箩/摆在房檐下能晒到的地方/往玉米皮扎的草墩上一坐/再取出老花镜来,架上鼻梁/像要给春天绣花儿一样/一切就准备就绪了//从小布袋里抓出一把菜籽/一粒一粒地端详,一粒一粒地挑拣/两只手来回移动的样子/像极了在竖琴上弹奏曲子/目光里流动的都是音符/种子丢进小笸箩时发出的脆响/再一次叩响了春天的门铃———
诗人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是丰碑式的,是没有落上尘埃的,她把熟悉的事物以快递而原有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像把一部分乡村的生活搬到了我们面前,仿佛也让我们成为了一名乡村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有着白皙手指和白皙脸庞的路人。
我们对乡村生活已经开始陌生了,我们渐渐地远离了泥土,远离了鸡鸣、方言和节气。城市正在压倒乡村的生活,而城市生活却缺少了乡村的趣味,城市生活即便再热闹,比起干净的乡村,比起乡村的時光,总是有其暗淡的地方。
返回来再说这节诗歌,从技术上讲,前面的实写是在引伸,而最后一句才是这节诗歌的灵魂。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人,才能让一首诗歌有了这样的荣誉。
在日常写作中,有许多人写诗,往往是不注重结尾部分的。他们在写一首诗时,以实写开始,最终以实写结束,这样让一首诗处在了不温不火的状态中,使一首诗歌缺少了展示肌肉的机会,也缺少了一朵花儿在盛开时的爆发力,缺少了冲锋和高地。
就一首好诗而言:语言是铜,要有情趣。立意是银,要有思想。结尾是金,要有包袱。我的这种说法,不知是否和诗歌写作的方法及其规律沾一点边儿。
在《农事》的第6节中,你这样写道:
大地终于想开了/在田野的尽头/刷了一层薄薄的油彩/黄色的,鹅黄色的//母亲换上下地的衣服/荷了小锄,牵了小铲,开始忙碌了/没几天,棋盘似的菜畦里/便过起了五颜六色的日子
俏皮而放松的语言,诗人放牧着娴熟的想象和比喻。我们说,一首诗歌里如果缺少了想象和比喻,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样的诗歌可能会是一具干尸。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两首诗歌:
圆从苍穹、果实/和乳房上/找到了自己//它也从炮弹坑、伤口/穷人的空碗中/找到了/残损的部分//涟漪在扩大,那是消失在努力/而泪珠说/———请给圆/找一个最软的住所//所有的弧度都已显现/所有的圆,都抱不住/它的阴影……———毛子:《圆》
每次剥柚子的时候/你都只剥一半/让剩下的一半/在妈妈的胎盘里/多睡一会儿
———灵鹫:《剥柚子》
这两首诗歌的比喻和想象都是一手货,是诗歌创作信念的凯旋。而你的诗歌正是有这样的倾向、这样的信念,使我在阅读你的诗歌时有了向往。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诗歌的比喻和想象上,要毫不退却,要跳出窠臼,要有敢于去推动火车似的想象。这样,我们手中的苹果才可能会与众不同。
一个能写长诗的诗人,你的能力会让你接近一座果园。
当然,在接近这座果园的路途上,远处会有落雪的声音,会有石子磨擦着鞋底的声音,会有浪涛打在船舷上的声音,会有绳索断裂的声音,会有劈柴的声音,会有蜜蜂飞行的声音……爱玲,那些都是你的必经之路。我是说,只要你还爱着诗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