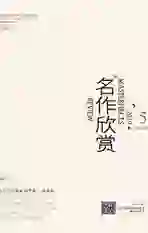“海外华文写作永远不会凋零”
2019-09-10白舒荣张娟
白舒荣 张娟
白舒荣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社编审。现任香港《文综》杂志副总编辑、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联盟副秘书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副理事長、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以及多个海外华文文学社团顾问等。出版有《白薇评传》《十位女作家》《热情的大丽花》《自我完成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以笔为剑书青史》《回眸——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缘分》《走进尹浩的故事》《华英缤纷——白舒荣选集》等数百万字的作品;合著《中国现代女作家》《寻美的旅人》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等多套海外华文作家丛书。近日,白舒荣的《海上明月共潮生》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18年),这本书大部分都是按稿约要求,写了与海外华文作家的交游经历,记录了这些作家的成长历程和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另有一些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一些现代作家撰写的传记文字。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曾寄语作者:“坐镇北京的编辑,能四海沟通,知交遍天下,当今第一人也。”笔者特意应《名作欣赏》之邀,采访了被誉为海外华文文学“教母”的白舒荣老师,请她谈谈写作《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台前幕后。
张娟:20世纪80年代中期,您开始专业编辑海外华文文学杂志,90年代主编《四海》(后更名《世界华文文学》),不仅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发表海外华文作家创作与研究的重要阵地,也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请谈谈您的编辑工作对您写作是否有促进作用?
白舒荣:因为喜欢文学,读了中文系。文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文学作品。编辑工作需要读大量的文稿,加上平时的阅读,对我写作当然是促进。其实颇有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编辑部门,逐渐比较专心写作,最终脱离编辑队伍,正式当了作家的。我的《白薇评传》出版后,当时有位名作家说他连夜读完,劝我不要当编辑了,该当作家。我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读书人,觉得做好本职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在写作上多用心。
张娟:据我所知,您毕业于北京大学,那个时代北大毕业可谓“天之骄子”,您的家学、您的北大生涯,对您日后的创作道路和职业道路选择有没有影响?
白舒荣:我是干部家庭出身,几乎从记事起就住校过集体生活,只有周末才在家里住一天。父母忙自己的工作,无暇也没条件(因为我很少在家)管我学习,不过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那时娱乐少,休息天常带我逛书店。我在书店流连忘返,种下了文学因子。读了北大中文系是我的荣幸,当时的老师基本是今日视为大师级的人物。我不是很用功的学生,但毕竟毕业于中文系,工作和爱好顺理成章吧。
张娟:在阅读您的新书时,注意到此书不但是您对华文作家的记录,也侧面看到了华文作家们对您的一些评价,比如欧华作协创会会长赵淑侠说您很早就打扮时尚,使她感觉很亲切;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说您“含笑的眸子明察秋毫,总能在不动声色间把他人内心世界的斑斓捕捉于心,展现于笔”;香港作家联合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潘耀明说您是“文坛女侠客”,这些评价呈现出了您性格的不同侧面。这些评价您认可吗?您的很多文章都是写入,您的性格特质对您知人论世的写作有帮助吗?
白舒荣:朋友们的评价难免溢美,却也不太离谱。比如赵淑侠说很早就会打扮,这与我接触的多是海外作家有关。一方面自己天性爱美,更重要的是环境(指接触对象)使然,当年海外作家多出自中国台湾,打扮时尚得体,我不免受影响。当然骨子里还有点不想让对方看贬大陆女性的私心。我的性格乐观开朗,笔下的这些作家多数交往长久,比较熟悉。我念旧,讲义气,常不自量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张娟:您采访过很多华文文学作家,我在阅读中感觉您特别善于抓住人物特质,特别善于描写细节,这些是否和您作为女性作家敏锐细致的观察力有关?
白舒荣:其实写这些作家时,真正去采访的并不多,主要是平常接触的印象和从其作品中捕捉一些东西。有些人物细节的描写,基本是出于我认识对方时的第一印象。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首次见白先勇,敲门后他的第一声回应,令我惊艳,牢牢回旋在脑海。
张娟:您在“自序”中说道:“或许,这也可算作是我的传记。”我注意到从早期的中国现代作家素描到后来的记人散文,您的作品中也是以人物传记居多,您为什么这么偏爱传记这种文学体裁呢?
白舒荣:我有一段在北京语言学院教书的经历。那时几位老师自动组合研究现代作家。我接触到白薇后,为她一生的磨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也为她曾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被重视而打抱不平,所以我放弃书写在文坛享誉比较高的作家,主动选择了不被人注意的白薇。这本书,还有另一本也是写作家的书,把我送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写作会上瘾,但我写不了小说。我觉得写小说,开始多少总离不开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没那勇气把自己放进去。工作使我和作家接触的机会增多,“顺手牵羊”写作家便成了我的主攻。
张娟:作为一个作家,成就她的不仅是创作,同时还有约稿的编辑、出版社、读者的认可和鼓励及写作环境等,在您写作的过程中,您作品的传播媒介怎么样?出版环境怎么样?
白舒荣:我比较懒,写作多少都带着“任务”性质,比如《白薇评传》是当时大家合作的专题项目,这是我的分工。再如写台湾女作家施叔青那本书,当时中国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主编一套台湾文学丛书,我就领了写施叔青评传的任务。最近这本《海上明月共潮生》中不少文章是缘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约稿。我写完一篇,她让我再写一篇,没有她的不断约稿,也许写不了这么多。报纸杂志和出版对作家写作是极大的推动和鼓励,尤其对我这样比较懒,也没决心从事专业写作的人。
张娟:您的这本书涉及的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余个地区和国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海外华文作家形象,这个写作过程一共持续了多少年?出于什么样的契机您决定将其结集出版?回顾写作的过程,有没有让您难忘的往事?
白舒荣:这本书里的文章,我在该书“后记”里提过,内中篇目都曾在国内外不同场合见过世面。有朋友覺得我这些文章有意义也好看,早就建议结集出版。我不是个高调的人,拖了好几年,后来觉得结集出版也好,就像把同类东西建个文件夹,方便存放。有位朋友看了结集的目录,动议了现在的书名,又建议找人在书前写点什么。对这个建议开始我不以为然,觉得找谁都是让对方耽误时间。临近出版,朋友的建议浮出脑海,突然灵光一闪,何不找熟悉的文友每人写几句话。于是当即发邮箱发微信,并“强制”一两天务必完成。果然都够朋友,或短或长的文字很快给了我。我便把它们当作“代序”命作“寄语”放在前面,如一串闪烁的珠链,为这本书增添了华光。想想,颇有点“拉大旗作虎皮”的意味。
张娟:《海上明月共潮生》出版后,您有没有遗憾,或者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接下来您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白舒荣:这本书最大的遗憾,就是在编辑过程中,我只想到赵淑侠晚年因为投靠亲人移民美国,就按国籍把她放入美华作家系列。其实,她开始文学创作,多半的创作成就都发生在欧洲,更何况如今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就是她当年在瑞士时辛辛苦苦努力创办的,我们最早的交往也开始于她在欧洲时。把她归于欧洲华文作家之列更合理。
另外的遗憾是我漏放了香港作家刘以鬯。被香港拍摄成电影的《花样年华》系根据刘以鬯的《对倒》改编,这已是在该书出版多年后的事。刘以鬯先生这部长篇在香港报纸连载二十几年无人肯出版,是我首版实现了他的愿望,而且当时的出版经费和稿酬是我拉的赞助,并为此书撰写介绍发表在香港《文汇报》。虽然这些遗憾有点如骨鲠在喉,但世间哪有完美!释然!
目前手边正写一本有关“侨批”的书,探寻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先祖们当年下南洋的种种。
张娟:您常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界的“教母”,可以说,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了解,您是中国第一人,您能不能评价一下今天海外华文发展的状况?在新的形势下,海外华文作家如何书写“中国故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白舒荣:“教母”的称呼我不大喜欢,“第一人”更非如此。只不过我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编辑工作比较早,结识的作家多点。我当编辑有一个特点,比较重视雪中送炭,不大追求名家。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我颇多家国情怀。从早期移民作家作品中看到华人在海外生计艰辛,还能坚持华文写作实属不易,作为国内的专业杂志理应为他们多创造发表机会,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继承和传播,也算为国家尽一份力。当时我重视的尚在成长中的写作者,如今皆已成名。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的状况比我当年想象的要好。第一,随着中国人留学移民的增加,凡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有华文写作者,华文作家分布的地域日益广大,人数日渐增多;第二,由于中国大陆外出留学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在美欧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兴旺,不少华文文学社团经常组织各种文学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华文写作者的创作热情。国内许多大学有不少学者从事华文文学研究,兼之国家出面组织大型世界作家大会,对华文文学的创作发展和繁荣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相信,海外华文写作永远不会凋零。至于海外华文作家写什么是个人的自由,似乎没有必要要求他们必须写中国故事吧。他们所写,只要对人类的进步、人类的良知有正面引导和启迪作用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