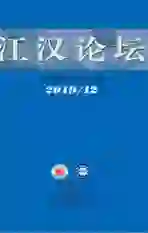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演变、 特征及司法界定
2019-09-10张子豪
摘要:黑恶势力犯罪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经历了从有到无、死灰复燃和发展变化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基于实证分析,考察黑恶势力犯罪中出现的新手法及其新动向和趋势,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当前黑恶势力犯罪对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与腐化,其违法犯罪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合法化以及去暴力化等特点。黑恶势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一步上升,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着社会生活、经济秩序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发展。为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我国刑事立法应及时予以应对,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界定标准。
关键词:黑恶势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司法界定标准
基金项目:湖北省法学会2018年度省级法学重点课题“湖北省黑恶势力的发展态势与侦查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108-04
黑恶势力是当前我国刑法的打击重点,这里的黑恶势力的“黑”指黑社会性质组织,“恶”指恶势力。①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贩毒、恐怖主义活动一起被联合国大会并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当今,国际社会上的黑社会组织已由早期单纯暴力型集团犯罪,向政治、经济领域进行渗透,其中势力强大者甚至具备左右国家经济命脉的实力,对国家的政治政策产生影响。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我国黑恶势力犯罪产生了诸多新特征,这也向相关司法工作,尤其是司法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复杂的问题。
一、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演变
在我国,从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如各种秘密会党、教门和帮派。尤其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一些帮派组织逐渐演变成了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如旧中国上海滩的青红帮等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展了剿匪清匪、镇压反革命和肃毒禁娼等活动,并实行严格的社会管控,旧中国遗留的黑社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失去了滋生土壤。到20世纪50年代,除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外,我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基本被彻底肃清,也出现了三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空白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原有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之也出现了犯罪高峰期。我国的一些犯罪分子受境外黑社会组织影响,甚至出现主动邀请境外黑社会成员参加的情况。一时间产生了大批犯罪团伙,其中有的犯罪团伙成员较多,组织严密,且具有职业性。他们有计划地组织进行犯罪活动,手段恶劣,危害严重,并呈现出向黑社会(性质)犯罪转变的趋势③。当时,大量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甚至转向合法身份,为攫取更大的社会利益,一些黑社会组织开始介入政治领域,寻求“保护伞”。我国1979年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无明确规定,也未提及“黑社会”。在涉黑犯罪情况严重的个别地方,一些地方率先针对涉黑犯罪作出了规定,如深圳在1982年颁布的《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公告》。1992年,公安部第一次明确黑社会组织的六个主要特征,对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具有重要意义。1993年,公安部刑侦局成立了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指导全国公安机关的打黑行动。同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广东省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对黑社会组织的概念与处罚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当时,处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违法行为多处劳动教养或者治安拘留、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以“敲诈勒索罪”“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或“流氓罪”等定罪处罚。1997年,我国在修订刑法时,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294条中,专门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个涉黑犯罪的罪名。这也决定了“恶势力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其产生之初并不具有规范属性。无论是79年《刑法》还是97年《刑法》,都没有直接规定恶势力犯罪,……2000年以来随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不断推进,作為从普通共犯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过渡阶段,恶势力概念逐步规范化、法治化。”④
进入21世纪,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更高形态发展,涉黑犯罪活动愈发活跃,危害性日益增加。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四种特征,即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阐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大特征,同时提高了组织者的法定刑、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纳入了特别累犯的范围、增设了财产刑。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纪要》),详细规定了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危害性特征和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等内容。
二、我国当前黑恶势力犯罪的特征
“任何犯罪都有社会危害性,即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恶势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它的危害性要大于普通犯罪。因为恶势力犯罪的严重危害结果和恶劣社会影响及于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其社会危害性具有散发性和辐射性。”⑤ 通过对湖北4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33个恶势力集团、上海 ⑥ 1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广东 ⑦ 2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浙江 ⑧ 30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河北石家庄 ⑨ 等地黑恶势力犯罪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有:
1. 犯罪主体。(1)职业构成。首先无业、刑满释放人员较多;其次为农民、其他社会闲散人员、吸毒人员、个体户和工人。(2)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高学历人员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公司化经营、新型犯罪、网络化的组织犯罪中。(3)年龄结构。31—4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4)成员来源。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大多来源于组织所在地域。上海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力军则是外来人员。同时,在同案件中,同户籍成员居多,且多为亲戚或同乡,从而也形成“家族型”犯罪组织,稳定性和内聚性更强,犯罪得逞率更高。(5)成员前科。无前科的人数占总人数的78%,但案件中主犯多有前科,且前科所涉罪名大多是抢劫等暴力性犯罪。(6)成员身份。首领、骨干分子的身份发生变化,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从小偷小摸、两劳释放的社会底层人员变为企业家以及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2. 组织结构。(1)人数规模。上海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人数较少;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规模上大多为中小型组织;湖北涉黑组织人数集中在11—30人之间;涉恶集团人数集中在4—10人之间,人数特大的恶势力集团较少见。(2)纠集和集合方式。一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结合而成的家族式犯罪团伙。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二是以行业为纽带形成的各类“市霸”“行霸”。主要在城乡结合部、城市的某一部位,或在公路、市场等地带,其活动范围一般不大、辐射能力不强。(3)组织形式。可分为松散型、过渡型和紧密型三类。(4)存在时间。3—5年、6—10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数量占总数的80%。(5)组织体系。有由并联向串联转变的趋势,而且随着组织日益健全,由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犯罪的比率越来越小。
3. 犯罪形式与涉足领域。可分成三类: 以经营传统的非法行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型、通过运行合法的或者表面看起来是合法的经济实体获得经济利益的公司型与兼具二者特征或者曾经经营非法行业,后来逐渐向合法行业过渡的混合型。
4. 犯罪行为模式。(1)犯罪手段。一是日趨隐蔽化。“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与专项整治,提高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成本。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行为,不得不趋于隐蔽。”⑩ 二是日益智能化,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2)所涉罪名。由犯罪行为向违法活动转变。行为强度不断弱化、柔性化、威胁化。从过去大量使用暴力转变为打擦边球的、相对节制的轻微暴力或软暴力。(3)活动范围。多是在控制力较薄弱的县以下城郊、行政区划的结合部等地方存在。也有少部分黑恶势力的活动区域和犯罪领域在扩大,本地作案与跨地区、省份、行业作案结合,越境、异地作案成为一种潜在趋势。(4)犯罪工具。使用管制刀具,但使用枪支弹药的组织占比更高,同时展现出由内生暴力向雇佣暴力转变的趋势。
5. 寻求“保护伞”和向政治领域渗透。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其实质是通过公权力,以进一步扩张其非法控制的程度和效果。
三、我国黑恶势力犯罪司法界定的相关问题
对于一个立足于中国的刑法研习者或立法者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共同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这种考验要求在理论上积极探索、承故纳新,而非抱残守缺、胶柱鼓瑟。{11} 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明确的立法规定,恶势力属于没有立法依据的非法律用语,即司法惯常用语。我国最早对恶势力作出明确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座谈会纪要》,其将恶势力总结、归纳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指导意见》)中, 恶势力的定义被进一步厘清,将恶势力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有的最终发展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时规定可以使用“恶势力”等表述于相关法律文书关于犯罪事实认定的部分,逐渐使之成为法律化概念。《2018年指导意见》关于恶势力的规定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危害性特征,增加了“欺压百姓”,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中的“犯罪团伙”修改为“违法犯罪组织”;二是组织特征,将“纠集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中的“骨干成员”去掉;三是行为特征,进一步进行了细化与扩张。
2019年,全国扫黑办发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更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指引——《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9年意见》),其第4条规定:“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普通违法犯罪团伙区分开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往严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深度延续,但‘扫黑除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严打’,其是在现代法治的范围内依法打击犯罪,注重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12} 恶势力应有以下特征:
(1)组织特征。首先,组织存在是前提,该组织并非临时纠集而来,但也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紧密程度。在人数要求上,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将恶势力的成员人数把握在3人以上。只有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十分明显、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极个别情况下,才可考虑认定“2人恶势力”。“1人恶势力”明显不符合构成条件,应排除{13}。同时,成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求“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此外,对特殊人群要慎重把握。其次,对纠集的时间和频率、跨度有要求。时间要有跨度,不能过于短暂,违法犯罪的频率要“经常”,不能相隔太久。再次,组织中要有相对固定的纠集者。同时纠集者并不强调一定为同一人,可以是多人,是否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是关键。
(2)行为特征。第一,暴力性。一是恶势力的主要违法犯罪行为包括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罪名。二是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具有上述罪名的犯罪团伙,就应认定为恶势力,还应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三是伴随相关罪名,并具有“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特征时,才能以恶势力论处。并且在两高两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正式将“软暴力”手段划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以及《2018年指导意见》“恶势力”概念中的“其他手段”。第二,多次性。这是指在一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据《2019年意见》第9条规定,“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至少要有一次犯罪活动。认定过程中,在反复实施单一性质违法行为的情形下,单次情节以及数额虽尚不构成犯罪但按照刑法或相关规定进行累计后应作犯罪处理的,可将已累计的违法行为算作一次犯罪活动,而其他违法行为则单独计算。除不符合法定情形而不得重新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形,对已处理或已作民间纠纷调处后,经查证发现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也可作恶势力认定的事实依据。
(3)危害性特征。一是综合判断危害性特征。《2019年意见》第10条规定,在认定危害性特征时,应结合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把握。考虑到恶势力是“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其在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同时,存在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具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之外,恶势力还应具备雏形特征{14}。二是必须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2019年意见》第7条规定,对尚不足以造成较为恶劣影响的情形,一般不应作恶势力认定,体现出认定上的从严掌握。同时,其也规定人民法院只能判决、裁定已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主动认定,以及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相关权利,体现出程序上的从严。
因此,根据《2019年意见》第11条关于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相关规定,在認定恶势力犯罪集团应着重把握以下两点:其一,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是恶势力标准加犯罪集团标准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根据1984年《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的规定以及《2018年指导意见》第15条的规定,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一是较恶势力仅要求“纠集者相对固定”,恶势力犯罪集团则要求其首要分子与重要的成员相对固定,且人数在3人以上。首要分子较为明显,部分首要分子为组织、领导纠集与行动者,有的则是在纠集的过程中产生;二是常纠集在一起,有预谋地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性质恶劣的刑事犯罪活动。但作案的次数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对社会的危害性、危险性的严重性高。其二,恶势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应参照《2018年指导意见》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即恶势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为:(1)为该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树立非法权威、扩大非法影响、寻求非法保护、增强犯罪能力等实施的;(2)按照该组织的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实施的;(3)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4)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5)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6)其他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
注释:
①⑤ 陈兴良:《恶势力犯罪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
② 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③ 张琦:《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原农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④ 刘仁文、刘文钊:《恶势力的概念流变及其司法认定》,《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⑥ 参见金泽刚、李炳南:《上海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与思考——基于十四个已决案例的实证分析》,《法治研究》2014年第2期。
⑦ 参见张翔、李康震:《广东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研究——基于已判刑的2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考察》,《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⑧ 参见严励、金碧华:《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分析——以30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⑨ 朱和庆等:《〈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报》2019年6月13日。
⑩ 林毓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暴力手段及软性升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11} 焦旭鹏:《现代刑法的风险转向——兼评中国当下的刑法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12} 何显兵:《论“扫黑除恶”中的没收犯罪工具》,《东方法学》2019年第5期。
{13} 参见智世勇、刘枚:《浅议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的特征及防范打击对策——以石家庄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4} 戎静:《“扫黑除恶”背景下“恶势力”的司法认定:争议与破解》《政法学刊》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子豪,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李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