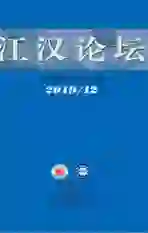中国古代借贷契约中的 义利观及其当代镜鉴
2019-09-10武航宇
摘要:我国古代借贷契约文书篇幅有限,内容简练,传统义利观作为一对古老的概念,存在于借贷抵押、利息率确定、偿债方式等诸多方面。放贷方以 “计套贫民”的方式对借贷方进行掠夺,这体现了逐利的本性。同时,民间以“平借平还”的舆论倡导互利之义,国家分别以立法禁止“违法取息”的方式规范互利之义和以禁止掠夺式索债来保障互利之义,从而缓解借贷双方的矛盾。但实际上,将借贷契约中的义与利把控在一定限度内,使之既符合“君子之义”,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才能促使借贷契约的顺利、有效履行。针对当前问题繁多的民间借贷案件,可以将传统的义利观作为价值考量融入到公序良俗原则中,并在没有确定裁判依据的疑难案件中适用,这不仅是对客观要件认定原则的补充,同时也能使裁判结果更加符合我国传统的价值观。
关键词:义利之辨;“计套贫民”;互利之义;君子之义;公序良俗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097-06
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①。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② 这里的“利”主要是满足人生存需求的客观存在,属于事实范畴;“义”则是规范行为的道德伦理法则,属于价值范畴。“义”与“利”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借贷契约中既有“计套贫民”的博弈,也有“平借平还”的共生,当然也有赦免债负式的辩证体现。所以,“利”本身不具有伦理意味,正是因为以“义”为目的才具有伦理价值。如果说“义”是以公共利益取向为主,“利”则是维护私人利益的载体。“义,利”③,对于国家而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④ 对于社会来说,是以“仁”“礼”为中心的。虽然自汉代以降,儒家的伦理思想占据主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情感为表达方式、以情理法为判断机制的人情社会逐渐巩固,借贷契约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符合儒家伦理之义的元素;但同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了满足迫切的资金融通需要,还要遵循逐利的经济规律而缔结借贷契约,所以“义”与“利”往往杂糅在借贷契约的理念与实践中。
一、逐利忘义的“计套贫民”
我国古代社会,借贷契约在缔结和履行过程中包含了很多逐利的因素,尤其是部分借贷契约在缔结时约定了高额利息,甚至以“计套贫民”的方式对借贷方的本利进行掠夺式执行,即先以“男女质钱”,而后逐渐“子本相侔”,最后则“没为奴婢”,致使借贷方“老稚转乎沟壑”,其状凄惨,完全无视伦理之义。
1. 高利贷使“老稚转乎沟壑”
单纯就借贷而言,夏、商、周时就已经存在,它起到融通资金、货物的作用。最初放贷主体多为官府,《周礼》云:“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⑤ 当时,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主管借贷,规定有无利息、具体利息数额及还款期限。春秋战国以降,民间资本聚集,并开始进入借贷领域,从借贷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多是借贷方急需钱物使用而实施借贷,如《管子·轻重丁篇》载:“桓公曰:峥丘之战,民多称贷,负子息,以给上之急,度上之求。”但由于借贷方在困境中无法与放贷方协调利息高低,所以只能由放贷方依具体情势而确定。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放贷方会收取本金一倍,甚至数倍的利息。《史记·货殖列传》载:“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作为放贷方则几乎不考虑放贷之义,而单纯追求高息带来的利,《新唐书·食货志》载:“州县典史捉公廨本钱者,收利十之七。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另外,民间放高利贷的组织或个人更是最大化追求利,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全唐文·宪宗》载:“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
在高额利息的驱使下,放贷方全然不顾借贷之义,充分暴露出借贷契约之逐利特质。因为高利贷的利息过高,放贷者获取这些利润的代价是借贷者的辛苦劳作,甚至是倾家荡产,虽然国家为了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会规定借贷利息的上限,但却并非长期有效。晋国大夫叔向曾抨击放高利贷的行为,即《国语·晋语》载:“桓子,骄泰奢侈,食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孟子在谈“为国”時,也论述了高利贷对百姓生活的危害,即“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⑥
2. 以“儿女为质”违背亲伦之义
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借贷方往往不惜代价,甚至以人口为质获取贷钱,汉代民间甚至有以夫妻二人为质而借贷的情形,如《居延新简》载:“贷钱三千六百以赎妇,当负臧贫急毋钱可偿知君者,谒报敢言之。”也有以己身为质而贷钱者,如《太平御览·孝感》载:“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一旦还不上这类高利贷,借贷方则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以人口为质的高利借贷现象屡禁而不止,在韩愈为柳宗元所写墓志铭中即有表述:“(唐宪宗)元和中,……柳州……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⑦ 宋人勿守素曾上表曰:“容州……部民有逋赋者,或县吏代输,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⑧ 即使在借贷契约中没有以“儿女为质”的约定,在借贷期限届满后,高利放贷者如果收不到本息,也会无视伦理之义,侵夺借贷者家中人口为奴婢,如《通制条格》载:“哈剌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⑨ 在大多数时期,对于以儿女为质借贷而无法偿还者,儿女则为放贷方的奴仆,对于此种现象,官府并不干涉管理,而是依契约之约定。永乐初年即有一案,“有以男女质钱,久不能偿,没而为奴者二十余家,诉于官,官无以理之。”⑩ 从事实范畴来看,借贷方以“儿女为质”可以理解,但是却违背了价值范畴的人伦法则。
3. 抽离基本生产资料无视社会伦理之义
放贷方为了保证借贷资金能够如期收回,掠夺式索债屡见不鲜,如唐时,通常在契约文书中注明“若延引不还,听牵取白家财及口分,平为钱直”,明确约定借贷方到期无法还钱,放贷方可以牵掣其家中财物及口分田。同时规定“身东西不在,一仰妻儿偿还”,即一旦借贷方死亡,则由妻儿偿还,因此,放贷方根本不考虑借贷方的基本生活状况,只是一味逐利。对于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借贷方而言,所借贷金额的数倍本息如果以田产、牲畜等基本生产资料抵债仍不能偿还,则只能由保人偿还,在这种情况下会对保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泾包眉村徐悌者,尝为所亲周熙假人白金六两,熙无还,债主逼悌偿,其妻又相怨詈,悌乘忿往缢熙家。”{11}
为了减轻借贷者的负担,保障其基本生存需要,李元弼在《作邑自箴》提出:“放债人户切须饶润取债之人,轻立利息,宽约日限。即不得计套贫民,虚装价钱,质当田产,及强牵牛畜,硬夺衣物动用之类,准折欠钱。”{12} 作为基层政府长官的李元弼,熟知县、乡里放贷方欺骗贫民的逐利伎俩,所以他提出在索债时应讲究义,即禁止掠夺性偿债的借贷契约,不能由放贷方将田产、牲畜全部夺走,应该将所欠本息折成银钱履行债务。由此可以看出,官府允许放贷方在逐利的同时也应考虑义,保护债务人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是实际牵掣财务抵债的逐利现象很普遍,基本无视社会伦理之义。
二、符合互利之义的“平借平还”
中国古代政府在借贷契约利息率的确定、索债的方式,以及纠纷的救济途径等方面体现出诸多义的因素,但对于利息率的管理最为集中,也最能体现统治者维护正统伦理之义的努力。
1. 民间以“平借平还”倡导互利之义
民间生活离不开借贷,“富者贫之母,贫者一旦有缓急,必资于富;而富者以岁月取赢,要在有司者处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说而行,各为其主张,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两手,贫富犹左右手也,养右以助左,足以便事”{13}。正常情况下,民间百姓认可适当利息的借贷,如《孟子·滕文公篇》云:“又称贷而益之。”赵注云:“称,举也。有不足者,又当举贷子倍而益满之。”索隐云:“子谓利息也。贷子,盖汉时常语。”{14} 对于有息借贷而言,只要“不使有偏”,利息适当,则是符合人际交往之义的。从明朝时文人的记载来看,民间的月利息率确实维持在3%左右。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记载:“(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不可奈何也”。{15} 适当利息,即“平借平还”,是借贷方所期待的,而且这种利率也符合民间的经济需求,所以在借贷契约缔结、履行过程中,如果放贷方做到这一点,则值得“相约记善”。
另外,在古代民间借贷中,有些地区以借贷金额为标准区分利息率,即“湖郡典息,向例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16} 区分利息率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对借贷金额少的贫民而言,却是看得见的额外负担,所以当“恤民瘼”的巡抚金公轸“准行审勘,断定盖以一分五厘起息”,则为百姓减少了数额巨大的利息,“数十年来贫民阴受其福,所省典息,何止累万?”官员这种解决借贷方额外负担的举动,从公权力角度助推借贷契约“平借平还”的实现,从而受到百姓称颂。当公权力无暇顾及借贷利息率的时候,民间或有“义士”出面维护“平借平还”之借贷,如“自童国泰控之当道,与典商结讼十三年,卵石不敌,深陷缧绁,有啗之以利者,志不少变。”{17} 这种官府与民间合力控制利息率的行为,受到百姓赞扬,也的确彰显了借贷契约的互利之义。
2. 立法禁止“违法取息”规范互利之义
汉代即颁布法令,限制利率。《汉书·食货志》载:“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其所得受息,勿过岁什一。”对于违规取利者,国家使用公权力手段予以制裁,《汉书·王子侯表》载:武帝元鼎元年,旁光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至唐代,国家对于利息率的规定更为具体,《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公私以财务出举”条明确规定:“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国家不仅开始规定了具体的利息率,同时规定全部利息总额不能超过本金,其目的是体现借贷契约的互利之义,防止放贷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获取过高利息。但是民间放貸者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规定,获取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元时民间为了规避“钱债只还一本一利”的国家相关规定,实践中进行“转换契券”,形成“息上加息”的结果,即收取所谓的“羊羔利”,以重签借贷契约的方式达到借贷利息形式上的合法化。明时,借贷契约使用更为频繁,但是法律对利息率的限制更加严格。明太祖朱元璋在宝训中要求“今后放债,利息不得过二分三分”{18}。《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明时国家所规定的年利息率36%,为唐时国家法定利率的一半,说明当时国家对百姓借贷问题管理更为严格。同时,相较《唐律疏议》而言,《大明律》增加了对违法取息的刑事处罚,即“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如果放贷方因放贷而获取的违法收入过多,则会按“坐赃”罪处罚。清时,国家法定利率与明代相同,年利息率仍为36%,国家也规定禁止索利过本,即“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实属违禁,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即至十年,不过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当然,民间仍然有借贷利息超过本金的现象存在,如清人胡承谋在《吴兴旧闻》中记载:“贫民衣饰有限,每票不及一两者多隔一二年,本利科算,不能取赎,每多没入。”{19}
由汉至清,国家调控借贷利息的立法在不断完善,最初只有限制借贷利息的规定,而后针对利息超过本金的行为予以明令禁止,后来对以“转换契券”方式变相收取高出本金利息的行为予以严格规范,目的是维护稳定的借贷秩序,使借贷保有互利之义。但民间的放贷方往往无视法律规范而行“重利剥民”之实,所以明时法律规定对“违法取息”的行为处以笞杖之刑。这说明国家公权力对于借贷之息的调控越来越精细且严格。
3. 禁止掠夺式索债保障互利之义
唐时民间借贷现象非常普遍,且数量庞大,国家从尊重经济规律出发,赋予借贷双方自由缔约的权利,《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务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但从实际的操作来看,部分借贷契约利息率过高,如《唐乾封元年高昌郑海石举银钱契》中载明:“乾封元年四月廿六日,崇化乡郑海石于左憧憙边举取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半。”从契文中可知,这份有息借贷的月利为15%,属于高利貸的范畴。高额利息极易使借贷方到期无法偿还本息,直接导致放贷方采用掠夺式索债方式收取本息。因此,唐时国家从五个方面对索债的方式予以规制。
首先,官府受理严重影响百姓生活的借贷纠纷,即“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同时,禁止私自牵掣借贷人财物过本息,《唐律疏议·杂律》曰:“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另外,也不得私自处理、占有借贷方质押财产。放贷方对于所收质押之物要经“市司”售卖方为合法,即“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而且“有剩还之”{20},不得非法占有本息之外财物。其次,禁止将借贷人扣押为奴。《唐律疏议·杂律》“良人为奴婢质债”条明确规定:“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叁等”,即如果放贷方将借贷人扣押作为奴婢使用或买卖,要判处流刑,与未经政府批准自卖为奴同罪。这一规定说明国家关注了百姓的人身自由,放贷方不得因借贷未偿而侵犯借贷方的人身自由。再次,法律同时保护放贷人的利益,规定“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掠夺式索债不是唐时的专利,其存在于有高利贷的所有历史时期。比如元时放贷方掠夺式索债手段恶劣,经常“强行拖拽”人口和牲畜,即“诸称贷钱谷……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21} 国家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禁止此种掠夺式索债,体现了国家对于弱势贫困人口的保护,如《元典章》卷二十七《户部·钱债·私债》规定的,“勿得径直于州县将欠债官民人等一面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搔扰不安,如违,定行治罪。”
三、明确义利界限的“放免债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的根本区别在于利的受众,君子为天下众生求利,不为自身索取,是为义,即“儒者知义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君子以利天下为义”{22};小人为自己求“利”,完全不顾他人,他所见到的利就是利于自己,即“小人利而后可义”。利作为“生人之用”,其与义的界限在借贷契约的“放免”问题中体现的颇为明显。
1. 国家“放免”官债求“君子之义”
汉代以降,皇帝为了表现“君子之义”和“恤民”的情感,会在重要的日子“大赦天下”,其中对国家贷给百姓的债负完全“放免”。汉宣帝在位期间颁布“大赦”诏书十次,其中含“放免”国家债负数次,如汉宣帝元康元年颁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23} 晋时皇帝沿袭前代的“大赦”制度,赦免官府所放债负,其目的仍是彰显其胸怀天下之利的君子之义,如“晋武帝泰始元年,受禅即位,大赦。逋债负皆勿收。”{24} 在赦免债负的问题上,皇帝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考虑,其所要表现的是“仁政”爱民,解决百姓借贷所带来的重利之苦,使借贷契约在执行时有了“温度”。宋太祖乾德四年诏令:“诏西川民欠伪蜀臣僚私债者,悉令除放。”{25} 这一诏令是太祖对特定债务的除放。其后,宋哲宗元祐元年,面对严重的旱灾,时任右司谏的苏辙认为,可以赦免“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的“官本债负”,可以“收民心,民心悦附”。{26}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官府对其所放官债具有所有权,同时具有天然的处分权,官府赦免借贷方的债务,可以视为追求“仁德”的表现。
2. 国家“放免”私债“非美事”
至北魏,皇帝不仅赦免官府所放官债,甚至将私人债负也全部赦免,如《魏书·孝庄帝纪》载:永安二年八月,孝庄帝颁诏曰:“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官府赦免私人债负则超过了其所处分的界限,不属于义的行为。唐代经济社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除了官府的官债之外,民间私人借贷急剧增多,因此国家规定了赦免公私债负的不同标准。宪宗元和十四年曾颁赦令云:“门下……御史台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公廨及诸色本利钱,其主保逃亡者,并正举纳利,十倍已上;摊征保人,纳利五倍已上及辗转摊保者,本利并宜放免。……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应在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本主及元保人死亡,又无资产可征理者,并宜放免。”{27} 至穆宗长庆四年,国家颁布诏书,确定:“契不分明,争端斯起。况年岁寖远,案验无由,莫能辩明,只取烦弊。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28} 敬宗宝历元年正月七日敕云:“京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曾出利过本两倍,本部主及元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征理。”{29} 从唐代的这三条赦文可知,其赦免的私人债务属于“坏账”,即官府已经无法找到借贷契约的债务人及保人,债务人及保人也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因借贷而产生的欠款已经没有回收的可能,为了稳定经济秩序,也为了展示统治者对百姓的“体恤”,颁布了赦免令。总之,国家是从公权力的角度对于官债及私债中的“坏账”予以“放免”,其本意应该是追求“君子以利天下为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奸佞之徒滥用,导致民间私人债权受到侵害,因此在民间借贷契约文书中出现了“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抵赦条款”,用以保护放贷者的私人债权。
实质上,就赦免私债的行为而言,统治者的出发点是体恤贫苦的债务人,超出了“君子以利天下为义”之义的界限,用行政权破坏了放贷者私人之利,使放免债负的行为转换成了不义的行为,违反了经济规律。所以,历史上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南宋时,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温州布衣万春曾上书言:“乞将间有私债,欠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除放”。{30} 万春乞请赦免债负,他看到的是大多数高息放贷者倚势欺压百姓的现实,请求国家以强制手段免除民间私债,从而解决百姓的困难。万春的行为似乎是符合了“君子之义”,但是他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借贷行为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不符合借贷的运行规则。高宗的意见是:“若止偿本,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害。乃诏私债还利过本者,并以依条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31} 高宗的这种解决方式就是国家不禁止借贷,不会通过公权力赦免债负,而是要保障民间借贷朝“公正”的方向发展。其后,光宗淳熙十六年赦曰:“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针对这一赦令施行的时间暂且不论,后人对此评论颇多,清人俞樾认为,“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这样处理“私家逋负,以恩诏免,其事殊不便于民”{32},似有不妥,所以,宋以降,国家公权力不再赦免债负。
3. 私人“放免”私债行“君子之义”
除了统治者之外,民间也常有以免除私人债负行“君子之义”的善人。《史记·孟尝君传》载:战国时,齐国孟尝君的食客冯马雚受命到采邑“薛”地,向负债百姓催债,却“齐为会日,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当孟尝君责问他时,冯马雚声称是为孟尝君博“善声”的。《后汉书·樊宏传》载:东汉樊氏家族“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但樊宏去世时却:“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樊宏的这一善意举动为乡里称颂。《魏书·卢义僖传》载:北魏卢义僖,曾“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北史·李士谦传》载,北齐李士谦:“士谦出粟万石,以贷乡人……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明年,大熟,责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清人何元锡也曾免除穷困债务人的债务,也曾“勇于赴人之急,而不责其偿。其客山左也,有马别驾登鳌者,假贷数千金,即倾囊予之。无几何,别驾殁,遗孤贫不能自存,君即焚其券,虽以此致困,终不悔也。”{33} 民间债权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债权,免除债务人的债负,符合“君子之义”,通常会博得“乐善好施”之名。
另外,也有为教育子孙追求“君子之义”而主动免除债负的情况,清代人钱泳在《登楼杂记》中记载:“徽州人有汪拱乾者,……人有告借者,无不满其意而去,惟立券时,必载若干利,因其宽于取债,日积月累,子母并计之,则负欠者具有难偿之患。一日,诸子私相谓曰:‘昔陶朱公能积能散,故人至今称之。今吾父聚而不散,恐市恩而反招怨尤也’。拱乾闻之,语诸子曰:‘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于是检箧中券数千张,尽召其人来而焚之,众皆颂祝罗拜,自此以后,诸子亦能自经营,家家丰裕,传其孙曾。今大江南北开质库或木商、布商、汪姓最多,大半皆其后人,当为本朝货殖之冠。”{34} 汪拱乾将负欠者的“难偿之债”全部免除,当借贷契约文书在债务人面前被全部烧毁的时候,众债务人感激涕零。汪拱乾因为追求“君子之义”,免除了百姓久不能赎的债务,在道德上得到了极大的赞颂。
从民间来看,舆论导向允许借贷行为的存在,但是仍然追求公正的借贷行为,希望国家能用公权力对利息进行适度管控,将利息率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无论是官方“放免债负”,还是民间“焚其契券”,均会因为其中的“君子之义”而博得百姓赞誉,但实际上来看,民间债负作为“私有之权”,一概免除会损害守法放贷者的利益,也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即“赦非美事”。因此国家放免因借贷契约而形成的“死账”,或者放贷者焚烧极度贫困之家的债负,符合“君子之义”,而无标准的“放免债负”或“焚其契券”则“非美事”,所以,义介入借贷契约需有一定的限度,要符合经济规律的运行。
余论:传统义利观对公序良俗原则的丰富
当前,“套路贷”“现金贷”“校园贷”等与借贷有关的案件迭出,放贷者攫取利益的手段不断突破价值底线,这类案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针对这类借贷纠纷,我国已经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目的是配合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非常详细并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借贷发生的背后原因异常复杂,借贷担保形式多样,放贷方索债方式五花八门,所以造成了司法裁量的困难,很多情况下无法用具体法律条文予以客观化裁量。
作为一个西方法律体系的概念,公序良俗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较少。在《德国民法典》的借贷利息管制方面,却将“善良风俗”原则作为裁量的主观方面予以充分利用,该法第138条第1款明确规定:“违背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处理借贷纠纷时,法官一般将这类抽象性的原则与具体的法律规则相结合进行综合裁量。处理借贷案件时,法官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规则与纯客观化的法律规则相比,虽然在可预见性与确定性层面有所不足,但更灵活,更适合个案。
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立法本身的滞后属性,造成法官在裁判民间借贷案件时完全采用客观要件认定原则有一定难度,同时法官又缺乏相应的商业经验与社会经历,所以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在缺乏明确客观的法律规则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况下,可以将公序良俗原则引入到裁判中,这不仅是对客观主义审判模式的补充,同时也能使裁判结果更加符合主流价值观。但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却需要传统价值观念的丰富,针对民间借贷案件,可以将传统的义利观作为价值考量引入借贷案件的裁判过程,并与具体法律条文原有价值基础进行比较权衡,使传统的义利观更能契合社会现实需要。
“套路贷”“校园贷”,或是“现金贷”,均是以借贷为名,采用“计套贫民”方式逐利,放贷者以诱骗的方式签订借贷合同,恶意使借贷方无法偿债,而后以“转换契券”等方式实现债务的放大,最后以威胁、暴力等手段掠夺性索债。对于这种复杂的借贷案件,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通常没有对应的完全客观化的法律规范,因此可以从传统义利观的角度,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进行主观裁量。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复利计息”“迟延利息”等显失公平的民间借贷问题,均可以从逐利忘义的角度出发,以公序良俗原则来裁断。实践中民间借贷的复杂之处还表现在以借贷的形式掩盖其他的债权纠纷、借贷合同的具体条款约定不明确等等,司法机关很难进行完全客观化的司法裁量,将公序良俗原则中所包含的“君子之义”应用于这类案件进行主观方面的衡量,能够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操作性,也能够促进公平原则的适用。
注释:
① 《孟子·离娄章句上》。
② 《荀子·荣辱》。
③ 《墨子·大取》。
④ 《大学·第十一章》。
⑤ 《周礼注疏》卷第15《泉府》。
⑥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⑦ 《柳宗元集》附录《新唐书本传》。
⑧ 《宋史》卷449《列传·勿守素》。
⑨ 《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
⑩ 《泊庵集》卷11《彭县丞墓志铭》。
{11} 《石田杂记》卷1。
{12} 《作邑自箴》卷5《规矩》。
{13}{15}{16}{17}{19}{30}{31}{34}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200、200、200、200、205、205、210页。
{14}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1页。
{18} 本文中利息均为月利息。
{20} 张中秋:《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21} 《通制条格校注》卷28《杂令违例取息》。
{22} 《论语集释》。
{23} 《汉书·宣帝纪第八》。
{24} 《文献通考》卷172《刑考十一·赦宥》。
{25} 《續资治通鉴长编》卷7《太祖乾德四年》。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哲宗元佑元年》。
{27} 《文苑英华》卷422《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
{28}{29} [宋]窦仪:《宋刑统》卷26,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4、618页。
{32} 《茶香室杂钞》卷6。
{33} 《潜研堂文集》卷45。
作者简介:武航宇,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辽宁沈阳,110034。
(责任编辑 李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