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日子里
2019-09-10靳育德
靳育德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结束后,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胜利的快乐,三年内战又开始了。马步芳为了维护其家族利益和保住所割据的地盘,卖力地追随蒋介石,疯狂扩充兵力,顽固地站到了反共的第一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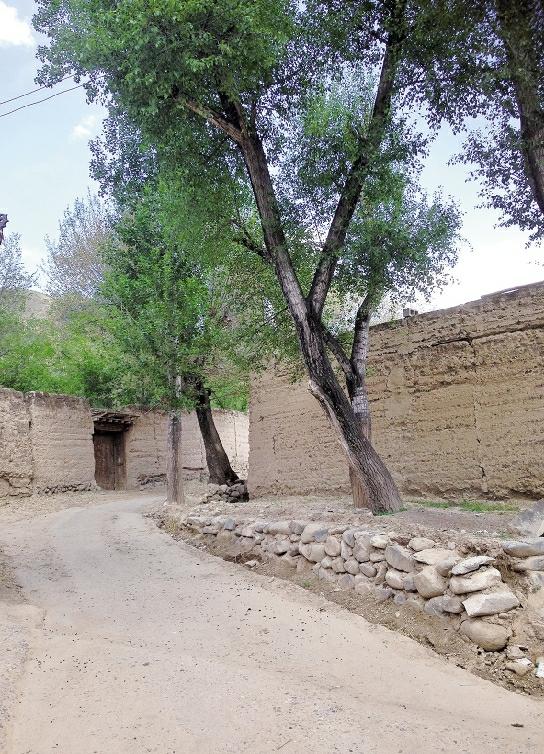
那时,我家是一个有20多口人的大家庭,当了一辈子私塾教师、年近70的曾祖父和曾祖母操心着家中的事情。三个爷爷和伯父是大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带领着几个裹了脚的奶奶,成天在村后山坳和村前沙滩里务劳着那几十亩贫瘠的旱地,以填饱全家人的肚子。1947年的某一天,就在这平淡得没有一点儿味道的日子里,村上的保长按照县“衙门”里的命令,传达了这次拔兵的名额,“两丁抽一,三丁或四丁抽二”,摊派的兵员还要自带马匹、鞋袜,并限定准备时间为10天,届时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前往西宁乐家湾军营进行训练。我的老家是一个不到200口人的小山村,竟被分摊了近10个名额,其中我家被摊派了两名。这些年里已经拔过几次兵了,10年前拔壮丁,“衙门”里组织的“湟中民团”赴河西打“共产”,村上有人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这次保长又来摊派兵额,真像晴天里的一声霹雳,摊上壮丁名额的家里顿时乱了套。本来笑声就不多的我家,大人们脸上都挂着阴云,曾祖母和奶奶们的房里不时传出的是哭声。爷爷是家中老大,刚年过50,是家里干庄稼活的主力,血气方刚的伯父“替父从军”,站出来顶了一个名额。可是家中还得再出一个人。二爷爷无子嗣,曾祖父不忍心让他去,那就得三爷爷去了。三爷爷是曾祖母的“奶干兒”,怎么也舍不得让他去,盘算来盘算去,三奶奶于是想到了她娘家的小弟弟。她的娘家在山后的羊圈村,家境很不好,经商量,愿意顶替我家的兵额,那时一个兵额的价格为500块银元,于是曾祖父忍痛将家里最好的一块名为“碱滩大地”的土地典给了塔尔寺,凑够了500块白圆(银元),雇了三爷爷的小舅子,顶了一个名额。两个拔兵名额有着落了,还要两匹必需自带的马。那时,家里为了干田间农活,养有一匹马和一头骡子,还有两头牛,马值钱,牛、骡较便宜,只得又以牛和骡子换了一匹马,一家人在哭天抹泪中送走了他们。隔壁的“房后头”家也出钱雇了远在西纳川的党家子宗祖大大的弟弟,顶了他家的兵额。
伯父他们到乐家湾军营后,被编入马家军整编100师,听说师长是谭呈祥。经过短暂的训练,被送往今民和享堂驻防,不放心的曾祖父曾让三爷爷专门到城里,坐汽车到享堂看望了伯父和他的小舅子。后来,听说伯父他们的部队开拔去了陇东,在西峰镇、固关一带打仗。据那时的《民国青海日报》说,马家军在前线上天天“打胜仗”,有一天城里还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祝捷大会,但人们还是在忐忑不安中过着惶恐的日子。
父亲在西宁中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马步芳办的干部训练团参加技术培训,学的是测量专业,速成班培训后就跟着技术人员到乐都大峡测量水渠。测量工作完成后,又奉命沿着日月山、恰卜恰、都兰、巴隆、宗加、诺木洪一线,测量将要开建的青新公路路线,在茫茫草原、干旱的沙漠里,顶风雨,冒严寒,吃了不少苦。据说后来领薪水时,竟领上了像“菜瓜”枕头大的一墩“法币”,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曾祖父曾抚摸着那墩整齐的钱捆,在来家串亲戚的占朝阿爷面前炫耀,称赞这个孙子有出息。但很快那些舍不得花的“法币”却贬了值,最后竟被当作花纸糊了墙。1949年8月,正当测量工作进行之际,测量队突然又接到上级命令,工作立即停止,人员全部被征调编入马步芳后勤部队,父亲被调入新编骑兵军一旅二团当军需,立即到河州征粮。曾祖父听到家里惟一成人的孙子又被“拔了兵”,欲哭无泪,只得成天夹着香匣子,爬上高高的东山顶,到山神庙里去敬香,祈求冥冥之中的山神爷保佑两个“吃粮人”(过去,人们把当兵的称作“吃粮人”)能够囫囵身子回来。我奶奶眼看着两个儿子全被抓了兵,哭红了眼睛,晚上跪在炕头上,双手合十,一遍遍地祷告着“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

一天,突然“房后头”家的大门上人声鼎沸,只见混乱的人群中宗祖大大赤裸着上身,手攥石块,欲和“房后头”家拼命,他的父亲瑞安阿爷也脱了汗渍斑斑的破汗褟,哭喊着要以头撞“房后头”家的大门。“房后头”家大门紧闭,任凭门外喊声震天,大气也不敢出,没有一个人敢开门出来,巷道里劝说的、叹息的、看热闹的乱成一团。原来是宗祖大大的弟弟顶着“房后头”家的名额当了兵后,再也没有活着回来,把身子撂在了千里之外的陇东。当初只说是顶个拔兵的名额,谁知连命也搭上了!后经人劝解说和,“房后头”家在庄廓边的好地里给宗祖大大家打了一副庄廓,盖了一溜七间房子,并给了他们一两块地,让他们从西纳川搬回来住,才算解决了一条人命的风波。村上更安阿爷的大儿子“尕起娃”也折在战场上了,撂下了过门不久的媳妇;左右邻堡死的也不少,村村有哭声。
伯父虽然身子囫囵地回来了,但落下了使他痛苦一辈子的枪伤。那一段时间里,他整天躺在炕上,没白天、没黑夜地哭喊“疼死了!疼死了!”后来隐隐约约听大人们说,他在陇东打仗时右臂负了伤,被人从阵地上拖了下来,经过简单包扎,和其他伤员一起,用卡车一路颠簸拉回了兰州,住进了马家军的医院里,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嵌在肱骨里的子弹却没有取出来。起初,从前线上九死一生回来的伤员们以为自己是火线负伤,居功自傲,还对医护人员呵斥指责,但随着马家军节节败退,医院里塞满了伤病员,缺医少药,多数伤兵得不到一点基本救治,医护人员又成了他们的救命菩萨,每天从后门里抬出的多是血迹模糊的尸体。伯父创口虽然一直发炎化脓,但还是留下了一条命,兰州解放前夕,幸运地被拉回了西宁。那时,风雨飘摇中的马家政权已岌岌可危,无人过问这些战场上卖过命的伤员,伯父只得托人捎话,让家里人用马车拉回了家。那时候,农村人生病,多是用民间土方法治疗,再就是求神问卦,有人说,如果把活鸽子胸腔打开敷在伤口上,止痛又治伤,于是热心的庄舍尕四爸等半夜三更到下院楼上抓鸽子,但敷上后并未止痛,叫喊声依旧。伯父的创口一直溃烂,几年后弹头才从创口里掉出来,愈合后留下了一个鸡蛋大、微凹的创疤,干活时右臂使不上劲,背地里人们叫他“折胳膊儿”。
恍恍惚惚记得,那是一个晴热天的下午,爷爷们都下地干活了,里院土楦门外突然传来了“阿爷,阿爷!”的叫声,曾祖父应声从南房里急忙走出来,只见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的父亲跌跌撞撞地迈进土楦门,曾祖父见状来不及走过东房台地,直接抬脚下到院坑,和扑上前来的父亲抱在一起,在院坑里放声大哭。“人有金山在”,第二天,曾祖父专门到下院供《家谱》的供桌前点灯上香又磕头,之后又爬上高高的山神岭敬香,以感谢冥冥之中的神灵和祖宗护佑之恩。

后来听说,父亲从公路测量队被强征到马家军后勤部队后,被委任为上尉军需官,分配到河州各乡去强征军粮。征集到的军粮由各乡保长负责运至黄河边,用当地借助水力磨面的“当当磨”加工成面粉,再用汽车运往前线。由于前线“仗口”吃紧,催粮的命令一日几催,他整日骑马奔波到各乡去催保甲长。他在河州的20多天里,一个和他刚混熟的保长悄悄地给他说:“这几天河边的几个庄子里都来了共产党的便衣,老百姓大家都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还到处催粮,你可要小心啊!”父亲听后后背直冒冷汗,才惊觉这几天路上就是突然有了许多“呼郎子”(即手摇拨浪鼓的货郎),他们走村串户卖针头线脑,好像并不在乎生意的好坏,或许他们就是共产党的便衣。他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一夜,没等到天亮,就撇下手头材料,悄悄地骑马上路,朝青海方向奔去。天明后当他路过一条河边时,就远远看见河那边有一行像部队一样的人马在行进,情急之下,他匆忙扔掉军服,策马沿山间小道逃命。晌午后,来到一个荒凉的山村,村边是一片杏树林,因战乱风声紧,村民早已藏匿山间,空旷的巷道里不见人影,又累又饿的他只得钻进杏树林,以杏子充饥。晚上又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里,敲门进了一个人家。落脚的房主人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知道父亲的来由后,尽其所有,热情地招待了父亲,这时的他除了那匹屁股上烙有号码的军马以外,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硬是将马留给了那对老夫妇,带着几个杂面馍继续向西方奔去。现在回想,当年父亲返家路径,估计是沿着黄河边进入循化,再过化隆翻青沙山,经平安来到湟中的。只不过一路走的是山野小道,绕来绕去才回到家的。
伯父和父亲都回来了,三爷爷的小舅子也幸运地囫囵身子回来了,尽管伯父负了伤,全家还是很庆幸。可是没安静几天,就传说东西邻堡有钱汉家被土匪抢劫了,说那些土匪一个个骑马带枪,行踪飘忽不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来到我们庄子里,所以人心惶惶,寝不安席,都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一天傍晚,突然有人在门前的东坡儿上大喊:“快跑啊,土匪来了!”女人们急忙拽着自己的娃娃奔出门,踉踉跄跄地朝碱滩豁口跑去。豁口那边是几块庄稼地,再前行就是村后大山。恍惚记得妈妈拉着我刚迈过豁口没跑几步,暮色苍茫中只見十多个骑马的人冲进了豁口,避难的人们霎时像羊圈里冲进了狼一样,丧魂失魄地立即朝两旁躲避,但他们却马不停蹄地朝沟脑奔去,黑影里还闪烁着刀枪上金属的寒光,其中有人还说了一句:“这些庄稼人也孽障啊!”村后的沟脑是个封闭的山沟,不知那晚他们去了哪里?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来未曾忘记,他们也许就是在兰州战役中溃散,逃回青海的马家军的散兵游勇吧?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家里人一夜数惊,晚上都不敢脱衣睡觉,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匆忙往后山里避难。我清楚地记得,避难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大沟红土阳坡上一个像洞不像洞的土窝里,一处是隆益湾梁梁上一个长长的土洞里。每次我们避难时,曾祖父和曾祖母都会留在家里,坐在土炕上念佛。爷爷们不放心,都劝他们也出去躲一躲,曾祖父却说:“我们的耳门背后铁铣响了,黄土快埋到脖子里的人了,还害怕啥哩,你们去吧!”

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人通知村上的大人们到邻村大庙里去开会,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村委会,原来的保长和甲长的“官儿”都被撤了,说是“解放了!”开会回来的爷爷们把这些新鲜的事儿兴冲冲地说给曾祖父,曾祖父却说“朝代变了”。但不管怎么说,担惊受怕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又过了些日子,村庙里办起了夜校,因为村上绝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要求庄子里男男女女都来识字,而且还要“跳秧歌”。父亲不但当上了村委会的主任,还承担了村夜校里扫盲的任务。再后来,县上民政科通知父亲,让他到西宁省民政厅报到,最后被分配到市城建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