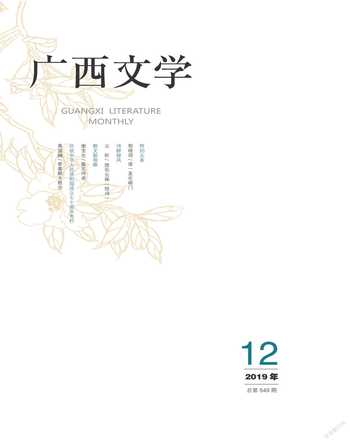匿名诗者
2019-09-10谢宝光

一切存在都在威胁我,从最小的飞虻到道成肉身之谜。
——[丹麦]克尔凯郭尔
最终,我的笔尖还是没能绕开一月。
不爱说话的未成名诗人一月。
他长了一张欲言又止的嘴巴。听他说话,你不能急,要拿出吃热茶的工夫,抿一口,再涼一凉。他的很多话都是断头桥,说着说着,没了。没了也就没了,别指望他嘴里多蹦出一个字。
我不会忘记他跟我说过的第一句话,那是十二年前,我们还在鄱阳湖边的一所大学读书。住的是6栋740宿舍,里一间外一间,挤着六人,都非庸常之辈。天南海北的少年拼出一个人文艺术系,肤色秉性、看家本领各不相同,人人都在暗中搜寻趣味相投者。有一次,我从寝室厕所出来,正猫腰系着鞋带,额头前冷不防冒出一人,冲我说了句:“宝光,我做了个决定,以后你去哪,我就跟你到哪。”
说这句话的人正是一月,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十二年后对他的所有记忆是以这句话为起点的。在那之前,我们已经相识了两个月,但是很抱歉,关于那段日子里的一月,我的印象比糨糊还糊。幸好有了这句话,它一下子就从乌泱泱的人群中帮我点出了一月的存在——大概一米六八的个子,有点瓜子脸,不太分明的鹰钩鼻,头发油腻腻的,一脸不知何来的忧郁,因为瘦而骨骼清奇,两袖生风;他爱穿七分裤,那几年我侧身躺在下铺时,眼前经常晃动着两条毛茸茸的瘦腿,他睡我斜上铺,每次腿一蹬就上去了,铁架床一阵嘎嘎响。
一月有点自卑,我想这可能和他的身高有着几厘米的关系。可是他的弹跳力极好,有豹跃之势,在篮球场上呼呼生风,投篮也准,抢篮板起码不输一米七五的我。下了球场,就不起眼了,和他的名字一样,势单力薄,泯然众生。他在校园里不声不响地走着,眼眉低垂,醒着时也像睡着了,瞳孔里好像蓄着一层雾,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肯定是当你以为他睡着时想到了什么,那么突然的一下蹿到你面前,神灵附体似的说了句让你不明所以的话。然后你才蓦地发现,哦,有这么个人,在同居了两个多月的那块屋顶下。哦,他还写诗。哦,难怪他话那么少,原来是和诗通宵幽会去了。
后来,我们还真走到了一块。可能就是第二天,在去图书馆或者实验楼的路上,当然不是他跟着我,而是并肩走着,因为文学的缘故,我们在好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同志一样齐整的步伐。他写诗,我写散文。这很好。谁也不抢谁的饭碗。虽然有几年,他拉开了架势,往散文、小说的领地不时张望,我也因为恋爱而一度误入诗歌的沼泽地。
我写字有个恶习,就是磨蹭,孕妇分娩一样,伴随着拉锯式的痛苦,枯坐一整天也写不了几段;一月不同,他的写作可以用疾风骤雨来形容,数步成诗,一日百行,有时连标点都赶不上他的灵感。那时,我怀疑他的脑袋就是一口诗的源泉,需要的时候,拧开盖子,往纸上倒一倒就是了。比如有天晚上他在寝室和蚊子进行一番搏斗后,五分钟一挥而就的《蚊帐》:
我鲜红的血液
从头顶倾泻而下的蚊帐下
自由如窗前飞鸟
洁白如洗的蚊帐像一顶帐篷
一副等待结局的棺木
我成了这容器的晚餐
所有目的都指向我
我那鲜红的血液
这是他十九岁时的常规一首,虽然破绽明显,但他那时的状态确实让人觉得是上帝在握着他的手写诗。我这么说自然是不客观的,诗情就如他一脸茂盛的忧郁,一半是天赐,一半要归咎于和现实的摩擦。二十不到的年岁,最大的现实是什么?不用说你也知道。
他写“思念是半夜醒来的一只拖鞋”,对于像我这样拥有一觉到天亮的良好睡眠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我的费解更多在于,他可以和一个未曾谋面的姑娘,将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情延绵三年之久。我只知道,让那只拖鞋彻夜失眠的姑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小鱼。她远在昆明,游弋在南方以南漫漶着栀子花香的空气中,谁也没有见过,姓甚名谁也无人知晓,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谜一样的存在。有关她的所有线索都在宿舍隔壁墙上的一台公用电话机上,那只听筒每天晚上都被一月的耳朵捂得发烫,几乎要在两个灵魂长达数小时的依偎中融化掉;寝室门是敞开的,或者半掩,为此通话时他尽可能降低分贝,传到我们耳边时,已是一团黏土一样质地湿沉的声音,提炼不出任何一个有效的词汇。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小鱼的夜话融入了我们的夜晚,成了740宿舍集体梦境的一部分。
几年后,小鱼彻底从一月的世界里消失了。那只听筒也被遗弃了,静静地悬在走廊的墙上,像个失聪的耳朵,残留着一丝无法褪去的余温。
现在想想,我和一月并肩行走的时光其实很短暂,也就几个月时间,基本集中在他的爱情遇冷,而我又尚未遭遇情感之前。记得2007年平安夜前的一天晚上,我和一月头脑一热,去北门街边买了一包一块五的庐山烟。我们之前都不抽烟,那天是头一遭,说不清理由,似乎是烟莫名其妙地找到了我们的嘴巴。然后我们莫名其妙地乱走,转过一个十字路口,踩着落满黑色小樟果的水泥马路往郊外走,那是条通往共青城火车站的荒凉大道,两边没有房子和灯火,连狗都碰不到一条。狡黠的风从衣领、鼻口往里灌,但不觉得冷,肺部有香烟带来的川流不息的热度。我们说话,说到我可能萌芽的爱情,或者不说,就这样一直走,不时瞟一眼两边光秃的稻田,让一支烟在指尖闪烁着奔向死亡,一切都淹没在黑黢黢的夜中,只有唯一的星辰,从亿万光年外对着地球上两颗漆黑的头颅射出惺惺相惜的微光。
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我们置身其中,怀揣和马路一样苍白的心情,向路消失的地方眺望着未来的某个日子。
不知为何,十二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和一月有关的经历时,首先冒出来的就是那个夜晚,顺着那条荒凉的马路,我和当年自己眺望的目光迎面相撞。我相信那个夜晚也一定烙在一月心里。写这篇文章前,我特意去逛了逛一月的空间,兴许有着蛛丝马迹,逆着那么久远的时光一页页往上翻,果然我看到了,是一首诗,不会是别的。写感觉,如用手抓水,《总在苍凉的夜色中走得更远》,我觉得它办到了——
总在苍凉的夜色中走得更远
很远的不着边际的远
那个时候手指夹缝里的烟头火光闪烁
星子微微放亮 言语如水声流淌
我们的路四面八方充满每个清晰的角落
眼光明亮如同水藻疯狂生长满怀希望
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们都到达了
我们的路不知道如何收尾才不辜负当初的美
是中了蛊吗?那时候,除了爱情,我们那么迷恋苍凉和远。
还有一次,我们在校门口租了两辆自行车,用轮子代替了腿,以便走得更远。有多远呢?几乎是两个轮子在一天内可以翻滚出的极限距离。终点是六十公里开外,一座位于庐山南麓密林中的书院,叫白鹿洞。关于它,我们一无所知,纯粹是出于这个名字的天然指引。抵达是那么吃力,没有导航,凭着一本旧地图的微弱指示,我们在鄱阳湖西岸的广袤平原上穿针引线了整个上午,从西南往西北方向吱吱呀呀地摇晃,坚硬的土路硌得屁股一颤一颤地生疼,肥茂妖娆的芦苇林和灰蒙蒙的村庄将两个人吞噬又吐出。不记得一路上经过了多少次盲目的分岔,后来是一块掉漆的朱红牌坊在头顶提示,白鹿洞到了。
抱歉,和书院无关,我想说的其实是返程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拐上国道后,没骑多远,就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向着天际铺展而去。来时是下坡,轮子畅快奔袭,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当方向调转过来,它便陡然地立起来了,似乎在以強势的口吻命令我们乖乖地从车上下来。正要下车推行,这时看见一人,和我们年纪相仿,也弓身在一辆单车上,两只肩膀很有节奏地一耸一落,汗湿的衬衫牢牢地粘住了他的后背,很明显,他是要挑战那道长坡。了无尽头的国道线上,只有马达偶尔的咆哮声,一路都没碰到骑行者,他是唯一的一个,我们怎么可能放过?不觉中,他就成了两个陌生人的目标。我和一月暗自达成了默契,右脚轻踮一下就跨上了车,那道坡很快就成了三个人的赛道,没有裁判,没有观众,更重要的是,没有终点。在陌生的旅途中,两队互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为对手,且如此心照不宣地绷红着脸,加速着轮胎的疯狂旋转。经过几个回合的相互赶超,那个没能看清长相的人,终于被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那是我和一月唯一的一次骑车漫游,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光了。
小鱼消失之后,一月依然在写诗,并且更加疯狂,他简直把诗发展成了对自己的一种语言暴力,或者说精神刑罚,总是有那么一股阴郁之气游走其间,像满天的云翳,任风肆虐也扫不净。看看他写的《被一道彩虹逼上绝路》里面都用了什么词吧,“瞎子”“拐杖”“孤独”“坟墓”“饥饿”“蝼蚁之穴”……那几年的一月,心境恶劣到了极点,似乎只有借助这些词,他才能活下去。
这些,仍不能够。
为了不至于死,他得借助更多,烫头、穿耳洞、打CF……可他不抽烟,和我不同,他始终没有学会和烟做朋友,否则他就不至于如此孤独,也不至于愤而退学。在大二那年,他忽然决定不读书了,拎个包就奔向了火车站,谁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干什么。他憋着一股气,他被那股气拧成一团乱麻,如果不离开,如果没有一道决绝的仪式点化,那几乎是致命的。“想起写青海湖的诗人已死/天远在远方/来路不见去路”,那时他的诗里尽是海子的影子,那个殉道者就像病毒一样牢牢盘踞在他的体内,远方、死亡、空空……海子真是一个很不好的榜样。但他的出走与海子无关,严格地说,也与小鱼无关,他的敌人始终是他自己,像卡夫卡说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而那些诗,就是他与那一切障碍一次次搏斗后留下的血迹。
一月的出走显然不够彻底,没几个月,他就回来了,抖落一身的尘土,不声不响地爬回了他的上铺。回来的一月比以往更热衷于睡眠,谁也休想打搅,否则少不了被他一顿臭骂。他常常引用《圣经》里的那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把自己弄成一副高高挂起的样子。他开始孤绝于寝室,孤绝于我,两年多,我们都没有说过像样的几句话。之前就不多,之后就将更少。有时碰面,他连睫毛都懒得抬一下。没有任何提示,我和一月就走散了。后来他干脆搬离了740,似乎为了将这种孤绝进行得更彻底。后来,我有点理解了,出走显然不是孤绝的最佳方式,好比把石子扔进一个无底洞,溅不起任何回响;只有回来,回到熟悉的人群中,只有在起伏的喧嚷中,他的孤绝才能找到最柔韧的跳板。
那几年,我和一月唯一雷同且持续的是,我们都用写的方式来说。我们都渴望从无人知晓的黑暗中杀出一条康庄大道来。我们暗自较劲,看谁能拿下更多的报刊版面。我们笃定,蚁鼠横行的740宿舍会是另一个被世人传诵和铭记的尚义街六号。记得有个冬天的周末,大家正窝在床上看着电视,他突然猛地一下从上铺蹿下来,跳到凳子上,把墙上的电视机挡住了。我们以为他是被老鼠赶出了被窝,可他脸上写着的分明又不是惊吓。只见他提了提衣领,像希特勒发表演说前一样鼓足了气,然后冲我们挥举着手臂,喊着老子将来一定要拿下茅盾文学奖!是的,我没有听错,他说的不是鲁奖,他一个诗人居然要和写小说的抢奖杯。我看见他腮部的肌肉随着嘴角的一开一合欢快跳动着,那么自信、活络而有力量。不仅如此,他还在日记里进一步强调:“我总是说要留名文学史。我真的觉得自己说不定就上去了,像爬凳子一样。”为了名正言顺地爬上去,一月真写起了小说,有几个月,他在纸上秘密地建造一条街,工匠一般,每天乐此不疲地在那条街上种树、盖瓦,街上的人和他一样,过着一种破绽百出、难以愈合的生活。他把这条街命名为平安街。这条不安的属于他的灵魂街道,蔓延到了两万字的长度,后来终于无疾而终。
因为孤绝,一月越来越活成了一个传说。
那几年,我忙着恋爱和旅行,没有怎么关注他。有关他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来的,真假莫辨。据说有一年开学返校,他从莲花县城转道萍乡乘火车,山路崎岖,中巴车摇摇晃晃,把一车人都晃进了梦乡。只有一月无聊地醒着。他的座位挨着过道,要往窗外看风景则必须越过身边那人的头顶,可当他的视线正将翻越时,却被一张脸绊住了。那当然是一张娇嫩好看的姑娘的侧脸,有着匀称而柔软的弧度,否则也不至于让一束准备滑翔的目光匆匆降落。可是,目光的力度未免太过轻浅,经过一阵踌躇之后,他更进了一步,把嘴唇也往姑娘的脸颊上轻轻落了下去。姑娘熟睡的眼皮瞬间弹开,却不是惊,甚至也不恼,她转过头,上下打量了一下身边的这个陌生人,什么也没说,便合上了眼,继续着她未尽的残梦。——这当然不是故事的结局,戏剧性的东西总在后面,当它通过长途跋涉抵达我耳郭的时候,那个姑娘已经成了一月的第二任女朋友。
谁也没见过那个姑娘,和小鱼一样,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一个谜。或许,那压根就是一月在被窝里虚构的产物,就像他那几年的诗、冰凉、空幻、抽象、阴鸷,让人越来越费解。可以说,他几乎把日子过成了诗,还是波德莱尔那种。
在我们彼此陌路的几年中,有一天,一月突然找上了我,邀请我参与他某首“魔幻诗”的建设。仍然和一个女生有关。这一次,并非虚构,我见过,她确有其人,一月虚构的只是她作为他的第三任女友身份。样子记不清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女孩年纪足足比他小了八岁,且就在和我们大学同一条街上的中学读初一。现在,女孩遇到了点麻烦,简单说,她受到了某所小学一个六年级男生的频繁骚扰。而且这个骚扰,多少带了点性的朦胧色彩。女孩没有求助老师和家长,而是找到了一月,一月立即找到了我。他冲我挥了挥手,说:“走,咱去给那瓜娃子一点颜色瞧瞧。”然后我一拍屁股就跟着去了——那年月,很多事都这样不明就里且又不由分说。
那天下午,我们去到这座小城东湖边的那所小学,在门口的一棵樟树下徘徊来徘徊去,听久违的小学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说不清是什么心理,在等候男孩放学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的初中校园门口,也曾经徘徊着两个外校的高年级学生,他们个子格外高大,气势汹汹,面目狰狞,手里还紧攥着一把银光闪闪的砍刀。我不敢多看,把頭埋进衣领里匆匆而过。我至今不知道那把砍刀是否落下,或者又落在了谁的身上。想到这里,我的眼皮颤了一下。我看了看一月,他的手里没有砍刀,面目也不狰狞,甚至神情还异常缓和。他站在樟树的阴影里往校门里面似有若无地张望,样子不像是来“寻仇”,更像在等候即将放学的弟弟。而当最后一声下课铃声响起,一群被红领巾束住脖子的小朋友洪水般欢呼着把我们淹没时,我才发现一个巨大而又可笑的破绽——关于男孩的长相、班级和姓名,一月居然都一无所知。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没有再去找那个男孩。也许,一月原本就不打算找到他。找就是全部的意义所在,当两个局外的成年人趾高气扬地介入另两名少年的情感冲突时,一种荒诞的张力产生了,它抵消了一月与现实间的部分紧张关系,使他结构失衡的日常获得了短暂的几许稳定。可是,我知道,和遥远的丹麦的那个叫克尔凯郭尔的忧郁青年一样,一月终究摆脱不了对自我的悲剧性认识,那是一种比真正的忧郁症更棘手的处境,它源于内部神经或者心灵的某种错乱,连诗也已经丧失了疗效。最极致的那段时间,一阵风,甚至一只蚂蚁,都可能将他粉碎。他哪里都去不了,只能退守在被窝里,将肉身在天地间缩到最小。他在纸上写道:“白屋子里的一月神情疲惫,躺在棺木上呼呼大睡,窗外美好生活打马溜过。”一月是他的笔名,也是他的衍生角色,好几年里,他都把自己整个地装进这个角色,去生发,去淬火,去锻造,去虚拟的诗歌江湖流浪,而肉身则过着一种似是而非、呼呼大睡的生活。相信刘慧萍老师会记得,那两位整个学期都在她的现代汉语课堂上庄周梦蝶的学生,他们像两个纨绔子弟,屈腿并排着躺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从一道铃声睡到另一道,从先秦睡到解放后,他们成功地用对老师的极端蔑视收获了期末两份醒目的红卷。那年,班里唯一挂科的俩人,一个是一月,一个是我。
写到这里,忽然觉得,当我费尽口舌地叙述一月的时候,其实诠释的也是很大一部分的自己。
我们因一部分的共通而走到一起,又因隐秘的分歧而相互走散。
在通往语言的巴别塔的路上,我没有一月走得那样决绝而疯魔。说到底,我始终是一名诗的过客,而他才是匿名的王者。当然,一月从未意识到这点,他只是写,一直写着,并且从来不认为自己写得好。和诗无关,他所有看似轻狂的举动,都源自一种卑微、私人而又天然的教徒式的信仰;他以诗的方式自虐,以触发灵魂的高度收获快感;他一次次用走失和反常规堕落的方式,来寻求并确证一个孤独自我的终极存在。
可能,我还是把一月的面孔描摹得过于冷硬了,他其实一点也不吝啬自己的微笑,即便在他因失去小鱼而最混沌不堪的日子里,他脸上也时常出现蓬勃的景象,哪怕只是虚假繁荣,也意味着某种和解的努力,和自己,和世界。即便这个叫一月的虚拟角色一次次怂恿他,他也从未尝试一次走向外在形式的极端;而这条路,我走过,我的室友那宾也走过。是在大三的一天下午,没课,我在寝室看书,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那宾发来的。那条短信很长,语气很复杂,但归纳起来,只有三个字,那就是——“永别了!”那宾睡我边上,我往他的床铺瞥了一眼,没人,被子是散乱的,一包没抽完的白沙烟还在枕头上咧着口子。他很可能在楼顶!我大喊一声,上楼!室友们倾巢而动,上到天台,找了一圈却没发现那宾的踪影。我冲到天台边缘,趴在栏杆上,往楼底下望去,没有,没有,没有血!前、后,左、右,水泥地一片白!
后来我才知道,那宾在给我发完人生最后一条短信后,临时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他是班长,怎能不去?就这样,一次临时会议把他从死神手边拽了回来。
多年后,我读到朋友写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长大是一件危险的事》。
我们曾经如此如履薄冰。
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一月的人生轨迹再没有了任何的交集,但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复苏了联系。我们像两个断交多年的国家,因为毕业这一历史性事件,莫名其妙地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径直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三天一闲聊,十天一长谈。
聊什么呢?和诗有关或无关的一切都聊,他和我聊他在武功山新结交的女朋友,聊女友在莲花某乡镇卫生院作为护士的琐碎日常,聊他们之间可能的命运走向,聊他们的一次次分手又复合后的悲戚相拥,聊她半夜趁他睡着时偷看我们的聊天记录,然后因为他毁其形象的措辞而大发雷霆……我呢,和他聊我在南昌上海北路的蜗居生活,聊我即将荣升父亲并步入婚姻的懵懂与惊喜,聊我剃须断发出征天堂杭州却沦落在运河边一家莆田系不孕不育医院做最低级的码字工,聊我后来相继被三家公司辞退并连续八个月找不到工作靠妻子的微薄工资度日,聊我带着一家三口在杭州的一次次可能了无止境的迁徙……
在聊天的过程中,一月的职业和我一样,发生着各种始料未及的切换。他从莲花县电视台的记者,到某政府部门的外聘职工,到某工程建设公司的文案编辑,到某单位的秘书。现在,他居然混成了一个性格分析师!他循循善诱地领我走出关于催眠的认知误区,又给我发来一个关于夫妻情感的调查问卷,我在手机前给了他一个白眼,说:“饶了我吧,要得罪老婆的。”
就这样,我们聊了整整八年,把除那宾、吴林军和我妻子之外的大部分同班同学,都聊到了杳无音信、记忆模糊的地步。
八年间,我们见过两次,都在杭州,一次是他专程来看我,一次是公干。第一次是在2016年夏天。那年仲夏的杭城,热得可以在马路上煮鸡蛋。他背着双肩包混迹在火车站甬道的人流里,阳光一笔一笔把他五年后的样子勾画出来,几乎没什么变化,还是一头油油的头发,黑金子一样闪闪发亮。我们互相骂了一句他妈的,以示故人重逢的喜悦和祝福。他说:“我要结婚了。”我说恭喜,也该结了。然后借给他一万块钱,但第二年开春的婚礼因故没去参加。他第二次来,是两年后的冬天,我在西湖边转了半天,才在梧桐掩映的一栋民居里找到他。脸上没有了两年前的血色,他看起来和一碗寡淡的稀粥一样。他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时,语气像在谈论天气。我没法透露得更具体,我只能说,这场变故对他的影响,类似于一条觅食中的鱼突然被银钩拽上了岸。
活在岸上的一月从此不再在诗里关注自己,转而关心起了整个人类。都有谁呢?他们是打锡艺人、拾荒者、女患者、快递员、擦鞋匠、修鞋匠、泥水匠、理发师、母亲、父亲、祖父、断臂者、猎人、不抽烟的老妇人、在轮椅上行走的人、中年男人、甲亢患者、鼠人,还有毛志、潘总、周承志、严文华……在这一系列名单中,唯独没有他自己。
2019年,三十岁的一月终于要出版他的个人第一部诗集,书名叫《恍若星辰,恍若尘埃》。
我知道,还未成名的关心人类的一月最终指向的仍是他自己,那个卑微、低频、匿名而又无限辽阔的自己——
他们已经跑不动了
连起身的动作也无法完成
出租房后面的墓地
已被生活剧终
我在高速路上奔向他们
三分之一的路程远在脑后
其实我想慢下来,和身边的爱人
沙滩漫步,到无人知晓的地方
将人生的需求降到最低
世俗標准统统绝弃
呵,但我明白
整整一生,我都会在胸前
烙上乞丐的标签
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行乞
责任编辑 韦 露
→ 谢宝光 1990年生,江西南康人。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