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人性”的温度
2019-09-10鲁雅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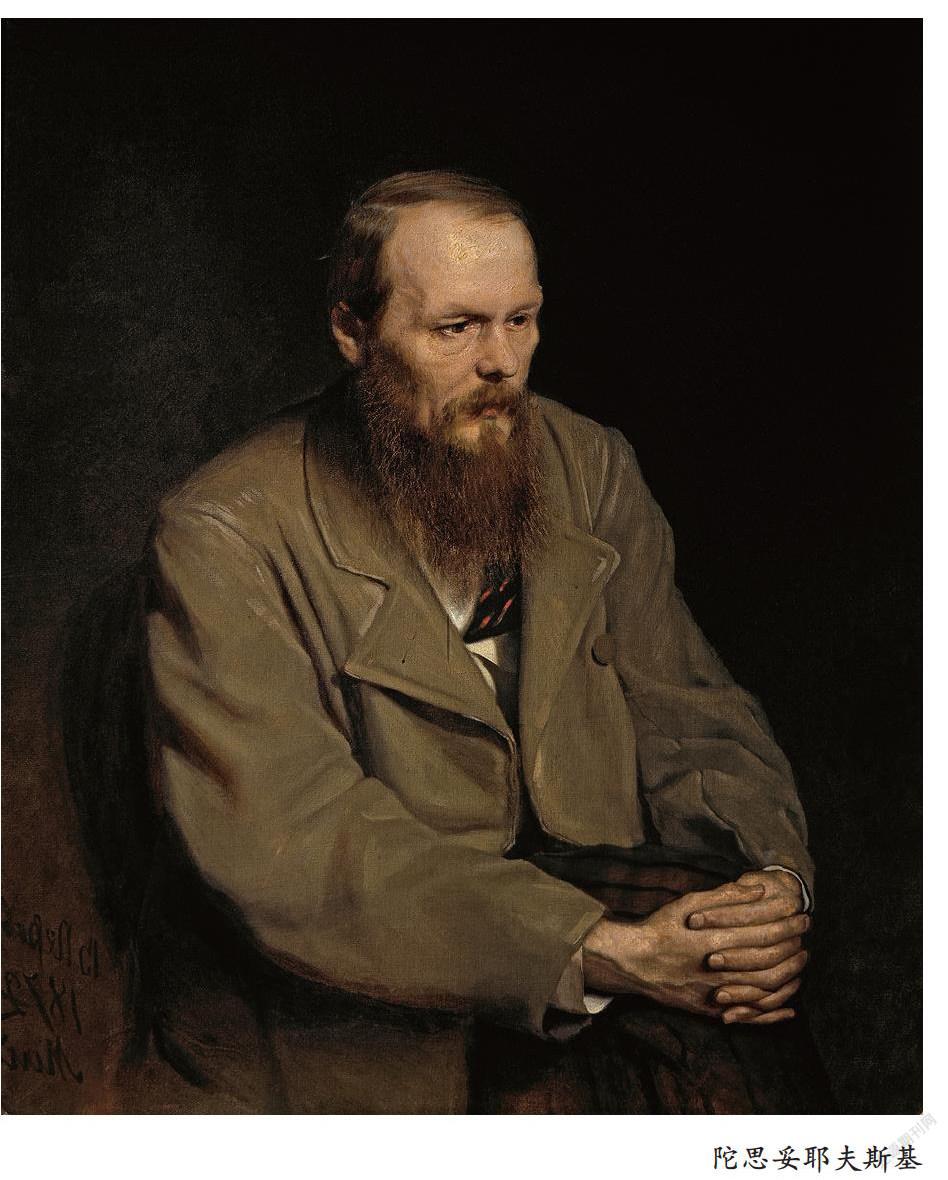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探讨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不同于其他作家大多描写小人物悲惨处境,或是表现其精神世界的丰富、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所有人都感兴趣,不论庸人还是天才,在他的笔下都散发着光芒。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撕裂事物表象的平静冷酷,他的作品包含着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显露出的人性更柔软、更有温度。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白痴;人性;魔鬼;小人物;生命
“人”是所有伟大作家共同关注的主题。从文艺复兴开始,超验的、神的存在领域被打破,人开始走进自己的精神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探讨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在他的创作作品中,直接以人名命名的非常多,例如《少年》《地下室人》《白痴》《穷人》等,足见“人”占据了他写作的中心地位,这些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在不同时空中展开精神的对话。穿透陀思妥耶夫斯基字里行間弥漫的“冷峻”,能看出作家借助人的内心碰撞,自觉剖析人性,迫使人物的灵魂出场,探索人精神深处的自我,从而表达对人本质的肯定。
一、人性的辩证法:魔鬼和上帝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要以完全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1]丰富多样、错综复杂的人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触下完全袒露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的探索,发现罪恶的产生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相应的社会、制度、体制。罪恶的根源正是人性本身。“人们在取得高度发展之后,试图超越人的正常标准。人越彻底了解生活,就越迅速接近暂时的现有存在的界限并力求达到另一种状态。而魔鬼状态就是其中之一。”[2]178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基督教中找到了魔鬼存在的根据,说出了存在有个人的魔鬼,并在小说《群魔》中写了有关哈达拉赶走群魔的引文。为了探索人性之谜,陀思妥耶夫斯基选取了各色各样的人去挖掘深藏在人心中的魔鬼和上帝。别尔嘉耶夫称他“在人的深处裂开一道深渊,在那里重新发现上帝和魔鬼、天堂和地狱”[3]。
在小说《罪与罚》中,自由意志和权力意志是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心中的魔鬼,他的精神被狭隘的“超人”意识所奴役,从而杀了女房东阿廖娜·伊万诺夫娜和她的妹妹莉扎薇塔。在《罪与罚》的开头,大量的梦境放大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内心世界,将他对世界不公的控诉一一披露。在光与暗的交汇点、梦境与现实的接缝处,陀思妥耶夫斯基逐一审视拉斯科利尼科夫心灵的挣扎和潜藏的罪恶。《罪与罚》题目中的“罪”一方面在于拉斯科利尼科夫对别人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另一方面是他自身内心的“罪”。这“罪”源于他自身严重的心理失衡与自我冲突。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揭露罪恶的同时,也怀着强烈的怜悯和同情心揭示了人身上的“神性”。即使是在那些堕落的反面人物身上,读者也能看到其蓬勃的生命力。《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因为一张三万卢布的借据,娶了他的妻子彼得罗夫娜。这不是一段平等的婚姻,而是以借据为锁链的捆绑式婚姻,斯维德里盖洛夫被牢牢锁住。这段婚姻给斯维德里盖洛夫带来的心理上的空缺, 使他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孤独和愤懑。“当成人的苦难无法忍受,希望破灭或者是自身存在的意义丧失殆尽时,摆脱绝望状况的唯一出路就是到信仰或罪恶中去追寻。”[2]180斯维德里盖洛夫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种丑陋和充满欲望的社会现实,犯罪了可以被妻子从监狱赎出来,社会道德和法律并不能对他有丝毫束缚。受人类低劣本能的诱惑,斯维德里盖洛夫自己亲手释放了内心的恶魔。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性的本质和人被掩盖的深度并不是静止状态,而是内在的,在它的深处是火一般的运动。这火来自于人性的对立。斯维德里盖洛夫一出场,作家就为读者呈现了他的种种恶行。但通过杜尼娅与他人对话可以得知杜尼娅在乡下面对流言蜚语时,斯维德里盖洛夫通过赶走杜尼娅使她脱离人言可畏的环境。面对魔鬼势力,斯维德里盖洛夫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但他终日生活在诱惑中,金钱、妻子和他手中的权利都变成了魔鬼的帮凶。之后,斯维德里盖洛夫想通过重新娶妻的方式杜绝自己对杜尼娅的欲念。但在一系列精神斗争中,魔鬼始终给予他强烈的反击。在与杜尼娅对峙的过程中,斯维德里盖洛夫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有着两极对立的激烈冲突。当杜尼娅的枪口转向她自己时,外在的制约使得斯维德里盖洛夫心中的魔鬼被打压下去:“仿佛有个什么东西一下子从他心上掉下来了,也许这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恐惧。”[4]484在最后给杜尼娅钥匙的时候,斯维德里盖洛夫用一种可怕的声调反复说着“快!快!”,光在黑暗的深渊燃起,他的心灵脱离了魔鬼的压制,从而给了杜尼娅一线生机。
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梦也是上帝和魔鬼厮杀的战场。在创作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人物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设计了梦境来展现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前的精神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梦境的探索始于小说《少年》,他坚信在现实生活中被有意识排斥的内容其实一直存在,就好比埋藏在灵魂里的种子,若受到外界的某种刺激或者振奋,种子必然会缓慢生长甚至发芽。一开始,斯维德里盖洛夫梦到一座美丽的宅院。微风、青草、小鸟和花朵的宅院美得像天堂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写道:“天堂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5]这又何尝不是斯维德里盖洛夫心中期待的天堂呢?在花的中央躺着一个穿白纱衣的少女,那正是被他逼迫到不得不投河自尽的少女。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提到这个少女时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斯维德里盖洛夫此刻被女孩脸上的悲伤震骇到了,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少女受了怎样的折磨。可当他藏在灵魂里的种子正想要发芽的时候,梦境却戛然而止。
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梦境还在继续,他救出了一个受虐待的小女孩,“她的嘴唇张开,微微一笑;嘴角微微抖动,仿佛还在忍着”[4]496。与她的年龄毫不相称的是,“这张完全不像小孩子的脸上露出某种无耻的、挑逗的神情”[4]496。纯洁被情欲摧毁,斯维德里盖洛夫惊恐地从梦中惊醒。与其说这个梦是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自我剖析,不如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他来鞭挞人性的丑陋。在这时,斯维德里盖洛夫才终于意识到位于深渊的魔鬼在凝视他,他未来将会一次次亲手制造悲剧。最终,他选择走上自杀的道路。斯维德里盖洛夫擦去恶的表面,依稀能看到美好的神性,却在自我欲望的恶魔的引诱下,走向了灭亡。而饱受精神煎熬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却被真理的光芒照亮,只需要抱有坚定的意志,“天堂会立即美丽地出现在我们面前”[2]231。通过笔下的人物对世界的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了人自身的本质存在着天堂和魔鬼,至于最终走向哪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感觉、激情、酸甜苦辣、悲喜爱恨以及痛苦煎熬等这些人类所拥有的感情不正代表了人类蓬勃的生命力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在衰败中新生,在苦痛中得到救赎。人的一切都处于矛盾变化中,在思想和内心的张力中辩证发展,这不正代表着作家对于生命本质的洞见吗?
二、底层人物的内在矛盾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具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即使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有着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罪与罚》中,马尔梅拉多夫洞悉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图谋,不仅不加以阻拦,并且还隐隐往图谋实现的路上轻轻地推了一把。马尔梅拉多夫与拉斯科利尼科夫有这样一段对白:“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罪恶。贫穷的时候,您还能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高尚气度。在赤贫的情况下,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做不到。为了赤贫,甚至不是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从人类社会里清扫出去,让他受更大的凌辱。”[4]11马尔梅拉多夫清醒地认识到造成自己一家如此處境的原因是赤贫。赤贫毁了这个家庭:他因为酗酒无法承担起养家的重任,间接迫使女儿索菲亚领了黄色执照。但马尔梅拉多夫也深信苦难能够拯救自己和家人,也许必须经受更多的苦难天国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在他身上,作家向我们展示的是普通的“多数人”,有愧疚、悲伤和信仰,底层人物的愚昧、无知、落后的标签在马尔梅拉多夫的身上消失了。他和拉斯科利尼科夫谈话时表现出的“理性”已然脱离了那个年过半百的落魄官吏的卑微躯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透过马尔梅拉多夫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反问读者:庸人和愚民需要批判和讽刺吗?为何“平凡”的生命就要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呢?生活和命运本身就是矛盾的,人在“时代”的洪流会被淹没,但是“平凡”之人微弱的反抗却会让人从混乱的不可预知的命运中寻求到一个内心受保护的角落,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无比曲折,但是在曲折的过程中,却能感受到一个联结所有生命并且克服“混乱和黑暗”的某种振奋人心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在世界中找到正确的位置并融入进去于自身或世界而言也是一种付出,这样的生命个体难道不值得赞颂吗?
无论是马尔梅拉多夫对自我困境的清晰认知,还是《白痴》里众多小人物对社会各方面的侃侃而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都是“独特并独立的”。在现实生活中,小人物们一般不发表对政治或者时事的看法,他们更多的只关注物质满足。在《白痴》中,拳击手凯勒尔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高贵的大人物们赏光与他交谈几句,他就感到无比幸福和感激。在公爵生病后,却和别人一起质疑公爵继承遗产的资格,亲手写了登载在报刊上的文章想要揭开“公爵的真面目”。但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却用简短的话点出了写社会文章的诀窍。《白痴》中在列别杰夫家里有一场的“学术争论”,别杰夫、巴甫洛维奇、普季岑这群公务员、商人和投机者们从“信贷”谈到“自我保存”,从“铁路谈到饥荒”,从“犯罪”谈论到“文明”。针对社会上的种种议题,每个阶层的人都是长篇大论、旁征博引地进行平等对话。有些人虽然自比老鼠,却极其希望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列别杰夫能看出“自我毁灭法则和自我保存法则在人类身上势均力敌”[6]417。加尼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信贷的缺陷,“人要活、要吃、要喝,这是普遍的需要,而缺乏普遍的合作和利益的兼顾是不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6]416。这些言论无一不体现着小人物丰富的内心,他们从不真的自认为低人一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出自小人物之口的政论,让读者看到了“小人物”内心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意识。伊波利特表面上是一个患有肺痨到处说疯话的小人物,却毫不掩饰自己野心家的真面目。他把卑鄙当成自己的“独特”之处,借刺破别人的内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当公爵一出现,并可以不问背后缘由宽恕这种卑鄙时,他反而愤怒了。公爵的这种宽恕对他而言是“独特性的剥夺”——恰好就是对他自尊心和梦想最沉重的打击。“他那怒不可遏的脸上每一道线条好像都在震颤,都在说话。”[6]332他扯开尖嗓子吼叫:“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个个都恨!但我最恨的是您,您这个假仁假义、口蜜腹剑的小人、白痴、百万富翁慈善家,您比世上所有的人,比世上的一切更恨!”[6]333在外界环境和身体的重压下,伊波利特对尊严的追求更为深刻,当公爵剥夺了他尊严的那刹那,他才会说:“是您把我逼到了这般地步!”[6]333卑鄙的人反而对尊严异常渴望,害怕自己成为“平庸之辈”,这背后不正灌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辨证的思考?
三、结语
从原始社会到信息时代,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自己、谈论人。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代,人工智能必然取代人类职能的呼声甚嚣尘上。人意味着什么?人的生命代表着什么?人是否可以被取代?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杀人后,对着索尼娅呐喊:“我想尽快跨越过去……我杀死的不是人,而是原则?原则嘛,倒是让我给杀了,可是跨越嘛,却没跨越过去,我仍然留在了这边……我只会杀。”[4]266他的挣扎是因为他亲手打破了生而为人的原则。人没有权利去统治谁、改变谁,科学也不足以洞察生命,因为就算掌握科学,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苦痛、沉重甚至死亡也无法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人”的角度去了解自己,进而了解生命,于作品中映射出的人的生命力如此炙热、人性如此纯粹,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温度”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冯增义,徐振亚,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17.
[2]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M].沈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
[4]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非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陈燊,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275.
[6]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鲁雅俊,华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