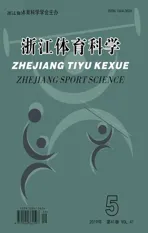课例研究对小学体育教师反思的影响:基于“实践表象”框架的分析
2019-09-05林楠
林 楠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体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1 课例研究的前期概况
1.1课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随着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教师质量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教师培训体系正处于转型期,如何建立更适应教师专业发展、多样化的职后培训体系,是当前我国教师培训面临的重要问题[1]。其中,强调从短期的、脱离情境的教师培训转向提供给教师更多基于情境的、长期的专业学习机会,已成为今后教师专业发展方式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此背景下,课例研究(Lesson Study)作为校本研修的方法与教师专业学习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99年“国际数学与科学学习趋势研究”(TIMSS)参与者Stigler等出版著作《教学差距》,通过对比分析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教学,提示日本教师广泛开展的课例研究(Lesson Study)是日本学生学业成绩表现优秀的根本原因。由此,以美国为中心的课例研究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
概括来说,课例研究是教师以课为载体,对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展开的合作性研究。课例研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形态,但通常由如下重要环节形成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循环:准备-计划-授课-反思-准备……[2]。吉崎静夫关于课例研究的目的有如下阐释[3]:第一,以改善教学为目的;第二,以促进教师专业能力形成为目的;第三,以发展教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为目的。他同时指出,课例研究促进教师发展这一点,在相关研究与实践领域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中外学者对于课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机理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课例研究促进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community)的建立,为教师提供了有效的学习方式。专业学习共同体是基于“实践中的知识”的基本假设,认为教学知识是不断生成的,教师通过共同探讨、有意识的探究、对材料加以质疑和阐释等过程,实现专业的发展[4]。有研究者认为,教师学习的关键机制是能够拥有观察并参与共同体的核心实践机会,当教师拥有观察、讨论和参与共享实践的机会时,他们的学习就得以促进[5]。课例研究促进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形成具体表现在:
首先,课例研究的操作方式,即教师合作设计教学、教师合作观察课堂教学、课后研讨、再一次教师合作设计教学……等等,为教师之间发生更多关于教学实践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了契机;同时,课例研究注重“聚焦于学习者”而非执教教师的教学行为,以及确立共同的反思依据和程序等特征[6],易于教师之间形成平等良好的人际互动,建立合作规范,达成实质化的合作,以促进教师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观念的转变,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
其次,课例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实践”。坂本笃史将作为校本研修的课例研究划分为两个部分(必要时两个部分再加循环):第1部分,某位教师的研究授课被校内其他教师参观的过程;第2部分,校内教师共同对研究授课进行回顾与评价的讨论过程[7]。同时,安桂清指出课例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表现为“过程性的反思”,即教师是在反思第一轮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教学实验,这种舍恩所谓的“框架实验”通过一个教学重塑的迭代过程,有机会发展和检验能够用于理解和改变情境的试探性理论[8]。可见,课例研究的实际展开方式注重教师的反思,是基于经验反思的“实践的理论化”(theory through practice)。
1990年以后,课例研究作为校本研修的方法,在数学、理科等学科的课堂教学改进、以及教师专业成长(包括教师职前培训)方面,被广泛地关注与运用,成果繁荣。然而,实施课例研究的方法与背景具有很大的可变性[9],表明了课例研究这一理想模型在实践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要处理,这对于课例研究的发展和效果具有关键影响,也就是说,课例研究的效能最终体现在它的实施过程中。但目前,关于课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与原因的实证性研究尚显不足。
1.2课例研究促进教师反思的发展
佐藤学将作为“专业”的教师界定为“反思性实践家”(reflective practitioner),而体现“反思性实践家”的核心专业性,就是教师的“反思”(reflection)。
舍恩认为,专家型教师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通过回顾自明的、缄默的“行动中的知识”,进而重新审视新生成的“行动中的知识”,以获得问题的解决[10]。这个“思考”被认为是“行动中的反思”;相对的,在实践之后,回顾“行动中的反思”的“思考”,被称为“关于行动的反思”,专家型教师通过“行动中的反思”和“关于行动的反思”两者的不断往复,使自己的思考框架得以洗练[11]。
鉴于上述舍恩提出的“关于行动的反思”的重要意义,坂本笃史依据Little提出的“实践表象”的概念,对课例研究实施过程中教师的“对行动的反思”进行了探究。
关于“实践表象”解释如下[12]:通常通过语言描述的教学实践,是从教学的具体情况中“脱情境化”(decontextualizing)的。换句话说,由于教学实施所处的背景、状况以及叙述者隐蔽的自身感受等,不能全部由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得倾听者通常仅能获得部分的重要信息。因此,倾听者需要对叙述者所说的“实践表象”进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ing),即必须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与事实相关的信息进行推论及再解释。上述的“实践表象”成为教师思考教学实践的重要资源,即每个教师在讨论会上听取了别人的“脱情境化”的“实践表象”,并在自己的教学体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对这个“实践表象”进行“脱情境化”的理解。进而,每个教师都会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与思考。
坂本笃史依据“实践表象”的概念,以6次日本小学实施的课例研究中教师的发言谈话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确立了用以分析教师谈话的“实践表象”框架,将教师的谈话分为“课的表象”、“推论”、“问题的表象”、“可能性的假设”、“解决方案”以及“其它”,并指出其中的“问题的表象”、“可能性的假设”、“解决方案”相对集中地体现了教师合作性反思的发生过程。
可见,通过“实践表象”框架,能够判断课例研究实施的讨论会中,是否促进了教师发生“关于行动的反思”,这对于了解课例研究影响教师反思与学习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木原成一郎等研究者[7],以日本某小学实施的体育学科课例研究为对象,应用“实践表象”框架,对其中1次体育课教学观摩讨论会中执教者、观摩者、专家指导者的发言谈话进行分析,指出3类参加者在发言谈话数量和具体内容上的异同,并推测讨论会中通过集体性反思的学习过程,给予了执教教师和观摩教师重新思考体育教学的契机,进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学习。然而,木原成一郎等的研究仅限于1次讨论会,对于教师是否获得反思发展的探讨尚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试图在完整的课例研究实施过程中,考察教师反思的变化、以及不同“角色身份”的参与者对促进教师反思发展的影响。

表3 关于“实践表象”的谈话类别的说明
2 研究设计
2.1研究目的
本研究聚焦体育教师在课例研究讨论会中的发言谈话,通过“实践表象”框架分析教师谈话内容和反思内容的特征,考察课例研究中教师反思的变化过程。
2.2研究现场
根据质性研究典型性样本的抽样要求[13],本研究在杭州市拱墅区有意愿参与到本研究的学校中,选取地理位置相对接近市中心、教研组规模适中的普通公立小学A小学,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A校成立课例研究小组,其成员包括A校体育教研组专任体育教师5名(其中W教师为体育教研组组长),以及教育学博士学位、从事体育教师教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B大学教师1名、同时也是本研究的研究者。B大学研究生1名负责每次课例研究实施过程的摄像与录音工作。各成员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在课例研究全部实施完成后,为深入理解本研究的相关研究问题,笔者分别对5位体育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每人访谈时间20~25min。访谈内容包括:①这次课例研究对您有什么帮助?为什么?②这次课例研究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困难或想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表1 A、B课例研究组专任体育教师的基本信息(2016年8月为止)
2.3研究实施过程
按照课例研究的关键步骤在A校进行2轮如下环节,即:①研究组集体研讨并确立主题;②共同制定单元教学计划和教案;③由研究组的1名新任教师执教,其他成员进行课堂观察;④以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集体反思;⑤修改教案,由研究组另1名新任教师执教再次实施教学,其他成员进行观察;⑥以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再次进行集体反思,并总结。A校2轮课例研究的基本实施情况如表2所示。
同时,本研究从“视角”与“时间”两方面对反思讨论进行控制,以确保反思讨论的质量。首先,遵循课例研究侧重关注学生学习表现的特点,课堂教学观察与课后反思讨论均以学生的学习为视角,基于学生的课堂具体表现对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各个方面进行反思讨论。其次,反思讨论的时间控制方面,每次反思讨论均按照从执教教师、观察教师的顺序依次轮流发言、再集中商讨的流程,既保证每位教师意见发表的时间,也确保教师之间充分的意见交流与协商。

表2 课例研究的基本实施情况
2.4研究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研究者收集了A校2轮课例研究实施过程的全部摄像与录音、以及相关教案等材料。其中,将4次授课后集体反思讨论会中、全体成员发言谈话4h37min的音频人工转录为文本,形成32 684字的文稿,并对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对谈话内容本身的编码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教师-时间-事件。首先对6名成员分别以P、S、L、W、Y、N编码区分,并分别用1、2代表第1轮、第2轮课例研究,再将谈话内容以关键事件为准进行顺序编码,最终形成了170则关键事件(第1轮73则、第2轮97则)。例如P-2-3,表示的是P教师在第2轮课例研究反思讨论会中谈话的第3个事件。
3 研究结果
3.1谈话内容的特征分析
3.1.1 教师全体谈话类别的变化特征。根据坂本笃史关于实践表象的谈话类别,对2轮课例研究4次反思讨论会中全体教师的谈话内容进行编码。为了保证编码的信度和效度,由研究者与另外1名研究人员(从事小学体育教师职后培训的相关工作与研究9年,具有教育学硕士学位)以及1名体育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分别对谈话内容进行编码,各自编码结束后,将3者中存在分歧的关键事件筛选出来,共同商议并编码以达成一致。

表4 全体成员2轮课例研究关于实践表象的谈话类别的分类统计
编码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2轮课例研究中,“课的表象”、“问题的表象”、“解决方案”是教师谈话内容的主要构成类别。“课的表象”是教师对教学实际情况的事实陈述、或限于印象与感想层面对教学所进行的评价和判断。相对的,聚焦“问题的表象”和“解决方案”的谈话内容,是基于教学实际情况的进一步思考,促成了执教教师和其他参与教师对自身教学实践的回顾与反思。其次,伴随课例研究的实施,“课的表象”占总体比例下降,“问题的表象”和“解决方案”两者之和占总体比例上升。可见,伴随课例研究的实施,整体上谈话趋向有利于教师合作性反思发生的内容。
课堂观察聚焦学生学习表现,可能是教师讨论中反思性谈话比例提高的重要原因。传统教研形式中,较为常见观课教师以执教教师的教学技能为中心、且依据自身教学实践经验对授课进行课堂观察、以及评价的情况。本研究中,部分以教师的行为活动为主的“课的表象”的发言,反映了这一类观察与讨论的特点。比如:
“S教师这节课的练习密度还是足够的,基本做到了精讲多练……(Y-2-2)”
“最后P老师给学生的总结,是我一直以来上课都容易忽略掉的部分……(S-2-17)”
“S老师这一堂课感觉很流畅,但是我个人最大的感觉是整堂课中S老师缺乏对学生的个别指导。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好像没有一个时间点是针对某一个学生进行指导,而是一直站在前面,做比较整体的一个点评……(P-2-4)”
如上所述“课的表象”的发言,体现出观察者对课堂中教师实施于学生的直接指导行为的关注,这对执教教师反思和提高自身教学技术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观察与讨论,可能会因为同僚之间“碍于面子”不愿意过多评价,造成讨论环节流于形式、反思无法深入等问题[14]。比如,在本研究的教师谈话中,如上述例子中以“某某教师”作为开始的发言,肯定性评价的数量远远大于否定性评价。
相对的,本研究在课例研究的实施过程中,针对教师的课堂观察,强调尽量聚焦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但并未对观察什么、如何观察做出具体的要求。以L教师为例,他在第1轮第1次课后的集体反思讨论中,针对自己观察的小组做出如下反馈:
“……后面我观察了我这一组9个人过障碍时候的表现,前面3个人跑得很好;第4个人过‘树林’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把要求听清楚,也有可能是自己灵敏性不是很好,就往‘树叉’的地方钻过来;那么第5个人呢,他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过所有障碍的时候全部是减慢速度,所以他任务虽然全部完成了,但是速度是很慢的;第6、第7个人很好;第8个人可能觉得这些太简单了,可能本身身体素质很好,所以跑的时候他几乎都没摆臂,也很轻松的都过了;第9个人很好。然后,观察他们在练习时,无论是过障碍的、还是做障碍的学生,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L-1-3)”
L教师聚焦每一位学生学习状态和效果的观察与反馈,促成了讨论中教师关注学生所暴露出的对游戏规则不明确、对障碍跑中要体现协调性、连续性和节奏感等动作要求不清楚的问题(“问题的表象”),进而探讨如何在游戏中确保学生动作质量、提高技术的改善策略(“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聚焦学生学习表现的课堂观察与反馈,才能更多地指向并连结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的问题与解决方法的反思,才能发生课堂观察环节对课后讨论环节的积极影响,促使反思性谈话的发生。
教师也在课堂观察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来自L教师第1轮第2次课的例子:
“……后面我就记录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在分配谁来扮演障碍物时无法确定听谁的,导致后面他们实际练习时间是非常少的,大概只有三分钟左右,也不够系统。然后我这时候就开始走神了,想这么环节怎么办。后面已经开始在小组练习了,但是我始终还在想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弄好……(L-1-8)”
可以看到,尽管L教师在观察中聚焦于学生的表现,但对于如何进行课堂观察,L教师显示出较大的随意性。与其他学科相比,体育学科具有教学空间开放,动作、技能学习表现的一过性等特点,加大了观察学生学习表现的难度。那么,针对体育学科,在建立以学生为焦点进行课堂观察的意识的基础上,不同的观察与记录的操作是否会对课后反思讨论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1.2 不同教师群体谈话类别的变化特征。从2轮课例研究谈话类别的分类统计来看,执教教师占总体比例最高的类别是“课的表象”,且与同僚教师和高校教师相比,“问题的表象”与“解决方案”比例较低,表明执教教师针对教学实施的反思性谈话相对较少。作为执教教师,教学过程中很难兼顾教学实施本身与教学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谈话内容相对偏重于对教学实施情况的单纯描述。另外,两位执教教师均是入职时间不足2年的新任教师,其教学实践经验尚不够丰富,也是本文考虑的原因之一。

表5 不同教师群体2轮课例研究关于实践表象的谈话类别的分类统计〔个数(%)〕
另一方面,2轮课例研究中,执教教师和同僚教师群体均显示出“课的表象”占总体比例下降,“问题的表象”和“解决方案”占总体比例上升,即反思性思考增加的变化趋势;并且,执教教师的谈话个数增长1倍。
但是,促进执教教师和同僚教师反思性思考增加的途径,可能并不相同。访谈中,针对“这次课例研究有什么收获”,P、S两位执教教师都对课例研究的实施过程中与经验相对丰富的同僚教师交流的机会给予了充分肯定。通过课例研究的实施,保证同僚教师和执教教师在准备、设计、授课和反思各阶段充分交流的时间,以及避免指令性的指导、形成合作交流的氛围等,可能是促使同僚教师对P、S两位新任教师产生有效指导、反思性思考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同时,3位同僚教师关于课例研究的收获中,与执教教师相类似的、肯定了同僚之间的充分交流对自身学习、成长的重要性。尽管3位同僚教师在课例研究实施过程中更多地站在向执教教师进行建议、指导的角色上,但借助观察与讨论,提供了同僚教师回顾与审视自身教学实践的契机,促进反思性思考的发展。
另外,同僚教师从不同方面对校外人员N教师作用的肯定,也值得关注。比如:
“……(针对N教师介绍的球类战术游戏)以前我们总在说球类课很难开展,场地、人数的问题,那现在想想看,其实不需要什么篮架呀,可以设计成战术游戏玩起来的。现在我们上课也就是要么运球、要么传球、要么就是说一些基础的东西,但是层次上面没有再往上延伸一点,比如传球、运球怎么样组合起来了,或者在实战中怎么样去运用。其实篮球里面的突破呀、防守呀、站位呀、团结合作呀,确实是蛮有意思的,我接下来要好好琢磨一下,以及单元层面上如何设计球类内容……(W教师的访谈)”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N教师问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目标”,当我无言以对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平时我对这个问题是“视而不见”的、不太考虑的。在平时课堂当中,可能我们也是这样在做的,老教师、新教师都一样,但通过N教师给我们出的“难题”,这些教学的核心问题能够提出来了,能够让我们重新能够去想这节课,想想究竟有没有更好的练习方法啊、组织方式啊,然后对学生的意义在哪里……(L教师的访谈)”
“……其实每周三教研活动也是有的,但很容易懒散的……N教师的加入,我感觉尽管在时间上有些压力,反而能够静下心来去想一节课、看一节课……(Y教师的访谈)”
可见课例研究过程中,N教师作为校外研究人员,在理论知识方面给予了同僚教师一定的支援;同时,在对待教研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等情感因素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木原俊行指出,众多研究成果报告了教师的反思发生在与多样化立场的人展开对话、建立共同关系的过程中。这提示我们,对于具有一定教龄的熟练教师,校本研修中打破常规的教研室组织、积极引入校内外专业人员的参与,可能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其学习和反思具有积极作用[15]。
3.2反思内容的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教师反思性思考的内容特征,本研究全体成员的“问题的表象”、“可能性的设想”、“解决方案”、共计88则谈话(第1轮34则、第2轮54则)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探讨。
根据“KJ法”[16],分别对上述88则谈话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应用“KJ法”的具体步骤,是将表达内容相类似的关键事件集合到一起成为小类别,并且用可以描述这些关键事件的词语对这一小类别进行命名。接着,如果小类别中存在表达内容相类似的情况,小类别继续集合到一起成为中类别,同时对中类别进行命名。这个步骤一直持续到不存在可以继续聚合到一起的类别。根据“KJ法”的操作程序,首先由本文作者、前述的1名从事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研究管理者、以及1名体育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分别对谈话内容进行归纳、统计,再将各自归纳、统计的结果进行讨论和协商,最终抽出、形成7个大类别:“教师”、“学生”、“教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材”、“教材与教师”、以及“教师与学生与教材”。各类别的具体含义与例子如表6所示。

表6 反思内容的分类项目与谈话的具体例子
进一步,对全体成员2轮课例研究反思内容中、各大类别所占比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全体成员2轮课例研究反思内容分类统计〔个数(%)〕
根据表7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全体成员在反思内容的特征上,表现出以下2点趋势:
第1点,通过比较2轮课例研究中占总体比例最高的大类别可以发现,伴随课例研究的实施,教师的谈话逐渐由“教师”相关的反思内容转向与“学生”和“教材”相关的反思内容。这一变化,与课例研究强调课堂观察聚焦学生的学、而非教师的教,以及实施相对完整的课例研究步骤——第1次授课后、经修改教案、由不同的教师和不同的学生再次实施相同内容的教学,使得讨论倾向于聚焦下次教学的改进、而非本次教学的好坏,提高了教师进行“观课”和“评课”的针对性和规范性,进而促使教师的谈话发言更多的趋向于“问题的表象”和“解决方案”等反思性思考的发生,并且促使反思内容逐渐由“教师”转向“学生”和“教材”。
第2点,全体成员的反思内容中存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材”、“教材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与教材”的4类复合类别,且2轮课例研究中整体占总体比例略有升高。
反思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师具备的知识,那么,复合类别的反思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教师具备的相关“教师”、“学生”、“教材”的复合知识。可以认为,这类复合知识本质上属于学科教学知识的范畴。吉崎静夫认为相比一般的教材、教法和学生的知识,教师更需要具备教材、教法、学生的复合知识——即与教材内容相关联的特殊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教师从学习、理解教材内容本身的学习者立场,过渡到向学生传授、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的教授者立场[17]。本研究中2轮课例研究中4类复合类别反思内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课例研究对于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生成的影响。
王荣生等认为“课例”作为所研究问题的载体,只有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变动才能真正完成这一“课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18]。同时他们指出,专家参与的“共同备课”可能是触及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改善、进而取得课例研究实践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次课例研究中,规范实施“主题准备会议”与“教案讨论会议”、以及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全体教师的全程参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教师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选用等问题的研究质量,促进“行动”与“研究”相结合,为教师对原有知识的再构和重组、进而学科教学知识的生成,提供了契机。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杭州市拱墅区A小学为个案,应用坂本笃史的关于“实践表象”的谈话类别对体育教师在课例研究中的发言谈话进行分析,对课例研究影响体育教师反思性思考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4.1 课例研究促进体育教师反思性思考的发展。教师反思性思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与课例研究的课堂观察强调聚焦学生的学习表现有关,同时也受到本研究所采用的相对完整的课例研究实施流程的影响。但是,以教师的行为活动为主的“课的表象”的谈话发言所占比例不低的现象,仍然值得注意。这一方面是受到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研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考虑今后课例研究的实施中加强对教师进行体育课堂观察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比如开发、应用各类适合的体育课堂教学观察量表、从定量与定性等多方面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观察,以提高教师“观课”和“评课”的质量。
4.2 不同体育教师群体在课例研究中反思性思考发展的途径不同。针对本次课例研究中的互助同伴,新任教师倾向于肯定同僚教师对自身教学实践成长的关键作用,而同僚教师相对强调高校教师介入带来的积极影响。课例研究促进教师合作、且满足不同阶段体育教师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可能是促进教师反思性思考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课例研究在校本研修层面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参与人员的多元化与异质化,最大程度满足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不同需求,以促进教师的共同成长。
4.3 课例研究中体育教师的反思内容体现出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的特征。本次课例研究中,体育教师的反思内容转向关注“学”的变化特征,与其规范的同伴合作制度具有一定关系。区别于以往多数“教研活动”中的教师合作教研——集思广益或分工完成任务,课例研究通过教案研制、教学实施、教学观察、教学反思等各阶段、多途径的一系列同伴合作,强化和确保过程中的“研究”意识而避免个体教师教学展示的倾向,进而在“研究”与“行动”的有效往复运动中,促使与“学生的学”密切相关的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得到激活、提炼、改善和发展。今后,进一步审视和规范课例研究中教师之间如何合作、校外专家如何介入指导,将对本土课例研究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应用“实践表象”框架对体育教师在课例研究中的发言谈话进行了分析,提供了一种考察课例研究促进教师群体反思性思考发展过程的方法。今后,课例研究的理论背景尚需进一步考虑,需要使用更多的概念框架对其复杂过程进行多层次的透视,以深入了解课例研究促进教师反思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