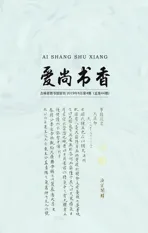文坛艺苑旧行迹(五则)
2019-08-23聂鑫森
聂鑫森
“二髯”敦煌过中秋
民国时的名流中,被誉为美髯公的有两位:于右任、张大千。他们长髯飘飘,风神俊秀,声名远播。
于右任既为当时的政要,又是诗人、书法家,而张大千更是书画界的大腕。同时,他们对敦煌文化的保护、宣传和弘扬,功不可没。乙未年盛夏,我与株洲友人同访敦煌莫高窟,所见所闻,深感人类文化瑰宝的存留和传承,是一个极为艰辛和卓越的过程,令人肃然起敬 。
“二髯”曾在1941年10月5日,农历为中秋节,相会于敦煌莫高窟,把酒临风,吟诗赏月,并商谈敦煌石窟的保护,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大千在《敦煌石窟记》中写道:“我于三十四年(1941年)二月前往敦煌,于去年(1943年)冬十二月始返成都,去敦煌勾留了两年又七个月,作长时期之研究,并收敦煌现存之北魏及隋唐壁画,率门人子侄及番僧数辈,择优临摹,依其尺度色彩不加丝毫己意逐一临抚,得画一百二十余幅……”随行人员中,既有他的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还有门人(学生)及画界友人的学生。所谓“番僧数辈”,是指张大千结识的几位藏族喇嘛画师。
那时的敦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气候严峻,生活条件艰苦。张大千自筹资金、自置设备、自理生活,对敦煌文化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保护工作,殊为不易。在为莫高窟编号记录时,“先生见下层小洞多为流沙埋没,为完整考察起见,先生遂出资请人掏沙,或自己挖个小洞钻进去考察、记录”。(张永翘《张大千全传》)
张大千说他临摹壁画百余幅,是不准确的,他的儿子张心智在所写《张大千敦煌行》中称:“临摹将近三百幅壁画(最大幅达几十平方米),全都是在丝绸和布匹上画的,所着的颜色,多是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
1941年中秋节,“先生老友、民国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等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在视察河西时,专程来到敦煌莫高窟与先生相聚。先生十分欣喜,一直陪同参观莫高窟并为详细讲解”。(《张大千全传》)下午亦然。当时的张大千四十三岁,于右任六十三岁。
当晚,张大千请于右任、高一涵等人,到他上寺寓所晚餐,亲自下厨掌勺。然后,饮酒赏月,相谈甚欢。“席间大家谈到莫高窟的价值和保护问题。”(姜德治《敦煌史话》)于右任激情满怀,作诗记其事:“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他在诗后加注:“莫高窟所在地为唐时莫高乡,因以得名。是日在窟前张大千寓作中秋,同到者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会文、南景星、张心智等。”
张大千还向于右任禀报他对石窟的考察过程,介绍许多珍贵文物被外国文化强盗斯坦因、伯希和等偷盗、破坏,令国人痛心。于右任沉吟良久,又作诗:“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同时,先生又将自己前不久在敦煌拾到的唐时张君义断手及告身拿出给众人传观,见者莫不感慨。于右任又有诗记之。”
我翻阅家藏的《张大千诗词集》两大本,这一晚他确实没作诗。他只想通过于右任向政府及社会各界进言和大力宣传,对莫高窟及榆林窟等古迹进行有成效的保护和研究。同时,张大千还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于右任颇感兴趣。
高一涵虽是个高官,亦有文人情怀,他作了长诗《敦煌石室歌》:“我来又后四十年,烟熏壁坏损妍鲜……张子(张大千)画佛本天授,神妙直追吴道玄。请君放出大手笔,尽收神采入毫颠……”
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席后,先生与右任等当晚为随行者互相作画写字至深夜。”(《张大千全传》)这就是先贤的雅集和书画笔会。
张大千这一夜虽未作诗,但在敦煌期间却留诗多首见于他的诗词集。如《题莫高窟仿古图》:“燕塔榆林一苇航,更传星火到敦煌。平生低首阎丞相(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刮眼庄严此道场。”
八年抗战中的齐白石
丹青巨擘齐白石,生于1863年。他于五十五岁时避乱北京,两年后在此定居,直到1957年辞世。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齐白石当时七十有五。从北京沦陷至抗战胜利的八年中,他虽年老力衰,仍在多灾多难的煎熬下,保持一腔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决不媚敌、事敌,至今尤为人称道。
这八年中,齐白石的家庭屡遭不幸。1937年春,他的一个女孩齐良尾病死。1940年2月,他的结发妻子陈春君在故乡湘潭逝世;同年12月,他的儿子齐良年因病而亡。1943年12月,继室胡宝珠病故。因敌特骚扰,物价飞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生计艰难,但齐白石顽强地活着,如松柏岁寒而不凋。
《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写到“七•七事变”的情景:“后半夜,日本军阀在北平广安门外卢沟桥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事”;“第二天……果然听到西边嘭嘭嘭的好几回巨大的声音,乃是日军轰炸了西苑。接着南苑又炸了,情势十分紧张”;“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继都沦陷了。”他说:“那时所受的刺激,简直是无法形容。我下定决心,从此闭门家居,不与外界接触。艺术学院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教课,都辞去不干了。”
齐白石维持家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画画、卖画、刻印所得。因他的名声很大,便常有日伪官长和手下的人前来买画、索画和表示亲近,他便贴出告白云:“齐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会客。……便又补写:‘若关作画刻印,可由南纸店接办。’”(《齐白石年谱长编》)1940年春节后,“为躲避骚扰,又在大门加贴‘画不卖与官家,窍恐不祥’告白,云:‘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同上)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说:“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欺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贴了告白:‘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
1941年5月的一天,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齐家。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住,他们直闯进来。齐白石从容镇静,“我坐在正中间的藤椅子上,一声不响,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问我话,我装得好像一点儿都听不见,他们近我身,我只装没有看见,他们叽里吐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
1943年,齐白石八十三岁。“因不堪官兵骚扰,这年起闭门作画,拒售,并在大门张贴‘停止卖画’告白。从此无论是南纸店经手,或是朋友介绍,一概谢绝不画。”(《齐白石年谱长编》)
北京沦陷后,北平艺术学院改为艺术专科学校,由日本人任顾问,并配有日本教员,一切权利归日方。曾邀请齐白石主持该校,被他拒绝。1944年夏,学校给齐白石配送烧煤,6月7日,他在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信中说:“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教职员,贵校之通知误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
齐白石既是书画、金石家,也是诗人。在这漫长、黑暗的岁月里,目睹日寇横行,金瓯残破,国恨家仇时刻萦系于怀,便借诗文画印予以倾吐。
他为学生李苦禅所画鸬鹚图题跋:“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干,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饿者不食。故旧有谚云:鸬鹚不食鸬鹚肉。”以此讽刺做日寇帮凶的汉奸走狗。
他画群鼠图,题诗为:“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年冬已换五更鼓。”画蟹题款曰:“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去年见君多,今年见君少。”鼠和蟹都是指代日本侵略者,他坚信天将晓、敌必败。
他在为友人所画的山水卷上,题了一首七绝:“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
经过中国人民浴血八年抗战,1945年,“到了八月十四日,传来莫大的喜讯,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听了,胸中一口闷气,长长地松了出来,心里头顿时觉得舒畅多了。”10月10日,友人来齐家看望八十五岁的白石老人。“留他们在家小酌,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诗,结联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白石老人自述》)
这年的12月28日,徐悲鸿与沈尹默共同发表《齐白石画展启事》,称:“白石先生以嵌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今年八十五岁矣。丹青岁寿,同其永年。北平陷敌八载,未尝作一画、治一印,力拒敌伪教授之聘,高风亮节,诚足为儒林生光。”这是对齐白石抗战八年期间,为人为艺的最高评价!
特殊年代的赏花会
2002年,叶至善、俞润民、陈煦所编《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付梓面世。该书收录俞平伯与叶圣陶二老于1974年到1985年之间的来往书信,涉及内容十分宽泛:国运家事、典籍字画、诗词唱和、学问切磋,其文人风骨、情怀、意趣历历如在眼前,为研究二老的重要资料。特别是1974年至1976年,正处在“文革”的晚期,二老的生存境遇十分艰难,但他们依旧营造出一种传统文化的古典氛围,护卫心中的一块净土,活得从容且率真,令人感佩。
以赏花邀饮雅集为例。他们(还有其他老友)多次以赏花名义相召而聚,亲自然,叙友情,唱和诗词。“事情的起源是因为叶圣陶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文革’后期开始,每年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叶圣陶总会邀请俞平伯、王伯祥、顾颉刚、章元善共同赏花,这一聚会被他们戏称为‘五老赏花会’。”(鲍良兵《“暗淡岁月”中的文化传统——以〈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为中心》)
1975年4月4日,叶圣陶致俞平伯信中写道:“奉遐来敝寓小叙,或在十二日或在十九日,看海棠如何而定。定即以电话奉告。且将约元善兄共叙。”而俞之回信称:“……前岁四月十九日,五老会于敝庐;去岁四月十九日,贤乔梓临况。今年十九,有兴再为一叙乎?”从书信上查对,五老赏花于这年的4月19日举办,俞平伯在信中称为:“逃学饮酒,良可笑也。”
俞平伯生于1900年,辞世于1990年,系诗人、作家、红学家。在1974年至1976年,他的年纪为七十四至七十六岁。他与叶圣陶的订交,始于1918年,青年时代共同创办《诗》月刊,组织“朴社”;合编文学刊物《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合出新诗合集《雪朝》、散文集《剑鞘》……可谓情深义重。到1966年5月16日“文革”风暴骤起,俞平伯被抄家、批判,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锻炼,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提前从干校回到北京。叶圣陶则在1966年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之职,此后一直在家中闲居。
“1967年,我刚到北京时,听文研所沙予说,俞先生被赶出老君堂原宅,搬入跨院北房内,颇有恋旧之情,有诗云,‘先人书室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屋角斜晖应是旧,隔墙犹见马樱花。’”(林东海《大家风范——记俞平伯先生》)被迫迁家的磨难中,俞平伯仍能感受到马樱花的诗意氤氲。
养花、赏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花为他们的生活增添盎然情趣,也是一种精神的高雅寄托。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人的情怀与趣味,往往被视为另类,遭人白眼,但这种文人传统却依旧顽强地传承着。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专设一篇《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印象》。康同璧(1883—1969年),为康有为的二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里”,院子里一株“御赐太平花”,是当年光绪皇帝赏赐给康有为的。“所以,每年花开时节,我(指康同璧)都要叫仪凤(同璧之女)制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因章诒和之父母章伯钧夫妇,偶访而逢此盛会,“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意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
何谓太平花?它为虎耳草科。落叶灌木。叶对生,长椭圆形,边缘有稀疏小齿,基出三大脉,两面常无毛。夏季开花,总状花序,萼光滑,花瓣四枚,白色。产于我国北部和中部,栽培供欣赏。(《辞海》)
太平花并非什么稀罕珍奇的花,但它是光绪皇帝赐给康有为的,并植之于家院。作为康之后人,康同璧自然对此花有一种特殊情感,此花既是一段往昔岁月的记忆坐标,又是对父亲的一种怀念,所以开花时,会邀约一些与其父有关系的名人后裔前来赏花宴饮。章诒和说:“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热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社会流行的是‘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的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所谓“文革”寿终正寝。在当今,不仅是文人骚客,一般平民百姓对于养花、赏花亦兴致勃勃。正如宋人杨万里《南国赏花》所称:“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花好多。”
田汉与聂耳
每当我们唱起庄严、雄壮的《国歌》,崇高的爱国热情就会油然而生。它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虽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弘扬民族精神、壮我国魂的赤子衷肠,至今令人感怀不已。
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口述、李华钰整理的《我同聂耳最后相处的日子》一文,称:“1933年秋至1935年春,我在上海音专继续从黄自教授学作曲。当时正值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寇铁蹄横行上海,国难家仇,激励着我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青年作曲家聂耳和戏剧家田汉,亦在此为救亡运动效力。我曾看过聂耳参加演出并作曲的《扬子江暴风雨》,深感他那些富于时代精神和战斗气息的歌曲,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田汉(1898-1968年),湖南长沙人,为戏剧活动家、戏剧家、诗人,“1930年前后参加民权保障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并任执行委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辞海》)
聂耳(1912-1935年),云南玉溪人,为现代作曲家,于1930年至上海,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工作,从事创作及艺术评论活动”。(《辞海》)田汉年长聂耳十四岁,他们既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同志,又是才情并茂的文朋诗友。
《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田汉所作歌词的雏形,“是田汉1934年5月创作的《扬子江暴风雨》主题歌《前进歌》:‘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同年冬,田汉又为上海地下党创办的电通公司写了一个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他在一张香烟盒包装纸的背面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后来,夏衍完成了分镜头剧片,交给聂耳谱曲”。(陈漱渝《田汉的命运》)
著名作家、报人曾敏之,为田汉好友。他说田汉一生写过六十三部话剧、十二部电影剧本、二十七部戏剧剧本、新诗旧体诗两千多首、七百多篇文章,此外还有翻译作品、书信等,总计一千万字左右。“在三十年代与聂耳、冼星海、张曙合作创作了许多歌曲,其中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广泛流传,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号角,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浩歌声里请长缨——记田汉》)
参与《风云儿女》音乐创作的,有贺绿汀、聂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则由聂耳作曲,贺绿汀说此曲:“以慷慨雄壮的旋律,坚定勇敢的进行节奏,鼓舞人民团结抗战,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们的吼声。不久,聂耳怀着提高音乐文化素养、提高音乐创作的心情,经日本去苏联学习和考察。他走后,我只好去找阿甫夏洛穆夫配乐队伴奏,这样,这首歌曲通过影片和唱片,冲破了黑暗社会的阻力,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我同聂耳最后相处的日子》)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当时的田汉,作为左翼运动的领导人,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受尽磨难,刚刚出狱不久。闻此噩耗,极为悲痛地写下《哀聂耳》一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为吾民诉不平。”
聂耳二十三岁辞世,为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而田汉这样一位对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才华横溢的文化巨擘,却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数年前,我曾访云南昆明,到西山拜谒聂耳之墓。墓碑为郭沫若题字,碑文镌刻田汉、聂耳合作词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尘前事,读之使人铭记先贤的丰功伟绩。他们与《国歌》同在,将传之千秋万代!
高长虹这个人
由萧乾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新笔记大观》中,收入姚青苗的《我与高长虹同住一孔窑洞》一文。文中说:“我初会高长虹是在1941年秋天,当时我在阎锡山的妹夫梁綖武主持的二战区党政委员会挂了一个名,住在资料室。……高到来时,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手提一只皮包,没带行李,风尘仆仆。”总务处安排高长虹与姚青苗同住一孔窑洞,每夜面对一盏暗淡的油灯,两人作长谈。高长虹“对春秋史兴趣浓厚,时作谠论。还记得他几次谈到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见到茅盾的情形,他把应茅盾之请所写的几篇论文的剪样拿出来给我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记述他与许广平交往经过的记录。”
在鲁迅的日记、书信、文章中,关于高长虹也有多处记载。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在新文学史上,颇让人注目。
“这个仅有小学毕业证书的山西盂县旧书香之家子弟,1924年二十二岁时只身闯入北京,实行他的文学‘狂飙运动’,以所办的《狂飙周刊》获得鲁迅的青睐,遂结为盟友,共建‘莽原社’。”(张放《孤独的“狂飙”高长虹》)当时的鲁迅很欣赏高长虹的才华,称“他很能做文章”(《两地书•一七》),曾全力提携他,还熬夜为他编校书稿。鲁迅一般不参与“语丝诸子”等文人们饮宴,却愿意同高长虹等文学青年聚餐,如鲁迅1925年4月11日的日记,写到他们“共饮,大醉”。
高长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受尼采作品影响,自信到狂傲的地步。当他渐成气候,就表现出难与鲁迅和平共处的姿仪,或在编辑事务上与鲁迅意见相左,或主观臆想产生误会。还有一个隐潜的原因,是高长虹暗恋许广平而不得。“鲁迅结识许广平时,长虹与许广平也有过‘八九次’通信联系讨论文学,然而谁也不知道他正对许患着单相思,当鲁许明朗化后,长虹即多少转入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见张放文)陈漱渝在《高长虹的家世及其与鲁迅交往的始末》一文中,对此亦有详细的记叙。高长虹在诗《给——》及一些随笔中,对鲁迅进行含沙射影或露骨地攻击,如:“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给——》)“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走出出版界》)
对于高长虹的胡搅蛮缠,鲁迅不能保持沉默了,于是进行有力地反击。对于高长虹所称的“月儿”“交给”“夜”的关系,写出《新时代的放债法》一文,给予辛辣的讥讽与尖刻的驳斥,令高长虹在圈内圈外无地自容,不得不败北而隐匿。以后,他漂泊海外,穷困潦倒;到抗战时方回国,在1941年后去了延安。
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恭和误解,其错在自身,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更高层面上说,他于抗战时回国,并去革命圣地延安,表明他对时局具有明晰的评断。姚青苗在文中称:“高长虹的皮包里还装着一篇他写的《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未胜利》的草稿,直言不讳地揭露和指斥国民党当权派的腐败堕落与后方社会的混乱、黑暗。”此文还被油印了七八十份,散发给一些“进步同志传阅”,同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但此文并非出自共产党人之手,而是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的手笔,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好视而不见。”
1941年底,高长虹由向导领路,徒步去了延安。经有关方面考察,“给了他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职务,还在鲁艺兼课。他在延安住了大约五年。1946年随军奔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病逝抚顺,刚届知天命之年。”(姚青苗文)姚说的病逝没有说明是患什么病,张放文中则说高长虹的思想、性情,与革命队伍的格调、氛围难以“完全合拍”,“故此生活郁郁寡欢,神智渐出问题,据说四十年代末病故于东北解放区一所精神病院。”
在张丽婕所编的《民国范儿》一书中,有《高长虹》一文,称高长虹生于1898年,卒于1954年。“《太原日报》有文章说,找到了当年在沈阳东北大旅舍招待科负责照料和管理高长虹的当职员工崔远清、阎振琦、李庆祥三位老同志,他们共同回忆……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楼服务员向招待所报告,高长虹房间没开门,人们都以为他在睡觉。到了上午九点许,阎振琦见门还未开,赶忙跳到二楼外雨搭上,登高往内眺望,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老人趴在床边地板上。阎设法打开房门,才得知老人已经死亡。……经检查确认高长虹夜里系突发性脑出血死亡。”此文还说:“高长虹生活很俭朴,享受着供给制县团级干部待遇,吃中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