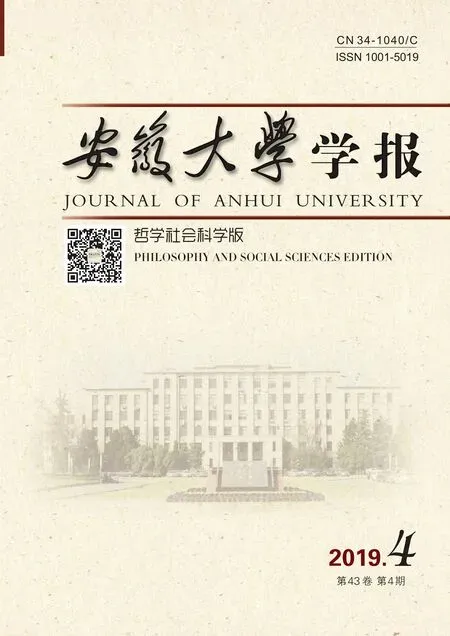在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
——从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县的赋税争议看明代的知县行政与地方社会
2019-07-18王浩
王 浩
明初制定的徭役赋税制度,从明中期开始渐遭破坏。为了保证政府的税粮收入,局部地区的田税改革从正德、嘉靖以后开始不断出现,这些变革的浪潮终于在万历初年演变成张居正改革经济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赋役变革的浪潮中,徽州府休宁县在嘉靖、万历年间围绕赋役问题发生了几次焦点事件,包括嘉靖十七年(1538)休宁知县傅灿增加徭赋、隆庆至万历年间的丝绢纷争、万历九年(1581)休宁知县曾乾亨主持的田地清丈。赋役事务不仅是知县日常行政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的直接交汇博弈点。在明代社会变迁显著的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县上述几次对赋役的调整,都引起地方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应,乃至发生朝廷注目的“民变”。本文在梳理这些焦点事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参与其中的各任休宁知县,在面对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的分歧与对立时,如何做出抉择,以及这些不同的抉择对知县本人及地方社会的不同影响[注]在关于明代州县行政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州县官施政会受到来自“上面”“左右”“下面”以及“自身”的“阻力和障碍”(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254页)。这里的“上面”和“下面”,就包括本文所论的“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
一、傅灿增赋
对于徽州府自明朝建国以来的赋税情况,嘉靖《徽州府志》有如下记载:
国朝稽古定制,贡赋皆有常额,而额外无名之征,及诸榷场一概革罢。永乐迁都时始有军需之派,遂岁为常额。其后稍稍额外增加。嘉靖以来又益以不时之派,一岁之中,征求亟至。其弊孔之开,由一二大贾积赀于外,有殷富名,致使部曹监司议赋视他郡往往加重。其实商贾虽余赀,多不置田业,田业乃在农民,赋烦役重,商人有税粮者尚能支之,农民骚苦矣。[注]嘉靖《徽州府志》卷8《食货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嘉靖府志编者直言自永乐迁都以后,额外军需之派渐成常额,且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嘉靖朝日益严重。嘉靖府志编者将此归因于在外经商的徽州大贾引起朝廷官员注意,使徽州赋税往往较他郡为重[注]最早提及徽州因商贾售虚名而受实祸的,应为弘治、嘉靖年间的休宁人汪循,详见(明)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9《敬竹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99页)。汪循的说法得到后世徽州士绅的认同与引用,成为他们强调徽州困境的依据。相关研究参见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年,第159~166页。。赋税增加给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也使嘉靖府志编者产生怜悯之心,在由士绅组成的编纂人员的脑中,农为邦本思想根深蒂固。嘉靖年间担任休宁知县的傅灿[注]傅灿,生卒年不详,江西进贤人,举人,嘉靖十四至十八年(1535—1539)担任休宁知县。康熙《休宁县志》卷4《官师·职官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451页。似乎也意识到商人势力崛起对休宁社会的冲击,试图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改革。
明朝徽州赋税大体有四种——二税、丁口、均徭、杂变,且均徭、杂变均按丁口折秋米以征,定制丁五口算米一石,出口赋钱僦役。嘉靖十七年,休宁知县傅灿向巡抚都御史欧阳铎[注]嘉靖十六年,时任右副都御史、应天等十府巡抚的欧阳铎在江南地区开展田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清理税源,确定“计亩均输”的田赋征收原则;二、整顿地方财政,建立以“八事定税粮”的田赋收支原则(相关研究参见唐文基《论欧阳铎的赋役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傅灿增加休、歙二县徭赋的建议或与此改革相关。按:在明代徽州的一些地方文献中,多将傅灿增赋一事系于嘉靖十六年[如(明)程一枝纂修《程典》卷6《本宗年表第二下》,第31页a,明万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家刻本;(明)范涞纂修《休宁范氏族谱》卷7《谱表》,第26页a,万历二十一年家刻本],此举或与欧阳铎的田赋改革开始于是年有关。本文则采用吴子玉的说法,将傅灿增赋系于嘉靖十七年。建议:由于休、歙二县民多商贾,改五丁折米一石为三丁折米一石,余四县则照旧五丁折米一石[注](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31《纂采嘉靖间休邑事略·丁口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06页。。此举使休、歙二县原本每丁0.2石米的税额提高为每丁约0.33石米,增加近65%。傅灿增加歙、休二县丁米的理由有其内在逻辑:二县多商贾,则多富人;既然富人不置田业,则可在增加徭赋上做文章。据此可知,傅灿建议的出发点是考虑到歙、休二县商、农的不同情况,依据社会变迁的实际调整具体税收政策。学界已有研究的确表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确以歙、休两县为主,承继宋元商业传统,两县之民外出经商从不间断,奠定了明中叶徽商兴盛的基础[注]王裕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所以,傅知县提高丁口折米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徽州的实际。
傅灿的建议得到欧阳铎同意并很快付诸实施,然而休、歙之民对此改革反对之激烈出人意料。这突出表现在,休宁人汪道弘率二县之民赴阙上奏,详细申述反对傅灿增税的理由。休宁人吴子玉在讨论嘉靖年间该县的赋税问题时,记录了该份奏疏全文,成为我们展开讨论的基础。这份奏疏的内容大体分为六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所谈为上文述及的明代徽州税赋之则与知县傅灿增赋之法,后四个部分则详细论述反对傅灿增加歙、休二县丁税折米的理由:
六邑一邑也,六邑之民一民也。以二邑之为贾而重困之,然岂尽二邑之民而皆贾乎?四邑不事贾,然岂尽四邑之民而皆不贾乎?以贾而苦之,二邑之不为贾者又何辜也?四邑之不贾而宽之,则四邑之为贾者而又何徼此幸也!以田言之,婺、祁、黟、绩赢于田,田之所入足以供一岁之经费,是谓世业常产。即一丁而当米二斗,借田之余以办,可估定者。二邑之人稠,而田之所供不能十半,不得不贾。贾之赀无常息,或盈或亏,不能预定。所在有僦费,不足以更费者又十半。诸为大贾不能百一,而木之租、盐之策,缗钱见算十五,或二十而算,一轺车一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百货算皆有差,匿不自占、占不悉,没入之。是已重其罚于外矣,而又重其罚于内,则二邑之民日削月朘,呶呶何以聊生也!内外并见侵牟,民命将泛,莫之振救,诚可哀痛。郡犹之一家,家丈人之令行于子弟而子弟遵之不敢逆者,以公而平也。同一子弟而为丈人者有低昂于间,何以使之趋乎?杨子云言,为人父而榷其子为不可。况榷其子而左此右彼,又何如其可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则虽征之重而民不以为怨,不均则征之薄而民有不肯供,供而不能无怨望。嗟嗞之声,有不胜其毒矣。夫有田则有租,租之不均,岂肯输租?有身则有庸,庸之不均,岂愿输庸?以朝廷之敦大庞厚而直使民为此廪廪也?“商不出而三宝绝,海加租而鱼不出。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此《北山》之诗所为作也。宋苏学士轼有言,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总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况五丁之折为首宪定令,而三丁弊政随时所立。二邑之大残也,岂容因仍以为民怨。谚曰:怨不期浅深,其于伤心。此固二邑之民所早夜以伤心者。[注](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31《纂采嘉靖间休邑事略·丁口略》,第606~607页。
休宁县民的第一个理由是强调“六邑为一”,不应畸轻畸重。既然因休、歙二邑为商者众而增加丁口折米,那么傅灿的做法忽略了二县中的非商人群体和其余四县中的商人群体,这种“一刀切”的简单做法使前者受损后者获益,尤其是对二县中的非商人群体不利。这不仅违背“六邑为一”的原则,也使一邑之人各有损益。第二,指出休、歙二县之人不得不经商的缘由:人多田少,田之所入不足供一岁之经费。经商之初衷,非为谋利,实为谋生。第三,进一步指出经商之人有盈有亏,成为富贾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况且商人本身已有沉重的税收负担(木之租、盐之策、百货之算),如果再提高丁口折米无疑会使商人内外交困。第四,为了加强说服力,援引杨雄、孔子、《诗经》、苏轼等先贤及儒家经典的论述,再次强调郡犹一家、六县为一,希望皇帝能够一视同仁,取消对二县的加赋。
然而此次上奏可能石沉大海,《明世宗实录》对此事并无记载,吴子玉亦用“不报”二字形容上奏的结果。更有甚者,进京上诉的二县百姓中,有人病死于京师。傅知县的建议得到切实执行,这表现在其后担任休宁知县的宋国华、林腾蛟等多次请求恢复五丁折石米的旧制;并且,林腾蛟在升任御史后还上言此事,但都没有结果[注](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31《纂采嘉靖间休邑事略·丁口略》,第607页。。休宁人金瑶还提到,参与其事的休宁后街人“汪君”,“尝鸣其事于当辖,而行之未就,因集先后牒诉为一册,题曰《如砥录》”,以期“秉大同之政者”复其旧制[注](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卷4《如砥录引》,《续修四库全书》第13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3页。金瑶在文中对傅灿的改革也表达了反对意见,其理由与吴子玉所引之奏疏相近。。虽然“先后牒诉”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休宁(包括歙县)之民对此增赋之举显然无法释怀。事件的始作俑者傅灿于嘉靖十八年即调离休宁,但其留给休宁百姓的影响则远未结束。其实在此事之前,傅氏颇得休宁士民之心。嘉靖十五年,傅灿在担任休宁知县仅数月后即受到巡按御史的表彰,“士大夫咸幸君之遇,播之歌诗,以颂其事。庠生金子一镕、邵子龄辈次为册,题曰《鸣琴早誉》”[注](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卷1《鸣琴早誉诗序》,第507页。。但经过增赋一事,傅氏可谓大失士民之望。这直接导致在明清各版《休宁县志》的名宦传中,均无傅灿的身影。
二、丝绢纷争
从隆庆四年(1570)到万历七年,徽州府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丝绢案”。这是歙县和徽州其他五县之间围绕作为税粮项目之一的8700余匹丝绢(折银6000余两)应该如何负担而引发的一起纷争事件。对此事件,夫马进、廖华生、李义琼等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日本学者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介绍了丝绢纷争事件的原委,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廖华生《明清婺源的官绅关系与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务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中,讨论了纷争双方的士绅阶层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认为他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依然是谋求各级官员的支持。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则对徽州府县的赋役结构及丝绢事件的五个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分析。。所谓的事件主谋、被判斩监候的婺源生员程任卿,为辩冤在狱中编纂八卷《丝绢全书》,成为研究这一事件本身及当时徽州社会、经济、法制等问题的重要史料[注]秦庆涛:《〈丝绢全书〉的整理与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52~155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讨论此事件所体现的徽州府属六县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时任休宁知县陈履、陈正谟在面对丝绢纷争时的基本态度与处事方式。
夫马进在梳理丝绢纷争的详细过程时,以万历五年六月的“激变”为中点,将此事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但作者也注意到,从隆庆五年到万历三年三月的几年间,此一事件没有任何记载,其间发生何种变故已不得而知[注][日]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万历三年,徽州府听闻北京户部即将发出命令的消息后,关于丝绢分担的调查才再次被提上日程。除了逮捕挑起纷争的歙县人帅嘉谟,徽州府再次要求六县官吏“即查帅嘉谟呈内,歙县额征丝绢应否分派五县,是否先年成规,并审该县人民有无输服加纳,逐一查议申府”[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57页。。在六县回复的申文中,围绕歙县丝绢应否分摊其余五县,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歙县知县表示同意帅嘉谟的主张,希望将原本由歙县一县承担的丝绢改为六县分担;婺源、绩溪、休宁、祁门、黟县五县则以知县或署理知县的名义表达了一致主张:按照原来的方法仍然由歙县单独负担人丁丝绢。其中,休宁县的查议申文由时任知县陈履[注]陈履,广东东莞人,隆庆五年进士,万历元年由蒲圻知县调任休宁,万历四年丁忧归。康熙《休宁县志》卷4《官师·名宦》,第500页。署名,但其据以立论者,一为“城都里老耆民张护、朱文政、金宗稷、朱朝用”等联名递交之呈文,一为“乡官胡文孚、举人程时言、监生邵龄、生员胡景星”等联名递交之呈文[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休宁县查议申文》,第464~466页。。可以说,陈知县的申文不过是为休宁士绅的意见背书,完全代表休宁地方社会的意志。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四县的申文也与休宁大同小异。
如果说此时六县间的对立尚停留在官方公文字面上的争论,那么,当万历五年六月徽州府向各县传达朝廷的处理结果,即将歙县人丁丝绢中的3300两“悉依分加五县,多寡数目递年派征”[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户部坐派丝绢咨文并府行县帖文》,第530页。时,无疑宣告了五县的失败。五县人士并没有默然接受,而是采取聚众反对的行动,使六县间的对立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在歙县所辖,遇五县人民辄行殴辱,阻绝生理;在五县地方遇歙商贩,肆行赶打,抢夺货物”,两方面“视如秦越”[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本府禁约》,第540页。。
前文已经指出,在嘉靖年间休、歙二邑之民为反对休宁知县傅灿增加丁税折米而赴阙上奏时,“六邑为一”是他们的重要论点。由于傅灿的改革对于休、歙以外四县采取的是维持现状的政策,当二县之民不断上告时,未见有四县支持或反对的记载。但在此次丝绢纷争中,由于牵涉各县的切身利益,六县便分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虽然徽州一府六县的行政架构早在唐代就已基本成型,但六县的利益绝非完全一致,彼此的分合仍以自身利益为基础。
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万历五年六月休宁士民“激变”发生时知县陈正谟的态度。万历三年,陈正谟任黟县知县,在回复徽州府关于丝绢是否应由六县分担的申文中,他依据黟县乡宦汪如海、汪尚功等人的呈文,强调应该遵守成法,仍由歙县一县承担丝绢[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1《黟县查议申文》,第468~469页。。万历四年,陈正谟调任休宁,他反对丝绢分派各县的立场没有改变,且在休宁士民聚集围堵徽州府官员时态度暧昧。万历五年六月,徽州府推官舒邦儒前往婺源署理知县一职,在经过休宁县时,县民程文昌、胡文盛,合县里排、耆老、民人等拥道递呈,“民情忿怒,鼓噪不服”[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舒爷过休宁准休民告词申文》,第531页。。舒邦儒本人关于此事的申文尚较含蓄,而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则在奏疏中直言当舒邦儒道经休宁时,“婺源之人号召诸邑,遮道鼓噪,将门吏肆行殴辱”。更有甚者,当徽州知府徐成位闻变亲自前往休宁县城时,“聚者已盈数万,鸣金约党,竖旗结盟,挟求申豁。于时道路禁阻,文移隔绝,即今该府一申一揭,众必索验之而始发焉”[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南京礼科等给事中彭一本》,第552页。。这些过激行动的主谋是程时鸣、汪十保及生员吴大江、叶挺等人,其中除“吴大江假写本县朱票,拘唤各乡人民到县聚集”外,四人又“当先倡领遮道喊告,阻留推官舒公往休宁,逼求转申分豁”。而当知府徐成位来休宁时,程、汪、吴、叶四人“复行聚集乡村愚民、城市棍徒,执旗喧哗”。程时鸣更“将木梯搭上县首屏墙,揭去原给告示,藏匿在家。复扇[煽]乡愚入集公寓,赴诉求理,仍与门外呐喊鼓噪,求其必听”[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本府原拟供招》,第564页、565页。。在这些集体反对行动中,徽州府的推官、知府受到休宁士绅为首的民众的直接冲击,而身为知县的陈正谟在此过程中只是“亦行禁谕”,没有采取切实举措保护官长。在推官舒邦儒遭到休宁人士围堵之后,陈知县在万历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给徽州知府的申文中,不仅再次要求恢复丝绢分担的旧制,而且语气颇显强硬:
为申明国法,以弥变乱事。据合县里排、耆老、民人程文昌、胡文盛等连名呈称前因等情,据此看得国家制赋,原有定额。歙县夏税丝绢,遵行二百余年,今乃改为人丁,加派五县,宜百姓之鼓噪不服也。本县虽以奉有明旨,谆谆晓谕,乡民惟知遵守祖法,纷纷告扰。近日通县人民,耕者弃弄,贾者罢市,甚至五县会议,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决战,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情实激切,势必不已。事关五县人心,终难威势强服。若不转申钧台,代为区处,诚恐变生莫测,贻害匪轻。为此申乞上裁。[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5《休宁县申文》,第531页。
在这份申文中,陈知县对于变乱成法后果的描述可谓耸人听闻,“兴兵决战”一语使人几以六县为敌国。除了在处理“激变”时的不作为(某种意义上,是在纵容休宁士民的过激行为),以及申文中对上司语涉威胁,对于陈正谟在丝绢之变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休宁县在此次事件中的特殊作用,休宁人邵庶有如下记载:
海阳东望婺,西望祁、黟,南介歙,北控绩溪,五邑父老子弟呼号扶挈,日趋海阳。御史台、中丞台、按察使者闻变来,车毂日相击也。大夫(即陈正谟)上则破盈庭之议,忤触用事者心;下则弥亿众之情,汹汹不测,而以身提衡其间。当是时也,抚剑无所用威,弹舌无所辨,而大夫束带一呼,五邑横目,踊跃罗拜,无不人人为左袒者,何哉?大夫之神气定也。[注](明)邵庶:《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万历《休宁县志》卷7《艺文志·记述》,抄明万历刻本。
明中期以后,在徽州府六县中,休、歙二县商业发达,宗族特盛,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四县的独到之处,所谓“《太函》《大泌》书千折,其中十九皆休、歙”[注](明)汤宾尹:《睡庵稿》诗集卷9《汪景谟六十寿诗》,《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97页。。故而在反对丝绢分担的五县之中,休宁县隐然成为领袖盟主。加之休宁地势居中,四县绅民纷纷在此聚集议事,作为东道主的陈正谟顺理成章地成为五县的带头人,这自然不会给知府等上级官员留下好印象。日后陈正谟在休宁知县任满后黯然去职,丝绢案中的所作所为肯定起了关键作用[注]方志中的通行记载是陈正谟因在丝绢纷争中的表现触忤用事者而落职以归,吴子玉则提到陈正谟于万历七年“被劾逮问”,但所言过简,且为孤证,故只能存疑。说见(明)吴子玉《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卷10《社会记》,抄本。。
丝绢纷争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人丁丝绢的6100余两仍然由歙县负担,2530两的均平银则由六县分担。其中,休宁应负担的份额为650两[注](明)程任卿:《丝绢全书》卷6《奉都院吊取各邑认状宪牌》,第572页。。知县陈正谟因为积极维护地方利益,在休宁县留下了“轸念民瘼,触怒上官而不顾”[注](明)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卷2,胡中生、王夔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39页。的光辉形象,顺理成章地进入地方志的名宦行列。
三、万历清丈
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进行田地清丈。两年后,又陆续在全国展开土地清丈,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朝廷明确规定,清丈一事“以各右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注]《明神宗实录》卷106,万历八年十一月丙子,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2050页。。休宁县主管其事者,正是时任知县曾乾亨[注]关于曾乾亨与万历九年休宁清丈,可参见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149页。。曾乾亨于万历五年进士及第后出任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知县,万历八年调任休宁。可以说,此时的曾氏已经具备相当的从政经验。
当曾乾亨开始进行清丈时,一些休宁士绅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时人金瑶的文集中,收有一篇《代免丈量呈》,顾名思义,此呈文旨在请求知县免于清丈递交呈文者的所有土地。其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仔细分析。这篇呈文以官方文件《户部丈量事例》为立论依据,其主要论点有三:第一,休宁县(乃至整个徽州府)的田地均不需丈量;第二,即便要进行田地清丈,也没有必要在休宁全县展开;第三,田地丈量弊大利小,希望曾知县不要举行。呈文认为,《户部丈量事例》明确规定需要进行田地丈量的三种情形,即失额、豪右隐占、小民包赔,在休宁县均不存在:
窃念本县产土以税为业,税多则业多,税少则业少。凡有出入,计此税直入毫忽,每轮造册,数并溢额无失额,一也。自市区以至各乡里,虽时有产土告争,然多是界至上出入,尺寸之间,不能相让,初不及一亩一段,此乃民间强弱相欺以有此争,不可谓豪右隐占,二也。各里虽有绝户赔貱,然赔貱之税,旧例是洒派人户,每户多不过斗升,小止合勺间,并无身家累,此不可谓小民赔貱,三也。
呈文指出,休宁田土数额可以依据税额查考,有溢额无失额;田土之争多由田地界限不清而起,所涉仅在尺寸之间,此乃强弱相欺而非豪右隐占;各里绝户之税洒派各户,每户多不过升斗,难称赔貱。据此三点,“徽州概不应丈量,不独休宁”。如果官府定要举行丈量,也应该区别对待,不可一概丈量:
又曰先清而后丈,曰清,清其某处失额、某处不失额;失额则丈,不失额则不丈也。未尝清,不可概言丈。又曰除境内额全者几图几处,先行出示免丈。曰免丈而统言境内,又分言某图某处,则州境应丈而属县必有一县、二县不应丈,县境应丈而属里必有某都、某图不应丈。不得以州应丈而概县,以县应丈而概里。又曰额全者不得一概丈量,曰不得,则律所谓不应得,此乃明示以一概丈量之禁。又曰计各省直州县失额者少,不失额者多,是丈者少不丈者多也,此乃明示以应丈不应丈分数之差,而不应丈之分多,则有司亦不得逾数而多丈。
这四点“乃丈量细目”。呈文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述,指出“徽州应丈,休宁亦必不应丈;其诸一图一处之微,姑不暇论”。意思是,若徽州应丈则休宁不必丈,若休宁应丈则某些都图(可能就包括呈文递交者土地所在的都图)不必丈。在呈文结尾部分,作者总结道:“盖丈量之法,本以遗远利而未免有近害”,朝廷是不得已而行此法,如果有司在不必丈量时举行清丈,不仅扰民生事,而且违背了朝廷清弊恤民的初衷。因此,呈文作者对知县提出明确的请求:“今丈量一事,不适于吾民甚大。幸明台体念户部事宜,深惟百姓惊扰之虑,必究其例以申明之,申明之不得则面质之,面质之不得,幸不惜以职相争挽。即使因是而获谴,是亦为法受屈,为民受屈,虽屈而益申矣。”[注]以上引文均出自(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卷10《代免丈量呈》,第637~639页。此一请求近乎苛刻:曾知县应该和上级官员据理力争,即便丢官罢职也在所不惜。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丝绢案中时任知县陈正谟的所作所为与最终结局。而曾乾亨作为陈正谟的继任者,对此事也不会感到陌生。
呈文的递交者(即请金瑶代笔之人)为谁目前尚不清楚,但身为士绅当无疑问。金瑶肯为此文,说明文中观点得到以金瑶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休宁士绅的支持。不过,在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身为知县的曾乾亨选择了前者。但他并没有因违背地方公议而遭到非议,在其去职后仍然名列地方志的名宦行列,这与他在清丈中采取的具体办法有关,明人汪道昆在《曾令君经野记》一文中对此有细致的描述。万历九年清丈田地在全国展开后,“庶司皇皇,宇内骚动”,曾乾亨并没有急于一时,而是“博讨而深求,周诹而独断”,“逾月而始定章程,列八议上上官,条二十事示境内”。通过调查研究,先定清丈之法(只可惜汪道昆并未记录“八议”“二十事”的具体内容),再划定实施清丈的基本单位,其办法是依托当时休宁的里甲都图体系:“邑三百有十里,里为图,图有正,则以驯谨者一人职之,小事从隅都质成,大事专达。郭以内合十里而各为隅,隅有四;其外合三百里而各为都,都三十有三,隅正治隅,都正治都,小事则稽于众而决其成,大事专达。然必择可以使,务得端靖长厚者一人职之。”曾知县以休宁编户的三百一十里为基础,一里为一图,设图正;将县城之内的十里分成四隅,设隅正;县城以外的三百里分为三十三都,设都正。图正、隅正、都正可相机处理小的事务,大事则直接上告县衙,由知县亲自处理。如此一来,“三正”承担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因此对于他们的选任便极为重要,此即引文中所谓的“驯谨者”“端靖长厚者”。不仅如此,对于他们的工作,“日有稽,夕有报,旬有会,月有要”,进行严格的考核。
在整个丈量活动中,曾知县并非安坐县衙之中批阅各隅都的汇报,而是亲自下到田间地头,参与其中:“令君躬行周视,路冕弗具,车徒弗烦,千里裹粮,箪食壶浆弗敢进。于是而绳不法,饬不虔,戮不用命。”[注]吴子玉也提到,曾乾亨制定清丈条规后,于该年冬“巡行郊野”。参见(明)吴子玉《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卷10《社会记》,抄本。上下齐心,丈量之事用时三月即告成功。此次清丈取得了如下成果:首先,使休宁县官田、民田的亩制和税则得以划一。“故额,邑土田以税计者万一千二百余石,以粮计者二万五千五百有奇。顾民田三壤而一则,率以广狭为差。官田籍岀多门,其则至百三十。自今比而画一则:亩百九十步为上田,加广三十步为中,又加四十步为下,其赋更若一。地视田加广,亦以广狭为差。赋则官与民平,官居什二三,民居什七八。”其次,黜税粮之浮额。“先是税粮千二百石,失额而浮。既籍,则为之核实黜浮,视故额无所加损,土田均矣。”第三,平力役。“明年(万历十年)民间当更版,按旧版浮者且六千丁,令君悉召三正赴丛祠,与之约:力诎则弛,赢则张,弛则虽丁壮不兴,张则虽老弱不复。具曰:惟命。力役于是乎平。”[注]以上引文均出自(明)汪道昆《太函集》卷75《曾令君经野记》,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538~1540页。
汪道昆的记载有两点需要检讨。首先,汪氏所言不乏溢美,且非全豹。据万历《休宁县志》所载,万历十年清丈时官民田地山塘均为一则(此即汪道昆所谓划一官、民田的亩制和税则),共计五千六百九十二顷六十六亩二分八厘五毫,“较隆庆六年总撒数目溢五百一十一顷二十八亩六厘七毫四丝五忽”。粗略计算,此次清丈在隆庆六年基础上新增田地近百分之十,不可谓不多,故而万历《休宁县志》编者认为此次清丈是“土地不加益而计亩大逾故式”,并归咎于“里胥之逢上使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休宁县的田赋并未相应增加。万历《休宁县志》提到清丈以后,夏税麦仅增四石一斗余,秋粮米仅增十一石一斗余,可谓微乎其微[注]万历《休宁县志》卷2《食货志·公赋》,抄明万历刻本。。曾知县此举实为增亩不增税,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地方社会认为清丈是政府借机增税的担忧。其次,汪道昆的文字侧重于知县曾乾亨,对于实际负责丈量事宜的“三正”群体较少涉及。按照曾知县的办法,理论上共有310名图正、4名隅正、33名都正共计347人参与此次清丈。除了对他们的品行有“驯谨”“端靖长厚”的要求外,有时还需要其人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如张子璁即因“善握筭”而担任图正,并做到丝毫不紊[注](明)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卷2,胡中生、王夔点校,第354页。。“三正”尤其是图正在清丈过程中往往会遭到豪右的阻挠,程积即因“不挠豪强,凡弱家产业久遭占夺,一一改正”[注](明)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卷1,胡中生、王夔点校,第132页。而受到赞扬。但图正们需要处理的更棘手的问题,则是因清丈而引起的田土纠纷。前引金瑶的《代免丈量呈》即曾强调“本县地方地窄人众,小民惜此寸土如惜寸金,一经丈量争论必多,狱讼猬兴,莫知纪极,为患不细”[注](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卷10《代免丈量呈》,第637页。早在成、弘时代,休宁人程敏政即指出,围绕田地与坟山、继承产生的纠纷,是徽州诉讼的三大主要起因。说见(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7《赠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9页。。田土纠纷成为士绅反对清丈的理由之一,而清丈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则证明士绅的担心绝非杞忧。
休宁人吴文奎提到清丈开始后,其俗故嚚的徽州“讼争因猬起”,文奎之弟吴廷用即因闵口渡先茔卷入一场纠纷诉讼[注](明)吴文奎:《荪堂集》卷8《三弟吴廷用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86页。。屯溪是横江、率水与新安江汇合之处,作为皖南山区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中心,这里商业繁盛,寸土寸金,田界屋址“稍有出入,则争讼无休”。屯溪人程权年轻时曾补兰溪县学庠生,后以途远乞恩终养于家。万历初清丈时,程权因齿德俱优被举为图正,负责其事,“虽有尺寸之争,秉正谕之,无不悦服”[注](明)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卷1,胡中生、王夔点校,第135页。。兖山人汪海是经营酒、典致富的商人,曾有筑堤、建桥之功。“邑大夫曾公疆田畛,以方正属处士(即汪海),履亩计之,不爽秒忽。以疆事讼者,大夫属之,处士剖决为当。”[注](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48《处士汪长公墓表》,第800页。一些都正如黄廷侃,则利用自己的财力解决因丈量而产生的纠纷。休宁“县之田广无如黎阳,而田极上贾,以争尺咫,至破其产”,曾知县遂以黄廷璧为都正。其时廷璧游外,其弟廷侃自告奋勇担当此任。面对当时“县以田畛上课讼者万数而不止”的局面,为了解决本都因清丈而产生的田土纠纷,“或以田构,田与仲公(即黄廷侃)比者,即捐己之田解;或以田之值构,即出赀偿其值以解。所解凡千赀,而是都无一谍至于大夫”[注](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33《黄仲公传》,第631页。。当然,在三百多位“三正”人员中,像汪海、黄廷侃这样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商人应是少数。但这个由儒生、商人构成的“三正”群体,确可视为各自都、图内的精英人物。他们是知县曾乾亨顺利开展清丈事务的支柱,官方也乐于通过他们将自身置于繁重的具体事务之外,仅担当政策制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
万历九年的清丈在地方上的执行十分严格,是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掌印官同知李好问等官员即因“清丈田亩怠缓”,受到“住俸戴罪管事”的处分[注]《明神宗实录》卷119,万历九年十二月乙未,第222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知县曾乾亨不可能听从休宁士绅的建议不进行丈量,进而不惜牺牲官位前途与上司一争。既然清丈势在必行,为了尽量减少阻力,曾知县利用已有的里甲都图体系,任命地方上的精英人物担任“三正”负责具体的清丈事务,对于清丈所产生的田土纠纷,也由“三正”进行初步调解,问题较大者方由官府出面解决。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使官府得以从繁重的丈量事务及由之产生的诉讼纠纷中脱身而出。而清丈的结果,特别是黜税粮之浮额,做到与旧额相较几无加增,则可以视作对地方社会有利的结果。可以说,曾乾亨在丈量一事中,既能执行朝廷功令,又能做到兼顾地方利益,处事灵活,通达权变,相较于陈正谟在丝绢案中完全站在地方士绅一方与上司对抗,更显高明。
四、结 论
明代知县日常处理的两大主要政务,一为钱粮,一为刑名。所谓钱粮,即本文所讨论的赋役事务。清朝官修《明史》对明代知县职掌的记载即以赋役为先,所谓“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债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5《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0页。。毫无疑问,在《明史》编者看来,赋役钱粮乃知县首要政务。明人叶春及以自己担任知县的亲身经历编纂《惠安政书》,其讲政务也以田土、户口、贡赋、力役等事关赋役的内容为先[注](明)叶春及:《石洞集》卷4《惠安政书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3~324页。。
与刑名即司法事务相比,赋役事务由于事关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它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在地方社会产生震动,这在山多田少、力耕所出不足以供所需的徽州地区尤为明显。弘治年间担任休宁知县的福建闽县人李烨,即曾因以“丁田之法”大幅度提高军需之赋而导致民怨四起。汪循写道:

不过,李烨的“丁田之法”尚属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朝廷功令。而本文所论休宁县关于赋役事务的三次焦点事件,则处处可见朝廷的身影。这些焦点事件的共同点,在于都不同程度地引起地方社会的反对,凸显了国家与地方利益的某种对立。作为亲民之官、牧民之令的知县们,正处于这种对立的交织点和冲突的最前线。
傅灿增赋之举的出发点,是当局注意到徽州商人崛起对徽州社会造成的影响,希望通过采取针对性的税收调整来因应新的社会形势。但具体举措失当,不仅使傅知县本人大失民望,更直接导致县民进京上告。隆庆、万历年间的丝绢纷争凸显了徽州六县在事关切身利益时的分歧与紧张关系,以及地方公议对于朝廷功令的公然反抗。先后担任休宁知县的陈履、陈正谟均选择站在地方社会的立场,与上司告争,后者在士民激变、冲击知府的危急时刻,甚至威胁上司,最终因此丢官去职。相比较而言,曾乾亨在万历清丈中的表现最为高明。面对朝廷考成的严苛功令与地方反对清丈的不利舆论,曾乾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依托已有的里甲都图体系,任命地方上的精英人物担任“三正”处理具体的清丈事务以及由此引发的田土纠纷,而以知县为代表的官府则充当起监督者的角色。曾知县在执行朝廷功令的同时兼顾了地方利益,在赢得声誉的同时保证仕途顺利。由此可见,知县行政不仅事关官员个人的声誉与前途,也对处理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以及地方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