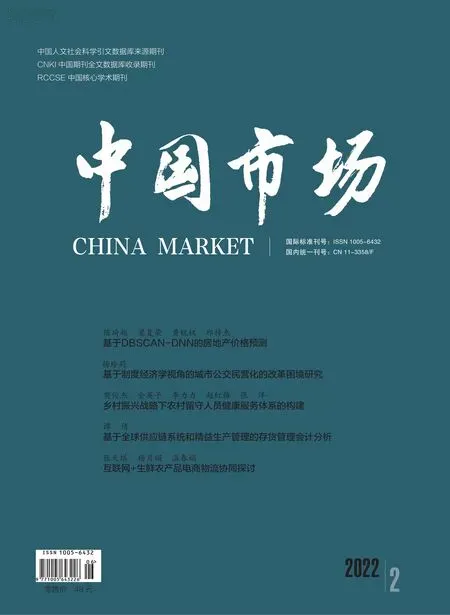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我国居民幸福感
2019-07-13孙计领
孙计领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8 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 2008 年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 2010 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 年的1.8%提高到2015 年的15.5%。即使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仍然不低。2013—201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3%,远高于世界同期2.4%的平均水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实属不易。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我国居民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上,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1978—2015 年,我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6.15%; 1978-2013 年,我国人均财富增速达到6.65%。
1 “中国谜题”的提出
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一直以来是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政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水平。幸福感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上分别被称为效用和主观福利(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 。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效用被假定为消费的函数,消费从微观上讲依赖于个体收入,从宏观上讲依赖于经济增长,所以一个共识是收入增加或者经济增长能提升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从而提高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关于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水平的关系,早在1974 年,Easterlin 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在某一时点上,富裕国家的幸福水平高于贫穷国家,但在进行跨期比较时,当一国不断变得富裕时,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却并不会随之提升,而是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现象后来称为“Easterlin 悖论”或“收入-幸福”之谜。在过去几十年,研究人类幸福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文献呈指数式增长(Kahneman 和Krueger,2006) 。关于收入和幸福的文献大量涌现,幸福的研究渐已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形成了经济学的新方向——幸福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 。
与“Easterlin 悖论”不同的是,从1990 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没有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水平反而下降了。中国的这一现象显然比较独特,既不同于“Easterlin 悖论”,也不同于Stevenson 和Wolfers (2013) 的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能提升国民幸福感) 。世界观调查数据的统计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总体生活满意度(最低为1 分,最高为10 分,共十级) 由1990年的7.29,下降到2001 年的6.53,轻微反弹到2012 年的6.86,主观幸福感(最不幸福为1,最幸福为4,共4 级)在1990 年为1.95 分,在2001 年为2.87 分,在2012 年为3.01 分。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 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联合推出的《全球幸福报告2013》显示,中国的幸福指数在156 个国家排在第93 位,比较靠后; 《全球幸福报告2016》①该报告采用使用“坎特里尔阶梯”法 (Cantril Ladder) ,最好的生活是10,而最差的生活是0。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对目前生活进行从0 至10 的评分。比较流行的盖洛普数据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显示,中国的幸福指数仅为5.245,在156 个国家排在第83 位(Helliwell 等,2014,2017) 。虽然排名上升了10 位,但仍然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排名不相称。
Easterlin 等(2012) 综合多个调查数据,进一步研究发现,自1990 年以来,我国居民的幸福水平大幅下降,虽然自2001 年以来,呈现上升态势,但仍低于1990 年的水平。为考察中国幸福水平的长期变化趋势,Li 和Raine(2014) 也综合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并通过计算发现,在过去20 多年里,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很大进步,但幸福水平呈现一个明显的下降态势。Bartolini 和Sarracino (2015) 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阴暗面 (The Dark Side of Chinese Growth) ; Brockmann 等 (2009) 称 之 为“中国谜题”(China puzzle) (为区别于“Easterlin 悖论”,本文沿用这一研究,把中国经济高速却伴随着增长幸福感下降的现象称为“中国谜题”) 。对于“Easterlin 悖论”,有两个主流的解释: 社会比较理论和适应性理论(Clark等,2008) 。对于“中国谜题”,一个重要的解释是,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Brockmann 等,2009) 。
2 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典型事实。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0 年的0.346 快速上升到2008 年的0.491,之后出现小幅回落,但仍处于高位水平,2016 年为0.465,较2015 年又有所上升。邵红伟和靳涛(2016) 认为,中国收入差距大致已在2011 年后进入“库兹涅茨”拐点区域,但很有可能稳定一段时间。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很严重(李实,2016) 。
皮凯蒂(2014) 认为,分配表是研究财富(收入) 分配的最佳工具。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数据(http: //wid.world/) 显示,1978—2015 年中国最贫穷50%、中间40%和最富裕10%人口所占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最贫穷50%人口的收入份额从1978 年的27.6%下降到2015 年的15.9%,下降了11.7 个百分点,呈明显的下降态势; 最富裕10%人口的收入份额从1978 年的26.1%上升到2015 年的37.2%,上升了11.1 个百分点,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中间40%的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比较稳定,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因为最富裕10%的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越来越高,最贫穷50%的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越来越低。中国的这一现象符合Palma (2014) 的研究发现。如果考虑财富差距,中国的不平等将更为严重。1995—2015 年中国最贫穷50%、中间40%和最富裕10%人口所占财富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95 年以来,最贫穷50%和中间40%人口所占的财富份额都呈显著下降态势,最富裕10%所占的财富份额呈上升态势。说明财富主要流向了最富裕10%人口。
3 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
然而,收入不平等是否一定是降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根源? 从现实来看,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均等化的收入分配制度,难以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发展,那时人们也未见得更幸福(陆铭等; 2014) ; 刘军强等(2012)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3—2010 年五个时点的数据,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均值从2003 年的3.27 上升到2010 年的3.77,而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基尼系数并没有明显下降,反而上升了。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幸福感下降的重要原因似乎并不成立。在理论上,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人们通常偏好于更为平等的分配(Dalton,1920) 。一系列相关实验研究也证明,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物质收益,还会关心他人的收益; 人们不仅有自利偏好,还有公平偏好,表现出不平等厌恶特征(Fehr 和Schmidt,2006) 。在实证研究中,如同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争议较多一样(Banerjee & Duflo,2003) ,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也存在较多争议(Schneider,2016) 。从根源上说,这是由现实中收入分布(结构) 及演变过程的多态性与人们认知工具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差距或矛盾造成的。
现有实证研究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之所以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是因为常使用基尼系数等总体不平等指标,忽略个体有限理性和异质性感知的现实。微观与宏观的人为分离,是现代经济学的固有弊端。类似于基尼系数的单项指标超过0.4 的警戒线并不一定就会引起人们不满和社会动荡。一方面,从总体不平等指标的计算来看,以基尼系数为例,是某一时点上各收入组之间的差距进行加总平均,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指标,不能反映各个收入组动态的变化趋势,在动态比较上,不能反映实际的结构变化。所以,基尼系数旨在用一个数值指标就能概括所一种分配状态中所有关于不平等的信息,难免让人误入歧途,单维指标不可能概括多维现实(皮凯蒂,2014)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个人角度,总体不平等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最重要的、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关键特征与个体感受(王国成,2014,p.63) 。收入不平等及其影响是极其复杂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同样的收入分布,对不同的人(群体) 产生的效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动态变化是不同的,甚至是有显著差异的。最终而言,收入差距严重与否,取决于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稳定有实质影响的不是平等问题,而是公平问题(Wu,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