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2019-07-12新乔赵晓宁任熙俊
新乔 赵晓宁 任熙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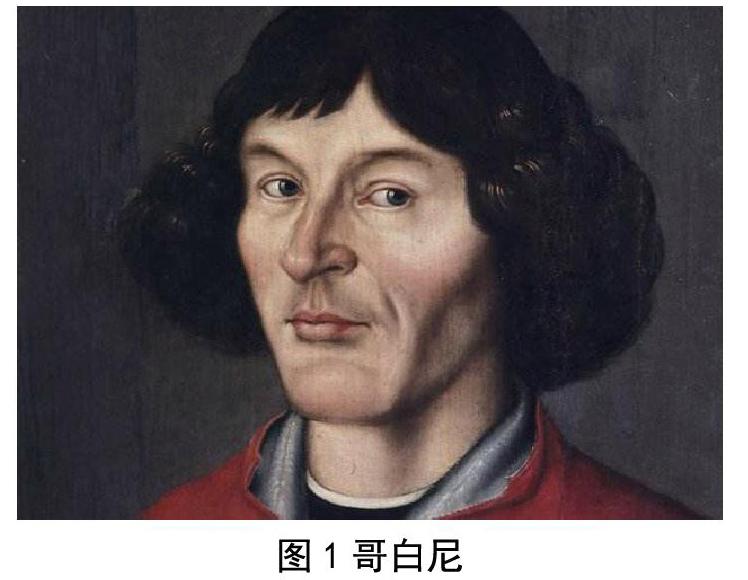
1 前言
追求对事物本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是人类前进的前提。人文主义观念引发的16世纪之后的科学变革非同小可,它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社会增加了更多的包容性,自然科学在整个欧洲突飞猛进地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广泛的规模向前发展。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相信宗教,相信金钱财富,相信帝国王朝。15世纪之前,人类相信孔子、释迦牟尼、耶稣。一直到15世纪,人类开始认识科学,以前认为不能解决的贫困、疾病和战争,都可以通过科技去完成。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强烈呼应教育变革,推动教育成为国家和广泛覆盖全体公民的事业,使科学教育有了科学依据和强大的生命力,带动了科学教育的普及。
持续发展的科学教育是近代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教育变革和科学革命为西方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到19世纪,近代科学教育在经历了漫长的16—19三个多世纪的曲折探索后,逐渐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体系,发展科学教育成为共识,科学教育相继进入欧美诸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到19世纪后半期,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民众与官方达成广泛共识的科学教育的建制化潮流,推动科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建制化(各种有关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和机构、规章和制度形成及发展的过程)的背景下,政府机构开始对科学教育重新规划,科学教育逐渐被大多数西方国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获得稳定的体制基础,走上全面发展轨道。
科学教育建制化对教育技术装备的发展具有重大转折意义。这不仅是对教育技术装备产生需求而言,也意味着扩大的规模化供应,适应性的分类设施开始出现,为教育技术装备的发展、融入教学体系、成为课程内容重要载体,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
科学教育与教育技术装备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论从哪一视角观察科学教育进入教育教学体系的过程,都可以看到科学教育与教育技术装备的产生和发展的紧密联系。科学教育发展产生的广泛需求,是教育技术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因,正是从科学教育开始,进而涵盖至教育教学各個领域,教育技术装备才得以形成不断拓展的体系化趋势,正如今天所看到的情形。
2 科学教育的历史演进
中世纪的科学教育 西方科学教育有着长期的传统。古希腊智者们研究自然科学也教授自然科学。智者们继承前人自然哲学传统,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变化来对自然现象进行推测和猜测,以某种具体物质如水、火等来推测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宇宙的本质。有些智者也研究天文、几何,如有的智者观测天象,“观察月亮的循环轨道”,用空气、云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认为“没有云不能下雨”“雷是云卷动时放的”等。
但据此便认为西方近代以前科学在社会上很受重视,一直有较高地位,就不符合事实了。如古希腊哲学及科学的创始人之一、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6,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古希腊“七贤”之一,几何学、抽象天文学的奠基人),曾经成功预测了日食的发生,因其常常在走路时也思考问题,以至于某次不慎跌入坑里,路人嘲笑他:“你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眼前的小坑啊!”在古罗马,人们崇尚雄辩和演说,当时在教育中学习自然科学多是为了给雄辩、演说提供论据和素材,科学只是作为雄辩术的一部分保留在培养演说家的教育中。
中世纪的欧洲,科学走向全面衰落。此时宗教神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要求人们的言行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与宗教教义相悖的言论被称为异端邪说,犯异端邪说罪的人轻则坐牢,重则被判火刑。作为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神学体系,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而科学教育也不过是为了解释和装饰至高无上的神学。虽然当时七艺的教学中也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内容,但这些知识也多是为教义的学习服务,多浅薄粗疏,夹杂着迷信、谬误和偏见,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和“圣经的注释”。
但科学教育也并未因此完全被湮没于钟磬和骑士的马蹄声中,新的科学教育理想仍在旧的土壤环境中顽强生长。11—12世纪,教会学校崛起,取代寺院学校而成为学术中心,这种学校环境培育了对世俗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智力兴趣。1025年前后,科隆学校的拉吉姆伯德(Ragimbald)和列日学校的鲁道夫(Radolf)进行了一次极不平常的学术交流,相互交换过八封讨论数学问题的信件,由鲁道夫发起的一系列数学问题被提了出来,答案不仅在两个通信者之间传递,而且交给了评委们(他们是这场科学竞赛的仲裁者),说明当时对世俗和科学兴趣开始有所鼓励。
13世纪后,西欧出现通过大学来归并、吸收并扩充卷帙浩繁的新知识的现象。在西欧,大学的创建大都始于中世纪,12世纪晚期已经有了提供住宿的专科学院。巴黎大学(成立于1110年)和牛津大学(成立于12世纪)作为科学和哲学的中心而享有盛名,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公元425年)却以其法律和医学闻名于世。这三所大学以及随后建立的大约八所大学(北欧仿照巴黎大学,南欧则以波洛尼亚大学为样板),成为后来智力传承、耕耘、播种的中心。13世纪,类似牛津和剑桥模式的知识分子集中的校内学院成倍增长,到1500年,各大学内总共建立了大约68个学院。中世纪大学是一种学者的行会,按学科分成专业教师队伍(主要有文科、法律、医学和神学),在每一个学科内都针对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设置了必修课程[1]。
传统的课程表维护科学、文学、人文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平衡分布。随新知识、新学术的逐步引入,教会学校中内容贫乏的传统课程就显得陈旧不堪。以数学为例,由于对希腊和阿拉伯数学的无知,他们的几何学知识少得可怜,唯依赖于罗马的综合工具书,或归古希腊数学家写的粗糙的几何论文中的少数几篇几何学论文。随着大学完全投入新的哲学和科学知识,大学课程大幅度增加,新设置的课程表强烈冲击了传统课程。到13世纪中期,文科硕士学位(凡要在法律、医学、神学诸领域深造的人必须先获此学位)所要求的课程特别偏重逻辑和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科学和哲学著作这时成为核心课程,逻辑和科学破天荒成为所有高等教育文科学生的基础[1]。牛津、剑桥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必修的内容也有了很大变化,逻辑(还包括语法学中大部分内容)、物理学(包括各种物理学变化)、宇宙学、天文学和数学基础已成为当时所有文科学生公共课程的主要内容。
近代大学角色、地位的转圜 大学的状况是整个教育乃至社会的晴雨表。20世纪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大学看作科学研究的中心,或者至少是主要中心之一。类似的情形中世纪就有过,大学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的科学、教育中心,当时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智力活动实际上都在大学墙内进行的。
传统的大学体制受到挑战早在16世纪就开始出现。1570年,H.吉尔伯特构思了国家教育改革纲领,提出建立包括数学、医学、军事和法律在内的学术总体机构的计划。这个方案虽成了泡影,但仍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接着,E.博尔顿于1617年提出建立皇家学院的计划;F.基纳斯顿于1635年提出关于建立教授近代科学的学院的建议。虽然遭到牛津、剑桥的反对,但追求大学科学教育变革的浪潮已初露端倪[2]。17世纪,英国成为“西欧科学的引导者”,英国的科学教育首先取得一些进步。在培根的鼓励和呼吁下,第一个讲授科学的格雷沙姆学院建立。1631年,定居英国的哈克就科学问题与英国知识界进行广泛交流。1648年,牛津实验俱乐部诞生;1660年,以此为基础,正式成立皇家学会。皇家学会声称遵循培根的训诫,以追求科学为宗旨,对17世纪以后的英国科学教育产生积极影响[2]。
科学开始脱离大学显示出大学地位已开始下降。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晚期,王公们的王庭成为给许多科学人士及其研究工作提供资助的中心和来源之后,更加速了这一变化。1610年,伽利略离开了他执教18年的帕多瓦大学前往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廷,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笛卡儿以及其他很多杰出科学人物的经历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现象的发生一般认为与17世纪科学革命导致亚里士多德哲学衰败,影响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堡垒的大学机构的吸引力下降有关。对此还须从它们赖以产生的环境以及它们的功能出发去理解:一方面,由于13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主体的形成,大学被有效地造就成学习的中心;另一方面,“大学从一开始起,便一直与天主教会相联系。当教会是知识的主要贮藏所时,大学几乎不能独立于它而存在”。大学发展滞后的原因部分还由于大学体系一直是精英子弟独占的领域,学习科学的窗口很少对贫寒的学生或妇女广泛敞开。
总体上来讲,17世纪,大学作为科学新事物的核心地位发生明显衰落。17世纪的欧洲大学不仅已不是科学活动的中心,还曾一度是反对近代自然科学观念建构的重要阵地,进而导致其在科学方面的落后。直到17世纪中叶,尽管认为大学在科学发展中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突破中没有起作用并不正确,但大多数科学多是在大学之外的地方进行的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有必要说明的是,谁都不否认17世纪几乎每一位重要科学家都经过大学培养,然而同样真实的是,科学既没有进入大学的普通教室,也没有进入大学课程中。当17世纪进入尾声时,始于中世纪的传统课程还没有被系统地替换。
尽管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仍在为科学和自然哲学提供组织制度方面的基础保障,在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学显然已不同以往。一般而言,18世纪的大学和学院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它们中世纪时期的智力特征和机构特征。从全球角度来看,传统的大学和学院还在继续为科学教育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基础。首先,它们还是教学机构,大学给学生讲授自然科学并使他们接触自然科学,而且绝大多数未来的科学学会成员最初都是通过大学来接触学术界的。其次,对于当时的科学界来讲,大学仍发挥着“守门人”的重要作用,因为在18世纪几乎每一个发表过研究论文的人都曾在某个大学注册过,并且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科学学会成员的最初都是通过大学来接触学术界的。像荷兰的布匹商人兼显微学家安东·凡·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1632—1723)这样的特例是少之又少,这种匮乏确切地证明了这一规则。但18世纪的大学和学院仍不能被称为科学研究或创新的进步中心,科学院和学会则取代大学成为科学活动中最为活跃的中心。
18世纪,科学事业的重组预示了大学转换为科学教育中心的复兴。到1700年,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欧洲大学的数量由40所上升到约150所,它们分布在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美洲新大陆也建立了大约15所大学学院,其中有三所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教会学校发展很快,耶稣会已有700多所高等院校,仅在中部欧洲就有200多所。但相对而言,学院和大学的数量虽有增长,却相对缓慢,尽管大西洋两边的欧洲人口快速增长,入学人数却有所下降。在北美,从1746年普林斯顿大学创立开始,宗教斗争和地理发现使得学院和大学的数量在这个世纪下半叶急速增长。至1790年,新合众国出现19所这样的学院,然而除了耶鲁大学,它们吸引的学生数量还不多。重组的科学不仅涉及专业学会、科学院、学科杂志,更包括一种“复兴的大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发展是19世纪科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那些曾经以怀疑态度审视干预大学的国家政府,也赋予大学以新的突出地位。
突破神学和传统的束缚 近代科学教育的变革首先要冲破来自两个方面的羁绊:首先是神学的束缚,其次是解决新科学与传统哲学的矛盾冲突问题。如若不然,科学教育变革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新科学的产生,使科学教育发展获得强大依托,奠定了科学教育发展的基础。
封建主义的主权、神权、特权之所以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占统治地位,其重要的前提之一便是人们的迷信与愚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會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为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继文艺复兴之后,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了一场遍及欧洲的轰轰烈烈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破除迷信、批判愚昧主义为主要使命,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又一次影响了科学技术发展与观念革命,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对教育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
1)摆脱神学束缚。在18世纪以前,无论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概念,还是科学传播模式,都与人们的通常理解相去甚远。那时还没有人靠科学研究谋生,甚至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还没有被构造出来。几乎没有人把作为信仰的宗教与作为实验和分析活动的所谓自然哲学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博物学和宗教还没有完全区分开。
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教育和智力活动的主要依托,13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神学家对他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抱着怀疑和敌视的态度。直到17世纪,所有的科学都仍然处于神学的统治之下,这就是那个时代科学教育当然也是科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1210年,刚出版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拉丁译本不久,桑斯地方宗教会议发布命令,在巴黎禁止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及其注释,公开的和秘密的都不行,否则将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1215年又针对巴黎大学重申了这一禁令。1231年4月13日,该禁令经过修改,获得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许可。格列高利在一篇有名的教皇训谕《教牧法规》(常被称为巴黎大学的大宪章)中,要求清除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带有冒犯性的错误观点。为此目的,他在4月23日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于该委员会并没有呈送过一份报告,至今尚不清楚因为何种原因,清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命令根本没有履行。
1245年,英诺森四世又将这一荒谬禁令扩展到图卢兹大学。之前在图卢玆大学可以公开阅读和讨论那些已在巴黎受禁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29年还曾为此向大批硕士和学士发出邀请。直到大约1255年禁令解除,巴黎因禁令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制裁岁月,之前,在巴黎似乎只能公开教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逻辑学著作(物理学、哲学著作可能只能私下阅读)。1255年开始,压在巴黎学者身上的石头终于被卸掉,他们拥有与牛津学者同等的特权,巴黎大学讲座课程的教材目录包括所有能得到的亞里士多德著作。
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古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对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产生重大影响。该流派主要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支主要代表力量。他们为促进人们研究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因为上帝的本质或神性就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上帝的映象,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要想认识上帝,认识神性,就只有研究自然界,舍此别无他途[3]。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起柏拉图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学说,“此种热忱堪与古代晚期对柏拉图的热忱相匹敌”。但是,“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突出了宇宙之美,神性、太一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崇高的宇宙统一体,繁多性谐和地孕育于其中,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得以歌颂宇宙无边无际,引人神往,他陶醉于歌颂神性为普照的光的形而上学中”。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眼里,上帝的本质与宇宙是合一的,神性实质上就体现在自然界的奥秘中,这无疑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3]。
在自然科学为争取独立而同神学的抗争中,有两个作为划时代的标志而载入史册的突出事件:一是哥白尼(图1)(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他指出地球及其他行星绕太阳运动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在1540年发表《天体运行论》;二是血液循环理论(由英国医生、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威廉·哈维于1628年提出)的提出。前者在对大宇宙——天体结构的解释上,把天地翻转过来,用太阳中心说推翻了被宗教奉为神明的托勒密(Ptolemy,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地心说的创立者)地球中心说,被称之为近代科学史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天文学革命;后者在对小宇宙——人体结构的解释上,冲破了神学所说的人体内部不会有循环运动的信条,使生理学、解剖学、医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首次从根本上纠正了太阳系天文学。哥白尼提出与教会宣扬的地球中心说相对立的太阳中心说,科学地论证了地球每天自转一周,每年绕太阳运行一周的客观规律。
《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写给神学的挑战书,也是科学宣布独立的宣言书。哥白尼本人也深刻地意识到他的学说的革命性质,预见到公开发表他的著作将给自己带来的后果。长期以来,宇宙结构问题是科学与宗教迷信斗争的最为敏感的地带。哥白尼经过几十年的观测和研究,几经犹豫,终于以科学家应有的勇气和信心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深深地意识到,由于人们因袭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对于地球居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的见解深信不疑,因此,我把运动归之于地球的想法肯定会被他们看成是荒唐的行动。”他更预见到一些空谈家们肯定会摘引圣经的字句对他的著作加以曲解和攻击。对此,哥白尼以对教会权威的蔑视态度和大无畏的精神郑重宣告:“我鄙视他们,把他们的议论视同痴人说梦,加以摒弃。”由于《天体运行论》刚发表,哥白尼便与世长辞,教会无法加害于他。
围绕日心说而展开的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在哥白尼逝世之后便爆发了。《天体运行论》发表后,没有立刻引起罗马教廷的注意,但经过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和伽利略(Galileo Gililei,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努力,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开来。这就使教会大为恐慌,并组织了对哥白尼学说的围剿。罗马教廷对哥白尼学说的继承者们实行了严酷的报复行动,布鲁诺惨遭教会杀害,伽利略被终身监禁。1616年,《天体运行论》被列为禁书。
在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中,科学家们曾用血和肉坚持了科学的真理,这种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景仰。布鲁诺是意大利的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由于接受哥白尼学说而被革除教籍,不得不于1576年逃出意大利,在国外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不仅到处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猛烈抨击宗教的陈腐教条,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宇宙体系。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边际的,没有中心,太阳只不过是太阳系的中心而已,在宇宙中存在无数个太阳系;生命现象也不是地球上独有的,有些行星上也可能像地球一样有生物存在。布鲁诺的无限宇宙思想集中反映在《论无限性、宇宙及世界》一书中。
布鲁诺的无限宇宙是包罗一切的,唯独没有给上帝留下任何位置,因此,教会也就不能容忍布鲁诺的存在。1592年,罗马教廷设圈套诱捕了布鲁诺,逼迫他“当众悔罪”,但布鲁诺在宗教裁判所的八年监禁和折磨中始终不屈。在宗教法庭向他宣布死刑的时候,他说:“你们比我要更感到恐惧。”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由于害怕他在临刑前发表演说,宗教法庭还在事前割掉了他的舌头。
西班牙医生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在《人体构造》一书里,详细地记叙了关于人体骨骼、肌肉、血液以及各种器官的解剖结果,并附有解剖图。他批判了盖仑所说的血液可以通过人的心脏中隔从右心室渗入左心室的错误结论,通过解剖实践证明,人的心脏中隔很厚,并由肌肉组成,血液是不可能通过中隔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的。尽管他在当时还不能指明血液是怎樣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的,但开辟了通过解剖研究血液循环理论的道路,并对盖仑医学的错误予以否定。
正像托勒密地心说的错误被教会绝对化、宗教化一样,教会也把盖仑学说的错误加以利用,为宗教目的服务。因此,维萨留斯也遭到教会的迫害,宗教裁判所以“巫师”“盗尸”等罪名判处他死刑。虽然死刑因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御医而幸免,但是财产被全部没收。以后教会又逼迫他去耶路撒冷朝圣,以“忏悔罪过”。在朝圣的归途中,他困死在希腊的一个岛上。
另一位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继承了维萨留斯关于血液的研究成果。他在匿名出版的《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指出:人体内只有一种血液,静脉血和动脉血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的血液不是从右心室直接流向左心室,而是经过肺部形成循环,即血液先从右心室被运到肺,暗红色的静脉血在肺里摄取了吸入的空气,变成鲜红色的血液,再通过肺静脉到达左心室成为动脉血。塞尔维特主张,在血液里只有一种灵气,即神的唯一灵气,并不存在盖仑所说的三种灵气——这被教会认为是否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宗教教义。特别是塞尔维特主张灵魂本身就是血液,这就等于把超自然的神归结为自然物,更遭到教会的反对。正当他要继续探索整个人体血液机制的时候,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将其逮捕,1553年被判处火刑,临刑前还活活烤了他两个小时。
宗教和科学的相互纠缠的典型特征是一直围绕对宇宙间生命问题的思索,主要涉及有关物质和物质世界的起源、发展、宿命与意义的问题。16、17世纪以来,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和经院哲学传统的质疑,引发人们不懈探索,以期普遍解决一些矛盾和困惑,由此产生科学革命,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在科学革命中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信。人文主义思想使研究自然界合法化,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
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摒弃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反对宗教神学的束缚;注重现实世界,看轻来世和天堂。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研究问题的对象,逐渐从天上转到地下,从注重上帝与人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使古希腊人注重研究自然界奥秘的传统得到全面继承和发扬。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人们把探索自然界看成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最有价值的事。因此,探索研究自然界成了人们热衷的事。
神学的束缚始终伴随着科学教育,但近代以来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后来启蒙运动的持续影响,使这一趋势不断被淡化,持续推动了科学教育发展。启蒙运动在当时乃至后来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为科学教育得以逐渐从封建神学束缚中走出来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哥白尼、伽利略在宇宙观上对宗教神学的反叛,有了牛顿的“力学体系”;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创立者)的“进化理论”,引发了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的“启蒙运动”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等人发出“上帝死了”的宣言。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包括了人们自然观念的转变。 1693年德国哈雷大学的建立是个关键时期,因为这所普鲁士大学是虔信派教徒奥古斯特·赫尔曼·佛朗克(1663—1727)
创建的产物,他谴责神学的理性化,并想重建路德教义,将其作为宗教的圣经和精神。在科学界,人们不但对科学,还对人类思想的其他领域提出大量问题。机械哲学从物质和运动的角度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用数学来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理性主义赋予人类理性以极大的力量,通过仔细考察各种传统观念和信仰,摒弃错误的教条:整个宇宙可以被充分认识,它是由自然而不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的;通过使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人类可以被“教化”,从而获得无止境的改善。
在冲破神学束缚过程中,人们对各门学科的认识速度加快,新的知识不断涌现;引发技术改变,帮助人们驯服和征服自然,减轻人的痛苦、贫穷和疾病,增进人的健康和幸福。新科学与技术进步又极大地推动了普及的教育,阅读、写作和学习取得惊人的进展。这些曾经被看作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现在成为所有阶层的一般权利。民主革命以卷席之势横扫法国、英国和美国,进而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以致对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的捍卫现在被全世界接受了。正如汉金斯所说:18世纪的自然哲学家相信,科学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理性是正确方法的关键,它甚至会毁坏宗教法庭的基础。
如上述,对于职业的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来说,对宇宙间生命问题的思索是主要的长期相互纠缠的结点,科学与宗教之间为此展开了长期论争,直到在有关世界的多元性方面达成一致,即相信存在许多有生物居住的世界以及基督教的观点。但这种看似一致的和谐,又随着托马斯·佩因(1737—1809)对基督教激烈批判的《理性的年代》一书在1796年的出版而失去意义。事实上,佩因接受存在其他有生物居住的世界的观点,无法接受一个人同时持有多元主义,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种“狂想”:地球上的救赎计划竟然是宇宙万物的某种例证。对于佩因来说,接受宇宙中其他地方的生命,使得存在唯一救赎手段的基督教断言变得荒谬可笑。
对于佩因的结论,有许多排斥者,但他们大多支持将外星人当作上帝伟大存在的证明的更新论证。这证实了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克提出的关于自然神学在面临19世纪科学和思想新发展的挑战时具有反弹活力的观点。19世纪中叶发生的转折点是威廉·惠威尔(1794—1866)于1853年写的《世界的多元性》一书的出版。这位矿物学家、哲学家和剑桥的英国国教牧师以及大学最杰出的人物,推翻了他早期接受的世界多元主义,因为他开始相信事实不可能与基督教相一致。
在这个历史变迁过程中,近代自然科学教育也不断挣脱传统和神学的束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生长,并日益焕发出活力,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科学课程教学中,即使是耶稣会士和其他亚里士多德派的教授的课程教学,也并非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完全无关,包括教会学校。在天主教盛行的南欧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然科学在大学的附属学校的讲授相当普遍,且课程内容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启蒙运动“使原有的神谕性世界图景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命名的世界图景:自1690年代起,科学即是光明之路的前导”。以黑格尔的话讲,就是“人类的和神圣事件中一切的猜测都由启蒙运动完全逐灭尽绝了”。启蒙思想家们创出了最早的百科全书,他们以牛顿的《原理》为起点,把既有的各门知识类别重组,有的还添加新的分支。为了醒目,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主编)于1751年推出《百科全书》并第一次配有显示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图画。科学教育开始取代神职人员把持的知識学问,“主张一切知识——不分道德的、政治的、历史的——应都具有科学性。在任何知识领域里产生疑问探求答案,都应以客观地追求通则为目的;每一门知识都是可以系统化、条理化的,甚至读与说的行为也不例外,人的思维与语言的互动,不论今古东西,都能以科学方法理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革命后的法国教育学家第一次面临创立亘古未有的、主要不是为了学习神学的学院和大学体系”的任务。自然科学第一次被永远地解放,推动解放科学教育的车轮在新教国家不懈地前进。
法国大革命以前,德意志北部新教徒大学的哲学学和神学的关系便已经疏离。随着19世纪初康德学说在德意志北部大学中的胜利,在许多信奉基督教的邦国内,哲学和神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被永久且坚决地斩断了。康德唯心学说的信徒、普鲁士的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1767—1835)通过支持每个学院甚至神学的专业自由,完成了解放性的革命。与康德一样,洪堡也试图改变传统大学的架构。1810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这是第一所按照规定,教授需要像从事教学一样从事研究的大学,此时保持了传统的四个学院。道德科学和自然科学仍然结合在一个独立的机构中,不过环境是崭新的,教授可以自由讲授自己热衷的内容,学生可以自由参加自己喜欢的课程。在德意志的大多数大学中,这种传统的结构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