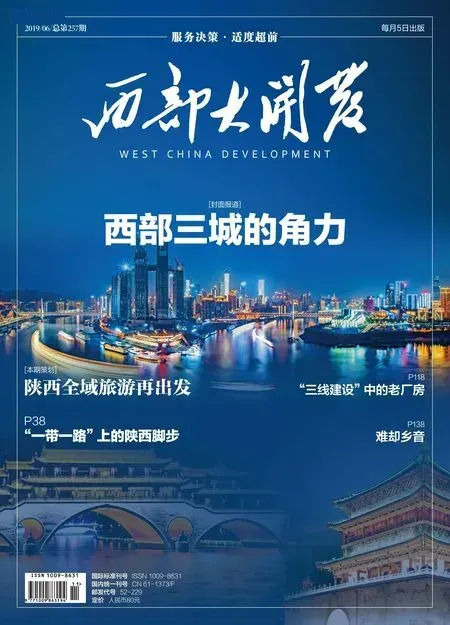难却乡音
2019-07-09刘新中
文 / 刘新中

解放路道北一带——曾经河南人在西安的聚集地
文学
乡音是故乡的声音,所有的人无不是在乡音中启蒙,伴着乡音长大,乡音是人们的文化脐带,妈妈用它来唱摇篮曲、教孩子牙牙学语。所以,乡音属于人的根脉一类,这就是许多外出远游的人一听见乡音,顿时泪流满面、不能自持的原因。那是一种渗进血里骨里的记忆,是一个人永恒的精神烙印,是真正的最能表达情感的载体。
我在陕西长大,祖籍是河南,小时候,在我们居住的铁路家属院,绝大多数是河南人,一张嘴全是一个音,一个味,父辈们那一代在河南土生土长,当然能听来哪是洛阳话,哪是开封话,什么豫东豫西黄河南北,十里九不同。我们的辨识度则差了许多,外人更是一头雾水。河南话是我的乡音。
那时候,生活圈子很小,即就是坐过几次火车回郑州老家,沿途也都是河南话。陕西省曾调侃河南人是“河南担”,意即挑着担子逃荒。由此还诞生了新的民谣:“陇海线,三千八百站,站站都有河南担!”我理所当然的认为,河南话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流通语言,以至于偶然听到陕西话,还以为见到了异类。直到上了学,才知道,还有普通话,那才是正经八百的中国通行语言,还有其它各地的方言。
渐次长大,河南话一直伴随着我,因为,我居住的城市,长长的街市,百里煤海,沟沟岔岔,河南人起码占了一半。那时候,铜川、宝鸡、咸阳以及西安解放路道北一带,河南话是通行的市井语言,即就是其他省籍人,他们的后代,在这个环境里生长,也是一口顺溜的河南话。曾有人开玩笑说,那些年不会说河南话,你都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在社会上混。我初中毕业后,参加三线建设,我们的连队70%都是河南人,一张嘴,叽里呱啦全是河南口音,以至于连队的四川军代表很是疑惑:陕西话怎么有点像河南话?有一次,一个广东兵说河南人的不是,竟差一点招致挨揍。
河南人在陕西究竟有多少,有一个不精确的统计,铜川大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宝鸡占总人口二分之一,西安主要集中在解放路向北一带,大约有几十万人。
现代历史上河南人往陕西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主要是沿着铁路线流动。第一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黄河花园口决口后,河南被淹的灾民逃离大概有180多万人,顺着铁路线一直往西走,很多人都到陕西了;第二次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粮食绝收。又遇蝗灾,有300万河南人扒着火车携家带口西出潼关到了陕西,电影《1942》详细再现了这个苦难历程;第三次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一大批又一批的河南人坐着火车来到陕西的煤矿、纺织厂等各行各业的单位工作,前前后后,合起来也有好几十万人。
西安市人口1934年仅为124645人,而1947年则飙升了4倍,达到547450人,就是大批河南人涌入之故。
《铜川市志》记载:1942年铜川人口54889人,1949年就增至94998人,到了1964年成了236300人,1970年300000人,且城镇人口比例达到了70%。河南人在陕西安家落户,繁衍子女,那些年不计划生育,家家普遍五六个孩子,加上他们的后代,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18年最新统计,陕西省人口总数为3000多万人,河南人占多少,我没有资料,数字说不准,四五百万大约应该是有的。

1942年,通过陇海线往陕西逃难的河南灾民
现在陕西省流行的河南话早已经不是纯粹的河南话了,没有了什么豫东豫西郑州洛阳这些地域的差别,就是一种河南普通话。对于老一代来说,乡土乡音是一种家乡的恋情,情感的寄托。他们的口音永远不变,嘴里蹦出来的,经常是已经消失了的连他们的后代也听不懂的老家的土音。对于年青一代,就是一种地域根脉的联系,一种血缘依稀的印迹残存,一种对故土的回望和尊重。他们和父母在一起或者在河南人圈子里说的是河南话,而在外面更广大的区域,基本上都说普通话,陕西话,抑或河南话,根据场合,随时变换频道。
实事求是讲,曾几何时,占陕西人口众多的河南人在陕西人的眼里形象并不好,尤其上个世纪,中国人普遍居住条件差,逃荒的河南人居住环境尤甚,他们从茅草庵土坯房起步,密密麻麻挤成一疙瘩,又脏又乱。即就是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单位盖了公房,也是一家一间,几十户上百户用一个水龙头,用一个厕所,加之胡搭乱建,拥挤不堪。贫困带来了卫生的不良,许多人居住的地方,污水横流,蚊蝇乱飞。教育的缺失,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屡见不鲜,社会治安情况令人摇头。在这个区域里,是河南话的一统天下。
人微言轻,人穷语贱,很长时间,河南话被认为“土”“粗俗”“野蛮”。
贫困的正效应是第一位的,那就是河南人的拼搏奋斗。他们凭着手艺或者凭着力气去唱曲、卖艺、扛活、拉车、修脚、搓背、理发、卖菜、拾煤核儿、拾破烂,下煤窑,艰难度日。一切陕西人不愿做懒得去做而生活中又少不了的行当,河南人都去做。原因当然显而易见,河南人为“蝗灾”“水灾”“旱灾”“兵祸”所逼迫,赤手空拳来到陕西,地无一分瓦无一片,许多人只能干社会最卑微的职业,为得有口饭吃,根本没有条件选择生活。无论如何,活得有尊严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保证,说话有分量同样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保证,这是生活的法则。
其实,河南话被人轻贱并非与生俱来。可以这样说,上溯百年,河南话还是一种时尚语言。清末民初,河南人袁世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北京的上流圈子,就以会说河南话为荣,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里,就有这样带几分羡慕的赞美河南话的台词:“人家不说好(三声),人家说好(一声)”。
所谓的“土”“粗俗”“野蛮”当然是一种偏见。河南话中有些实际上还是很雅的古语,可以在古诗文中寻觅到它的踪影。譬如“幌子”,本意是指挂在店铺门外,用来招揽顾客的招牌。金瓶梅中第十八回就有:“朱红小柜,油漆牌面,吊看幌子,甚是热闹。”唐代陆龟蒙《和初冬偶作》:“小垆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幌子”高大醒目,河南人形容某人个子大,称为“那么大个幌子”。还有河南人爱说“噫”,表示惊讶或感叹,古文中就大量出现,譬如梁鸿《五噫歌》“民之劬劳兮!噫!”
现在最早的有关河南地区的语言记录便是《诗经》,《诗经》代表了先秦时代通用的语言“雅言”,也就是那个时代洛阳一带的方言;唐代标准语便是以当时洛阳、长安两京的方言为基础的;北宋定都开封,洛阳为西京,开封洛阳的语言为全国的通行语。
历史上,河南人来到陕西,是堂堂正正的来的,是以导师或者文化使者的身份来的。河南话曾是一种贵重的语言,代表先进的文化。
著名的文化学者商子雍曾说过,有三个河南人,在陕西把事干成了。这三个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老子,一个是玄奘。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被尊奉为“中华始祖”,河南新郑人, 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河南新郑那一带古时又叫轩辕之丘,所以,号称轩辕氏,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并因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的许多业绩是在陕西完成的。因此,升天以后,就葬在陕西的桥山。

道北真理村的集市上,老人们用河南话交流着

位于楼观台的老子骑牛雕像
老子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老子年近80岁时,他看到周王室日益衰落,诸侯纷争,社会矛盾突出,感到非常厌倦,便决意退隐,到相对清静稳定的秦国安度晚年,就辞官不做,骑着一头青牛,离开了洛阳向西来到陕西周至的楼观台。老子在楼观台完成了“道德之经五千言”,对自己的道学观点进行了总结,并继而在此讲经授徒。老子的《道德经》博大精深,在中国千古流传,至今仍被人们顶礼膜拜。

大雁塔前,屹立着的玄奘雕像
玄奘俗姓陈,名袆,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意为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他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也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玄奘到天竺取经,就是小说中的西天。他从凉州玉门关出发,经过今天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区,单独行走十万里,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天竺,学习了近20年,最后回到了长安,并同时带回了657部佛经,受到唐太宗的热情迎接。为了保存从天竺带回来的珍贵经文,唐太宗特地在长安城内的慈恩寺西院修筑了五层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玄奘还将西行沿途的风土人情、政治、历史、文化等编纂成《大唐西域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玄奘译经19年,先在西安的大雁塔后在铜川的玉华宫,最后圆寂于玉华宫。玄奘大师留给后人的是“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玄奘精神,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脊梁”。
河南人在陕西把事干成的,当然不止这三个人。
北宋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张载,祖上是河南开封人,小时候父亲死于涪州官任上,于是侨居在现在的陕西省眉县横渠乡,这就是张载被人称为“横渠先生”的由来。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关学是他在关中地区讲学而形成的一个大的学派。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冯友兰先生尊为“横渠四句”, 被马一浮先生尊为“横渠四句教”,其作者,正是张载。
秦王扫六合,中华民族由此走上大一统,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也有四个河南人。
头一个是商鞅,又名公孙鞅,本是诸侯小国卫国的没落贵族,河南濮阳人。商鞅从卫到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辅佐秦孝公对秦国进行了变法。可以说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改革,秦国由此走上强盛。
第二个是尉缭,他是河南开封人,相传尉缭是鬼谷子的徒弟,是中国兵家四圣之一,曾著有军事著作《尉缭子》,据说还是兵仙韩信的启蒙老师。尉缭在秦王政十年时,来到秦国,此时秦王政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六国的最后一击。尉缭的到来,于秦国是旱田里的甘露,尉缭被拜为秦国国尉,用自己的军事思想对秦国军队进行了整顿治理,对秦国的军事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个是吕不韦,河南安阳滑县人,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对落魄的秦国王子嬴异人下了血本,最后帮助异人回秦即位,即秦庄襄王,自己也被拜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广为招揽门客,让他们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多万字。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而且书成后,悬于城门,遍请天下贤士,称有可以改一字者,奖以千金。“一字千金”的成语就是从此而来。吕不韦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为秦统一准备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基础。
第四个是李斯,河南上蔡县人。李斯早年为小吏,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和韩非子是同学。学成后到秦国发展,从小吏干起,一步步赢得嬴政的信任。最终成为嬴政的心腹。李斯向秦王献上离间各国君臣的计策,又提出了“灭韩,以巩它国”的主张,一跃封为客卿。李斯在帮助嬴政废分封,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方面,居功至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可以想见,当那些风格各异的河南话或策划于密室,或高亢于疆场,或娓娓道来,或激情四射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盎然意气、恢弘景象。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河南人喜欢说“中”。“中”是河南话的精髓,意喻“好”“肯定”。中字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代表不偏、中正的意思,也表示一种人生处世的态度,比如中庸之道,其核心是仁爱、友善、宽恕、和平。河南人认为“中”是一种文化认可,是一个地域性的人文历史传承。这个“地域”,就是华夏人文历史上最早的“中国”。“中国”之名,来源于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的简称。“中国”之“中”字,不仅是华夏“太极”、“五行”等朴素唯物主义理论组成的核心内容,也是对华夏文化发源的最高和集中表述,更是对现代“中原”、“中华”最早产生地理方位的历史传承和认定。三皇五帝等华夏先祖把最早共同居住的“中国”传承给了“中原”河南,“中原”河南又将其传承给了大“中国”。可见,“中原”是“中国”人文历史的传承地,是现代中国人文历史的核心地区和发源地。历史上河南人的文化自信就来源于此。
还有一个“美”字。河南人把一切舒服的惬意的都称为“美”,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老美”。美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想象,用美来界定一件事物的整体,是对一个好的东西从里到外的综合描述,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肯定。
美是语言的极致,河南人说“美”是黄帝那里批发来的。美字从羊从大。“羊”意为“驯顺”,“大”意为“国土辽阔”。“羊”与“大”联合起来表示“国土辽阔、人民驯顺”,这是统治者的愿望;而老百姓的美就是有肉吃,有土地,这是理想的生活状态。
环视中国,能把地方语言一个字解释和阐发到历史人文高度的,也只有河南人。
近代,也有三个满口河南话的河南人予陕西影响甚深。

张凤翙创办的西北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凤翙,原籍河南沁阳县。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今西安市),在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赴日本振武学校兵科学习,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张凤翙1909年回到西安,武昌起义后,他与钱鼎、张钫等发动西安起义,被推为临时总指挥。1911年11月陕西军政府成立,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兼民政长(省长),12月被南京临时政府正式任命为大都督。1912年8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陕西都督。
张凤翙最大的功绩是助力推动创办了西北第一所大学——西北大学。张凤翙认为创办西北大学,“关系于现时建设”、“关系将来之建设”和“关系于外部之防御”。因此他以原陕西法政学堂为基础,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高等学校等校并入,设大学预科和法、文、商、农各专科。
西北大学在1912年正式开办,中国名校,海内外华人世界里,无人不知。100多年来,为陕西,为西北,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河南新安铁门镇人;幼年念私塾,1902年到陕西;1904年后入陕西陆军小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春毕业后入军旅,成为陕西新军中主要领导;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任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陕军第二镇统制、师长;参加护国运动。张钫主要成就一是参与西安起义,二是抗战期间组织赈济河南灾民。
陕西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张钫的一些事迹。赈济时,张钫安排支起大锅熬粥,灾民饿急了,一拥而上,张钫一口河南话让人亲切:娃子乖,慢点,多着哩,还有……
最臭名昭著的是曾任陕西省省长的河南巩义县人刘镇华。刘镇华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开始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授将军府阜威将军,辛亥革命后,他凭这支号称十万之众的地方武装,依违于各大军阀之间,先后投靠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最后归附于国民党蒋介石。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职。
任陕西督军兼省长期间,刘镇华用了不少河南子弟,一时间,各个机关衙门,到处充斥着河南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次年初,刘镇华出陕去洛阳督战国民革命军,结果大败而逃。转往山西投靠阎锡山。不久,他以陕甘总司令的旗号,收罗镇嵩军残部和豫西土匪,号称十万兵马,进攻陕西,企图重温土皇帝旧梦。1926年4月,兵临西安。著名的“二虎守长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杨虎城时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李虎臣时任陕西军务督办,他们二人殊死坚守西安,刘镇华久攻不破。于是分兵攻咸阳、三原、泾阳、高陵诸县,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拉丁征夫,无恶不作,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十数万民众流离失所。被困在西安城内的军民更是饥寒交迫,以麸糠、油渣、树皮,甚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腹,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的军民有五万多人。几乎占当时城内人口的一半,可谓万户萧疏,人影零落。西安解围之后,将所有死难者掩埋,堆起两个墓冢,名为“负土冢”。两冢之间,建“革命亭”一座,并将该处辟为公园。第二年春,西安市民在此举行大祭,追悼在此次守城之战中死难的军民。杨虎城将军含悲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刘镇华给陕西人带来了深深的伤害,由此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河南和陕西的渊源,当然是有原因的,从文化上,一条黄河把两个省连在了一起,周秦汉唐,两省密不可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大唐近三百年,洛阳作为陪都,和长安来来往往;从地理上,紧紧挨着。尤其1934年底陇海铁路的修通,为难民逃荒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抗日时期,西安属于大后方,陕西八百里秦川,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西安作为西北最大的城市,生产和生活资源丰富,易于生存。
历史一去不复返,终归只活跃在书本里,活跃在历史学家的研讨之中。河南人留给陕西最直接印象的,是现代河南人的所作所为,是那一口浓浓的带有中原气息的河南话。
现代河南人来到陕西,除了贫穷、除了乞讨,还有辛勤,苦干,坚忍,他们中不乏优秀者,出类拔萃者。他们为陕西省的建设,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广义是讲,他们代表陕西,也代表河南。
譬如英年早逝的赵梦桃,河南中牟人,因花园口大水,逃荒至洛阳,后参加工作在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她集思广益创造了“巡回检查操作法”,在全厂推广;她提出“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口号,对同伴们在技术上帮助、生活上关爱;她先人后己,11次把好车换给别人;她进厂11年,年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42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她身体不好,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她不但自己是先进,而且带领整个小组成为先进。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成风。她也因此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赵梦桃死后,陕西作家协会的著名散文作家魏钢焰含泪为她写出了名噪一时的报告文学《红桃是怎样开的》,三秦大地,一时震动;
譬如吴桂贤,河南巩县人;西北大学毕业,曾被评为中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
吴桂贤是共和国第一位由工人而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女工人,不言绝后,绝属空前,注定,要被写入当代中国的历史;
譬如河南密县人张金聚,铜川煤矿工人,全国第二届三届人大代表,十三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成为一代又一代煤矿人的骄傲和美谈。
一个工人,如此大密度、高频率的见到最高领袖,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绝属凤毛麟角;
譬如河南巩县人冯玉萍,全国劳动模范,为了抢救井下的矿工兄弟,奋力关住着火的压风机闸门时,不幸被大火烧了双手,耳朵、鼻子,留下了永远的伤痛,成了残疾人……
有一张照片,周恩来总理接见冯玉萍,陪伴在旁边的,是“铁人”王进喜。王进喜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先进典型,与王进喜同列,可见冯玉萍在那个特定岁月里的分量之重;
譬如河南省淅川县人郭秀明,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当代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创业之歌、奉献之歌。他被誉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脊梁,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一面旗帜。
郭秀明有大胸襟,曾抒壮志:为干一件大事而来,为干一件大事而去。郭秀明11岁来到陕西,久居乡村,河南话已经淡去。而冯玉萍生活在河南人集中的煤矿,多年乡音不改,曾经在一个场合,我听到过冯玉萍的一次讲话,她反复念叨:其实,我没干啥。当那朴实的河南话从那略微变形的嘴里发出时,不由得令人湿了眼眶。
上述仅仅是数百万在陕西的河南人的一部分,是河南人的优秀代表,他们身上共同体现出一种精神。如今,陕西加速发展,人们大力提倡“浙商精神”。 “浙商精神”的核心就是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思变精神。实际上,河南人早就把这样一种精神融入到陕西的血脉之中。
扯起这个话题,有陕西人说,当年,赵宋王朝南逃时,许多达官贵人同行,还裹挟带走了河南的大批能工巧匠。如今的许多浙江人,就是河南人的后裔。
事物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类比,但无论如何,它是如今陕西人对河南人的一种肯定。
80多年前,铁路线就像河道,河南的逃荒者讨生活者就是奔涌的潮水。
陇海铁路通车后,西安火车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没有人烟,逃难的人流就搭棚子住了下来。抗战时为了防止飞机炸弹袭击,西安城墙挖了很多城墙洞,抗战以后,很多难民看到有城墙洞就住了下来,到最后很多都成为了自家的院子。上世纪70年代以前,西安城墙北边城墙洞都还住着人;如今,这地方叫大明宫地区,街道宽敞,高楼林立。西安火车站的新规划已经开始实施,附近的民乐园地区以及太华路形成了繁茂的商业区。


西安市豫园豫剧团惠民演出
陇海铁路往西通到宝鸡,河南的难民潮们沿铁路流到此处,大多就居住下来了,在铁路边卖煤卖炭,是好多能吃苦的河南人的首选。后来铁路旁边的这条街就叫炭市街了。还有一条布市街,是河南裁缝们做生意的地方;如今,这地方也是街道宽敞,高楼林立。一条渭河穿城而过,绿树成荫,宝鸡已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咸铜铁路是陇海铁路的支线,一路向北,难民潮流到铜川,则沿山沿沟挖掘窑洞,搭茅草庵,铜川几条沟诸如狼沟、老虎沟、小河沟等挤满了人;如今,这地方同样街道宽敞,高楼林立。铜川因煤而市,十里长街旧貌换新颜,河南人从无到有,在创造自己家园的同时也参与创造了他们居住的城市。
潮水是一种比喻,潮水过后,是乱石滩,是遍地的垃圾;清理了垃圾,改造了乱石滩,就会是湖水盈盈,碧映蓝天。
河南人到陕西,不惟改变了陕西,也改变了自己,新一代河南人中,不乏作家、记者,教授、艺术家、白领、公务员、企业家等。
当人们在胡辣汤、水煎包等小吃的摊子吃着早餐时,河南话在人群中漂浮着,抑扬顿挫,此起彼伏,人们是否意识到,河南话如同这流行的早餐一样,也成为了陕西的一部分了呢。
还有河南豫剧在陕西发扬光大,陕西关中各地,都有豫剧团。
豫剧最早什么时候跻身陕西,说法不一,但大规模来到陕西,毫无疑问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曾有人说,在陕西的几个城市,可以没有秦腔,但绝对不能没有豫剧。
豫剧又叫河南梆子,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醇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
河南人高兴时听它,唱它,难受时听它,唱它;思乡时也听它,唱它。许多老一辈河南人听收音机、看电视,固定不变的常常是河南台的豫剧节目。
那是真正的河南声音,伴随河南人一路走来,是几百万远离故土河南人的精神家园。
1951年,共和国之初,铜川煤矿的大规模建设刚刚拉开序幕,著名豫剧演员崔兰田之妹崔兰玉在西安组建豫声剧社,在铜川演出盛况空前,受到欢迎。在一片河南人的鼓噪声中,铜川地方政府拍板,与剧社协商,接收改建为红星剧团,后更名为铜川市豫剧团。

由西安演艺集团豫剧团创排的原创豫剧现代戏《秦豫情》
那时,西安还没有豫剧团。西安曾经有一家著名的狮吼剧团,由著名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樊粹庭于1934年在开封创办,后辗转演出,落户西安;以后和著名演员曹子道于1950年在三原县创办,1952年落户西安的民众剧社合并为西安市豫剧团。狮吼剧团曾经和“易俗社”等剧团一样,在西安市民中有广泛影响。
宝鸡市豫剧团1957年5月在原“宝鸡市曲艺实验团”的基础上,并招收潼关“复新豫剧团”的40余名演职人员联合成立。咸阳市有咸阳豫剧团。渭南市有豫剧团。
1958年时,西安铁路局也成立了一家豫剧团,理由当然是丰富职工文艺生活。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也说明了豫剧在一个以河南人为主的单位的深入人心。以后,这批演员分到了各个站段,我们所住的铁路家属院有几个,傍晚,经常能见到他们在家门口,拉起胡胡,哼哼呀呀,周围聚拢一圈人。
时间在不经意的流动中,慢慢凝固成历史。一瞬间,百年沧桑。
无疑,当代几百万河南人的入秦,于河南,于陕西,都是一件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大事件。它是一种文化的漫洇,不知不觉中,改变或者更新了陕西的面貌。这种面貌,包括文化地理的,包括人文生态的,也包括精神观念的。仅仅就语言上,毫不夸张,某种程度上,河南话也成了陕西语言的一部分,河南豫剧被许多陕西人接受,成了他们的所爱之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河南某豫剧团由马金凤领衔,到铜川演出。那时,父母还活着,我为他们买了两张票,曲目是《穆桂英挂帅》。看完戏,父母第二天都激动着,父亲说:到底是马金凤,那戏,真中。母亲说:连此地人(陕西人)都来看戏,一张嘴都是此地话。
那天晚上,我散步顺便到剧场转了一圈,黑压压一片自行车。散场时,陕西话“嫽得太”和河南话“美得很”交织着,俨然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2016年,铜川市王益区出了一本书,《天南地北王益人》,我作为生于铜川长于铜川的王益人,也应邀入选。从理性上,我认同我是陕西人,因为,陕西给我的太多太多。
我的父亲是2008年去世的,为他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我们原来居住的家属院早已拆迁,邻居四零八落。老邻居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说,我们原来家属院的谁谁早走了,谁谁这几年去世了。一片儿时听熟了的河南话,温馨而又亲切。
我母亲2014年去世时,那几个老邻居也已经不在了。他们是一代人,是一棵棵从河南移来栽种在陕西土地上的树,曾经葱绿过,茁壮过,但谁也抗逆不了岁月,春风秋雨,暑往寒来,他们纷纷凋零了。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双手的创造,一堆儿孙,再就是那一口浓浓的乡音。
无论如何,乡音难却,它是所有离豫来陕河南人永远不灭的故土印痕。这篇文章结尾时,换脑子,打开电视,十分巧合,竟然是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辕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 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高亢,嘹亮,舒展。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了父母的声音,竟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