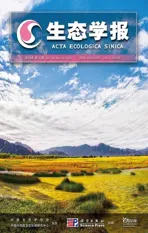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2019-07-05张婷婷彭昭杰张昊楠鲁长虎周大庆
张婷婷,彭昭杰,张昊楠,鲁长虎,周大庆,*
1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南京 210037 2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 210042
栖息地亦称生境,是能够维持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在其中完成其全部生命过程的场所[1- 2]。栖息地可以为鸟类提供住所、食物、躲避不良气候和敌害,鸟类的数量、地理分布、繁衍成功率以及雏鸟存活率等都受到栖息地质量的影响[3]。因此,在鸟类生活史中,栖息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丹顶鹤(Grusjaponensis)是世界上现存的15种鹤类之一,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并被定为濒危物种[4],同时也是我国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处于湿地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层,是反映湿地环境动态变化的生物指示种[5- 6],业已成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之一[7]。世界现存的丹顶鹤依其地理分布和迁徙行为可分为岛屿种群和大陆种群。岛屿种群分布在日本的北海道东南、东北部湿地,是不迁徙种群。大陆种群是迁徙种群,可分为东部种群和西部种群,其中东部种群在三江平原、乌苏里江流域和兴凯湖湿地繁殖,在朝鲜半岛中部越冬;西部种群在黑龙江中游俄罗斯一侧、松嫩平原和达乌尔地区繁殖,主要在江苏盐城滨海湿地越冬[8]。目前,全世界现存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约3050只[9],岛屿种群和东部种群数量均不断上升,而西部种群数量却基本在历史最低位徘徊,栖息地变化被认为是丹顶鹤西部种群下降的最主要原因[8,10- 11]。
繁殖期是野生丹顶鹤进行繁殖,种群得以延续的重要时期,近年来,丹顶鹤繁殖地研究主要集中于巢址空间分布[12-14]、生境变化驱动因素[6,15]、巢址选择[16-17]和气候变化[18-20]等方面。对于繁殖地动态变化,张艳红等[21]运用GIS技术分析了1979—2000年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适宜生境的动态变化过程,发现湿地面积不断萎缩,生境破碎化不断加剧,严重威胁野生丹顶鹤生存;刘宇轩等[22]也发现1978—2016年莫莫格自然保护区沼泽面积大幅度减少,湿地质量总体呈恶化趋势。总的来看,现有研究虽然明确了很多丹顶鹤繁殖地的生境变化情况,但一般局限于单个保护区,缺乏全面系统研究。迄今为止仍没有对丹顶鹤大陆种群整个繁殖地动态变化的研究,而全面系统研究的缺失不利于在宏观尺度把握丹顶鹤的生存现状,制约了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工作的开展。
本研究以丹顶鹤大陆种群重要繁殖地为研究对象,依托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相关技术,全面分析了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转移特征、生境破碎化以及东、西部种群生境变化的差异,为有针对性地开展栖息地保护管理工作、促进丹顶鹤野生种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丹顶鹤重要繁殖地筛选
基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数据库中的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总体规划等资料,并根据《中国脊椎动物就地保护状况评估》[23]一文的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了我国有丹顶鹤分布记录的自然保护区112个,其中繁殖地71个。通过查阅保护区科考报告和总体规划、《中国鹤类通讯》(1999—2012年)、《迁徙的鹤类和水鸟快讯》(2014—2016年)等非正式出版刊物,公开出版的论文专著、部门咨询、实地调研、电话咨询等方法,初步归纳整理2000年和2015年(或前后时段)71个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繁殖种群数量,作为基础数据以供后续筛选。
为兼顾丹顶鹤种群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采用2006—2009年越冬季的丹顶鹤种群数量计算丹顶鹤大陆种群总数。2006—2009年,丹顶鹤西部种群主要越冬地——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的越冬种群数量分别为718只、801只、640只和502只[24],东部种群越冬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越冬种群数量分别为840只、861只、1041只和1019只[25],即2006—2009年越冬季丹顶鹤大陆种群的平均值约为1606只。参考国际重要湿地的相关标准筛选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即“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而丹顶鹤大陆种群1%的个体数量约为16只。鉴于丹顶鹤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稀少,且西部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保护形势严峻,故将标准适当降低,即:只要该保护区有10只及以上的丹顶鹤栖息,即被列为重要繁殖地,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经筛选,确定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共计18个,分别为:黑龙江扎龙、挠力河、兴凯湖、平阳河、八岔岛、洪河、乌裕尔河、三江、哈拉海、友谊、三环泡、七星河、龙凤湿地、吉林向海、莫莫格和内蒙古辉河、科尔沁、图牧吉自然保护区;其中,黑龙江挠力河、兴凯湖、八岔岛、洪河、三江、三环泡、七星河、友谊和平阳河自然保护区是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黑龙江扎龙、乌裕尔河、哈拉海、龙凤湿地、吉林向海、莫莫格、内蒙古图牧吉、科尔沁和辉河自然保护区是西部种群重要繁殖地(图1)。

图1 丹顶鹤西部和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分布图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important breeding habitats for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populations of the red-crowned crane
1.2 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量化
以自然保护区范围边界矢量图为地理参照数据,运用遥感影像处理软件ENVI 5.1和ArcGIS 10.2,对18个保护区2000年和2015年Landsat TM遥感图像进行假彩色合成、图像掩膜等预处理。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利用分类标准,结合自然保护区实际土地利用现状和丹顶鹤生境需求,建立景观分类体系;将研究区域划分为耕地、林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草地、人工设施(包括居民点、道路等)、水体(包括水库、坑塘和河流等)、沼泽湿地、盐碱地7种景观类型。通过监督分类与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对遥感数据进行解译。基于遥感影像解译成果,使用ArcGIS 10.2软件分别计算2000年和2015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以及占保护区总面积的比例。
为掌握丹顶鹤重要繁殖地的生境破碎化程度,采用Fragstats 4.2[26]计算每个自然保护区的景观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和蔓延度指数(Contagion Index)。斑块密度是描述景观破碎化的重要指标,值越大,表明景观破碎化程度越高;蔓延度指数能够有效描述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值越小,表明景观破碎化程度越高,反之景观连通性越好[27-29]。
1.3 数据分析
采用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分析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的景观格局转化[30-32];利用ArcGIS 10.2计算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及比例,制作和整合18个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基于Fragstats 4.2计算结果,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Ttest)比较2000年和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的斑块密度和蔓延度指数是否有显著差异。以2000年和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为自变量,以东部、西部种群为分组变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Ttest)比较:①丹顶鹤东部种群和西部种群重要繁殖地的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有无显著差异;②丹顶鹤东部种群和西部种群重要繁殖地不适宜生境(包括耕地、林地和人工设施)的面积变化有无显著差异。所有统计分析均在SPSS 19.0[33]中进行。
2 研究结果
2.1 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及转移特征
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土地利用变化明显,主要表现为:①沼泽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其中沼泽湿地总面积减少了1400.5 km2,耕地总面积增加了1085.4 km2(表1);②林地和水体面积均呈增加趋势,人工设施面积有所减少,其中林地和水体面积分别增加了206.9 km2和453.0 km2,人工设施面积减少了24.5 km2(表1)。由此可见,耕地扩张和沼泽湿地萎缩是丹顶鹤重要繁殖地面临的主要威胁。

表1 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情况
丹顶鹤重要繁殖地2000年景观斑块密度(均值=12.5个/km2)和蔓延度指数(均值=55.4%)均大于2015年的斑块密度(均值=12.3个/km2)和蔓延度指数(均值=54.6%),但均无显著差异。部分自然保护区破碎化程度加剧,其中2015年斑块密度较2000年相比增长了10%以上的自然保护区有8个,斑块密度增长率居于前四位的依次为黑龙江七星河、吉林莫莫格、黑龙江挠力河和洪河自然保护区,其增长率分别为56.6%、44.9%、43.1%和31.0%。
丹顶鹤重要繁殖地的土地利用转化主要发生在湿地与耕地、湿地与林地、湿地与草地、草地与耕地、林地与耕地之间。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耕地面积增加最多,其主要由沼泽湿地、草地和林地转化而来,三者转化面积分别为1083.3 km2、481.2 km2和274.1 km2;沼泽湿地减幅最大,主要转化为耕地、水体和草地(表2)。林地主要由草地、沼泽湿地和耕地转化而来,转化面积分别为278.5 km2、223.4 km2和205.4 km2;水体主要由沼泽湿地和草地转化而来,转化面积分别为531.2 km2和156.9 km2;草地面积减幅不大,主要转化为耕地;人工设施减幅较多,主要转化为草地和耕地,转化面积分别为43.9 km2和29.6 km2(表2)。
2.2 丹顶鹤西部种群与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丹顶鹤西部种群和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2000—2015年七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均无显著差异;2000—2015年不适宜生境(包括耕地、林地和人工设施)的面积变化也无显著差异(t=-0.43,P=0.67)。但是,2000—2015年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沼泽湿地缩减面积(平均值=103.9 km2)远大于西部种群(平均值=50.1 km2),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不适宜生境的增加面积(平均值=83.8 km2)也大于西部种群(平均值=57.1 km2),表明2000—2015年丹顶鹤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的恶化程度比西部种群更为严重(图2)。

表2 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图2 2000—2015年丹顶鹤西部和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图Fig.2 Changes in areas of various land use types of the important breeding habitats for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populations of the red-crowned crane during 2000—2015
3 讨论
土地利用变化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19,34- 35]。东北地区是丹顶鹤的主要繁殖地,气候变化对其栖息地的影响日趋明显。本世纪初扎龙自然保护区由于连续干旱和随之而来的火灾以及湿地退化等原因,导致丹顶鹤适宜生境大面积减少即是明证[17,19]。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在深刻影响着丹顶鹤繁殖地的变化[36- 37]。本研究发现2000—2015年期间,虽然丹顶鹤重要繁殖地的人工设施面积不断减少,但人类活动的强度并未因此缩减,耕地面积的剧增是人类活动加剧的直接证据。2000—2015年,沼泽湿地面积减少了1400.5 km2,耕地面积相应地增加了1085.4 km2,马尔科夫转移矩阵也表明耕地主要是由沼泽湿地等转化而来。虽然扎龙等自然保护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湿地注水、禁止捕鱼、生态移民等保护管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17],但是很多重要繁殖地(如吉林莫莫格、黑龙江挠力河等自然保护区)耕地、林地、人工设施等不适宜生境面积不断增加,栖息地质量不断恶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明显下降[22]。实际上,耕地扩张和沼泽湿地萎缩业已成为丹顶鹤繁殖地面临的主要威胁。
2000—2015年,由于自然保护区对丹顶鹤湿地生境的保护和管理投入不断增加,人工设施面积明显减少,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连接度总体维持稳定。但是,仍有部分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如吉林莫莫格、黑龙江七星河等自然保护区)因人类活动干扰导致沼泽湿地面积大幅减少,耕地、水体等景观类型面积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22,38]。例如,吉林莫莫格自然保护区内油田占地广且较为分散,外加一系列的勘探、打井等作业破坏了附近的原生生境,从而导致斑块形状复杂化,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景观异质性不断增加[39- 40]。除耕地外,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沼泽湿地转化为水体的比例较高。例如,吉林莫莫格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面积减少了169.5 km2,同期水体面积却增加了155.0 km2;黑龙江挠力河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面积减少了417.1 km2,同期水体面积却增加了101.0 km2。根据《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技术导则 第3部分:景观保护》(LY/T 2244.3- 2014),沼泽湿地转化为水体,虽然其生态级别赋值未发生变化,但对于丹顶鹤而言,其生境适宜度却明显降低。
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移,且程度不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湿地的转出和耕地的转入。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在人类干扰加剧的情况下,沼泽湿地面积呈萎缩趋势。以黑龙江挠力河自然保护区为例,其2015年沼泽湿地占保护区总面积的比例较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32%,其中高达341.8 km2的沼泽湿地面积转化为耕地,导致耕地面积增加了~57%,生境破碎化程度明显提高,这与宋晓林[41]和张弘强等[4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作者认为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近十几年来,随着区域气候变化影响,水环境的变化和天然降雨的减少导致湿地生态功能减弱[43- 44];二是人为干扰因素,湿地资源被掠夺式的开发、过度垦荒和放牧,以及大量水利工程和铁路高速公路的修建破坏了湿地原始景观格局及水文状况,导致湿地干涸,逐渐演替为干草甸甚至为盐碱地,严重威胁着湿地生物多样性及丹顶鹤栖息环境[45- 47]。
从整体来看,2000—2015年丹顶鹤东、西部种群繁殖地的湿地生态系统均处于逐步退化的阶段,湿地破碎化不断加剧,农耕用地的大量开垦破坏了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甚至造成了永久性的、不可恢复的面积变化与破碎化。2000—2015年丹顶鹤西部种群繁殖地退化速度相对减缓,典型代表有黑龙江扎龙、八岔岛等自然保护区[17],而黑龙江挠力河、兴凯湖、七星河等自然保护区作为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不适宜生境面积的增加值和生境破碎化程度均比西部种群高[41- 42,48],可以说其生境质量恶化程度比西部种群更为严重,需引起高度关注。东部种群繁殖地的恶化有可能导致丹顶鹤繁殖地向北推移,近年来黑龙江珍宝岛自然保护区丹顶鹤繁殖种群不断增加很可能是东部种群对原有生境恶化的响应[49]。
近年来,丹顶鹤适宜生境持续丧失和退化,尤其是耕地面积持续扩张,西部种群数量持续减少。为更好地保护丹顶鹤赖以生存的湿地生境,为丹顶鹤生存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基于本研究,笔者建议:一方面有效控制耕地扩张,大力推进退耕还湿工作,并开展湿地恢复;另一方面高度关注丹顶鹤东部种群繁殖地的生境动态变化,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另外,目前栖息地变化对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的影响研究较少,尤其是量化研究。下一步应着力开展栖息地变化(包括繁殖地、中途停歇地和越冬地)对丹顶鹤野生种群影响研究,为科学评估我国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锐减的原因、有效抑制丹顶鹤野生种群的持续下降提供技术支撑。
致谢: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徐网谷副研究员、吴翼博士和张建亮博士,南京林业大学李明诗教授在遥感影像处理过程中给予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