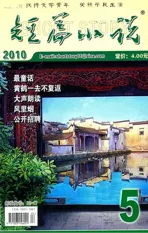死亡日记
2019-07-04王东梅
◎王东梅

01
龚姐出现的时候,我刚刚恢复了单身。
分手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平静地吃了一顿饭,宣告这段关系的结束。从前男友的家里搬出来的那天下着小雨,他贴心地帮我把行李一件件装上车,然后嘱咐我,以后要好好吃饭,晚上睡觉要关紧门窗。他把手中的伞递给我,然后带着苦笑说:我也是多此一举,你一直都是很独立的。我知道你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与他,还有上一任男友的恋情,都是这么和和气气地结束的。没有狗血的三角恋,也没有令人难堪的撕破脸,我们从一开始的交叉线慢慢变成平行线,互不干扰也过得很好。
直到有一天,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受够了这样的生活,他们感受不到自己被需要,所以他们要去找一个需要他们的人。我竟然无法反驳,缘分这东西,有来就有去。我能做的,只有接受。
就这样,我搬回了自己在利民街的公寓,又开始了独来独往的日子。刚开始的一两个星期确实有些难熬,可渐渐的,我开始享受独自在家不被打扰的静谧,和自给自足、不用对别人负责的生活。
没有了男女私情的烦扰,我开始更加投入对待自己的工作。我在报社里负责情感专栏,每天都会在报纸上分析男女情感中的各种问题,替人解答疑惑。每周我都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大多都是电子邮件。除了咨询一些感情问题外,也发表一些对我文章的看法,我会从中挑出一部分来进行回复。
龚姐就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她的信是通过邮局寄到报社,然后再由报社转交给我的。来信的频率也很频繁,几乎一周一封。我把它们都收了起来。现在我有了大把时间,我按照寄来的顺序一封一封地拆开阅读。白色的信纸,黑色的墨水,字迹干净而娟秀,这让她的诉说更有了一种娓娓道来的温柔。
她说她叫龚淡菊。人淡如菊,信也有人如其名般的清爽。我不再把收到她的来信当成是例行工作的一部分,而是我独身生活里别样的、每周一次值得我期待的东西。
她的来信我都保存得很好,有的时候夜里失眠,就翻出一封来读,竟也让我烦躁的心底浮上一层安静和清明。她在信中向我讲述她与自己丈夫的爱情故事。他们青梅竹马,当年一起创业,一路从底层打拚,她一直在他身后默默支持,现在他已经是个成功的商人。
她人到中年,回想年轻时的岁月,心里忽生感触。她说自己一直都梦想当作家,可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她只能把这个梦想压在心底。
我回信鼓励她开始写作,还把副刊一个编辑的电子邮箱告诉了她。
后来她果真发表了一篇小小说,为了感谢我,她提出邀约,要请我吃饭。她的这封信我一直没回,我犹豫着自己是否应该和她相见。龚姐在我看来,有种藏在那些温柔文字后的神秘的美感,我怕一旦见面,这缕神秘会烟消云散。不见她的面,更让我有想象空间。
我看她在信封上留下的寄件人地址,是在西郊,我上网一查,果然是片我从未去过的高级别墅区,离我住的利民街车程也要两个小时。她在信中,言辞恳切地邀请我一定要去她的家里坐坐。她说到了她的这个年龄,才更加深知,有个能时不时谈天说话的朋友该有多可贵。
她的诚意我很感激,可我却不得不回信婉拒。我说现在有些重要的私事需要处理,等过了这一阵,一定登门拜访。
关于这点,虽是推辞,但我却没有撒谎。我说的“重要的私事”,就是胡燃。
到了今年的六月十一日,胡燃就失踪整整十年了。
02
胡燃是我最好的朋友。胡燃失踪以前,我们同在C城十中念高二。
胡燃的性格很活泼,在学校里人缘不错。我的性格就内向一些,除了前后桌的同学外,也很少与别人说话。
高一的时候,有个好事的高三男生把拍我的照片,上传到了学校的贴吧里,虽然很快就被管理员删除,但一时间还是闹得沸沸扬扬。放学的路上,还有外校的男生堵我。这件事也让我在班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女生们恨透了我,她们在背后说我不要脸,是风骚的狐狸精。
胡燃是我的同桌,我们上下学也同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开始保护我。她替我大声喝退那些在放学路上等着我的外校男生;听见班里的女生议论我的时候,她就跑过去帮我解释,说:景宜才是受害者,大家都是同学,你们要讲点道理。
她的解释作用不大,班里的女生也开始连带着她一起孤立。但这却让我们的关系更加要好。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吃饭,彼此之间都没有秘密。
我文科好,她理科好;我好静,她好动。我们是如此不同,却又如此亲密无间。我们商量好,要报考同一所大学,毕业后要在同一个城市生活。
胡燃没有爸爸,每次学校的家长会都是她妈妈来。她的妈妈姓齐,在市场里经营一家面包店,胡燃有时会去帮忙。齐阿姨脾气很好,总是笑眯眯的样子,每次去她们家,齐阿姨都会拿出些西式糕点来招待我。胡燃和她的妈妈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公寓里,屋子很干净,但却丝毫没有男主人的气息。
关于胡燃的爸爸,我知道那背后也许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所以在胡燃面前,我从来不问关于她爸爸的问题。只是有一次,我搞砸了数学测验,拿着不及格的卷子要家长签字的时候,挨了父亲的一记耳光。第二天,胡燃见到了我肿起来的脸,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哭着告诉了她。
她一边安慰我,一边小声地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爸爸。我连我爸长什么样都没有印象,他就病死了。胡燃的眼睛湿漉漉的,想哭却又没哭。那是我记忆中她唯一一次提起自己的父亲。
胡燃失踪的那天,是个周一。我参加的文学社每周一都有会,有的时候胡燃会留在教室里做作业等我开完会,然后再和我一起回家。可那段时间胡燃妈妈的蛋糕店也许是很忙,每到周一一放学,她就会着急地赶回店里帮忙。
胡燃失踪的事是那年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则新闻。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高二女生,突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人间蒸发,警方和民间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追查和寻找。我和胡燃放学回家总是会经过一条商业街,那天,一家商户安装的摄像头拍到了胡燃失踪前最后的画面。她的脸上带着微笑,正对着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后视镜整理自己的刘海。那之后,她一步步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胡燃出事后,我做为她最好的朋友,接受了多次警方和媒体的询问。而我最后和胡燃说话的画面也被我无数次放大、放慢,如电影般一帧一帧、一格一格、一秒一秒地在脑海中回放。她穿着有些松垮垮的校服,向我挥挥手说:明天见!然后笑嘻嘻地离开了。
齐阿姨在市场等到关门,也没有等来胡燃,回到家,她也不在。后来,她惊慌失措地跑到我家,我的父母和她还有一些街坊邻居如无头苍蝇一般,在这个城市的夜色里找了很久。后来天亮的时候,他们去了派出所报案。
女高中生失踪的新闻震惊了整座城,人们追寻、分析、讨论,可都没有换来胡燃的任何消息。后来,总有更大的新闻爆出来,胡燃的失踪案渐渐冷却了。齐阿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警局打听案件的进展,可回回都是失望而归。
齐阿姨见了我,情绪时而激动、时而伤感。最开始的那几年,她经常在我面前哭,她也总是说:如果那一天,胡燃能留下来等我开完会,再和我一起走,也许一切都还是好好的。她哭,我也哭。
后来,眼泪渐渐流尽,想起胡燃,我们都哀伤又温柔。我们一起回忆那些有胡燃参与的往事,对于未来,却是不敢说的。齐阿姨的心里始终怀有信心,她觉得胡燃终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十年里,她没有搬家,就连胡燃住过的房间也都每天打扫。我虽然心里不愿意承认,可我总觉得,在胡燃的身上,恐怕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不过,这些想法我从来没有给齐阿姨说过。我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看她,陪她说说话。她依然经营着面包店,但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胡燃失踪后,她身上的那股子干劲也随之消失了。更多的时候,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见人。
背阴的一居室里,光线很差。家具摆设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客厅显眼的地方,依旧摆放着胡燃的一张单人彩照。我记得那张照片,是学校艺术节的时候,摄影部的人帮她拍的。她很喜欢那张照片,千方百计要了底片,自己洗了好几张。照片里,胡燃梳着马尾,瓜子脸、细长的眼睛、小小的虎牙,很瘦。她对着镜头有些羞涩地一笑,看起来有种苍凉的美。
我把带来的水果和营养品放在桌子上。因为知道我要来,齐阿姨正在厨房里包馄饨。我每次来,她都要留我吃顿饭。电视里正播着新闻,说的是近日本市又有一名女大学生失踪,警方、家人正在全力寻找,可还是毫无进展。我趁着齐阿姨端馄饨进来前,赶紧换了频道。
我们俩一起吃饭,齐阿姨问起我最近的情况。我说自己和男友分了手,现在自己住。齐阿姨叹了一口气,说: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懂。如果胡燃在这,她或许还能帮你出出主意,你们俩也一定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点点头,我们俩沉默地吃完了馄饨,我问齐阿姨,我能不能去胡燃的房间里坐坐。齐阿姨说好,她麻利地收拾起碗筷,去了厨房。
我推开胡燃房间虚掩的门,她卧室里的一切如旧,就连写字台上的笔和本子,都保留着胡燃最后一次用过后的样子。我拉开写字台的椅子,坐了下来。写字台上复着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一些胡燃喜欢的明星图片和她自己的艺术照。还有一张纸片,纸片上的字是我写的。当时我在练硬笔书法,见胡燃那么喜欢我的字,心中也很得意,就抄了很多诗给她,她都很喜欢。其中的一张被胡燃压在玻璃板下。
我盯着那张纸片,觉得它如同这房间一般,像是在时间流逝之外,十年来没有一丝改变,却又像是时间里的一个黑洞。这黑洞吸走了胡燃,把她带向了无人得知的境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齐阿姨进来说:小景你今晚住下,咱们娘俩好好说说话。
却是一夜无语。我和齐阿姨并排躺在大床上,月光从没闭严的窗帘里泄进来,我撩开窗帘的一角。
今天是满月呢!我轻声地说。
我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晚上,也是满月。我的父母叮嘱我待在家里不要乱跑,然后他们一群人在月色里,找遍了这个小城的各个角落。
是啊!已经十年了。齐阿姨轻声说着。她握住了我的手,谢谢你还记着胡燃。
03
快进来!门一开,龚姐就笑盈盈地说。
你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她热情地把我迎进门,然后在我背后关上大门,口气中带着一些惊喜:终于见到你了,真是太好了!
虽然知道这片别墅区大概的价格,心里做了准备,但当走进龚姐家的大门时,我还是不禁在心里暗暗地赞叹。穿过玄关的走廊进去,就是个大到像个舞池一样的客厅。再往里走,是个有天井的中庭。中庭里种着花草,还有一个茶桌和两把椅子。
随便坐啊!龚姐热情地招呼我。想喝点什么?咖啡、茶,还是饮料?
她在我身后等着我的回答,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光顾着欣赏豪宅,连龚姐都没好好打量过。
她看起来四十岁上下,笑容亲切,人有点胖,但隐约可以看出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
茶就好,谢谢你。我在客厅的沙发里坐下。
龚姐端茶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她的手。那是一双干活人的手,皮肤也不像脸上那么光滑,手背上还有清晰可见的伤疤。
我四处看了下,这么大的房子里,好像只有她一个人。
龚姐,你的家真漂亮!我由衷地赞美道。
谢谢!她笑着在我对面坐下,不瞒你说,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打理的,因为就只有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所以我也没有请保姆,他的饮食起居都是我在照顾。
真了不起!
其实习惯了也没有什么,而且他经常出差不在家,所以也只有我一个人。来,我带你四处看看!她有些兴奋地站起来。
跟着龚姐在她的家里转了一圈,我不得不再次感叹,这房子虽大,可因为每处都被龚姐精心地布置和设计过,所以并没有冰冷空洞之感。
我们俩坐在中庭的长椅上聊天,到了饭点的时候,龚姐执意要留我吃饭。我有点不好意思,她却说:你难得来一次,就当是陪我好吗?我一个人在家很孤单的。
我望着她,觉得自己何尝不是。
胡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不是没有机会,但我却总是适可而止。也许我是担心,自己一旦再找到一个像胡燃般无话不谈的朋友,就会彻底把她遗忘。而她的失踪,不知道为什么,也成了我心底最深的秘密。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提起。
我成了龚姐家的常客。龚姐说: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周末应该去约会才是,却来陪我一个老太婆。真是罪过啊!
我把龚姐教我配好的调料包,放进文火上的鸡汤里。先生不常回来吗?
他忙。以前没有多少钱的时候他忙,现在有钱了,反倒是越来越忙了。以前是全国到处跑,现在成了欧洲美洲了。
好看吗?她给我看她手腕上的一串手链,看起来价格不菲。
这是他上次出差回来带给我的,说是从巴黎买的。
真漂亮!
可惜啊!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男人啊,再有心,也还是难免大意。
那不如下次他出差的时候,您陪他一起去。他工作,您购物,不正好。
不,我喜欢这房子。而且我认床,换了别的床我会睡不着。
当初这房子是我看上,然后买下来的。家里大到家具、小到碗碟,都是我一个人一件一件添置的。那会还没有发财的时候,就想着哪一天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好了,但到了真正实现的时候……
她停顿了下来。
您现在不幸福吗?
幸福,当然幸福。她扭过头来一笑,有你,这个好友,就更幸福了。
她的笑让我温暖,我很庆幸当时自己决定和她见面。
吃完了饭,龚姐说她去接个电话,我无聊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频道又在播失踪女大学生的新闻,我睏意袭来,靠着沙发睡着了。
梦里是那年高二四班的教室里,胡燃神神秘秘地从背后拿出一个大牛皮纸的信封给我。我把信封打开,里面是一本杂志。
我问她:这是什么?
她说:你翻到第八页。
竟然有我的照片。
胡燃笑嘻嘻地说:这本杂志举办一个“寻找封面少女”的活动,我觉得你肯定可以当选,所以就先斩后奏,替你报名了。没想到这么顺利就通过初选了。
我有点不高兴,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离开了。
胡燃追上来说:是我不对,别生气了好不好?我只是真的想看到你当封面女郎,这样我也可以去摄影棚里沾光。听说头奖得主还可以签约经纪公司拍广告呢!
梦醒了。龚姐不在,我的身上多了一条毯子。屋里很暗,我看了看表,已经八点了。
龚姐,你在吗?我叫她。房子大得竟然有回声,我有些害怕。
我望向中庭,没有人。我去厨房、餐厅,还有会客室,龚姐都不在。
龚姐。
我叫着她,然后走向二楼。龚姐你在哪儿?我要回去了。
走廊的灯光很暗,只有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里似乎有光,我一步步走过去。门虚掩着,我敲敲门,没人应。我推了一下,门开了。
是一间书房,应该是龚姐老公用的。我觉得不妥正想离开,可书架上摆着的一张照片,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是一张双人照。照片中的龚姐比现在年轻,这大概是十几年前的照片了。照片里搂住龚姐肩膀微笑的男人应该就是她的先生。
一种奇异的感觉忽然包围了我。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
我放下照片,从房间里退了出来。一转身,却在昏暗的走廊里,差点撞到了龚姐身上。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
小景,你怎么了?龚姐问。我在楼下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已经回去了。
没有,我摇摇头,我以为你在二楼。我说,我有些不舒服。
怪不得脸色这么难看,我看你睡着了,就没忍心叫醒你。后花园里有两株花快死了,我去培了培土。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过了这么久。
我得回去了。我说。
要不要我送你?龚姐说。本来还想留你住下呢……
可能是见我脸色不对,她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我快速地离开了。我开着车,又想起了那张照片,头开始隐隐作痛。
04
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和胡燃去了一个饭局。
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可杂志社的赵主编言辞恳切地求我帮他一个忙。他说:我明白你不愿意参加后面的比赛,也不想拍广告当明星。但这次活动最大的赞助商真的很看好你的,本来想力捧你,但也尊重你志不在此。所以只是希望你能去和赞助厂商一起吃一顿饭,见个面。而且如果你觉得自己一个人不放心的话,可以找个同学,和你一起作伴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的。
吃完饭后,这个事情就算了结了。你看怎么样?
我告诉赵主编,我没有兴趣,也不会去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景同学,你以为我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吗?我怎么说也是一个主编,学文学的。你以为我愿意做这些四处赔笑的事情?可现在杂志社不景气,没有销量,拉不到广告。到了生死边缘,才想出了这么一个选封面少女的主意,都是为了挽救杂志。我知道当然这些都和你没有关系,也明白是你的朋友帮你报的名。可不管是谁,当初报名表里“同意参加一切后续活动,并不会在中途退出”的一栏里,是打了勾的。现在都讲究契约精神,如果真要追究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联系律师的。现在只是让你去吃一顿饭,一顿饭而已。我也明白你担心的是什么,这个你大可放心。我用人格保证,不喝酒,也不会太晚。到时候我会亲自开车接送你和你的朋友。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燃。她说:对不起,本是一番好意,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我问她:那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她说:如果你不想去,那就不要去了吧!
可我又怕赵主编会打电话到学校,来找我的麻烦。如果被我父母发现,那就糟了。
当初胡燃瞒着我填报名表的时候,应该写了学校的名字,而且她说自己也实在记不清楚,报名表上是否真的有赵主编所说的那一栏。
我们都只是高中生,被狡猾的大人一吓唬,就立马什么主意都没有了。我和胡燃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我们俩一起去。
推开门,烟雾缭绕的私人会所包厢里,一双眼睛盯过来。赵主编说:那个人就是本次活动最大的赞助商。
十年后,我在龚姐家的照片里,见到了同样的眼睛。这个发现太奇怪。一个念头浮上了我的心头,我却无法解释。
从龚姐家回来的第二天,我就病了。我在家里躺了三天,期间龚姐打来了两次电话问我的情况。我告诉她,可能最近都不能去她那里了。她说没有关系,让我好好保重。
十年前的那顿饭我如坐针毡,平时话很多的胡燃也很安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吃什么东西。虽然赵主编已经说好不会让我们喝酒,但还是有两个中年男人让我们和他们碰杯,他们说,感情深,一口闷。我望向赵主编,他也只当没有听见,脸转到一边,假装在听他身边两个人的交谈。
就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男人说话了:你们行了,她们还是高中生,未成年人,怎么能喝酒?你们别过分了。
听他这么一说,那两个人悻悻地坐下了。
一晚上他没有再说话,但我感觉他的目光好像时不时地就会望向这边。
饭局结束后,赵主编已经喝高了,被同行的人送了回去,留下我和胡燃两个人。就在我们准备拦出租车的时候,那个男人的车靠了过来。
上车。他说,挺晚了,两个女孩子坐出租车不安全。我送你们回去。
我和胡燃并排坐在车后座。空气里都泛着昂贵的高级感。
你们的家在哪里?他一边开车,一边问。
本以为胡燃会回答的,她却没有。她的脸望向窗外,像是没有听见他的问话。
我告诉了他一个地址,在我和胡燃家的中间。我们骗家长说要去对方的家里做功课,所以车停在两家中间的地方最安全。
车停稳后,我和胡燃各自从车两侧的门下了车。那个男人也从驾驶室里出来。
谢谢你。他说,见到你,我很高兴。然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他说:如果以后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
他的表情很真诚,语气中也没有任何轻佻的意味。我却在心里笑了,我只是个高二的学生,怎么会有需要联系他的时候呢?
我接过他的名片,放进口袋里。后来那张名片被我弄丢了,我只隐约记得那是张纸质很好、很厚的名片。名片上的名字是三个字:尚朔青。
05
不好意思,尚总不在。
公司前台的小姐连我递过去的名片看都没看,就甩过来一句话。
那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知道。
我没有离开,就坐在写字楼电梯旁的长椅上,用随身带来的笔记计算机,处理一些工作上的邮件。从早上等到下午,依旧没有见到尚朔青。我肚子有些饿,可为了不错过他,也只好忍着。
大概是可怜我,或者是怕了我这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前台小姐故意在接一通电话的时候提高了音量。她说,尚总在休病假,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来公司上班了。
我从他公司的大楼里出来,已是傍晚,夜风凉爽。
我去了齐阿姨家。
我问齐阿姨:胡燃每个周一,都是什么时候回家?
齐阿姨有些奇怪地看着我,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她凑上来,抓住我的手。小景,你是不是想起来了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问问。
齐阿姨眼睛里的光灭了下去。她想了想,说:大概七点吧!她来店里跟我打声招呼,然后就自己在市场里随便买点东西吃。我的面包店到了晚上八点半关门。她吃完了饭,总是等在店里,然后等我关了门后,我们再一起回家。
每个周一都是这样?
是啊!齐阿姨说,你参加的文学社不是有会吗?胡燃不是总等你开完会,然后你们一起回家吗?
我点点头,在心里默默地盘算。
我的家离学校更近些,在学校和胡燃家中间。从我家到胡燃家还要再走十分钟左右。
哎,唯一一次没有和你一起走,就出了事。齐阿姨像是自言自语道。
还说什么面包店忙,需要回来帮忙,其实周一哪有那么忙啊!又不是周末。她每次回来,也都是在店里做功课。
我在脑子里快速地回想,高中的时候,都是七点早读、十一点四十放学;下午两点上课、五点四十放学;然后晚上七点晚自习、八点四十放学。不过因为每个周一是教师例会,所以没有晚自习,五点四十的时候就会放学。
胡燃失踪前好几个星期的周一,她都说要赶回去帮齐阿姨的忙。可齐阿姨说她大概七点多的时候才会到。从学校到齐阿姨的店,步行绝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五点四十离开学校,到了七点才会到面包店,这其中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她去了哪里?
我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又去了胡燃的房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地四处寻找。我的眼神扫过这间屋子的每个角落,最后停留在玻璃板下面压着的那首诗上。我看着那首诗,不妙的预感终于印证了。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那几句诗总共有二十八个字,其中有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人的名字:尚朔青。
我匆匆告别了齐阿姨,开车去了龚姐家。很多事情就像是散落在各处的珠子,现在总算都串起来了。
胡燃失踪前的那个寒假,我们一起跟着电视里的美食节目学做菜。我不小心被油星溅到,有些丧气地扔下菜勺说:我不做了。
胡燃拉过我的手,对着被油烫到的那一块呵了一口气,然后口气温柔地说:再试试嘛!你想,你以后可以亲手做菜给你喜欢的人吃啊!
我望着她,惊讶于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学校里,胡燃对男生们一直是不屑一顾的。当女同学在花痴某个长得有些像男明星的学长时,她也总是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我们每天都会聊很多事,八卦同学、讨论功课、研究杂志上最新的发型,还一起收集一个少女组合的海报。可她从来没有告诉我,她有喜欢的人。
那段时间,胡燃的眼睛里时不时会隐隐地泛起甜蜜的光彩,那也许是一个被我忽略了的信号。我隐隐地觉得,胡燃的心里,是有着一个人的。
而我,却从未对人说起这个。警察、校方,还有家长们,很多次都问我,胡燃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喜欢的男生,我却都坚定地说了没有。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做,也许是做为胡燃失踪前最亲近的朋友被采访这件事,带给了我一些满足。如果我告诉他们,胡燃可能在心里爱着一个男人,那么他们就会转移注意力,我也不会被人们看做是和胡燃最亲近的人。
我并不是想要得到人们的注意力,而是想要尽力保持我作为胡燃最亲近的朋友这个位置。
我爱胡燃。
是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对待胡燃,不仅仅只是友情。这个发现让我惊慌失措,我还没有想好该怎样处理这件事,胡燃就失踪了。我的生命里,也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像胡燃一样的人了。
06
我去找龚姐,小区的保安一见是我,没怎么盘问就放行了。
对讲机里,龚姐问: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最近都不会过来吗?
我说:我只是想你了。
进了门,家里好像还是只有龚姐一个人的样子。
我说:先生在吗?
龚姐说:去欧洲出差了,要下个礼拜才回来呢!她笑了,你怎么问起了这个?
我说:好奇而已,我们报社想要做一版幸福夫妻的访问,我想采访你们两夫妻。
真的吗?龚姐说,那太好了。我待会给他打电话,让他忙完就快点回来。
龚姐高兴地留我吃饭。我要打下手,龚姐不让。她说:你坐在那看看电视就好。
我打开电视。龚姐从厨房里系着围裙走出来,一脸抱歉地说:哎呀,本来想做松鼠鱼,再炒两个素菜的,可是配菜不够了。给超市送货的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只好我自己开车去一趟了。你在家里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龚姐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我听见车从车库里驶出的声音。
这还是我第一次单独待在龚姐的家里。我环顾四周,还是觉得大得惊人。
我快速地上了二楼,再次跑到那个书房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找什么。翻了好几个抽屉,一无所获。倒是最底层抽屉的最里面,放着一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卡片、收据之类的,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我随便翻了一下,一件东西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竟然是十年前,胡燃拜托我帮她抄写的一首诗。
笑眯眯的胡燃跑过来说:你能不能帮我抄一下这首诗。她拿出一张漂亮的信纸给我。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的字很好看,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
我想象着她把这封表达少女心思的情诗,作为别致的礼物送给她心上人的样子。
我的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了起来,尚朔青果然是胡燃的那个男朋友。那么,她那天去见的人会不会就是他?如果是这样,胡燃的失踪,一定与他有关。
这个发现远远超出了我能掌控的范围。我得报警。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刚刚输完解锁屏幕的密码,脑袋上就挨了狠狠的一下。
我顿时陷入黑暗。
07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渐渐成像的视线里多了两个人。龚姐和一个男人。那男人似乎是病了,脸色非常不好。十年不见,他胖了,也老了。
龚姐,我叫她。试着移动身体,我才意识到我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这是……我完全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龚姐脸上浮起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老情人相见了,分外激动吧!龚姐说。
都说过了,我不认识她,你为什么要这样?那个男人说。
他像个快散了架的沙包一样有气无力,看起来虚弱极了。
为什么要这样?
龚姐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龚姐看着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就是我先生,尚朔青。他是不是还和十年前一样英俊潇洒呢?
你别说了,你病了,我带你去看医生。那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哭。
我当然病了,大夫说我是癌症,只有一年好活了。你还不知道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了看龚姐,再看了看尚朔青。
胡燃在哪里?我问尚朔青。
他却哭了。
她就在这。龚姐说。她的眼神飘去中庭的方向,她就在那些花草下面。
她死了?我的全身开始颤抖。
是的,十年前就死了。我没想杀她的,不过说这些也没有意思了。你很快就会见到她了。
我这才注意到龚姐手里的刀。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记得那些我写给你的信吗?那就是我信奉的爱情,年轻的时候,为了成就他、成全他的事业,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结婚第二年,我怀孕了。可他说现在还不是要孩子的时候,我前前后后做了四次人流。后来成了习惯性流产,大夫说我的子宫壁已经薄得像纸,再也不能生育了。
多次的流产让我憔悴不已,人也不好看了。他却在这个时候有了二心。开始和小姑娘胡搞。高中生啊!十七岁的小姑娘,你也真下得去手。龚姐狠狠地瞪着尚朔青。
脸色苍白的尚朔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用他的名义把那小姑娘约了出来,我只是想好好劝劝她,让她好自为之、让她离开。没想到那姑娘伶牙俐齿,说得我实在是生气了……后来,我把那姑娘埋在家里。我告诉了他一切,他向我道歉,他说他那是一时糊涂。那之后好几年,一切好像都慢慢好了。他按时回家吃饭,那些花草也越长越好。我以为他天天看着那些花草,就会想起我曾经为他做过的事,就永远不会再背叛我。可日子长了,他老毛病又犯了。他享受那些泛着香气的年轻肉体,全然忘了我也曾经年轻过。
一年前,我被查出了癌症。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辛苦栽培的植物长成了别的掠食者眼中的珍馐美味。那些小姑娘们,她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别人辛苦半生才换来的果实,凭什么?
这个手链是我从一个小姑娘手上扒下来的,是他带她去欧洲的时候买的。他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也会喜欢这样的手链的。
龚姐慢慢地抚摸着戴着手链的手腕。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没有事业、没有孩子,连原本爱我的男人也失去了。我什么都没有,还快要死了。龚姐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如果我要死,那她们就都该死!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尚朔青说。
可我并不是她们。我对龚姐说,我从来没有和你老公,有过任何交集。
那你怎么会写情书给他呢?香喷喷的信纸,寄到他的公司,被秘书拦下来,直接送到我这里。信封上只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为了找到你,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呢!你的字迹,我记了整整十年。直到看到市里举办的硬笔书法大赛,你是第二名,照片和姓名被登在报纸上,才找到了你。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因为胡燃喜欢我的钢笔字,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练习。比赛的时候,我抄写的,也是胡燃最喜欢的诗。竟不知道,龚姐为了接近我,花费了多少周折。
凡是和他有过暧昧的女人,我都不会原谅。他是我的。
很快就结束了。龚姐站了起来,一步步向我走过来。
我闭上了眼睛,眼泪落了下来,胡燃,等着我。
龚姐却在我眼前倒了下来。
尚朔青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就在刚才龚姐说话的时候,他偷偷地解开了自己的绳子。他的手抖个不停,哆哆嗦嗦地用掉在地上的刀,帮我割断了绳子。
你走吧!快走,就当你永远都没有来过这里。
我逃出了那栋房子,天上是很美的月亮,我这才意识到,今天也是满月。
我报了警。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了两具横卧在中庭里的尸体。死因是中毒。警方发现了中庭花草下埋着的,已经变成白骨的胡燃的尸体。警方还在现场发现一封遗书。根据遗书里的线索,在龚姐的后花园里找到了两具女大学生的尸体。
十年前的高中女生失踪案和近期的两起女大学生失踪案成功告破。
我烧掉了那些龚姐寄给我的信。
火苗吞噬着一张张纸,发出细碎的咀嚼般的声响。我看着那些字字句句一点点化为灰烬。
最后一封,是龚姐分享给我的箴言,那是《圣经》里关于爱的描写: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08
2006年11月17日
今天我陪景宜去了一个饭局。
因为我瞒着她,替她报名参加比赛的事,她有些生我的气。因为这个,我不得不陪她去了那个饭局。我能看出来,景宜是非常不想去的。
我虽然心里有些抱歉,但我现在无比庆幸我自作主张替她报了名。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遇到他。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像是被雷击中。我说不出话来,整个晚上都是恍惚的。后来他要开车送我们回去,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我时不时望着他的侧脸,但每望一次,都要快点把头移开,我害怕我脸上的表情会出卖我的心事。我多么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啊!
后来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他给了景宜一张名片。这才明白过来,今天的主角不是我,我只是陪景宜来的。我只是一个陪衬。就像她是小姐、我是丫鬟,她是明星、我是经纪人的感觉。
我的心里有点失落。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得先把那张名片弄过来。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呢!
2006年12月5日
今天我鼓足勇气,给他打了电话。他应该有些失望,打电话给他的不是景宜。但我提出想要再见他,他居然也很高兴。挂了电话,我的心还是怦怦直跳。
2007年1月18日
今天景宜问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高兴。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敷衍过去了。我提醒自己要注意,别太忘形。
在心里,我对景宜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分享给你我现在的幸福。因为我答应过他,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他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地方,问我愿不愿意去。我隐隐约约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虽然心里有些紧张,可我还是说了“愿意”。
2007年2月14日
也许是因为过年,他好久都没有跟我联系了。他交给我的手机,我从来都没有在学校里拿出来过,只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才开机。最近半个月,它死气沉沉,我想,他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2007年3月12日
今天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最最重要的一天!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但是我还是做了。
他带我去了一个公寓,然后,他开始吻我……有些疼,我哭了。他很感动,抱着我说,会好好珍惜我。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我情愿相信是真的。他说,他早就不爱自己的妻子了,可是每个周末都不得不陪着她。不过,他周一的傍晚是我的。他把公寓的钥匙交给我,他说,这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乐园。
09
合上那本日记,龚淡菊脸上的表情更加复杂了。她开始感激自己在那女孩的书包里找到了它,读了几页,她心中因为女孩的死所带来的负罪感,已经少了很多了。
她面无表情地把那本日记扔进了火盆里。
然后她走到窗口,拉上了窗帘。六月了,天气很热,可她却有些发冷。
她得先去洗个澡,把这惊心动魄的一天都洗掉。她累极了,但中庭新栽种的花真是漂亮。
她在浴室的花洒下,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明白从此以后,家里不能再请钟点工和园丁,也只有她能照顾中庭里的那些花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