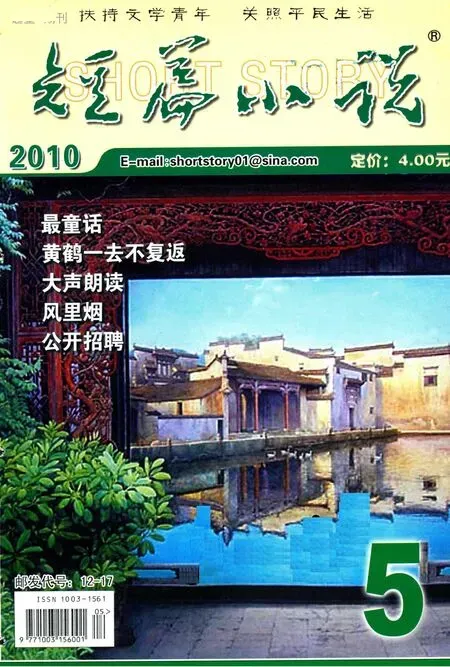坐庄
2019-07-04李业成
◎李业成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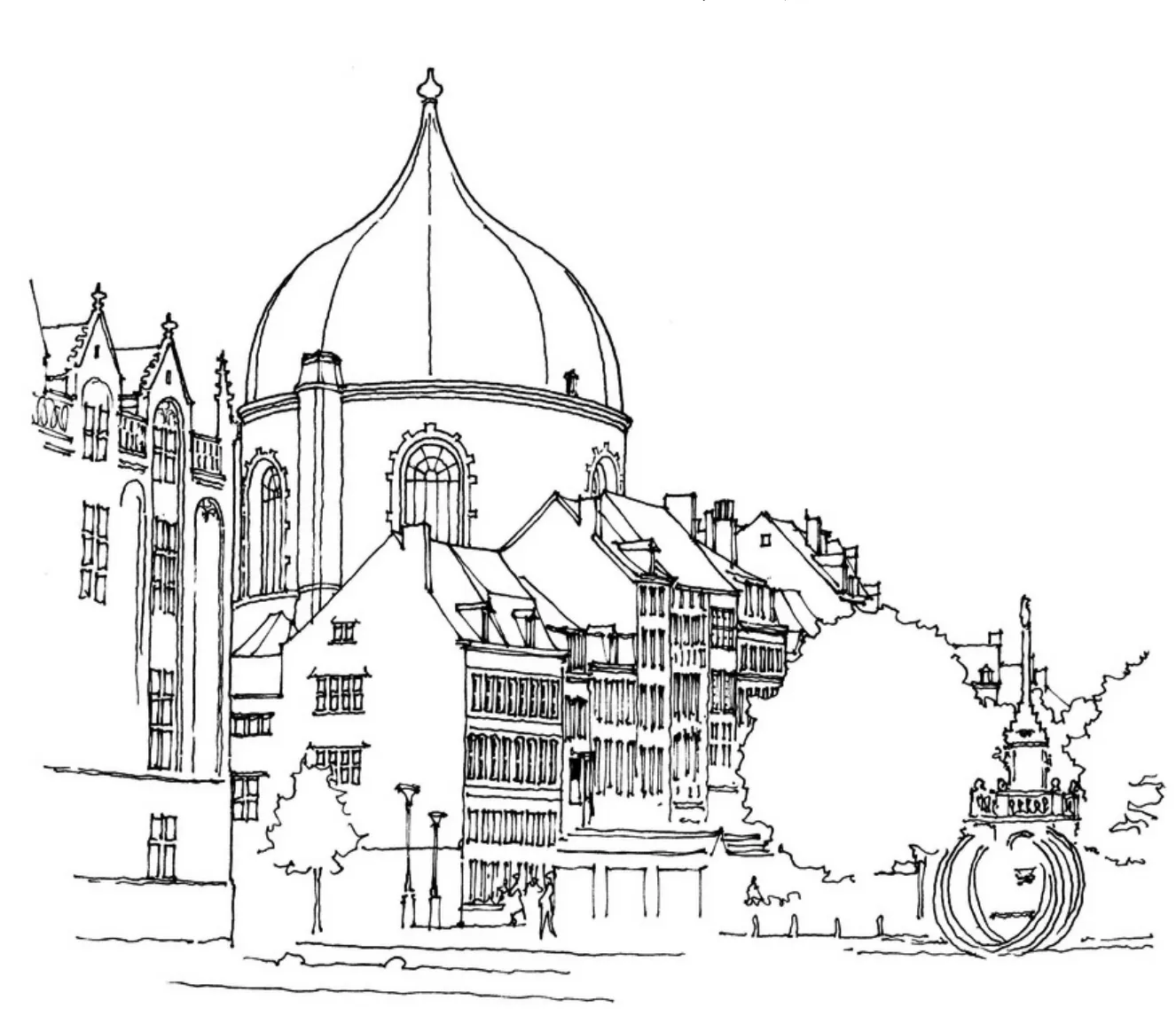
山西头村是个杂姓庄,全村有十四个姓,以高、徐、李、王为四大姓氏,村子又是个大村子,这就给坐庄订亲创造了条件。坐庄订亲很有意思,比如老高家与老徐家斜对门,老高家的儿子与老徐家的闺女出门就互相瞅,从十五六岁开始瞅,瞅到十八九岁,眼睛对光了,便结连理了。一个村子里的男女,互相看着对方顺眼,便想办法接触,一个村最方便了,最后恋爱成了,就不再藏着掖着,公开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众人就是一杆秤,村里人把他们双方衡量一番,都说好,这桩婚姻就以“双赢”的结果在村里吆喝起来。如果有人问闺女找婆家了吗,回答说找了,哪庄的,坐庄,问的就会道贺,坐庄错不了,知根知底,家底不用说,人品一定靠得住。如果问儿子订亲了吗,回答说订了,哪庄的,坐庄,问者也一定会道贺,坐庄的闺女知根知底,作风肯定没问题。一个村里生活,谁家的儿子谁家的闺女,谁家什么门风,彼此都了如指掌。老王家的闺女,前两年还不起眼,忽然出脱得亭亭玉立,立刻招人眼光了,又听说那闺女勤快过日子,这便动了心,找人去说,找贴己的人去说,一说就成了,成了马上订亲,这个闺女十七八岁就被坐庄一个小伙子占下了,或者这个小伙子十七八岁就被坐庄一个姑娘占下了。所以外村的小伙子发牢骚,说你们山西头村好姑娘都留下自己用,虾头蟹腚往外嫁。这话有点不中听,但也有一定的事实。平时走在街上,—个小伙子一个姑娘本不相干,忽然有一天就成了一对了,将来要一个锅里摸勺子,既正常又不可思议,早晨还遇到老王家的丫头与老李家的小子在井台上打水,还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人,过午村子里就传出消息,说老王家丫头与老李家小子订亲啦。婚姻这事就这么简单,吃顿饭的工夫就决定了一辈子的事。实际上他们双方互相观察很久了。不过,这一类型的坐庄属于自然婚姻范畴,我要说的坐庄是一种婚姻方式,没有儿子的人家,把闺女嫁在坐庄,把女婿当儿子使唤,女婿门前门里全部“三包”,连丈人丈母娘养老送终也包了。
婚姻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倒插门”(也叫招养老女婿),男方到女方家里落户,有人称之为给丈人门上扎觅汉。扎觅汉是日照一带的说法,就是当长工的意思,过去穷人在地主家做长工叫扎觅汉。倒插门不是一种好婚姻,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项,双方都要降低条件,否则不好谈。女婿要到丈人门上生活,要看丈人丈母娘甚至丈人一家人的脸色,身分自然降低难免受歧视,只有条件差说不上媳妇的男子才肯倒插门。婚姻这东西也是要讲求平等的,平等是根基,这个平等就是人们常说的门当户对,不能差得太大,差大了让人担心不稳定。婚姻是一件大事,买把菜都要横挑竖挑,婚姻大事岂能不挑不拣?倒插门是个两利工程,也是个两不利工程,两方都要受些损伤,在双方心理上没有赢家。婚后如果遇到强势的丈人丈母娘和强势的媳妇,这个女婿就惨了。坐庄这种婚姻方式改善了倒插门这种婚姻方式,所以极受推崇。
2
老刘家,男人外号刘锅腰,不用说,这个外号是与身体对号的。刘锅腰叫刘好,他的名没人叫,村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名,一说刘锅腰,连七岁的娃都知道。有一回刘好家里来了一个邮包,邮递员从村东头问到村西头,问刘好在哪里住,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因为街上遇到的全是妇女和孩子,他们都不知道刘好为何人氏,幸好遇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知道刘好家在哪里住。邮递员每次进村,谁家来了邮件或钱,都要送到门上,在大门外喊户主的名字:“徐茂山,来钱啦,拿手戳来!”一群孩子往往跟着邮递员屁股后面穿街过巷,帮着喊。刘锅腰家还没到,孩子们就跑在前面喊上了:“刘锅腰,拿手戳来!”他们第一次知道刘好就是刘锅腰。刘锅腰拿了手戳取了邮包,然后回家了,孩子要送送他,于是一同喊——
锅腰子畸,
锅腰子弯,
锅腰子骑驴不见天。
锅腰子不敢仰着睡,
仰着睡觉打旋旋……
这首童谣是山西头村的大人们敬献给刘锅腰的,作为一种知识趣味,纳入小孩子学前启蒙教材,所以村里小孩子都会唱这首童谣。虽然没有乐谱,可背诵时的特别节奏,听起来跟唱差不多。
刘锅腰在村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与人很难沟通,是他自己把与人沟通的渠道闸死了。他的性格很特别,与人说话不能一问一答,别人说完一句要等半天,半天他才回话,就好比吃饭,他老是担心这饭里有钉子或沙子,必须先挑挑看碗里有没有钉子或沙子,他老觉得别人的话里有钉子或沙子。这样村里人都害怕和他说话。这正好,没人与他说话他一百个放心,别人一与他说话他便以为别人要嘲笑他。即使表面上不嘲笑他也会拐着弯儿嘲笑他,他总认为别人有很多嘲笑他的理由。刘锅腰年轻时说了一个漂亮媳妇,漂亮媳妇生了一个漂亮闺女,漂亮媳妇被他看得牢牢的,漂亮闺女不能一辈子不嫁人。他本身是个锅腰,身材又小,龟得厉害,九十度以下,走路就是这个样子,但头还要费力地抬起来,因为只有抬起来,才能平视前方。他的那个头好像特别累,如果与身子一同保持九十度往前伸才能不累,可他必须抬起头才能看到前方,那脖子好像牛筋一样硬。见他来了,小男孩子便立刻要唱童谣,当妈的便狠命捂住小孩子的嘴,等刘锅腰过去才肯松手。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当年说了那么一个俊俏媳妇呢?这在村里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流行的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早年男女不兴见面,媒人一手操办。但刘锅腰当初相亲丈人门上有人来见了,媒人让刘锅腰操碓舂米,人坐在北墙一个凳子上弯腰舂米,小白脸眉清目秀,哪会想到是个锅腰。等女方过了门,熬到半夜,闹房的人都走了,进来一个锅腰关门上床要睡觉,晚了,这就好比鱼肉上了菜板。
刘锅腰一辈子就生了一个闺女,没有儿子。闺女生得实在漂亮,村里一些嘴不干净的男人常犯嘀咕,刘锅腰什么本事,这么一个陀螺身子,咋弄出这么一个漂亮闺女。刘锅腰的闺女叫刘贤香,今年二十五岁,十七岁那年就订的亲,坐庄的,姓王,小伙子叫王培囤。刘贤香中等偏高一点的个头,对女人来说,这是最理想的个头,人们说媳妇本来喜欢高个子,可有人硬说高个子女人福薄,中等个最好,硬把女人的身高差别给扯平了。有些人就是迷信,对比了村里几个高个子女人,发现个个福薄,于是当了真,对高女人又喜欢又担忧。人的心态就这样作怪,冒尖的总要给它掐去一块。刘贤香是最理想的个头,也是庄户人最喜欢的身材。庄户人最喜欢的女人的身材是硕壮,肢体宽大,男人能在上面打场。刘贤香长得是那种方方正正型,方方正正型女人就是脸方方正正,两肩方方正正,臀围方方正正,刘贤香就是这样一个方方正正型女人,但腰凹得狠。刘锅腰养了这么个漂亮闺女又添心病,老惦记给她找个什么样的人家,那年代吃国库粮的最为吃香,凭女儿这脸蛋这身材,找个吃国库粮的不是没有可能,但刘锅腰还有一个小算盘,他没有儿,想招一个上门女婿。招上门女婿也不难,这么漂亮的闺女不怕没人愿意倒插门。可刘锅腰的小算盘打得过精过细,招上门女婿倒插门这种婚姻双方都要让步都要吃亏,可以叫“双亏”,再说,招养老女婿对男女两个家庭都不是光彩的事,招女婿上门只有无儿的绝户头才不得不选择的办法,倒不如把闺女搁坐庄。
3
倒插门是乡间的一种婚姻。通情达理的女方父母还好些,有的直接给人改了姓,生的娃要跟女方姓,很让男方难堪。这样的婚姻都是男方考虑再三最后一咬牙才做了倒插门。而坐庄和正常婚姻没有什么差别,效果与招养老女婿是一样的。凡刻意把闺女搁在坐庄的,都是没有儿子的人家。没有儿子不仅养老是个问题,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问题,可以讲男女平等,但不能不讲男女差别,农地里的脏活重活非男人莫属。一个农业家庭没有男人那便非常艰难。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土地承包到家庭,更显出男劳力的重要性。男人能推大车,男人能杠子上肩抬机器打麦,男人能抢水,男人能做女人体力无法承担的体力活。还有场面上的事,也非男人莫属。在人民公社时代,确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吃的是大锅饭,但一个家庭的男劳力同样不可缺少。那个时候农民除了在生产队里分口粮,自己也有自留地,还有菜园,送粪这样的重体力活也必须由男人来做。男性与女姓的差别表现在体力劳动上是最明显的,很多男人的活女人连动都不能动。很多没有儿子的家庭便早早地在本村物色一个女婿,早早地就给闺女订亲,订了亲,这个未来的女婿就等于拴到家里的一头牲口,不,比养牲口更划算,养牲口还要喂它草料,即使一把草料,你不喂它它也不给你干活,而坐庄找个女婿则不同,丈人家里有什么重活累活,喊一声,立刻就到,自家的活先放下,丈人门上的活优先,而且不用管饭,甚至连茶都不用管,给丈人家干活,回自家吃饭,丈人家可以锅不动瓢不响。而且不用过问,须干的活,闺女婿一定会保质保量干得圆圆满满。别说媳妇还没娶到家,就是娶到家,老丈人家的事也要赴汤蹈火。再说,闺女婿半个儿,论亲情论责任也没有二话。皇帝对大臣天天念“忠”字经,不忠的家伙层出不穷,而闺女婿才是真心保主啊。不只是丈人家有什么脏活累活重活要上,丈人丈母娘有个头痛脑热,冲在最前面的也是闺女婿。闺女搁在坐庄,闺女婿比儿子还好使,而且长期有效,还包养老送终。如果搁在外村就大不相同了,闺女婿走丈人家是客,要客客气气,找来帮个工还要好酒好菜伺候,丈人丈母娘还得客客气气地不停地提示“歇着点”,真的歇了,又抽烟又喝茶,老丈人老了干不动重活了,可偏偏又是个急脾气,眼着的闺女婿烟一支接一支地抽,茶一杯接一杯地喝,急得干搓脚。坐庄女婿,哪有这些客套,说干就干,别说抽烟喝茶,饭不吃也要先把活干了。
山西头村是个杂姓庄,坐庄这种婚姻方式很多。这种婚姻往往双方都满意,因为一个村子知根知底,优点全部彰显,缺点反而忽略,何以把缺点忽略了呢,有道情人眼里出西施,实际是熟人眼里出西施,媳妇本来不怎么漂亮,可天天见着她,看习惯了,她就好看了。女婿本来也不怎么优秀,可丈人丈母娘就是喜欢他的那个勤快,脾气那个好,闺女嫁这样的男人一百个放心,所以看女婿就越看越好。比如王培囤,人长得并不帅,帅小伙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身高必须在一米八开外,否则即使国字脸也称不上帅。王培囤生了一张四方大脸,却是个矮脚虎,他那种个头按说是不好找对象的,可刘贤香就忽略了这一点,就觉得他好,从她脸上的幸福表情可以证明。刘锅腰家一有什么重活累活脏活,不用兵符,救兵立刻就到,到了就干,干完就走,连饭都不吃,甚至连一杯茶都给老丈人省了,这便很让刘贤香感动。还有他干活的那种麻利劲,那种架式,那种不疼力气的拼劲,都让刘贤香看着喜欢,将来依托这样的男人她感到踏实。庄稼地里的男人就在一个勤,勤就有饭吃,好吃懒做的男人在哪里都无法混,在庄稼地里尤其没法混,哪个女人跟了一辈子生气受累。想到以后,她便越发喜欢王培囤了。刘锅腰想的与女儿想的不一样,他就是要找一个无偿劳动力,王培囤最诚实最肯出力,仅此而已。
刘贤香十七岁那年就订了亲,王培囤比他大三岁,那年是二十岁,二十岁就成了刘锅腰家的长工,什么累活脏活重活一喊就到,不喊也到,什么时间什么季节什么天气王培囤就知道刘锅腰家里有什么活要做。丈母娘百倍热情,而刘锅腰不冷不热,你想娶我闺女,干点活算啥。
刘贤香十七岁那年,还没觉得出这个叫王培囤的人多亲,也没觉得这个人多重要,可过了十八岁,女孩子一岁成精,知道疼人了。王培囤人长得虽不帅,但好品格村里没有不夸的,这些夸赞刘贤香都能听到,村里人的夸赞使刘贤香对王培囤的爱不断加分。刚订亲的那阵,村里的一群小男孩淘气,常常跟在刘贤香屁股后面起哄:“大站媳妇,大站媳妇。”大站是王培囤的小名,一个村,连小名都知道,大站媳妇便回头追打这些淘气小子。这些小子更来劲:“大站是个大鸭子!”男人的鸡鸡叫鸭子,刘贤香羞红了脸。这些小男孩并非信口开河,夏天大男人小男人都脱光了一起在河里洗澡,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给这些小男孩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坐庄也有一个不好处,那就是知道的太多太细,不但连小名都知道,连身上的胎痣都知道。那年代,不只是男孩子光屁股长大,很多女孩子光屁股光到八九岁,直到懂事了,知道害羞了,没衣服死活不肯出门,大人们才用姐姐替下来的旧衣服给她改条小裤头,穿上这条小裤头才肯出门。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提,不知是哪个“提”,庄户人起名不可能起出“娣”这般洋气的名子,应当是提手旁的“提”字,提菜篮子,提草筛子,表示勤快。小提小时候没人看,大人们都下地干活了,把她放在院子里的一张破席子上哭,小孩子气性大,气出一个大肚脐,别人的肚脐都是凹下去的,她的肚脐却是鼓起来的,而且很大,有成人的一截大拇指那么大。小提八九岁还光着屁股,肚子上的那个大肚脐给所有孩子的印象都特别深。小提长到十八岁,父母看中了大站的弟弟二站,也要来个坐庄。二站不干,他想起小时候见过的小提的大肚脐,那个大肚脐睡觉一定硌人。这门亲事没成。
刘贤香长到十八九岁便是个庄重的大姑娘了,十七岁残留的那点稚气没有了,小男孩们都知道放尊重了,十来岁的男孩子开始懂得对异性的欣赏了,见了这个漂亮大闺女自己倒先害羞了。刘贤香这会反倒希望从这些男孩子嘴里听到胡话。美对异性是有一种震慑力的,能让人变得规规矩矩。
4
贤香十九岁时就想嫁了,喜欢接近男性,王培囤是她最容易最合理由接近的男性。但刘锅腰眼毒,贤香心里害怕。王培囤到她家里干活,她便瞅着爹的眼,趁爹打盹时,便上前帮王培囤。实际帮不上什么,只是给他递个擦汗毛巾之类。她就是想接近他,想跟他说话,想闻他身上的汗味。可刘锅腰像猫一样灵敏,闭着眼都能看世界。刘锅腰一整理嗓子,刘贤香立刻变成淑女,站在王培囤一边,不动手也不动嘴,只看他干活。这对年轻人亲切得像兄妹,却不能像兄妹那么放肆,他们身后老是有刘锅腰那双即使闭着也能看事的眼睛。女大心事大,刘贤香转眼二十三岁了,转眼二十五岁了。而王培囤二十八岁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小伙子二十三岁之前差不多都完婚了,过了二十五岁没完婚的都是没有说上媳妇的,二十八岁没结婚的都是光棍。王培囤的父母急啊,他们当初很满意这门亲,是看中了贤香人长得好脾气又好,可万万没想到把儿子拖到这么大,心里恼,可又不敢得罪刘锅腰,刘锅腰与正常人不一样,不能惹。他们便通过各种亲朋关系去说情,可刘锅腰就是不给一个明确的完婚日期。难道这锅腰子想耍赖不成,锅腰子真的有锅腰子的算盘。王培囤给他家做了那么多年的长工,这些都不在他心里,他想悔婚,一直想。王培囤是个老实人厚道人,依然真心保主,为老丈人一家敢于赴汤蹈火。
伏天,白天实在是太热了,要往地里送车粪,蹲下身还没拾起车襟,汗就哗地下来了。伏天往菜园子里送粪是准备种大白菜的,大白菜喜欢大肥水,家家户户都要种很多大白菜,从秋后一直吃到第二年三月。大白菜在伏天种,从整地送粪都是一件苦差事。伏天易中暑,白天太热,没人敢行动,都瞅早晚凉快时整地送粪。打王刘两家订了亲之后,每年的这个活都是王培囤的,贤香母女做不了这个活,刘锅腰自然也做不了这个活。王培囤因为还要忙自家的活,便瞅晚上往地里送粪。农历六月十五,月光明亮,王培囤想借着月光给丈人家送粪。他吃过晚饭,从自己家里推了大车,推到刘锅腰家的院子里,装上粪,准备往地里送,粪白天他过来给摊开晒干倒好了,种地不能用湿粪,湿粪会招蛆或导致菜苗烂根。他正往车上装粪,贤香从闺房里跑出来,夏天穿得少,下身穿一个短裤光着雪白的大腿,上身穿一小短衫,小短衫四处都短,短得没有袖子,短得没有领子,短得差点盖不住腰。
“我给你拉车吧?”贤香问培囤。
“这……”培囤先看贤香,又看丈母娘。
刘锅腰偏偏在这个时候整理嗓子。贤香大热天像掉进了冰窟窿。
“去吧!”丈母娘头一回一言九鼎。
5
王培囤和刘贤香往田里送了三趟粪。回来还要送,被丈母娘阻止了。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活也要一点一点地做,不能一口气做完,剩下的明天做。丈母娘特意在院子里放了一张茶桌,打开门头灯,院子里一片雪亮。其实不开门头灯用月光照明更好,丈母娘不懂这个情调。刘锅腰在屋里睡下了,不知真睡还是假睡。
丈母娘亲自给女婿倒茶,王培囤慌忙隔手。
夏夜很静,三个人在院子里喝茶,凉风下来了,吹得人很舒服。王培囤和刘贤香干了半晚上的活,出过汗之后,凉风一吹非常振奋。
“你今年多大啦?”丈母娘忽然问王培囤。
“二十八。”王培囤回答。
“哦……”丈母娘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年龄,她话里有话。都订亲八年了,人早已是你的人,咋这么老实?
“真是个老实孩子,”丈母娘叹了一口气,“我乏了,你们坐吧。”她想把时间交给两个年轻人。
刘锅腰忽然在屋里整理嗓子,并且咳起来了。王培囤看了一眼刘贤香,“我回去了,不早了。”
女婿是个实心眼,点不透,闺女却是个一点就透的人。
第二天晚上接着送粪。一个推车一个拉车。昨天是六月十五,今天是六月十六,最圆的月亮不是十五而是十六,一出门,遍地都是亮的,街两边的树筛下一地树荫,树荫在月亮地上画图,画得真好看,像剪出来的,像贴在地上的大窗花,地上的树影随风移动,神秘而有趣。山西头村有一条东西大街,接近村东头的地方有一个坎,这个坎不小,劈成一个漫坡,因为夏天水冲,便用石头铺成,成了一段石板路,不知是哪一辈人铺的,都是现在的人搬不动的大石块,石块表面磨得像鹅卵石面一样光滑,不是行人脚底磨的,是一年年发大水磨的。夏天经常发大水,这些石面总是干净的。路北是老李家的院墙,院子内地势特高,两棵大栗树如伞一样张到墙外,夏天的晚上女人们都喜欢坐在这树下乘凉。树下墙根还有一个石头大马槽,也是现代人的膂力搬不动的,孩子们白天都在大马槽上砸瓦片,忙得像个加工厂,晚上则爬到马槽上玩。街上乘凉的多是妇女,她们光着大腿,穿着短衫,借夜色掩护都想少穿,大热天身上多个布缕都是负担。
王培囤与刘贤香送粪必须要经过这个街口。纳凉的女人们老远就发现他们来了,按乡间的伦理,这些年轻的妇女大多要叫嫂子。其实这些妇女中的小媳妇很多比王培囤小,也比刘贤香小,以她们的年龄不好意思挑逗这对未婚夫妻,但不妨跟着起哄,逗乐的是那些年龄比王培囤大的妇女。
“培囤,你好福气,昨天晚上没干够啊。”小媳妇们都忍不住要笑,她们都知道下面没好话。
“培囤,今年多大啦,还等啥?”女人们借着月色的掩护,肆无忌惮,“草垛里,河沙里,都一样,比被子窝还暄乎。”
“放下车子,月亮地里就行啊。”女人们注定不会放过他们,“贤香,培囤傻你也傻呀?你教教他!”
女人们还说了什么,走远了,两个人听不见了。这一段路平,不用拉车,拉车的绳搭在车上的粪篓里。平时王培囤一个人送粪,车子走得很快,推车有一股前力,让人无法不快起来。菜园在村外的河边,这段路还没有上坡,其实是不用人拉车的,稍有点儿不好走的路段,刘贤香便象征性地拉一拉。
出了村有一条河,没有桥,要趟水过河,贤香立刻从车上拾起拉绳,把脚上的凉鞋脱了扔到车上,赤着脚才能使上劲。如果没人拉车,培囤推车过河是要费些力气的,有人拉车,很容易就过河了。过了河有个小杨树林,小杨树林下是白沙,贤香把拉绳重新搭在车上的粪篓上,从车上拿过凉鞋,在河水里冲了冲,穿在脚上。她发现小杨树林里有一男一女,忙指给培囤看,那一男一女抱在一起,见人也不躲。村外的这条河是从东南方山里流来的,是一条倒流河,河都是由西往东流,这条河却从东往西流,要说山西头村有什么特点的话,除了坐落在一座大山的西头之外这条倒流河便是最大的特点了。出了村,河的上一段,被村里人称之为东南河,村里的菜园子就在东南河的左岸。
此时的菜园子都腾出来了,土豆早刨回家去了,芸豆架黄瓜架也拔了,就等着种白菜萝卜了。昨天晚上送了三趟,今晚这是头一趟。王培囤把粪倒下。
“我不干啦。”刘贤香说。
“为什么?”
“不想再遇到那堆女人,嘴太臭。”
6
菜园子边就是河,几天没下雨,河水便流清了。前一场雨发了大水,把河底豁出一条沟来,又在河右岸拥出一块新沙滩。刘贤香把凉鞋扔在水边,在水边的沙坎上坐下,两条腿放进河水里,被河水冲着,她说:“真舒服,我今晚不走了。”村外寂静,河水流动的声音很响,月亮比先会儿升高了,更亮了,贤香脸上很兴奋。她说怕再次遇到街上的女人,那便只有等夜深了街上乘凉的女人们散了。王培囤上身穿一件蓝背心,下身穿一条白裤衩,背心早已汗湿了,倒下粪后便脱下来搭在肩上。他在河里弯下腰,把肩上的背心拿下,在河水里搓了一把。
“洗不掉的,明天我给你洗。”刘贤香说。
“你坐着,别乱走。”培囤说。
“你去哪?”
“上游,洗一洗。”
就在这里洗,我不看,”她瞅着他,月光下,他看着她,那声调那脸色都在向他撒娇,“我才不稀罕看呢。”她扭过身。
培囤还是往上游走了二三十步,脱了,把自己浸在河流里,洗完了,穿上衣服,回到刘贤香身边,刘贤香用手拍了拍身边的沙,说,坐这儿。
两个人坐在一起。月光更亮了,照在河上,照在沙滩上,照在河两边的庄稼地里,照在对面的山上,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河水流动的声音。
“那堆女人嘴真臭。”贤香说。
“是臭,她们说月亮地里就行。”
话没说完,背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我娘说你傻,我看你一点都不傻。”
王培囤笑了,展臂去揽她,她顺势倒在他的怀里。她说,我也要洗洗。他说,我还到上游去。她说,不用,你背过身就行,不准看。
刘贤香起身,也到了上游,但只在不到十步远的地方,脱光了,下到河里,河底被前一场大雨豁出了一道沟,水深且急,人躺下能没过身子。贤香先是捧着腹在河水里蹲下,她感觉脚底的沙在抽,脚底往下陷,因为脚底水流受阻,冲力就特别大。她试着趴下,身子下面的沙子在抽动,痒痒的舒服。她把头扎进水里了,小时候在河里洗澡,七八岁的样子,男孩女孩都还不知道避讳,女孩子也学男孩子在水里扎猛,贤香也扎过,她一扎猛子,立刻想起了小时候。小时候男孩子女孩子全光着屁股在河里疯玩,其中就有培囤,那时候叫大站,可一转眼,便是二十五的大闺女了,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孩子应当好几个了。她在水里仰过身子,让身体的另一面接受水下沙子的抽动,而身体的上一面,接受河水光滑的冲抚,真快活。她把双手垫在脑袋下面,长发像被水流冲击的岸边的水草。她的双手垫在脑袋下面把头托起来,对着王培囤,王培囤却背着她,她喊他,他回过头。她向他招手,喊他过来。
王培囤的背心丢在河沙上,只穿了一条裤衩。
“你试试,这水多滑呀。”她伸出手,拉着他的手,“来,上来试试。”王培囤行动迟缓,被贤香一把拉到自己的身子上面,问他:“你恨我爹吧?”
“不恨。”
“撒谎,我都恨你不恨?”
“恨。”到底是个实在人,“不过,我相信你,是我碗里的……”贤香一把抱紧了他,恨不得在他肩上咬一口,真咬了,培囤直喊疼。
……
两个人上了岸,躺在前一场大水拥起的沙滩上。细沙软得像毛毡,两个人各堆起一堆沙作枕头,贤香一丝不挂,月光下白花花的身子,她感到屁股下面的细沙像自己的皮肤一样软。月光下贤香的一双眼睛扑噜噜闪动。她拉过王培囤的一只手,放在胸脯上,她的胸脯丰满柔软光滑,湿漉漉的,然后牵着这只手往下探,停住了,按了一下,说:“今天晚上嫁给你。”她闭上眼。
7
第二天早晨起床,贤香的娘一见贤香的体态和眉眼,便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四个月过去,贤香的娘忽然告诉锅腰,说女儿有了,四个月大了。刘锅腰跺脚,晚了,他的算盘到底打错了。憋了半天,终于发话:“马上办了。”
说办就办,王培囤一家早等急了,嫁妆铺盖五年前就准备齐全了,新被子新褥子新床单都在箱子里压着。嫁妆是五年前上的漆,现在要重新漆一遍,图的是喜气新鲜。一张楸木抽屉桌,两个梧桐大木箱,一对沙柳棒盒,两张柞木方杌,全部重新上漆,好几条街全是新家具的油漆味。这油漆味告诉全村的人,王培囤与刘贤香要结婚了。
结婚这天,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按风俗落日时分新媳妇过门。乡间婚礼都是在日落时分举行,无论坐庄还是外庄,外庄的按里程计算,掐准时间发嫁,无论远近,进村时间都在日落时分。村子里的锣鼓家什迎出村,欢天喜地,把新娘子迎进村,然后过门,过门是最重要的婚礼仪式,新娘子脚不踏地,要买三张新席子,从大门外铺到大门里,再铺到二门里,这时新媳妇脚还不能踏地,由新郎抱起新娘子进洞房,直接抱到床上,然后新媳妇坐床,闹房的看新媳妇的挤得水泄不通。三张席子远远不够用,新娘过门,前脚踏过去,后面的席子又卷起放到前面,那个卷席铺席的人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农历的十月二十六,好日子,本来还穿不住棉袄,新娘子刘贤香却身穿大红袄,脸红红的,俊极了。贤香怀孕四个月,脸上还没有起斑,一般人看不出破绽。贤香一脸的笑,坐庄出门子,眼前老的少的一张张都是熟脸,一张张脸瞅着她笑,她对着一张张脸笑。那些女人们,什么事都瞒不过她们,这么庄重的场合也不妨打趣,“贤香,急啥呀,再过两个月,抱着娃过门。”贤香听见了,假装听不见,她一脸的笑,她知道,女人们不是在笑话她而是祝贺她,她赢了,最主要的是培囤赢了,她替培囤笑。
看媳妇的人都说刘锅腰有福,刘锅腰的算盘打对了,把闺女搁坐庄,女婿当儿子使,王培囤一定比亲儿子还孝。
笑得最好的还有抬嫁妆的人,抬嫁妆不但管酒管饭大鱼大肉伺候,每人还有十块钱的喜钱。那时十块钱是好钱。五里路十块钱,十里路十块钱,十五里路还是十块钱。可给刘锅腰的闺女刘贤香抬嫁妆,不但不出庄,而且对门,几十步远,刚上肩便落肩了,这十块钱揣进兜里像捡的一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