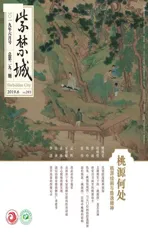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唐寅诗书画里的桃源仙乡
2019-06-26曾诚
曾 诚
唐寅,明代中期吴门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名列「吴门四家」、「吴中四才子」,「点秋香」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他早年因获得南京解元而春风得意,紧接着又因科场舞弊案案发而黯然失意,短暂人生中的大起大落造成了唐寅亦仕亦隐的矛盾思想,而这种思想无时不刻地表现在他的诗词、书法、绘画中……
唐寅是中国书画史上大名鼎鼎之人,他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为「明四家」,也叫「吴门四家」,是明代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同时又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合称为「吴中四才子」,是明代中期江南文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唐寅本人亦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常常在画上自诩「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就是这么一个江南才子,却因「场屋案发」身陷囹圄,直至罢黜功名贬为「浙藩小吏」,备尝坎坷。
民间由于仰慕欣赏唐寅之才华,托名其人敷衍铺陈了「三笑」、「点秋香」等戏文故事口口相传以讹传讹,一方面使得唐寅的风流形象妇孺皆知,另一方面也使得唐寅的真实形象暧昧斑驳。本文拟就唐寅诗书画里的「桃源之念」谈谈唐寅书画艺术中的出世与入世问题。
桃花庵里桃花仙:富贵梦与清贫乐
唐寅是很想做官的,这也是古代读书人的一个共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甚至以「美人」自况,希望自己的才艺能够得到君王长久的青睐与宠幸。这样的例子很多,唐寅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甚至情况还非常特别。唐寅之父唐广德在苏州闹市经营一家酒肆,迎来送往招徕四方过往宾客,一心「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将振兴家门的希望寄托在了唐寅身上。唐寅本人主观上也有这个强烈愿望,他在《与文徵明书》中说「获奉吾卿周旋,顽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很直白地表述了自己的功名之念。由于勤奋与聪颖,唐寅的学业似乎也较为顺利,十六岁参加苏州府试高中第一,二十八岁时南直隶乡试高中第一,二十九岁上京赶考会试。他的好友,同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从成化十六年(一四八〇年)到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年)连考了五次乡试才中举人,其后七次赶考会试无功而返。另一好友,同为「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考到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九下科场,次次名落孙山。就这一点较之其他士林中人,唐寅是很幸运的了,他在《夜读》一诗中说:「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夜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其读书显名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
前面说到很多读书人常怀功名之念,但又常有山林之志,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陶渊明,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尽显名士风流,而他又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则尽显名士风骨。李白甚至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文人狂放不羁的人生观做了很好的注解。这种放诞任情、狂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唐寅身上也有,而且还很有特点。《桃花庵歌》是带给唐寅极高文坛声誉的作品,现将此歌抄录如下: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里将「老死花酒间」与「鞠躬车马前」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人生态度放在一起比较,一个安贫乐道的「桃花仙人」形象跃然纸上,很多人对这首歌中咏唱的安乐清闲的气象非常欣赏,也很认可这种「志在高洁」的人生态度,这也正反映了唐寅的出世与入世观念。事实上,唐寅终生都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摇摆,一方面希望登堂入室为官宦,一方面又想及时行乐做神仙,于是有了唐寅的富贵梦和清贫乐。
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寅的一幅《桐阴清梦图》,画面中桐花荫下闭目养神的名士派头跃然纸上,给人一种清闲惬意的养生之感。此画构图简洁,用简笔勾画了一幅风格洒脱、韵致秀逸的画面,是唐寅白描人物画中的精品。此图题画诗中说:「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试醉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直白表露了自己绝心仕进、悠然林下的心态。
唐寅晚年又有一首《梦》诗: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
人们津津乐道桃花庵里种桃树的那个桃花仙人,殊不知此君亦是「桐花荫下南柯梦」的梦中人,只是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梦,是不是富贵梦,也只有唐寅自己知道了。南京博物院藏有唐寅的一幅仕女画代表作《李端端图》,描写了唐代扬州名妓李端端和诗人崔涯之间的春闺秘事,画中的人物几可认为就是唐寅自己风流韵事的一个写照。此画里的题画诗说:「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此诗正好言明唐寅自身处境——看似香艳风流,实则潦倒穷酸。一边是富贵梦,一边是清贫叹,这种心态在唐寅晚年的创作中尤其明显。唐寅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在富贵梦与清贫乐间摇摆,任人截取,一方面说明唐寅的想法是多样复杂的,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唐寅的认识是复杂多样的。
逃禅仙吏:「三笑」和「二裸」
孝宗一朝的朝堂政治较之明代其他时段还算较为清明,但是不知官场险恶、不谙人事,又意气风发的唐寅却偏偏不知不觉陷入了「科场舞弊案」的麻烦纠纷中吃了大亏,被罢黜了功名,打发到浙藩做小吏,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唐寅有一方印镌刻有「逃禅仙吏」四字,这里这个「吏」字就隐含着他失去功名贬为小吏的伤心往事,可见他对弘治年间科场舞弊案是在意的,既难以释怀又噤若寒蝉。这里的「仙」字说明唐寅的思想里有一些道教出世的成分,有些求仙问道的气味,这与唐寅的身世、自身的性格气质、人生的际遇有很大干系,其名山大川的冶游经历更是加强了这样一种倾向。
唐寅祖上有武职的功名(据唐伯虎的族亲后代、清人唐仲冕《六如居士全集序》记载,其始祖唐辉为前凉陵江将军),这一点从他自号「晋昌唐寅」、「鲁国唐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颇以祖上的这份功勋为念,身上多有「豪侠之气」,他的生死交徐祯卿在《唐生将卜筑桃花坞,谋家无赀,贻书见让,寄此解嘲》一诗中说:「唐伯虎,真侠客。十年与尔青云交,倾心置腹无所惜。」唐寅本人也颇以自身这种「英雄气」自得,他作《侠客》诗说:「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座,郭解始横行。相将李都尉,一夜出平城。」除了这种「仗剑济人」的豪侠气,他身上还有非常浓重的「狂」的性质,这从早年他与好友狂生张灵的交往中可见一斑。
明人阎秀卿撰写《吴郡二科志》,分「文苑」、「狂简」二科辑录吴郡文人故事,将唐寅故事收入「文苑」,张灵故事收入「狂简」,明人王世贞评论唐、张二人说「张才大不及唐,而放诞过之」。时人皆视张灵为一轻狂恣意之人,唐寅与张灵却是意气相投,最相友善,二人的最大共性就在于「狂性」。
阅读链接
唐伯虎与张灵的交往逸事
—
◎ 张灵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张方坐豆棚下,举杯自酬,目不少顾。其人含怒去,复过唐伯虎,道张所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讥我。”
——(明)曹臣《舌华录》“冷语第六”
唐寅身上这种「豪侠气」和「狂性」与汲汲于功名的仕途举业又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不能为中规中矩、方正保守的名教中人所接纳,因此也注定了唐寅的仕途之路会充满艰辛,虽然他的才华让他在科举之路上先声夺人、先行一步。
诗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里有一句夸赞诗仙李白无拘无束、风流自在:「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把一个恃才放旷、狂傲单纯的「谪仙人」形象说明得淋漓尽致,无独有偶,这种不受拘束的狂放性格唐寅身上也有,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唐寅学李白痛饮泥醉,模仿李白的《将进酒》写了《进酒歌》、《把酒问月歌》、《花下酌酒歌》等名篇,他在《把酒问月歌》中说写到:「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其比肩诗仙李白的狂放心态可见一斑。其实以唐寅之才他是可以「登天子船」的,他差一点就做到了,也差一点因此身陷囹圄丢了性命。如果说唐寅是一心求仙问道无心功名所以「不登天子船」,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是有心仕进的,只是身陷科场官司难「登天子船」,却误打误撞上了宁王朱宸濠谋逆的「贼船」(幸亏退步抽身早,全了名节),这里再看唐寅的所谓「仙吏」一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处顺便还想说说唐寅的「二裸」事情。每每言及唐寅,人们很容易想到「三笑」、「九美」的故事,却恰恰回避了「二裸」之事。事实上,「三笑」、「九美」皆为唐寅死后好事者的牵强附会,倒是「二裸」是发生在唐寅身上的真实经历。
唐寅的第一次「裸身事件」发生在他的青年时期,明人黄鲁曾在《吴中故实记》中记载披露此事:唐寅与吴中狂生张灵交好,二人有一日曾赤身裸体立于苏州府学泮池中用手激水嬉戏,谓之「打水战」,其旁若无人、狂放非礼之状令人侧目,此乃唐寅苏州府学之「一裸」。
唐寅的第二次「裸身事件」发生在他的中年时期,明人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卷十五里写到:
宸濠甚爱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余,见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差人来馈物,则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
此外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徐咸《西园杂记》、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清人张潮《虞初新志》这些笔记稗谈中均有此类叙述,只是在一些文字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情况大抵如此。唐寅被宁王朱宸濠重金延请到江西南昌做幕宾,由于唐寅察觉宁王图谋造反,故而做出种种疯狂举动以求脱身自保,是为唐寅南昌宁藩之「二裸」。
魏晋时期的文人阮籍、刘伶等人也曾「裸」过,一脱成名被视为风流名士,唐寅的「二裸」却和风流完全沾不上边,少年时期在苏州府学的「一裸」算是少不更事、贪玩胡闹不拘小节之举,中年时期在南昌宁藩的「二裸」则是假装疯癫、避祸求生的无奈之举,差一点「失去大节」。从这两次「裸身事件」去看唐寅的出世与入世不禁莞尔——经世济民的入世之人断不会于少年上进之时在府学行裸体水战之事,仙风道骨的出世之人也绝不会在人之初老的中年之际在藩王幕府裸体自丑。江兆申先生在他的唐寅研究中有「全大节」之说,基本上是充满同情、理解的爱才之论,「不拘小节、保全大节」也是对唐寅出世观与入世观的一个中肯注解。
唐才子的桃源天台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人多有心系桃源的山林之志。自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来,历代文人墨客的桃源山林之作非常多,直抒寄情山水的胸臆,表达超凡脱俗的志气,谋求个人高尚人格,此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充满天趣、真意的性灵之作,也不乏附庸风雅的无病呻吟,但「好天然」、「尚真趣」的「桃源之作」成了屡见不鲜的人气主题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具体到绘画方面,山水画反复加强了前述这一倾向,「桃源图」成了传统山水画中的一个大宗。
山水画中有天然真趣的作品很多,从画的部类而言,此种天然真趣进入文人画与士大夫文人的「书卷气」相糅合便有了诸多文质彬彬的秀润之作。此种天然真趣与和尚禅僧的「禅机」相糅合便出现一些充满生机与真性的禅画,有如「桃源春水」一般。唐寅所处吴郡文物阜盛、人物风流,吴门画派的人笔下少不了寄情山水的「桃源之作」,身为「吴门画派」领军人物的唐寅自是不在话下。事实上,「吴门画派」的人大多画过「桃源图」一类的风景山水,比如唐寅的老师周臣。唐寅早年学周臣,最终超越了周臣,在于唐寅的画法不步人后尘,不拘于一格,更在于唐寅的「书卷气」,也就是他的才华。周臣曾画过一幅《春山游骑图》,从此画的布局、皴法来看,周臣的画法偏于宋人路数,画中远山、林木、流水、小桥、山中人物俱为「桃源图」的格套标志,这类景致在唐寅的山水画中也很常见,是画的泛滥了的东西,但是周、唐二人的画格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唐寅师从于周却反有「青蓝之誉」?面对时人的这一诘问,周臣自己的回答极其中肯:「但少唐生三千卷书耳。」唐寅作画不仅仅停留在画法技巧,更在于他的文采风流,在于他崇尚天趣的文人胸臆。
「吴门画派」中的仇英也是画过「桃源图」的,他的桃源之作尺幅巨大、篇幅恢弘,精细描摹,令人有耳目为之一新、面貌为之一振的感觉,通过细节的精细描绘再现了群山林立中「桃花林」的神秘浪漫。仇英不是文人而是一个画工,不像唐寅那样画里画外有那么多故事,也没有像唐寅那样壮游各地山水,他就是一个关在画室里看画、学画、作画,一辈子以画为业的人,卖画谋生这一点上倒是与唐寅一样。仇英的经历与见识较之唐寅少了很多,他就是勤奋、用心地画。仇英的画上一般不题诗,更谈不上用题画诗来表达画的主旨境界、与同道相互唱和,通过各种钤印题款来表明心志态度,这一点仇英做不到,但这恰恰是唐寅的拿手好戏,其缘故仍是唐寅作为文人的「书卷气」,当然经历与游历的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有趣的是,唐、仇二人皆为周臣的学生,同列「明四家」之一,两人却是不同的画格。正如老话所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周臣、唐寅、仇英他们是「一师二徒三个样」。
再和文徵明相比较,唐寅与文徵明相识甚早,为通家之好,唐、文二人过从甚密,甚至因性格差异一度不相往来,后来二人又重修旧好。文徵明的山水画中也有「桃源山林」的题材,比如现藏南京博物院的《万壑争流图》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木寒泉图》。两幅画均为设色立轴,画面信息丰富,充满了山峦、林木、流水等素材,一眼观之从画面布局、景物比例、尺幅设色、皴法等角度来看文徵明的师从来源也是很复杂的,取法多家,画法很熟练,对画笔有很强的把握力。这两幅画都是画面满铺风景素材,仅在尺幅顶端留出少许空白,画面「立地不顶天」,题画诗用小字悬于上首,显出非常节制的样子,毫不夸张。这与文徵明的性格有紧密联系,文徵明其人遵守法度不逾矩,心态平和自律性很强,做事情极为认真,这些性格特点都反映在了他的画作上——不偏不倚,中规中矩,温润谦和,显示出经营和维持的功夫。这一点唐寅与之截然相反,唐寅的题画诗更加汪洋恣肆、狂放潇洒。观画如观人,从画面上乍看上去,文之中正节制与唐之恣意潇洒一目了然。这里征引唐寅忘年交、文徵明之父文林的一句话作为佐证抄录于下,画格与人品之关系略见一斑:
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
以上将唐寅师友同门的情况简单做了一个梳理并与唐寅作了比较,专论唐寅的画是很需要花一番功夫的,这里仅从唐寅的背景经历和性格来简单谈了一下。除了以上提到的「书卷气」、狂放个性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唐寅山川游历的经历。祝枝山在《唐子畏墓志铭》中说唐寅「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足迹遍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山清水秀之处的风云际会都滋养了唐寅的书画修养,成为他血肉化的一部分。于是「胸中大丘壑」、「腹内三千卷书」,加上狂放恣意的性格成就了唐寅这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笔下的「桃源天台」也就格外与众不同。他在《姑苏八咏》之四《桃花坞》一诗中说「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吐露了自己的桃源之念、山林之志。唐寅又在苏州城外桃花坞中筑起桃花庵,过起桃花树下诗书画的生活,他曾在杂曲《大圣乐》中说「想天台缘未泯」,借以感怀自己的「桃源之念」,这些文字都很好地说明了唐寅的出世与入世观念。
关于唐寅的讨论很多,有一类做法是将唐寅临终之际的绝笔诗与明代另一位名人王阳明的遗言相比,从性质上来说明阳明先生的光明气象。王阳明亦是坐过牢、流放过、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的人,也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阳明的心法为无数后来人所激赏,他在辞世之前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唐寅的绝笔是「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王阳明的话有大气魄,唐寅的话则显得郁郁寡欢、压抑低徊。这里我想引用唐寅在《漫兴一律·龙头诗》里「镜里自看成大笑,一番傀儡下场人」一句对唐寅的绝笔诗作一注解。唐寅有庙堂之念、惊世之才、山林之好,他既是入世却不得志、极不顺利的,也是出世但无法尽兴、得遂心愿的。我们讨论唐寅的书画艺术,讨论其思想中入世和出世的观念,他的绝笔诗与《龙头诗》给了一个很直观的回答。唐寅大抵自己心里也明白,较之「龙虎榜中名第一」、「南京解元」、「吴趋浪子」、「桃花庵主」、「逃禅仙吏」、「六如居士」等自况之语,自己不折不扣是个「傀儡下场人」。「一番傀儡下场人」虽系自嘲,应该是唐寅对自己最为客观真实的一个自我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