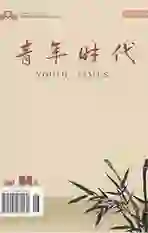从历史语境下解读“亲亲相隐”
2019-06-25张杰潘心颖
张杰 潘心颖
摘 要:“父子相隐”的论述最早提及了“亲亲相隐”的思想。《论语·子路》篇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于在现代政治、社会、文化中成长的现代人来说,合理地理解 “亲亲相隐”的内涵并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亲亲相隐”、“证”、“攘”、“直”等相关语词的含义与现代通行意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对理解孔孟言论至关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也与现代社会所对应的迥然不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采用通过“直躬证父”的语境还原,依托于孔子与叶公当时对话的语境分析孔子提出“直在其中”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孔子是否真的认同“亲亲相隐”,从而对亲亲相隐进行新的解读。
关键词:亲亲相隐;直;隐;叶公
一、文本释义
(一)对话地点
孔子与叶公关于“直躬证父”的这一段对话发生在鲁国受挫,孔子为了实现理想抱负,选择同诸学生们一起离开“父母之邦”去其他列国推崇自己主张,游说君主施行仁政。《史记·孔子世家》:“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秋,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入叶。①”这段话具体交代了孔子入叶的行程安排。孔子携弟子与叶公见面,学术界对孔子自蔡入叶的起点和终点各执己见,是蔡国管辖的“蔡”还是楚国的负函之“蔡”?《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斥江入郢,将奔命焉。②”根据考证,负函之蔡的史料起源就记载在《左传》上。为了达到称霸中原的目的,楚国实施实边政策。此时,蔡虽已迁至州来,楚国高官把不愿意搬去州来,死抱着蔡国不放的那些人都迁至负函,此即负函之蔡。江永谓:“孔子自陈如蔡就叶公耳,与蔡国无涉。③”前贤所论甚是,孔子去陈适蔡即为负函之蔡。
(二)“直躬”之义
“万氏《困学纪闻》集证:淮南子氾论训‘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④”高诱注“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之。”,将“直躬”解释为楚国的叶县人,认为躬其实是他的名字,因为平日以“直”的性格特征闻名于乡党,所以称之为“直躬”。高诱以为, “直”相当于“狂”、“盗”, 是指人物品行,“直躬”之名类似狂接舆、盗跖;“躬”相当于“接舆”、“跖”等,是人物名字。
(三)“攘”之义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攘进行了解读: “攘,盗也。”这里的“攘”有趁火打劫的的含义,是偷盗的意思。从现有的《论语》注释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攘”的注释是“偷”或“窃”或“盗”。王力在其《古代汉语》中则指出:“攘,本指扣留自己跑来的家禽牲畜,和‘偷有些不同。”笔者同意王力的看法,郭璞注释认为“皆因缘也。《费誓》曰:‘无敢寇攘。郑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儴、攘音义同”。在《论语集释》中的集注“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盗曰攘。⑤”“有因而盗”也属于“盗”的一种,其中所隐含的“小利”与“大义”的问题、“道德”与“法律”的争论、“公”与“私”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容置疑的。
(四)直之义
《群经平议》:“躬是其人之名,直非其人之姓也。⑥” 群经平议记载说,此人的名是躬,但姓不是直。在孔子和叶公的对话中,我们也可发现,对于叶公提及的“吾党有直躬者”,孔子的回答是“吾党之直”,这足够表明在孔子看来“直”与人名并无关联,且孔子对于“直”有着相异于叶公的解释。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指出:“‘直掩恶扬善的‘人道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实际上应该归类为人情,维稳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珍惜并重视这种人情,所以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乃是‘不求直而直在其中也。⑦”这句中的第一个“直”字,隐含着直躬证父之“直”的大义灭亲,但即便这样,钱先生仍指出隐而不发来维系亲情是“直在其中”。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亦指出:有些表面上的“直”,其实是“罔”。比如偷别人羊的父亲,显然是坏事。对于他儿子来说,真情实感的流露应该是不希望父亲的坏事流传出去,而不是主动报官,大义灭亲,这种大义灭亲实则是“罔”⑧。另外,《中国儒学精神》中亦把“直”解释为“正直”。针对于“直”的解读还有 “直行”、“直率”、“隐恶扬善的直道”以及“由中之谓,称心之谓”等。由此,可以判定“直”与一个人的姓无关,代表的是一个人德行的正直。张志强先生和郭齐勇先生持有这样的看法,“直在其中矣”的“直”指的是人的情感和亲情之直,而不是单一情感喷薄的“率真”“直率”。
其次,孔子提出“吾党之直”。春秋时期礼乐崩坏,孔子因鲁定公轻信诽语受冷落而离开鲁国,诽语产生的契机是鲁国堕三都失败,而齐国施计向鲁定公献媚。从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发现当时诸侯贵族斗争激烈,在鲁国不尊周公古制的现象已经出现了。依孔子之见,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该当延循周礼,施行礼乐文明。这里的“直”该当解释为孔子希望的鲁国甚至是华夏民族都该当遵循的“直”。
二、“子证父攘羊”
(一)叶公何人
《春秋大事表》记载:楚迁许于叶。王子胜曰:“叶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乃使迁许于叶,而更以叶封沈诸梁,号曰叶公。叶公子高即沈诸梁,字子高,楚左司马沈尹戌之子。据考证,沈氏出于楚国王室, 乃公子贞之孙、公孙戌之子。沈梁在春秋末年楚国政坛上很有名,自公元前524年任叶尹为大吏,至公元前476年盟于敖,政治活动的历史时间长达49年。据《叶县志》记载,叶公在叶执政期间,大兴富国强兵之策,政绩显赫。楚惠王十年,因平叛有功,被授予“令尹”和“大司马”的称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二)叶公之“直”
春秋末年,孔子选择为心中政治理想,实现自身抱负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求仕,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找工作,但却屡遭排挤和谗毁,有时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而当孔子离开陈国到楚国,途径叶地。叶公主动找到孔子,明面上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直”的道德问题,实则从叶公与孔子的对话得知,叶公在与孔子表现的是一种得意、自满的心情。我们从“叶公与孔子曰”能看出在此次对话中叶公首先开口并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叶公主动向孔子提起此事,其动机已初现端倪。其次,叶公不仅自发提及“直躬者”,而且认定他是“吾党”之人。叶公显然为能有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在他的统治下而倍感自豪。历代诸多儒家学者也都将此举视作叶公对孔子及其儒学思想的挑衅。笔者认为,当叶公把直躬的故事当作一则“社会新闻”讲述给孔子听,实则是在挑战孔子所推崇的孝道。子证父攘羊确实缺乏应有的孝,但表面上的不孝背后藏着的是行为的正义; 儿子因正义的行为而作为正义的人。因而被叶公称其“直”。叶公用一个司法案例来挑战孔子所提倡的孝道伦理,一方面完成了对儒家伦理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儒家伦理和法律在法律变革时代所起作用的质疑。
其次,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也是由于叶公轻信,缺乏定见的性格使然。叶公并非亲眼所见,仅仅是听取了“直躬者”单一的辩解,听过之后未加思索,便对“直躬者”有关“直”的的辩白表示赞赏,叶公如此武断的赞赏,其实与叶公缺少主见,易被旁人华美言辞左右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不禁会问:“子证父攘”就一定是“直躬者”吗? 你愿意当这样的直躬者吗?
(三)孔子提出“直在其中”之缘由
到底是“子证父攘”为直,还是“子为父隐”为直?我们重新审视孔子之言,孔子没有对“子证父攘”的直表示反对,只是说自己与叶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孔子也没有对“父子相隐 ”之直表示赞同,只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则“直在其中矣”。证父攘羊,事虽直,但违背天伦之理,其中有诈,实不可取。父子相隐,出于天然,事虽屈,而理至直,所以孔子说:“直在其中矣”。为此,孔子设想了另一种看似不“直”却“直在其中”的情境,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母儿女之间的串通一气和包庇隐瞒,怎么是“直在其中”呢?现代人对此往往不能理解,实际上,人们对于孔子的这种看法往往没有深入研究。朱熹《论语集注》抓住这一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出,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刘宗周在这一问题上阐述的更清楚:“直之理,无定形。……曰“直在其中”者、无直名,有直理也。⑨”以儒家之见,直躬的行为虽然称得上直,但这种直却只是“非直之直”---套用孟子“非礼之礼,非义之义⑩”的看法,也就是说,直躬的行为从表面上似乎是无懈可击的正直,但若是深究起来其实并不是如此,这就牵涉到了孔子对“直”的看法。
众所周知,孔子注重人的外在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但更重视道德的内在性。孔子在继承周礼的同时,突出了“仁”的重要性,主张把“仁”为“礼”的内在根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同样,孔子认为外在的“直行”必须有内在的“直感”为基础,才称得上真正的“直德”,因此,我们可以说直躬之直仅仅是一种外在行为的直,孔子之直则是一种内在情感之直。如前所述,“直”原指外在行为之直,孔子将内在情感因素注入其中,并且认为,在道德评价中内在情感应是主要依据。在“直躬证父”事件中,孔子对直躬之直表示怀疑,原因即在于直缺乏真情实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一味感情用事?
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提及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从深层次去看,是孔子对价值判断一般原则之一特殊肯定,即是‘价值在于具体理分之完成。即价值意识之具体化问题。”在孔子论“直躬证父攘羊”一例中,孔子之意以为,每一人在每一事中,有不同之责任及义务,不能以“证人之攘羊”为“直”,而应说,各依其理分,或证或隐,始得其直,由此可以解释父亲攘羊,举报不是儿子该做的,而隐瞒则是他该做的。总之,孔子论“直”,其本旨是说价值即具体理分之完成,故每一事之是否合理,须就具体理分决定。
其次,周孔教化下的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家族为核心。在聚族而居的时代,家的地位更加重要,在和亲属生活在一起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慰藉,此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显得更为重要,亲亲相隐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孔子提出“直在其中”不是在回答“直”是什么,而是把直置于怎样的一段关系中区理解。如果在一段关系中,因为行为“直”或“直”的人品而破坏了原本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直”也是错误的。反之,如果将“直”置于关系之中,而使这段关系得以稳固乃至加强的作用,那么这样的“直”才是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在“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这件事上,就“隐”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怎么也不能把“隐”理解成正面的意思,但因为“隐”的行为而维系了父子关系,所以“直在其中”。
(四)亲亲相隐新解
孔子之所以提出“父子相隐”,并不是认为父子相隐本身是根本的道德原则,而是认为父子相隐是面对“其父攘羊”时所作出的合理的道德选择。前文提及,叶公在提及直躬者满是自得之意,而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正是这是孔子对叶公的否定回答。笔者认为,孔子此举一开始就是在提醒叶公对他的“直”观进行比较和反思。孔子随后对“直”的具体解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的主旨及目的,也就是要提出另一种意义上的“直”,从而为叶公反思和纠正他的“直”观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应当说,“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向外告发父母的道德过失,不合情合理,因而无正直可言。而“父子相隐”,对于父母的道德过失,不仅应不宣扬,而应进行尽力劝谏,合情合理,虽然不为直,“本非直”,但“直在其中”,不求而自至,包含了正直。当然,由于父子相隐,不只是不向外告发,而且还包括对父母进行劝谏的复杂过程,是否一定能够由“直在其中”而达到正直,如何才能达到正直,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在回归文本注解中,我们能发现后世的众多《论语》注本中,关于此章的断句几乎都是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中间断句,加一个逗号,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且在各注释译本中,“为”字都作介词,读作wei(去声),解释为“替、给”。朱熹《论语集注》:“为,去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耶?”但是,当我们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语境,重新解读“亲亲相隐”。笔者认为,孔子在回答叶公时,可不可以断句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句中的“为”字作动词,读作wei(阳平),解释为“做、干”之义。也就是:父亲犯错,儿子隐默;儿子犯错,父亲隐默。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断句解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其一:回归到当时的语境下,叶公只是提及直躬之父攘羊直躬证之,如果按照对话的逻辑顺序,孔子也应先回答“直躬证父”这一案列,即“父为,子隐”。如果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正确顺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父为子隐”是孔子针对叶公提出的哪一语言成分而作出的回答呢?因叶公赞赏“直躬证父”之直,所以孔子毫不相让的指出“吾党之直异于是”。并且孔子不但提出“父为,子隐”,而且要“子为,父隐”。孔子主张的是双向容隐,父慈子孝的思想,既有“子孝”,又有“父慈”,这种关系是父子之间的双向对应。其二:为,读作wei(阳平),做“干、做”的意思时,解释为“父亲犯错,做儿子的不宣传,儿子犯错,做父亲的不宣传”,这里重要的是为了亲属把自己隐,而不是为了亲属把亲属“隐”。隐在这里做“隐默”解释,即“知而不言、沉默、不宣扬”,而非窝藏、包庇之义。其三:“亲亲相隐”有其界限,即只限于家庭成员的所作所为没有逾越社会公认的法律规范、原则;其四:“亲亲相隐”仅是不对外人或官府宣扬或告发亲人的过失,但“隐”亦要求家庭成员之间以公义来相互教育、帮助、规范、批评。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1927页-1928页.
②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302页.
③江永著.乡党图考.[MJ.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④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七(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289-290页.
⑤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七(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
⑥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七(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290页.
⑦钱穆.论语新解[M].成都:巴蜀书社,1985.第320页.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82页.
⑨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⑩《孟子·离娄下》
《论语·八佾》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96页.
[宋]朱熹论语集注[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11),第115页.
参考文献:
[1]《论语·八佾》.
[2]《孟子·离娄下》.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七(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钱穆.论语新解 [M].成都:巴蜀书社,1985.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9]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宋]朱熹.论语集注[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