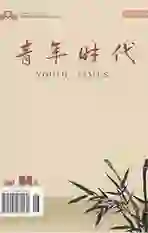《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翻译“忠实性”问题探索
2019-06-25杜柳
杜柳
摘 要:《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金译本和葛译本对“忠实性”问题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背后潜藏着中国对“译出”翻译策略的固化思维模式。本文拟从这一矛盾聚集点出发,以接受语境为导向,重新评价金译本和葛译本对忠实性的处理。
关键词:《骆驼祥子》;翻译;忠实性
在《骆驼祥子》出版以来的80年间一共出现过四个主要英译本,其中1945年伊文·金译本和2010年葛浩文译本都是由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翻译,也都在美国出版发行。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译本在美国都颇受好评,在中国却遭遇批评与褒扬两种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问题主要出在对翻译忠实性的考量上——葛译本基本忠实于原文而金译本改编甚至重写了原文内容。两个译本均参照老舍连载于《宇宙风》的初版本,从译者身份到受众群体,再到“为读者而译”的翻译策略都呈现出跨时代的一致性,这让笔者不得不考察造成两个译本截然相反的评价的根源——忠实性问题,何以在中国受到如此重视?
一、“忠实性”的历史渊源
1898年严复为其翻译的《天演论》一书书写的序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原本是抒发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感悟的却成为后世翻译的金科玉律。继严复的“信达雅”说之后,影响较大的有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认为翻译“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在他心中“理想的译文放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这一提法对后世的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影响极大,甚至成为翻译学的金科玉律。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始终对金译本改译甚至重写的现象耿耿于怀。
对此,谢天振认为这些研究多数属于研究者们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和体会出的,“带有较明显的经验主义性质或色彩”,并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这些研究都是围绕着译入翻译活动展开的”。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让外来作品在本国实现更好的理解与接受,而我们却常常拿“译入”时的翻译原则与习惯来检阅中国文学“译出”研究,这实际上是不恰当的。谢天振注意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一种特殊现象或者事实——“时间差”。所谓时间差,就是中国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时长和接受程度要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接受。中国自晚晴到现在对西方的认识、了解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需求度与接受度都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而西方对中国的全面了解才短短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并且中国文学在西方图书市场占有率极低,仅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翻译出版物仅仅占美国总体出版物总数的3%,而在这3%的翻译出版物中,来自中国文学的作品数量更是微乎其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的普通读者,其接受水平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时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
鉴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今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大多都会删节或改写,1945年伊文·金对《骆驼祥子》的改写就更不足为奇了。在西方对中国文学接受度和理解力较低的事实下,我们是否应该对不得不为之的“改译”现象更宽容一些呢?把眼光更多的放在接受与传播上。
接受与传播的重要性在当今“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时代热潮下显得尤为紧迫。对于深受语言因素制约的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翻译必然成为其中绕不开的核心和焦点。关于译者模式,学界“基本都认同汉学家译者模式或者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这就好比我们在进行“译入”工作时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人来翻译外国作品,对于中国本土读者独特的审美偏好、细微的用语差别,只有中国译者最为了解,并能恰如其分地选择词汇、排列句段以迎合读者的口味,取得良好的接受,对应到“译出”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对于中国文学外译工作应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目前学界尚没有达成共识,还处于探索阶段。不过,我们可以从成功的中国文学“译出”案例中得到一些启发,比如1945年金译《骆驼祥子》在美国的大获成功。
二、金译本和葛译本翻译策略的处理
伊文·金在没有与老舍商议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了一些增删、改写。1945年伊文·金译《骆驼祥子》出版之后“成为美国《每月佳作俱乐部》的选书,这和民众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和译笔本身的质量有关(老舍也赞赏过其“译笔不错”),但笔者认为正是伊文·金对原作的增删和改写才使得金译本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而长久的传播,就像林纾的翻译,正是林译中的这部分“讹”才起了抗腐作用,使得林译“免于全部淘汰”。
金译本删减部分主要集中在小说开头关于北平洋车夫分类的描述上。改写部分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对小说结尾的改编。
原文: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陌路鬼!(老舍,2008:215)
金译本: In the mild coolness of summer evening the burden in his arms stirred slightly, nestling closer to his body as he ran. She was alive. He was alive. They were free.(King,1945:384)
原文里当祥子终于下定决心迎娶小福子时,却得到小福子自杀的噩耗,从此祥子彻底走向了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陌路鬼”。伊文·金将这一悲剧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小福子没有死,祥子也没有走向堕落,祥子从白房子里救出小福子后,两人重新获得自由,幸福地走到了一起。译者为什么要如此处理呢?被奉为西方中国文学领域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曾在一次访谈中透露:“英美读者习惯先看小说的第一页,来决定这个小说是否值得买回家读下去……国外的编辑认为小说需要好的开篇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从题材来看,美国读者最喜欢的小说,“一种是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政治多一点的……”。而在小说结尾上,英美读者普遍爱看大团圆结局。如此,直接进入正题的小说开头、好莱坞式的英雄抱得美人歸的结局和中间适度的性描写无疑为金译本增加了进驻美国市场的诸多胜算。在美国对中国几乎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走向成功的“美国梦”里,怎么会轻易接受一部宣扬个人主义失败的案例的中国作品呢?应该说,伊文·金的改写并非有意所为,而是在特定时代语境下采取的特定翻译策略。伊文·金采取的无疑是面向目标语语境的翻译策略。
有人不禁要问,倘若我们中国走出去的是某种程度上被误读、误解的文学和文化,那么走出去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忽视了翻译的直接目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西翻译研究开始注重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并把翻译看做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我们在慨叹译者的辛苦劳作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的同时,不禁要问忠实性原则究竟适不适应当下的中国文学译出工作?如果不适应,增删、改译是否就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涉及到对“忠实性”内涵的理解。
三、“忠实”的丰富内涵与动态过程
如果按照批评界批评金译本的逻辑,认为其增删、改写是对原文的背叛,是不忠实的,那么葛译本岂不是也要背负不忠的罪名?葛浩文把“先斩后奏”翻译成“先上车后买票”,并没有翻译出这一成语的全部内涵,只翻译出它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男女有了孩子还没有结婚。翻译对原作的“忠实”指的是文字忠实、意义忠实、审美忠实还是其他忠实呢?忠实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的忠实,还体现在意义忠实、审美忠实和效果忠实,增删、改译的翻译模式也并非与忠实绝对的对立。
很多时候,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是目標语读者的口味与期待。目前,西方翻译中国作品时多存在删节、改译的现象,具体操作时常采用归化法,这种翻译策略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目标市场的要求,并且这种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西方对中国文化需求的增加,译者在处理原文时会考虑保留更多的中国元素。葛浩文近年来的翻译就体现出这一趋势。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美国开始渐渐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葛浩文近几年的译作《青衣》、《玉米》和《骆驼祥子》几乎对原文没有删节和改译,《青衣》的封面是一个中国京剧脸谱,以中国元素来吸引美国读者。随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度,伊文·金式的增删、改译的方法也将像林纾的翻译那样被历史淘汰。
四、结语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展开了激烈讨论,笔者认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要区分中国的“译出”与“译出”的不同翻译策略,其中关系到对忠实性问题的客观评价,而对忠实性问题的客观评价则是实施正确翻译策略的前提。
参考文献:
[1]谢天振. 隐身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刘云虹.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 [J]. 外国语. 2014(5).
[3]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 2014(1).
[4]孙会军.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5]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载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6]王德威.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矛盾,老舍,沈从文[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